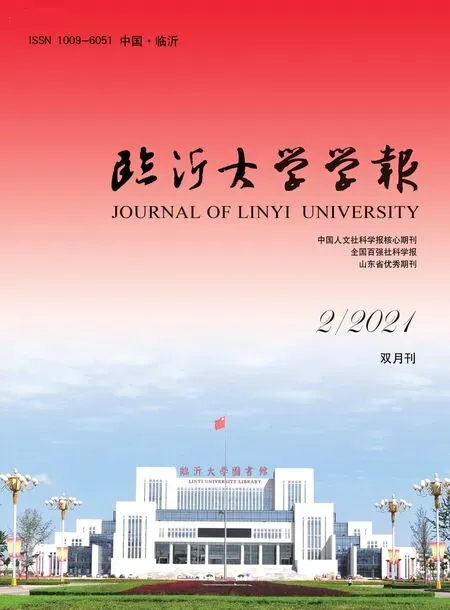美国大学学术创业的组织保障研究
杨 婷
(合肥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在美国,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使命,追求经济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合法目的,其可追溯至1980 年《拜杜法案》。[1]美国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转变。大学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实体供给者,如软硬件购买者、劳动力雇佣者、地产开发者、纳税者等,更是成为促进学术创业的策源地。 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本身就充当一个创业孵化器的角色,允许学生和教师们会面、组成团队。[2]然而,即使大学具有创新创业的内在基因,在缺乏大学创业服务组织的支撑下,大学师生也难以将知识进行创新应用。
美国大学为了跨越学术创业的心理边界,打通学术创业的物理壁垒,积极与社会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进行交互与融合,在协同合作中发展了三类主要的创业服务组织。包括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如创业学系、创业中心、创业学院等;以产业合作交流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如产业合作研究中心、产业联络办公室等;以创业孵化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如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TTO)、孵化器、加速器、概念证明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研究园、联合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创客空间等。 这三类不同的组织虽然都有各自的侧重方向,但它们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重叠功能,如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也具有创业孵化的功能,尤其创业中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被划归为创业孵化机构;创业教育在创业孵化机构、产业合作机构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产业参与的广泛度也不仅限于产业合作机构,其他两类机构中都会有不同产业的协助。整体而言,这三类组织不仅在某些具体的创业项目上存在合作关系,而且它们富有张力地存在于大学相对开放与适度封闭的过滤地带,不仅使校内师生各取所需,实现共赢,而且也形成了推进大学学术创业的强大合力。
一、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
美国不少大学在正式的组织架构中,创造性地利用现有资源,抓住创新变革机会以实现创业的合法性与强调创业的重要性。学校通常在领导层面指定负责研究的副校长承担学校创业事务,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直接委任创新创业副校长,如堪萨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 美国大学内部还专门设立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主要体现为创业学系、创业中心、创业学院。 这对于营造校园创业文化、提升师生对创业的接受度具有基础性的奠基与引导作用。
在创业学系方面,美国不少学校在商学院、管理学院或其他学院创建一个专门致力于创新和创业的学系。 这类创业学系享有与其他学系相同的权利,包括雇员招聘、课程教学、学位项目、学生管理等,以作为正式开展创业教学与活动的一种方式,并为这一领域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学术之家”,如哈佛大学创业管理系、雪城大学创业与创业企业系。 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决定直接在与创业具有紧密关系的学系中加入创业维度,如管理系改为管理与创业系。印第安纳大学、贝勒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科罗拉多大学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将创业升级为主导性的学科。 这在塑造本学系创业文化的同时也会吸引那些对跨学科感兴趣的创业教师。
在创业中心方面,这是美国大学促进校内创业教育发展最常见最有效的组织形式。 虽然中心通常设在商学院,但也可以在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和其他学院设立,也可以直接作为校内独立的单位,有时甚至直接向校领导报告。中心既有具备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创业捐赠席位、终身教职教师,也有具备创办企业经验或拥有特定行业领域专业特长的教师(包括全职和兼职)。中心的运营资金主要通过各种途径的捐赠获得,如许多中心是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也不乏有些学校先初步设立一个中心,然后以冠名权的方式吸引捐赠者入资。创业中心服务范围广泛,包括创业学分课程、孵化器、奖励计划、商业计划竞赛、培训、咨询、项目指导、促进获得资金和协助制定商业计划等。除了这些职能以外,某些创业中心还会负责本校的创业教育报告或创业报告,以及从事创业相关的学术研究。
在创业学院方面,其理念是创造一个创业之家,充分开展创业学术研究与创业培训、鼓励全校任何学科的师生参与创业、实施全校范围内创业项目、活动交流与合作。这种模式资源投入比较大,也是从创业项目发展到学系再到学院的一个进化过程。 美国已有大学开始实践创业学院这种模式,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圣托马斯大学、布拉德利大学等。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是率先实践这种模式的主要大学之一。该校的创业学院坐落在斯皮尔斯商学院内,由学校校友捐赠成立,建立的目标是为对创业感兴趣的任何学科领域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一个家并协助师生创业。学院主要包括创意机构、创业教师、跨学科创业项目、技术创业项目、里亚塔创业中心,同时具有内外部两个咨询委员会。学院共有近20 名教职员工。学院设置本科主修与辅修专业、研究生创业证书、MBA 集中课程、硕士/博士创业学位项目等,提供50 门课程,并通过孵化器、工作室(创客空间)、俱乐部等机构提供课程、研讨会、学习社区等。[3]创业课程与创业项目的重点是发展学生创业思维,帮助所有的学生学会如何以更具创业者精神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以及了解创业过程,提高创业能力。
二、以产业合作交流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大型企业开发了不同的研发组织模型和人力资源战略,并将经过学术培训的科学家融入创新过程。 其中网络组织模式是产业研发结构转型中最新的主导模式。 从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技术S 推动”模式演变为20 世纪70年代至80 年代后期的“市场拉动”模式,以及当今新兴的“网络”模式,这三个模式反映了企业内部“科学”与“商业”之间以及产业研发与学术界之间关系的变化。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也与这些不同的研发模式共同发展。 在第一个模式中,以大型企业为主要生产力的产业界通常以垄断、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占据市场,大学与产业界是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的线性关系,产业实验室以聘用大学科学家的方式作为主要的联系机制。 20 世纪80 年代,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许多企业分散研发以加速产品创新,并通过更多的外包商追求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战略。在90 年代早期,科学和技术革命促进产业界加大外部研发合作,技术研发的加速空间使得企业内部实验室竞争力削弱,另外企业研发的缩小使公司内部研发人员产生了职业不安全感,存在吸引和留住必要的核心科学人员的潜在困难。[4]许多研发密集型大型企业采用的解决方案是转向网络模型,并跨越组织边界融入科学家网络来增强其内部知识库。 这模糊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和开发工作之间的界限,削弱了科学与技术学科之间的传统障碍。特别是在基础科学成为创新和形成经济优势的关键来源领域,许多大型企业与研究型大学开展合作。
产业与学术界的交互并不是新现象,而当前美国将学术创业活动与产业界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向研发网络模式的转变涉及产业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即从单向知识流的旧线性模型发展到两个部门之间的双向知识交换的互动模型。这种关系通常由广泛的链接机制维持,包括研究合作(基础设施与研究工具的共享、共同出版、共同申请专利等),对学生的联合培养(课程开发合作、学生实习项目、硕博联合培养等),人员流动(学生雇佣、教师学术休假时期的产业界实践、产业人员授课等),商业合作(合同咨询、大学专利许可、共创公司等)。 产业界与高校的互动可能性非常广,几乎只要涉及与创业创新相关的活动都会免不了产业界的参与,尤其产业界中的个体与大学师生之间的接触。 如图1所示,师生与产业界的关系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具有互动与协作的本质特征,双方承认彼此的相互作用并实现互惠互利。
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发生在具有流动性、可渗透性的重叠空间中,超越了大学原有的学科组织边界。以科研项目为例,科研项目具有固有的长期性质,并且需要来自不同学科和职业群体的投入,因此职业和组织归属就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家们在参与此类合作时也必须与自己的知识网络保持联系。他们不是在售卖知识,而是为企业提供持续性的、快速更新的知识。在科学研发合作项目中,跨边界组织的存在尤其重要,因为大多数科学合作都不是一次性的。 如果成功,他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 一般情况下,美国大学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办公室、产业合作中心、研究中心等跨边界组织为师生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与服务。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确保教师和学生意识到现实世界的条件和需求,将师生研究兴趣与市场的长期需求相匹配,内部对师生的研究问题敏感,在外部则对市场的需要做出响应,并成为产业界获取研究信息、了解参与教师情况以及雇佣优秀学生的重要渠道,同时随着需求的变化和新的利益的出现,伙伴关系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具体到合作伙伴的选择,大学往往需要在与产业界合作前对合作伙伴进行评估,包括是否能够相互理解,是否具有包容性文化、互补能力、合作经验、称职员工、清晰规划,是否有过合作历史。 在具体的合作中二者需要考虑的步骤包括确定共同的目标与各自的责任; 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制定项目规划;确定大学与产业界内部能够充分理解项目规划;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保证大学与产业界的频繁互动;建立持续交流机制,即使一个项目已经完成。 在合作的成果上,二者应同时关注无形产出与有形产出。有形产出包括出版、技术发明、共同专利、共创公司等,无形产出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人员知识资本提高等。[5]
在知识驱动经济的社会中,美国公共政策也极力提倡学术界与商业界的紧密合作。 截至1990 年,美国有超过一千所大学产业研发中心,其中大部分(60%)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6]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产业界—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I/UCRC) 项目在20 世纪80 年代得到了充分的授权和扩展,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ERCs)计划在1984 年正式开始筹建。 这些中心在美国政府的发起与支持下,建立起高校内部不同学科的进一步交叉机制、密切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在整体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加速技术研发与创新,推动产业化进程。 通过跨边界组织,美国产业界与大学发展出多种具体的合作模式,多大学/多公司合作模式、单一大学与多家公司共同合作模式、单一大学与不同公司的单独合作模式、多大学与同一家公司的合作模式。[7]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培养教师与学生专业知识为重点的大学—产业界合作中,很多学院可能直接与产业界进行联系,而不是通过跨边界组织。
a.多大学/多公司合作模式(多对多)。美国有许多研究中心涉及多所大学和多个行业合作伙伴。 如先进制造研究中心(The Commonwealth Center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涉及的大学包括欧道明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涉及的行业伙伴有十几家,中心设在弗吉尼亚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有时候会有政府的参与,如很多产业界—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基本上就是当地产业、大学、联邦政府、当地政府合作的成果。
b.单一大学与多家公司共同合作模式(一对多)。 美国一些大学单独建立了与多个企业合作的研究实验室,但不需要在大学之间进行协调。 如威斯康星大学电机与电子研究中心(Wisconsin Electric Machines and Power Electronics Consortium),合作对象超过80 家企业。
c.单一大学与不同公司的单独合作模式(一对一)。 许多大学都有大量的企业合作伙伴,并与他们合作。但是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经常是一对一的具体项目的合作,如罗斯—霍曼理工学院与谷歌合作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凯特林大学与通用汽车研究所合作的学生带薪实习项目(co-op program)。
d.多大学与同一家公司的合作模式(多对一)。 很多情况下,同一家公司会与多所大学分别合作同一项目或者开发不同的目标相异的项目。 如波音公司的教师发展项目(A.D.Welliver program)可以服务多所不同的大学。
以上四类不同的合作模式虽然涉及的单位数量不一样,但在某一特定的大学中,不排除会同时出现以上四种合作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主要根据学校资源、合作目标、项目内容、合作方式等进行调整。 如学校可能以更系统和战略性的方式与少数关键企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主要目标是集中注意力并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几家最有可能获得互补性能力与包容性理解的企业。[7]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不仅仅是技术产生方与技术接受方的关系,也会存在倒过来的现象,如阿克伦大学和蒂姆肯公司之间的合作成为大学—产业合作的一种新模式,在该模式中,阿克伦大学接管了蒂姆肯公司一项关键技术,使其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全球市场。[8]
三、以创业孵化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
大学是知识的生产地,但不等于是现实的生产力,大学新知识的发现与商业化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 为了跨越大学与产业界之间存在的“死亡之谷”,美国大学在外部不同组织机构的协助下成立或运营不同类型的创业服务机构,包括技术转移办公室(TTO)、研究园、概念证明中心、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创客空间等。 这些组织在缩短创业者的学习曲线、帮助解决创业障碍、提高创业成长速度、搭建创业网络平台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创业孵化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根据主要的服务内容不同,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技术转移办公室,另一类为创新创业孵化空间,即研究园、概念证明中心、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创客空间等。
(一)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不是在做发明,我们不是在销售产品。我们是最终的中间商。”[9]从发明的披露环节开始,技术转移办公室始终贯穿于专利、许可、衍生公司各个阶段并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大学科学家、外部公司创业者等,见图2。 一方面,技术转移办公室协助发明者申请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等。 其中关于是否申请专利的思考包括:研究结果获得专利的可能性、可能用途、潜在商业潜力、有无追加投资等。 如果一项发明申请专利的可能性被质疑,而其涉及的版权材料具有市场价值,大学可以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将发明直接出售给外部机构。 或者当版权材料并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而却有研究价值时,可通过材料转让协议(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s)与其他机构分享。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技术转移办公室将其资助的研究发明在未能获得专利的情况下,将研究材料在科学共同体中共享。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材料转让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包括:材料提供者拥有所有权;供方不承担因接受方使用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不作商业研究使用;供方材料准备与分发的费用由接收方报销等。 至于许可合同,其通常包含的要素有:独占或非排他性、使用领域、地理限制、许可期限、商业化里程碑、年度审查、续签间隔与费用、大学成本补偿(如专利费用)、研发资金、设备设施咨询协议、获取有关本发明的专有技术信息、股权股份(如初创公司)是否可作为支付等。[10]对于许可的交易策略来说,马克曼(Markman)等人发现技术转移办公室实施现金策略最不可能产生新建企业,股权分配策略与新创企业正相关。[11]当版税税率过低时,科学家可能更愿意自己创建企业。就许可交易的谈判时间与复杂性来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致力于实施一种创新方法来应对大学在从事知识产权管理时经常遇到的这种挑战。华盛顿大学认识到技术转移办公室的首要目标是使公众能够利用大学产生的技术,因此制定快速启动许可协议(Quick Start License Agreement),没有预付款、维护费、专利成本,只有一个低的固定版税率以及退出/清算时的费用,减少了花费在知识产权价格和版税上讨价还价的时间。 该协议允许初创公司投入时间和金钱开发该技术,而不必承受立即向该大学支付的负担,而且将焦点放在公司的管理团队、商业化战略、研发时间表、资助状况上。 这一措施不仅加速了许可交易过程,确保技术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被许可人尽快开发,而且也减少了初创企业发展的障碍,更有利于初创企业与大学伙伴关系的建立。
另一方面,技术转移办公室帮助发明者获得商业化资金,见图3。 当某项研究发现没有获得足够的商业资金或商业赞助者时, 技术转移办公室往往通过寻求外界资金包括政府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术转移项目(SBIR/STTR)基 金、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 或者以人员交流、 行业/技术会议、出版、中介服务等方式建立关系网络为发明者带来潜在的商业投资。
对于特定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来说, 每个任务的相对优先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因素:(a)大学的主要任务和目标,(b)大学的规模、 行政结构和预算,(c) 内部和外部环境,(d)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e) 风险投资基金的可获得性。[12]2010 年时任美国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 专利商标局局长在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成立40 周年之际,称它是技术转移办公室的黄金标准。技术许可办公室向校内的研究管理部门报告而非向分管商业事务的部门报告,这被认为是有效支持技术转移的基本做法。 充分考虑合作关系的长久性与灵活性,每个协议都是根据被许可方的情况进行协商的;协议的精神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比实际合同更重要。[13]这些都是重要的实践经验之一。
(2)美国大学创新创业孵化空间
“过去,校园设施的竞赛体现在豪华宿舍和娱乐设施上,现在,学院和大学正在建造利于产生奇妙想法的豪华建筑,……为服务商业、工程和应用学习的新建筑物倾注了数百万美元,这些新建筑类似于高科技的工作场所。 ”[14]创新创业孵化空间是经济、人口和文化力量的物理表现。 创新的本质是不断变革,这要求大学内部将空间转换为开放、灵活的场所,使独立的专业和学科更容易融合。这些正在使高校的空间设计发生改变,使其成为更舒适、更具社会性和与技术具有协同性的场所。[15]关于创新创业孵化空间的位置,密歇根大学泽尔·卢里创业研究所(Zell Lurie Institute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的一位主任说:“靠近校园是关键。 我们不会考虑从中心校园步行10 分钟以上的位置……如果学生不能步行到那里,他们就不太可能参与其中。 ”[16]而有些学校考虑到孵化空间与区域生态系统之间需要建立联系便有意将其设置在城市里,这当然就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凯勒创业中心(Princeton’s Keller Center)的“设计思维空间”因多是设置在城里而不是在校园里,往往晚上挤满了人,白天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无论孵化空间设置在校内还是校外,美国高校正在开发多种形式的这类空间,以便向全校师生发出邀请,在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对所有师生开放,并适应师生不断变化的需求。目前较为普遍的孵化空间包括孵化器、加速器、研究园、概念证明中心、联合办公空间、创客空间等。
美国孵化器/加速器一般由学术机构或经济发展组织或政府机构主办。 超过一半的美国孵化器都附属于大学内。孵化器是为商业创意、初创企业早期孵化所设计的空间,提供共享空间以及访问导师和各种服务(例如商业扫盲计划,市场研究,营销协助,商业指导等),包括为大学外部合作公司提供额外服务,例如授权使用大学实验室和计算机设施,雇佣学生作为工作人员、聘请教师作为顾问等。孵化器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生态系统的所有参与者,并帮助学校师生的创业活动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21 世纪初,为进一步鼓励知识创业,美国建立追求高效的创业孵化模式——加速器。 与传统的孵化器相比,加速器主要的特点是短期项目制、入驻项目筛选与学员制的创业教育以及与投资者的广泛联系。 加速器为初步成型的商业设想或初创企业提供指导与创业资源网络的空间,可在数周至数月的密集且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帮助师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商业创意。 通常情况下,初创企业会给予股权以换取指导和小种子投资。 加速器是孵化器概念的一种变体,孵化器计划的目标是企业的早期启动阶段,加速器计划适用于正在扩展到下一商业化阶段的初创企业。 二者区别主要在于运行的商业模式不同,而不是空间或设施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加速器项目会在孵化器空间中运行。 而且,很多时候这两个术语会互换使用。
研究园是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实践的中介渠道。 当前,美国不少研究园区已从最初的郊区分散式布局发展为嵌套在学校工作—生活区中并兼有复合功能的创新区域,不仅包括大学研究空间,而且也具有服务生活的餐厅、零售店等设施,这些为互动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2012 年,美国大学研究园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Parks,AURP)对北美洲174 个大学研究园区(美国占84%)进行调研,其中97%的大学研究园将创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环境为首要任务,其次是为师生提供与企业合作的工作空间、为企业人才招聘提供平台、 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鼓励大学知识产权商业化等。[17]另外该报告罗列了美国大学研究园的典型特征,见表1。
20 世纪初,美国已经有些大学意识到跨越“死亡之谷”的重要性, 在私人捐赠下建立了学校内部的概念证明中心。 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德什潘德技术中心、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2011 年 3 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将概念证明中心作为“创业美国”计划 i6 绿色挑战的一部分, 并予以资金支持扩展现有的概念证明中心或新建概念证明中心。 同年 9 月商务部经济发展局投资1200 万美元支持6 个大学附属的概念证明中心, 第二年拨款100 万美元给7 个新成立的概念证明中心。[18]典型的概念证明中心关注的是大学技术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允许教师与学生在实验室继续进行研发,服务包括种子基金、商业和咨询服务、孵化器空间和市场研究。在与技术转移办公室合作下,概念证明中心使发明者能够评估他们研究的商业潜力、开发早期产品并且测试原型。 这会使发明者更容易从外部投资者(如天使投资人或风险投资家)那里获得资金,用于进一步的产品开发。

表1 美国大学研究园的典型特征
联合办公空间在于创建合作社区、促进思想的碰撞。 通过创造灵活、共享的工作环境,如办公桌和可轻松重新配置的空间,高校内外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可在此空间中获得合作、社交的机会,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同时能够更快发现新思想,帮助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形成潜在的协同效应,迸发新创意或发展最初的创业理念。根据一项调查,这类办公空间最大的吸引力与特色在于社交互动、随机式互动与机会发现、信息与知识的共享。[19]
创客空间的概念并不新鲜,这与创客运动的兴起是联系在一起的,创客运动以创造事物为基本,类似于自己动手(DIY)的文化。而与自己动手相比,创客运动也强调社区和分享。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注重创意原型制作的创客空间,为发明和原型设计提供了模块化的、可灵活再配置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空间环境与文化环境。在这一空间中,通常配备传统的制造设备,如手动铣床和车床,也有更先进的设备,如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新兴的快速原型制作工具,如3D 打印机,以及工作台、椅子和沙发。 与传统工作坊类似,特别是较大的创客空间会根据材料组和制造方法分为几个区域。师生在开放的协作环境中并肩工作在相同或不同的项目上,共同学习、创造、发明、修改和构建材料。其中原型设计是产品开发中的一项关键活动,可实现教育中的实践学习,同时有利于产品开发社区中同行之间的迭代学习。 2016 年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欧林工程学院8 所高校还专门发起了高校创客空间的行动倡议(Higher Education Makerspace Initiative)。
整体看来,美国大学以上六类创新创业孵化空间虽然在某些方面会存在不同的差别或侧重点,如表2 所示,但它们提供的服务存在相当大的重叠性。 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创新空间的区别变得模糊,相似的支持活动在不同的创新空间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包括提供办公空间、帮助评估市场机会、支持产品开发、提供创业资金、建立创业者关系网络等。这些为师生创业提供孵化服务的创新空间,为师生提供了通过实践学习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建议和支持,使得他们成为第一线的实验者,同时有条件与能力做出反应和响应,测试和尝试,试错并继续前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合伙人最感兴趣的是自己不知道,但合伙人知道的东西,即他们共同点之外的领域。 而要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新知识,他们则需要至少在语言系统上达到互相理解,这种共同点是进一步互动的载体和基础。 美国有些高校开始利用设计的手段来支持转化过程, 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学术创业联系起来。 麻省理工学院感知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借助各种设计包括草图、可视化、原型等将研究概念转化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理解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实验室成员还会在公开演讲中进行演示。这些研究主题不是仅仅以诸如论文、书籍等学术形式被编辑呈现出来,而是转化为可由各种利益相关者体验、理解甚至享受的方式。

表2 美国大学六类创新创业孵化空间的一般性差异
四、分析与总结
美国政府、产业界、社会基金会(包括个人捐赠)与高校合作发展专业化的创业服务组织,如研究园区、孵化器、概念证明中心、产业界—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创业中心等,加之高校内部设置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产业联络办公室等,这些跨边界组织既为加快实现知识价值提供了各类要素的保障,包括导师、资金、项目等,也为有效融合大学的传统功能与学术创业提供了缓冲地带。 美国大学愈发地成为创新创业的枢纽而不仅仅是来源。 这些或以创业教育为核心、或以产业合作交流为核心、或以创业孵化为核心的创业服务组织是校内外不同的创业支持要素间的重要合作桥梁。 校内外创业合作项目可短期可长期;可以教师为中心,也可以学生为中心;可以教育为依托,也可以研究为依托,还可以社会服务为依托。这些灵活的项目往往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载体与平台,特别是如果它们要排除不可靠的要素包括对师生创业的质疑,并作为知识创造、流动与转化的场所发挥作用。因为合作项目的临时性与多样性要求校内设立固定的跨边界组织为信任建设和有效的知识价值创造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稳定的伙伴关系中,资源不仅得到共建与共享,而且信任逐渐建立,并且当利于学术创业的关系环境足够开放、足够理解时,师生创业的自然力量与外界作用力量也相互叠加、相互应和。
另外,校内不同的跨边界组织作为一种学术创业支持机制,它结合了创业教育、创业资金赞助、创业导师咨询、社会网络构建及技术开发服务等多项资源为校内师生服务。虽然不同类型的跨边界组织具有各自的服务重点,但它们都基本瞄向类似的创业支持要素。 这种策略措施反映了美国大学鼓励子系统在创新中互相学习或向兄弟院校学习,试验性的政策或方法如果证明是成功的,则会在创业服务组织中被采用进而扩大影响范围,并且从侧面验证创业教育、创业资金、创业导师、社会网络关系、创业服务组织等创业资源的重要性,而创业服务组织通常是通过校内外相互的协作连接创业课程与活动项目、 大学内部创业资金、政府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术转移项目(SBIR/STTR)基金、社会投资(基金会、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驻校企业家、校友导师、创业共同体等创业资源,并帮助形成、加强与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创业网络。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提供类似的创业资源的组织策略也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创业服务组织在同一所学校内同时以校园计划或活动来竞争相同的稀缺大学资源,例如资金和专业人员。 美国大学或以全校资源联动、或以集中管理、或以委托管理的方式从全校范围内对学术创业进行统筹式的保障,正是应对资源紧张或是资源庞杂的最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