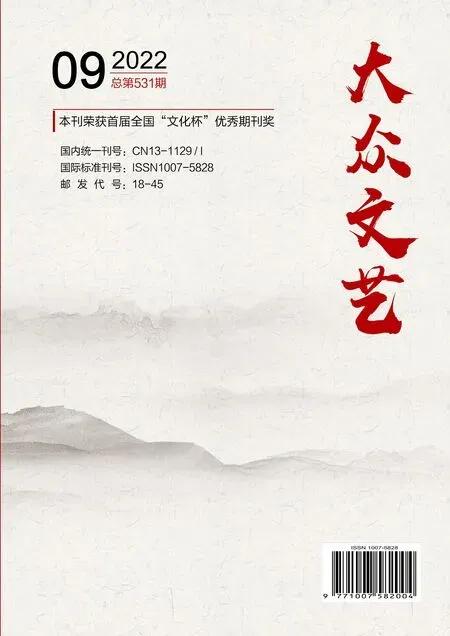荒谬英雄:一场生与死的对抗与融合
——从《西西弗神话》看加缪生死观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 411100)
纵观加缪《西西弗神话》中对希腊神话中西西弗这一形象的再阐释,可以发现在加缪存在主义视域下对这一神话原型作出的全新解读,他书写了文学史上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西西弗形象:他已然不是因贪恋人世而受到惩罚的悲剧之徒,恰恰相反,加缪肯定了其存在的意义,并将西西弗的形象内涵与存在主义相结合——这是一位在生之热烈与死之永恒中挣扎和沉浮的荒谬英雄,而通过对西西弗这一形象的思考可以看出加缪对于生与死的思考。
一、西西弗经历:荒诞产生自由
加缪并没有改变西西弗在生之时的纵情欢愉和不循规蹈矩的生活背后所包含的人性的欲望与野心,西西弗留恋于“流水、阳光的抚爱”“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等人世间的种种美好,于是他绑架了冥王普鲁托以便于长久地存地留于现世。神话结尾众神对西西弗的惩罚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纵欲之行的否定。然而,加缪尽管没有改变这位英雄的最终归宿,但是正是这种对生存的热烈的追求和人欲的遗留使他尽管在没有阳光的地下也依旧能够承担和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趋生而存在,西西弗生时的纵情欢愉实际上就体现了人的欲望。
从西西弗的人欲中可以见出加缪的生命哲学:一种活在当下的处事态度。“荒谬是我在这一点上豁然开朗:不存在什么明天。从此,这就成为我自由的深刻原因。”也就是说,加缪所认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是已经对过去和未来冷漠的,仅着眼于当下的、自身的存在意义的探寻。
但西西弗的命运却已成定局,命运并不能主宰一个人的精魂,但它的强大规定了一个人的存在方式——西西弗将在无尽的苦修中度过,这样的苦修正如它的本义一样,这是一种向死而行的无尽折磨,是生如夏花之后漫长而寒冷的冬之凌烈。尽管如此,加缪依旧赞颂这样一位在经历死亡之后依旧向阳而生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诞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历的磨难。”加缪在文章中对于西西弗形象的第一句阐释,这样的激情就是人欲,人欲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这种生命观是以对荒诞世界的认知为前提的,人欲的展露伴随着前程的憧憬和对命运的远望,但只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才会彻底断绝对未来的期待,从而真正获取意义上的“荒诞自由”。而西西弗恰好就是这样的存在,只有最近距离的接近死亡以后才能明白生活的荒谬,因此当他获取普洛托的允许重新回归到人间之时,才会更加“穷尽一切既定的激情”来挽留自己的生命。
可以说,这也是西西弗性格和命运中的矛盾,是向阳而生的人性与向死而行的命运之间的对抗,而只有明白了死亡,才能真正地活在下,直面荒谬。这种对抗使得西西弗的形象在荒诞的世界中成了加缪笔下的一个理想的生命载体,因此西西弗在生之时的种种行为成了加缪生命观的具体而有力的体现。
二、西西弗苦行:荒诞支配死亡
以西西弗重返阳间为界,西西弗在经历了对神背叛的两次死亡,除了生时的纵欲是对荒谬的认识,西西弗死后的苦行在加缪眼中依旧是荒诞的产物,加缪认为“荒诞支配死亡”,具体在文中,这种死亡观体现为一种荒诞支配下的向死而行,即“世界的先验意义或本质意义的缺失和人的必死性共同构成了荒诞产生的前提”,因此可以认为世界的荒诞是导致西西弗死亡的原因,也是导致其死后遭受惩罚的原因。
结合加缪的生平经历来看,肺结核给尚处于青壮年的他带来的无疑是病痛身体上的折磨与无法治愈的精神上的灰暗,疾病的降临、死亡的逼近对加缪来说确乎是一种毫无理由的荒谬,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迫使加缪寻找在这荒诞世界里幸福生存的意义。对加缪个人来说,死亡貌似意味着一切的终结,意味着荒诞的结束,意味着“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逃脱光明的逃遁”,但从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来看,死亡并不意味着荒诞的结束,反而意味着漫长无尽折磨的序幕,因此,荒诞是永恒的,“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结局,而如何对待死亡——即是否相信有超越的上帝和彼岸世界则关系着荒谬的产生”荒诞支配下的死亡不仅意味着死的瞬间,也同样意味着死后彼岸世界漫长的时间中的未知与无法预测之经历。
自杀与反抗成为加缪在死亡前提下提出的两种面对方式,面对死亡,他更加强调的是除死亡本身以外存留于世的可能性。
加缪在《哲学性的自杀》中提到荒谬的反面就是自杀,生理自杀是对荒谬现实的躲避,而哲学自杀是对灵魂的叛逃。西西弗的死并没有停止他人生中的荒谬,命运对他的生命之灵的消耗依旧没有停止,然而就西西弗这个形象而言,其本身就似乎存在是否能够“重复死亡”的问题,西西弗能否用自杀逃避已经死亡后的荒诞?加缪对生理自杀的否定显然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在认清自己悲惨命运的一刻没有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走上自我放逐之路一样,俄狄浦斯王的存在同样是以活着为前提。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于西西弗与生理自杀的叙述是模糊而暧昧的,这是西西弗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他并不能取得身体的解脱,也无法进行哲学的自杀,而这种局限性在加缪的笔下则为西西弗的反抗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由此,加缪提出了其死亡哲学命题下的存在方式——既然荒诞并不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结束,所以他“更多的是对荒谬世界中对人否定的同时给予肯定,是既说‘不’又说‘是’的反抗者。”人将成为“征服者”,去反抗不可理喻的世界和命运。同样加缪也认为死亡既是最后的放纵。死亡作为一个节点,虽然无法阻止荒诞的继续,但它却成了放纵的终点,西西弗结束了在人世间的种种纵欲之行,因而在死之后受到的惩罚,无疑是一种命运的复仇和代价的终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死亡也成了在荒诞世界中的人的最后反抗——用死亡对世界发出最后一声呐喊,随后沉寂于无边无际的灰暗。而西西弗的反抗则显得更为象征化,绑架冥王哈德逊实际上就是对死亡的最后放纵。可以肯定的是,西西弗是加缪塑造众多反抗者的雏形之一,但西西弗的反抗终究显得暧昧模糊,加缪既没有明确提出反抗的方式,也没有规定反抗的限度,而“南方思想”的提出则进一步完善了反抗的内涵,从孤独的荒诞英雄到集体的斗争,“在节制中永远进行反抗”代替了“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绝对对立的生死观,可以说,加缪站在西西弗的肩膀上完成了关于其荒谬哲学以及死亡哲学的完整论述。
三、西西弗之境:荒诞是生与死的融合
荒诞在加缪笔下被叙述为世界的变幻无常和不可理喻,而荒诞感的产生则来源于个体对于所处现状的清醒认知,“荒诞感的产生是一个由麻木到清醒的过程。”因此,西西弗形象背后的荒诞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第一是内在对荒诞的认识。死后的西西弗的日复一日地推动巨石这样的遭遇无疑是荒谬且痛苦的,就如同盲人眼中永不消退的黑夜一样,这样的无意义劳动永远没有尽头,对于西西弗来说,从麻木地接受惩罚到清醒的明白处境就是一种意识到荒诞的体现;而同时,荒谬也同样来源于“肉体的反抗”:这种对于宿命的顺从转变为对明天的期待所体现出的变化也是一种荒谬,人性的趋利避害要求人们远离苦难,而西西弗却从这种酷刑之中体会到了幸福感,这违背了人之本能,从常理来说也是不可理喻的,但在加缪看来,荒诞和幸福是合为一体而存在,常人无法领会的折磨依旧可以构成一个人生活的全部意义。
如果说第一次将巨石推上山顶是命运的压迫,那么当它轰然落地之时西西弗的继续劳动就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这时他已然不是命运的提线木偶,而是命运的主宰者。荒谬和幸福实际上就是生与死所要包含的情绪,幸福是存在的证明,而荒谬往往以自杀为终结。这时的西西弗俨然已然成了在生与死之间的奇妙平衡者,他死于世界荒诞却又为这世界的荒诞而持续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他被赋予了生与死的双重意义,这是一种存在方式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因为西西弗这个统一体而共存。
总之,西西弗生时作为人的种种私欲与追求让他在脱离人性的死寂之地继续以自己的姿态存在,这是生的存在持续了死之修行;他能在荒谬的、日复一日的劳动中获取自己存在的快乐与幸福,这时死的修行延续了生的意义。在这里他肉体已死而灵魂永存,西西弗的死就是再生,而这样的再生意味着永恒不死,生与死的意义在这里已经被消解,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生死的融合,结果就是只有运动(抑或加缪所说的劳动)成为唯一能够存在的证明。
这个特殊的场域是同样特殊的西西弗斯的所有物,“这块巨石上的每一个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来说才形成一个世界。”西西弗没有摆脱身上的重负,但是正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完成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和驯服。
四、结语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既是命运的安排者,也是生活的审判者,他是生与死这两个伟大哲学命题具体化的产物。西西弗作为加缪荒诞哲学的承载者,我们能从加缪的叙事中总结出一种以荒诞世界“活在当下”的生命观以及“向死而行”的死亡观。同时通过总观西西弗其所处之境可以看出其生死观的哲学意义,这也正是加缪赞扬“西西弗精神”和西西弗被称之为荒谬英雄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