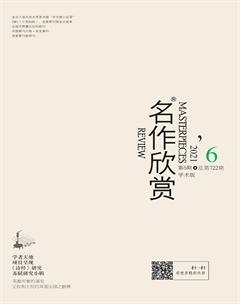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层次理论分析
摘 要:当代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的现实主义小说,其选取主人公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来展现土司制度下的社会,同时读者也能直观了解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层次理论的相关观点,笔者对主人公的心理以及意识驱动下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精神层次理论 潜意识 心理 转变
《尘埃落定》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北大教授严家炎评价其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的确,作品中讲述主人公“傻子”对土司制度超越时代的预言、对地震的预感、对新事物的缔造等,都带有神秘莫测的魔幻色彩,但在描摹人物的思维、心理以及意识驱动下的行为举止时,又未脱离现实的人性,恰恰是结合特殊而具体的文化环境、个人能力来反映人性及真实的心理活动。文学评论家丹纳在其巨著《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品的高低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作品框架宏大不足以深入人心,对人物心理、思想的刻画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广度与深度才是具备不朽生命力之所在,而就《尘埃落定》来说,书中极具个性色彩的主人公“傻子”的内心活动非常值得分析与探究。
一、解读文本中主人公的心理
作品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与主人公预知未来能力相结合的方式将限制视角和全能视角混同使用,是叙事视角运用中一种全新的方式,不仅能在全知视角下对故事进展进行客观描述,而且能充分地表现限制视角下的主观想法。“这里的傻子我们绝不能轻视,它不仅可以视为独特的文化符号,而且是一种富有意向特质的社会人性标志:二少爷既傻又不傻,这既傻又不傻的丰富性或多义性,乃至历史感或现实感,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是绝无仅有的。”主人公的心理非常微妙,而心理的转变过程更是值得推敲。作品以第一人称来表达,开头就自我表明“傻子”的身份,这不仅是旁人贴的标签,也是自我默认的特殊身份。“我”反应不灵敏,咧嘴流口水,但“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考虑到生母出身卑微,为避免在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我”很多时候其实清醒又甘心地去做好一个傻子,这里的“傻”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可即便已然接受这个身份,“我”在经历大大小小事情的过程中仍不断考量着所谓的傻与聪明,并对此有着不同于众人的见解。“我虽然是个傻子,却也自有人所不及的地方”,无须背负一些期望与野心,在某些方面反而能看得更明白透彻,甚至比所谓的聪明人更有作为,因此“我”起初并不太在意那些固有的看法,而是以敏锐的目光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用自己的价值和理解来生活。比如,书中特殊的土司社会等级森严,用“骨头”把人分成高低贵贱,“土司们没有法律,我们并不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但它是一种规矩,不用书写也是铭心刻骨的”,这种等级已经深入人心,而“我”也看得明白:“虽然我是个傻子,但方圆几百里没有人不知道我,这完全因为我是土司儿子的缘故。如果不信,你去当个家奴,或者百姓的绝顶聪明的儿子试试,看看有没有人会知道你。”世人常把“我”与被看作土司继承人的“聪明”哥哥作比较,哥哥一开始因“我”傻而宽容待之,常常“用聪明人的怜悯目光看着我”,但他其实空有勇猛与冲动,缺乏谋略又贪恋美色,且许多做法都不比“我”歪打正着得来的提议更得父亲的欣赏。而这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更让“我”发觉世人对聪明与傻的判定是肤浅的、不准确的、不足以让人信服的。
尤其是在经历了改罂粟种粮食、参与土司间的战争、开辟边贸市场等事件后,“我”发现自己往往能突破聪明人的思维误区而看到事物的本质,发现自己能够做得比哥哥更好,再加上母亲、塔娜和仆人们对“我”的期待,这些因素慢慢发酵,让“我”的心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想继承土司之位。这一目标的确定激起了“我”对“傻子”这个标签前所未有的在意和抗争,尤其在老土司准备逊位时达到了高潮。书记官翁波意西反对让大少爷继位,而老土司给出的理由竟是“人人都说他是个傻子”,“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却因“傻子”的标签而被否决,导致“我”的情绪最终爆发于人前。
可以说,整本小说的一个个情节是由主人公心态转变的线索来串联,而情节也在一步步见证和推动着主人公的内心变化。
二、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层次理论分析主人公的心理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被世人誉为“心灵的哥伦布”,他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学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其中“精神层次理论”是该理论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判断、情感等。总共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无意识)三个精神层次。三者之间的关系暂且可概括为:人类大部分意识是潜意识的化身,潜意识使意识形成动力和目的,即意识源于潜意识的需要,经过前意识的审查,最终化成意识。而代表“本我”的潜意识、代表“自我”的前意识与代表“超我”的意识三部分构成了人类的人格结构。
运用精神层次理论分析作品中“我”的心理与行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我”对“傻子”这个身份的认知与反应。
“傻子”是自小伴随着“我”的标签,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仅早已成为“我”的一个意识来评价和估量自己,还深深烙印在父母、哥哥、仆人、其他土司以及一切知道“我”的百姓的认知里。这种观念的形成,首先是“我”的一些表现在周围人心中产生了印象和想法,这些细碎的未成型的片段经过慢慢累积在合适的时机转化成内心认同的潜意识,并在反复证实后固化形成意识,最终成型的意识得以流传。大家心中“有非常之强有力的心理过程或观念存在着,虽然它们自己并不是意识中的,但能够在心理生活中产生普通观念所产生的一切结果”,以至于都从未把“我”当作土司继承人,而“我”成长于这样的观念熏陶下,潜意识里被反复灌输也慢慢形成认同这种评价的意识。
这种状态可以用柏拉图《理想国》中阐述的“洞穴理论”来形容。“我”刚懂事时就从大家口中得知自己是一个“傻子”,那时并不理解“傻子”这个词的具体感情色彩,只知它是用来指代和定义自己的特殊性,“我”彼时的状态就如洞穴里只能看到洞壁上影像而看不到外界全貌的囚徒一般,认定一直以来所见到的就是实质。但“我”在感受到大家的态度、语气和眼光,目睹和亲历了众多变故,到新疆域听闻了新的观念与见解之后,就如弗洛伊德所說的那般“由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我”的心底对于“傻子”这个评价产生了由怀疑、否认到抗争的一系列潜意识,就好比那个挣脱了锁链和桎梏的人决定到洞外去认识真实世界、获得真理。这个心理转变的微妙过程,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观察。“洞穴理论”涉及“理念论”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我们还可以用与“傻子”突破成规想法相对的一个例子来比较。“我”的父亲麦其老土司,一开始与“我”都是只能看到影像并认定它为世界本貌的洞穴人之一,但观察到“我”一次次出色的提议,立下不小的功劳,做出开辟性的创举以后,他开始动摇“傻”这个认知,被“我”拉着去看外面不同的世界,但又无法做到像“我”那般去改观、尝试,逊位时还因世人有成见的愚昧理由而固执,最终只能困囿于洞穴之中。对于他思想的转折和挣扎在文本中也清晰可见:“土司的话大多是说给自己听的,准备让位的土司说给不想让位的土司听。有时候一个人的心会分成两半,一半要这样,另一半要那样。一个人的脑子里也会响起两种声音,土司正在用一个声音压过另一个声音。”这就是弗洛伊德曾在论述中提到“一个意识状态在特性上是特别短暂的;此刻作为意识的观念不一会儿就变了样,虽然在某些条件具备以后它还会恢复原样”的现象。而这个脱离轨道的间隔中的意念,“我们可以说它是潜伏的,意味着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变成意识,或者称它是无意识”,它具有形成意识的可能。在这个节点上,老土司的意识坚持了原样,而“我”却得以萌生出崭新的观念。
另一方面,是分析“我”对土司之位态度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意识层面的观念被舍弃后,潜意识中有意义的概念控制了整个现时思想”的表现,与“我”对“傻子”身份的心理变化在模式上相似,但其差异也使本质与效果方面产生了不同。
首先“我”对继承土司的自身能力上有一定的自信和底气。从看待事情的独白中可以发现,“我”对事物本质的见解、解决问题的方法、交涉技巧以及人员管理和调配都具备了统治者的基本素质。比如,“我”包容卓玛的行为,因为懂得“即使是奴隶,有人也有权更被宠爱一点,对于一个统治者,这可以算是一条真理”;当发现母亲的奇怪举动时,“我”明白“只要身上流着一丁点儿统治者的血液,傻子也知道多把握一点别人的秘密在手上是有好处的”;当看到家里的喇嘛和庙里的喇嘛竞争时,“我”认为地位崇高的两方相争会有利于土司的地位。这些潜在的统治者素质和观念受到所在家族统治血统以及土司制度背景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留存于“我”的观念中的,没有刻意地去学习和练就,是一种遇事自然形成的价值和思维。而这些潜在的素质就是一种无意识,“无意识的东西并不是就不存在,而是仍然间接在发挥作用”,它们指导“我”的行为,做出大家有目共睹的打仗功绩与开边贸创举。而这些经历与感受又为下一阶段“我”决定成为土司的意识提供潜意识基础。
其次要具备推动“我”迈出决定性步伐的外力。曾经的“我”愿意借着“傻子少爷”的身份闲散度日,但也并不无忧无虑。比如,哥哥怜悯的目光“对我来说是一剂心灵的毒药”,是从小到大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同样,母亲的虚荣心和“我”的无奈、书记官对“我”的赞赏、塔娜以及跟随“我”的仆人们对“我”的期待都在“我”心底暗暗深藏。以至于当大家以为“我”继承土司毫无希望而表现出沮丧或冷漠的神情时,“我”的内心前所未有地激起“想当土司”的欲望,就像猛然绷断了一直压抑着的神经,“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想”。经过推敲“傻子”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想法,可以看出两种心理转变的不同:“我”对“傻子”标签的反驳是自己省察后自发地想去探寻和改变,而对土司之位的追求大部分是由外力来推动的。文中“以前我以为当不当土司是自己的事,现在我才明白,土司也是为别人当的”,这番话便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出来。此外,就算“我”的心态有所转变,对哥哥并没有嫉妒、怨恨之心,也没有像哥哥那般做出陷害、羞辱的事情,哪怕哥哥的过世意味着“我”没有了竞争对手,但“我”还是出于真心地难过了许久。最后土司之位别无选择传给“我”时也没让“我”感到过分高兴,甚至在看到了土司制的前景后觉得土司理应顺应时代而消亡。这些不仅是因为“我”长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洞察和思考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作为旁观者对历史的发展保持清醒,更是因为“我”对土司地位的争取,在意的根本不是权势与地位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外界因素与内心冲击综合驱动下的反应。
三、魔幻与现实结合下心理刻画的总结
《尘埃落定》展开了一幅土司制度社会的历史画卷,描摹世态人心,晕染异域风情,在突显权力问题的同时还追问着“聪明”与“傻”的哲学话题。“它注定是一部可以从不同角度评说的长篇小说,史学家可以看到历史;文学家可以看到诗;文化人类学者可以看到异族文化;批评家可以看到拉美和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本文是从人物心理的角度,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层次理论”,从潜意识的积累、意识的萌发以及对行为的影响来分析主人公的心理与行为。阿来的《尘埃落定》“写出了自己肉体与精神原乡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历史现实与自我理想结合的产物,既有对预知未来能力的畅想,对时代更替的现实把握,也有自我人格的探寻与思考。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尘埃落定》划定为魔幻化、寓言式叙述,毕竟它展现人的心理感情尤为到位和深刻,体现出了“文学的真实性”。人生、战争、历史,以及情欲、贪欲、仇恨和执着等都是“一路落不定的尘埃”。但我们在这漂浮不定的尘埃中,可以探察主人公,这位见证时代兴衰的特殊人物的心理,体味其中对人性的思考、对自我的认识、对权力的冲动以及对时代变换的洞察。
参考文献:
[1] 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2] 庄秀芬.独特新颖的构思模式——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东疆学刊.2002(3).
[3] 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53.
[5] 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
[7] 弗洛伊德.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
作 者: 曹滢瀛,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讀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