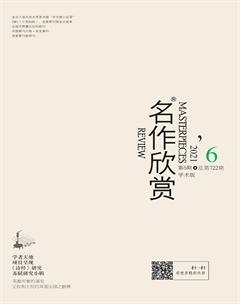焦虑与恐惧
摘 要:“恐惧”不单作为人受困于现实时的反应情绪,更重要的是透射着现代人的生存状况。《镇物》书写命运无常,审视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展现出人在面对未得到解决、处于无意识中的冲突时的态度,引人思索恐惧倾向的根源。本文从先锋作家恐惧书写的共性着手,以期探寻留待小说的先锋性,并结合作家的文本,力图挖掘文本中透射出的恐惧情绪,同时运用相关理论聚焦主体的行为,分析恐惧存在的文学意义。留待着力展现个体生命被现实挤压时的生存问题,竭力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纠缠,他依托日常生活挖掘生命的真实,关注的是现代人的存在境况。小说对人的异化原因进行探求,作出独特的思考,恐惧主题成为解读文本的关键。
关键词:留待 镇物 恐惧 生存困境
《镇物》是山东作家留待创作的中篇小说,原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12期,后由山东省作家协会编,经山东文艺出版社收录于小说集《三朵》。留待擅以控制自如的叙事手法和精练的语言,巧妙转换叙事视角,构建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作为一个先锋作家,留待自言“探索是作家的本能需要”a,特殊题材的选取,叙事视角的精心使用,使得留待的小说叙事具有别具一格的魅力。《镇物》以刘晓光与镇物的纠葛为线索,细密地叙述刘晓光的经历和体验,内在透射其若隐若现的恐惧心理。小说由“镇物”这一意象切入,表层追寻因镇物的存在导致突发事故的真实性,实则揭露出引发刘晓光持续恐惧的根源是其不适应起伏不定的生存境况。这种因恐惧心理招致的生存悲剧,层层冲撞着读者的感官,让读者饱受心灵的震颤。
一、先锋作家恐惧书写的共性与留待的先锋性
留待的写作虽然立足于鲁西,却与乡土小说有异,多年漂泊的经历使得他的生活轨迹与许多本土作家不同,循着感觉和生活体验创作的留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留待专注于从经典小说中挖掘艺术与技巧,兼并着眼于当下文学动向,由此探索出一条有别于山东文学传统的小说道路。王干认为小说叙述可以分为神叙述、人叙述和鬼叙述,他指出鬼才鬼意的鬼叙述较难,尚在实验和探讨阶段,留待的小说局部有鬼叙述,有鬼气。对应到《镇物》中,留待透过刘晓光的视野,小说开头将林芳菲以诡异的鬼魂形态呈现出,结尾当刘晓光完全沉沦于恐惧中时陡然交代出林芳菲的身份,巧妙地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留待又选取“镇物”这一扑朔迷离的意象,在紧张、惊悚、神秘的氛围中揭露隐蔽在刘晓光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三方面的殊异映射在小说中,交融出留待小说的先锋性,留待践行写作者要真诚面对自己内心的理念,坚守着自己的先锋立场,顺应求新求变的先锋文学思潮,不断探索自我的先锋标准。
先锋文学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使其以激进的姿态烙印在历史进程中,正是波澜壮阔式的激变才构成先锋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来看,出现社会、群体的绝对价值到强调个体生存状态、个体生命体验的转变,这种叛逆的过渡促使当代文学突破禁锢,涌现出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根基于当下生存现状进行写作的先锋小说追索者。先锋文学呼应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个体对自身起伏不定的命运的恐惧。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的萎靡会滋生持久的焦虑,长期内心的自我挣扎将断绝人的出路,否定人的价值,进而将其困守于恐惧的牢笼。
余华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将对生存的恐惧注入小说。他由早期的暴力书写逐渐聚焦非理性欲望的叙述,笔下的人物陷入无法排遣且无法逃离的恐惧,这种强烈的情感源于人的不确定性。余华自言沉醉源自人内心渴望、充满激情的暴力。正是以直接揭露死亡情绪和生命悲剧的方式创作,余华的小说才得以直抵人的真实。苏童作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在访谈中谈道:“我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与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b苏童的小说致力于表达人的处境,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人”的关注。不论是“枫杨树”系列小说中寄予的还乡情结和披露出的逃亡书写,还是“新历史”小说系列中的性叙述,都承载着苏童的恐惧情结。
铸就留待小说先锋性的因素可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是留待的小说根基于乡土,以老家鲁西北为背景,本土的文学传统滋养了留待,但因自身漂泊的经历和对写作技术的注重,他弱化了小说的乡土气息,其二是作品中流露出的作家气质,即作家的自身素养。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回绕着西方文学大师的身影,大量外国文学的流入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留待从经典小说出发,多受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影响。可以说,作家自身素养决定他的创作方式,而选择接受的外来影响又将反馈到作品中,时代、其他作家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的经历体验形成了作品中的“气”,这种气“是作者对小说题材和写作手法有了把握之后的自然流露”c。
二、生存困境下恐惧心理的透视
《镇物》书写命运的无常,表达的是人生存困境背后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源自不确定的日常生活。留待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构建小说的框架,叙述时却巧妙加入幻觉描写,从而打破日常生活的真实,将读者从变换的现实里抽离出,放置到个体生命悲剧中体悟生命的真实。小说采用交叉叙事的写作手法,围绕镇物这个意象具体展现刘晓光恐惧程度的变化,刘晓光把变动归结为镇物的存在,他对挖出镇物的执着,蕴含着不适应外界变化的恐惧,而逃避方式从最初的找女卦师发展到最终的挖地洞。刘晓光疯魔的悲剧结局反映出当代人陷入生存困境时的现代性焦虑,以及对不确定事物存在的恐惧,刘晓光的人生态度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刘晓光的恐惧始于狗肉馆破产,精力集中到贴磁砖的工作后暂时忘记恐惧。恐惧升级是在见到林芳菲后,光头找到刘晓光要求其为林芳菲的新房下镇物,而良心难安的刘晓光瞒着光头取出埋下的照片,此时相较于初次下镇物恐惧减缓。光头发现刘晓光的所为,逼迫他再次给林芳菲下镇物,刘晓光突然认出林芳菲是之前相机拍到的狗肉馆里,与自己对坐着吃火锅的女人,真正的恐惧击溃刘晓光最后的理智,促使其发疯似的钻进地洞以此躲避外界。苏童早期的小说十分注重营造意象,往往通过意象传达潜藏的主题。同样,在叙述恐惧的过程中,小说多次提及“镇物”这个意象,“镇物”被用来塑造和推动恐惧情绪。“镇物”是处于困境中孤獨无助的刘晓光为陌生的恐惧找到的托词,只有把不知根源且无法捕捉的恐惧情感具象化,他才能够寻找解决方法,以此重新获取继续生存的希望。
暴力、逃亡、还乡这些主题都透射着恐惧情绪。刘晓光与李大壮见面前设想了三种惩治李大壮的办法,用假想的暴力方式施加给迫害者伤害成为刘晓光恐惧情绪的输出口,实际上,刘晓光已经将对镇物的恐惧转换为对李大壮本人的恐惧。刘晓光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寻求破除镇物的方法,实则因为他把内心不知名的恐惧外化为家中的房子,全村最好的新房附着上刘晓光的恐惧变成小时候梦到过的怪异的坟墓,因此从逃离狗肉馆到逃离家乡,都是他逃避自己内心真实的恐惧情感的表现。初到北京时刘晓光对陌生城市的印象,也可以看出他对变化的排斥和不适应,而还乡时刘晓光已经精神失常。
刘晓光恐惧的是不确定的事实,这种事实背后其实是与他人的接触。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她没有延续弗洛伊德的本能论,而是强调要首先从社会环境和个体环境中寻找焦虑的根源。刘晓光在与他人接触时呈现出的退缩在初中就已显现。初中时刘晓光被叫麻三的街头混子欺负过,软弱的性格使其没有反抗,对突如其来且无法抗拒力量的恐惧植根于刘晓光内心深处。光头初次要求下镇物时,刘晓光因极度恐惧产生了幻觉,当年麻三手上戴着的一个戒指,他在光头的手指上看到了三个,特定情景下由恐惧情感主导的刘晓光彻底失去主观判断能力,成为顺从光头指令的躯壳。逃脱出当时的环境后,刘晓光恢复思考能力并和老张商议对策,再次见到光头时才意识到之前看到的戒指是幻觉。光头绑来刘晓光令其再次下镇物,刘晓光想起林芳菲的身份实际上意味着想起被自己刻意埋藏的往事,过去未处理事件的反噬将他的恐惧情绪推向顶峰。由此,可以看出《镇物》从多方面透射出刘晓光的恐惧心理。
三、命运逆转背后的恐惧根源
弗兰茨·卡夫卡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处于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囊括多种研究视角,他之所以能够直接影响众多现代派小说家的创作,在于他将自身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独特地展示出人的存在境遇。父亲执掌的绝对权力促成卡夫卡软弱、时常抱有内疚感、缺少安全感、缺乏自尊的性格,竭力逃脱家庭影响的卡夫卡把自我恐惧灌输到文学写作中,试图从中得到解脱。荒诞不经的故事叙述蕴含着卡夫卡对事物的恐惧,难以名状的恐惧成为其小说美学的典型特征。人会无意识地对当前所处的困境产生恐惧情感,反过来恐惧同样使人感受着自我存在,并构成人的一部分,卡夫卡借助“恐惧”展示出人存在的多种可能。从卡夫卡到先锋作家再到留待,无不清醒地关注着现实与内心世界碰撞下的人性,在写作中弥补现实里忽视人存在境况的缺憾,他们剥开现实生活的外衣,呈现出埋藏其下的事物的本质和人的真实。
克尔凯戈尔认为,恐惧是一种精神体验,它与人内在的永恒性有关。持久存在的恐惧强化了生命意识,在中国小说中却多以消极的形式出现。《镇物》中伴随着刘晓光的显而易见的恐惧情感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反而将他引向精神崩溃,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刘晓光不能清醒认知到自身恐惧的存在,他为了逃避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后果,远离没有安全感的生存感受,自欺地将不适应变化归结为镇物的存在,接连频发、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的堆积最终压垮刘晓光。“恐惧”对刘晓光而言不是特殊的生命体验,而是使其痛苦地陷入其中且无法排解的存在方式。
小说中刘晓光的行为表现有两方面涉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首先是“自我”到“本我”的变换,“自我”意味着受制于现实规则,需要主体基于理性意识做出合理的行动,“本我”则不受外在的约束,彰显着基本生存欲望和原始生命力。刘晓光最初试图从现实中找到解决困境的方法,虽然他意志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但理智尚存,此时“自我”占据主导地位,刘晓光被压抑已久的恐惧情绪击垮后,苦苦维持的理性之弦崩断,最后的疯狂状态便是“本我”的体现。
其次是关于本能的理论,性本能是本能理论的核心,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性本能长期受压抑,会导致个体精神失常或者个性扭曲。刘晓光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寻找去除镇物的办法,偶然间得到贴磁砖的工作,生活上的顺遂激发了刘晓光的性欲,在他憧憬着与于秀芳相见时遇到了林芳菲。初见林芳菲,刘晓光不仅觉得似曾相识,还对她的身体细节了如指掌,小说中为了揭示林芳菲的身份在此处埋下伏笔,表面上构建关联,对应开头刘晓光看到的幻象,实则这个现象的成因在于刘晓光对林芳菲的身体过于关注。贴完磁砖后,林芳菲请刘晓光在火锅店吃饭,刘晓光对林芳菲的身体再次产生欲望,他的目光带有性的色彩,但受到意识的制约压抑着性冲动。
来到北京后刘晓光的性本能处于受抑状态,不能通过合理的途径宣泄,间接导致性幻想,而林芳菲尚未摆脱因离婚原因衍生的恐惧,想借机寻找合适的依靠,这种情形的指引下同样产生性幻想。弗洛伊德对幻想的解释是由“本我”中的本能冲动造成的,不符合社会和道德原则的性欲受到“超我”的压抑,主體无法将冲动直接表现出来,只得借助幻想进行掩饰。刘晓光看到的赤身裸体对坐着吃火锅的幻象,实际上是由于双方对彼此的性吸引,两人却同时把精神出轨的欲念转接到似曾相识的借口上,留待对此情节采取了魔幻现实式的处理。刘晓光与林芳菲相聚吃火锅时,两人都未消解事件带来的恐惧,刘晓光的恐惧来源于变动的现实,林芳菲则来源于婚姻,双方受压抑的情绪都没有得到合适的宣泄,转而试图躲避到性幻想中解压。两人失去联系的原因也有迹可循——他们相互敲破幻想,将对方拉入充斥着恐惧的现实中。林芳菲因为刘晓光的提醒,回忆起往事,而刘晓光借助林芳菲被迫回忆起破产的狗肉馆和自己的经历。
综上所述,恐惧作为文学母题之一,以不同的形式萦绕在作家笔下,汇聚至今成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文学中。留待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充满恐惧不安,这种现象不仅源于主体对不确定现实的不适应,还在于其内在精神的缺失。《镇物》以别具一格的叙事手法,选取怪异的题材,表现出现代人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迷惘的生活状态,小说熔铸着留待对于真实人性和命运的思索。留待通过营造的非理性世界,聚焦人在面对不可解的冲突时的真切感受,传达出对生命的领悟。
a 李婧、留待:《“留白”是一种能力》,《当代小说》2019年第5期,第79页。
b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第28页。
c 留待、吴永强:《留待:“迟到”的归来者》,《齐鲁周刊》2018年第42期,第57页。
参考文献:
[1] 留待.三朵[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
[2]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7(6):131-145.
[4]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2):25-35.
[5] 王国猛.霍妮的焦虑理论述评[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129-131.
[6] 留待,吴永强.留待:“迟到”的归来者[J].齐鲁周刊,2018(42):56-57.
[7] 李婧,留待.“留白”是一种能力[J].当代小说,2019(5):77-80.
[8] 张厚刚.时代精神与“恐惧的日常化”赋形——评留待的中篇小说《镇物》[J/OL].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9ee4e240102x8qu.html.2016-12-29.
作 者: 吕亚斐,聊城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