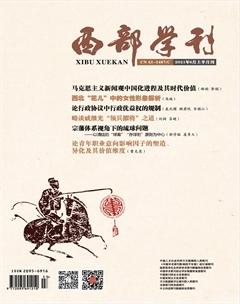西北“花儿”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花儿”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约八个民族间的山歌,它以爱情为主要的歌唱内容。在女性主义阅读视角下,“花儿”文本中许多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实则是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她们变成了男性文化中“空洞的能指”。“花儿”中的女性表现出集体性失语、千篇一律的模样和顺从柔弱的姿态,是男性的审美客体和欲望对象。女性形象的塑造是西北地区宗教文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西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它们一起构筑了西北地区女性生存的现实基础,也是男性话语建构“花儿”文本的根据。
关键词:“花儿”;女性形象;男性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I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1-0016-04
“花兒”是流行于我国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山歌。这些区域的人们时常在田间地头、山坡高地、旷野高原上放声高歌,歌声嘹亮、悠长,感情时而奔放热烈,时而苍凉悲怆,曲调颇多曲折变化,极富当地特色和民族风情。“花儿”的内容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以爱情婚姻题材为主,刻画了男女青年从互相倾慕到相知、相恋、相别甚至离弃等各个阶段不同的情感体验,为我们了解西北地域人们的生产方式、社会习俗、道德风尚等提供了极好的窗口。然而,尽管当地的美貌女子是“花儿”的主要歌唱对象,却往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大部分“花儿”虽句句描写的是心爱的姑娘,但是明丽的语词背后是一个个苍白无力、若隐若现、甚至完全消隐的“他者”。
一、女性形象批评
女性形象批评在西方指的是“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在男性评论家评论女性作品时所运用的批评范畴中去寻找女性模式。它以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为主要方法,以将文学与读者个人生活联系为主要特点。以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的评论为主要内容,以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为主要目的。”[1]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集中剖析了西方五位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揭示出这些文本中的她“永远是特权的他者,以她为媒介,作为主体的男人实现了目标:她是男人的一种手段,对抗他的力量,他的救赎、历险和幸福所在”[2]110。只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并反思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才能颠覆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结构,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下扭曲变形、被淡化的女性形象,还原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女性,而非想象或神话中的她们。
二、“花儿”中的女性形象
(一)失语的女性
“花儿”中涉及女子相貌描绘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这些“花儿”无疑都是从男性创作者或者男性歌者的口吻或视角下产出的结果。尽管“花儿”文本中的确使用了大量色彩艳丽的词汇用以描绘女性,如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等,但是造就的却是一个个苍白的、面目模糊不清的女性形象。她们千篇一律,没有鲜明的个性,犹如一尊尊雕塑只适合被人观看,却从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花儿”中的女性集体失语了,在男性的叙述视角下,无力呈现自己真实面目。由于男性掌控着“花儿”文本的话语权势,她们根本无法澄清面对那些表白“花儿”时自己真实的态度。
首先,被描绘的女性是男性理想异性的心理投射。她们的存在符合男性注视和审美想象,能够唤醒男性的观看欲望,是“生来的俊模样”“天仙女下凡”,是“貂蝉”“真稀罕”,是风姿绰约、温柔善良、楚楚动人的女性。一如劳拉·莫尔维所指出的:“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的形体上……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因此,这些文本中的女人犹如西方电影镜头中的女人一样“作为形象”,而男人则“作为看的承担者”[3]。
白杨树栽子谁栽来?
叶叶儿咋这么嫩来?
娘老子把你咋生来?
模样儿咋这么俊来[4]205?
阳山里开下的水晶晶,
阴山里开下的探春,
生下的好来长下的俊,
赛过了皇上的正宫[4]206。
菊花湾里的一湾湾水,
风刮是水动弹哩;
毛洞洞眼睛一点点嘴,
说话是心动弹哩[4]208。
“花儿”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是刻板印象化的女性,她们的面目大同小异。女性几乎从不自主发声,进行自我描绘。即使当男性表白或求爱时,她们也依然沉默不语,似乎在男性眼中,她们根本无需回应只能默默接受。
胭脂川买下的胭脂马,
回来了马圈里吊下;
我俩的婚缘铁打下,
生死的簿子上造下[4]330。
兰州的大路通各州,
戈壁滩,
嘉峪关通的是肃州;
活着连尕妹手拉手,
死了时,
你把我嫑丢在后头[4]331。
这两首“花儿”以男性的口吻表达对心上人的不离不弃,同时也暗含希望对方于己忠贞不渝。这类情比金坚的表白背后实则是不容对方抗拒的强硬命令,而女方的真实态度无从得知:她们或许抵触这样专断地被表白,或许当时已心系他人,又或者想要放弃这段情缘。总之,她们在男性话语的压迫下缄默无言,与此同时她们作为个体的鲜明形象被涂抹掉,消隐在“花儿”语句中。
(二)被物化的女性
“菲勒斯中心主义”统御下被看的女性只有符合婀娜妩媚、温柔可亲等标准,才能作为男性观看的客观存在。通过把女性联想成具体的事物,并赋予她们种种令人向往、激发欲望的特征,男性完成了对女性的“物化”。“花儿”文本中充斥着“牡丹”“嫩白菜”“花喜鹊”“葡萄糯米酒”等事物,进一步塑造了女性作为物的工具性。正如张岩冰指出的:“女性一直就处在这样一个被波娃认为是对象性存在的位置上,她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她是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一切。女性的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加诸女性身上,不让女性开口说话,不让她成为她自己。”[5]104除了是男性理想的审美对象之外,女性还是男性的欲望客体。这在“花儿”文本中表现十分充分,以女性主义阅读视之,则近乎露骨。
上山的老虎下山来,
清泉里吃一趟水来;
我好比蜜蜂采花来;
你好比牡丹者绽开[4]219。
太子山它本是石头山,
一道吧一道的塄坎;
尕妹是麝香鹿茸儿丸,
阿哥是吃药的病汉[4]297。
大红的灯笼寺门上挂,
再点上一对儿洋蜡;
尕妹是宫灯阿哥是蜡,
蜡点上红灯里照下[4]322。
上面这些“花儿”中的男女关系分别被比作“老虎——水”“蜜蜂——牡丹花”“病汉——麝香鹿茸儿丸”和“蜡——宫灯”。它们连同“锁——钥匙”“鱼——河水”等类比形成了性意味十足的意象场。譬如,包括“牡丹花”在内的各类花意象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极容易让人联想到阴性,进一步则是女性的生殖器。久而久之,女性与花便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联系,进而用以指代女性,如本文研究对象“花儿”。“如果组合成一根认知链条,即花=红色=血=生命=女性,如果将中间的三个等项抽出去,凸现的便是‘花=女性的观念。”而“蜜蜂采花”则暗示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对此,有学者撰文指出“花儿”中有许多这种“诗的内核”(主题),经过多少代的演唱依然保留了它的本质内涵,依然能够引出某种固定的情绪反应。比如,以“牡丹”“云雨”之类的物象和现象比兴的歌,其“所咏之词”多为爱情和婚媾[6]。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花喻女子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红楼梦》女儿国更是一个花的世界,如此等等。不独中文语境如此,西方花意象的出现同样久远。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西方传奇文学描写骑士历经艰难后摘得玫瑰并连根拔起的意象已深入人心,它象征着夺取女子的贞操[2]74。英文单词“defloration”意为“the act of depriving a woman of her virginity”,即“采花”“破贞”之意。其词根来源于拉丁语flor/flos花,而Flora则是古罗马神话中的花神弗洛拉,而前缀“de-”则有“去掉”“去除”之意。可见,花的性意象其实是中外文化史上共同享有的。
此外,“鱼——水”的意象也屡屡出现在“花儿”中。闻一多先生曾指出,中国语言文学以“鱼”来代替配偶的隐语非常多见。很多时候,“鱼”的性能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汉乐府《江南》的“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就是以鱼喻男,以莲喻女,“鱼戏莲叶”,就等于男与女戏[7]。在男性的叙述口吻下,“花儿”里的“鱼”象征着男性的生殖器,而“河水”则具有指代女性的意涵。“蜡——宫灯”的意象也具有相同的性意味。总之,“花儿”中的女性在男性的话语建构下倾向于被物化、客體化,同时作为男性理想的审美对象和男性的性欲客体而存在。
(三)柔弱无助的女性
“花儿”本就是以歌唱爱情为主的山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男性示爱类的“花儿”。其中男性作为叙事主体,虽不免被诟病“自说自话”,但主体性和话语权的突显是不言自明的。此外,我们不能忽略,“花儿”中还有相当篇目的确是以女性视角进行叙述,这里姑且称之为“闺怨花儿”。顾名思义,这些“花儿”里的女性有思妇和弃妇两大类,她们皆怨怨哀哀、分外惆怅。然而,从女性主义阅读视角观之,这些哀怨凄切的女子形象千篇一律、言辞单调乏味、情感缺乏深度,与现实生活中情感细腻、复杂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中国文学中不乏女性诗人所作这类诗,如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并无强说愁怨,然而温婉典雅的女性情志尽显无遗。由此观之,这类“花儿”出自男性的可能性极大,就也是古已有之的“代言体”,其中尤以男性假托思妇口吻创作的诗歌为多。
一天想了难做活,
黑夜想的睡不着;
想下哥的哥不信,
擦眼手巾是铁证[4]119。
月亮上来一面锣,
一夜想郎睡不着;
脑壳担在炕沿上,
眼泪淌得像江河[4]130。
既然女性并不掌握“花儿”的话语权,也就不难理解男性的“代言”现象。同时,由于我们无法洞悉与爱人分隔两地的情况下女性真实的心理和情感,这类“闺怨”就多少有点男性一厢情愿的意味了。在他们话语建构起来的世界里,女性无一例外是柔弱、被动、顺从,等待着被拯救的形象,一如马睿评价古代中国代言体闺怨诗:“男性诗人虚拟了她们的愿望与失望,一时间使精致的诗词文本仿佛成为‘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事实是,她们并没有参与言说,却是言说的对象,或被塑造被虚拟的抒情主人公。男性诗人以女性形象出场却只顾自言自语,实际上是盗用了女性的表达,取消了女性的声音。”[8]正是这样的“代言体”文本,塑造并固定了“花儿”中女性作为男性依附者和从属者的形象,满足了男性充当“拯救者”的心理,展示了他们凌驾于女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从“天使”到“恶魔”
西北“花儿”里绝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婀娜多姿、凄楚动人的,字里行间不难推断出这些女性在家里的角色是相对固定的:作为听话的女儿和温顺的妻子,即所谓“屋子里的天使”。她们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范围仅限于熟悉的乡里,除了家中的日用起居,她们很少能在其他事务上面做得了主、说得上话。换言之,她们缺少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主体性。这大概是“花儿”反映出的中国西北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的身份和地位。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阻碍了女性的自我发展,从而限制了女性的话语空间和身份表达。男性因而得以在文本中按照他们的心愿描绘女性,塑造一个个“天使”。男性实际上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寄托在这些神圣化了的“天使”身上,然而“她们只是一种对象性存在,没有自由意志……她们只是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5]66
然而,“花儿”文本并非完全贯穿着男性期待的这种“永恒的女性”,男性话语者似乎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们对另一些不顺从、不屈服、敢于追求他爱的女性的厌恶和排斥。这在“花儿”文本始末并未多见,却构成了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所谓的“恶魔”式女性形象。
老鸦飞在磨沿里,
把你新鲜几年哩,
磨子老了可碫哩,
把你老了谁缠哩[4]97。
园子边里胡麻草,
姐的人好心不好,
人连牡丹树一样,
心连花椒刺一样[4]148。
上面第一首“花儿”透露出男子追求不到女子时的心态。女子甚至包括所有女性在他眼中一旦衰老就被弃如敝履,甚至还不如老旧的磨耐用,言语中充满了对女性的鄙视和压迫。男人追求失败尚且如此,倘若她变心或者反抗他的一片好意,那她无疑就是最自私、最恶毒的女人,心肠像“花椒刺”一样。一方面,男性把“天使”的女性形象强加于现实中的女性,压制她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使她们沦为“丧失自由意志的艺术品”;另一方面,男性话语对“恶魔”式女性的诅咒,也是“对妇女创造力的明火执仗的贬损和压制”[5]67。
三、影响女性形象的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花儿”是流行于我国甘、青、宁等地,涉及回、汉、土、东乡、撒拉、裕固、保安和藏八个民族的民歌。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不尽相同,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也有诸多差异。但是,无论何种宗教,它们与女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宗教对妇女行为、心理、人格乃至社会地位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女性自我形象的塑造依然存留着宗教的痕迹,比如伊斯兰教对妇女的制约深刻影响着穆斯林女性的社會形象,至少它在女性地位的规定上面表现出了“二律背反”性。比如伊斯兰教主张一律平等,《古兰经》明确指出:“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9]然而,《古兰经》还指出“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虽然女性处于被保护者的角色,但正如谭桂林[10]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保护并非出自对于女性人格的特别尊重……本质上这种保护是对妇女从属于男人的肯定,是对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一种约法。”
民族文化的保守倾向也必然会和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经过长期的磨合、碰撞和调试,最终形成各民族内部相对稳定的妇女观。中国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男尊女卑的思想经过明清穆斯林宗教学者“以儒诠经”运动(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与伊斯兰文化糅合在一起。佛教在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本土化”:佛教教义宣扬修行必须远离女色,所谓“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视女性为修行路上的一大障碍,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儒家传统妇女观。总之,宗教文化里妇女的低微地位、世俗文化的历史影响与西北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共同作用,构筑了西北地区女性生存的现实基础,也是男性话语建构“花儿”文本的根据。
四、结语
西北“花儿”塑造的女性本质上是一个男性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假的、失语的群体,它向我们集中展示了男性是如何想象、描述和要求女性的。“花儿”中的女性不掌握实际的话语权、沦为男性观看和注视的对象,既是他们的审美客体也是他们的性欲客体:“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11]通过物化女性,男性在满足了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剥夺了女性的成为她们自己。“花儿”中的女性所指已非任何现实中真实的女性,而是被偷换成男性随意可取、随意可弃的价值客体,被偷换成从属于男性的次等级。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文化中的“空洞能指”[11]。
波伏娃[2]121指出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花儿”中女性的形象是在西北地区多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和当地社会经济三者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她们的真实面目需要被书写、被还原,我们或可借由女性主义的阅读视角重读“花儿”文本,解除“封印”的女性力量。
参考文献:
[1] 顾红曦.凯持·米利特的性政治与“女性形象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1998(4).
[2]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3]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J].周传基,译.影视文化1,1988(9).
[4] 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5]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6] 阿进录.“牡丹”:一个“花儿”经典意象的文化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7(4).
[7] 闻一多.闻一多神话与诗[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11-113.
[8] 马睿.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9]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0] 谭桂林.宗教与女性[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44.
[11]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上海文论,1989(2).
作者简介:马瑞(1987—),女,回族,甘肃兰州人,单位为兰州交通大学,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和翻译。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