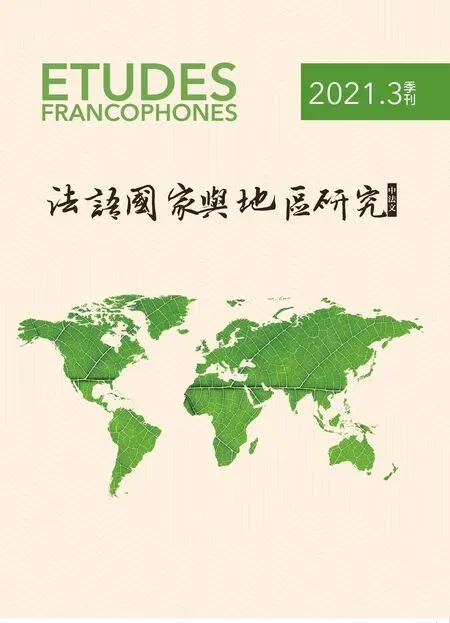唐代律诗语言独特性探索:还原虚境的翻译方法①
王钰禛 余力涵
内容提要 目前,许多译者在翻译唐代律诗时都缺乏对其特殊形式与内容的考量,导致译诗与原诗的意境有所出入。本文选取三首典型律诗中的名句,以其不同法译本为例,分析译诗对原诗实境的保留情况以及对原诗虚境的还原程度;揭示律诗独特的形式内容,如语词、对仗结构和意象等在诗词由实境转化为虚境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提出还原虚境的译诗法。
中国古典诗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或像唐代皎然所言“文外之旨”,司空图所言“象外之象”。因此,关于中国诗词的评说,历来离不开一个“境”字,如王昌龄的三境论、司空图的《诗品》,再到近代学者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等,其核心都是对古典诗“境”的考察,且此“境”更重在实境之外的虚境。董颖指出,实境是诗中“一个个可感意象的总和”,虚境则是意象与意象关联间生发出的不可见的深层意义,甚至自我内心中被激发的情感,“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隐约可感而实不可捉摸的空灵境界”。②董颖.《经典的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文本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第163页。当今,有许多涉及唐诗外译的译论或观点强调翻译时的改变与创造或再创造。然而,改动诗词的意象或破坏对仗的结构,哪怕是添减字词以重新赋予诗语言以西方的逻辑,皆会扭曲实境,以致于对虚境的自如呈现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唐代的律诗。因为在唐初,诗人对形式的探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精致,律诗中的意象也会被该形式激发出多种意义。所以,唐代律诗是在由实境转为虚境这一过程中展现得最为精妙的诗歌体裁。因此,本文选取了三联分别在形式、内容和意象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律诗诗句,对其不同法译版进行比较分析,揭示诗词的实境如何转化为虚境,同时强调还原虚境的重要性,讨论“诗性”的意义,并论证译诗改动实境对还原虚境的阻碍;最后,得出还原虚境的译诗法。
一、律诗的介词省略与对仗结构
从形式层面来说,为达到诗语言的最大灵活性,对仗结构自是诗人所采取的必要方法;其次,省略,如介词的省略,亦是诗人常常采用的手法之一。而无论是对仗结构还是介词省略,在律诗外译的过程中,都是对译者的考验。本段以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为例,对律诗中介词省略及对仗结构的翻译进行简要的分析,并阐明程抱一《商山早行》译诗的妙处。
1.介词省略:语词与事物位置关系的灵活性
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是唐代律诗中极具特点的一首。该诗三、四两句采用列锦的手法,即全部由名词组成,意象具足,历来脍炙人口。该诗三、四两句对偶,这又使其间意象彼此激荡出多重含义。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由六个意象组成,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且它们在诗中是并置的,未出现任何表示位置、时间的关联词,介词在该句诗中被省略了。“天边残月未落,房顶盖着茅草的山中小客店,传来报晓的鸡鸣。村外,木板小桥上凝着一层白霜,桥上留下一行疏疏落落的脚印”③张祥斌.《名师导读古诗词名句分类解析》.长沙:岳麓书社,2014,第182页。,这是张祥斌在其书中对该句诗所作注解。事实上,大多市面上附有注解、赏析类的诗词选大都如此:为了表明一首诗或一个诗句的表层含义,详尽的描写性的语言在这些书中必不可少。然而,古典诗却就是利用这种“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令‘物象自现’,使读者获致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并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④叶维廉.《中国诗学》.合肥:黄山书社,2016,第18页。因此,上述解读方法是在从多角度感受诗歌的可能性中框定其中一种,并不利于读者的想象与审美。比如说,这月一定就是茅舍之上的天边残月吗?或许这正是一轮西落的月,恰好从茅舍的檐边透出最后一丝光亮?且新月、满月、残月升落时间不同,残月可能夜半才升,凌晨正在中天。因此早行未必月落,夜半未必月在空中。综上,诗人利用语言的最大灵活性,取消物象的时间和位置关系,创建“物象自现”的世界——实境,由此激发读者的无尽想象——虚境。
程抱一深深地意识到了诗中这种意象位置的不确定性,在《中国诗画语言研究》里将该句译为:
“Gîte de chaume sous la lune : chant d’un coq
Pont de bois couvert de givre : traces de pas”⑤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231页。(直译为:茅屋在月下:鸡声 板桥布满着霜:人迹)
又在随后撰写的《云水之间》中将其修改为
“Gîte de chaume au clair de lune, chant d’un coq;
Pont de bois couvert de givre, traces de pas…”⑥François Cheng.Entre source et nuage, Voix de poètes dans la Chine d’hier et d’aujourd’hui.Paris : Albin Michel, 2002, p.34.(直译为:茅店在月光中,鸡声;板桥布满着霜,人迹)从前后的变动,包括“sous la lune”变为“au clair de lune”,还有句中冒号的消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程抱一为最大程度取消意象之间的位置关系,以求达到原诗意境所作的努力。其实,原诗中的“月”实是难以在翻译中省略相应介词的,这是不同语言的语法导致的;在许多译本中,如胡品清对该句的翻译,亦是出现了介词“lune sur le chaume de l’auberge”⑦胡品清.《唐诗三百首法汉对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21页。.(直译为:月亮在茅屋上)。但程抱一以月光的洒落代替月亮的位置,保证了月亮这个意象在场的同时,亦保留了原诗意象的无时间空间关联性,不可谓不绝妙。
2.对仗结构:空间的呈现
“Au chant du coq, de lune la chaumière est ivre ;
Le pont en bois est parsemé de pas et givres.”⑧程抱一,前揭书,第231页。(直译为:在鸡鸣时,由月亮茅屋醉了;板桥布满了脚印和霜)是许渊冲的译本,许译版尾韵虽是其他译本不具备的(ivre与givres的词尾音素一致,押韵),但该尾韵的拼凑不仅导致了月光与茅屋的关系变动,还导致了对仗结构不复存在。对仗与不对仗轮番出现在诗中,两种形式都有各自的意义。按照程抱一的理解,不对仗句意味着时间的进程,对仗句意味着空间的组织。⑨同上,第64页。以《商山早行》为例,他的结构是律诗最传统的“不对仗-对仗-对仗-不对仗”形式,首句点名“早行”,颔联颈联写一路经行所见,尾联采用“兴”的修辞手法,由二三联的眼前之景生发思乡之情,回忆梦中故乡的春天。因此,整首诗的时间脉络应如图。如右图所示,虽然整首诗呈时间线性进程,但在对仗的二三联中却生成了一种空间。二、三联的两行诗句都是完全对称的,其间含义相反或互补的词语两两对照,如:“鸡声”和“人迹”都是动作主体未出场,读者通过听觉和视觉想象出动作的发出者,接着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勾勒出引颈长鸣的公鸡与行色匆匆的路人形象;再比如,“月”和“霜”都是清冷之物,能够带给读者相似的感受,李白的诗中就有“举头望明月,疑是地上霜”;叶“落”地、花“照”墙,一明一暗,一萧索一鲜活,对比之间突出了“一起发行役劳苦之怀,一结含安居群聚之想”⑩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收录于陈伯海等主编.《唐诗汇评增订本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989页。。所以,“可以说,对仗是一种在符号的时间进程中对它们进行空间组织的尝试”⑪程抱一,前揭书,第64页。。简而言之,对仗绝非单单是一种律诗格式的要求,还是一种表意手段,将意象符号召唤在一起,从而进行内部的联系或对比,或展现一幅全景或烘托暗含的情感。而这些,都是属于虚境的——实境依靠着这特殊的对仗结构,向着虚境不断地延展。在程译文中,“茅店”对“板桥”、“月”对“霜”、“鸡声”对“人迹”,上下句的意象彼此呼应,原诗的空间性就得到了还原。而许译诗的韵虽是音美的体现,但“易词就韵,难免以词害意”⑫江枫.《江枫文学翻译自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9页。。

二、古典诗的画面感与“逻辑”性
于内容层面而言,中文古诗并不同于西方诗,它主要讲究一种画面感,这一差异就犹如中国的山水画比之西方以焦点透视构建出来的画作。诗人炼字、布景,为读者打造出一幅幅图景,可谓是笔补造化,为的便是使读者能够感诗人之感。而这于译者而言,是极容易忽视的一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会使其在译诗中以逻辑感代替原诗为读者带去的“感”。本段以《春望》为例,试图说明译诗需还原原诗“感而后思”逻辑的重要性。
1.感而后思:字句的画面性
唐代诗人杜甫,其风格独树一帜,后世模仿其诗风的人数不胜数。同时,杜甫的人生经历使其诗歌话语含蓄蕴藉,也使译者对译诗的内容、风格难以把握。
安史之乱后,杜甫身处沦陷的长安,目睹了长安城一片萧条零落的景象,百感交集,作诗《春望》。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写尽了大唐国都之破败。后世将该诗译为法语的译者中不乏大家。对于这一句,大略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译法:一为许渊冲的
“Le pays ravagé, restent fleuve et montagne,
Au printemps dans l’herbe ensevelie la campagne.”⑬许渊冲.《许渊冲文集中国古诗词选汉译法》.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第133页。(直译为:城破,山河在,在春天草里掩埋战场)和许钧的
“Les monts et fleuves demeurent du pays brisé,
Les herbes et arbres cachent la ville au printemps.”⑭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46页。(直译为:山河存留在已破碎的国家里,草和木掩藏城在春天);二为胡品清的
“Le pays est détruit, mont et fleuve demeurent,
Dans la ville printanière, touffus sont les herbes et les arbres.”⑮胡品清,前揭书,第138页。(直译为:国家被破坏,山河存留,在春天的城中,茂盛的是草木)与程抱一的译文:
“Pays brisé
fleuves et monts demeurent
Ville au printemps
arbres et plantes foisonnent”⑯程抱一,前揭书,第203—203页。(直译为:国破山河留存,城春树木植物繁盛)
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未对原文加以改动。古人以自然之生机反衬情绪之哀恸的很多,就如汤显祖在《牡丹亭·惊梦》中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是,杜甫不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仿佛是一种零度写作——诗人并非没有情绪,而是深深的克制,这也是他诗歌的一大特点,即沉郁顿挫——指诗文的风格深沉蕴藉,语势饱含停顿转折。杜甫一生的境遇,形成了他深沉阔大的情感,但要在诗中表达出来,就须用顿挫迂回的方式来表达,这亦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cacher”(藏)和“ensevelir”(埋)虽将诗的意思表达得明了,但却看不出是杜诗,大抵已与汤显祖无差;而“foisonner”和“touffus”就是草木繁茂之“深”,草木深深,完全还原了应有的画面感。语言在适当的安排下,可以提供类似视觉过程的经验,这种经验要通过“感”,即感受来达成;如果未感而“思”,即思考先行,就会成为一种阻碍,影响物象涌现的直接性。⑰参见叶维廉,前揭书,第21—23页。视觉可感的“城、春,草木深深”,通过译者的理解转变成了译文中的“草木遮蔽了城郭”。如此一来,以思代感,字句的画面性就遗失了。
感而后思,感实境而思虚境;就像在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读者的脑海中先有感受而来的画面,再通过思考,领悟生命的顽强不息——这是面对一首诗时不可替代的欣赏过程。显然,在唐诗外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赋予目的语读者“感”的体验,而非以译者之思代替读者之感。
2.感而后思:诗的“逻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汉语诗律学》⑱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274页。和《古典诗词特殊句法举隅》⑲王锳.《古典诗词特殊句法举隅》.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第65页。等书籍中被归类为让步式和因果式:“国虽破”与“国破山河在,因而城春草木深”。但这些书籍大都是以“主谓宾”等西方文法来剖析中国古典诗的。如果我们反观中国传统批评,就会发现前人的赏析大都是点、悟和看似零散实则画龙点睛式的,甚至有以诗评诗,如司空图等。此二者之异在于西方语言逻辑与东方经验感知的矛盾。
司马光评《春望》一诗,曰:“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诗,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⑳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上》.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第350页。其中“意在言外,思而得之”就意味着“先感后思”。读者很实在地感受到作者当时的情境之气氛,而得以展开其他的美感活动。按照诗人的经验,情境应是这样的:诗人望见荒凉的城池、自然依旧的景,他看到春天来临,草树繁盛。就如叶维廉所言,这种写作手法是一种“蒙太奇”技巧,“是两个视觉事象的并置与罗列”,而若把该句看成让步句和因果句,就是从西方理性的逻辑出发,是“思”,由国破直接推理出草木遮掩着荒芜的破碎的城,从而取代草木深深,这着实无益于读者领略杜甫诗作的风格。在唐诗外译实践中,以“思”代“感”将不利于译入语读者理应先感而后思的读诗“逻辑”——这个逻辑并非西方文法的语言逻辑,而是符合唐诗先感后思,从而物象自现、意在言外的“逻辑”。另外,在上述的四个译本中,虽未出现将整句诗视作互为因果关系的句式,但“Les monts et fleuves demeurent du pays brisé...中“de”的使用,明确表示出山河与国家是从属关系,这便会造成读者理解译诗“国破山河在”是具备因果关系的这一可能,即国将不国,所以便只剩下了国之山河,该词的用法是有待商榷的。
综上,译者除了需要考虑字句的画面感,还需要琢磨是否可以以西方逻辑代替古典诗的经验“逻辑”,以使译出语读者能够与译入语读者一样,体验到读诗的完整过程:感而后思。
三、古典诗的意象关系与主语省略
意象层面,是建立在形式与内容层面之上的,是一首诗的精妙所在。因而,在意象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同时受到内容翻译及形式翻译两方面的掣肘,从而对意象的翻译失去把控。本段以《月夜》为例,探究程抱一、许渊冲及胡品清三位译者在对诗中意象进行翻译时所做出的取舍。
1.意象、意象内在关联与语序
诗中的意象往往会赋予能指一个全新的所指,比如,竹有正直清廉之意,梅有孤傲顽强之意。诗人们采用了大量能唤起读者联想的意象,把诗的表面含义推向了更深的意味。在《月夜》中,“云鬓”和“玉臂”都是常见的意象。前者指女子盛美如云的鬓发,后者指女子洁白如玉的手臂,如在诗句“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辞》)、“怕红绡误染,翻成玉臂珠痕”(《群音类选·红蕖记·谐配》)等中。常见意象的引申义大都是因袭的,然而《月夜》一诗对其使用的方法却打破了因袭意象的老旧感。原因有二,一是与“香雾”“清辉”的连接使用,二是“湿”字与“寒”字的勾连作用。首先,云鬓与香雾相联结,这两个意象都含有水气的成分,它们共同的本性给人一种一个受另一个激发而生的印象。另外“香”又暗指女子,同云鬓呼应。同样,在第二句诗中,“清辉”的意象自然对映着“玉臂”的意象:“玉”与“月”本身是阴寒清冷之物,玉光月光交相辉映。这由月亮投射下的光辉,亦可看作是由女子裸露的臂膀所散发的。其次,结束诗句的动词“湿”,非常恰当地勾连起香雾与云鬓,将它们融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而展现月夜的“寒”,似乎也描述了人们在触碰一块玉时的感觉,将玉臂与月联系在一起。所以,该诗的因袭隐喻非但没有使诗句沦为窠臼,而且“当它们被巧妙地组合时,反而得以创造出意象之间的一些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且这种关联始终保持在诗句的深层所指中”。程抱一注意到了意象间隐秘的关联,在分析诗句后将其译为
“Chignon de nuage, au parfum de brume
Bras de jade à la pure clarté…”(直译为:云鬓,在雾气的芳香中。玉臂,在纯洁的光中)甚至在后来,又丰富了玉臂与清辉两个意象的关联性,改作
“Chignon de nuage au parfum de brume,
Bras de jade dont émane la pure clarté…”(云鬓在雾气的芳香中,玉臂散发出纯洁的光)但有一点却被忽略了,即“湿”字和“寒”字的意义,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第二点。而且,我们能够看出在两版译句里,两个意象的呼应感逐渐被削弱,月亮的隐含存在也在后者中消失了。这是改变语序所造成的。虽然以纯逻辑思维解读唐诗并不合理,但为了厘清意象的顺序问题,我们有必要参考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对该句的分解:“香雾初浓,云鬓以湿;清辉既满,玉臂亦寒。”不过,即使不考虑逻辑关系,当我们以经验来“感”时,意象的顺序也确如上述。因此,在进行唐诗外译时,译者需要对意象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关注;假使意象的语序被调整,那么可“感”的画面也会发生变动,从而影响译诗的实境与虚境。
关于对意象顺序的处理,胡译与许译都是值得参考的,尤其是许译的处理,既呈现了意象间隐秘的呼应,使其不至于因文化之异而让目的语读者体会不到这种呼应,又处理好了意象顺序的问题,几乎还原了原诗的全部内涵:
“Tes cheveux parfumés
De brume sont humides ;
Tes bras ont froid, noyés
Dans les rayons splendides.”(直译为:你飘香的头发由潮湿的雾气;你的手臂冰冷,被浸没在灿烂的光中)
2.主语省略:在场与不在场
“J’imagine la chevelure de mon épouse pareille aux nues et humectée par la brume parfumée,
Ainsi que ses bras pareils au jade et refroidis par le clair de lune.”
这是胡品清译本对该句的翻译,意象与意象顺序基本无碍译诗还原原诗的意境。但区别于前二译本,该译句出现了人称主语。中国古诗词大都省略主语人称代词,比较精妙的当属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国维称其是“无我之境”的典范。这种主语的省略,大略有如下的几个作用:反映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悠然见南山”便是一例;或使诗人不在场,从而邀请读者在场,以身临其境地“感”受物象,“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是后者。读者借诗人的遥想,“看到”“嗅到”一位美丽的女子。许译本中虽含有“tes(你的)”这一称谓,但却并不影响读者进行这一体验,反而更赋予了“感”的对象一种具象性。然而,胡译中的“Je”似乎就妨碍了诗人向译入语读者发出这种身临其境的邀请。
从文本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话语层面上的‘意义解读’指的是由形式衔接所支撑的文本在读者内心的连贯再现”。当读者将“J’imagine”和“Ainsi que”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即该联的第一二句都是以“我想象”开始,并引起两句意义的连贯时,读者的聚焦点将会放在由主语和主语进行的动作上。试感受胡译的中文直译:“我想象我妻子的头发像云一样,被雾气浸湿;我想象她的手臂像玉一般,月光使它冰冷”,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读者的注意力被主语的在场和主语发出的动作转移了。因此,原诗里人称代词省略的作用不可忽视。倘若译诗中明确了原本不在场的主语,那么读者的在场就会变成不可能。
很多学者认为,古典诗常常省略主语,但英语的语法习惯要求句子必须有明确的主语,所以在英译时,必须按英语语法的规范把主语译出。但唐诗语言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因其区别于散文、小说等诸多文学体裁,外译时实需多加思索。
四、实境到虚境:“诗性”
诗人在诗的形式、内容及意象层面上采用了种种手法,将读者从由意象组成的实境带入了由意象关联激荡而形成的虚境。如此,译者的翻译事实上就要同时兼顾重建实境与还原虚境。实境因其外显往往不易被译者忽略,而虚境却相反。因此,本段将引入“诗性”的概念,因为于译者而言,把握住“诗性”,便是把握住了诗人构建虚境的钥匙。
1.诗性
钱钟书在《围城》的电视编导来访时,一句话便回答了改编电视剧如何忠于原著的问题:“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信息)无独有偶,江枫对形式的重要性也一再做出了强调,“诗歌形式并不止是内容的外衣、信息的载体,在多数情况下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就是信息。”他还认为,“可以说,诗之成其为诗,并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是怎样说的;译诗,就不仅要译出它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译出它是怎样说的。”文本的形式,尤其是唐诗的形式,包括对仗结构、部分功能词(如介词)的省略、物象的自由关系等等,具有“信息性”,且能够自然地把实境推动到虚境的呈现,这就不是纯粹对内容做语际转换的译诗可以代替的了。
面对唐诗外译理论或主张强调“意译”“优化”“美化”时,译者需要思考中国诗词的“诗性”,即使一首诗得以成为诗的东西。在《现代俄国诗歌》一书中,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性”这个概念。他指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得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诗性”只围绕形式做讨论,“诗性”所涉及的是从实境,即表层意到虚境,即深层意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上文分析的语词、对仗结构、读诗“逻辑”等形式层面上的东西,以及意象、意象内在联系、字句的画面性等内容层面上的东西。至于音韵、节奏等,在此笔者并未将其纳入“诗性”的范畴。萨丕尔(Edward Sapir)曾论述过几种语言的诗律特点,其中对法语和汉语诗律的概括如下:法语音节本身响度很大,但音量和重音起伏不大,因此音量或重音节律在法语中很不自然,所以法语韵律的发展只能定格在单位音节组的基础上——因而,元音叠韵和尾韵都是作法语诗歌的必要手段。唐诗较之于法语,汉语音节是更加完整、更加响亮的单位,而音量和重音则变化无常,不足以构成节律系统的基础。所以,音节组,即每一个节奏单位的若干音节数目和押韵是汉语韵律里的两个控制因素。而第三个因素,平声和仄声的交替,这也是汉语特有的。总的来说,法语诗取决于音节数和押韵的原则;唐诗则取决于音节数、押韵和平仄对比的原则。由此可见,法语诗与唐诗就音律而言是先天就有所差别的。对此,程抱一还是尝试性地采用了“/”来处理节奏的问题,如“国破山河在”这一句,程抱一给出的逐字对译译诗如下:Pays briser / mont-fleuve demeurer。该方式是仿照了五音节诗的节拍停顿,标出了“/”的符号,即“/”前后的briser、mont以及结尾demeurer应是重读的;然而其应用是有限制的,几乎只能用于逐字对译中,并非每一首诗都可以如此套用。也正是认识到了这点,程抱一在意译的译诗版本中并未延续“/”符号的使用。不同诗语言的韵律和节奏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倘若归化地为译诗加上法语诗歌常用的尾韵,不得不改动他处来迁就这种押韵,那么结果恐怕会与还原原诗的本意大相径庭。综上,笔者认为,韵律、节奏等形式并非“诗性”中所必然包含的,而只是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译者在进行唐诗外译实践时,应将目光着重放在能使实境化为虚境的“诗性”上。
2.还原虚境
实境不外乎是表面即能见到的和诗人写出来的东西,但它不是古典诗词的绝妙所在。诗词之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所谓“意”,都是指可感而不可尽言的情境与状态,是作者用多重思绪或情绪,而读者得以体验这些思绪或情绪的美感活动领域。这个领域,要用语言去“存真”。读诗,必须在活动上近似诗人观,“感”事物时未加概念前的实际状况。为此,这“存真”就要存实境与令实境得以达成虚境的事物之真。叶维廉曾一度强调过“感而后思”,不外乎是“感”实境而思“虚境”。实境是诗中一个个意象和字词的总和,“思”的是“诗性”里包含的所有诗语言特点。当这两点皆能达成时,虚境就会呈现出来。
庞德(Ezra Pound)在《论中国诗歌》中认为,中国诗歌有几个难忘的特点,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诗歌比较委婉和含蓄。他说:“中国诗歌同我们西方诗歌第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中国读者喜欢那些发人深思的,甚至让人迷惑、意义模糊的诗歌。”的确,与西方诗歌比较来看,唐诗是模糊而含蓄的。其“模糊性”使读者能够在诗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重新体验诗中那些事物或事件。而为了达成事物与事情的存真,诗人利用了文言特有的“若即若离”、高度的语法灵活性,以此提供一个开放的领域,让读者进入去感受这些活动提供的多重暗示与意绪。所以译者的翻译实践,应该避免“以思代感”来确定化、单一化读者应有的“感”的权利,反而要设法重建作者的经验和由经验到传意的策略,即实境与“诗性”,从而真正地还原原诗虚境。还原虚境,这便是唐诗外译时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种方法。
结 语
通过对文中三个诗例译本的比较与分析,笔者揭示了唐代律诗外译实践中,面对语词、对仗、字句、“逻辑”到意象等内容形式时,译者采取不同处理方式所带来的效果,揭示了“诗性”,即诗的特殊形式与内容因素在虚境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论证了译诗时保留实境与“诗性”的必要性,并由此得出了还原虚境是律诗外译的一条途径。唐代的律诗是最享有灵活自由的文本形式,文字、语法、意象隐喻等一切形式与内容的自由都是为了邀请读者自如地参与诗词深层意的重现与阐发。为了保证原诗与出发语读者之间这种“自由”关系在译诗与目的语读者关系里能够再现,译者需要考虑原诗实境的重建和“诗性”,即诗词特殊形式和内容的移植,同原诗作者一样,向目的语读者发出“身临其境”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