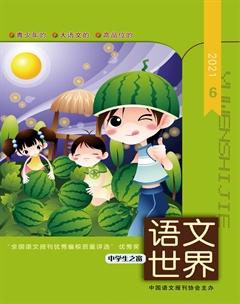生命的方向
王曼昱
生命中有一些事件是偶然,但更多的结局是必然。
做语文老师二十一年了,第一次认真回望人生,到底是什么让我热爱了文学,并走上了语文老师的道路呢?冥冥中总有一个人或一种力量影响着生命的轨迹。
我的爸爸妈妈家庭成分是地主和资本家,因为这个他们在婚姻问题上很受歧视,很晚才相识,彼此不嫌弃,34岁才结婚。我姥姥经常提起一件趣事:我爸爸第一次登门,为了彰显自己改造良好,和贫下中农一样以艰苦朴素为美,特意在衬衫胸口处缝了一块补丁。姥姥暗中窃笑,这孩子都不知道衣服哪里容易磨坏。
几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让他们远离学校,远离书本,对于热爱学习、立志要搞理工发展实业的父母来说是残忍的,更是一种折磨。家里至今保留了他们高中的课堂笔记,工整但陈旧,四角号码字典都磨毛了边,那是他们漫长知青岁月唯一的读物。长大以后的我,从他们身上更能理解伤痕文学的沉重。有一次我给爸爸读张贤亮的《绿化树》,里面的一处细节是主人公章永璘怎样利用视觉误差来做饭盒,从而能多打些食物。爸爸流泪了,他说你当作新奇的情节讲给我听,其实那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瞬间,我明白了张贤亮的小说细节打动人心,是因为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写的是他真实生活的体验。文学作品能打动人的,有时是建构在生活真实上的细节。
这点阅读体验影响了还懵懵懂懂的我。我5岁半就上小学了,那个年代国家要求7岁上学。我猜妈妈总是有点时代的阴影,觉得早点上学抢出来点时间。因为她和爸爸都是高三赶上“文化大革命”停止了高考,要是早一年就可以上大学,不用下乡浪费时光了。我是班级里最小的孩子,做什么都慢,经常放学回不了家,因为作业没做完。班主任劝我明年再来上学,我的妈妈领着我给老师送了一只大公鸡,我才磕磕绊绊地留下来。现在回想多么纯朴的时代,觉得给老师添麻烦了,能把孩子留下特别感激。可是这导致我上学的阶段总是比同班同学小两岁,什么都比别人学得慢,我老觉得自己又笨又傻,十分自卑。是语文课拯救了我,让我慢慢找到了自信。
上小学,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写自己身边喜欢的人。同学们大多写老师、母亲。我也写,但更多的是写不同的人:大杂院里的邻居、学校传达室的爷爷……有一次我写的《党奶奶》成了年级范文。党奶奶是大杂院里的邻居,六十多岁了,她没有正式工作。她没读过书,因为她是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所以姓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煤气的时代,给大家运送烧煤赚取生活费。我写党奶奶怎样運煤,怎样卸煤,也写党奶奶完成工作,回家认真清洗、打扮自己。她每个皱纹里,鼻孔里都是煤灰,指甲里黑乎乎的,但是党奶奶总是会用废旧的牙刷一遍一遍刷着指甲缝隙,再抹上厚厚的蛤蜊油。最后党奶奶总会对着镜子戴上鬓卡,干干净净,温柔慈祥。小小的我初次体验了另外一种人生,60岁的老人在那个瞬间是那样的美丽和坚强,苦难中更有生命的高贵。
老师说喜欢我写的“刷”指甲的细节,既真实又感人。长大后我明白,当我们不懂得感受生活时,生活就是事件,我们就是过客。但是在我小心翼翼写下生活的感受时,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细节就成了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体验,这些美好的体验就构成了生命的意义。
我做了老师,教学生写作文,最常强调的是要学会捕捉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没有生活,怎会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呢?
可能是因为人大多有补偿心理,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爱借书、买书、读书,也特别喜欢向我推荐书。我生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文学市场还很贫瘠,小人书是我童年最好的读物。《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这些小人书图文并茂,我都收藏到柜子里,还放了樟脑球,长大了还传承给我的表弟表妹,后来还经常去检查他们是不是像我一样善待这些宝贝。我最早的中国历史框架,就是小人书帮我构建起来的。
小时候冬天雪很大,我的妈妈从单位骑着自行车回家,身上有路滑摔到雪地的泥渍,但棉花包里从单位阅读室借的书却暖暖乎乎,还散着墨香。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工资都很低,每月大约三四十块钱,月末精粮的粮票配额吃完了,就得去买粗粮吃,每月的二两肉票都不舍得买瘦肉,要买肥肉,做成油滋啦炒菜吃。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也从没缺少过书读。借书成了我们家最频繁的事,以至于哪个单位图书室书多,哪个单位进新书了,是我们家经常打探的事,妈妈觉得我的童年绝不能缺书,饭菜可以粗糙,但书籍一定要丰盈。
有一次大杂院其他家着火,蔓延开去,大家都冒险回屋抢救财物,我妈妈顶着浓烟抢出来的第一件就是我的书包,之后火势太大,就再没敢进去。我在院外大哭,看到抱着我的书包冲出来的妈妈泪流不止,妈妈却淡淡一笑说,没事,明天别耽误上学。院子里的老邻居至今还津津乐道,你看人家读书的人就是不一样,你们抢的都是存折,人家把孩子书包先抢出来。
长大后我明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妈妈心中留下的伤痕,读书上学是这以后她心中最为至高无上的事。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了我,以至于很多朋友都说我身上有点视金钱为粪土的清高,其实我和妈妈一样,有些东西,觉得比金钱重要罢了,金钱也好啊,可以买书吗。
因为青春期被家庭成分打压,妈妈养成了内向的性格,甚至有些怯懦,但她竟然为了借书结交了很多单位的图书室管理员。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里,下了班骑一个小时车去串门,就为了给我借本新书。《海蒂》《海底两万里》,这些外国引进书籍,我在当时就能最先看到。
因为我们家书最多,我成了大杂院里的故事大王,讲故事给小朋友们听成了童年生活中有趣的记忆。前几年《海蒂》电影重拍了,儿时小伙伴还惊喜地相约一起去重温电影,还能回忆起可爱的海蒂、慈祥的海蒂爷爷。我觉得,与其说是重温电影,不如说是怀念童年,因为一本书,我们有了共同的童年记忆。
后来我有了零花钱,总会用来买书,看书前一定要洗手,我喜欢书干干净净。我觉得父母爱书的习惯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做了老师,也喜欢向学生推荐书,遇到共同喜欢的作者,还会有知音之感。学生也会向我推荐书,年轻人的视野拓宽了我的阅读领域。我们一起读,也一起写,学生们的创造力总会让我惊喜不已。我推荐他们读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他们就创造出《这是六点钟的校园》,描写上完晚课奔赴食堂的饥饿和奔跑。我推荐他们读舒婷的《致橡树》,他们写《致母亲》,抒发渴望平等尊重的母子关系。我把他们的创作结集,学生们主动作443字的长诗《青春不散场》作跋,写作已成为他们自觉表达情感的方式。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读书的力量,这种力量妈妈赠予了我,我将忠实地传承给我的学生。
在阅读中体验生活百态,在写作中传达生活感悟。妈妈、我、我的学生都用文学拓宽了自己的生命,丰富了自己的灵魂。文学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态度。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的成长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富强与繁荣。如果说妈妈爱书的习惯影响了我至今,爸爸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热爱旅行。爸爸总会利用各种闲暇带我出去走走看看,并用最朴素的道理教育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一次出远门就是爸爸带我去北京,那时是1983年,我五岁。那时候还没有因私旅游,出门住旅馆需要用单位介绍信。我现在还有模糊的记忆,天安门、长城、故宫,祖国和历史这个概念估计就是这次才有的吧。
长大之后的我明白,其实读书和旅行就是让我们总有一个灵魂在路上。一个没有看到世界的人,怎么会形成世界观呢?
我也常常把自己出行的感受和我的学生分享。我去壶口瀑布,我和学生说:黄河既有摧枯拉朽的毁灭,也有浴火重生的涅槃。我去罗马,走在凯撒归来的石砖路上,道路两旁是地中海油松,笔直高大,像罗马军团的士兵。我和学生说:这是配得上凯撒的树,就像子美写昭君是“群山万壑”,苏子写周瑜是“惊涛拍岸”,英雄的出场总是不同凡响。我去凡尔赛宫,我和学生说:欧洲园林是入世而理性,江南园林是出世而抒情。一个讲求霸气,一个追求诗意,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我去新天鹅城堡,我和学生说:新天鹅堡的主人路德维希临终时才41岁,他的人生就是一出安错人生位置的悲剧,否则他可以像瓦格纳成为音乐家,李煜可以像柳永成为词作家,宋徽宗可以像唐伯虎成为画家,他们都能流芳千古。后来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还开设了校本课“中西文化比较”“中外小说比较”。我鼓励学生:大师都是学贯中西,苏州博物馆的古典与卢浮宫金字塔入口的现代是因为贝聿铭老先生既有童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青年留学海外西方文明的洗礼。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涉猎中西文化,开阔视野,形成多元的价值观。
高中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文学创作,并且尝试写小说和剧本,我想考北京广播學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电影电视编导系,我想记录生活,更想分享生命体验。我写了很多校园文学作品,写青春期男孩儿、女孩儿的懵懂与梦想,也写他们的羞涩与脆弱。因为种种特殊原因,最后我与北广失之交臂,走进了师范大学。虽然有很多委屈、愤懑与失意,但我依然选择了中文系,冥冥中命运之手把我推向了讲台,文学依然是我生命的重心。虽然经历了17年来人生的最大挫折,虽然生命的轨迹和预期不同,但也许这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热爱阅读,热爱写作。无论我去哪所大学,从事什么职业,这一点都不会改变。只不过今天我有了更重要的使命,影响更多学生也热爱读书和写作。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不忘初心,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