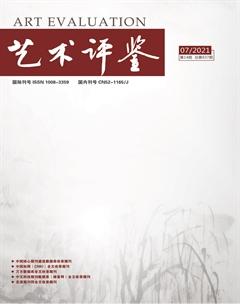略论周稚廉戏曲作品的叙事艺术
张雪纯
摘要:周稚廉是明清文人传奇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文学成就甚高,被时人认为可与关汉卿、汤显祖等比肩。周稚廉一生创作了大批优秀剧作,然传世的仅有《容居堂三种曲》,为清传奇的代表之作。本文拟从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时空和人物塑造等五个方面探讨周稚廉戏曲作品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周稚廉 《容居堂三种曲》 叙事艺术 明清传奇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4-0158-03
周稚廉的《容居堂三种曲》作为明清传奇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叙事艺术上既有明清传奇叙事方式的共性,同时也呈现出了其自身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具体剖析《容居堂三种曲》在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时空和人物塑造等五个方面的叙事艺术,探讨明清传奇在叙事上的共同特色,挖掘出周稚廉戏曲创作的独特性。
一、叙事主题
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戏曲作品,这些剧作家思想的复杂性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戏曲是他们针砭时弊、传达思想的重要途径,因而戏曲中的叙事成分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这些作品中传达出的关于思想教化、朝代兴亡、情与理的碰撞等一系列叙事主题,这些无一不反映出戏曲家们为戏曲情节化做出的不断努力。
戏曲家们大都极为重视戏曲的教化功用,高明曾在《琵琶记》中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周稚廉的作品即是忠孝节义教化题材的代表之作。“明清传奇呈现出了三种不同倾向:一是对教化主题的机械图解方式,传奇多从抽象的主题入手而相应的地设置出故事情节与人物;二是通过传奇反映生活的真实,教化目的通过生活中的实例而自然地归纳出来”。周稚廉的作品显然是第二种,不再是直白的教化,而是用带有良好品质的艺术形象施以隐喻,注重作品的故事性,逐步接近叙事化的戏曲创作。《珊瑚玦》中的晏继光即是忠与孝的化身。他主动进入敌营,成为卧底,最终消灭贼人,后又努力找寻自己的亲父。虽然也是以教化为旨意的作品,但整个故事符合生活逻辑,对人物的刻画也鲜明生动,不再是单纯为了教化而塑造出一个生硬的人物与背离生活逻辑的故事。
周稚廉的作品还显露出了对奸臣权相的批斗以及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注。《珊瑚玦》中的晏继光、《元宝媒》中的乞儿都体现出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双忠庙》则批判了宦官刘瑾的专权误国。由于思想局限性,如周稚廉等一批戏曲文人终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平民的关切之意,却无力解决现实中的实际困境。但尽管如此,对平民阶层的深入关注使得作品的叙事性大大增强,这样的作品更易被观众接受。
二、叙事结构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了“结构第一”。“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李渔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对剧作的整体构思与布局。在开始创作之前,首先要形成一个框架。戏曲作品篇幅有限,不可能做到枝枝节节为之,即“立主脑”“减头绪”。周稚廉的作品对结构的运用已臻成熟,大多采用双线结构。双线结构在明代已经被戏曲家们使用,但当时还处于初步阶段,及至清初,戏曲家们有了前人丰富的创作实践支撑,在情节的架构上更加完善自然。周稚廉的《容居堂三种曲》都采用了双线叙事的结构手法。《珊瑚玦》中,卜青与祁式分为两条叙事线,剧作开端两人共同逃難,后在战乱中离散。其后两条线并进,又以祁式为主线。剧作最后晏继光凭借珊瑚玦找到卜青,双线合一。《元宝媒》中的两条线索为乞儿与陶湘珠、乞儿与淑珠。《双忠庙》则把舒真和王宝、石氏和廉小姐分作两条线。纵观这三部作品,虽为双线叙事,但两条线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各行其是,而是彼此穿插、相互联结的。《元宝媒》中,乞儿先是救了淑珠,淑珠成为皇妃之后赐予乞儿元宝,乞儿以元宝救助湘珠,环环相扣。这种叙事手法使得传奇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有利于展现更丰富的人物形象。
周稚廉的剧作在结构手法上运用了很多叙事技巧,既包含了对忠孝节义、惩恶除奸的教化,也同时兼顾了曲折、突转、误会及巧合等剧作技巧的运用。误会与巧合的剧作手法在戏曲作品中比比皆是,巧合促成故事发展,而误会往往用来延宕。《珊瑚玦》中,卜青与妻子曾各持一半珊瑚玦作为信物,二人离散之后,卜青由于巧合刚好来到晏府做了马夫,才得以被祁氏认出。道具的运用也是周稚廉结构技巧的一大特色。珊瑚玦既象征了离散,也象征了团圆,承载着主人公或喜或悲的情感。通过信物珊瑚玦贯穿起整部剧作,对传奇作品而言无疑是巧思了。同样是在《元宝媒》中,元宝作为整部作品的一个重要道具,与主人公乞儿的命运休戚相关。乞儿因救助淑珠被皇上赏赐元宝,又因用元宝救助湘珠惹出是非,最终迎娶湘珠并成为了皇亲国戚。元宝这一道具使得剧情得以不断向前推动,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三、叙事模式
戏曲的“曲本位”思想使抒情性成为了戏曲艺术的一大主要特性,剧作家们借剧写心,在作品中大力抒写褒扬或批判之情。在研究明清传奇作品时,往往对抒情成分的关注多于对叙事模式的关注。但明清时期的剧作家们实际上对故事模式做出了很多尝试,其中运用最为频繁的主要有误会与巧合、道具与超自然因素,这三种模式分别在周稚廉的剧作中得到了体现。
超自然因素为戏曲创造了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实现了相当大的创作自由,或为鬼魂、或为神灵,他们身上往往寄寓着剧作家们的深层思考。《双忠庙》中,公孙杵臼与程婴是双忠庙里的两位神仙,这两个人物形象均取自《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与程婴为救赵氏孤儿,前赴后继的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忠义之士的代表。《双忠庙》将二人写作保护凡间具有忠义精神之人的神仙。在宦官刘瑾及其党羽祸害舒真与廉国宝一家时,公孙杵臼与程婴感念王保救护舒真之子的忠勇,赐予其乳汁以哺幼婴,又赐予放走廉小姐的骆善胡须,使其避于朝廷追杀。超自然因素的运用即是将虚幻的事物展现出来,让其在戏曲空间里成为真实。这种手法往往易于被观众接受,这些虚幻的事物寄托着人们心底深处的殷殷期盼。在封建传统的控制之下,戏曲家们无法自由表达出心中所思所想,只能借由神灵或魂梦传递出来。
误会与巧合是中西戏剧家们都惯常使用的一种叙事模式。所谓“无巧不成书”,随着传奇作品的不断发展,新传奇之所以能够精彩于旧传奇,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传奇愈发强调误会与巧合的写法,为传奇作品增添了故事性与曲折性。周稚廉的作品也采用了此种叙事模式,并且并不显刻意。《双忠庙》里,由于乳娘王氏自尽,徒留孤苦无依的廉小姐一人,恰好廉小姐遇到的是心怀良善的太监骆善,廉小姐才得以逃脱。骆善与廉小姐以卖字画为生,又刚巧与舒家公子相逢,舒家公子向骆善拜师学画,并与廉小姐成亲。这一系列的巧合自然流畅,符合生活情理。《珊瑚玦》中,卜青与祁氏在战乱中离散,祁氏进入晏府,晏夫人多年无子,遂将祁氏之子过继在自己名下,起名继光,并予以抚养。若非晏夫人无子,晏总兵不会想纳怀有身孕的祁氏为妾,晏夫人也不会过继祁氏之子。继光长大后,一直努力寻找生父卜青。战乱之后,卜青一路流散,巧合之下,行至晏府,在晏府谋求了一份喂马的差事。卜青喂马之后在檐下休憩时露出了自己的那一半珊瑚玦,被游逛花园的祁氏所见,遂得团圆。《元宝媒》同样运用了多重巧合。乞儿乐善好施,救助了父母双亡的刘淑珠,淑巧遇天子,成为妃嫔,深得天子宠爱。乞儿一路辗转,与跟随天子出巡的淑珠一齐来到大同,饥寒交迫的乞儿在此巧遇淑珠。淑珠向天子陈情,得到了一个元宝的赏赐。乞儿行至大名府时,用天子赏赐的元宝帮助湘珠,且未料被误以为偷盗官银,所幸最终真相大白。误会与巧合在这三部剧作中占比甚多,成为了情节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是构成“发现”与“突转”的必要方式,为剧作家们编排故事创造了巨大方便。
道具的运用也是周稚廉戏曲作品的一大重要特色。在《容居堂三种曲》中,《元宝媒》和《珊瑚玦》都使用了道具作为叙事手段,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得到了很大增强。道具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爱情剧中充当男女之间情感联系的信物,一类是贯穿全剧中心事件与主要情节发展变化的重要道具。《珊瑚玦》中,珊瑚玦是卜青与妻子祁式感情的信物,二人随着珊瑚玦的分裂而分离,最终由于珊瑚玦重逢。借用珊瑚玦这一道具作为剧作的名字,隐喻了人物的悲欢离合。珊瑚玦也是构建全剧的重要线索,若是没有珊瑚玦,改名成韦正的卜青与祁氏恐难以相认,无法成就最终的大团圆结局。这种金玉之类的配饰,或诸如手帕、丝绢等,常在才子佳人戏中作为爱情的象征。《元宝媒》中的元宝则是贯穿全剧重要转折的重要道具。主人公乞儿的命运与元宝紧密连结,乞儿获赐元宝,却因用元宝帮助湘珠而身陷牢狱,生死攸关。天子意识到赏赐元宝行为的不妥,派人前去探访,救乞儿于牢狱,并给乞儿和湘珠赐婚,可以说乞儿是因为元宝才成就了自己与湘珠的一桩良缘。不同于珊瑚玦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元宝仅作为发展延伸剧情的道具,作品的叙事性大大增强。
四、叙事时空
戏曲创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登台演出,而不能仅作为“案头之曲”。舞台演出的特性要求戏曲作品须高度关注时间与空间的调配。“明清传奇表现出来的时间处理的总体特性是整体上加以极大地压缩,而在局部段落中又往往加以渲染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这种压缩和延伸是基于故事时间和情节时间完成的”。一个完整的戏曲故事时间长度可达数年,但搬演到舞台上时就要进行大幅度压缩。《珊瑚玦》中,卜青自与妻子离散到重逢历经十几年的时间,剧作家需要对主要的事件情节多施笔墨,对无关紧要的事件予以删减。写到卜青至军营寻找祁式,随后情节直接跨越至十几年后,中间的十二年全被省去,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叙事的集中性,使观众对故事保持兴趣。
传奇对空间的表现也很自由。不同于西方戏剧的写实性,戏曲在空间的控制上更为灵活,往往以演员的表演决定空间的转换,不像西方戏剧一般将人物的活动限于一个固定的场所,空间的转换需要重新更换场景道具。但戏曲虽然在时空的设置上相对自由,却也不是毫无逻辑的肆意转换,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变换时空。《双忠庙》里,王保与石氏互为两条线索,处于不同的时空。第九出《出乳》与第十出《依侄》在舞台不变的情况下完成了空间转换,二者全依靠于剧作家对戏曲人物语言和动作的编排。
五、人物塑造
作为宣传忠孝节义的教化之作,周稚廉三部剧作中的人物塑造难脱传奇作品中人物形象类型化的窠臼。《双忠庙》中的舒真与廉国宝均为至忠之人,他们不畏强权,大胆进谏弹劾奸臣,即便因此家破人亡。二人死后,舒真府上的王保和廉国宝府上的石乳母继续将这种忠义精神发扬下去,竭尽全力保护舒真与廉国宝的后代。《珊瑚玦》中的祁氏则是忠贞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祁氏与卜青走散,遇到晏总兵,在晏总兵因无子欲纳其为妾时,祁氏秉持着“一女不事二夫”的思想坚决不从,毫不畏惧晏总兵的权力。为了孩子更好地长大,即使心有不舍,还是将孩子过继给晏夫人,甚至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如此隐忍了十几年才得以一家团聚。《元宝媒》中的淑珠与湘珠也是美好女性形象的代表。淑珠父母双亡,得到乞儿的救助后一直感念于心,时刻不忘恩情。得到天子宠幸后仍旧不断寻找恩人乞儿的下落。湘珠出身贫困,被迫进入员外府为婢,员外想要霸占湘珠时,湘珠因不舍母亲独自受苦,放弃逃走的机会。这样心怀良善的人最终都收获了美满的结局,这也是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常用模式。
《元宝媒》中的乞儿形象凸显出了周稚廉人物塑造的独特性。戏曲作品在营造侠义之士的形象时,很少会将侠义精神放在一个乞丐身上。乞儿虽行乞,但绝不向同一个地方行二次乞讨。他行乞得来的钱物几乎全被用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之人。这样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在过往的戏曲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可以看出周稚廉在剧作构思上的奇巧以及他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关注。
明清传奇历经戏曲家们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在叙事艺术上显现出了系统化的特征。周稚廉的剧作在集合传奇艺术特色的同时,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形象的设置上均呈现出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是兼具文学性与舞台性的优秀剧作。
参考文献:
[1]刘志宏.明清传奇叙事艺术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年.
[2]李渔.《闲情偶寄》卷之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焦艳云.周稚廉及其《容居堂三种曲》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
[4]刘其荣.周稚廉戏剧作品研究[D].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10年.
[5]朱万曙.明清戏曲小说评点的敘事理论建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04):148-158+162.
[6]孙书磊.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J].齐鲁学刊,2004(06):85-89.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校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周稚廉《容居堂三种曲》研究,项目编号:2020XKT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