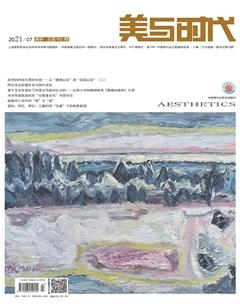基于互文性理论下的语义风格对比分析
王仲男 方环海



摘 要:林少华与赖明珠分别是在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最有影响力的译者。20多年的翻译历程中,林少华和赖明珠二人各自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翻译风格。关于二人翻译作品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学界和读者圈由来已久。立足二者的译本,试从描写、对话以及词语用法方面,总结二人使用语言的不同之处,并从互文性的理论出发,深层次探讨林少华和赖明珠二人译文的不同的成因和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林少华;赖明珠;语义风格;互文性;挪威的森林
一、引言
村上春树作品中展现的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写作风格,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挪威的森林》是他最具代表性、也最为华人熟知的作品,更是很多读者认识村上春树的起点。迄今,《挪威的森林》在世界各国已经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36种语言,发行量高达一千万册。
《挪威的森林》的中文译本有多种,其中最为畅销的中文本译者刚好分布在海峡两岸,其一是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少华,目前是中国大陆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译者之一。王向远指出,“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1]。其二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赖明珠,村上春树小说著名译者,是村上春树作品进入台湾地区的早期推手。她所翻译的作品在台湾地区流传度最为广泛、最受欢迎,藤井省三对赖明珠的翻译做出了“近乎完美的直译”的评价。
作为两位最为有名的村上春树中文译者,林少华和赖明珠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各自形成了极为鲜明的风格。关于林、赖二人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谁是谁非,无论是书迷还是在文学界以及语言界,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随着国内对村上春树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主体和角度也进一步扩展,涉及到了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翻译学和语言学等众多领域。就对“译者”这一视角,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林少华和赖明珠二位身上,但多是从翻译学的角度来展开,即分别对比二人的译文与原著的差异所在,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直接对比二人行文风格的则并不多见。当然,对译者和译文的研究,本来就不可能割裂翻译学和语言学二者的联系,只是在侧重点上略有不同。
不同于文学创作,翻译作品是对已经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这要求翻译者不仅仅要发现原著的风格、理解原著的內容,更要领会原作者传达的思想,并用另外一种语言将上述这些传达给读者。可以说,读者在阅读时,在作品背后站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与读者直接面对的就是译者。本文在此着重就译者与读者这个层面,从描写、对话以及词语用法方面,横向比较林、赖二人在使用中文上的风格差异,总结二人使用语言的不同之处,并从互文性的理论出发探讨林少华和赖明珠二人译文不同的成因和所带来的影响。
二、词汇的选取:林、赖译文的描写差异
邹东来、朱春雨认为,关于翻译的评论无一例外要落回到文字以及文本中[2]。两位译者语义风格的差异,在场景描写部分如何选择语词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描写极为重要,因为人物不得不生活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环境描写很大程度上起着塑造人物的作用。同时,环境描写对于确定整体基调,揭示小说人物的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小说中最能体现作家风格的地方。
村上春树的小说被读者们广泛接受,既得益于他的作品往往能触及到灵魂的深处,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也有赖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能构筑出光怪陆离的世界而引人入胜,特别是几部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如《海边的卡夫卡》《1Q84》等。在这些作品中,场景和环境的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是形成小说中独一无二风貌的重要材料,描写也成为了形成村上春树风格必不可少的元素。《挪威的森林》虽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为主的作品,描写依然在小说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如何处理描写部分,也最直观地体现了译者的翻译风格和语体风格。
纵观二人的译作,林少华在描写的部分文辞更加华美,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使用了大量的四字结构的“固定构式”,尤其是对成语的运用,更使语言简练优美。潘文国认为,汉语音节之所以有如此美的特质,因为汉语具有较强的“柔性”,音节之间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超浓缩力,各个音节的联结几乎是胶着式的,一经合成就凝结为一体了。林少华在使用成语上得心应手,这也将汉语的音韵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相比而言,赖明珠较少使用这种结构,她认为“自然就是美”,所以“在翻译他的小说时尽量不用成语,希望保持他的用意和文意,让中文读起来仍能感觉到村上的特色”[4]。
如林版中这样的一段话:
车沿着溪流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随处可见的晾衣杆上挂着衣物。
相对应的,在赖版中则是:
沿着河谷在那杉林中前进相当长一段时间,……盆地里尽是绿油油的田园,沿着道路旁流淌着清澈的河流。到处都看得见挂着晾衣竹竿。
再如,林版:
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5]
而赖版则是:
两个人都长得很漂亮,好像很愉快地谈着话。……到处聚集着四、五个成群的学生,他们各自针对什么主题发表意见,或欢笑、或喊叫[6]。
两个版本中,可以挑选出很多代表着二人风格的词汇,如下表:
通过上面两段文字以及表格中所列的词语,我们能明显地发现林少华的版本更优美且简洁。他认为,美的极致就是洗练,无需任何累赘。汉语本来就具备简洁性和艺术性,成语更是这两种特点的集中体现,可以说是汉语中浓缩的精华。相比来说,赖明珠版进行直译则略输文采,避免使用成语和过多的修饰,尤其是在需要着笔墨的场景描写中,无法像林少华那样有较强的画面感和四字结构带来的独有的音韵美,但较之林版却多了一分平和清新,也为其增添了一份自然柔和之美,如讲述者坐于身边娓娓道来。当然,不使用成语和华丽的辞藻并不是因为赖明珠的文笔仅限于此,而是源于她的翻译观。
词汇虽小且零散,但却是组成语言的最基本材料。这些词汇进入句子,而句子进入段落,最终就像不同的设计师用不同材料构建的同样框架结构的两个建筑。同一段原文,在不同的两位译者手中形成了这样两种各自风格鲜明且彼此截然不同的文字,以表格所总结出来的词汇选取为代表,二人对词汇的选择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三、句式处理与成分省略:
林、赖译文的对话设计差异
除了描写之外,在人物对话上,二人的译文风格差异也十分鲜明。对话不仅仅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更能直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如何设计对话的风格,也是作家文风的直观体现。总地来说,林少华的译本中,人物对话的风格更加简洁、明快、人物更加鲜活。相比来说,赖明珠翻译的人物对话则更加清新,对话句式语法结构趋向于完整。两位译者对于句式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句子成分的存留,是形成对话风格差异的最直观体现。
(一)林少华设计的人物对话,更加简洁流畅,话轮转换速度更快,前文对话中出现的称呼,在下面对话中经常被省略。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他习惯在对话中省略主语,无论是说话人对听话人还是说话人自己的称呼,这在往来频繁的对话中尤为明显,例如:
再如:
如上文例子,在频繁的对话中省去主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对话更加紧凑,给人以简洁、凝练的感觉,而这也恰恰符合林少华作品的特有风格。除此之外,省略主语可以使对话的口语性更强。很多人批评赖明珠翻译的作品较为生硬,有种“翻译机”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话的设计所导致的。
(二)林少华在对话中的问句的处理上,较少使用疑问句的标志性词语,如“怎么”“为什么”等疑问代词以及提问语气词“吗”,但保留疑问句的句号作为疑问标记。如此一来,这些发问的句子就成了带上疑问语气的陈述句。其中,多数问句含有能愿动词,如“能”“可以”。相比来说,赖明珠在问句的处理上则较为传统地使用常规形式的、结构完整的疑问句。例如:
再如:
林版对话中不使用疑问词和语气词,意在表现同不加主语相类似的效果,使对话更简练。然而,江海燕认为很多疑问句中“吗”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疑问语气信息,去掉则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提问的效果,特别是如果在口语中没有了标点符号的加注,对没有疑问代词和疑问标记“吗”的句子,听话人并非总能很好地判断是否在表达疑问的意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章的口语感[7]。
无论是习惯于省略称呼还是省略疑问词,林少华在翻译人物对话的时候,集中体现的就是“简洁”两个字。他在《挪威的森林》的译序《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中指出,村上春树的风格既是“简洁、明快、清爽、流畅,而又独具匠心,韵味绵长,丝毫没有传统日本小说那种无病呻吟的拖沓,那种欲言又止的迂回,那种拖泥带水的滞重,那种令人窒息的汗臭”。他还举出他翻译村上春树另一部作品《舞》中的一段话:
“结婚了?”“一次。”“离了?”“嗯。”“为什么?”“她离家跑了。”“真的,这?”“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了。”“可怜。”她说。“谢谢。”“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怎么个理解法儿?[5]”
这段对话可以说既能十分鲜明地反映了村上春树写作的风格以及林少华翻译的风格,更能凸显出林少华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认识和自己翻译观的认知。
(三)林少华在对话中经常使用文言句式,在对话中,能言简意赅地表达说话者的意思。
如林版(41页):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赖版则是(48页):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呢?”我吃惊地问。
再如林版(42頁):
而显示他具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
赖版(49页)则是:
显示他具备……“这男人是个特殊的存在”而敬畏他。
林少华本人重视比较研究中日古诗歌,因而在翻译中也较喜欢使用古诗文。使用文言,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译文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用最少、最简洁的话语准确地传达文意,也能通过这样的对话让文中人物更加生动、立体。然而,对现代感十足的小说,尤其是像《挪威的森林》这样受欧美文化影响较深的作品中,使用文言是否恰当,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正面效果,则是见仁见智的。正如赖明珠所说,村上春是本人是一个“穿着T恤的”现代人,对于林少华使用古文她认为“好像把村上穿上了唐装”,读者虽较容易接受,但“那已经不是村上春树”了[8]。
四、互文角度下的语义风格差异
互文性理论源于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一理论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基础,因而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的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
互文性理论庞大复杂,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不断地对互文性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也形成了诸多流派。一般认为,互文性理论可以大致界定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互文性,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他们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而狭义的互文性,以热奈为代表,认为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
互文性的理念不仅重视文本,更重视文本所辐射到的任何元素,包括作者、读者、批评家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延伸到翻译中也是如此。而在这一视角下,我们考虑的翻译也必须跳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转换即“语际翻译”的范畴,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两版不同翻译作品背后的成因。
读者和学界关于林氏村上和赖氏村上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看似这也是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而事实上,从互文性角度出发,无论是林氏村上还是赖氏村上,它们都与原版的村上是一种互为文本的关系——原版为前文本,译本为文本。二者作为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也处在一种互为文本的关系当中。在同一种语言背景下的同一部作品出现的两个译本,并非要以有你没我的姿态针锋相对。二者的互文关系,无所谓谁是前文本谁是后文本,实际上一版的存在加强了另一版的存在,一版的存在突出了另一版的独特性。因为有着林少华版村上的存在,赖明珠版的村上的特点才被凸显出来,得以成为独树一帜的风格,反之亦然。越来越多的关于村上春树中文译本研究,在涉及到一位译者时总会出现一名或多名其他译者用以对比分析,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于接触同一部作品的多个版本,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互文性更加重视文本的作用,也更加重视读者、文化、社会、批评家等多方面的作用。在互文性延伸至翻译领域后,也格外重视译者的作用,认为译者的声音是十分活跃的。译者进入原作并产出译作,这本身就是具备较强的对话性。译者的痕迹与他人的痕迹,建立了一种全新又独特的关系,它会打断他人的讲话,但不会掩盖他人的声音,因而我们在阅读译作时,亦会发现其较强的风格。这种风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和传递,不仅要求译者具备过硬的双语能力,也要求译者有能感知前文本互文性的能力,并将这种感知传达给读者。不同的译者,其感知能力不同,也就造就了不同风格的译本。而这种感知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二位译者翻译观不同所带来的结果。二人对于翻译的理解,直接决定了译作的风格。
林少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大部分文学都是艺术,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不是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对于“信、达、雅”三项标准,林少华认为“雅”最难做到,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据此,他强调“100%原装村上”是不存在的,只能“组装村上”。林少华乐于使用华美的文辞,源于他对文体和语言风格的重视。他十分推崇语言修辞的“自觉性”,认为这是值得“贊扬和重视的”[10]。对于原版村上春树小说中的风格,林少华认为村上春树所使用的带有英文翻译腔的日文,本身不像传统日语,因而翻译应该使之不像以往翻译过来的日本文学作品,尽量消解人们所熟悉的日文式翻译腔。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林少华版村上独特风格的根源所在。对于有些人质疑林少华对文章进行了美化和整容,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前言”中说:“翻译不同于数学,1+2可以等于任意数。”而赖明珠则认为,“信、达、雅”中“达”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信”和“雅”都需要斟酌而来。她把作家比作咖啡,认为“咖啡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香味,作为一个翻译者,应该像无色透明的白开水一样,尽量把不同咖啡的原味表现出来”[8]。她认为本来日文和中文就具有不同特性,一般说来日文比较优雅柔和,中文比较简洁有劲,日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时,最好尽量保留日文的特色,如果只以中文的标准来评断译得好不好,可能不一定适当。
很有意思的是,赖明珠的《挪威的森林》也有很多版本,原版与修订版也有所不同,从中可见赖明珠本人对翻译文本的游移。比如:
我为了不让头涨得快要裂开,而弯下身子用双手掩盖着脸,就那样静止不动。(旧版,页7)因为头胀欲裂,我弯下腰用双手掩住脸,就那样静止不动。(新版上册,页8)
在这里,赖明珠“新版里”运用了四字结构短语“头胀欲裂”,而不再运用“头涨得快要裂开”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见赖明珠与林少华的译本之间并无什么绝对的对立。
我们看来,互文性更加重视文本的作用,也更加重视文化和读者等多方面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二位译者的作品都是成功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大部分不懂日语,无法阅读原版,即使有些读者有一定日语基础,也很可能因为水平原因无法充分理解原著的神韵。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承担了更多的使命。读者对村上的认识,其实就是对译文所表现出来的村上的认识。二位译者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群中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读者们通过阅读他们翻译的作品认识村上春树、热爱村上春树,其实正是对他们作品成功的最好印证。互文性是技术和客观的结果,它是记忆文学作品的结果,这种记忆文学的努力是长期、微妙、有时又是偶然的。作品本身的独立和个性取决于它和整个文学之间可变的联系,在这种变化中,作品描画出自己的位置[11](蒂费纳·萨摩瓦约2003)。诗应该由众人写成,像村上春树这样优秀的作家,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日语读者群之间,而是进入各种文化形式之中。翻译家和翻译作品,就是这个“可变的联系”,是村上春树作品与这个世界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组成村上春树这个文化符号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五、结语
金兵,刘青梅认为,林少华和赖明珠二人翻译风格迥异,这是由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12]。一般认为,译本是译者根据自己的解读,将原著再创作的结果。而在翻译过程中究竟是应将自己和目的语的风格带入到译本当中,还是应在译本中保留原版和原语言的风格,即“归化”和“异化”的问题,直至今天,学界依然没有定论。林少华与赖明珠二人,实际上也是一种“归化”和“异化”的交锋,如有关使用习语和文言方面,二人的看法就是背道而驰。
从日文到汉语这个过程中,在翻译观的指导下,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再创作的“度”的把握,而这也造就了两个版本巨大的风格差异。诚然,普遍认为林少华的作品有更多的自我发挥而赖明珠的作品尊重原版,但正如林少华所说,纯净水的翻译根本是不存在的,区别只在于“林氏村上”和“赖氏村上”。林少华版本的村上充满了十足的自我风格,但我们不能认为赖明珠的作品缺乏个性,这种尊重原文的习惯,使赖明珠汉语译本的语言上整体偏自然清新,这也正是赖明珠在日中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己的风格所在。只是,这种风格并非一种张扬的、强烈的,因而往往被读者们所忽略。
但是,有人质疑,正如赖明珠将原文一一对应地译成汉语以后,是否也能将原文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准确地传达了呢?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认为,汉语将所有的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也因此,“象喻”是汉语本质在具体运行中的外显。在我们看来,在林少华和赖明珠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背景下,“林氏村上”意在用这种外显的方式,通过语言的解构、重组和修饰来传达的是村上春树的气质,而“赖氏村上”在尊重原文的翻译观影响下,则是使用一种内隐的方式,将村上春树独特的韵味隐藏在看似平淡自然的文字背后,等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品味出。这种内隐的方式,也是一种平静之美。
法国的纪德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把莎翁的原文语句“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翻译成“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这就涉及到“达其意”与“传其神”的问题。英法两国对如何描写“静”的状态,认知并不相同,法语中用“猫”来形容安静的状态,而英语中则习惯用“老鼠”来形容。若将莎翁的这句原文翻译成中文,大概法语里的“猫”、英语里的“老鼠”都不行,应该译为“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或者直接用一个成语“鸦雀无声”。类似地,赖明珠如果尊重原作,只是为了“达意”,而将莎翁的句子依据原文译为“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这样的汉语表达不是显得很奇怪吗?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莎士比亚的表达习惯,这样的直译倒是不会犯错误的。
不过,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跨文化过程,无法忽视译者在翻译时的创造,因为原始文本的适应是基于他者文化的需要[13],而不是为了翻译文本,可以说是外国文化、异文化的移植至另一文化,并被该文化接受、演绎的过程与结果。可见,《挪威的森林》的初始状态只是为了日本的读者而并非为了说那36种翻译语言的人群而创作的,所以林少华的“传神”某种程度上看,应该更得翻译的精华,甚至也更得汉语之精华,其字里行间充满的也是汉语的智慧。所以,与其说林氏的“村上春树”有自我风格,还不如说更具有“汉语文化风格”;与其说赖氏“村上春树”尊重原文,还不如说所具的是“日语文化风格”。用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名言来说,林少华是“六经注我”,赖明珠则是“我注六经”,两者之间的结合与博弈,或许正是翻译学的两大原则的一个精炼的表达。
对此,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的认识很是精到,“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固定(亦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解释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势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14]。當然,译文一旦成为阅读文本,则进入互文性的考察范畴,译者已经无权决定什么,而对读者而言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林少华文笔优美,神采飘逸,也有人批评他“添油加醋”,“浓妆艳抹”;有人喜欢赖明珠的清新自然,直白率真,也有人批评她“索然无味”,是“翻译机”。可以说,两位作家翻译的作品所具有的极为鲜明的特点,在一部分人眼中成为了优点,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则是不足,甚至连“每个译者首先也不过是这众多读者中的一个而已”[15]。近年来,也涌现出了更多的译者,将村上春树更多更新的作品带到了中国,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更乐于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因为有竞争才会有成长,才能在林少华和赖明珠两位翻译家本已足够优秀的作品之上,展现出更加完美与多样化的村上春树。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邹东来,朱春雨:从《红与黑》汉译讨论到村上春树的林译之争——两场翻译评论事件的实质[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2):24-28.
[3]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4]新浪女性.翻译眼中的村上春树[EB/OL].[2010-07-05].http://eladies.sina.com.cn/qg/2010/0705/12091002055.shtml.
[5]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新版)[M].赖明珠,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7]江海燕.疑问语气意义的两种表达途径[J].南开语言学刊,2005(1):45-52.
[8]小.林少华X赖明珠:村上春树两岸热潮(讲座摘要)[EB/OL].[2008-09-0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b7de70100anna.html.
[9]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72-79.
[10]林少华.王小波、史铁生、村上春树:为了灵魂的自由——兼谈莫言与村上春树的比较[EB/OL].[2011-06-27].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1/2011-06-27/99236.html.
[11]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2]金兵,刘青梅.林少华与赖明珠的翻译风格之比较[J].绥化学院学报,2011(1):120-122.
[13]André Lefevere.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14]文军.翻译: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152.
[15]赖明珠.我,与村上春树森林[N].中国时报·浮世绘,1997-06-25.
[16]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17]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8]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9]孙树林.论“村上春树现象”[J].外国文学,1998(5):21-27.
[20]藤井省三.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M].张明敏,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21]张俏岩,宿久高.从《挪威的森林》看村上春树的孤独感[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4)4:61-64.
作者简介:
王仲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荷兰拉德堡德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海外汉学、手语语言学。
方环海,博士,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国际汉语教育、欧洲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