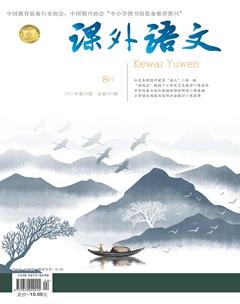窦娥之冤的悲剧性重读
【摘要】《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倾心打造的一部代表剧作,剧情取材于东汉民间故事“东海孝妇”。《感天动地窦娥冤》作为元杂剧悲剧的典范,其中的悲剧性成因具有多重层面的解读。关汉卿通过窦娥这个代表性的悲剧形象,深刻分析了封建伦理纲常中的“孝道”以及男权中心下的“贞洁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深刻影响——男权的桎梏使女性失去独立的意识,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和牺牲品。并且紧扣当时社会现实,真实且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黑暗、混乱与残酷的悲剧时代。
【关键词】窦娥;悲剧性;社会现实;孝道;父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490(2021)24-023-03
【本文著录格式】李凤.窦娥之冤的悲剧性重读[J].课外语文,2021,20(24):23-25.
引言
《感天动地窦娥冤》被节选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4)》中的戏曲单元,从实际的教學现状来看,大多是通过对窦娥不幸的命运与强烈的抗争精神两个层面来分析《窦娥冤》的悲剧效果来源,对于其悲剧性的解读不够深刻与全面,并且对于窦娥的人物形象分析一味地赞美,这种认识太过于片面。在《窦娥冤》的解读中应充分考虑其综合语境来达到对人物分析以及主题的理解的全面深刻性。窦娥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符合父权统治下对女性的要求的,因此作者站在男性视角下对其是持赞美的态度的。本文对于窦娥之冤的悲剧性重读,试从社会背景、伦理孝道观、父权社会三个角度进行。
一、社会背景:混乱统治下社会的失衡与理学的桎梏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朝代。关汉卿写作《窦娥冤》的时代正值元蒙统治时期,统治中心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导致了元代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民族矛盾的环绕下,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番混乱、黑暗、失衡的场景。
在《窦娥冤》中我们随处可以看见这些失衡混乱场景的具体化——首先,窦天章卖女还债,寻取钱财进京求取功名。这缘于窦天章想要摆脱当下的困境,也侧面反映出对功名官位的追求的不计代价,在当时的时代环境决定了做官是改变其处境的直接途径,秀才读到老也只为一朝上榜,这是一种非平衡化的社会现象与价值观的偏颇。其次,借债不还、杀人封口的庸医赛卢医,“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道医死无数人,却被人乐道一手好医。可以说这个人物为故事情节的推动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连接张驴儿父子与窦娥婆媳之间的桥梁,也是窦娥冤死的助力者。赛卢医的种种行为让人不禁感叹社会职业道德的缺失以及狭隘的钱财观对人性的泯灭。再次,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流氓集团更是反映出社会的混乱黑暗,流氓无赖无处不在,作为底层的人物,他们邪恶的内心正是这个社会真实的写照。最后,衙门的腐败,昏官当道,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对于窦娥的屈打成招是造成悲剧结局的直接推力。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下到平民百姓,上到衙门官员,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腐败黑暗。关汉卿通过戏剧的冲突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揭露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窦娥式”冤案的发生并不令人惊讶,“窦娥式”悲剧的发生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窦娥的悲剧也是当时元代民众处境的一种“本色反映”。
此外,谈到元代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作为当时元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元朝是一个靠军事武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带有几分粗俗与野蛮的民族风气潜移默化地在汉族文化中滋长,汉儒们为了挽救当时如此的社会风气就开始极力推行理学,理学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普及、渗透。理学的教化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同时也逐渐完成着对人思想的固化,窦天章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这又恰恰体现在窦天章对窦娥的教育中——窦娥正是从小受到窦天章三从四德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才会导致她如此地守孝守节,这也间接地造成了窦娥的悲剧。
二、伦理孝道:“愚孝”的恪守
常言道:“百善孝为先。”为了巩固封建伦理纲常中的孝道观,历朝历代都在塑造孝道人物方面花足了功夫。最为广泛普及的莫过于《二十四孝》。这种孝的观念,一方面在控制不孝现象的发生方面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子女对长辈无限制的“孝”。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愚孝”对人的荼毒。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孝”的典范。她的“孝”使她为人们所世代称道,但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份“愚孝”构成了她悲剧性的因素之一。
在《窦娥冤》中窦娥的“孝”被施加在两个人物身上。第一个人物是她的父亲窦天章。窦娥身世坎坷,从小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已是万分不幸,父亲赶考却狠心将七岁的她抵押给蔡家当童养媳,但为了回报父亲的养育之恩,她甘愿牺牲自己给蔡家做童养媳。在元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融合,元代的婚俗也呈现多元化。元蒙人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也影响了汉族的婚姻制度,继婚和招夫婚这两条婚俗被公认,由童养媳过渡到寡妇也成为多数元代女性的现状,所以在当时没有人会去质疑童养媳的合理性。这种婚姻制度也为后来蔡婆婆再嫁,张驴儿想娶窦娥提供了法律依据。窦娥之“孝”被施加的第二个人物是蔡婆婆。嫁到蔡家后,她孝顺婆婆,勤劳持家。窦娥的丈夫死了之后,她与蔡婆婆二人相依为命,她也是恪守做媳妇的职责。为了婆婆不受皮肉之苦,她甘愿认下了杀人的罪名,哪怕是变成鬼魂之后,也不忘嘱咐自己已经出人头地的父亲,照顾好蔡婆婆,以保证蔡婆婆的晚年无忧。从上述的两点来看,窦娥是一个孝顺的好女儿、好儿媳的典范形象。然而,这份“孝”是在经由历史上长期的孝亲观念的强化而对人们的一种思想荼毒。仔细推敲起来,封建的孝道观念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行为标准,与一般儿女对父母长辈的孝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封建的孝道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是旨在维护封建家长制,正所谓“父虽不慈,子不可仵”,毫无平等可言。对于窦娥来说,这份“孝”使她成为一个善良、孝节的好女儿、好儿媳,但这份固化的“愚孝”也是杀她的帮手,奉上人生求得父亲仕途,奉上生命求得家婆安然,而她自己也深刻地认同自己的这份“孝”。这种孝道观与我们今天的孝道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具有浓厚的节孝观念,这也是当时时代广大下层妇女的真实写照,是一个群体的形象标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纲常观念的严密禁锢,也成为《窦娥冤》悲剧性的因素之一。
三、父权社会:男权桎梏下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窦娥的悲剧结局的实质是父权社会中男权中心对女性的一种压榨和束缚。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看作是男性的一种附属品,是可以随意擺弄甚至是可以随意交易的。女性在这样的男权桎梏下丧失了主体的意识,在性别政治和传统的贞洁观的驱使下女性成了绝对的他者。而这也构成了窦娥之冤的悲剧性成因。
(一)《窦娥冤》中的性别政治
《窦娥冤》存在着多重的性别政治关系,这些关系的交织构成了一张束缚以窦娥为代表的女性的大网,在这张大网下女性处于“失声”的状态,是《窦娥冤》悲剧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窦娥冤》中共有五重性别政治关系。第一重性别政治关系:窦天章与窦娥之间。窦天章为了还债和取士,将窦娥换给蔡婆婆做童养媳,这其中其实是一个显然的交换关系——窦娥被父亲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在父权社会,女子始终只是男性的附庸,窦娥在未出嫁之前,是从属于自己的父亲的,父亲对窦娥有任意支配的权力,这在男权社会,是被公认的事实,这也为窦娥被父亲抵押提供了法律和社会认知上的合理性。第二重性别政治关系:窦娥与丈夫之间。嫁与蔡家为媳之后,窦娥便从属于另一个男性,也就是她的丈夫,在丈夫面前,窦娥是绝对的从属关系,所以她这一辈子都要对自己的丈夫保持贞洁,这也就解释了窦娥宁死不从张驴儿的原因。第三重性别政治关系:窦娥与蔡婆婆之间。窦娥的丈夫死了之后,窦娥表面上从属于她的婆婆,好似对窦娥的支配权由前面两个男性的手里终于转交到一个女性的手里。实质上,窦娥还是从属于夫家,只不过蔡婆婆成了夫权的代理。第四重性别政治关系:窦娥及蔡婆婆与张驴儿父子之间。张驴儿父子分别想占有作为女性的蔡婆婆和窦娥,张驴儿父子其实是作为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占有的代表人物,窦娥及蔡婆婆在此处作为被男性侵犯的对象。第五重性别政治关系:窦天章与州官之间。戏剧的高潮部分是窦娥被不明是非的州官判了死刑,但是窦天章数年之后一举及第归来,窦娥的鬼魂出场,窦天章知道女儿枉死的原委之后为窦娥翻了案。窦天章能够成功为窦娥申冤的前提是他身居官位,最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此时是大于州官一众人的。上述的几重性别政治关系交叉在戏剧中推动其悲剧性的形成,放眼到整个社会,这其中的性别政治并不是以个案的形式出现在《窦娥冤》中,在父权社会中,这些性别政治关系的存在是覆盖整个社会的。
(二)从《窦娥冤》中透视传统贞节观
在古代封建社会,对于女子的贞节的束缚十分严厉。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道:“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对于女子的贞节禁锢是父权社会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有两类人共同拥护——包括规则制定的男权中心的男性和丧失主体意识的女性。
窦娥的形象被塑造为男权社会的典范女性形象:在样貌上她“生得可喜,长得可爱”,在品质上她恪守孝道、死守贞节。可以说窦娥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天使”的形象。而文中的另一个女性蔡婆婆的形象与窦娥的形象形成了对比。在面对张驴儿父子要求她们各自嫁与他们的要求时,蔡婆婆在初步反抗后应允了,并且她还劝说窦娥也答应这样的要求。按照父权制文化对女子贞节的要求,蔡婆婆的这一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是没有贞节的表现,作为一个女人,蔡婆婆也只能属于自己死去的丈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蔡婆婆也是一个考验窦娥的试探者,代表着父权社会对窦娥贞节的一种考验,而窦娥通过了这样的考验——首先,她极力反对婆婆嫁给孛老,在劝说无果后,她甚至搬出来自己的公公(这个家庭中男性权威),在这里窦娥是贞节观的卫士。其次,戏剧中有一处细节描绘的是窦娥的心里情感状态:“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这一段表达出窦娥的闺怨。丈夫短命,自己日日独守空房,但是她心中时时刻刻念着的依然只是她的丈夫,她始终恪守为人妻的本分,对丈夫并无二心。这本质上也是贞节观念的桎梏。最后,她对张驴儿的占有誓死不从,以死捍卫自己的贞节,保全自己的“天使”形象。
从上述可知,窦娥作为一个贞洁的“天使”,是符合男权社会对女子的审美和要求的。所以作者从男权的视角,对窦娥的形象是赞美和认可的。而作者的观点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对窦娥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悲剧中,作者在极力减少窦娥这个人物的悲剧性以便符合当时大众的诉求——这样一个贞烈的女子不应该得到这样悲惨的结局。所以,作者在戏剧的结尾极力去减轻悲剧的色彩:血溅白素、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结尾窦娥以鬼魂的形式出现申冤,窦天章为窦娥申了冤。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观众对不公的社会现实内心诉求的精神抚慰。
(三)《窦娥冤》中的绝对他者
《窦娥冤》中窦娥是一个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丧失了女性主体地位的绝对他者。在整个社会的男权意识灌输下,以窦娥为代表的女性都是丧失主体地位的,再加上窦娥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熏陶,而窦天章又是一个典型的儒士,这种“他者”的观念在窦娥的意识中更加深刻,他者特性逐渐内化为她的自我意识,造成了她的自我钳制。除此之外,《窦娥冤》中的蔡婆婆也是一个绝对他者,面对所谓的救命恩人,在钱财答谢无果后,她选择应允以自己相嫁作为答谢的报酬,她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筹码,从深层的意识上,蔡婆婆也是认为自己是从属的关系。作为绝对他者的女性们思想固化,按照男权中心的要求打造自己,丧失了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是造成《窦娥冤》悲剧性的重大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窦娥冤》的悲剧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权的更替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当权者有效的解决、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人性的钳制以及父权制文化下对女性的压榨所共同导致的。窦娥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反抗的精神,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并不是女性意识崛起对男性的反抗,而是关汉卿及当时的社会民众通过窦娥发声,去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以及对社会现状的失望痛心的悲歌。
参考文献
[1]王跃平.窦娥人物形象及社会意义多元解读[J].黑河学刊,2019(3).
[2]曲雪峰.窦娥悲剧命运的解读[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5).
[3]张红娇.《窦娥冤》中的窦娥形象分析——兼谈中国古代女性悲剧命运之根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1).
[4]陈若帆.窦娥“节”“孝”观念摭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5]张秀英.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2).
作者简介:李凤,女,1996年生,四川崇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