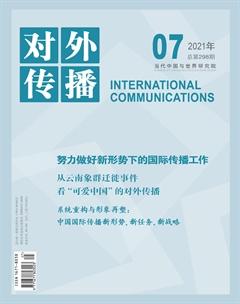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逻辑和构建优势
周庆安 卢明江
【内容提要】在创新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中,要重视中国叙事的构建。这其中既有对我国国际传播任务的新定位,又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国叙事体系的独特性。同时应当理解,在世界议程中构建中国叙事,更需要从“世界之中国”这一维度入手,将融通中外的概念落到实处。
【关键词】中国叙事 世界议程 融通中外
2021年的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见的历史大变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类共同挑战,中国叙事不仅不能缺位,更面临一个新的出发点。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将中国叙事与世界体系深入融合。要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表达,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共同完成。
一、中国叙事重新定位我国国际传播使命
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500多年的全球现代化历史中,中国无疑是一个后来者。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其实是中国独特性与世界融合的历史进程。国际传播工作,既是一个全景式展示中国真实立体形象的过程,又是一个清晰叙述中国独特性和东方魅力的过程。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的统一,在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是一个定位层面需要明确的问题。
首先,构建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的统一,需要对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体系有更加清晰的总体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国叙事不是简单的外宣工作,而是从战略层面上重新认识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观,也体现了大国公民的国际传播素养。在当前内宣外宣不分家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叙事既反映了我国对外的传播能力,也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过去,我国国际传播更多地归属于外宣部门和外宣媒体,但是今天的国际传播任务,需要全员、全民、全域参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要共同参与完成,这其中高校更是责无旁贷,不可回避。
其次,中国叙事重新构建了国际传播的任务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分别代表了国际传播在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工作。其中每一个“力”,都覆盖中国叙事的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群体来共同完成。其核心,仍然是对中国自身的道路、文化、内涵、惯习以及与世界关系的阐释。对外传播的中国文化自信心和影响力,就需要通过这些“力”的维度来定义和体现。
最后,中国叙事强调了我国国际传播任务的特殊性,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到,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于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任务要求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个层面的统一:一是要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与旗帜鲜明地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二是要保持世界发展的共同规律与中国叙事体系独特性的统一。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战略层面上提炼我国国际传播的体系,并重新完整定义了我国国际传播的任务和目标,以中國叙事体系的构建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资源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叙事本身的特点分析和归纳,就变得极为重要。
二、认识中国叙事体系的独特性
中国叙事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东方哲学以及我国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现实关照下,中国叙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时空观。这种时空观的核心固然有中国历史文化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灵魂中的烙印,更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发展的奋斗历程。因此,中国叙事,既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原点、制度初心,又要讲清楚当今中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以及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比如中国人的均衡稳定、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和谐观、天下观,中国人对于大国强国责任的理解等,都与欧洲文化传统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现代性有显著差别。因此,面对这样的复杂中国,曾经有西方学者说,中国是不可阐释的。其实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恰恰相反,中国不仅可以被有效地阐释,中国叙事对于今天全球体系的完整性、多样性甚至发展性还有着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世界面对深层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资本形成的发展停滞、宗教种族对立的加剧、文化的单一性,即便是在单个社会内部,民粹主义、种族问题也不断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叙事体系就变得更有价值。
中国叙事不但提供了中国发展自身的历史故事和现实成就,而且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未来的视角。一方面,中国叙事尝试解释了人类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多元努力,在探索文明进程中,中国所提供的历史智慧在今天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比如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互通互鉴,就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尊重文明彼此需求的对话。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天下观念,更多地强调多中心、多文明的相处关系,而非零和博弈。在这种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明,必然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范式有着巨大差别。另一方面,中国叙事也在解释当代世界的多样性。二战以来,随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到底是在现有的现代参照系对照下发展,还是在自身的内生性因素中寻找动力,这个问题曾经是一个国际传播的大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曾经就国际传播新秩序展开讨论,尽管讨论没有成功引导实践,但是对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发展多样性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在面对全球共同议题的复杂和艰巨任务中,中国叙事的独特、稳定和可持续,都能够给国际传播提供更加完整的答案。
三、在世界议程中完善中国阐释
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国际传播工作更是一个世界议程和中国叙事统一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毕竟面对着中国以外、有着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和不同制度道路选择,甚至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受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播理想,在国际传播的现实语境中,仍然有较大落差。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目前的世界体系构建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文化基础上,这种文化基础所形成的关键概念,从主权国家到民主价值,成为衡量世界各国的一把“尺子”。“尺子”到今天,已经不尽如人意,但是要完善这把“尺子”,中国叙事也需要构建一种融通中外的表达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际传播的重大挑战恰恰在这里,即如何更重视中国叙事和世界议程的统一,认识到二者之间曾经存在一定的差别,并用发展预期和世界议程调和这种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也体现在国际体系的构建逻辑上。应该说,中国近代以来受到的各种封建殖民压迫,使得中国很晚才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也正是这样的反封建反殖民运动,树立了中国人更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團结感。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格,又推动了中国人用更短更快的时间,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差别,留给世界的不仅是震惊,更多的也是疑问,是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无法解释的问题。
那么国际传播中,中国理论、中国阐释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世界体系,如何参与世界议程,中国与世界的相同之处在哪里。因此,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的理论创新,就在于找到一条既能说异,也能说同,异同同合的话语道路。世界与中国,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秩序体系的差别,更多的是在观念和选择上;世界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其实更多,尤其是对于未来人类命运的共同承担上,今天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历史选择的回溯,而是未来命运的共同担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就是长期具有优势心理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中存在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存在疑虑、对立甚至敌视情绪。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叙事面对着这些情绪基础上的误读、曲解甚至是谎言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要辩证统一地看待异和同的关系,在文化自信基础上,一方面要构建国际社会能够更加充分理解的中国理论,另一方面的确也要更加勇于回应竞争挑战,不回避问题。
四、在世界之中国中构建中国叙事
当下,我们既要面对中国叙事的挑战,也要深入理解全球话语体系对中国叙事提出的新要求。目前全球话语体系正在出现一种安全泛化的态势,强人政治、民粹主义、极端情绪、观念对立、街头游行的背后,所有议题都在出现安全化的态势。在今天的国际传播中,哥本哈根学派对于话语安全化的警告,带来了巨大挑战——“所有的话语,都能成为与安全有关的话语,而安全是人们包容度最低的一种文化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叙事,需要再度构建有效的文化认同。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传播维度上已经深深植入全球体系中,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密不可分。而全球各国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文化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和制度认同,这其中的核心常常被认为是文化认同。中国叙事的文化认同,不仅是餐饮旅行甚至云南大象出行这些软性的异域审美,更是生活方式、思想体系和道路理念这些共同面对的社会元素。
我们应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传递清晰的理念,每一个国家的叙事,都是全球文化认同的多元组成部分。一个良性的全球文化,应当是多种文化认同的综合体。近年来,我国在文化、经济甚至政治领域,都产生了不少国际传播的爆款产品。这里既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案例,也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理念,还有实现控制碳排放的中国做法,以及这些做法背后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一系列有逻辑联系的中国叙事,围绕当前全球关心的气候变化问题,打造了多元化的文化认同。
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传播叙事,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描述,嵌入到世界体系中,让全球提升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度。尤其是疫情暴发以来,我们看到了不少世界级的思想家,不管他们是哪国人,都撰文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和世界体系未来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更期待看到更多的中国思想家,以中国叙事回应世界议程。我们不仅要传递中国故事,更要传递中国人在叙事中所认识的世界。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提出的“三个中国说”:“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世界的中国,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叙事的核心。
要认识到,国际传播工作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和行为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身份证和宣言书。因此,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本身也需要久久为功,而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但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世界议程已经无法缺少中国的阐释和回应。不管东西方各自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我们都将面对同样的世界挑战,也应当作出共同的回应。这样的统一叙事,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同仁参与和创造。
周庆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卢明江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