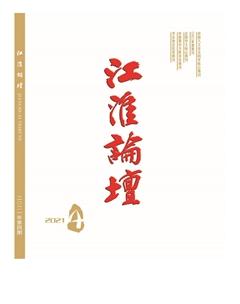论新时代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陈文胜 李珺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兴盛繁荣成为当务之急。党中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尊重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必要前提,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时代要求,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探索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文化;文化兴盛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迁,其中,在乡村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差别不仅在于物质差别,更在于文化落差”[1]。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2]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必須以相应的文化来引领社会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中国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文化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规划和设计,明确提出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事关全面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根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3],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整个社会的的“根”在乡村,“魂”在家乡。[4]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下,乡村人口、资本等快速向城市流入,乡村出现凋敝样态。[5]因此,如何在城市文化浪潮冲击下尽量避免乡村文化的衰落,成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关注的现实问题。不少学者关注了乡村文化的宏观变迁,尤其是对“遭遇”现代化后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剖析。代表性的观点如徐勇等认为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不可因此重返过去那种传统的乡土社会,要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村的价值,从后城镇化的角度看待乡村,从而让农民有归属感、幸福感。[6]陈波等从社会关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三方面考察农村文化的变化特征,提出农村文化变迁要考虑四组重要关系以及这几大关系之间要如何平衡的问题。[7]陈文胜等认为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变化的实质,就是由以人身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到以经济利益独立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变,由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伦理本位到个体本位的变迁。[8]赵秀玲等认为乡村文化振兴要把握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四大关系。[9]
针对当前乡村文化面临的“失衡”危机,欧阳雪梅等提出繁荣乡村文化首先要改变“城市=先进、乡村=落后”的思维定式,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丰富符合农民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等。[10]吴理财等从文化治理的视角,认为乡村文化具有文化本身功能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和功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等乡村文化发展体系的建构。[11]朱启臻等认为振兴乡村文化应当采取“培土”的方式,而不能简单地“移栽”,因为乡村文化的创作主体是农民,而乡村环境是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如果离开主体和环境就是再多的资本也无法维持其真正的生命。[12]还有通过乡村经典案例剖析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微观具体路径,如王宁等通过对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来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路。[13]鲁可荣等以浙江三个传统村落为调查样本,对村落公共空间变迁过程及其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要更好地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就必须实现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及协同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14]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基本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为乡村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下的乡村文化研究还不够充分,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衔接不够紧密。因此,亟须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二个百年目标,结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要求,探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二、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
必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5]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这不仅强调了要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科学回答了乡村文化发展中“传承什么”与“谁来传承”“怎么传承”等重大问题。孔子认为,“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在庙堂之上,很多传统的礼节、道德、文化都普遍丢失了,反而还能在乡下找到。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16]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引领,从一开始便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并在现代化进程上领先于农村[17],乡村社会的农耕文明被视为落后的社会文明,首当其冲受到城市文明的强势冲击,因而,在占有主导地位的现代化价值观念中被日益边缘化。不难判断,乡土文化的衰落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变迁的深刻体现。[18]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增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历史上流传悠久的民歌逐渐失承,传统节日习俗逐渐消亡,而一些地方政府“重经济、轻文化”的乡村发展思路,更使得文化发展遭受冷落而流于形式。文化建设既虚又实,虚是指文化建设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可以立竿见影,通常需要多年的耐心培育才有效果;实是指文化虽然看似无形,但实际上可以发挥凝聚人心、塑造乡村共同体的强大功能。[19]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人文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就各有不同,乡村文化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同时,乡村社会发展的滞后使乡村文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特别强调:“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20]作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几十年甚至是百年工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因此,乡风文明建设重在引导,使之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而不能简单粗暴地用行政手段过度干预。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乡村民俗习惯是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生祭婚丧节庆是农民作为普通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更是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的精神家园。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不加区分地进行硬核规定,不仅一刀切地规定婚丧酒席的具体桌数,甚至还一刀切地规定只能吃几道菜以及哪几个菜等,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普遍反感和排斥。
因此,要高度警惕把传统风俗习惯视为陈规陋习或是封建迷信,不分青红皂白地移风易俗,应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2]城乡只有地域与生活方式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执意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取代传统的乡村文化,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可能是灾难性的。移风易俗要以尊重传统文化为前提,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如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机构的自治劝导作用,对农民那些世世代代传承的民俗习惯存有尊重、敬畏之心。[16]
三、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农民由农业向非农职业不断分化,乡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人际结构由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跨越。[23]一方面,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逐渐退场;另一方面,根植于现代社会的乡村文化图景却没有完全形成,乡村社会价值追求无序化现象突出,这无疑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互动带来的阵痛直接相关联。因此,如何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探索推进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对接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以破解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的矛盾,成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中国乡村的传统文化伴随着农耕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演进,蕴含着社会文明演进中不断沉淀的最朴素文化和乡风民俗,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一个标志性的文化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4]因此,乡土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体现着中国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仍然具有不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的时代价值。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也必须从传统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会因赋予时代特点而不断演进,因此,既要尊重传统乡土社会中符合时宜的元素,又要剔除其不符合时宜的成分,在对接时代中实现优秀传统与现代理念的有机融合,激活传统文明的精华。也就是说,“在保持乡村特质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因素融入到乡村文化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新的生长点,实现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重塑的方式留住农耕文明,留住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情感。”[25]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与建立在理性、民主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互动,加入新的时代元素实现有机融合,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费孝通所说,要“切实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26]。
在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冲击下,迫切需要引导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对接。一方面,既要尊重传统的风俗习惯与乡规民约,传承乡村传统文明,继承优秀乡土文化,留住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乡愁”;另一方面,又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不断融入现代文明,把形成良好的现代法治观念作为现代乡村文化的内核,构建新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之一,随即在同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求“传承發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27]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繁荣兴盛乡村文化。[28]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要求和价值目标。
四、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探索乡村文化兴盛
之路的基本途径
在乡村社会,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可以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的行为和心理。[29]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发展乡村文化可以给农民带来最直接的精神福利,如果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就失去乡村之魂,没有乡愁的乡村就难以成为农民心灵的归属,也难以构建高品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在新发展阶段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把制度建设作为净化乡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探索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从而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一)突出乡村文化发展的农民主体地位
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承载者、受益者、衡量者。要实现乡村文化的发展,就必然要从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什么”与“乡村文化谁来振兴”“乡村文化怎么振兴”的问题上,关键是如何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要求上来,真正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创造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真正主体。[30]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巨大,农民未能被视为“平等主体”来对待,无形之中形成了“乡村就是落后,城市就是先进”的社会心理,对乡村文化的不自信也就必然导致农民群体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1]振兴乡村文化事关民族文化的自信,而只有发动农民广泛参与,增强乡村文化主体的认同感,才能让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起来”“活下去”,乡村的文化发展才能不断层。[32]
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乡风文明建设不充分的矛盾,农民贫困不仅仅是物质收入方面的困难,精神层面的困境尤为突出。在精神层面上,农民的乡村文化生活被城市文化生活所主导,乡村传统的价值观念被城市文明、工业文明所颠覆,从而导致了乡村生活价值的沦陷。
实现乡村文化兴盛就必须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始终,也就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给农民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实现乡村文化由农民所创造又为农民所需要,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创造者、参与者、受益者,才能让积淀深厚的乡村文化不再断层,真正留住一方乡愁,疏浚乡村文化振兴的源头活水。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唱主角,全方位鼓励农民大胆实践创造,增强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农民真正自信起来。有尊严的农民才有希望建立一个幸福与富强的乡村,才有希望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
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观上的集中体现,而且指导了新发展阶段社会变革的路径选择,它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乡风文明建设是以文化为核心的乡村精神家园建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下,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33]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行动逻辑,做到知行合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应该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个综合完备的体系,而不是简单的几张标牌、几句广播宣传语。现在一谈到乡村文化建设,往往就会想到建设一批文化小广场、小长廊等,并在其中植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要素,毫无疑问这些标识、标语确实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宣传效果,让大街小巷的农民都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的文化建设很难对乡村社会生活产生较深层次的影响。
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自然而然地融入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不能被迫学习,而要主动靠近;要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传播途径与方法,要在充分了解把握农民的心理、行为习惯、思维模式、现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采取适合乡村特点的形式,激发农村传统文化活力,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发动农民积极参与“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活动,树正压邪,形成风清气正、向善向上的舆论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与行动体系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和全程监督,敢于与歪风邪气进行斗争,让不良风气失去根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主题在乡村文明创建与评议的小活动中落地生根。[34]
(三)把制度建设作为净化乡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
持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要求坚持高效能治理的新发展理念。按照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乡村社会的现代秩序必然以法治秩序为根本要求,以正式制度的法律作为规范乡村所有主体行为的准绳,用现代的法治文明来整合与规范乡村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利益共享的现代乡村制度文化和治理结构。也只有通过法治文明才能从根本上引领和保障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在乡村社会的实现,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建立和维护。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并不是靠一个国家的正式权力来推行[35],维持礼治秩序主要依赖乡土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整合力量。而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之中的乡村,每个人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商品社会,礼治秩序再也无法应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只有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才能保障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乡村社会活动都生存在正式制度的现代秩序之下。
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把乡风文明纳入制度建设轨道,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和保障乡风文明建设,以规立德,净化乡村社会风气。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重司法成为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基本取向,在遵循和整合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强化村规民约对乡村的文化引领和价值认同,使乡村社会不文明行为得到有效约束,让乡村好習俗、好习惯、好风尚的文明乡风和良好家风蔚然成风,从而推动乡村社会自我教化,形成良好的村风民俗。[36]
五、结 语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传承五千年而独不断,其背后的密码正是建立在中国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之上的家国情怀。中国几千年来通过乡村民俗习惯把血缘密码与宗族、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连在一起,形成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的家国情怀,故情系故土,小而思乡,大而思国,这份家国情怀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归属与命运共同体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根在乡村,才能更好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与方向。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拐点,一方面是全球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是大国小农由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构成了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双重语境。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来统领乡村的文化建设,让现代文明融入到乡村的日常生活,而且要包容乡土文化的区域差异性和发展多元性,顺应乡村文化的演进规律,传承乡土地方本色,彰显中国民族风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的讲话,引自:郑晋鸣.冬日暖流一路春风——踏着总书记徐州考察线路采访记[N].光明日报,2017-12-15(02).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
[4]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J].东南学术,2018,(5):132-137.
[5]王秋月,郭亮.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祖先崇拜及其功能——基于赣南农村的田野叙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47-56.
[6]徐勇.“根”与“飘”:城乡中国的失衡与均衡[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4):5-8.
[7]陈波.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J].中国软科学,2015,(8):45-57.
[8]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观念的变迁[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9-113.
[9]赵秀玲.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发展向度[J].东吴学术,2018,(2):5-12.
[10]欧阳雪梅.振兴乡村文化面临的挑战及实践路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5):30-36.
[11]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12]高瑞琴,朱启臻.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基于《把根留住》一书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03-110.
[13]王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J].湖北社会科学,2018,(9):46-52.
[14]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22-2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05.
[16]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99.
[17]陈雪娟,胡怀国.中国现代化进程透视下的城乡关系演变[J].经济纵横,2021,(5):9-17.
[18]陈文胜.论中国乡村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06.
[19]李珺.在全面推進乡村振兴中传承提升乡村文化[J].农村工作通讯,2021,(1):34-35.
[20]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9(01).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23]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2):57-62.
[2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24.
[25]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97-108.
[26]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207-208.
[27]董峻,王立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30(01)
[28]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3-9(01).
[29]黄平.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188.
[30]陈文胜.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何以实现[J].中国乡村发现,2018,(5):48-51.
[31]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
[32]高瑞琴,朱启臻.何以为根:乡村文化的价值意蕴与振兴路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03-110.
[3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44-145.
[34]陈文胜.以“三治”完善乡村治理[N].人民日报,2018-3-2(05).
[3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8-65.
[36]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J].求是,2018,(6):54-56.
(责任编辑 蔡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