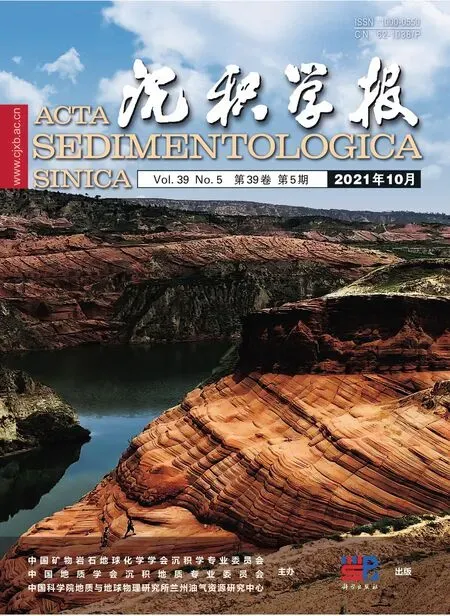干旱环境河流扇概念与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满盆砂”成因新解
李相博,刘化清,邓秀芹,王雅婷,龙礼文,魏立花,郝斌
1.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兰州 730020
2.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西安 710018
0 引言
长期以来,三角洲砂体被认为是我国陆相含油气盆地主要储集类型[1],由此形成的三角洲成藏理论指导陆相盆地油气勘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3]。可以说,在我国陆相盆地中,找油就是找三角洲,找到三角洲基本就能找到大油田。但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沉积学家提出在湖盆中央地区发育大规模河流扇砂体的新认识,并认为它们也是良好油气富集相带[4-8]。这一新观点及其结论都源于他们对现代沉积、露头剖面的详细描述和对沉积—搬运作用过程的精细研究,尤其是遥感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沉积地质学家在更大尺度上观察沉积体系的整体形态和规模、进而分析源汇系统提供了方便,代表了目前干旱环境下湖盆沉积研究的最新进展。
事实上,以往在湖盆沉积相研究中,可能夸大了三角洲沉积的作用,就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而言,人们按照传统思路所编制的沉积相图为一种“满盆三角洲模式”。这一情况也与现代沉积相悖,青海湖等现代沉积考察表明,一个湖泊在某一地质时期最多发育1~2个主水系及相关三角洲体系。
河流扇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陆相盆地砂体主要为三角洲成因的观点,对于预测湖盆中心地区含油砂体分布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根据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一方面对河流扇概念、沉积特征及控砂机理进行评述;另一方面,应用这一概念,对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原先普遍认同的“三角洲控砂模式”进行重新分析,以期为该区今后的油气勘探部署提供科学依据。
1 干旱环境河流扇概念及研究进展
1.1 河流扇相关概念术语与发展由来
追根溯源,河流扇(Fluvial Fans)概念的提出起始于人们对冲积扇(Alluvial Fan)的研究。最早认为冲积扇是一种发育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山前或地形陡变地带呈扇状分布的沉积体系,其沉积物颗粒通常较粗,主要发育辫状河,泥石流,漫流和筛积物[9]。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内陆盆地中并非所有呈扇状展布的沉积体系都具有冲积扇特征,于是根据“扇状沉积体系”扇面上发育的河道类型以及是否存在泥石流等现象,将其划分为泥石流扇(Debris-flow Fan)、辫状河扇、曲流河扇等类型,后两者统称为河流扇(Fluvial Fans)[9-10]。21世纪以来,对河流扇的研究不断增多,Hartleyet al.[6]和Weissmannet al.[7]将半径小于20~30 km的扇体成为冲积扇,将半径在30~100 km的扇体称为河流扇,将半径大于100 km的扇体称为巨型扇,并将三者统称为分支河流体系(Distributive Fluvial System,DFS)。
DFS概念将冲积扇、河流扇和巨型扇等整合在同一个术语体系,其提出得益于遥感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地学领域的应用,尤其卫星遥感技术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范围,使得人们能够对沉积盆地内发育的一系列沉积体系进行总体的理解和把握,促进了“扇状沉积体系”分类和描述的系统化、沉积微相和沉积模式研究的多样化、沉积过程响应解释的精细化及源汇体系分析的定量化[8,11-12]。至此,人们对陆相盆地“扇状沉积体系”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代表了目前陆相盆地河流沉积体系研究的最新进展。
最新研究表明,在DFS体系中,冲积扇与河流扇(含巨型扇,下同)虽然都呈扇状分布,但沉积动力、沉积特征与模式相差很大。其中河流扇是由曲流河反复决口(Successive Avulsions)而形成的扇状沉积体系,常发育在地形地貌平坦的内陆干旱地区,其沉积物粒度通常较细,主要为洪泛平原、河道与决口扇沉积[5,13],有时伴有风成沉积[14],但不发育泥石流与筛积物。正因为具有上述特征,也有人将河流扇称为“干旱曲流河末端体系”[13,15]、“末端河流扇”(Terminal Fluvial Fan)[14]及“洪水—河漫湖”[16]等,虽然术语不同,但指的基本上都是干旱—半干旱环境下、远离物源区的洪泛平原沉积体系。
此外,在河流扇河道描述中,Weissmannet al.[7]与Northet al.[5]还区分了Distributive与Distributary两个单词的含义。Distributive一词带有沉积学意义,意味着河道呈分支状,但不一定同时期都在活动,经常反映不同时期的河道叠加复合而形成的放射状水系;Distributary一词包含了地貌学意义,即各分支河道都存在流水,是同时活动的(除非主河道不是满负荷的)。鉴于此,本文建议采用“分支型河道”与“分流型河道”两个术语,分别与英文单词Distributive channels与Distributary channels相对应。对它们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不同河道(河流)类型形成的砂岩储层构型、几何形态及其连通性不同[5],分流型河道砂岩连通性好,而分支型河道砂岩在纵向上多被泥岩分割,两者的油气勘探意义差别较大。
需要说明的是,对河流扇概念的认识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术语—末端扇(Terminal Fan)。末端扇一直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概念[17-18],其最初提出者是Friend[19],但他只是对末端扇主要沉积特征做了描述(如向下游沿程方向砂岩粒度减小,粉砂质成分增多,砂体厚度减薄(与河流深度变浅有关),发育小型交错层理,河道底界面平直,无下切现象等),并没有提及形成末端扇的河流特征。Kellyet al.[20]通过对印度北部的Markanda河与苏丹的Gash河两个典型现代河流沉积体系的观察研究,建立了末端扇形成的河流分布模型(图1a)。该模型明确地反映了一种分流河道体系(Distributary Channels)(下文简称“分流型河道”),其特点是向下游方向河道分叉呈扇形撒开,河道的平面形态较为顺直,且是同期活动的(Coeval Distributary Channels)。受这一观点影响,一些学者又提出了河流分流体系(Fluvial Distributary Systems)概念[21-22],将末端扇、非末端冲积扇和河流扇全部涵盖其中,并试图用如图1a所示的“分流型河道”模式来解释其成因。
Northet al.[5]对上述模式与观点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被“末端扇”理论支持者做为经典范例的两个现代沉积露头即Markanda与Gash河流体系的重新考察,认为“分流型河道”与地质实际情况不相符合。Markanda与Gash两个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经常处于干涸状态,不存在各分支河道中同时有流水的情况,而且两个地区都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包括灌溉、种植和河道治理等影响,很难区分目前的河流地貌形态是受到人为因素干扰还是自然条件的影响。于是,Northet al.[5]及后续研究者[14-15]通过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多个现代沉积实例的深入解剖,提出了如前所述的河流扇模型(图1b)。该模型揭示了一种分支河道体系(Distributive Channels)(下文简称“分支型河道”),反映了在洪泛平原环境中,河道的反复决口(Successive Avulsions)是形成这类“扇状沉积体系”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河流扇模型中,Northet al.[5]诸多研究者虽然都强调了“分支型河道”的主导作用,但并没有否认“分流型河道”或“末端扇”的存在,认为洪泛平原上的决口扇在未形成新的河道之前就是一个小型的“分流型河道”或者末端扇,代表曲流河的河流末端未河道化部分[22],只是其发育范围非常有限或者很小,与整个河流扇的形成没有多大关系[5]。
1.2 河流扇的空间分布与主要沉积特征
Northet al.[5]认为河流扇并不是只在河流末端才能形成(这也是他反对Kellyet al.[20]末端扇的理由之一),在河道交汇处更常见,尤其当支流的流量超过干流时会造成主河道堵塞而形成河道汇聚型扇体(Tributary-Junction Fans)。在干旱环境洪水季节,情况更加复杂,由于每次的洪水流量不同,加上水体流动过程中蒸发下渗消耗,只有少数情况下沉积物才能搬运到河流体系的末端,大多数情况下陆源碎屑沉积物被卸载到搬运路途中的不同位置上,如澳大利亚的Cooper Creek河就是这种情况。而且Northet al.[5]认为河流扇上的河道也不是图1a中那样的顺直河道(这是他反对Kellyet al.[20]末端扇的又一理由),而是向下游方向逐渐变窄变浅的高弯度的曲流河。

图1 “分流型”与“分支型”河道模式(据North et al.[5]修改)(a)分流型河道,表示所有分支河道同期都含水;(b)分支型河道,每个时期通常只有一条河道含有水(T1、T2、T3分别代表不同时期,X代表河道T2改道至T3的位置,Y代表新河道T3叠加在废弃河道T1的位置)Fig.1 Different patterns of(a)distributary channels;and(b)distributive channels(modified from North et al.[5])
总体来看,河流扇环境的上游近端河道较宽、深度较大,向下游沿程河道截面积逐渐减小直到河道完全消失。由于河道向下游变窄变浅,洪水容易越过或冲刷侵蚀堤岸形成决口扇[15]。事实上,决口扇是干旱环境下河流扇沉积体系的标志性特征。Liet al.[23]通过对Colorado河末端区域主河道决口扇的研究发现,从上游到下游,决口扇在数量上具有明显递增趋势,而且新的决口扇倾向发育于先存决口扇间的低地处,从而造成多期决口扇相互叠加,形成面积较大的席状砂。河流扇体系的另一个特征是河流改道现象频繁。改道主要是在先前决口河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与决口扇分布一样,下游末端区域河流改道频率远大于近端区域[13]。由此看来,河流扇体系的主要沉积单元包括河道沉积、天然堤、以及以决口扇沉积体为特色的洪泛平原沉积。其中河道沉积包括点坝沉积和河道充填,洪泛平原沉积(以决口扇微相为主)主要以泥岩和粉砂岩为主,发育水平纹层,大部分缺乏沉积构造,风化作用强烈,可能发育植被或者没有[13]。
1.3 河流扇控砂机理
如上所述,河流扇主要形成于干旱区,那里的植被稀少,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尤其在热漠环境(Hot Desert)中,气温昼夜变化无常,岩石的页状剥落、劈裂、压碎等机械风化作用强烈,加之在这种环境中,风是主要地质营力,风吹砂和尘土的磨蚀作用会进一步加剧岩石的机械风化作用[24]。长此以往,在母源区形成了丰富的细粒碎屑物质,为河流扇中砂质沉积物准备了充足的物源。
同时,在这种干旱环境中,由于降雨频率极低,缺少大面积汇水区,地表径流水源主要由高山冰雪融水及雷暴引发的洪水,尤其洪水能够引发地质灾害并形成事件沉积。据文献记载[24],干旱区降雨从每年几次到每10年或20年几次,这样的降雨可以快速发生,在短期内形成大量雨水和地表径流,由于缺乏植被覆盖,河流快速流动并容易造成暴洪,瞬间裹挟着大量泥沙沉积物长距离向湖盆中心推进。在此过程中,由于旱区的强烈蒸发与下渗作用,大部分的洪水与河流会消失在干旱湖盆岸线以上的荒漠中,同时也将携带的沉积物卸载于同一地带[15,23,25]。多次洪水事件,能够在湖盆中心地带堆积大规模的砂质沉积物。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具有“满盆含砂”的沉积特征,也许与此过程有关,详见后文。
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在冲积扇—辫状河—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中,受传统沉积模式影响,人们一直认为三角洲是沉积物卸载的最主要场所,砂体主要分布在三角洲相带上,而河流相(包括辫状河与曲流河)为长条形的相带,砂体分布有限。从上述干旱背景河流扇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陆上河流的反复改道与迁移形成的河流扇,同样发育大规模富砂储集相带[11]。我国陆相盆地众多,沉积演化历史长,古气候干湿交替频繁,沉积模式多样。因此,正确应用当代国际沉积学界上在内陆坳陷湖盆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和新理论,对提高我国陆相盆地油气勘探成功率、促进石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经济意义。
1.4 河流扇与其它相关沉积微相区别
从上述河流扇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在干旱环境下,洪水量向河流的下游方向不断减少,冲涮侵蚀能力也不断减弱。虽然河流扇上存在数条呈“分叉状”或“放射状”分布的河道,但在洪水季节,通常也只有一条河道是活动的(有水),其它均为废弃河道;在非洪水季节,这些河道处于干涸状态或存在由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少量水量。所有的这些特征,与在潮湿环境下,由于支流的汇入,河流向下游方向水量增大、河道加宽、侵蚀冲刷能力增大的情况大相径庭。
河流扇沉积容易被误认为是三角洲沉积,尤其是因为其容易与潮湿环境下的浅水三角洲体系相混淆。如前所述,河流扇的形成与河流入湖(海)处的三角洲分流作用无关,而是由不同时期的河流改道迁移和叠加所形成。它们在沉积过程与模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表1所示。
表1中清楚地表明,河流扇体系中河流并没有进入湖泊水体,而是消失在湖岸线边缘或者岸线以上区域,因此不能称为三角洲。实际上,河流扇所在盆地的湖泊水位受季节性降水控制,通常为雨季时存储一定水量,一旦雨季停止,湖水快速蒸发甚至干枯。例如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湖常年处于无水状态,仅是雨季阶段有水,因而Colorado河流扇体系不发育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13]。相比较而言,三角洲是陆上河流入海(湖)后形成的常具有扇形特征的沉积体,其形成与水体关系密切,既有河口区湖盆(洋盆)水体的顶托与分流作用,也有和波浪和潮汐有关的改造作用。就陆相浅水三角洲而言,其通常发育在水深数十米范围内[27],由于位于相对潮湿地区,所在湖泊水位较高,河流入湖,容易形成河口坝,进而形成分枝状模式[26]。

表1 干旱环境河流扇与浅水三角洲的区别特征一览表Table 1 Contrast between fluvial fan in arid environment,and shallow water delta in humid environment
除了河流扇与浅水三角洲容易混淆外,如前所述,在河流扇下游,由于频繁的漫溢事件形成了大量的决口扇。填平补齐过程促使决口扇沉积体相互叠加,形成面积更大的席状砂,而这种薄且分布范围大的砂体容易被误认为是三角洲前缘席状砂体[13]。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要搞清沉积背景。在以往的延长组研究中,可能正是被这种“席状砂体”所迷惑,所以才夸大了对三角洲沉积的认识。
总之,气候差异是导致河流扇与浅水三角洲及三角洲前缘席状砂在沉积环境、沉积模式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进行现代浅水三角洲沉积研究时,均以我国南方温湿气候条件下的鄱阳湖为例[26,28],而在研究河流扇或者季节性河流沉积作用时,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中国西北干旱环境下的新疆地区[8,29]或河西走廊与宁夏内蒙地区[30-32]为例。
2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满盆砂”成因模式讨论
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沉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是该盆地的主要产油层系,为一套连续分布的、厚度达千余米的碎屑岩岩系(1 000~1 500 m),前人根据沉积特征自下而上划分长10—长1共10个油层组,其中长7油层组为最大湖泛期,发育了盆地内最主要的一套烃源岩系—张家滩页岩。过去一直认为,整个延长组沉积期为温暖潮湿气候环境[33-34],受其控制,每个油层组沉积时期都发育了完整的河流—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只是不同时期湖泊与三角洲面积有大有小而已。近期,笔者通过野外考察及室内综合研究,认为延长组沉积期古气候具有干湿交替演变特征,其中在潮湿时期,汇水区面积大,湖盆发育三角洲沉积体系;而在干旱时期,汇水区较小或者不存在大面积汇水区,三角洲沉积作用有限,砂体以洪水主导的河流扇沉积为主。下面主要从古气候及沉积特征方面对延长组“满盆砂”成因做简要讨论。
2.1 延长组沉积时古气候具有三分性
大量证据显示,只有延长组中期(长7油层组沉积时期)为温暖潮湿气候,而延长组早期(长10—长8油层组沉积时期)属于干旱气候环境,晚期(长6—长1油层组沉积时期)属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
2.1.1 古生物证据
孢粉植物群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气候环境信息的重要载体,孢粉化石组合的发生、发展、繁盛和消亡与气候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孢粉组合与古植物群的研究能够恢复其生存时期的古气候环境[35]。本次研究的孢粉样品取自湖盆中心地区庆36井,通过对整个延长组孢粉化石组合的系统分析,显示各层位似乎鲜有自己独有的属种。但比较各种植物发育的丰富程度,差异还是较为明显(图2)。
长8—长10油层组蕨类植物孢子含量明显高于裸子植物花粉含量(分别占71.1%和28.9%)[36]。其中光面三角孢属占绝对优势,显示孢粉分异度相对较低,植物种类单调,指示气候较为干旱。
长8—长10油层组相比较,长7油层组沉积时期,植物的分异度显著增大,除蕨类植物孢子含量仍然较高外,裸子植物花粉含量明显增加,分别为55.8%、44.04%。植物种属也明显增多,蕨类植物中以光面圆形孢属(Punctatisporites)和旋脊孢属(Duplexisporites)最为丰度,分别达17.8%和13.68%,其次是紫萁孢(Osmundacidites)属,占8.02%。另外,还发现一定数量的松柏类植物花粉(如云杉粉属)和苏铁类植物花粉(单沟粉)。此外,前人在长7暗色泥页岩中还发现了大量介形虫、双壳类、鱼类化石及光球型疑源类、葡萄藻藻类等反映淡水沉积环境的化石组合[37],所有这些均指示气候转为潮湿温暖环境。
长6—长2油层组沉积时期以松柏类为主的裸子植物花粉含量有所上升,为51.82%,其中以松型粉属、云杉粉属、开通粉属、单脊双囊粉属等含量较高。此时,蕨类植物孢子含量相对减少,光面圆形孢属和旋脊孢属等含量较长7也显著减少。上述信息揭示,长6—长2时期的气候条件可能已经由长7时期的温暖潮湿演变为此时的相对干旱温凉。
2.1.2 稀土微量元素证据
许多学者利用微量元素特征对延长组气候进行过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区域不同,所选用的微量元素种类与方法各异,但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即延长组中期为潮湿温暖环境,早期与晚期为相对干旱环境。例如,张才利等[38]利用微量元素对长7油层组沉积时古水介质环境进行了分析,发现Sr/Ba值为0.19~0.65、Th/U值为0.36~5.03,V/Ni值为1.75~5.53,认为属陆相淡水还原环境。范玉海等[39]利用喜干型元素Sr和喜湿型元素Cu的比值对盆地西部定边—吴起地区延长组沉积介质环境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长8—长9的Sr/Cu比值总体大于长7,尤其长9的Sr/Cu比值大于10,认为该地区长9期气候较为干旱,长7期转为温湿气候。罗顺社等[40]通过对姬塬地区长8泥岩样品微量元素Sr/Ba比值的研究,发现Sr/Ba比值变化于0.1~0.4,平均0.24,显示湖泊水体为微咸水。最近,谭聪等[34]系统测试了盆地中下三叠统Sr/Ba变化规律,发现长10油层组与下伏地层纸坊组一样,具有较高盐度。水体盐度的变化与气候环境有关,较高盐度被认为是气候干旱、蒸发量大造成的[41]。此外,张新建等[42]利用稀土微量元素研究证实,延长组晚期为半干旱—半湿润环境。
2.1.3 深湖—半深湖面积分布证据
湖泊水体面积、尤其深湖范围增大—减小往往与气候的干湿变化过程相对应。不同时期深湖—半深湖面积统计结果表明(图3),延长组沉积期水域面积表现为震荡式扩张—萎缩特征,其中长10期主要为河流相,缺少湖相沉积[43],长9期湖盆开始发育,深湖区面积有限,仅占盆地总面积的1.24%,为4 336 km2(以厚度大于6 m的深色泥岩计算)[44],主要分布在盆地东南部志丹—富县一带。长8期未见明显深水区,其泥岩中普遍含炭质泥岩、劣质煤线及浅水生物遗迹化石,总体属于浅覆水沼泽环境。长7期湖平面快速上升,深湖面积达到最大,达65 000 km2,占盆地总面积的17.57%,水深达50~120 m[38],长6期以后湖盆面积迅速减小至26 781 km2,至长1期,除陕北子长地区残留有小面积汇水区外,深湖区基本消失[45]。上述特征同样反映了延长组沉积时期古气候环境由早期干旱转向潮湿再向干旱变化的过程。

图3 延长组各时期深湖区面积Fig.3 Areas of deep lakes in each period of the Yanchang Formation
2.1.4 古土壤证据
本次通过对陕北地区多条露头剖面(宜川仕望河、延河)观察与实测(图4a),在延长组下部的长10—长8及上部的长6—长1共发现了近20层古土壤,它们主要分布在河流相沉积韵律的最上部洪泛平原或者天然堤环境中,主要特征是岩石普遍呈疏松状,层理不发育,除个别颜色较深,可能为潮湿环境下形成外(图4d,e),大多数古土壤层的颜色呈现黄色与淡黄色,普遍见植物根系、垂直虫孔等生物遗迹化石(图4b,c),常伴生高岭土黏土层、钙质结核或铁质氧化层等。

图4 延河剖面延长组长7—长6段沉积相与古土壤露头照片(a)长7—长6段实测岩性柱状图(据邹才能等[28]修改);(b)长62顶面古土壤层(位置见图4b);(c)照片b的局部放大,淡黄色泥质粉砂岩中见大量植物根系,指示干旱环境;(d)长7顶面古土壤层(位置见图4d);(e)照片d的局部放大,淡灰色—黑色泥质粉砂岩中见大量植物根系,虫孔等,指示潮湿环境(注:白色双向箭头及数字表示古土壤层的位置及厚度)Fig.4 Sedimentary facies and paleosol outcrops of 7-6 member,Yanchang Formation(Yanhe section)
上述大多数古土壤层颜色、层理构造、生物遗迹等特征与前人在现今鄂尔多斯盆地东缘豫西地区的发现与研究基本是一致的[46-47]。豫西地区济源盆地油房庄组(与延长组长10—长8地层相当)、谭庄组(与延长组长2—长1地层相当)普遍发育古土壤及钙质结核,一般认为是干旱环境下沉积物(岩石)土壤化作用的结果。此外,在延长组古土壤层顶部,经常伴生有薄层有机质层如炭屑、植物碎片、炭质泥岩及劣质煤线等,有时还伴生泥裂现象,这些也代表浅覆水或干旱暴露现象。
2.2 延长组沉积中存在多期洪水事件层
受上述潮湿气候环境影响,长7油层组沉积期汇水区面积大(包含长63油层组),为湖盆发育鼎盛时期,全盆地以富含有机质的泥页岩(烃源岩)湖泊沉积体系为主,并广泛发育三角洲体系。这一时期湖盆中心地区的砂体主要为重力流成因或三角洲与重力流复合成因等,目前已有众多研究成果发表[48-51],不再赘述。
除长7油层组外,其它油层组砂岩均以河流相为主,单层砂体厚度几十公分到数十米不等,内部普遍发育平行层理、大型槽状、楔状及板状交错层理等牵引流沉积构造特征。在最近的野外考察中,作者在这些砂岩中发现了大量树木化石,其保存状态指示了这些树木曾遭受过洪水袭击,其宿主砂岩可能属于洪水成因。
树木化石大多分布在河道砂岩与古土壤层界面附近,一般树茎秆部分分布在砂岩底界面以上的决口扇砂岩中,根系部分保存在洪泛平原顶部的古土壤层附近(图5)。它们的形态各异,有的树木根系与茎干部分均保留完整(图5e~g);有的因受洪水袭击,茎干已被完全折断或部分折断,折断的茎秆或原地倒伏(图5a,b)或被洪水冲走缺失(图5c,d),残留部分与根系一起呈歪斜状态分布在地层中,歪斜方向指示了洪水流动的方向(图5a~d)。此外,在河道砂岩底部,常见大量呈定向分布的炭化植物茎秆,单个茎秆长度通常3~50 cm不等,直径在1~8 cm,显然,它们也是洪水事件的产物。

图5 延长组洪水事件地质露头特征(a)被折断的植物茎秆与根系一起呈斜歪状态展布,歪斜方向指示古洪水流向,延河剖面罗子山长9露头;(b)照片a的解释;(c)植物茎干大部分被折断缺失,残留的少部分与根系一起呈斜歪状态展布,歪斜方向指示古洪水流向,薛峰川剖面长3露头;(d)照片c的解释(;e)在地层中直立分布的树木化石,其根系部分宿主岩石为暗红色粉砂质泥岩,发育大量生物遗迹化石,显示为洪泛平原微相;茎干部分宿主岩石为含泥质粉细砂岩,块状,无层理,底面平直,显示为沉积速率很高的决口扇沉积,由此推测该树木当时位于河流末端低洼处,因洪水决口被一次性掩埋而成化石,延河剖面黑家堡长3露头;(f,g)在地层中直立分布的树木化石,其宿主岩性与照片e基本相似,照片f为延河剖面长4+5露头,照片g与照片e位置相同.图中蓝色箭头指示洪水流动方向,红色箭头指示化石分布位置。Fig.5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flood events in Yanchang Formation
上述特征充分表明,在2亿年前的延长组沉积时期,洪水事件频繁发生,这些形态各异的植物化石,正是遭遇了洪水袭击的结果,其宿主砂岩应该属于洪水成因。实际上,洪水事件形成的植物化石,在延长组各砂岩层段均有分布,这意味着大部分砂岩可能属于洪水成因,相关研究工作将另文讨论。
2.3 延长组“满盆砂”成因模式探讨
综上所述,延长组沉积的气候具有三分性,其中延长组中期(长7)为潮湿气候,汇水区面积较大,主要发育三角洲及重力流砂体,其沉积模式以湖泊—三角洲—重力流为主导(图6b)。延长组早期(长10—长8)、晚期(长6以上)砂岩沉积均以河道牵引流为特色,砂岩层与层之间常被干旱环境古土壤层所分割,砂体内部沉积构造主要为平行层理、大型交错层理,常见植物茎干化石及泥砾,总体反映了一种反映水浅流急、水动力强、河道摆动频繁、水体间歇性活动的特征,结合前述的干旱气候特征,作者认为属于河流扇沉积(图6a)。其形成大致过程是,在长期的干旱环境下,由于强烈的机械物理风化作用,在盆地内部及周缘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细粒碎屑物质,当百年或千年一遇的暴雨发生时,地表径流或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沉积物从四面八方向盆地中心方向推进,由于蒸发与下渗作用,大部分的洪水会消失在干旱湖盆岸线以上的沿程路径上或者荒漠中,同时在湖盆岸线附近形成泥沙沉积物堆积区。由于洪水事件经常伴随着河流改道,多次这样洪水事件与河流频繁改道,最终在湖盆中心地带形成类似三角洲一样的扇状砂质沉积物,这也许就是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满盆含砂”形成的原因。

图6 延长组沉积模式图(a)干旱时期的河流扇沉积模式,图中揭示在干旱环境下,陆相盆地汇水区面积较小,主要沉积单元为洪泛平原、河道与决口扇,河流扇中的“扇状沉积体系”主要由洪水期曲流河决口、改道迁移而形成;(b)潮湿时期的湖泊—三角洲—重力流模式,图中揭示在潮湿环境下,陆相盆地汇水区面积大,主要沉积单元有河流、三角洲,深湖—半深湖及重力流沉积。Fig.6 Sedimentary model of fluvial fan of Yanchang Formation in arid period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的大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延长组砂体成因为“湖泊三角洲”或者“浅水三角洲”观点[28,52-55]。如前所述,区分两者的关键是要确认是否存在一定规模的汇水区以及河流是否汇入到了水体当中,笔者认为这需要结合古气候、古地理以及岩性岩相等多方面的资料综合判断(详见表1)。
3 讨论与结语
湖盆在不同沉积演化阶段,通常具有不同的砂体成因类型。过去人们一直沿用一种固定模式即三角洲模式来解释延长组所有的沉积体系与砂体分布,导致整个延长组从长10到长1表现为一种“满盆三角洲”的沉积格局,这在现代沉积中很难找到实例,令人费解。
笔者从前述古气候演变角度出发,认为延长组中期长7油层组(在湖盆中心地区,可能包含长63油层组)沉积期为湖盆发育鼎盛时期,气候温暖潮湿,汇水区面积大,全盆地以富含有机质的泥页岩(烃源岩)湖泊沉积体系及三角洲—重力流体系为主;延长组下部长10—长8与上部长6—长1油层组沉积期,气候炎热干燥,湖盆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缺少大面积汇水区,全盆地沉积以河流扇为主。
在以往延长组沉积研究中,夸大了三角洲的沉积作用,实际上许多砂体是干旱背景下、由河流作用形成的事件沉积,即河流扇,与三角洲作用无关。河流扇体系的砂岩与潮湿环境水进域富有机质泥岩相匹配,十分有利于大型岩性油气藏的形成,从而使延长组由“满盆含砂”变为“满盆含油”。该研究完全改变了以往大型坳陷湖盆以“三角洲模式”为主导的传统认识,对丰富发展陆相盆地沉积理论认识及指导油气勘探实践均有积极意义。
致谢 阿根廷南方国立大学Carlos Zavala教授参加了野外地质考察工作,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