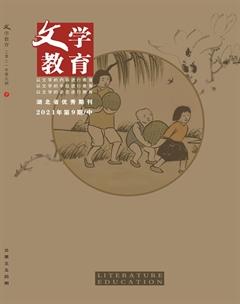郝敬东散文集《西路苍茫》读评
今年六一,天气陡然热了起来。我坐在电脑前,读郝敬东先生的散文集《西路苍茫》,我的身心仿佛跟随着他在祖国大地驰骋穿越,风的倩影擦身而过,清凉随之而来。
美丽的画面一帧一帧在眼前展开,意境的湖水开始蔓延,持久的快意让你感觉不到疲惫。
郝敬东先生足迹所到之处,风光迤逦迷人。把这些风光用文字呈现出来,确非易事。倘是照相,就直接明了,文字的描述首先需要經过大脑的接纳然后再外显出来,时常会感觉到字词的匮乏、苍白和无能为力,郝敬东先生有很好地文字功底,遣词造句,结构语言,如同常胜将军调兵遣将,井井有条,各得其所。
清晨的太阳,却那般明丽,照在山顶上特别耀眼,与还未被阳光照着的硕大山体形成强烈的阴阳反差——山顶是草,一抹亮绿;山腰多树,一片黛绿,乍地一看,有一种失真感。这里已是典型的藏区,路边就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石墙红檐,白塔金顶,与其遥遥相对的北山半腰,成圆锥状缠扎的五彩经幡(印有佛经、佛像等图案的丝质布块,有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缠挂的色序不可错乱,分别象征天空、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像是搭建在山上的一间花屋,甚是惹眼。(《西路苍茫》)
这里关于新都桥的描写就颇见功力,给读者展示了一幅美丽迷人的画面。同时,由于文字表现的间接性,又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长篇散文《西路苍茫》中,这样的描写俯拾即是,比如:
借着晴朗通透的好天,我们在色季拉山山口停车观景拍照。远处的南迦巴瓦峰呈三角形的巨大峰体覆满了冰雪,峰顶似一柄直刺蓝天的战矛,寒光熠熠。据说,因其积雪终年不化,云雾常年缭绕,真容从不轻易露出。而我们轻易不来,来则即幸运地远观到了这座“西藏冰山之父”的真身。
远望南迦巴瓦峰,冰雪覆盖,峰顶似一把长矛,寒光熠熠,一下子就在读者心中建构了一幅雪峰图,雄伟和凛寒的意境在读者思维中弥漫。
如果仅能如此,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散文家,顶多可能只是一个会写下水作文的语文老师。
有人说,情感是散文的灵魂。无论是描写风光,还是叙述情节,或者是刻画人物,都饱含作者的情感。
《西路苍茫》中写了作者到过的很多地方,不论是国内的名川大山,知名州府,还是襄阳本土的山山水水,作者都是饱含深情地叙写和描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西路苍茫》时,时常被文中深深的情感所打动,情感的共鸣打通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审美的通道,读者情不自禁地被作者带入了某个场景,某个时间的断面,和作者同喜同乐。
我依窗观河,咀嚼出了两种风景——长江像一个深沉的汉子,有一种古朴、雄伟、刚劲的美;大宁河则似一位纯朴的村姑,初次见面,一种清纯、野性、飘逸的美,很是让人沉醉。(《沧浪悠悠小三峡——大宁河纪事》)
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比喻,形象地展示了长江和大宁河两种不同的美,两个比喻的喻体都是很美的,汉子的古朴、雄浑、刚劲,村姑的清纯、野性、飘逸,因为作者对这两条河充满了情感,他才会想到这些美好的喻体,才会用如此美妙的比喻来形容这两条河。
面包车在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草原上驰骋,车灯再怎么耀眼,也只能照出草原的一抹细线;偶尔,在微弱的天光下,好像看见远处安静地矗立着圆形的毡帐;高低不一的岗丘不时隆起伏下,把天幕亦拉扯得有了一丝动感草原的夜,变得更加深沉了……(《醉在乌兰察布》)
作者对乌兰察布充满热爱之情,才把她描写得如此美丽。作者把深深的情感寄寓在描写之中,透过这些描写草原的美妙句子,我们仿佛听到了作者快速的心跳,仿佛看到了脸上泛起的红晕,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原来,向往草原的梦境就是这样与现实相遇的呵!这一句,已经直接抒情了,赞美,已经溢于言表。
《西路苍茫》这篇数万字的长篇散文是整本散文集的“重头戏”,这篇文章里,更是可以窥见作者深深的情愫。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者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厚情感。比如:
小城的夜晚安静之极,人声、车声、市声全无,偶有狗吠,当然还有江水的声音,却使小城的夜晚更有了一种永恒的宁静。半夜风起,是阵风,动静很大,夏天的风却如朔风,呼啸而过。原来,这是因为朗县南靠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北依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南北两山组成一个巨大“∨”形谷地。谷地易生风,风生水起,水助风势,风便格外“爽朗”、格外“显现”(朗,藏语意为“显现”)了——朗县,名副其实呵。
我们读到这里,难道没有感受到作者对朗县的喜爱之情?
情感的直接抒发,富有冲击力,恰当地运用,会增强文章的气势,增强感染力。与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把情感隐藏在描写之中,隐藏在叙述之中,隐藏在字里行间。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这个意思。郝敬东先生深得此道,他的很多景物描写、场景描写,包括一些叙述的应用,都是蕴藏了很深的情感的。
阳光静好,风轻气爽。上得江堤,豁然开朗。宽阔的汉江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清澈,江北的樊城、甚至江东北更远处的襄州,在如洗的碧空下,林立的高楼竟然一眼望不到尽头;正东方向的鱼梁洲,被浩渺的碧波环绕,一如静静的处子,孑立一隅,独享清宁;往西回望,汉江铁桥飞架南北,往来的汽车忙而有序,偶有列车驰过,铁轮滚过铁轨,声响铿锵有力。(《徒步古城外》)
这段描写,作者怀着对襄阳深深的热爱之情,为生在襄阳而自豪,每一笔描写,仿佛都是作者深情的吟哦。作者对襄阳的热爱,真是欲罢不能,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向读者展示一幅又一幅故乡的风景画、风俗画:
临江的滩涂上,牛羊正悠闲地咀嚼着青草。当然,临江不只有滩涂,还有一片水杉,大约四五公顷,密度略厚,树干挺拔,横竖成排。三五成群的市民,或在林间拴上网状吊床,或在空地搭起纱质帐篷,怡然自得地躺进去享受着从树梢间渗漏下来的阳光,聆听着微风轻激、细浪拍岸的江波……
散文需要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让读者在阅读之中跟作者在审美上结为统一战线,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好的散文。优秀的散文家不会就此止步,他们往往希望将自己的价值观,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判断传达给读者,他们会在文字的波浪之下沉淀自己的思索,或者说,对作者进行精神输入。
郝敬东的散文就具备这个特点。
在《西路苍茫》一文中,作者写了三江源:2003年,经该联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三江并流”作为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正式成为伟大的“世界自然遗产”。
接下来,作者写道:人在旅途,看山看水,总会想到山的前生、水的今世。今日之“三江”不再是“藏在深闺人不识”的处女地,它们正在被现代科技改变着亘古未变的命运。现代勘测表明,“三江”水能资源总量达17880万千瓦,其中可开发14100万千瓦。沿途我们看到,刷写着华电集团、华能集团、水电工程四局、八局、十二局等字样的水能开发团队,在“三江”主流及其各个支流拦河筑坝,机声隆隆,尘土飞扬,开发场面极为壮观;一些河段已是水坝巍然屹立,发电尾水欢畅喷涌。
壮观的场面描写之后,是作者的思索:
我不知“三江”流域在建和已竣工的电站装机容量有多少、发挥的效益有多大,也不知还有多少个电站在等待被规划、被开发,但在心里总为美丽的“三江源”感到失落与遗憾。人在大自然中真的能够人定胜天吗?真的能够主宰一切吗?
其实,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人定胜天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作者虽然语气委婉,但立场其实是鲜明的,这种委婉的语气反而会更加坚定读者的某种思考,更加坚定读者的是非判断。
像这种思索还有很多,比如在《大宁河记事》中叙述了很多小孩子向旅客兜售三峡石的孩子的情节之后,作者写道:同许多游客一样,面对一群群兜售三峡石的孩子,我前后掏了四五次腰包,破费虽然不多,但心中隐隐作痛——这些孩子,本应是天真可爱的读书郎啊,可此时此刻,他们的天地不在学堂,而在枇杷洲的市场玩着小聪明,去讨得游客的可怜施舍。孰轻孰重?哪长哪短?开放而封闭的小三峡啊,你可曾知道?可曾想过要改变这一扭曲的价值取向?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作者用行动做了回答:我只能默默地把“买”来的一把把满河皆是的石子,一粒一粒投还给处子一样的大宁河……
郝敬东先生就是这样带着情思启程,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也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不舍跋涉,把一篇篇优美散文呈现在我们面前,带给我们美好享受。
什么是好的散文,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话题。谢有顺教授说,有一种散文是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的,它并不适合阐释。我以为这就是真正好的散文,郝敬東先生的散文大抵属于这一类。
应该说,郝敬东先生的散文已经写得很好了,不过还有提升的空间,还可以写得更精致一些,更纯粹一些,语言的个性化还可以更突出一些。对于小说而言,能让人们记住的话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出人意外的情节,而散文若能产生影响,多半是因为有突出的语言风格,避免了同质化,展示了自己的语言个性。其实,这也正是我个人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出来跟郝敬东同志共勉。
好散文不好阐释,只适合阅读回味和享受,我建议在这本《西路苍茫》正式面世后,爱好散文的朋友们来认真阅读回味和享受,从中体味它的精妙之处,我希望在这样一次美的享受的队伍中和朋友们相遇。
散文让我们记住彼此,文学让我们携手而行。
温新阶,著名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