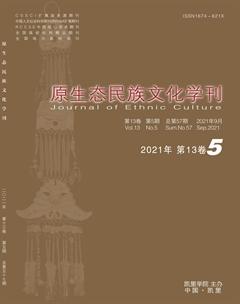视物有命:华北乡村营生方式变迁中的信仰民俗
杨化强
摘 要:鲁西北L村对机动车的崇拜现象,是在相信动物有灵的地方知识语境下,因为生产方式和工具的变迁,民众将对传统农耕牲畜的情感转嫁到现代营生工具——机动车之上而形成的。这一现象由对车的“供养”时间和仪式、人与车共同的生产叙事等构成,而“车神”却并未出现在这一现象之中。经研究,其本质是乡村民众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具象化表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乡村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过程中农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而使得物的社会生命具有了情感色彩。这对当下信仰民俗研究、包括现代民具在内的物的研究以及乡村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乡村;生产;生命;车;信仰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70 - 10
当代华北的信仰民俗研究,多是以庙会为中心,通过庙会来探究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尤其侧重于探讨民众信仰与地方权力秩序的建构关系,整个信仰民俗研究也多是围绕一个神以及相关的民众活动来进行论述。其实,信仰民俗在微观层面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现象,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发现更能凸显出变迁过程的轨迹,这些细微的现象能够更细腻地展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与以往学界侧重于传统“神”的信仰研究不同,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时代变迁背景下关于“物”的微观信仰。在本研究的田野点华北L村,这一物的信仰被具象表达为村民们对自家机动车的崇拜现象。当地的村民们每逢春节都要装饰、祭拜自己的机动车,然而这种祭拜的背后并没有发现车神的存在。所以,车神不存在的现象将我们直接的关注点聚焦于物,即车自身,于是便产生了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即这一拜车现象背后的形成逻辑是什么?它反映了村民怎样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变迁历程?为此,笔者将从两个层面加以探究。
首先,在乡村语境下,笔者将机动车划归为民具范畴,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呈现出村民生产和生活的变迁轨迹。民具属于物质文化范畴,“物”一旦与人发生关系,其便拥有了社会生命,民具便成为“庶民生活的见证”[1]。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器物(material artifacts)、符号和象征(signs and symbols)以及分析物之“意义”(meaning)三个相互交错的立足点[2]。阿帕杜莱在“面向物的人类学”(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ings)专题章节中,即提出“物”皆有成为商品的可能性,而商品则拥有社会生命[3]12,其意在强调回到“物自身”来研究“物”。而目前以民具为代表的物之研究多侧重于传统物件和“特色民具”[4],而相对忽略机械器具,就像彭牧所言:“民俗学从学科肇始关注的核心即是与大机器生产和现代科学知识相区别而日益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地方性知识。”[5]126在生活革命的大环境下,机械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及其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而这恰恰被民俗学所忽略。近年来王宁宇主编的《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陕西合阳县传统农耕器具向机械化转变的现象与原因,但是仍旧以记录为主[6]。而詹娜则非常具体地阐释了北方沙河沟村传统的农具在农民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意义[7]105。但周星从物质文化研究体量角度认为:“基层村落的物质文化研究仍然显得非常稀少。”[8]40这便是从民具范畴探讨物之信仰的价值所在。其次,在具体的分析方法层面,主要以叙事分析为主,即分析他们如何通过讲述物的故事来无意识地呈现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生活的变迁,以此来探究物被赋予情感和信仰因素的方式。在整体的宏观背景中,叙事可以建构民族的辉煌与苦难[9],而具体到个体也同样如此,村民们在讲述他们使用、保养车辆的过程中,也是在无意识地讲述他们个人的生命以及生活的变迁历程。人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实践和叙事赋予车辆以生命,这也造就了物的情感生命,物不再仅是一种商品,而是通过叙事被建构成为具有“人性”的特殊存在。
本文以鲁西北L村为中心,在完整的村落营生方式变迁语境下,从最贴近民众生产生活的运输工具及其与之相关的俗信活动——有“拜车”仪式却未见“车神”——现象入手,致力于跳出信仰和地方权力秩序研究的窠臼,从微观的民俗志角度来探究当下乡村民众的精神世界,深入到民众的心理层面,最终落脚于新时代下人们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明,回归到民俗学通过“俗”来研究“人”的学术归旨。其实,阿帕杜莱回到物本身的研究,其一个内涵层面也即是“人”的研究,是人的行为活动激活物的存在,“在理论上说,是人的行为给予物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视域下,却是运动中的物,说明了人以及社会内涵”[3]13。与阿帕杜莱不同的是,笔者不是以商品的特性来探究物的流动与价值,而是在物的“使用”层面来理解人的情感及其话语表达方式。这也就是王铭铭在总结季羡林和西敏思两部糖史研究后所说的启示,即“在‘观物见人中,学者能够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生活的微妙层次,能发现所谓‘无意义之物的‘隐藏意义”[10]。
一、鲁西北L村营生方式的变迁
(一)L村的地理环境与营生方式
L村地處山东西北部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地带,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两年三季的耕作制度。芒种前后收小麦,紧接着种下玉米,中秋节前后收获,而后种下越冬小麦,次年芒种收割,如此循环往复。较早的耕作方式是用耕牛,这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零星存在,一些家庭还在饲养驴、骡、牛等牲畜作为劳动生产工具。而运输方式在同时期则是人力拉车、人驴或者人骡协作等,之后就有了拖拉机等农用机械的普及。当时基本是以家族为单位合伙购买,而后日渐以家庭为主独立购买,至现在,一个独立的家庭通常有多种农用机械,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村民ZT说,“以前割个麦,两三个月,那可真是个大活,割麦子、压场、硌场、挛穰,可累人了。现在都是联合收割机,有的户麦子都不进家,直接送到粮点,两三天就完事儿。”现在的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割几乎全部机械化,播种机、旋耕犁、大型联合收割机、粉碎机等多种机械的出现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使得农民有了充足的体力和精力进行农作之外的多种经营,目前L村从事与运输有关的行业有物流订单运输、建筑材料运输、粮食收购运输等,这些行业的收入基本都超过传统的耕作。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传统耕作的收获量除去交给国家的粮食,剩下的部分基本只能自足,当地有个名词叫作“落柴草”,即收获的小麦和玉米秸秆等会成为农村锅灶的主要燃料和饲养牲畜的饲料,像玉米的包皮内层较嫩的部分还会成为编制一些器具的材料。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和增加一些补贴之后,据当地人粗略计算,1亩地1年的收入大概是1 000元,但从体量和现代家庭支出角度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很小的收入。
总之,在人们需求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过程中,传统农耕带来的物质财富仅限于基本的生活保障。“穷则通变”,L村村民根据当时的环境开始探索生存门路。
(二)“拉麦秸”:一时兴起的致富门路
在外出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在当地普及之时,L村的村民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门路,他们将自家和邻村收麦剩下的秸秆用车运输到临县的造纸厂,从中间赚取利润,因为是当场结算,所以“来钱直接”,几乎全村的男性劳动力,或是几人搭伙,或是夫妻搭档,都参与到了这一门路当中。最初,是以人骡(或者驴)结合的方式运输,牲畜在前方拉车,人用两手在后撑住车架,徒步前行,此时主要以男性为劳动力。之后,有了用拖拉机运载的案例,其速度快、载量大、行程远,人们纷纷效仿,此时夫妻搭档成为主流,一时间,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了拖拉机,在农忙时节负责耕作任务,农闲之后专门搞秸秆运输,这极大地提高了村民们的收入。20世纪90年代末,彩色电视机、VCD音响等潮流设备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了L村的家庭。L村在当地以“拉麦秸”出名,村庄在时任村主任的带领下,曾经建造了一个秸秆集散市场,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向省道的“石碴路”来方便运输车辆的进出,至此,这一致富盈利达到了顶峰,当地人看到“拖拉机拉大车架”的形象就知道是L村的人,“拉麦秸”俨然成为L村在当地的“符号”。刘铁梁曾就北京房山区的农民劳作做过调研,他认为当地人编筐的身体劳作模式增强巩固了村落认同[11],与之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L村是“人 - 机”共同的劳作模式,造就了本村村民自身以及村落在地方社会的身份认同。但随着联合收割机、秸秆还田等技术的影响,秸秆资源日渐枯竭,同时,在造纸厂污染和效益降低等多重原因的综合打击下,这一致富门路的运输利润极具下降,村里的秸秆市场也最终倒闭。村民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多元转向,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或做城镇零工,剩下固守乡村的人转向了各种运输、养殖等行业。已经改行的村民ZG说:“那时候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就是只顾着往下比,没有往上比,当时外出打工的现在很多都混好了。”他的妻子补充说:“那时候一趟能赚个二三百,后来就不行了。”现在他自己有两辆车,专门运输碎石子、砂子等建筑材料,另外还承租了二十几亩地,家中另外配置了播种机、旋耕犁等农用工具,这些机械是其日常经营、季节生产的必备工具。
“拉麦秸”可以说是L村的改革开放时代,快速、高额的利润回报使得很多家庭的收入倍增,促使了生產和营生工具的快速更新换代,尽管其没有一直延续下来,但是“车”的出现让其活动范围扩大,营生方式多样化。如今,“车”已经成为村民生产、经营和外出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完全取代了之前的骡马、人工时代。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世界里,“车”不仅能带来方便,还能带来财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家中有其特殊的位置,这一位置在春节的时候最能体现出来。
二、车的“供养”时间和仪式
“供养”,作为动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持,多是侧重于低级对高级,而且在宗教信仰领域最为常用。L村所在的当地人通常在用贡品祭祀神灵或祖先时才使用该词,而且都是连续两词,即“供养供养”。现在的“供养”仪式也很简单,奉上贡品、点香、磕头。平时,村民家中凡是煮饺子、蒸包子或者油炸一些食物的时候才会专门在家中的各个神位“供养供养”,但只是简单象征性地将贡品在神位前“驻足”一两秒,不会下跪磕头,只有在春节这样的特殊阈限中才会行此大礼,此时的“车”也会具有神格意义。
在中国的民俗实践中,一般新车进家门亦如进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往往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新车会被主人系上红色的布条,然后燃放鞭炮,有的也会摆上香炉,甚至还会邀请一些宗教人士做个法事。设置一个“阈限”礼仪、通过仪式,将车正式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民间信仰层面,“红”也代表了喜庆和驱邪,意在表达红火、喜庆、禳灾、平安,当然也包括财富,这样新车在进家门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在平时,除了日常的保养维修之外,并不能明显看到与车有关的仪式性行为,但是在春节的时候就明显不同了。
L村一般在除夕当天的白天贴春联,除了门窗的对联之外,像家中的各类工具、器械等都会贴上大大小小的“福”,以喻来年的使用顺顺利利,不出问题。这与周星笔下的江南地区也相似,“江南地区的农民在过年时,总是要在农具上‘贴红,有的人家在祭祖时往往也要摆上农具或用于制作农具的工具等”[8]45。而在L村,车辆就格外特殊了,除了前后会贴上“福”字,另外车的正面也会贴上对联,比如,“车行千里路,福来万贯财;横批:一路平安或者平安是福”,意为平安和财富。同样,牲畜的居处会贴上“福”字,下面附上“六畜兴旺”“槽头兴旺”等条幅,随着牲畜逐渐被机械化的车辆所代替,以上两联在当地已经极为少见了,只有一些喂养家畜的老人家中才会偶尔看到。同时,家中会用截断的纸质包装酒盒、瓷碗等制作成简易的香炉,中间填满粮食或者草灰,分别放在自家的神位之上,如“天爷爷”(玉皇大帝)、灶王、财神等,待年夜饭前插香使用,其中还会准备香炉为自己家的车辆使用。男主人还会用黄纸折叠成“元宝”,在除夕晚上的神位前烧掉。
白天忙碌完之后,晚上正式开始过节,全家人一起放鞭炮、吃饺子,不提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到了凌晨,即正月初一的0:00(现代当地的年夜饭都提前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一家人准备吃年夜饭。这时,村民ZT点燃一捆香,在家中的每个神位(包括车前)前各插三支,妻子在锅中取出三只刚煮好的饺子,盛放在带汤的碗中,并在碗上整齐地平放一双筷子,交给丈夫。丈夫端着碗恭恭敬敬地在每个神位前洒下一些汤,以示供养;同时,吩咐儿子在神位前,烧两个“元宝”。当走到自家的机动三轮车前时,他吩咐儿子:“这车今年为咱家出力了,多烧几个元宝。”在供养结束之前,锅中的饺子是不能吃的。供养结束后,ZT和妻子分别在各个神位前恭敬地磕三个头,心中饱含祈祷,在自家车前也不例外,车的待遇和诸神并无二致。尽管如此,但并未见到家中供奉有“车神”。这些仪式结束之后,家人才会聚在一起热闹的吃年夜饭,然后相聚在一起去拜年。
这些仪式比之一些宗教仪式来说,可谓是简约至极,但这一简单仪式的背后却透露出民众生活世界的诸多“心意现象”1。首先他们拜的是“车”还是“车神”?通过访谈观察,笔者发现在他们的信仰世界里根本就没有车神,相对而言他们相信有“路神”的程度会更高一些,如果存在“车神”,那么就应该像“拜佛”“拜仙”一样,通过信仰装置看到背后宏大的宗教信仰体系,而“车”本身在其地方性知识体系中也未见相应的信仰体系。因此,他们拜的并不是“车神”,即“拜车”却未见“车神”。
其实,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较少存在“车神”,倒是路神更突出一些。姚晨晨曾对山东淄博石马庄的车神崇拜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在当地的信仰体系中,的确存在“车神”和相关的祭祀仪式等,并且还有《车神佛》经卷,类似于南方的宝卷,里面言车神老爷姓陈,车上的灯、方向盘、刹车都被冠以佛、菩萨、老爷或神仙之名,总体意在保出行平安,以“弥陀佛”结尾[12],很明显是各类宗教信仰在民间杂糅的产物,而且主要是针对汽车而产生的信仰创造。其祭拜有专门的供桌和贡品,挑选六月和十月的“好日”。而李金发笔下的彝族塔冲村“车神”则是与传统的毕摩巫术结合,将其信仰与祖先、山神结合,使其拥有了“保平安、带财富、旺子孙”的功能[13]。而在近几年的民间信仰现象中,“车神”的形象也被塑造出来,比如河北保定易县奶奶庙中的车神,清华大学徐腾写道:
一位神仙端坐于神坛之上,手握一个方向盘,保护人们出入安全。一旁有简易的壁画告诉路过的人们,如果不来朝拜,将会出现驾车安全事故。
奶奶庙将造神的权限向承包户开放,承包户则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出各种新型神像,车神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一尊新神仙[14]。
以上无非都是民间需求和经济运作之下的“造神”现象。在公共空间下的车神,主要是以“安全”为主要的功能,是汽车流行之后产生的文化现象,古代仙人与现代方向盘的结合属于信仰的再生产。亦如布鲁范德笔下那些消失的搭车客,它是美国汽车文化兴盛背景之下产生的文化现象,二者本质是一样的,皆是民间应对现代化的产物。
“车神”的功能是人们对技术世界不安因素的朴素应对,诸如“车祸”“车损”“抢劫”等意外事件,人们选择在传统中挖掘一种心灵慰藉。在L村所在的地方知识中,笔者并没有发现“车神”,甚至很少人提及“路神”,一些车辆的“突发”事故,往往会归结在事发地点有“不干净”之物作祟。不同于“车神”崇拜,L村人对车的祭拜,虽然也囊括了平安之意,但更多的是与情感和生产有关,这在当地人们大量的情感叙事中得以体现。
三、从“牲灵”到“车”的生命叙事
语言学家罗兰·巴特曾说:“任何的阶级、人类族群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被其他不同的乃至相反文化背景(雅俗之分)的人所欣赏,叙事与文学性的好坏无关,它就是生活本身,跨越國家、历史和文化。”[15]叙事本身就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故事是“作为人类体验、意义赋予和现实建构三者的交汇点”[16]。叙事研究在探究民间精神世界当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优势,正如应星所认为的,叙事研究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17]。春节作为特殊的时间阈限,其中的“拜车”现象可以被视为一种事件,事件是日常生活的中断或者集中体现,理解事件势必需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L村的生产工具从以前的“牲畜”逐渐被现在的“车”替代,他们相关的叙事话语在表面形式上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其叙事的内在逻辑似乎仍旧在遵循传统。
在L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般称干重体力活的大型牲畜,如牛、骡、驴、马(比较少见)等为“牲灵”,有时候也称“牲口”,但是在富有感情的聊天谈话语境中,多是称“牲灵”。仅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其对于村民的特殊性,在传统农村,牲畜是一个家庭主要的生产力,就像杨懋春所定义的中国农村家庭,其“不完全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家庭是家庭成员、家庭财产、家庭牲畜、家庭声誉、家庭传统和家庭神祇构成的复杂组织”[18]。虽然牲畜不会完全等同于人,但是在这一家庭观念中,人对牲畜存在着复杂的情感。在当地人,尤其是老人关于动物的闲谈之中,经常可以听到“可不能活摆1某某动物”的话,这样的话要么是就某一件事发表感慨,要么是用来教育下一代人。笔者在他们的聊天中听到另外一个张村的老人,自己家的羊下崽,他要专门熬一些“益母草”给母羊喝,俨然是“人”的待遇。当地还流传着关于某人杀害黄鼠狼和蛇等动物而遭遇个人或者家门不幸的故事,虽为故事,但是故事的主人公都能具体到村里或者当地其他村的某个人,这与北方关于狐仙、柳仙的信仰传说很类似。无疑,这种文化背景影响了人们对于动物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影响最大的仍旧是牲畜的生产力及其带来的财富。
村民YQF老爷子夫妇(年近八十岁)至今家中仍饲养着山羊和鸡,他们讲述自己以前养过牛、猪等牲畜,为干农活也为卖钱。村民YQF说:“比方说准备卖这些牲灵,以前都是有说法的。不能守着它们说,其实不说它们也能感觉得到。你要是说明天卖猪,第二天就不好逮。卖牛,有的牛也淌泪。”卖牲畜可以为家庭带来不少的可观收入,尽管在言谈中村民会露出一些不舍的表情或者语气,但是相对于家庭必需的收入,他们更多是喜悦的。像骡马这种大型牲畜,村民ZT也说:“以前骡子都记路,懂人性,出去拉麦秸回来的时候,直接在车上睡觉就行,它自己就能把我带到家里来。”在忙碌一天之后,男主人通常会将其牵到街上或者平整的土地上,让其尽情地来回“打滚”,按当地人的说法,这样能让骡马得到很好的放松。其实这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像詹娜笔下沙河沟村的“胡三太”“二虎马”等,都是村民眼中极懂“人性”家庭牲畜[7]106。可见,无论是饲养、经营还是贩卖,大型牲畜都被村民赋予了情感。
当“拉麦秸”活动刺激了生产经营工具逐渐机械化之后,农用车、汽车等中大型机械成为主角,村民的经营方式也逐渐多样化。村民ZXQ女士家,在放弃拉麦秸之后,买了一辆马力更大的中型拖拉机,专门从黄河南岸的采石厂、采砂厂向河北岸的建筑工地运送砂石等建筑材料。ZXQ女士回忆道:“那时候拉着十几吨重的砂子,过黄河爬斜坡,憋得那个车嗡嗡地响,听得都心疼地慌,我都替它使劲儿。”村民ZT在放弃拉麦秸之后,买了一辆二手农用机动三轮车,做起了运输粮食的生意,他在村民家中收购粮食运往收购点,赚取中间的运输费。他讲述有一次自己家的三轮车,因为前轮老化,被迫在故障中运营,在完成最后一次运输生意之后,前轮的机械彻底故障不能动了。车主当时说:“我过年得给它多磕几个头,活也干完了,前轮也不行了,没耽给(耽误)事儿。”他还讲述了有一次自己忘了加油,也是在完成当天的生意之后,车才彻底抛锚;他还说自己的车都快到了报废年限,但是自己保养得好(大谈自己的保养技术),机器运作依旧很好。最后,还不忘夸夸自己多年前买的拖拉机(已经锈迹斑斑),说:“那个车也下大力了,以前耕地、压场、拉麦秸没少干活,现在很少用它了,但是机器还特别好,从买来一直没有大修过。”总之,他想对笔者表达,自己的车都很辛苦,“就像也懂人性”一样,没有耽误生意。
这些零散的日常叙事,建构了人与车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日常的叙事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春节的除夕之夜,他们会有为车设香炉、点香、烧纸、磕头等仪式性行为了,也能理解为什么看到了“拜车”行为却没见“车神”,甚至在地方知识中也未见“车神”的原因了。从家中作为劳动力或者财富的“牲畜”到作为重要营生工具的“车”,似乎都是有“生命”或者“灵性”的,它们被劳动者赋予了感恩性质的“情感”。
四、生产、生命与“信仰”
生产角度的动物保护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就早已有之,像《周易》中的大畜卦、《周礼》中的“牛人”、西汉“杀牛者弃市”等思想制度,皆为生产、祭祀和战争服务,三者都关乎国运。有些被宗教引入,发展出了相关“护生”“放生”的思想和行为实践。其实,正是生产让人们对“物”产生了不同的情感,使得“物”拥有了生命情感。不同于人们对于诸如“猫狗”等家养宠物、“文玩”等器具的特殊感情,也有异于易县奶奶庙中的车神信仰,L村人对于“车”的情感是与他们的生存、生活,乃至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变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民众内在的一些精神还是传承了过去时代的一些特质。当与人们生计有关的社区“核心文化系统”(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提出)受到外来器具的冲击时,其“外围文化系统”也会随之改变,但“在相同社会条件下,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变速是不一样的,前者快于后者”[19]。传统的饲养技术,是内含有情感元素的,只是工业文明、生活革命带来了产业化,人们进入现代技术世界,物在很大程度上仅之为物、没有命,一切被理性化、扁平化。但技术世界中,饲养技术在传统的思想惯性下演化为车的“保养技术”,物仍旧有生命,从饲养到保养,机械存在了生命体特征,这是人的情感折射。这种感情有些类似于民间信仰,也存在一些功利性的色彩。在变迁的时间纵轴下,生产、营生方式发生改变,也代表着某位成员“祭祀”地位的变化。2019年因为L村所在的地方政府发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很多停放在街道边、不常使用的农用车被集中安置在村庄的若干空地,村民ZT的拖拉机也在其列,也因为如此,夫妻二人说过年的时候忘了去“供养供养”。相对而言,进入公共空间的车辆可能影响了较为私人化的供养仪式,但主要原因还是拖拉机不再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神圣性”被弱化,这也符合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功利化特征,与自家三轮车不同,村民ZT对拖拉机虽然仍然充满了感谢之情,但这种情感已经储存在了过往的记忆之中,而不是正在进行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其和之前的“淘汰”农具一样,逐渐被对象化了。
《消失的搭车客》是美国汽车文化流行的产物,日本出租车的灵异传说,也是带有“灵”的叙事,但其主角仍旧是人而非物,网络一度热传的“车神庙”,主角是神,本质也是人。无论是早期的牲畜还是现在的车,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农具,都是他们生产生活变迁的见证,机器也印证着他们的汗水。L村人在向笔者表达车的辛劳时,似乎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想象的灵性,看似是沟通人车共同经历的媒介,实质是人们与自己过往、内心的对话。就如詹娜笔下的沙河沟村村民所认为的:“那些‘服不了辛苦,下不了大力的人是绝对不适合饲养牲口的。”[7]108人与牲畜、人与机动车都在共同的劳动中得以长存,其中都能看到人与物“共情”的意味。彭牧在总结西方学界身体研究的转向时,指出:“正是我们身体所经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使身体的存在与经验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身体本身成为问题,成为思考与研究的对象,因为现代化、全球化、消费主义和医学技术的革新已使人类存在的身体经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5]25身體是实践的见证,黝黑的皮肤、沧桑的皱纹、手上的老茧、直不起来的肩膀等等,是身体对辛劳的直观诉说。技术革命之后,身体的劳作很大程度上被转嫁到了机械,无生命的机械极大地减轻了凝固在身体上的众多“苦难”,同时也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财富,叙事发生的聚焦也就自然地转向了机械。也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创造一个“车神”,也许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车神”,那么当地的拜车祭祀仪式究竟所指为何?黄应贵所研究的台湾东埔社农人对于汽车的情感处理或许具有启发性。在东埔社农人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物皆有“hanitu”,即物有类似于人的“主体性”。汽车是他们生活世界的新事物,农人通过生产的灵验来表达自己对车的情感或者解释,比如因梦占上帝的灵验种植某种作物而获利,他们用这一收入购买汽车,那么汽车就成为人与上帝或者上天互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他们试图透过教会的活动将车子的物性转化为经个人与上帝互动而来具有主体性的物”[20]。L村的这种视物有命的“信仰”虽然不是宗教式的,但它介乎于生命与非生命、神与非神之间,其不仅仅是中国乡村式的“感恩戴德”,更深一层的表达,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命故事、复杂情感和美好希望的表达。他们对于自家车辆“下大力气”“心疼”“懂人性”等等的叙述,何尝不是在诉说着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的艰辛,从而更进一步体现出中国乡村的历史变革。
五、结语
拜车的信仰现象,是通过村民的身体实践和叙事共同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过程既呈现出了物的生命产生方式,也反映了当代村民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历程。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L村一时兴起的致富门路导致了村落生产工具和营生方式的快速变革,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在器物变革的现实之中发生了“转嫁”现象,这在他们相关的“拜车”仪式行为和叙事之中表现出来,其本质是人们对于自身生命、生活的叙述表达。“拜车”现象是中国民间俗信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类似的民俗事象大量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类现象是中国民间应对现代化乃至现代性而做出的“发明”或者“妥协”。从生活革命的宏观角度看,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国人日常生活同样也存在着技术革新与生活观念相“协商”的问题。因此,民俗学将面临的是更为复杂、更具张力的研究对象。民具将不能忽略机械,乃至未来的人工智能;民众信仰的界定也将会复杂、模糊,可能会找不到“神”的存在;活生生的身体揭示了民俗生活根本的创造和传承主体[21],但身体的具体劳作会更多地转向代表技术的器物,正如保罗·格拉维斯 - 布朗对汽车的研究,他认为汽车是人身体的第二皮肤,具有“暧昧的像人的特性” [22],而“技术作为我们自身的延伸,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技术(就像鲍德里亚1981年说的)和身体‘混淆在了一起”[22] 。人们将更多地通过“物”来反观自己。在学科层面也要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研究面向和学术关怀,但正如马佳在物的人类学研究历史中总结到的,21世纪近几年,物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使得人重寻‘谦卑,反思‘人类中心主义”[23]。这将是人与物建立良好“生态”关系的肇始。
在当下城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因空心村等原因,一些地区推出“合村并镇”计划。可以预见,农民的生产和营生方式还将迎来一个新的变化,与此同时,原生的村落文化也将会被打破,相应创造出适应新生活的思想观念,其中必然会滋生各种矛盾、妥协,但这也将是值得民俗学关注、体现学科社会关怀的方面。
参考文献:
[1] 天野武,王汝澜.庶民生活的见证——民具[A].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134 - 153.
[2]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56.
[3] 阿尔君·阿帕杜莱.商品与价值的政治[M].夏莹,译.//孟悦,罗钢.物与物质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06.
[5] 彭牧.身体与民俗[J].民间文化论坛,2018(5).
[6] 王宁宇.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35 - 37.
[7] 詹娜.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周星.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J].民俗研究,2018(4).
[9] 范可.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途径、观念与叙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6):37.
[10]王铭铭.心与物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3.
[11]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J].民俗研究,2013(3):40 - 46.
[12]姚晨晨.民间信仰的功能想象——以山东淄博石马庄车神崇拜仪式为个案[D].沈阳辽宁大学,2019:20.
[13]李金发.浅析彝族村寨中的“车神”信仰[J].学理论,2011(36):174 - 175.
[14]徐腾.弥异所052:保定易县奶奶庙车神[J].城市设计,2020(2):54 - 55.
[15]Barthes R, Duisit 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2): 237 - 272.
[16]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8(2):165.
[17]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3):73.
[18]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张雄,沈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5.
[19]彭兆荣,路芳.物的表述与物的话语[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91.
[20]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428 - 429.
[21]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J].民俗研究,2010(3):27.
[22]保罗·格拉维斯 - 布朗.撞的总是同一辆车[M].严蓓雯,译.//孟悦,罗钢.物与物质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81,476.
[23]马佳.中国人类学的物研究:历史、现状与思考[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6):46.
[責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