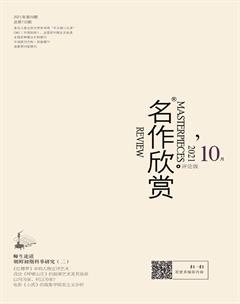李娟散文《冬牧场》文化内涵解读
关晨霞 吴晓棠
摘 要: 李娟的散文集《冬牧场》是一部纪实性散文。主要记录了李娟跟随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深入阿勒泰南部冬季牧场的生活经历。正是由于李娟的关注与书写,使得哈萨克族的游牧生存状况得以记录和呈现。李娟以她独特的视角观察并讲述着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冬牧场》的出现让新疆哈萨克牧民古老而又神秘的故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键词:李娟散文 冬牧场 文化内涵
作为新生代作家,李娟的散文是独特的,其作品在质朴、淳厚、细致的叙述中引发人们思考。对李娟散文的研究,或者说对以她为代表的“非虚构性文学”的研究近年也逐渐增多,但大多都是基于李娟双重文化身份、生活经历分析写作风格,以及基于李娟散文独特丰富的思想意蕴及“非虚构性”文学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少基于作品分析背后想要传达的讯息。本文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挖掘李娟作散文的深层含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游牧文化的坚守者
在《冬牧场》中,李娟用纯厚、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生活于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的日常生活,选取了居麻与嫂子等老一辈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活来展现游牧生活和游牧文化独有的意趣和韵味,也表现了他们对于游牧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一)传承游牧文化
哈萨克族对游牧文化的坚守是其他民族远不能及的,这种坚守是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赋予其独特的精神支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大众已经习惯信息获取的便利,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生事物上,导致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面临中断甚至消失,当一种文化后继无人时才是真正的悲哀。在这种形势下,哈萨克牧人对于游牧文化的坚守,无疑是珍贵且富有意味的。
在荒野中生活,骆驼是极其重要的牲畜,也是转场途中的主力军。但因条件限制,牧民不会专门建造供骆驼休息的地方,因此导致它成为荒野里最容易丢失的动物。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牧民寻找骆驼的身影。遇到大雪只要附近有地窝子都可以进去做客,即便主人不在家,客人也可随意取用食物使用炉灶。哈萨克族有句著名的谚语:“祖先遗产中的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a将他们的民俗体现得淋漓尽致。
包容、理解、尊重生命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赋予这个民族的特质。一月中旬是贩卖牲畜的最佳时期,居麻想要卖掉一匹马,但在价格没谈拢前嫂子就煮好了一锅肉。在他们眼中对方的身份不只是马贩子,同时也是客人。在这里,礼性与利益不能相提并论,这是荒野的生存之道,是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和风度,是他们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马背上的民族自然对马有着深厚的情感。这源于哈萨克族对马神的崇拜,他们认为马神是康巴尔阿塔,b并且认为马肉是最上等的食品,特别是遇有贵客一定要宰两岁的马驹子招待。马的肋条肉、肥肠肉、脖颈肉、臀部肉,装进马肠里做成“哈孜”,被认为是马肉中最好的肉,要敬给客人。c游牧人对马无比热爱,被称为哈萨克人的翅膀,从口头的神话传说到碑铭都有着清晰的记载,都以高超的手法描绘了一匹匹神奇的神马形象。“马文化”的崇拜始终渗透在哈萨克人民的生活习俗中。d李娟对这一现象也有所描绘:牧人只要在荒野中看到马头骨就将它放在铁架最高处。若有幸捡到马头皮,便将它带回家烘烤、化開再一针一线地缝在马头骨上,牧民在做这项工作时带有的虔诚是让人敬畏的。
除此之外,牧民冬宰前还要做巴塔,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仪式,主要是在宰牲畜之前举行,有祈祷之意;儿子成婚后第一个孩子要过继给父母当幼子。在他们心里,这古老的传统是一代代的基因血脉。
(二)恪守生活方式
居麻与嫂子是游牧民族的老一代,他们将一生都献给了牧场。正因为他们的坚守,李娟才有幸与其一起生活并辗转于各个牧场之间,读者才能领略到游牧文化特有的韵味。
在牧民的一生中转场是常事,且每一次都是神圣隆重的。居麻在转场前会穿上新衣服,并且每结束一天的行程就会搭起帐篷铺上毡垫,继而烧水沏茶。李娟对于上述做法不能理解,但对牧人来说却有特殊的意义。虽身处荒野,却从不妄自菲薄,这是他们贫乏、孤寂的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荒野上,劳动是获得尊重的唯一方式。这件事上从不论年龄与性别。进入冬牧场清理牛羊圈是最繁重的工作,李娟虽是客人但从不逃避劳动。扎达是居麻的小儿子,虽然年纪小但对于劳动也义不容辞。居麻与嫂子会像对待成年男性一样对待他,有客人来嫂子会坚持让他入正席。离开牧场转往下一个地点前会把地窝子周边打扫干净,这是牧人遵循多年的转场方式,是对馈赠给他们财富的土地最大的尊重。有人告诉李娟那年是羊群进入冬窝子的最后一年,而这最后的游牧景观正好被她赶上,李娟并不认为这是幸运。流传千年的游牧文化正在面临着中断甚至消失,牧人在精神上没有了归宿,关于转场,关于戈壁都只能转为文字被记载。
二、游牧文化的逆反者
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推进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观念。食宿的便利,让世代守护在阿勒泰地区的人们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加玛与扎达是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游牧民族新一辈代表,也是游牧文化的逆反者。
(一)新一代女孩的缩影——加玛
加玛中途辍学投入牧场工作,但毕竟在学校读过书受过城市文明的熏陶。接替父亲工作时,会在前一天向李娟请教几个汉字以便得空的时候温习,会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汉文报纸放在马背上的箱子里,会带着手机听各种流行音乐,会做广播体操、仰卧起坐、俯卧撑、立定跳远等等在学校里才有的体育活动,谈及未来,加玛表明不想一辈子被困在牧场,希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家,在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虽然生活在荒野,但却如此渴望外面的世界。
当然,加玛只是众多渴望现代文明女孩的一个缩影,与加玛同龄的人大多也如此,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李娟对加玛同学的刻画中。加玛的同学与她同龄,但在打扮上却要比加玛成熟许多。脚上穿着高跟鞋,在二月并不暖和的天气里穿着黑丝袜,脸上也涂了厚厚的粉底液,在加玛同学的身上可以看到城市留下的痕迹。加玛也向李娟透露过自己与朋友在一起时会去歌舞厅,并且在他们居住的小镇上这样的娱乐场所不只一处,而年轻人是主要的消费群体。
(二)新一代男孩的缩影——扎达
扎达是居麻最小的儿子,也是最渴望外面世界的孩子。学校放假会穿着自己新买的衣服回到牧场,对于火锅、凉皮等外来食物他也非常喜欢,在谈话间隙会为家人讲述食物的味道以及制作流程;扎达会用父亲给他看病的钱买手机,并且对汽车修理行业非常感兴趣,未来想要做一名修理工。这显然与居麻为他安排好的道路背道而驰。对于哈萨克族的一些传统习俗,扎达也有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客人用挂在壁毯上的白布做乃麻孜,铺好布后面朝西方啊啊啊的念叨,不时下拜、叩首。扎达看到以后最先的表现是嗤笑,他并非是轻蔑这些习俗,只是在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后,似乎不太能接纳这些原本一直存在于他生活中的“旧物”。“扎达是牧人的孩子他当然是热爱牧场的,却更向往牧场之外的闪亮生活啊……”e
李娟在《冬牧场》这部作品中,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居麻一家的日常生活。但作者只是客观的记述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加玛与扎达本就是牧人的孩子,似乎接替父亲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未来他们有权利去选择,作者深知这一点,因而在作品中并没有对他们的选择做任何的评价。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选择与游牧文化的发展是相悖的,也会将游牧文化推入一个更难的境地。一种文化的延续,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人。
三、“他者”视角的观察与讲述
李娟与阿勒泰的关系既亲密又疏远,在作品《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这世间所有的白》中,随处可见阿勒泰的痕迹,但由于地域和身份的不同,李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者”的形象。在构建《冬牧场》这部作品时,作者更多时候是以“他者”的视角写游牧文化,写居麻一家。
(一)“他者”视角的来源
李娟的身份是特殊的,她是一个出生在新疆的汉族人。幼年时期跟随母亲与外婆奔波在四川与新疆两地,动荡的生活、文化风俗的不同、语言的不通,种种的经历让李娟感觉到了自己与外在环境的格格不入。除去自身因素,还有外在因素。李娟在上中学时,因为学费的问题被同学和老师嘲笑,在之后辍学打工的时间里,又因为没有户口而东躲西藏。即使后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在阿克哈拉村经营杂货铺,李娟也依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处在此地的外人,这种地域与文化带来的差异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他们中间,因而,她常常以“他者”的眼光来关注并试图理解牧民们的生活。
(二)“他者”视角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语言不通,李娟在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过语言不通给自己带来的困扰。跟随母亲在小镇上经营杂货铺,平常的生意往来基本都是靠手势加一两个字完成,遇到不会说汉语的牧民顾客生意只能作罢。在她跟随居麻一家深入乌伦古河南面广阔的荒野时,这种困扰便更加突出。队伍迁移途中李娟多次询问加玛到达驻地的时间,但因语言障碍,谁也不能明白对方要表达的意思。语言上的困扰让李娟时刻觉得自己是处在此地的外人。
出发前,李娟希望自己跟随的牧民家庭中有会汉语的主人,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居麻一家。日常交流的对象仅限于居麻,嫂子是一个传统的哈萨克妇女,完全不懂汉语,因而家中只剩李娟与嫂子时,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最能让李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外人的情形便是家中有客人来访,席间居麻与客人的谈话李娟难以参与。她在《我在体验什么》一文中对自己的这种尴尬境遇做了描述,并认为自己明明跟他们处在同一空间,却又感觉到是那么的遥远。
哈萨克牧民独特的待客之道有时也是李娟所不能理解的。所在的地窝子有客人来访,不论食物是否充足嫂子都会铺桌布,切馕、沏茶,把家中最好的食物用来招待客人。在李娟看来,这样的方式似乎是不能接受的,身处荒野且物资匮乏,理应在保证自家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再去招待客人。这种待客之道除天性之外,更多受生活方式和地域的影响。
最后是生活经历与思维方式的不同。李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也习惯于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站在“他者”的角度打量牧区。对于李娟来说,政府实施定居政策的初衷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在亲身经历过之后她更是认为:这种顺应天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并没有给牧民带来稳定的收入,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病痛。李娟多次描述居麻与嫂子在疼痛难忍时大量吞食去痛片和阿司匹林的场景。作者认为居麻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利益完全不成正比,除此之外还要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定居则可以使牧民免于遭受这些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家庭收入会有所提升,一家人也免于颠沛流离。李娟的这种观念与看问题的角度,和自身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哈萨克族是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自然而然跟随草场迁移就成为牧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而李娟是汉族人,崇尚定居安稳的生活,不同的生活经历,在看待问题时也会有所不同。一个民族似乎与生俱来,便在他们的染色体中蓄存着固定的密码,特别是在族裔的认同上,先在的具有一种微妙的倾向,不管其身在何方、受到何种文化的熏染,祖辈的文化与原来的种族依旧还是像一股强大的磁场把他们深深的吸住,对他们的根源产生莫名的眷恋。f
对于新疆对于阿勒泰,李娟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者。虽然生活在这里多年,但对于游牧文化特有的代码她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先天的隔膜是后天实践无法弥补的,也是作者选取“他者”视角记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记述方式,读者才没有先入为主地对作品的思想内涵进行界定,更有利于发掘作品的内生意蕴。
在这部作品中,李娟把居麻一家真实的生活狀态展现给了读者。从另一层面来说,李娟所展现的又不仅仅是一家人的生活状态,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但由于文化归属感以及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作者始终是从“他者”视角进行描绘。李娟创作这部作品的起因是参与了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亲身经历转场之后,作者想要在作品中传达出一些信息和思考:如何让游牧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如何解决当前哈萨克族面临的精神与肉体双重困境?
a 陈经纬:《创伤体验与文学救赎》,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b 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玺.张德罡.师尚礼.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哈萨克族的游牧生产》,《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5期,第94页。
c 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玺.张德罡.师尚礼.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Ⅳ)——哈萨克族的衣、食、住、行及婚丧等生活文化》,《草原与草坪》2013年第1期,第78页。
d 黄适远:《“马”文化在哈萨克族音乐舞蹈中的镜像考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4期,第107页。
e 李娟:《冬牧场》,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f 许文荣:《文化混血与文化认同》,见周宪主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参考文献:
[1]李娟.冬牧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2]李娟.阿勒泰的角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3] 陈经纬.创伤体验与文学救赎[D].曲阜师范大学,2018.
[4] 谢悦.论李娟的非虚构散文创作[D].西北大学,2016.
[5] 何杭娟.多重文化视角下的李娟散文创作研究[D].海南大学,2015.
[6] 郑春光,翟钰莹.此中有真意——李娟非虚构作品中的两个世界[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 (2).
[7] 刘泽慧.李娟散文的民族文化解读[J].文学教育,2014(9).
作 者: 关晨霞,教育硕士,新疆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吴晓棠,硕士生导师,新疆伊犁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