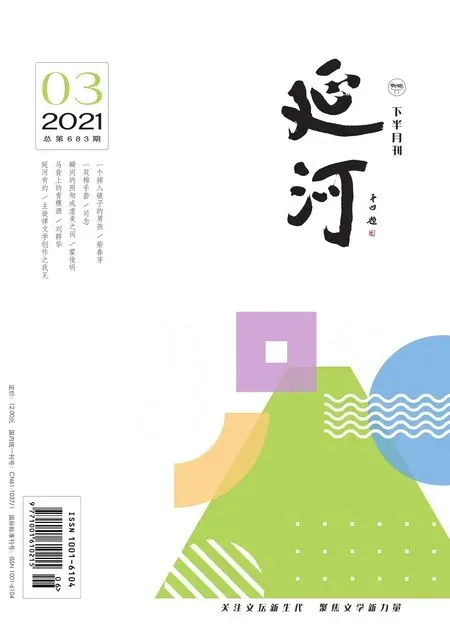叙事性与诗意化(评论)
——司念散文诗《冬日之诗》简评
司念的散文诗创作,可以放在诗歌的叙事学场域中考察,可以作为一种跨文类叙事学创作进行评析。同时,传统的古典化美学特质和现代的思辨式哲学意蕴,使得司念散文诗拥有别具一格的诗意化空间。
司念擅于在散文诗里盛装多层次的叙事。
首先,叙事时间与空间错落交叠,当下与历史时空更迭有序。这一组散文诗主题放置在“冬日”,带有明显的时间性——以社会“历史”时间和个人“历史”时间之反思反哺“当下”时间。如《下雪》,由“雪”创建出“当下”与“历史”并行的两个时空:当下时空——雪——雪人——孩子;历史时空——秦、唐、元时的雪——新时代的雪,分别对应帝王的雄心、仁人志士的忧心(担心)、逐鹿中原的壮志,以及新时代疫情之下人们同舟共济的真心与决心。再如《柏油路》,柏油路连接的小学与中学,是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长历程。诗人在叙事中追忆柏油路修成之前的生活图景。这一成长过程的追忆,实际上是在探讨作为个人化叙事经验的内在心理图式。种着“蔬菜和瓜果”的“大坝”,“坟地”上有着“失色的红纸”,以及“布谷鸟”“棉杆”,还有辛勤劳作的乡村女性……乡村生活图景在这种安静的叙述中蕴藏着生机与力量,而“八岁”的孩童,在奔走中开始找寻自我,开始成长。
其次,叙事在抒情内部显示出多重张力,利用叙述人称完成叙事视角的转换。无论“她们”“他们”和“我”的人称切换和视角比对,还是以他者叙述视角展开人物及其场景的铺排,再适时转换视角,给予表达的奇异甚或疼痛,这都是司念散文诗的叙事特色。意象叙事、人物叙事、能唤起诗人思索的各种场景叙事,叙事的多形态实践,拓展了散文诗对当下社会情境和个人历史经验的表达范围。
审美意蕴和哲学意蕴,生成了司念散文诗的诗意空间。
意象及其所显示的情境,构成司念散文诗鲜活的审美意蕴。比如“雪”,是时间(时令)叙事的典型意象。自古以来,诗歌里的“雪”蕴藏的意味甚为丰富。作品中虽未见得如中国古典诗歌般的美妙比喻或深宏象征,却具有独特的生命感受和情感意志。散文诗作对中国诗歌传统技艺的汲取,体现在诗行里呈现出典雅的意境和诗人信手拈来的古典化表达。如:
“我站在车的对面,一堵墙下面,看着络绎不绝的人纷纷化解冰霜,涌出一副副红光的脸面,腊梅开满了白墙。”
“我走往河边,看草黄漫坡,看野鸭戏闹,看河水缓缓流动。我知道它们在放慢脚步,积蓄力量,孕育新的自己。桃花依旧笑春风。”
“霜”“梅”“桃花”几个带有浓郁古典气韵的意象,极易引发主体与读者的情感、记忆,在诗作中发生于日常经验又超乎于现实日常经验,再度触发阅读的回响。再如,“公元一千三百年,大漠雪原上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桃花依旧笑春风”“山高水长,山花就烂漫”,无疑,这些经由古典羽化而来的诗句为整篇诗作增色颇多。
同时,散文诗作在叙述中渗透抒情,包括语言的诗性、柔韧度与哲学的思辨性。如:
“生命就是这样纵身一跃,向死而生。”
“宇宙之间立着一群发光的生物,隔离一切有机物,让病毒无处附着。”
整体上,散文诗作平淡叙事中彰显深沉,朴素描写里怀有大气深远。将情景叙述与人生感悟融进词句探索中,形成具有个人经验的诗意化策略,这是司念散文诗作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在司念散文诗作中,散文诗话语的结构、视角与语言等作为激活诗性的创作要素,强化了诗人自身的创作个性。在时空交叠中将个人经验通过多元化意象塑造寻求更为自由的创作境界,司念正在试图建构自身散文诗叙事特色、美学观念与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