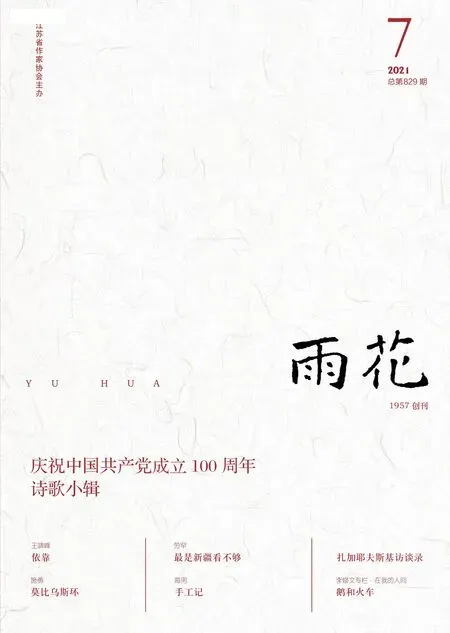开花沼泽
孟祥鹏
1
一个大雾迷蒙的清晨,我独自去港口给你送别。那时你站在我两步之外,没有行囊,衣衫也极单薄,丝毫不像是要背井离乡。表叔,你还回来吗?我仰头问你的时候,一颗露水正从你下巴上跌落。
我怕你回来,又怕你不回来,分不清这种心情是喜悦还是难过。你摸了摸我的脑袋说,我走了,船要开了。当时我想甩开你的手,但我劝慰自己,不必这样做,在生离死别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被原谅。我一直反感你把我当成小孩,明明我们之间只差了五岁不到,仅仅因为我要喊你表叔,所以很多你能做的事,我不能做。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天下就是有这么多毫无道理的道理。
那天你忽然把我叫住,我大费了一番周折才认出你——衣衫褴褛,满脸灰尘,还挂着乱糟糟的泪痕,从前我们常取笑林画家的画很难看,而那时你整张脸就像他的一幅画。你怎么了?我跑过去把你抱住,尽管我不是很想抱你,但至少这个动作能昭示我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谁欺负你了?又是美乐街的那些流氓吗?你点点头,又摇头,两只眼睛黯淡得可怕。从前你都是笑嘻嘻地说没事,胡乱闹着玩,这回却失魂落魄地沉默着。松松垮垮地,你把自己搭在我肩上,哽咽道,湿地里有一片开花沼泽,春山,你千万要当心。
轮船轰鸣的时候,你转身离我而去,那时大雾初散,晨光四起,你背对着我挥手作别,太阳在你的指尖晃动,冰冷的水汽迷蒙了我的眼睛。隐约间,我感觉到一种锥心蚀骨的疼痛朝我袭来,我似乎看到婴儿长出第一颗牙齿的样子,林画家的彩墨在宣纸上氲散开来,还有秋刀鱼临死前的最后一口喘息。可能,你不会回来了。
我发疯似的向美乐街跑去,时间大约是清晨六点,教堂顶上的大钟只响了五次,我猜测是胡三偷懒,少敲了一下,又或者他昨夜喝了大酒,还犯着糊涂。他站在塔楼上冲我喊,小子,你跑什么?我没工夫理他,他还是没皮没脸地喊,喂,小子,你的尿布跑掉了!我转头骂他,闭嘴吧,臭光棍儿!这个没有老婆又爱吹牛的老酒鬼,他从内到外汇集了所有令我讨厌的特征,永远说不出一句讨人喜欢的话,毫不夸张,如果你说的那个沼泽真的存在,我希望第一个陷进去的人是他。
蝴蝶发廊没有客人,崔兰心正在梳头,我扯开半悬的卷帘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她,我表叔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走了?走哪儿去了?她的声音向来这么甜,像是吃了好些个铃铛,不管说什么难过的话都带着喜庆,这在从前是个惹人心动的特征,此刻却让我觉得恼火。就是他离开这里了!永远都不回来了!我咬牙切齿地回答,希望能唤起她的一点悲痛,就算不嚎啕大哭,至少失魂落魄一会儿,起码要对得起你们那段被人指手画脚的爱情。哦,她把梳头的动作停在半空,从镜子里望了我一眼,或许是想判断我有没有说谎。走了好,走了倒也干净。她咕哝了几句,然后继续梳头。她的头发有半丈那么长,浓密乌黑又带着点光亮,几年前她来到榕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路过蝴蝶发廊时,她就在里面这样梳头,披散在背后的头发熠熠生辉,好像一块嵌满了星星的天鹅绒。我们俩把脚踏车停在马路边,痴痴地朝里边望着。你问我,她的头发好看吗?我点点头说,嗯。你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笑话我道,你小子还没长毛吧,懂个屁的好看。实不相瞒,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滋生了一种对你莫名其妙的厌恶,它若隐若现,时有时无。当它浓烈时,我总期冀着有什么厄运降临在你身上。
夏天的夜晚,我爸拿了家里最后一点零用钱和胡三他们去喝花酒打麻将,我妈百般劝阻,最后挨了两个耳光,于是她趴在床上开始流眼泪。流了一会儿,她起身把自己装扮一番,说赶着去教堂做礼拜,希望老天爷能让我爸改邪归正。临走前她还交代我留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课,情态深切,语重心长,像一些没本事的家长一样,把对未来的期许都放在孩子的功课上。我认真地点头,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带她脱离苦海。她走后,我觉得家里无聊,便翻找出自己的私房钱准备去理发。当然,剪头发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可自从那次在发廊门口看到崔兰心之后,我就莫名觉得自己的头发需要修剪。我曾多番向我妈求证,问她觉不觉得我的头发太长,该理发了,她说不长,不用理。因此我只好从每天的午饭里省下五毛钱,以便日后想去理发的时候不用被钱所困。
蝴蝶发廊刚开业不久,处处荡漾着崭新的气息,一间小屋子里挂着各种颜色的灯,繁华尽显,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推开门。你好啊,小帅哥,她闻声转身,你想剪个什么发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似乎并不真切,像是《小李飞刀》里的林诗音,又像《雪花女神龙》里的上官燕,随着她身体的摆动,还有一股让人晕眩的香气在我周围盘旋。她称呼我为“小帅哥”,这个词的意思非常浅显,但那时我不懂得类似词汇所表达的并非字面意思,就像榕镇人见了面互相问候“你吃过了吗”,其实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吃没吃过。我听惯了大家喊我“小子”和“兔崽子”,忽然有人把这么柔软的字眼用在我身上,我的心脏恍然一阵松动,人也变得扭捏了起来。
2
你走之后,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美乐街闲逛,之前剩下的游戏币没有用完,可你不在,没人跟我联机,也没什么意思。美乐街的那群流氓总是骚扰我,除了抢我的游戏币,他们还常把我围到角落,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走了。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便一通讥笑,说怎么搞了个家破人亡,然后撇下自己的姘头走了呢。
榕镇第一讨厌的人是胡三,因为他总是诱拐我爸去喝酒,第二讨厌的就是这群流氓,自己一塌糊涂,却整天想着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经常欺负林画家,虽然榕镇人人都欺负林画家,但他们尤其过分。林画家从这里经过,他们就朝他吹口哨,然后横七竖八地嚷嚷道,画画的,听说你画的娘们儿都不穿衣服,是真的吗?林画家寡言少语,只顾着低头赶路,从不和人争吵,流氓们偏偏不依不饶,拽着他的袖子不让走,非要逼着林画家承认自己是在耍流氓。有一次他们半夜喝醉了酒,去把林画家的铺子砸得稀巴烂,把各式各样的画撕得粉碎,丢在地上用脚踩,还在上面撒尿、呕吐。第二天我闻讯跑去围观,林画家跪在一片废墟中掩面哭泣,各色颜料混着腥臭味淅淅沥沥地流出去很远,外面众人齐聚,大家都捂着鼻子,嘻嘻哈哈地安慰他,画又不值钱,再画就是了嘛。
有一天那群流氓把我堵在公厕门口,问道,你为什么天天往蝴蝶发廊跑?我说我去剪头发,关你们什么事?你指定是和你表叔一样,对那个老女人动了歪心思。他们笃定地判断。放屁!我没有!然后他们便打了我,硬是想要我承认对崔兰心有非分之想。我无力反抗,只能双手抱着脑袋,任由他们在到处是尿液和粪便的地方对我拳打脚踢,直到其中一个人说该去吃晚饭了,他们才罢手,临走前还扬言说日后要见一次打一次。
其实我本想和他们讲道理,可没有这种机会,后面我也想通了,不应该妄想和这种人讲道理。尽管我对你和崔兰心之间的关系有诸多不满,但我仍坚定地认为,你们之间是正当的感情,因而不存在谁动了歪心思这个说法。还有,他们非要我承认我是跟你一样,这也是无稽之谈,不是只有你才能喜欢崔兰心,况且是我先推开了蝴蝶发廊的门,是我先坐在她的镜子跟前,和她聊家乡的风景和天上的星月,我们一起推心置腹的时候你还没出现。
那晚我面对着她,心狂乱地跳动,我的头发是不是很长?我似乎有点哆嗦地问道。她莞尔一笑,引我坐下,然后双手搭着我的肩膀,盯着镜子里我的眼睛,清淡又炽烈。我没想好自己会得到什么答案,但我知道,倘若她回答说不长,过些日子再来吧,那她肯定只是一个比别人多了点香味的世俗女人,再迷人也难掩日后的烟火气。假如她说,是的,你的头发很长了,的确应该剪剪,那我又会觉得她美丽的皮囊下藏了一个虚伪的灵魂,充其量也只是个聪明的生意人。我怯怯地抬头看向她,她仍旧微笑着,十指纤长,从我的耳后抚到前额,再从鬓角到眉心,春风拂花树,素练染青空。一瞬间,有万千悔恨聚集在我心底,我甚至想赶紧逃之夭夭,不用听到她给我答案,那我就永远不必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或许是我逃走的意味太过明显,又或者我的身体已经做出了逃走的动作,过于紧张的大脑却没有察觉,她的手稍微使了些力,将我靠在椅背上,弯下腰来贴在我耳边说,放松点,她声音绵软:剪头发不是因为长或短,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合心意,对吗?
这些言语从她嘴里带着一股甜腻的温热直接窜进了我的耳朵,猛然间,我觉得心里一道沉重的门忽然被打开,有些灿烂的光照了进来。我忖度了一会儿,点点头,对,声音已经激动得有些发抖。可能榕镇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却被她轻飘飘地、吹口气儿似的随便就讲了出来。好比从前我不懂贾宝玉为什么要纵容晴雯撕了那些好扇子来取乐,这一刻,那些别人不能给我解答的谜题忽然全都有了答案。我拥有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五块钱,恰巧这些钱又能让我剪一个觉得快乐的头,不会妨碍谁,我为什么要介意头发的长短呢?就像我妈天天跑去祷告,我爸却还是天天喝得不省人事,动不动就说要把她打死,可见她的那些祷告没人听见,但我从不对她加以劝阻,因为任何人都没权利剥夺别人的美好幻想。
遗憾的是,我妈没有这种觉悟,她非常喜欢对我指手画脚。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在一个我快要入睡的深夜,推开房门,坐到我床边来,苦口婆心地劝道,你别再去蝴蝶发廊了,那里不是个干净地方。我稀里糊涂地睁开眼,怎么不干净了?你在说什么?她叹了口气,愁绪万千,门外的光落在她身后,让她看起来神圣又威严。你离那个崔兰心远一点,她名声不好。听起来字字铿锵,不容辩驳。她名声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从床上坐起身,我就是去理个发。唉呀,你怎么不听劝呢?她有点着急了,你表叔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我想狡辩,但一时又找不到什么话反驳。谁也不能否认你在榕镇的结局和崔兰心有关系,但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到崔兰心头上。
那天放学的时候我看到你妈从五金商店出来,特意蹦着跳着去跟她打招呼,问她,奶奶,你买什么了?其实我应该喊她姨奶奶,可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呼陌生又绕口,所以简化了一下,她也因为这个简化的称呼和我分外亲近。她笑道,春山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被表扬了?我点点头,确实被表扬了。因为频繁理发,所以我的头发全校最短,那天学校开大会,我的头被当作一颗能够反映青少年精神面貌的示范头而公开展览,因此我心情很好。你呢?我去翻她手里的袋子,你是不是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她掏出一根绳子来,说家里有东西拴不住,买根绳子可能会派上用场。她语态寻常,要不是后来你告诉我,根本看不出她曾说过“你再去找那个老婊子,我就死给你看”这种狠话。临别她还挥着手嘱咐我赶紧回家去做作业,丝毫没有要与世长辞的迹象。
也许我是榕镇最后一个得知这个惨痛消息的人,在那之前,我对你的埋怨没有半分消减。我是一个喜欢责怪别人的人,任何事都不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我的缺点,但即便我没有这种缺点,我和崔兰心的生疏仍要归咎于你。我经常在深夜去蝴蝶发廊,榕镇陷入彻底黑暗的时候,那里依然灯火通明,她会把白天遮住的帘子拉开,露出发廊的另一半,一张略宽大的床,铺着绣了金线的红绸被,茶几上摆几个透明高脚杯,和高高矮矮的几瓶酒。后来,她请我喝了一杯,我才知道那是红葡萄酒。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的雕花壁橱里藏着的一架留声机,万籁俱寂之时,她把橱门打开,从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些硕大的黑色碟盘镶进去,再把唱针嵌进碟盘的凹纹里,一些刺刺拉拉的曲子就在屋子里晃荡起来。此时她换上一身旗袍,中指和食指捏住酒杯,随着音乐轻轻摆动她的腰身,头发肆意地散在身后,在昏黄的吊灯下微光四溢。
春山,学校都教过什么诗?她递给我一杯酒,手指顺势掠过我的脸颊。我沉醉在她的气息里,一种把茉莉花洒落进大海的味道,若非亲自嗅到,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会有这样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仰着头,醉醺醺地说道。哦,她双目迷离,轻轻地叹了一声,红色高跟鞋在高低错落的瓷地板上敲起了节奏,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还有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我记不清楚了。我也随着她的步伐,在满是碎发的地板上扭了起来。净瞎说,她伸出一根手指,在我脑门儿上戳了一下,学校怎么会教这个?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也跟着我笑,笑声像无数个梦里的水晶铃临风作响,在我的胸腔处轻轻撩拨着什么,不可名状的舒适感在这间小屋子里铺天盖地,把我们紧紧包围。“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个是学校教的,我把杯子里残存的酒一饮而尽,大声吼道,真他妈的痛快!
嘘——她把手指搁在嘴唇上制止我,下一句呢?
下一句?我目瞪口呆了一会儿,下一句?哦,想起来了,“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吗?是啊!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3
被打之后,我想起你之前告诫过的话,于是便去湿地那里寻找开花沼泽。那边的风很凉,触感就像细长的钢刀划破皮肤,野草茂盛,甚至有些嚣张,大片大片的,在黄昏下唰唰作响。我寻寻觅觅,跌跌撞撞,天色将尽都没找到一朵花,更没看到沼泽,反而遇见了林画家。他孤独地坐在画架跟前,上面铺了一张空白的大宣纸,脚下摆着瓶瓶罐罐的颜料。春山?他看到我连忙从凳子上起身,上前来拉我的胳膊,你怎么受伤了?
我不想在这么狼狈的时候跟他讲话,不想让他知道我也受到了那些流氓的欺负。其实那一刻,我对往日的行径也稍微有点后悔,如果从前不去死命地嘲笑他,如今也就不会多一份难堪。林画家是个很好的人,不呆不傻,只是整天穿着涂满颜料的破衣服,喜欢画画又画不出名堂,没什么该被嘲笑的事,天晓得是谁,率先发起了对他的讥讽,于是这个五彩斑斓的贫困者,成了整个榕镇的笑柄。我以前没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只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拿来打趣、戏弄甚至辱骂的人,从没想过榕镇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他不酗酒赌博,又不搬弄是非,甚至见了人还鞠躬行礼,怎么会落得好人没有好报的下场?
谁打你了吗?他关切地看着我,还帮我拍去了身上的尘土,似乎没有以牙还牙的打算。我瞥了一眼,放下戒备,但也没回答他的提问。你在这儿画什么?我指着他空空如也的宣纸问道。等着画夕阳,他真诚地说。画夕阳还要等?我不可思议。嗯,等天光,等灵感。等吧,我无奈地撇撇嘴,没忍住又损了他,反正你的画一直难看。他不说话了,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失望,或许他期待此时的我能够懂他。然后他看着夕阳,我望着天边,风从大海的另一端吹过来,不知怎的,我忽然真的有一种和他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不该如此莽撞去抨击他的画作——我觉得他的画不好看,榕镇人认为四十多岁的女人穿旗袍喝红酒就是婊子,这其中的道理可能没什么差别。我犹豫着要不要把今天在美乐街挨揍的事告诉他,反正他也不会参与榕镇的流言蜚语,明明就是几句简单的话,可当我转过身来面对他的时候,却郑重其事地跟他说,湿地里有一片开花沼泽,你千万要当心。
回到家躺在床上,我妈在外面“咚咚”地敲门,她带着哭腔询问道,春山,你要不要紧?春山,你千万别想不开。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么会想不开呢?我第一次撞见你和崔兰心眉来眼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全都摔在地上化成了灰——那日酒醒我忽然记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下一句,不是“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急于去发廊跟她分享这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惊喜,我逆着清晨的风跑向美乐街,其间还在十字路口翻了两个跟头,那年我十三岁,好像终于明白了人活在世间的伟大意义,并对未来充满了期许。而我踏进蝴蝶发廊的那一刻,你们两人暧昧的嬉笑声戛然而止,然后猛地转过身来,做贼似的一齐盯着我,可打情骂俏的气息分明还在屋子里招摇。春山,你怎么来了?你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呵责道,怎么不在家里好好睡觉?我瞪了你一眼,反问道,你怎么不在家里好好睡觉?我特意拉长了“你”字,希望你能从中听出什么玄妙。可很快,我的这种自尊和惺惺作态便零落成泥被碾作尘土。崔兰心见是我,随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正因如此,我才明白过来,你们刚才的戛然而止不是因为我,我根本没有捉奸讨伐的资格,换做谁在此刻进来都能看到一个戛然而止。
我踉跄着起身,刚打开门,我妈便猛扑进来抱着我嚎啕大哭,春山,你不要做傻事。我拍着她的后背安慰说,妈,我什么傻事也不做。可她完全听不进去,哭得悲壮凄凉,好像我真的死在了这里一样。我发现她身上也有被殴打过的痕迹,甚至某些部位已经血肉模糊,可见我爸又朝她下了狠手。她紧紧地抓着我,把我的肩膀哭湿了一大片。我们两个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她一抖一抖地说,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你明白吗?嗯,我点点头,不禁悲从中来,原来再怎么差的处境,只要活着就还有回旋的余地,我好像也突然懂得了你为什么非要离开榕镇,死亡不只是人体机能的丧失,更是所有与之有关的可能性的断绝,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失去了祈求原谅、冰释前嫌的机会,而遗留在它之前的缺憾和亏欠将再也不能弥补。
那个早上从蝴蝶发廊出来,我嘴里始终念叨着“月落乌啼霜满天”,其间还是遇到了那个倒霉的胡三,他在塔楼上一边唱什么妹妹坐船头,一边闭着眼敲钟,敲了个稀里糊涂。底下的人在里头读赞美诗,忏悔祷告,他却龇着黄牙唱些淫词艳曲。他看到我从大街上走过,便高声喊道,小子,你念叨什么呢?我没理他。他又喊,小子,念叨什么呢?我不耐烦了,念叨你妈呢!他虚张声势地嘶了一声,然后捏着嗓子说,改天老子非切了你那二两肉下酒吃不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下一句是什么,我又给忘了,直到我走回家门口,太阳升起,天朗气清,我都没想起来。
起得这么早啊?你妈在门口修剪花丛,她看到我刚拐过街角,便遥遥地冲我招手。她喜欢养花,扶桑、月季、天竺葵、秋海棠,一年四季,遍地花香,整个脏兮兮的榕镇,只有她数十年如一日地整洁,与小镇显得格格不入。我走上前去,说奶奶早上好,然后帮她把散落在地上的花瓣收集到一起。风吹过来几朵云,晨光漫漶起来,她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细汗,你见过你表叔吗?她笑着问我,一大早就没了影儿。哦,他呀!我笑嘻嘻地回答道,我见过!我激灵了一下,仿佛看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倾盆大雨,可以浇熄我心底的熊熊烈火。
4
这些年你一直杳无音讯,我自己一个人磕磕绊绊地长大。美乐街的那群流氓还是经常欺负我,时不时打我,所以我一般都绕着美乐街走,即便不得不到那个地方去,也是挑晌午黄昏那种时候,差不多打到一半就到了他们该去吃饭的点儿,我就会少挨些揍。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太像流氓,就拿他们殴打你和我这件事来说,似乎拥有一个充满正义的动机——他们在惩罚两个不知羞耻、没有人伦的好色之徒,好像在替天行道。可即便榕镇的人随着时间流逝淡忘了我们曾经有多么伤天害理,这群流氓却记得非常坚牢。有一回他们再次把我堵在公厕门口,先是围着我把陈年旧事数落了一番,绘声绘色,额外描述了很多细节出来,比如我们怎么爬上崔兰心的床,和她贴着脸跳舞,然后播放什么样的曲子来掩人耳目。他们分工明确,有的描述不堪入耳的情节,有的在旁边附和,同时有人再辅以下流无耻的词汇进行辱骂。当然据我判断,这群人也就只是道听途说,不然这种情景下他们肯定会提到那些榕镇人从没见过的红酒瓶子、雕花壁橱和留声机。
接着,在他们言语匮乏的时候便开始使用暴力,在我身体的薄弱之处用拳头和脚以及就地取材的棍棒、石头等物进行攻击。起初那几年,流氓们的殴打让我感到绝望,我责怪你,责怪崔兰心,责怪自己懦弱的性格,甚至责怪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感觉自己堕入了某种不见天日的轮回,不知道这段可笑的经历带来的苦难要熬到什么时候,只好每次都鼻青脸肿地安慰自己,没事的,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似乎逐渐爱上了这种被施以暴力的遭遇,疼痛过后的创伤反而滋生出一种令人着迷的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才不受煎熬,良心才不被审判。我一直怀疑自己那天到底有没有听到你和崔兰心在做些乱七八糟的事,可我却手舞足蹈地跟你妈比划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我表叔呀,我见过他,奶奶你知道蝴蝶发廊吗?对对对,就是开在美乐街的那个。哦,原来你知道呀,我看到表叔天不亮就进了发廊,然后和女老板在里面唱歌。是啊,花花绿绿的灯光,简直不成体统,我本来想进去喊他的,可你猜我在门口听到了什么?喔哟哟,真是造了孽啦!我个小孩子怎么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咿咿呀呀的,也不晓得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好在是被我听到了,换成别人,到外面要怎么说去呀!
你在榕镇的时候,我没有胆量把真相说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把脸一沉转身回家要做什么,我以为她顶多找根棍子去打你一顿,再骂几句“丢人现眼”就罢了,毕竟那些花瓣还堆在那里没收拾完,谁能想到她会用挂起来的绳子勒死自己,连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再给你。为此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梦见一片落英缤纷的虚空,她悬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双目灼灼,死不瞑目地盯着我,我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仓皇奔逃,却怎么都摆脱不掉那份恐惧。所以后来我每次在美乐街挨了打,心里就莫名地会好受很多,甚至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永远都不会离开榕镇,就这样以别人都不知道的方式在这里赎罪。
那群流氓最后一次打我时,从黄昏一直打到天黑,期间都没人提起去吃晚饭的事,我想恐怕这回真要小命不保了。那时我身上已经沾满了污秽,伤口的疼痛也比往常更剧烈一些,于是我抱着脑袋乞求他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再打可以吗?他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停手作罢。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认真清理身上的血污,内心充满了一种匪夷所思的感激。榕镇点亮了霓虹,如同各色琉璃在昏暗中闪耀,他们一行人已经转身准备吃饭去了,其中一个流氓却倒回步子,弯腰问我,崔兰心的屁股软不软?
什么?我有点费解地抬起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而他看起来手足无措,好像在为刚刚问出的问题而懊悔,眼睛慌忙躲闪,把往日隐藏于可憎面目之下的七情六欲全都给暴露了出来。另外几个流氓也折返回来,我以为他们是要把这个关心人家屁股的叛徒给带走,结果他们就静悄悄地立在那里,脸上都换了一副奇怪的表情,然后齐刷刷地望向我,好像极期待我对刚才的问题作出回答。你快说啊,另一个人发话了,她的胸有没有下垂?然后各种问题愈发不可收拾,她的腋窝里有没有毛?身上闻起来味道好不好?
我低下头,疼痛和委屈让眼泪止不住地下落。这几年来,他们锲而不舍的欺凌差不多已经让我相信他们是在替天行道,我也心甘情愿地受些皮肉之苦,就像榕镇的人早已经习惯了崔兰心用普通话说“你好”,一把年纪了还穿紧身旗袍,从没有人敢去指责她不要脸。现在倒好,水落石出了,他们一群癞蛤蟆把吃不到天鹅肉的怨恨全都往我身上发泄,到头来我想赎罪的那些期望全都成了赤裸裸的、金光灿灿的侮辱,我妈去给神像磕了这么多年头,依旧过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我干了缺德事却还痴心妄想早日解脱。于是,灰心绝望的我开始对他们破口大骂,做你妈的美梦,软不软香不香跟你有什么关系?想瞎了你们的狗眼。他们茫然四顾了一会儿,然后恼羞成怒……
后来,我听说林画家失踪了,他关掉了画画的铺子,连同里面那些被糟践过的画也一起消失。胡三去公厕小便的时候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他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还没醒酒,但还是很体面地把尿尿说成小便。警察根据线索去找林画家,想要收集流氓们曾经的罪证,那时候榕镇的人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大家揣着手聚在一起,讨论到底谁是林画家,不知哪个提醒了一句,就是那个画流氓画的穷光蛋啊,然后大家恍然大悟,前仰后合地笑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彼此之间在笑什么,却依然笑得一发不可收拾,眼神极其空洞。林画家的铺子在美乐街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一颗颗灰尘在夕阳中下落,正逐渐掩盖这里曾被侵犯过的痕迹,透过一扇窄窗和湿地上大片大片的芦苇丛,隐约能够看到明亮的大海。
远处轮船开始轰鸣,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你转身离我而去,大雾初透,晨光四起,你背对着我挥手作别,太阳在云雾中披荆斩棘,冰冷的水汽从眼前纷纷退散,月落乌啼霜满天,管他什么下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