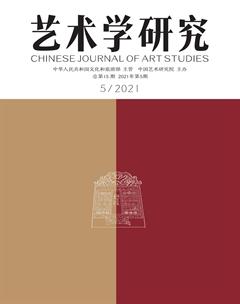庄子的心物一体美学与技艺实践
余开亮
【摘 要】 庄子在解构日常世俗“态度式”心物关系过程中,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心物直观关系。庄子主张以境界之心会通外物之性,成就了身心、主客一体共存的生命美学境界。这种生命之境并不局限于静观的精神体验,还以心—手(身)—物自由流转的技艺方式转化为一种人生实践。在艺道两进的视野中,传统技艺也不再是一种人为的技术或巧能,而成为人生之道的操守与修行。
【关键词】 庄子;心物关系;直观;技艺
“心物关系”是庄子[1]哲学反思人与世界外物应如何关联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思想内涵不仅体现了庄子对自然、人生、社会、政治等领域的诸多看法,而且蕴含了庄子对审美与艺术层面的深思。在批判世俗经验性的心物关系过程中,庄子提出的心物一体观念,以灵觉的自由境界之心去与物性相遇,打开了人与世界外物一体共存的整全之境。这种具有存在论美学色彩的心物观,经由庄子在有关技艺的寓言中证明与阐发,遂成为中国古典士人所向往的精神理想与实践追求。
一、庄子新型心物关系的提出
在一般的思想内涵上,心物关系聚焦的是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外物并形成相应的判断。面对同样的外物,关注的态度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判断方式。按日常习俗性理解,理性态度形成认识性的心物关系,实用态度形成功用性的心物关系,欲望态度形成占有性的心物关系,道德态度形成伦理性的心物关系,情感态度形成审美性的心物关系。然而,在庄子看来,对心物关系的这种习俗性理解,因隐含着特定态度取向之偏颇,故其本身是有问题的。在《秋水》篇中,庄子将这几种“心物观”归结为因“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而滋生的偏见与偏爱之产物。在《庄子》全书中,庄子从自身的哲学立场出发,针对具体以上五种日常世俗性心物关系一一进行了批评与解构,显示了其超凡脱俗的哲学智慧。
针对认识性的心物关系,庄子认为,分别之知与成见令人陷入了认识的迷途,让人作茧自缚。众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論》),于是世间争论不休,“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庄子认为,物本身乃是一个整体,认识分别之心只会导致物的割裂,所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天下》云:“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判断、分析、观察之理性态度是无法获得真知的。
针对功用性的心物关系,庄子认为,多数人只知道看到事物的用处而盲目索取,乃至于轻用其身,最终令自身如跳梁小丑般“中于机辟,死于网罟”(《逍遥游》)。《骈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而很多人与事物也正是因其有用性过于突出,而招致斧斫,难尽天年,故“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针对占有性的心物关系,庄子认为,其给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对生命自身的伤害。《至乐》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业;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庄子告诫世人,这恰是为物所累的不幸人生,处于这样的人生中,人永远被外物牵制而无法真正获得心灵的安宁和快乐。
针对伦理性的心物关系,庄子认为,仁义礼乐的出现恰是纯朴大全之道丧失的结果,是出自人有目的性的制作,故这种“文明的枷锁”亦是对自然无为生存方式的伤害。“故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马蹄》)与儒家对以道德善为目的的赞赏不同,庄子认为,道德君子和盗贼小人在残生损性方面并无二致。
针对人与外物之间情感往复的审美性心物关系,庄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知北游》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山林、皋壤虽然给人带来了欣欣然的审美愉悦,但庄子认为,这种执着于物感与对象形式的审美愉悦只是短暂的,其情感愉悦的来去都无法自已,最终依然情为物累,沦为外物的奴隶。同时,外物自性之美也正是在情感的灌注中受到了遮蔽。
可以看出,庄子对日常世俗性心物关系的批判主要是在心与物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就心而言,以上五种待物心态多为现实经验中的理性与欲望之心。这种现实经验的习俗之心被庄子称为“成心”“机心”“人心”“蓬之心”“怒心”“贼心”“谬心”等。就物而言,以上五种所待之物多指现实经验世界中的一切对象(包括人)与事情,以事物之形质性、器用性为主,即《达生》所言的“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由于人执迷于机心成见,执迷于声色嗅味趣的是非、爱恶,最终“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导致了人生生存方式的错乱。庄子对现实之人的生存方式不无感慨地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因此,以特定的态度去与外在事物关联的心物关系方式,既是对自然人性的偏离(一曲之士),又是对自然物性的割裂(在物一曲),最终远离自然大道。为了回归自然之道,庄子提出:一方面要在去除自己的习俗之心上做工夫;另一方面还需超越物的器用性的视野,对物的自然本性有所发现。
去除习俗之心,就是要去除超出自然人性的巧智与情欲。为此,庄子提出了很多对治“益生”之理智、欲望、仁礼、情感等方面的心性工夫。《知北游》中的“汝齐戒,疏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之心斋、《大宗师》中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之坐忘、《天道》中的“退仁义,宾礼乐”之遗物以及《德充符》中的“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之无情等,都是最典型的心性工夫。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能下功夫,关键在于人自身本具有一颗灵动自觉的大智慧之心。《德充符》中,常季在谈到鲁之兀者王骀的精神境界时说:“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韩林合解释为:“一个经验主体首先必须运用其心智(所谓‘以其知‘以其心),认识到他所拥有的成心是人生问题的根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必须对这样的心施以斋戒;经过这样的过程,他便可重新获得本然之心或常心(所谓‘得其心),这时他便升格为体道者了。”[1]这里,心性的修养呈现为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修道者需要发挥本然之心的自觉精神来对现实习俗之心进行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丧、无、绝、弃、退、宾、去、齐、一、斋、忘、堕、黜、离、外、遗等),从而将习俗之心自我转化为自然自由之“常心”。以本然之心的自觉精神否定与超越习俗之心,实现内在心灵的自我转化(成就自由境界之心),这正是《徐无鬼》中所言的“以心复心”的真人之道。由此,生命刊落了荣华而呈现本真的自然与自由之态。
超越物的器用性视野,就是重新发现物与自然之道的关联,以重新审视物的存在价值。钱穆说:“至庄子出,乃始进而对于‘外物观察其本质与真相,于是又为先秦思想界辟出一新境界。”[2]在老庄那里,万物本身就是道的创化,是道在经验世界的显现。《天地》云:“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自然无为之道在运转流动中生成了万物之形与万物之性。不过,作为物之内在精神与仪则的物性要比物形更为根本。徐复观说:“所以性是德在成物以后,依然保持在物的形體以内的种子。”[3]物形和物性虽然都是禀道、禀气而生,但物之性才是物的种子、本质与真相,体现了道的自然无为与神妙变化。庄子对“无所不在”“无乎逃物”“物物者与物无际”(《知北游》)之道物关系的重建,使得物不再只是一种物质性、欲望性的消极之物,而成为道的表征。这种对物所蕴含的道性价值的揭示,使得物成为领略自然大道的积极凭借。
由此,庄子通过对现实习俗之心与器用之物的价值翻转,在解构日常世俗性心物关系的同时,建立了一条以自由境界之心面对自然物性的新型心物关系。这种心物关系带来一种全新的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
二、心物直观与境界论美学
习俗之心被分解与终止,一方面意味着自然境界之心或生命自由本真状态的呈现;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将以一种“无态度”的方式去面对外物。以自由本真的生命去应物而不起态度、意念,最终与物一体共存而回归自然大道,这是庄子人生哲学的精神旨归。可以说,这种心物直观是庄子“虚己以游世”(《山木》)处世哲学的真正落实。其中,无心、无情与通物是这种心物直观关系的鲜明特色。
无心,一方面“无”掉习俗之心,另一方面凸显自由境界之心。以自由境界之心去应物,要求“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这就表明,庄子的应物之境界绝不是本能式的浑浑噩噩,而是一种高迈超越的自由心灵。所以,无心应物意味着对心灵自由本真状态的持守,以及对物之自然状态的顺化。以高蹈的精神自由去接纳物、顺应物,从而“乘物以游心”(《人间世》)。《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心斋”理论中所讲的“听之以耳”“听之以心”皆是现实习俗性的心物关系,而“听之以气”则是以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去虚而任物、与物一体。这里的“气”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气”“神气”,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4]。“听之以气”恰能使得心、使得整个生命反归于气在流转生成人时的自由本真状态。由此,境界之心则能与身同体,与万物同体,与道玄同。庄子还以镜与水为喻,对这种“乘物以游心”的心物直观关系进行了具体揭示。《应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天道》亦云:“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与日常习俗经验中心物将迎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不同,庄子要求人心如镜子、静水般去映照外物,感知外物,以维系心与物的互不相害、各得其是。由此,心不为物扰,是为“撄宁”;而物则无成毁,是为“复根”。
无情,一方面“无”掉习俗之情,另一方面凸显自由之性命之情。习俗之情,往往被物所制,来不能御,去不能止,为偏爱之情。性命之情则缘自然之性而动,因境界之心而发,为至正之情。《骈拇》即云:“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天地》云:“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 ,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骈拇》云:“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这里的情近于性,非以物为动力源的世俗人伦之情,而是以性为动力源的天地之情。所以,庄子并不是完全的无情者、绝情者,他反对的是世俗社会所滋生、所教化的情,追求的是与自然之性、自然之道合一的性命之情、天地之情、自然之情。以自由性命之情应物,要求“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达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这里的死生惊惧、喜怒哀乐皆为被物所制的习俗之情。体道者则能超越这种为物所感之情而“致命尽情”,“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致命尽情”乃以性命之情与物为春,“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这表明,体道者之无情乃是一种来即应、去即止的顺应人情而又超越人情的自然因任状态。这种无情于物,不夺物宜的性命之情,即《德充符》所言的“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与习俗经验中情物婉转摩荡不同,庄子反对有情感态度倾向性的迁物之情,主张在忘情融物、无为相因中守护着天地万物的自然运化、寂寞无为。这种情物关系,其敞开的是生命自然之性情与未受人为扰乱与情感灌注的自在之物、本真之物。于此,庄子的情物关系构筑了人之本质与物之本质直接相遇的生命自由关系,人与物也因此而独化、玄冥。
人之本质与物之本质的随遇相逢,打开了心物一体直观的会通之境。心与物的相通使得个人生命与万物打成一片,和谐共存于自然大化之流。心物能够相通为一,既源于心物在宇宙生成意义上气的同一,又源于境界之心对万物的临照。从宇宙生成论而言,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皆是道经由气为中介所进行的自然创化。《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道正是通过气的中介,特别是阴阳之气的聚散循环而创化万物并联通万物。“天下一气”使得宇宙万物,包括人与物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使心物的相通为一在材质上有了可能。不管是“通天下一气”还是“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地》),说的都是宇宙创化时的原始和谐与混沌状态。然而,历史的发展,使得这个未始有物、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的混沌世界被凿窍而亡。由此,人与物的相通为一只能通过精神境界的临照或“以道观之”方有复归的可能。故庄子心物直观的通物,乃出于一种精神境界超越性的“与物齐一”。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齐物论》)、“若一志”(《人间世》)、“同于大通”(《大宗师》)、“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天道》)等表述,都是经由心物的直观而达至的心物一体之精神境界。《秋水》云:“始于玄冥,反于大通。”世界万物始于气的原始和谐,最终通过心物一体而复返于境界的和谐,是庄子对人生终极问题给出的答案。
庄子的心物直观打开了人生在世的存在性境域,其美学性是不言而喻的。爱莲心在谈论庄子的心灵转化论题时说:“分析功能因此而完全分解了。与此同时,审美功能通过其与童真心灵的联结而联合起来。”[1]显然,庄子心物直观所激发的审美功能不同于曾被庄子批判过的山林皋壤之美。前者是一种“无态度”、无感物情动的人与万物一体之生命共存,属于存在论或境界论美学;后者则是一种因外物感性形式影响而滋生情感态度倾向性的心理学美学。《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議,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庄子看来,只有通过原(推原,本原地呈现)、达(通达、感通)和观(观照、直观)的直觉或审美方式才能达成对道或道境的领会。濠梁之辩中,惠施以对象性认知的方式认为人无法知道鱼儿是否快乐,而庄子则以审美直觉方式感受到了宇宙生命的感通之美。在心物直观面前,人与鱼、庄周与蝴蝶是物我两忘、相通为一的。也就是说,庄子的心物直观打开了人与物的存在本性,敞开了人与物、人与世界和谐自然的共存境域,生命由此感受到了与道合一的至美与至乐,这是一种“由根源之美而来的人生根源之乐”[2]。因而,心物直观使生命得以虚静澄明并散发出一种生存境界之美。
《知北游》云:“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自由无滞、惠照澄明的体道生命状态就是一种审美直观状态。人与道的相通之境,有如新生之犊一般明净素美。庄子极富诗意地把这种精神境界描述为:“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间世》)体道之人的内心世界是明亮而美妙的,如同太阳照进房子一样,映照出宜人的光芒。“莫若以明”(《齐物论》)、“此之谓葆光”(《齐物论》)、“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天地》)、“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庚桑楚》)等,皆为这种澄明之境的形象描述。朱良志说:“器宇安泰、心定神闲的人,发出的是自然的智慧之光。发出自然智慧之光的,人便自显其为人,物便自显其为物。人与物都在光亮中自由自在地存在。”[3]这道智慧光亮、境界的光芒让生命有了自我存在的意义感,有了纵迹大化的生命归属感,有了“和豫通而不失于兑”的、与自然之道相契的高峰美乐感。
三、心物一体之境与技艺的显现 / 通达
通过心物一体直观,人实现了自我的心灵转化,物也实现了自身物性的显现。生命居于这一人生境界,既是庄子对人生在世终极意义的回答,又是庄子对人生至美、至乐精神的终极体验。然而,庄子并没有让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隐微而不可见的生命境界仅限于一种静观的内在精神体验上,还为之打开了实操性的可感之径与通达之途。
心物一体使现实经验的身与心、人与物的裂隙得以抹平,心 —手(身)— 物之间也因此实现了无缝连接与自由流转。体现心 — 手(身)— 物贯通一气的技艺得到了庄子的极大关注。郭象《养生主注》曰:“直寄道理于技耳。”《天地》云:“能有所艺者,技也。”成玄英疏:“率其本性,自有艺能,非假外为,故真技术也。”张祥龙说:“技艺几微就是介于有(显)和无(隐)之间的发生机制。中西的古人之所以总将它与艺术、手艺、技巧联系起来,就是因为在这些无法依靠观念表象的技艺活动中,人获得了一种无形而可信的认知态势,从而进入了一个更廓大的、充溢着原发意义的境域。这活动与境域相互引发、相互维持,使得新的生命从中绵绵生出而不绝。”[4]《天地》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可见,庄子的理想技艺行为远不是人为的技术或巧能,而是不经外力、不假机械而发自生命性灵并与世界一体相通(引发、维持一种原发境域)的身心实践活动。它以一种直接的身体实践活动给生命体道境界留下了一个实践性“证据”:一方面,技艺成为道境的感性显现,是道境的在场证明;另一方面,技艺成为通达道境的媒介,是道境进修的身心操练。两个层面相互交错、相互引发、相互维持,彰显了艺道互现、艺道两进的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
为了让道境不局限于精神的内在体验之中,庄子寓言中讲了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吕梁丈人蹈水、梓庆削木为鐻、工倕旋而盖规矩等很多具有高超技艺的体道者所实施的实践活动。身体技艺作为心物一体之道境的实践性“证据”,为弥合身心、主客裂隙提供了实践例证,切实地架构起了“道进乎技”的文化关联。庖丁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养生主》)、轮扁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天道》)、痀偻者的“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达生》)、津人的“未尝见舟而便操之”(《达生》)、吕梁丈人的“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达生》)、梓庆的“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达生》)、工倕的“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达生》)等说法表明,这些技艺皆为顺应生命本性而发出的鬼斧神工之举,是弥合身心、主客矛盾裂隙而实现的心 —手(身)— 物之间自由流转的结果。这种身体技艺并不凭借外在的功利机巧,它任性而发,故这种身体技艺能和道境相通相合,把不可言说的道境具体呈现出来。因此,心物直观一体的精神体验之境经由身体的实践活动,转化为心 — 手(身)— 物一体自由联动的直觉式创作活动。这种“以天合天”的直觉式技艺创作过程是一种身心、主客两两相忘并忘其所忘的心、手(身)、物合一的艺术创作过程。在人显其心、身复其身、物返其根的心物直观创造中,“天机自张”、依本性发用的“艺能”以造化与心源为一进行创造,心手相应,“随物赋形”,便成就了“疑神”之作。这种技艺活动正因为展现了生命的心物一体之道境并成就了惊犹鬼神之作,而成为后世艺术创作活动的理想楷模。
正由于技艺以显现道境为目标,技艺也因此具有了实践功夫论色彩。通过技艺的不断训练与体悟所达成心 — 手(身)— 物的合一,不但是练就高超技艺的需要,同时也是成就生命体道之境的需要。前面提到,心物直观关系的建立需要对现实习俗之心与器用之物进行价值翻转。这里存在着两个环节的转化:一是人自身内在身心状态的转化,要由理智欲望之身心状态回归为自然自由之身心一体状态;二是人与对象外物关系的转化,要由主客二分的态度倾向性关系回归为物我一体遇合的关系。这种心物直观关系落到实践活动中,关键在于弥合身心、主客关系之间的矛盾裂隙,而实现心—手(身)—物之间的自由流转。手(身)创制活动的进入使得体验性的心物关系转化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实践论修行。将技艺活动视为一种心物直观境界的实践论修行或进修之道,庄子为中国艺术的存在意义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旨趣。
因此,技艺实践成为道境显现的关键就在于以手(身)的创造行为来实现与心物之间的无缝对接,使得技艺与心灵、技艺与物性打成一片。一方面,技艺活动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去摆脱身体动作与自由心灵之境的疏离,以实现手艺与心境的合一。《天道》载:“(轮扁)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说的是心和手(身)的关系。技艺的创作往往会受到表达手法的限制,但得手应心之人则不滞于手,不凝于心,打破了技艺心象和技艺传达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技艺活动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去摆脱主体积习对物性的分离。《达生》云:“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指与物化”可视为手和物的关系。“‘指与物化,是说明表现的能力、技巧(指)已经与被表现的对象没有中间的距离了。这表示出最高的技巧的精熟。”[1]技艺的创作还受到被表现对象的限制,但指与物化之人则“其身与竹化”,打破了技艺传达和对象之间的隔阂。
如同艰涩的精神修养一样,技艺的实践修行也是极为艰辛的。其不但需要心性修养工夫的配合,还需要身体技艺对身心与主客分离的双重超越。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如果藝术家缺乏精纯技艺的基础而奢谈神妙之法,只能是“效颦者徒劳捧心,代斫者必伤其手”。庄子的技艺练习不是出自书本理性知识的习得,而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不以心稽”的身体力行的身心妙会。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庖丁在刚开始解牛的时候,是以“所见无非全牛者”的眼光来对待外物的,其解牛的技术和族庖无异,只知道用刀去砍剁;三年之后,庖丁是以“未尝见全牛”的眼光来对待外物,其解牛的技术和良庖相当,开始去用刀割筋肉;当庖丁全盘体认了牛之物性并“以牛相观”时,其解牛的技术就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到一种依乎天理、顺应物性的游刃有余的高超艺术性境地。在痀偻丈人承蜩故事中,丈人从“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累三而不坠”到“累五而不坠”的技能进阶,以及身若槁木般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都是以技艺苦修的方式所进行的心、手(身)、物三者会通为一的磨合、领悟与操守过程。如同“以心复心”的心性修养一样,技艺的训练与实践也是在不断地心手协同与主客融通中渐趋合一,所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由此可见,庄子技艺观是在体道和证道的宏观视野下所进行的一种哲学运思。庄子在去除道境被逻辑言说可能性的同时,保留的是道境经由身体和技艺审美显现的可能性。
从对习俗心物关系的解构到心物直观关系的建构,从静观式审美体验到行动式技艺实践,庄子以心物一体美学打开了人与世界本源境域性的关联互动,为中国特色的美学经验与艺术实践树立了一道丰碑,被后世不断地仰望。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