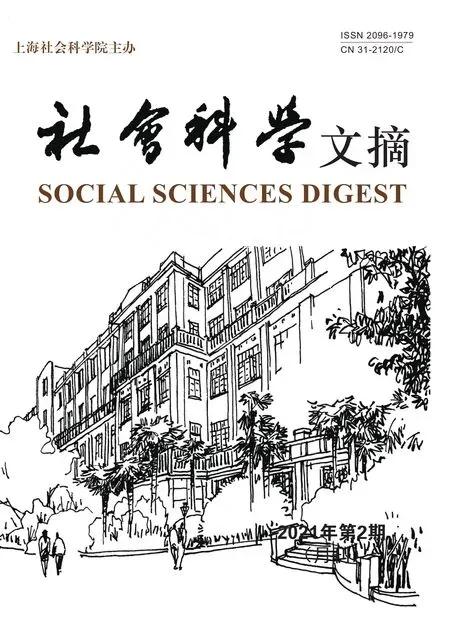“存在”与“家园”的双重探寻
——论格非小说中的乡愁乌托邦
文/廖高会
引言
“家园”与“存在”是贯穿格非小说的两大主题。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本土与全球、存在与现实等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中,格非一直在叩问和探寻着现代人“存在”的正途和理想的家园。在某种意义上,格非对存在的追问与其乌托邦冲动相关联,因为乌托邦不仅指向“未来”社会,同时“也是对人的内在世界和存在状况的分析”。格非对“存在”与“家园”的持续关注与探寻,对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的警惕与对抗,既源于其深沉而强大的乡愁乌托邦情感冲动,也源自其坚守“文化家园”的传统士人的弘道情怀和重建“乡土伦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对“存在”的哲学追问
格非小说创作可以世纪之交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无论哪个时期,格非都坚持着对存在方式和意义的追问。格非认为有两种层次的真实存在:一层是看得见的现实,这是传统现实主义所要再现的外部真实世界;另一层是隐秘的真实,包括人的复杂内心世界和那些隐秘的不为常人所知的可能存在。格非认为隐秘存在或曰“感觉的真实”是现代小说的重点表述对象。格非还进一步指出:存在是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具有“可能性”的现实,现实能被阐释和说明,因此也是完整、流畅和被作家复制的,而存在则呈断裂状,是易变和难以把握的,需要作家去“发现、勘探、捕捉和表现”。格非所说的两种层次的现实也即现代人的两种“存在”方式,它们对应着不同的家园形式,外在的“现实”对应着“存在”的物质家园,内在的“现实”对应着“存在”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对物质家园的映象式重现或回顾式想象,并在此过程中融入了对未来的瞻望和美化,最终形成具有理想色彩的家园形态。
格非小说创作呈现出“出走—回归”的心灵图谱。前期小说试图在“出走”中追寻存在的价值意义,后期小说试图在“回归”中筑就存在的栖居家园。其前期小说重在对个体生命“如何存在”进行探寻,以解决个体生命的具体展开形式等问题,后期小说则转向对“存在于何处”进行探寻,以解决集体、族群甚至人类存在的空间性或文化性问题。因此,可以说格非的转型是从前期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转向了对集体存在的关注,从对个体伦理的关注转向了对公共伦理的关注。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存在与家园皆或显或隐地贯穿于格非小说之中,这种对存在及家园的持久的形而上哲学思索,体现出一种乡愁乌托邦冲动。乡愁乌托邦一方面对“往昔”进行怀旧式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对“未来”进行前瞻式的美丽憧憬,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出一种全新的乌托邦精神家园形态。
欲望侵蚀下的“存在”家园
不断膨胀的欲望对传统乡土空间和现代城镇空间的侵蚀及其造成的“废墟化”,对于个体生命本真的浸染蒙蔽而致使精神的“荒漠化”,正是格非着力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格非对现代欲望化社会批判的动力来自其挥之不去的乡愁意识。格非的乡愁意识中既具有以怀旧为特征的传统乡愁,也有以线性进化为特点的现代乡愁。现代乡愁即“人们不再回望过去的家园,而是对建构未来理想家园作前瞻式展望”,并且与现代启蒙精神相呼应。无论是怀旧还是前瞻,都融入了乡愁主体的想象与美化,均具有乌托邦色彩,而这种具有浓郁乡愁色彩的理想化想象空间,可以称之为乡愁乌托邦家园。乡愁乌托邦冲动正是格非进行社会批判和哲学沉思的情感动力。
格非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围绕着“家园”与“存在”展开,其中又分为物质存在、伦理存在和哲学存在三个层面。作为物质家园的乡土社会是精神家园的基础,物质家园的丧失将直接动摇精神家园的存在基石。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逐渐解体,格非内心充满了忧虑,这种忧虑更多在其20世纪90年代后的小说中流露出来。比如,《夜郎之行》中导致城镇化给人带来了失落与迷茫,人们由以前的自信变得颓废,夜郎也失去了乡土本色;在《春尽江南》中,曾经山清水秀的鹤浦,如今雾霾严重,污水横流,如同“肮脏的猪圈”,让人连呼吸都很困难,已不再适合居住。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是全方位的,除给物质家园带来了较大冲击外,还造成了传统伦理秩序的解体。传统乡土社会伦理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个体欲望的放纵,于是欲望批判也成为贯穿格非小说的主要内容。格非小说《陷阱》和《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两篇小说相互关联,讲述的是现代人情欲失控、出轨而相互背叛的故事。《大年》中讲述了乡土社会中各种权力围绕着“女性欲望”展开角逐并因此带来的相互杀戮的故事。《春尽江南》中的主要人物庞家玉为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浪潮所挟裹,从一个真诚追求诗意的女孩蜕变成一个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可以出卖身体和灵魂的空心人。乡土社会的现有问题并不都是现代性冲击的结果,其本身也有落后愚昧的一面,格非对此也展开了反思与批判。这与其前瞻性视角和现代乡愁情感相对应,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等人的乡土批判传统。比如《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仍然存在着偷鸡摸狗、贪婪自私、至亲反目、告密卖友等乡村固有的丑行恶疾,它们同样侵蚀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
格非对存在家园的追问与探寻,不只停留在物质与伦理层面,还抵达哲学层面。这表现在他于小说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和追问。《迷舟》中,军官萧带着警卫员回乡奔丧,却沉迷于恋情和乡村俗事,带有监视任务的警卫员以萧出卖军队机密为由而枪杀了萧,萧的冤情与枉死便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陷阱》与《褐色鸟群》中,不同亲历者讲述的情节相互矛盾、相互拆解,从而使事实与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无可辨别。《敌人》《边缘》《江南三部曲》《望春风》《隐身衣》《月落乌寺》等小说都存在着叙事的空缺。叙事的空缺造成了历史逻辑链条的断裂,这不仅是格非语言修辞的结果,更是源于历史存在的本源性缺失。人除了活在当下,还需要历史、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维度的持续与连绵,从而获得存在的整体性,而对历史真相的质疑使存在(包括人的存在)遭到了悬置。一旦历史被抽空,存在的本源也无从获得,现在与未来也变得无法把握,存在的精神家园也变得虚幻不实。人和物的存在都面临着被时间洪流淹没的危险。对历史真相的质疑,本质是对时间与存在关系的拷问。历史的模糊与不确定,甚至被抽空,作为哲学层面的存在及其形而上家园便失去了依托而变得虚无飘渺。
乡愁乌托邦与家园重建
格非早期小说中乡愁意识多散布于不同故事的叙写之中,他常常巧用闲笔,在故事叙写之中荡开笔墨,描写乡村景致,回忆乡土风物,抒写怀乡情感。格非把自己的乡愁化在乡土风物之中,而乡土风物与文化已经化在格非的血液之中,不断地从他的潜意识中跳跃而出,成为他浓郁乡愁意识和家园情结的见证。早在1990年,格非就在短篇小说《唿哨》中进行了一次乡愁乌托邦家园的想象之旅。在这是一篇具有浓郁诗化色彩的小说中,格非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绝佳的世外桃源图。小说隐去了年代,时间被空间化了,主人公孙登穿越了古今,他静静地坐在藤椅中“守望着流转的光阴”而无所期待,他既是千百年来乡土田园生活的见证者与欣赏者,也是其中的在场者与参与者。孙登正是格非自己的化身,格非借助孙登的静观与冥想,完成了一次对民族传统的回望与精神沟通,也痛快淋漓地完成了自己乡愁家园理想模型的搭建。
格非所要探寻和建构的家园不仅是个体存在的归宿空间,而且是集体的、族群的共同存在的家园形态,而其中的伦理也属于公共伦理。格非说:“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佛教称之为‘彼岸’、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完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人面桃花》中讲到的桃花源也是这么一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所在。”继《唿哨》以后,格非于21世纪创作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隐身衣》《月落荒寺》等长篇小说,继续探寻着现代人家园的建构问题,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探索“存在”家园的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这个过程也展示了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乡愁乌托邦情感冲动,对现代知识分子格非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
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对乌托邦家园设想的演变过程,这也是他对理想家园重建的深度思考与探索。《人面桃花》中,王观澄、张季元和陆秀米有着各自的乌托邦家园建构模式。王观澄建构的花家舍乌托邦属于江湖乌托邦,张季元、陆秀米的乌托邦是革命乌托邦。花家舍属于王观澄等人打造的世外桃源,花家舍做到了礼仪教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和公平公正。在这里,百姓皆能安居乐业,但花家舍在繁荣兴盛的背后却干着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而张季元试图通过革命建构乌托邦家园,但他的革命目的本质上和阿Q“敛财、女色和报仇”的革命目的是一致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相差甚远。王观澄与张季元的乌托邦只重结果的公平而不求手段的合理,在本质上是反乌托邦的。后来,陆秀米也走上了革命乌托邦道路,但秀米的革命目的是感性而个人化的,在本质上是个人乌托邦冲动的意识形态化,这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设想无疑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继续着母亲陆秀米的乌托邦实验,试图实现天下大同的桃源梦想,这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家园理想,最后在现实面前以失败告终。郭从年的花家舍公社似乎实现了他天下大同的梦想。花家舍公社丰衣足食、人人自主、自由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尝试;但花家舍公社存在着“101”监督制度,这导致了花家舍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人人心存恐惧。这种放纵人性之恶的社会管理模式最后遭到了谭功达的否定。
以上乌托邦实验都属于现代性乌托邦实验。现代性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和道德的,因此为了社会历史进步可以牺牲固有的阶段性伦理秩序,但从个体伦理来看,牺牲固有的道德伦理甚至牺牲某些人的利益,则是非道德的。也就是说,王观澄、张季元、陆秀米、谭功达、郭从年等人的现代性乡愁乌托邦,都执着于历史的进步论,他们可以忽略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采用非伦理手段达到历史进步的目的,其本身是与乌托邦的核心理念即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以非道德甚至恶的手段获得乌托邦实现的物质条件,使王观澄、谭功达等人的乡愁乌托邦实验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悖论,但这种悲剧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激进甚至疯狂的乌托邦实验并不适宜在乡土社会中进行,否则只能是悲剧性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也逐渐过渡到后现代社会。格非的《春尽江南》《隐身衣》《月落荒寺》等长篇小说均以后现代社会为背景。后现代社会的乡愁乌托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资本开始渗透其中,从而形成了“资本乌托邦”。比如《春尽江南》中张有德投资建成的花家舍水上乐园、绿珠等人在龙孜(西藏)的“香格里拉的乌托邦”,都是资本控制下实现私人欲望的场所。同时在消费主义时代和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还把乡愁包装成各种商品出售,使乡愁成为一种消费式的“仿真体验”,“或者与文化旅游产业结合,成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被消费掉”。因而乡愁乌托邦也随即被产业化,而产业化的结果便是不断的复制。复制是利润产生的有效手段,于是乡愁乌托邦便成为毫无个性特色的被商业意识形态所固化的商品符号。
由于以上乡愁乌托邦探索都行不通,格非转而把乡愁乌托邦家园的建构寄托于艺术审美。在《隐身衣》中,主人公“我”与志趣相投的古典音乐发烧友组成了联系紧密的信誉良好的“共同体”或“乌托邦”。这种审美乌托邦在后来《月落荒寺》结尾处的音乐会上进行了集中叙写。格非把古典音乐《月光》、正觉寺(荒寺)和中秋圆月、古槐树等意象并置,通过音乐的召唤与净化,似乎找到了通往乡愁乌托邦家园的正途;但是依靠音乐等艺术建构的“审美乌托邦”只属于少数人的“乌托邦”,具有鲜明的贵族化倾向而远离了大众。这种乌托邦以“审美共同体”取代了“伦理共同体”或“制度共同体”,因而天然地存在着伦理或制度不足的缺陷,缺少了稳定性和恒久性。“审美乌托邦”所建构的共同体并不能规约参与者的人性与伦理道德,正如《月落荒寺》和《隐身衣》中的“审美共同体”成员由教授、老板、个体户、律师、公务员、黑社会头领等组成,有的堕落腐化,有的罪行累累,有的附庸风雅,有的沽名钓誉,他们只是更加高级的“乌合之众”。这种不可靠的“审美共同体”并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大众化的乡愁乌托邦家园。
为了建构现代社会大众所向往的乡愁乌托邦家园,格非把这种期望寄托于现代乡土空间。他在《望春风》中有意识地在近似废墟的儒里赵村完成了家园的重建,即小说最后部分让“我”和春琴回到赵村重过田园农耕生活。格非说,在《望春风》中他要给那些生活在苦难中而看不到希望的人提供一些安慰,他要创建梦想能部分地实现的乌托邦。这种乡愁乌托邦家园是面对大多数中国人建构的集物质、文化和精神于一体的家园,这使得格非的乡愁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社会主义本质。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探索之旅后,格非重新把乡愁乌托邦家园的建构锁定在乡土空间,试图建构“新乡土乌托邦世界”。这种以传统乡土文明为基础、融合现代文明的“新乡土乌托邦”,正是格非对20多年前《唿哨》中古典乌托邦的回应与超越。
总之,格非存在着显明回归传统的乡愁乌托邦情感冲动,这种回归的冲动并非保守与退缩,而是面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可能危机而采取的应对策略。它融合了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同时满足了回望式传统乡愁和前瞻式现代乡愁的情感需求。马克思曾指出,“东方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公社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可以和西方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相结合,“从而在新的历史层面上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非西方方式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格非推崇的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乡土乌托邦便有了实践的可行性。这种乡愁乌托邦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尝试着回答当今之世是否存在回乡之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