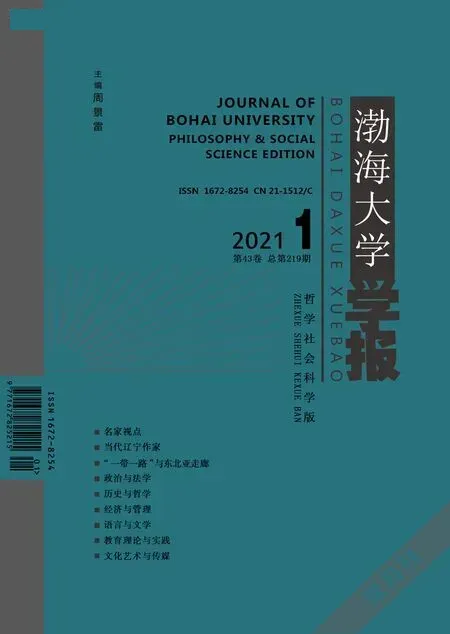深情叙写与诗的纪念
——李皓长诗《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简论
邢海珍(绥化学院中文系,黑龙江绥化 152000)
武汉的新冠疫情早就过去了,中国诗人激情饱满的“抗疫诗”写作大潮已经渐趋平静,其中与武汉有关的诗作可谓风起云涌、不计其数。在众多优秀的作品中,李皓的长诗《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应当是十分醒目的一首。无论是对人生世界的感悟力,还是诗歌艺术的表现力,诗人李皓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从诗人的整体创作态势看,李皓正值创造力的旺盛时期,他的许多诗作都呈现出生命智慧的灵性之光与高远襟抱的浑朴和大气,具有了走向成熟的通透与劲健。
长诗《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是以自叙传的形式所抒写的心灵独白,但诗人的“独白”有着鲜明的外向性,充分的叙事内涵打开了外部世界的天地,把心灵的封闭之门敞向他者,在丰富的具象世界里寄托情感,并使其博大和曲折的流势获得广阔的回旋空间。
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说:“中国文学未曾与中国的社会兴衰和万家忧乐相脱节,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但文学的天空从来是浩瀚而丰盈的:外在世界辽阔生动,内在世界隐秘而丰富。文学既面对着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文学也面对着人世悲欢和人生忧戚。应当认为,所谓文学的功利性,既包括文学的教化作用,也包括消闲作用。文学既教育人,文学又抚慰人。”[1]诗人李皓不是为潮流所裹挟的诗人,此诗虽然写作于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体现出文学反映现实的及时性,但又决不是应时应景之作,诗人不以空洞、浮泛的激情托举虚词、大话,而是从经验和经历的基点出发,是在生命和生存的直觉中获得的深切体验和感受。所以李皓的这首抗疫诗不会因为武汉的疫情过去而失效,它将以其自身的审美和抒情优势成为具有长久感染力的传世之作。
一、叙事的抒情化进程
《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一个“想”字便确定了诗的心理形态的说话方式,诗人的“去一趟武汉”还未付诸行动,而是一种畅想的心理状态。诗的口语化与生活情境的写实呈现,为全诗奠定了一个叙事基调,形成了回忆往昔、顾盼当下、怀想未来的自由而舒展的诗意情境。长诗的开头开启了个人“经历”的入口:
我妈妈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姥姥,那一年
头也不回,跟着我姑姥爷随军去远方
姑姥姥的口音从此改变,再也变不回来了
而让我妈妈艳羡不已的南方大城市
从此在我小小的心里,深深地扎下根来
啊!武汉,我妈妈一直把你念叨至今天
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
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
诗从“姑姥姥”即妈妈的姑姑开始,是从两代人的面前挖掘对武汉这座“南方大城市”向往的历史根性,而当前一个重大事件的催生因素诱发了有关武汉的诗性话题。尽管以前可能不止一次去过武汉,但在忽然之间却有了一种冲动,“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情感的流水潺潺缓缓,六句之后有一次反复,起伏跌宕,一唱三叹,诗人娓娓道来,在意味深长的诉说中就如车行路上。这种接近于散体化的陈述方式是诗人在语言表达上的一种个性化追求,语言的局部流于“白话”叙述,但整体的情境却是诗意充沛的。
在《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一诗中,诗人择取人生经历中与武汉有关的内容,是生命的感怀,是对命运的剖视。真实、具体的生存环境,完全真实的人物事件,是诗歌抒情和写意的饱满、结实的基础和依据。可以看出,诗人所引发的思辨、感悟和感慨绝不是一种想当然的“有感而发”,而是极为严肃的观察、思考与理解,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的过程。
当我知道中学生诗人洪烛和邱华栋
先后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的时候
我在东北一个叫做城子坦的小镇上
向西南方向深情地投去了初恋般热切的眺望
可惜位于山坡上的新金县第三中学
由于海拔太低,阻隔了我青春的激荡
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
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
1980年代的中学生,大都狂热地爱好诗歌
《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还有《春笋报》
是那些有点歪才的少年,书包里的标配
他们基本都荒废了数理化和外语。捧一张
《语文报》,为变成铅字的几行小诗陶醉不已
每天都在做梦,梦想被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
诗人描写了人生最真实的图景,这样的诗歌情境几乎呈现了纪实性的生活内容要素,而不是以虚构的方式来渲染、放大情感,诗的字里行间十分自然地凸显了清晰的生命纹理。诗中所写的著名作家洪烛和邱华栋,当年都是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没有参加高考,只是凭借文学创作的成就胜出。这在当年成了许多文学青年的梦想,诗人李皓正处在那个年龄段,也自然成了“破格录取”梦中的一员。
在对当年经历的回顾中,诗人李皓的叙写是平静而深情的,看见别人已被破格录取,而“我”却只能在“东北一个叫做城子坦的小镇上”投去“初恋般热切的眺望”,以两句极富想象力的情景描述,完成了美不胜收的诗意构想。“可惜位于山坡上的新金县第三中学/由于海拔太低,阻隔了我青春的激荡”,新金县第三中学虽在“山坡上”,但相比于大城市武汉,相比于名牌高校武汉大学来说,还是因为“海拔太低”而难以实现青春激荡的梦想。多么好的情境创设,既是真实的人生经历,又被诗人在情感的雨露中巧妙浸润,诗的境界立时释放出感染的张力,让人感受到灵动与美的艺术享受。
在情境写实的过程中,虚化是不可少的,除了描述中的比喻、变形等方式,诗人把每六句中间插入两句重复出现的“咏唱”形式,框定为一种稳定的歌谣体格局。其实这正是诗人的虚化手段,从整体看,长诗的叙事因素较强,在整体调式中实多虚少,就会冲淡诗的美质和抒情的艺术氛围,这种“咏唱”的虚化具有了补救的效应。所以我们读“1980年代的中学生,大都狂热地爱好诗歌/《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还有《春笋报》/是那些有点歪才的少年,书包里的标配”也感觉是虚中之实,这与“咏唱”的虚化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如果“叙事因素”在诗中只是平铺直叙,那么诗就不是诗了,就会失去灵动的风姿和气韵了。诗人李瑾在《谭诗录》一书中这样谈及诗歌的叙事:“诗歌是以一种场景结构展开的,亦即诗歌不必非得出现小说般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情节诸要素——这种全景式叙述、交代、描摹乃出于‘讲故事’的必要,且通常注重细节挖掘,架构起自足的文本空间,以其直达问题真相。”[2]诗人李皓善于找到一个可以“诗化”的点,让叙事的因素快速地上升为想象而挥发的亮度。
长诗的“叙事”是一种抒情化的叙事,与小说的叙事具有不同的品性。李皓是用回顾往事的方式历数曾经与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些交集,以“碎片”的“事”性因素展示了自己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段性内容,既避免了流于近似于小说的人物故事叙写,又实现了不使诗歌表现流于空泛宣泄情感的毛病。
从整体结构上看,诗人是以心理的结构方式,采取意识的流动来实现具象画面的拼接组合,以抒情调式的连贯性使“碎片”的叙事状态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诗中反复出现的“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一样”,就是诗人的“歌谣”形态对叙事结构的融通与整合。
二、穿越人间烟火的“诗化”叙写
《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展现了一大片内涵丰富、多姿多彩的生活情境,诗人李皓的灵性之笔点染了活生生的人情世故,把诸多生活中的实景实事化而为诗,从容不迫,大气凛然。描写武汉要写武汉人,“武汉是个敢于破格的城市”,而与“警卫连张指导员”的人生际遇,则改变了诗人的生存轨迹,所以有了“对武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感念。那些雷达兵战友们,“从武汉给我写来的信,总是湿漉漉的”,生活情味、地域特色总能把人带进现实人生世界的美好感受中来,成为诗之想象飞腾的立足点。“长江上的点点白帆,不断掠过中华鲟的身影/还不时地散发出鹦鹉洲萋萋芳草的芳香”,以景物点染浸润,注入了诗的张力与活性。
从生活的真实泥土到达诗意情境的天空,并非是天性的同一与必然归属的和谐,诗人创造的翅膀要经过艰难的穿越,生活诸多琐细的浮尘与人事的多余杂质必须清理剪除,人间烟火与诗意风景,尚有一段距离需要诗人的跋涉,才能抵达审美的澄明之境。李皓写武汉很是放得开,外物与内心的通透,使得生活的情境与人生命运相互映照,形成了主客互融的抒情整体:
从此开启的,除了眼界、胸襟和胆识
还有报业和一个人刻骨铭心的十年
神农驾神来之笔的一场雪,满地白银
心旷神怡的岁月,那是生命里的爱和黄金啊
生命所经历的十年岁月,与武汉的大天地有关,是武汉的一种神性的“开启”,“报业”之路,令人有无限感慨,写到神农驾“神来之笔的一场雪”,“那是生命里的爱和黄金啊”,生活的情境因心性和情怀的敞开而变得开阔、悠远。当疫情来临之时,诗人回忆有关武汉的往事是一种发自于心的深情的叙写,“武汉是个文人扎堆的城市,当我/与全国各地一干期刊主编,跻身刊博会/就像一滴水落进了不知深浅的长江/那一夜,大诗人车延高,张执浩,余笑忠/他们频频举杯,如果不是默白屡屡解围/我必定成为沉下去的河,成为一条武昌鱼”,那么多熟识的朋友,曾在酒桌上把酒言欢。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一场大灾难来临,诗人是凭着心中的记忆,抒写了对武汉、对朋友的怀念之情。诗中写到酒席之上食武昌鱼的鱼刺扎了嗓子的往事:
武昌鱼的刺,多么像那些冠状病毒
尖锐地扎进许多武汉人的喉咙
让他们咳嗽、发热,全身无力
而2002年的一根鱼刺,将大连旅游局长
对武昌鱼的美好想象,搅得涕泪俱下
他善于演讲的嗓子,被一顿午餐改变了腔调
一位大连的旅游局局长受了鱼刺之害,“被一次午餐改变了腔调”,联想到当下新冠病毒肆虐,因而导致封城封户的严重事态,许多武汉人中招,“让他们咳嗽、发热,全身无力”。具体的生活事象构成了一种叙事的比照、衬托,以自身经历的厚度来营造强劲的诗意氛围。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内蕴使叙事的内容变得更加亲切温暖,文字间所洋溢的烟火气息形成了极富情趣之美的感染力。
虽然长诗具有明显的叙事形态,但它的本质还是抒情的,叙事的本身就是抒情的载体。正如苏联诗人奥·曼杰施塔姆所说:“诗是掀翻时间的犁,时间的深层,黑色的土壤都被掀翻在表层之上。不论如何,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当人类对眼前的世界不满,向往深埋底层的时光时,他们便像耕犁者一样,渴望得到时间的处女地。”[3]用想象之笔描述疫情中的作家、诗人朋友们的现实情境,以具象的文字寄托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惦念之情。诗人就像深耕者一样,突破表层而走向深度,诗人的情感方式使记忆中的人与事物呈现出清晰的时间的影像。
因疫情而封城的武汉,有一大批包括诗人、作家朋友在内的英雄的武汉人民搏击坚守,为了战胜大灾难而为人们所牵挂。长诗在叙事的进程中抒发的深情厚谊,在歌谣的舒缓节奏中让人心旌摇荡,许多诗人、作家朋友们的具体生存状态的写真,让人进入了疫情发生时的现实情境之中,通过文字感受到当时设身处地的独特心境。
当然,我们可以把此诗称之为“叙事诗”,但是诗的本质是表达情感的,叙事进入诗歌的表达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诗化”整合。这就是让这些“人”和“事”的因素尽快超脱情节和故事的局限,在虚化中,把“实事”的形态变为“心理”的形态,把整体的形态变为“碎片”的形态。
诗人写乘机飞临武汉,一场大雾留下了朦胧、神秘的印象:
武汉是不是像重庆一样多雾,我不知道
反正我第一次飞往武汉的时候
大雾牢牢锁住了天河国际机场
我们的航班,不得不备降长沙黄花
那一夜,我们沿着扑朔迷离的洞庭湖
在昏昏沉沉之中,抵达细雨霏霏的汉阳
一次曲折的“备降”和“扑朔迷离”的雾中之行,在诗人笔下从容写来,可谓形神兼备、美不胜收了。这样的情境写得开阔、大气,在情景的交融中襟怀舒展,不能不让人陶醉其中。虽有一定的叙事因素,但诗人以主观化的方式对一次行程进行了虚化,其中暗含的情感因素,营造了一种让读者可以身临其境的艺术氛围。
李皓善于把人生现实中实在的物质性内容虚化为情感的流动,这种“诗化”的过程重心性、重主观,在从容的叙事中抵达充分的抒情化境。
三、诗性的纪念与情境的深度
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少有的大灾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和悲剧性的后果。李皓的长诗《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写作于中国总动员抗击疫情的重要节点,情思深切,诗意饱满,极具鲜明的风格特色,无疑是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诗性纪念。
一次举国动员的抗疫大潮如洪流涌向武汉,中国终于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李皓以诗的情感留下了关于这次历史事件的记录与感怀,这是有声有色的诗性的纪念。诗人内心的真诚抒写了面对巨大灾难的决心和信念:“我去武汉,绝不是给你们添乱/我只是想,像那些义无反顾的战友那样/做一个决绝的逆行者,迎着病毒/拉开格斗的架势,用尽全身的力气/铰杀。铰杀熙熙攘攘的飞沫/铰杀陌生的新型,铰杀恶毒的冠状”“我只是一个蹩脚的诗人,我无法/带来雷,带来火,但我笃信信念是神/如果我到了武汉,我第一个要去/火神山和雷神山,我不能为它们/添砖加瓦,但我愿意为它们守候信仰/守候一颗颗火红的心,跳动如雷霆”。
在疫情肆虐期间,诗人无法去武汉,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诗人只能用诗铺一条通向武汉的心灵之路。诗人在精神领域的高端,就是一个“决绝的逆行者”,与千百万驰援武汉的人们在一起,“拉开格斗的架势”,为全民抗疫做出了贡献。这样的诗篇留在了我们前行的历史进程之中,它就是火神山、雷神山的坚固的砖瓦,为守候信仰而高矗在文字中间。
从长诗《我想坐车再去一趟武汉》的创作看,我对李皓的诗歌创造内功是非常服气的,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抵达了极高的境界,这首长诗在众多的抗疫诗中应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一文中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4]长诗以丰富的含量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把人带入绝佳的情境之中,在“百意”与“万景”之中打开了武汉迎战疫情的独异画卷。李皓善于把握诗歌创造的整体性,尤其在情境的营造上达到了高度和谐、高度从容的艺术水准。长诗以每六句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单位,若从叙事的连续性来说是断裂的形式,但诗人的“歌谣”体式,使长诗成为咏唱的整体,在贯通中自适自足,形成了跳跃、起伏的壮阔、跌宕之美:“是的,在2002年之前我一直在揣度/揣度一个只有三个镇子的城市,如何/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一个伟大的地标/揣度那些伟人,为什么纷纷在武汉/到中流击水?在与杭州西湖遥遥相对的/东湖,写下那么多浪漫的诗篇!”诗人在历史和现实的联想中,把武汉作为中国的“伟大的地标”的城市生动地推举出来,其中涵纳了憧憬与崇拜之情。在情境的拓展中,李皓力求以主观的渗透实现诗意的深度,不是那种刻意追求但却获得了悠远、精粹的思辨效果:
我知道,通往武汉的高铁暂时停开
我只能寄希望春暖花开的时节
坐着我喜欢坐的复兴号
坐上十几个小时,朝发夕至
喝酒也行,喝茶也好
在风景如画的晴川,谈诗,谈文学理想
多么自然的抒写,但诗人却能在悠长的情韵中表现出生命的大境界,想象之中有希望、有哲思,“春暖花开”的美好光景,“复兴号”的寓意深切,以及“风景如画的晴川”的今昔思绪的勾连,可以在一种思辨中走向情境的深度。
长诗的叙事是一种“点”的闪现方式,是散点透视,而不具有情节连贯的整体性。诗中的人与事的出现是每一个独立“镜头”中具象的“情景”,是一种感性化的抒情方式。这样的叙事涵纳了足够的人生命运的情感内容,是为诗歌情感的表达服务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叙事是诗歌抒情的基础,没有一定量的叙事因素,诗的抒情就很难站稳脚跟,叙事要向抒情提供必要的物质性内容,才能使抒情克止虚浮,进而实现情境和谐的大目标。
抒情诗的抒情,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情感的表达既包含着叙事的因素,也有思辨的因素,甚至是思想的成分加入其间。很多时候,抒情就在叙事的过程之中,抒情与“思”很难分开。诗人把联想不断延长,以足够的事象和思辨因素来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到那时,你们脱下防疫工作服/露出甜美的面容,没有一丝恐惧和疲惫/我们也不用保持一米的距离/不再用眼神示意,不再用眉目传情/坦坦荡荡地,谈及先前那个冗长的噩梦/谈及我们如何肩并肩,众人拾柴”,把当时的艰难与对将来的美好预想融在一处,诗的描述既有现实感又不失应有的厚度。在长诗的结尾处,诗人这样写道:
到那时,我们将那些消了毒的口罩
互相作为礼物,甚至像防疫服那样
写上我们平凡的名字,患难时的泪水
写上真,写上善,写上美,写上
我们生命里大无畏的人格,最纯粹的良知
在心里默念一个大写的名字:武汉!武汉!
或许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诗的纪念!
虽然李皓的诗不是以激情胜出的类型,而我却是在阅读中总是心境难平,武汉早已“春暖花开”了,不知诗人是否成就了人生中再一次的武汉之行。当然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有了诗,诗意和灵魂的抵达已经涵盖了一切。如今,新冠疫情还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蔓延,仍在吞噬众多人的生命,人类真正的春天尚未到来,我们还无法敞开襟怀举杯庆祝。在此刻,记住“我们生命里大无畏的人格,最纯粹的良知”,既为武汉祝福,又为全世界多地的人们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