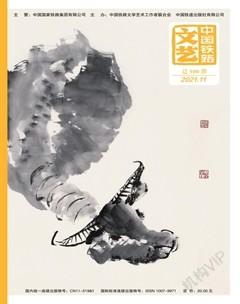罗西亚大街上的那栋老房子
95岁的吕老已经深度昏迷两天了。
吕老曾在开往辽沈战场的火车上做过司炉工,据说当年在火车上撮煤的时候,手上的血水顺着铁锹把子流到煤堆里,大鼻涕合着煤渣吃到嘴里。吕老上过抗美援朝战场,那位在敌机眼皮底下把喀秋莎火箭炮送到前线的火车司机是他的部下。他曾经是铁路局十几万人的老班长。退休三十多年,始终是局里的“镇宅之宝”。
路上堵车,进院等车位,住院处的电梯像公交车一样排队,离退科科长纪涛一边往干部病房走心里一边冒火。
腿酸点儿人累点儿都不是事儿,关键是脑袋里都是事儿。
要及时把吕老的病情汇报给局里有关领导,协调探视时间。要参与医院的治疗方案,听不懂也要在旁边坐着。私下里也要做好准备,开始整理生平事迹。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有点啥风吹草动都不是小事。
局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老战士还有十一二位,都是奔百的年纪。单位对这些国宝级的老人有一项工作内容,那就是一对一结对子关心照顾。在纪涛他们眼里,这些老人都是值得尊重和敬仰的,他们心里生怕有啥想不到的事。
1
吕家大儿子宝刚下了飞机就直接住进了宾馆,这习惯已经有好些年了。
宝刚在这座城市出生,3岁多就跟随父母到省会城市生活了,等到父亲退休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已经是在南方某部队服役十年的少校了。
宝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北方地级城市,传统风格,街道横平竖直。过年回来冰天雪地,就算他这军人体格,出门也是寒风透骨。国庆节回来时穿着短袖,到了家里就冷风嗖嗖的,不得不穿上外套。在部队这些年,他的探亲假总是被各种占用,真正休假回来的次数并不多。父亲好像也并不在意他回来还是不回来,好像这儿子就是给部队养的。从十几岁走出这家门,他和父亲就开始在各自的生活中单独作战,家对于他来说就有了和其他子女不一样的氛围,他对这城市也总是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说起来应该很温暖,实际上很陌生。
宝刚从参军开始,来来回回都是自己背着行李,也没啥接送的大场面。每次离家时,父亲如果在家,一定是在楼下使劲握一下手,挥挥大手看着他大步流星自己去车站。他家离火车站很近,父亲说,干铁路的,听不见火车声心里不踏实,宝刚从小就在火车的轰隆声中入梦。从家往火车站走,从火车站往家走,这条路就像生活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其他人那些离别重逢的感触。
有一次,父亲不在家,宝刚给战友带了很多书,母亲就让父亲的秘书开车送他到站台上,在家门口坐上小轿车的时候,他还觉得挺新鲜挺开心,可是在站台上提着行李下车,车站干部和职工都跑过来以为局长来检查工作,旅客都大包小裹奇怪地看着他时,宝刚一下子懊悔极了,尴尬得脸也红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骂自己实在太不像个军人,真是太给父亲丢脸了。
父亲退休回到这座城市的这些年,他是长子,是军人,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每次回家,吃过饭,不管和家里人喝酒喝到几点,都肯定是回宾馆住的,军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走的时候,老父亲会有点不舍,也还是赞许的。他和父亲,说起来是父子,其实更像老战友。
宝刚最喜欢的就是从家走到宾馆的这段路。
宝刚不熟悉这座城市的街道布局,但在他心中,这座城市只有一条街道,那就是这条罗西亚大街。这条街道尽头那座历经一百二十年风雨的老宅子是他在这座城市的家。无论他多晚回去,也无论多晚离开,那里都为他亮着灯。
这条街道不宽,对向两车道通行,反倒人行道有点不同寻常的开阔。
人行道上长成一排的老榆树,各有风貌各有表情各有悲辛。
这些树好像又长粗了很多,在这些砖头瓦砾之间,这些老榆树长出了自己的风骨,是一棵树该有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这些树被钉上了“古树名木”的铭牌,不觉让人心生敬意,是时光是坚守,是不计较时间空间的宽厚。树身上缠着黄色胶带,上面印着预防树木病虫害的字迹。几个大枝杈都没有发芽的老树,树身上挂着输液的药瓶,有黄色的液体顺着输液管注入枝干里。宝刚知道,这些树枝繁叶茂的背后,有很多人的辛苦付出。
这些年宝刚在罗西亚大街走了多少次,就看了多少次这些树。
宝刚每次见到这些树都觉得好像看到了时光在这里缓慢流淌。
春天的时候,这些树好像唤醒了这条寂寞沉睡的罗西亚大街。夏天的时候,树冠在头上连成茂密的树阴,让人忍不住走慢一点,再慢一点。秋天的时候,满地金黄落叶,罗西亚大街好像穿上了华丽的盛装。冬天的风雪中,罗西亚大街充满异域風情,在某一刻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故事里。
道路的左手边,是一座大学校园,临街几栋楼是老楼,有宿舍楼,也有教室,窗外经常飘着学生们晾晒的衣服,尤其到了晚上,走在路上看着房间里的灯光,挡不住的书香气混在空气中飘在街上。街道右边,夹杂在一些多层楼房中间,就是那些俄式老房子,院门紧闭,神秘又有几分寂寞。这片住宅区隔着一条街就是那座著名的苏军烈士陵园。陵园对面是中东铁路时期的一座火车站,火车站站舍保存着完整的俄罗斯建筑风格,进站天桥是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实木装置。这座火车站已经不再办理旅客列车业务,中欧班列货物列车呼啸着从这里通过,火车会让时的汽笛声清晰悠远地传到这条街上,传到这片老房子里,就像老邻旧居每天不急不缓如期而至的问候。
偶尔有吉他弹奏的歌曲飘荡在街上。
烈士陵园里偶尔也飘着若有若无的深情曲调,仔细辨别,可知是《小路》《喀秋莎》《红莓花儿开》。
罗西亚大街的尽头,就是宝刚家的这栋老房子。
这是中东铁路时期俄罗斯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官邸。1987年父亲退休,从省城火车站前的局长楼带着一大家子人搬回到这个地级城市,住进这栋老房子,大家都不觉感叹:“老房子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两扇墨绿油漆的木板门,好像谁走进去都会不自觉地低头弯腰。事实上,真走到门口,谁也不用弯腰,好像完全能容下两米多的身高,只是那个高高起脊的门斗让人不自觉地生出谦卑一些再谦卑一些的感觉,不知不觉行到近前就弯下了腰,低下了头。
围墙的石头都能看出来纹理,每一块都没有残损。父亲喜欢收拾房子,那些抹灰砌砖的活在他八十岁的时候还做得很轻松。父亲的生活标尺从来不会因为年龄而降低,哪能让这院子破落呢,用父亲的话说,要有过日子的样子,大家庭小家庭都是一样的。院子里的古树把这座三层楼房遮挡在了树阴里。楼房侧面那个小小的洋葱头若隐若现,让这小房子看上去有几分神秘,很多走过的人都曾经以为这里是一处教堂。
院子里小花园已经平整干净,那些过冬时储存在地窖里的花根都已经重新栽种下去了。那几棵老榆树好像枝杈又被修剪了很多,就像刚刚理过发的样子,有点愣。那把木头椅子孤单单地立在那里,旁边的茶桌、脚下的景观石都和这把椅子一样孤单单的。
宝刚抬头张望一下二楼,半圆形的露天平台,墨绿色的雨搭还是那年他回来探亲和父亲一起安装的,给这个小平台平添了几分洋气,也留下了很多父亲在那里看书晒太阳的照片。
进楼的大门早就改成了对开的防盗门,和周围的木格窗户很不搭调。这是当初四弟宝树趁父亲去疗养院疗养的那段时间,自作主张修建的,成为这房子的一大败笔。父亲回来后大发脾气,警告宝树以后不许动这房子一根草棍。好在当时是单独焊接安装在原来房门的外边,并没有破坏楼房的主体大门,不然父亲一定会让他拆掉的。宝树的原意是好的,是出于安全考虑,现在的房子怎么可以没有一扇防盗门呢。
楼下空荡荡的,家门没锁,没有人发现他进来。
他在楼下客厅站了好一会儿,才看到妹妹宝殊从二楼下来。宝殊看到他并没有觉得太意外,好像他一直就住在家里一样。
“哥——”
“爸爸昏迷前有没有什么话留下来?”
“哥,你是说遗嘱吗?”
宝殊这些年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从小就被全家人疼爱,如今年过六十,还是一副文艺女青年的模样,穿着格子衬衫,编着两条干巴巴的辫子,得过风湿病的腿下楼时横着身子一级一级从台阶上挪下来,下到一楼就赶紧坐在椅子上,再拿起羊毛围巾盖在腿上。
有老爷子在,宝殊一直就是个生病的孩子。宝刚知道,老爷子即便留话也未必见得留给宝殊。
“爸一直都挺好,这几天那本《百年史话百年说》就要定稿了,要赶在七一前印刷出版。每天家里都人来人往的,大伙走了,就让他休息,也没顾上和他聊天。”
“单位那边还是纪涛管这儿?”
“是,一直是纪涛,他一周总要过来三五趟,最近他带着摄影师给爸录口述史,爸见的最多的人就是他。那天去医院也多亏他,晚上爸上床时忽然晕倒,他第一个赶来,在门口接的救护车。”
宝刚朝楼上走去。父亲不在家,整栋楼都空荡荡的。脚下的实木楼梯实木地板都已经和这栋房子一样有百年历史了,父亲这些年坚持不对这房子做一丝一毫的改动,除了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基本没有添置任何新式家具。父亲那张老式实木的写字台和那把实木的大圈椅都已经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
宝刚走进父亲的书房,坐在大圈椅上,心里一疼,眼泪就下来了。这么多年,自己好像一直就是父亲的战友,战友之间哪能有撒娇有哭哭啼啼的事呢。
那些年刚参军,回到家,走路时腰板塌一点,父亲都会在身后踹一脚。回部队的时候,母亲买来一大堆红肠、面包让他带走,父亲眼睛一瞪,“整那些玩意儿干啥,去部队又不是去春游。”火车站台上,正在检查工作的父亲看到他背着行李从天桥上走下来,便停下来向他挥手,示意他快点上车,跟在父亲身后的秘书想跑过去帮他拎行李,一看父亲已经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了,秘书扎着手望着父子俩相向而去的背影犹豫着。
那时候父亲很年轻,走路大步流星,说话也是粗门大嗓。那时候自己也很年轻,会怨会恨,只有接到父亲寄来的信时,他才会确信自己是父亲日夜盼望长大的儿子。
“哥,你回来咋不告诉我,我去接你呀。你这么大年纪还坐大巴车,犯得上吗。”
四弟宝树也已年过五十,一米八多的大个子,四方的国字脸,剪的板寸头清清爽爽。看到宝树,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就连说话时那副不拘小节的样子都和父亲一样。
“纪涛来电话,省里医科大学的专家已经到医院了,咱们三个一起去医院吧。”
和宝树一起进来的还有他的两个朋友,俩人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见到宝刚又都有点不那么自然,宝树把两位朋友带到了二楼,俩人嘴里喊着“大哥”,眼神倒是一直往宝树那里瞟,站在楼梯口,看上去好像犹豫着要不要上三楼。
宝刚从书房走出来,和宝树一起下楼,那两个朋友也讪讪地跟着下了楼。
“宝树,你先和朋友去开车,大哥,你等我一会儿,我让张姨给你找件衣服换上。”
宝殊看到宝树已走出院子,又压低了声音说:“这样的朋友一年都来好几伙了,被爸骂出去就又这么偷偷地来。”
“老四这是动啥心思呢,是要卖这房子吗?”
“他一直和爸商量让我和爸搬到他买的电梯房去住,他要把这里开发成民宿。他说,图纸都设计好了,就等爸一句话。”
“这会儿没等来爸这句话,只好等爸闭眼睛了。”
2
这些年,纪涛见到宝刚的机会不多,印象中都不超过三次。在吕老的嘴里宝刚是那个在部队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就送到部队,长得溜直。”相对比的就是老四宝树,吕老的话是:“就这个熊玩意儿从小长在身边,被他妈惯着,长歪了。”
宝刚话不多,和纪涛说话很是客气。这让纪涛觉得很舒服,纪涛是局里指定负责吕老工作的干部,对于这个家庭来說,介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尴尬处境,这分寸不好把握。要是搅和到人家的家事里边,不拿自己当外人还真就错了。
宝刚六十多岁的人了,肩宽背直,面色沉着,白发夹杂着黑发,自有一些沧桑在其中,但掩盖不住军人气质。纪涛紧走几步在住院部门口迎上大踏步走过来的宝刚,俩人表情凝重,深深点头,使劲握手。
病房里,这会儿气氛有点严肃,当地医院已经是第三天抢救了,病情并无起色。医护人员心情沉重。省城来的专家面无表情地看片子、看化验单。
宝树有点不知深浅地拍拍纪涛的肩膀,“涛哥,这我大哥回来了,局长是不是该过来见个面啊。”
“刘院长,咱这医院行不行啊,省城那边不是来人了吗,我爹,那你得救啊。”
宝刚用眼神制止了宝树,用力拥抱了一下宝殊的肩膀,宝殊压抑的哭声令人心碎。十几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宝殊也是这样压抑着哭。那场景好像就在眼前。
每每这样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一定是那个心里最苦的孩子。
宝殊生在1960年,生下来就不像三个儿子那样生龙活虎,五岁时,风雪夜里发高烧,父亲在外地出差,母亲一个人抱着宝殊连滚带爬赶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医院,到底还是耽误了治疗,宝殊全身关节受损。这些年,家里很少提起宝殊的身体,孩子都会生病,在那些平常职工家里,孩子在病痛时能得到父母最好的呵护,可是宝殊他们却没有,这委屈宝殊要用一生去承受。宝殊在铁路局图书馆做些清洁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她是吕老的女儿,上了几年班,也就风没吹雨没淋地办了病退手续,和父亲一起回到了这里这座地级城市。
宝殊当年嫁给了一个到城里打工的木匠,那男人原本以为父亲会给他安排工作,结果吕老不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退休后还告老还了乡,这个男人和宝殊的婚姻也就慢慢散了。好在宝殊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后来那孩子也大学毕业了,宝刚把孩子留在身边并安了家,也算是帮妹妹解决了后顾之忧。
宝殊一个月有不到两千块钱的退休金,这些年在家和父母做伴,生活倒也安稳。孩子们在父亲的起起落落中,世间冷暖一点也不比别人体会得少。
如果父亲走了,妹妹以后怎么生活?
3
纪涛把吕老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向宝刚简要介绍了一下。宝刚知道父亲这些年虽然退休了,还是一直没闲着。父亲每年出现在局里的职代会上,提案、座谈一样不少。除了局里安排的老干部老战士一年两次的疗养,父亲几乎都在家里整理一些历史资料。
“我爸他最近有没有聊到有什么心愿?”
宝刚问这句话的时候,兄妹三个已经和纪涛一起回到了家里,都一天没吃饭了,张姨张罗着给他们煮面条。
宝树又和朋友出去了。他说,一个朋友给他约了一位中医,他准备去会会这位中医,晚上老婆和孩子坐火车回来,他直接去车站接回来。不等大家伙搭话,他已经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怎么也要吃口饭啊,老爷子要是在家,肯定要让我先给你们做饭吃的。”
张姨和宝刚年龄相近,孤身一人,在这家里已经做了快二十年的阿姨。张姨先是照顾生病的母亲,母亲走后就照顾父亲和宝殊的饮食起居,父母亲和孩子们一直把她当亲人,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张姨担起这家里的很多事。父亲做事有原则,大事上从来不糊涂。这些年,纪涛他们也经常劝老人找个老伴一起生活,吕老坚持自己一个人生活,吕老平常忙着做事,倒也没有那么寂寞。吕老一直和纪涛说:“不能给孩子们留下烂摊子。”这些年常来常往,纪涛倒是十分喜欢这位朴实能干善解人意的张姨。
“宝刚啊,你上次回来还是五年前哦。”
张姨一边整理餐桌,一边轻声细语地和宝刚说话,小心谨慎又带点主人的实在劲,很是能看懂家里人的情绪。一碟又一碟的小咸菜是吕老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日常吃饭可以没肉,却不能没有咸菜。张姨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竟十分擅长做咸菜,吕老家一年四季餐桌上都会有几样可口的小咸菜。宝刚见到这些小咸菜又是眼圈一红。
寶刚最喜欢的就是这栋老房子里的这间餐厅。如果说这么多年在外边,宝刚对这个家最大的想念,那就是这间餐厅了。
穿过一楼客厅往里走,厨房和餐厅的门藏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下,和客厅完全是隔开的两个区域,厚重的木头门像一堵墙,门上没有窗户没有玻璃。餐厅中央是一张大餐桌,餐桌面板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而是两端方正,长长的带有弧度的椭圆形。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张餐桌就让人想到好多好多好吃的,尤其是那种大锅大盘的好吃的。
还记得那一年,宝树给宝刚写信,“爸爸不当局长了,我们家要从省城搬到外地了……”宝树那时不知道父亲会把家搬到哪里,大哥透过信纸体会到了小弟心里的不安。
宝刚从部队探亲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的时候,是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亲站在临街的门斗下迎接他。早晨的阳光下,父亲红光满面,白发背向脑后,站在大门口冲着他暖暖地笑,轻松自在的样子,那扇小小的院门打开着,似乎刚好容下父亲一个人,身后,那座错落有致的三层小楼,就那么不卑不亢地立在父亲身后,好像这么多年,这座建筑一直在这里等着父亲,等着父亲人生的航船到达这处码头,他就会停留在这里。
见到父亲和这栋小楼的一瞬间,宝刚就接受了父亲的选择,人生如果一定有一些缘分的话,那人和这些建筑的缘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陪伴一段时光的缘分。
父亲那天舒展爽朗的笑声好像至今还留在这房间里。
那时候自己在部队刚提拔,心里骄傲满满,莫大荣光,没想到回到这座小城市,回到这个家里,站在父亲的面前,自己好像一下子又变成了那个刚参军入伍的小兵。
那座三层高的小楼,在那一瞬间走进了宝刚的生命中。
他喜欢这里。
他仰望这座小楼,就像小时候踮起脚仰望匆匆走远的父亲。
那时候这房子里住着还没有成家的宝树和带着女儿的宝殊,还有爷爷奶奶和姥姥,还有陪着姥姥的二姨,好像这栋小小的楼房里住满了人,每个房间里都有人。
那次回家,宝刚和一家人坐在这个餐厅里,这个椭圆形像个大大的橄榄核一样的大餐桌,饱满,丰盛,妈妈做了两条红烧大鲤鱼,在大桌子的两端各放一条,一盘红肠切成片,一盘红肠撕成块,饺子一盘又一盘,奶奶和姥姥的西葫芦馅,爸爸和爷爷的牛肉馅,妈妈和宝殊的猪肉大葱馅,宝刚和宝树的羊肉馅。对呀,那一次宝瑞也即将出国,从大学里回了家,文质彬彬的宝瑞戴着眼镜,挨个盘子挑着饺子吃。
餐桌的另一边是木头窗子,窗户没啥新鲜的,倒是那个大窗台,几乎就是一张床一样,那是那个年代很多平房都会有的大窗户,只是这里的木头窗框格外粗笨,窗玻璃看起来又厚又重,夜晚望出去,外边是一片漆黑的树林。多年以后,宝刚知道,那片树林后来被修缮一新,是如今的苏军烈士陵园。
走进这座房子,宝刚才想起来,这房里并没有他的房间,原来在省城生活的家里关于他的记忆似乎在这次搬家过程中悄悄抹去了。和他一起在这个家里消失的还有二弟宝瑞,宝瑞已经留校并且申请了国外的大学。用爸的话说:“养个白眼狼”。白眼狼宝瑞后来定居在国外。他和宝瑞并没有享受到父亲当官的福祉,在父亲告老还乡回到这座房子的时候,父亲已经把这两个儿子真正送到“大海”里了,“好男儿四海为家”。
坐在餐桌前,宝刚从窗户望出去,灯光宁静树影婆娑,宝刚觉得三十多年的时光恍然而去。
4
宝树回来的时候,宝刚正准备回宾馆休息。和宝树一起回到家里的还有刚刚从省城赶过来的宝树媳妇和儿子。
“哥,你别出去住了,你就在家住吧。”宝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即便是年过半百,说起来话还是自带一点撒娇的味道。
“让孩子和微微去宾馆住,咱俩在家唠唠。”
宝刚知道宝树有话要说。弟妹微微和侄子说起来是来看爷爷,实际上心里都知道这几乎就是奔丧而来。两个人一直在省城生活,和这个家一向疏远,他们待在家里,晚上真有啥事,难免会害怕,宝刚为俩人着想,也就没有拒绝,留在了家里。
宝树拎着两瓶啤酒拿了两个杯子进了书房。宝刚相信在这间书房里,可能经常出现香烟,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啤酒瓶子。
父亲最喜欢的喝酒场面是在那个大餐桌上正经地喝酒。
兄弟俩差不多是第一次这么正式地坐在这间书房里。谁也没去坐父亲的那把圈椅,而是坐在了那两把单人沙发椅上。说是沙发也是沙发,说是椅子也是椅子,父亲习惯叫椅子,这房间里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那些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
椅子的木头框架是俄罗斯桦木,扶手和椅子腿都透着黑红色的暗光,边沿处的雕花已经磨得圆润,四只椅脚微微屈起,就像四只老虎爪子一样牢牢地抓在地上,乍看上去就像蹲在地上的两只小老虎,偏偏这两只小老虎又是圆乎乎的靠背,框架连接处都是曲线曲面的圆润构架,这两把椅子就那么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笨笨地趴在那里,少了几分威严冷峻,多了几分稚拙古朴。椅子上墨绿色丝绒坐垫还是母亲在世时做的装饰,墨绿色的丝绒早已不见了从前的奢华气质,此时看起来是泛白的暗淡和绒面的粗糙,有那么一两处还有针线细细缝合的痕迹。这些年,这房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和改动。
两把椅子中间是一个木制的单腿独立小茶几,茶几的脚像一个大大的章鱼吸盘,稳稳地吸附在地面上,小茶几俏皮又羞涩地躲在两把椅子中间。茶几桌面上铺着白色的亚麻布,放着一把茶壶四个茶碗,都是从前办公室里的青花瓷带盖的办公用杯子。这房间里的东西,好像都经历了足够多的时日,经历了岁月的包浆,光滑圆润,淡淡的暖暖的。
“大哥——”宝树肯定是喝了酒回来的,心里的情绪也酝酿很久了。
“大哥——”
“大哥,咱爹说他以后还是要回到老家的。”
吕老的老家远在山西,百年之后魂归故土也是他一直念叨的心愿。
“二哥在国外再不会回来了,三姐也得和孩子一起去你那里住,这地方是不是就只剩下我了?”
“你将来也早点回到省城吧。一个家不能总是这么分着。”
“大哥,别人都说我是官二代,你说我算哪门子官二代啊,我刚参加工作老爷子就退休了。我想鼓搗点生意吧,老爷子又觉得我不务正业。”
“这么多年,你是军官,你给这个家光宗耀祖。二哥走向世界了,三姐身体不好,只有我天天在老爷子跟前晃荡,干啥都不对,咋做都瞧我不顺眼。”
“人家退休都在省城好好待着,他非要回到这个小城整个告老还乡,他自己回来不要紧,我和三姐还要和他一起回来,我想把工作调回省城,他又说了不算。微微是独生女,要不是我丈母娘坚决把她留在身边,我儿子现在就是小镇青年。”
宝树眼圈一红,说话就有了鼻音。
“要不是因为他,宝殊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宝树,你怎么越老越不懂事?”宝刚知道宝树心里委屈,知道他有话要说,老父亲在医院躺着,这埋怨的话无论怎么说,也还是这么让人难过。
“大哥,你说,省城的房子现在啥价钱,在这地方这房子有多不值钱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可要提前和你说好,咱兄弟四个,你得支持我,你得主持这事。”
“将来有一天,我准备把咱们这老房子开发起来,反正也卖不上价钱,还不如经营起来,你放心,我不会一个人独占,咱们四个都占股份,我替大家管理,也算咱爸妈留给咱们的念想,也算我没白白跟老爷子待在这小城这些年。”
宝刚喝了两瓶啤酒,坐在那里有点迷糊了,宝树好像一直在说,一直在喝,好像还哭了,好像还提到了好多人,宝刚好像忘了自己怎么回答宝树的,恍惚中抬头看看表,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了。
电话骤然响起来。
5
罗西亚大街更安静了,好像一路都没有车辆来往。宝刚和宝树从街口一直走到家。
推开门斗下的小角门,院子里的几棵树都显得孤零零的,窗下那些花盆里的花都开得茂盛,此刻也是娇艳得悲悲戚戚。抬起头,二楼平台上,父亲经常坐的那把椅子还在,孤单单灰蒙蒙的。楼下客厅空空荡荡,二楼显得那么高,楼梯看起来那么陡,好像走上去都需要点力气,父亲不在了,这栋一百多年的老房子没有了精气神。
宝殊在医院输液。
兄弟俩坐在院子里那把长椅上,院墙周围的绿植都发了芽,春天来得真快。这么多年,每次回来好像都能看到这小院的繁华和暖意。母亲去世了,宝刚在这院子里想念母亲,宝刚心里也还是觉得这个房子是暖的,这个家也还是暖的,甚至想起母亲来也是暖的。如今坐在院子里,六十多岁的宝刚第一次觉得这里这么安静这么空荡这么冷清,宝刚听到了烈士陵园里播放的那些让人落泪的歌曲,那首《小路》,是他最喜欢的,此时听起来好像也是在为父亲送行。宝刚还听到了火车进站出站的汽笛声,长鸣的汽笛是在和父亲告别吗?父亲这辈子真的一直住在能听见火车声音的地方。
心里一酸,这栋小楼这院落这花草树木都浸在了泪水里。
父亲,他始终在坚守着这两根钢轨。
父亲,他始终在坚守一段历史。
宝树到地窖里去取啤酒。
这老房子有一处神秘所在,那就是地窖。
宝刚当年第一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就对这个地窖情有独钟,可能和做军事指挥官的职业有关,他对复杂的地形地势特别留意。
厨房地面铺的都是土灰色地砖,大饭桌下面的地砖和其他地方的地砖并没有啥不一样,整齐拼接没有丝毫缝隙。墙壁上有一处存放消防设备的墙壁柜,里边挂着一个几乎嵌在墙上看不出来做啥用的大吸盘器,是那种沉重的铁器,吸盘器放在饭桌正中间那两块地砖上,几个按钮掰开按下,用力轻轻一提,两块地砖离开地面,一个边界平整、方方正正的地窖口出现在眼前。
地窖的另一处出口就在院子的西南角,那里是一圈低矮的榆树墙,沿着榆树墙一直走,就是缓缓的一直到地下的斜面台阶,给人的感觉,好像此时一个人明明在院子里散步,不知不觉就朝着地下深处走去,然后一点点消失。宝刚经常看军事资料,每次研究军事堡垒时,宝刚就能想起自己家这神秘的地窖。
从房子的里边伸展到院子里,可见这处地窖的宽敞。地窖不但有光感,甚至通风良好,里边是和房子一样的灰色砖石结构,甚至有砌起来的石桌,有高上两级台阶的分区。父亲喜欢的白酒多年来就藏这个地窖里,夏天家里的水果,尤其是大西瓜,從地窖里拿出来后那口味真是不一样呢。宝刚一直想,如果这个地窖出现在他们的少年时代,那他们兄弟的少年时期会多出来多少乐趣啊。
手机响了,是二弟宝瑞。
一声“大哥”刚出口,二弟就已经泣不成声。
“大哥,爹回山西老家的时候,我一定回去。”
“大哥,我很早就和爹说过了,我放弃父母的一切遗产。这么多年,按照中国文化来说,我没有在父母身边尽过孝,我放弃我的继承权。过后我会签一份文件邮给你。”
二弟宝瑞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如今已经是某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对家里这些问题说的很直接很客观。
“宝瑞,还记得咱爸的老房子吗?”
“当然记得,我现在的住房和那栋房子有点像,只是比那个要大一些。”
“宝瑞,爸的这栋房子,咱们考虑建成博物馆怎么样?”
宝树拎着啤酒从地窖里走出来。这两天,他瘦了,人明显憔悴了很多。宝刚的心,又疼了一下。
张姨拿着个档案袋从屋子里走出来。
“宝刚,你们兄弟俩都在这儿,这是你爹去年放在我这里的,告诉我等他百年之后,就把这个交给你们。”
6
这事有点大,纪涛完全没有经验。
以他对吕老的了解,他相信这是吕老真实的心愿。吕老这些年一直在说的一句话是:“做点留下来的事。”
有一次聊到这房子的时候,吕老说:“这房子要好好留下来,这是一段历史。”“咱们早晚都要离开这里,咱们谁也没有啥资格住在这里。”
宝刚按照信里留下的电话,找到了给父亲办理遗嘱的律师,吕老从来就没有糊涂过,那份遗嘱交代了身后的每个细节。
纪涛不知道吕老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惊动了中组部、市文物管理局。
在准备起草相关报告前,纪涛又来到家里,毕竟这是一大笔房产,这房子此时的价值在这座地级市绝对的No.1,没有其二。况且家庭兄妹多人,过的都是普通日子,没有谁会随便舍弃这三五百万的资产。
宝殊刚刚出院,躺在床上静养,宝树又住进了医院。张姨坐在院子里发呆,纪涛走进院子里的时候,张姨冲楼上努努嘴,“两天没下来了。”
宝刚头上的白发明显见多,在这高举架、实木到顶的房间里,穿着黑色T恤的宝刚看起来那么憔悴。
纪涛想起那时候,吕老每天都穿戴整齐地坐在那把大圈椅上等自己,那份沉着淡定的样子好像和这房子浑然天成。恍然间吕老好像在说话,“那些熊玩意儿有啥德行住在这房子里?”
“大哥,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老爷子的遗嘱是留给自家人的,怎么做,决定权还在你们兄弟几个这里。这房子是老爷子当年房改时掏钱买断产权的,这些财产单位没权利介入。局里领导一直关注着老爷子的身后事,家里有什么要求,我会回去协调的。”
“纪涛,我爹信里说的每个字都扎在我的心上,这辈子都抹不去了。”
“我爹说的对,我们兄妹比起他那些老战友老同事的子女何止是幸运,何止是幸福。”
“我爹当年不是为了住进这房子,是为了守住这房子,我们这些子孙要做的也是守住这房子,我们自己做不到,就交给专业的人员去做吧。”
“宝殊和宝树那里你们都不用担心,他们也都是我爹的亲生儿女,总有一天会想开的。”
“大哥——”
宝殊压抑的哭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张姨忙着打热水洗毛巾,出来进去都是孤单单的样子。
“纪涛,如果可能,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张姨找份能过日子的工作吧。”
7
春天来了。
罗西亚大街上,大树的年轮又长了一圈,笔直向上的有那么几棵,歪歪扭扭的也有那么几棵。粗壮的有几棵,枝杈自然枯死的也有几棵。尽管神态各异,却不影响这些树带给这条街的浓阴和景色,树叶都绿了,新枝也在自然生长,罗西亚大街深邃饱满。
工程车停在一处院落前,工人忙着把这处院落围上彩钢挡板,临街处立起了施工项目公示板,“╳╳╳市铁路博物馆”施工期一年,预计明年国庆节开馆。
纪涛这阵子忙得够呛,吕老这处房产作为国家不可移动文物移交给市文物管理局。相关历史资料一并移交,文物管理局经过几轮专家论证,要对这处房产维护修缮,收集整理中东铁路以来的历史文物,作为铁路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张姨帮助纪涛清理完房间里的最后一批物品后,就要去一个纪念馆做保洁员了。市文物管理局了解到张姨的情况后,希望老人家能在博物馆修缮完成并开放后继续回到这里做保洁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也足够张姨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也有局里老领导家庭需要阿姨,生活条件好,收入不错,纪涛征求张姨本人的意见,张姨都谢绝了。“等这房子修好了我还是去收拾这栋房子吧,这里,连砖头都认识我。”
博物馆维护期间,有几个晚上,一辆汽车都会停在公示牌前,有个男人从车上下来,起初蹲在门口,看起来像是喝多了酒,过一会儿靠着大门坐在门斗那里,有时候坐一小会儿,有时候坐到大半夜。院里的保安也许是睡着了,或者醒了也懒得出来,冲着那辆宝马汽车,也没人去招惹那个坐在那里掉眼泪的男人,由他去吧。
时间过得真快。
新落成的博物馆大门还是那个起脊门斗下的小角门,安静地矗立在罗西亚大街上。
雪下得大,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站在博物馆门前,大门左侧立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匾。
院子里已经扫出来一条小道,雪花还在飘落,一切都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场景。
院子里那几棵树在风雪中显得苍劲挺拔。
那把椅子还在守护着这个院子。
张姨身穿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块软布在擦拭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有雪刮进来,有人夹着风雪走进来,张姨向门口张望。
“宝刚,是你吗?”
作者简介:徐亚娟,1970年出生,哈尔滨铁路局高级会计师,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方文学》《黑龙江日报》《生活报》《新青年》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