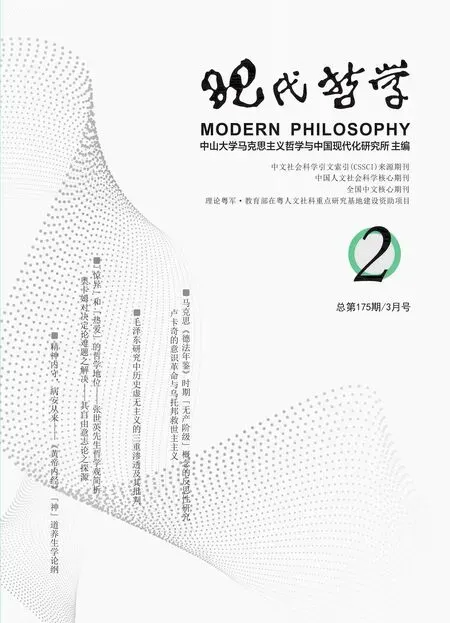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
——索恩-雷特尔经济认识论评析
李永虎
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是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1921-1989年,他数易其稿写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以下简称《脑体劳动》)一书(1)国内目前出版的中译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是根据1989 年德文版翻译的,与1978年出版的英文版相比,在内容上有较大调整,故本文根据需要分开引用。,提出了“纯粹知性的社会起源的命题”(2)[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认为以康德先验哲学为代表的先天认识论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隐蔽的一致性。对此,国内外学者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张一兵评价其“第一次完整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经济学革命中的认识论意蕴”(3)张一兵:《发现索恩-雷特尔》,《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那么,索恩-雷特尔的发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批判性地认识他的这种发现呢?
一、知识论的政治经济学起源
总体来看,索恩-雷特尔的认识论研究旨趣在于揭示知识论的政治经济学起源问题。那么,他为何会对此问题产生兴趣?在笔者看来答案有二:
其一,在20世纪20年代,索恩-雷特尔遇到一个令其讶异、亟待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所有被意识到的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应被理解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辩证发展着的;但另一方面,在现存的知识理论中,脑力劳动的自然科学概念形式却有着“永恒的”真理性质,“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概念形式突出了内容的非历史性。在这些知识理论中,这种非历史性被作为既定的基础接受下来”(4)[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6页。。简言之,索恩-雷特尔观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这样一个“裂隙”:虽然社会现象被看作是辩证的、唯物的,但在先验哲学、自然科学领域,唯物主义却让渡于有着客观、普遍真理形式的唯心主义信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分裂为两种相互矛盾的真理观的危险。在索恩-雷特尔看来,造成此种危险的源头在于“康德是因为没有将对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分析进一步导向对现实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分析;马克思则相反,他是因为没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自然科学的批判上去”(5)同上,第57页。。由此,在两位思想家之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遗留下了如此这般的“鸿沟”,索恩-雷特尔就此以填补这个“裂隙”为其研究使命。
其二,对于索恩-雷特尔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矛盾的发现还关涉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问题——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人的意识并非历史唯物主义所能完全把握,还存在着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绝对“客观”“纯粹”的真理形式,那么科学技术知识已然超越了历史和社会的限度。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为某种技术统治而奋斗:“如今,谈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甚至是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但却不知道科学与科学技术如何适应历史、科学源自何方、它的概念形式的本性与起源是什么,因而不知道社会应当如何控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为科学所控制与制服的人,是会被指责为荒谬的。”(6)同上,第6页。
作为一名“深入解释商品形式的普遍延伸的理论家”(7)[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光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页。(齐泽克语),索恩-雷特尔认为破解“永恒”真理概念形式之谜的钥匙就在马克思那里,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一种(社会)形式的观点,正是“这个观点将它与所有其他思维方式区分开来”(8)[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7页。,特别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石的商品形式分析,已“说明了康德式超验主体的骨架,即构成了‘客观’的科学知识的先验框架”(9)[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0页。。
具体而言,在《脑力劳动》中,索恩-雷特尔通过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以揭示知识论的政治经济学起源:在社会综合的形式要素和思维的形式要素之间有着秘密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既“指示出一种单纯的类比关系,也能指示出一种奠基性关联(Begründungszusammenhang)”(10)[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23页。。换言之,纯粹的知性概念(如康德的先验主体的预设、科学定律的结构、数学公设等)在逻辑和历史上都受到同时代的社会综合——社会形成的一个连贯整体的关系网络——基本构成的制约;反之,一个时代的概念思维形式即那些符合该时代社会综合的思维形式。这一论断无疑与历史唯物主义“生活决定意识”的原理是相契合的。而从索恩-雷特尔的具体构境来看,他又将对此种同一性的考察转入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领域,并将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发生学的秘密锚定在对“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上。
二、现实抽象与交换抽象
自1972年从英国返回德国后至去世的20年间,是索恩-雷特尔厚积薄发的创作高峰期。此间他发表作品有《唯物主义的认识批判与劳动的社会化》(1971)、《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柏林草案”)》(1978)、《认识的社会学理论(卢塞恩草案)》(1985)、《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扩展、修订版)》(1989)等二十余部,贯穿于这些著述并处于其认识论批判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现实抽象”。齐美尔虽然在其《货币哲学》中提到过此概念,但索恩-雷特尔认为这个概念的真正源头还属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社会制度。为了恰当地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做的工作,索恩-雷特尔认为必须将这种抽象判定为一种“现实抽象”,而从其论述来看,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
其一,现实抽象不同于思维抽象。例如,形而上学的“本体”概念和经济学的商品“价值”概念表面上看都属思维抽象,但“本体”抽象与“价值”抽象完全分属两个异质的层面:前者是纯粹的思维抽象,而后者确属“现实抽象”——“价值”本身源于人类现实的劳动并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抽象范畴。在索恩-雷特尔看来,马克思与传统形而上学、先验哲学所谈论的抽象有着明显的“断裂”: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抽象是思维活动的专属,在思维抽象之外来谈论抽象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实抽象”虽具有思维的形式但本身不是思想,而是一种时空中的现实,“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简言之,马克思通过揭示思维抽象形成的社会客观根源,强调了“现实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意识只能是以作为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为条件,现实抽象就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本身。
其二,现实抽象就是交换抽象。秉持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索恩-雷特尔在对“交换的现象学”描述中,把马克思所区分的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应到人的活动中,又区分出“使用行为”和“交换行为”,并进一步指认现实抽象并非源自人的意识,而是由交换者之间发生的交换行为所产生。“由于行为的抽象性以及与之伴随的意识的非抽象性都具有必然性,所以交换者不会察觉其行为的抽象性……人相对于他的交换行为抽象性的无意识性(Bewuβtlosigkeit),既不是这种抽象性的根据,也不是它的条件。”(12)[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15页。交换行为与使用行为相比,其显著差异在于前者具有一种“物性的格式塔”特征:交换行为不涉及任何自然的东西,它纯粹就是社会化本身,“是一种自然在其中停息下来的交往形式,因而是一种绝不掺杂人类之外的东西的交往形式”(13)同上,第35页。。在此基础上,索恩-雷特尔抛出了《脑体劳动》一书的另一核心论点:只是商品交换赋予社会综合以统一性,“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Austauschbarkeitsform),是社会综合的第一基本条件”(14)同上,第32页。。在他看来,在以商品交换实现的社会综合形式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生产,生产劳动并没有发挥构成性作用,起作用的只是交换抽象,“要谈论社会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综合,我们就必须谈论交换,而不是使用”(15)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trans. by Martin Sohn-Rethe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8, p.29.。简言之,对索恩-雷特尔来说,现实抽象因市场的功能纽带而与商品交换行为是完全关联着的。
索恩-雷特尔虽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把他的认识论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失的一环来看待。但在我们看来,在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过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却有着某种原则性的“背离”,因为当他将交换作为抽象的源泉时,从逻辑上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劳动”概念的。用他的话来说,马克思虽然发现了现实抽象的真理,但却用“错误的术语”来解释它,“抽象社会劳动的概念,就其在商品分析中所能识别的范围而言,是黑格尔遗产遗留下来的一种恋物癖的概念”(16)Ibid., p.70.。由此,索恩-雷特尔拒绝承认抽象劳动是构成商品价值与交换抽象的基础。他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生产仅仅是面向自然的一种前社会性的新陈代谢,在此阶段,劳动只表现为具体劳动,并没有抽象化,只是到了交换领域后,社会化的交换关系使劳动变得抽象化,才形成商品价值。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因耗费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凝结形成的商品价值,在索恩-雷特尔这里反倒是因交换关系的追溯才形成,从而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交换价值论”。
在我们看来,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背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一,马克思明确指出,交换关系本身不会使劳动抽象化,也不赋予商品以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为例指出:“交换运动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独特的价值形式。”(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4页。在商品的售卖阶段(W-G),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货币,只是它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表现。交换既没有形成价值,也没有让商品产生增殖现象,因为这一环节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次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价值的形成及其增殖的秘密只能在第一次流通过程(G-W)中,在对劳动力商品的购买环节处去寻找。
其二,马克思超出索恩-雷特尔之处,恰恰在于他洞察到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还未展开时就已被异化、抽象化了,商品的价值只能是抽象劳动的结果。“他的劳动还在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异化,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并入了资本,所以很清楚,他的劳动在过程中只能实现在迅速离开他的产品中。”(18)同上,第605页。索恩-雷特尔显然没有看到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体两面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不仅是工人使用价值的体现,而且是商品价值的本质。简言之,他没有看到交换行为中的抽象不过是生产中“已经实现了的抽象”(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在这种抽象中,劳动作为一种物质过程是具体的,但对处于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形式中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再是具体的了。
其三,当索恩-雷特尔以交换关系取代抽象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时,会得出一个荒谬的推论:商品的等价交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等需交换”。对这种“价值-需要”说,马克思在例举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实质理解的偏差时就已指出其谬误所在。亚里士多德看到,屋和床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的等比例交换必须要以某种共同的质,才能以可通约的量发生关系。不过,对于这种共同的质是什么,亚氏的回答是:“这一种东西实际上就是需要,就是它把所有东西联系在一起了。”(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马克思则指出,对床和屋而言的一种等同的东西是人类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早已预设了抽象价值的存在。而索恩-雷特尔以“交换反溯生产”导出的只能是一种价值的心理主义解释:如果没有交换者主观的均等需要,就不存在等价交换。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滑向资产阶级边际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距甚远。
三、现实抽象与现代科学、形而上学观念的诞生
尽管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索恩-雷特尔给出的答案,但它清晰地表达了现实抽象整个理论问题的显著优点,即商品交换中所包含的抽象决定了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概念思维形式。具体而言,索恩-雷特尔对脑体劳动的分离,与对现代科学、形而上学观念形式之间存在的“体系性关联”的揭秘,是从对交换抽象的形式分析入手的。围绕“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索恩-雷特尔提出了若干种对知性范畴影响至深的交换抽象表现形式,如“实践的唯我论”(praktischer Solipsisimus)“可交换形式”“抽象的量”“实体与偶性”“原子性”“严格的因果性”等。他对交换抽象形式特征的分析可被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无意识性。商品交易者出于自身利益之故,在双方所有物领域遵循私人对立的原则:我的,因而不是你的;你的,因而不是我的。这种实践唯我论的交换关系直接形塑了一种对个体生活宰制性的心理机制,即人们认为唯我论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在深层次上他们其实只是服从了交换关系的铁律。这是因为在以私人财产关系为交换基础的实践中,现代主体性已分化为有意识的人和无意识的行为:他们的意识被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占据,而其正在交换抽象价值的行为却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交换行为是社会行为,然而,行为者的意识却是私人的,并且辨别不出其行为的社会—综合特征。”(21)[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47页。
第二,非物质性。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占有与让渡活动中,一方面他们虚构了商品体不应当发生任何物理变化,因而预设了商品绝对的物质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发生交换,在于交换结束后能够使用商品,因而商品又作为使用客体的质与自身明显连接着。由此,商品产生的经济学价值概念的特点是“非物质实体性”,而其作为物质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属性则构成了偶性。换言之,商品在生产、消费领域中是物质的,但在交换领域只作为纯粹的价值而存在,并以一种无质的实体性与同样抽象的货币相交换。
第三,可交换性。在“y量商品b=x量商品a”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中,交换等式以一种完全脱离经验主义的方式预设了一种统一性——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其均等化的要求刨除了所有商品的感性的质,“同商品体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中连一个物质原子也没有”(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38页。。换言之,两种商品因交换而平等,而不是因它们有任何质的平等而被交换。这种可交换性抽象形式特征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理解:与过去只能说出物的价值,而不能说出脱离物质基础的价值的“生产社会”不同,人类自进入“居有社会”后(23)索恩-雷塞尔认为,人类历史演化可区分为“生产社会”和“居有社会”。“生产社会”是原始共同体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其特征是社会综合的形式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决定,社会的基本结构直接来自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劳动过程,人们以生产者的身份创造自己的社会。“居有社会”以社会非劳动成员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为基础。这种占有又可分为:单方面的由一个已设立的当局(通过税赋或纯粹劫掠等)占有在“直接领主和奴役”形式下产生的盈余;以私人交换和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互惠的占有。(See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pp. 83-84.),由于交换对象在交易过程中被假定是不可变的,从而空置了其时空的物质内容,时间和空间不再与特定的事件、现象有关,转而变成抽象的、连续的、均匀的、可以使用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范畴来处理的时空。
索恩-雷特尔对交换形式要素的解析,为所有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的抽象概念推理特征提供了一个母体,其显著意义在于揭示了合乎知性思维形式的普遍范畴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在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现实抽象中,也就是在第二自然中,一种不能轻易被辨识出起源标记的现实抽象传递给了个体思维,后者则将其转化为了普遍的、非经验的概念。带着这样的判断,索恩-雷特尔在《脑体劳动》一书的第二部分“社会综合与生产”中,对概念思维怎样伴随商品形式的演化而逐渐成熟的历史做了一番追溯:大约在公元前6、7世纪,建立在使用铁器基础上的希腊城邦发展出繁荣的工商业经济,私有财产和交换的增加导致产品变成商品,并创造了一种以货币经济和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综合。而在爱奥尼亚出现的第一枚钱币,意味着一般的现实抽象开始进入到人的头脑之中,因为货币是“纯粹抽象的非物质性”,它的意义只有人(而不是动物)、只有在作为人的相互关系的框架内才能被理解。货币在人类思维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为商业中的现实抽象找到适当概念的是巴门尼德,因为他提出了本体论上的存在概念,认为宇宙中真实的东西不是感官现象,而是“一”(Eine),它是完满的、充满了时空的,是不可改变的、不可分割的、静止不动的,不会消逝也不会产生。巴门尼德超越有形物的存在,显然是“对此处所证实的货币的物质本性的片面化和本体论上的绝对化”(24)[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52页。。此后,概念思维的历史起源以其完全发展的形式被翻译成脱离人的体力活动的纯粹知性概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交换的形式元素,如抽象的时空、抽象的物质、抽象的量、抽象的运动等非经验形式的运用。脑力劳动反过来又把这种知性概念应用于外在的实在——自然和社会,由此形成具有现代科学外观的各门知识。
索恩-雷特尔以“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为例,指出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一直存在着隐蔽的同源性(Stammverwandtschaft)。伽利略的惯性运动原理表明,只要物体不受外力的影响,它就保持运动状态。而得出该见解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有可能将一个物体与其物理环境隔离,伽利略才能将运动理解为与静止并列的存在状态,由此二者在同等程度上才可被视为是惯性的。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惯性运动原理背后的“原理”是:惯性运动起源于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所包含的运动模式。这种运动具有市场商品运动的时空现实性,因而也是货币和资本流通的现实。该模式是绝对抽象的,在不带有任何可感性质的意义上,它通过抽象的、连续的、均匀的空间和时间,使抽象的物质不受任何物质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运动只能通过数学处理。尽管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不断发生着这样的运动,但我们的私人头脑却无法察觉到——在它进入人的头脑中时,它已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形式,而其来源已不再能被辨识。
最终,索恩-雷特尔得出结论说,把精确科学的历史及其逻辑起源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能的。因为任何时代的社会必要的认知形式,除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综合“功能构序”(funktionale Ordnung)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正如他在1937年写给本雅明的《对先天论的批判性清算:一项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文所述,“人们只需要为了货币的一致的统一,为这个描述添加上‘自我意识的统一’,为服务于交换社会的货币综合功能添加上‘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进行的商品交换添加上‘物按照法则的定在’,即‘自然’”(25)[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132页。,就可以从对资本主义物化的分析中推导出康德的先天认识论及其内在的必然矛盾,从而使康德、黑格尔的全部形而上学得到唯物主义的彻底阐明。
四、关于索恩-雷特尔“经济认识论”的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7页。对待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成果,我们也应秉持这样的批判性评介态度。在总体上,其理论探索可被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哲学、抽象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围绕此问题,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其一,取法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开启唯物主义认识论新视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在索恩-雷特尔那里,体现为他力图论证“自然科学与先天认识形式有其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这样一个命题。当代法国哲学家贾普(Anselm Jappe)曾评价索恩-雷特尔“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因为他恢复了马克思理论最有价值和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和商品逻辑的分析。”(28)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 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21(1), 2013, pp.3-14.得益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方法论的启发,索恩-雷特尔没有简单地从传统二元论的“符合论”角度,即从物质世界或外在自然来推导认识概念,而是将本体论、认识论、经济学融为一炉,独辟蹊径地发展出一种“商品与知识本体统一”的经济认识论,从而极大深化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知识论表现,并有力诠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个人受到抽象统治”的深刻洞见。
其二,紧扣“现实抽象”概念破解自然科学虚假的“永恒性”逻辑。自然科学以发现自然规律为己任,并不断生产着具有“永恒”真理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一方面成为我们称手的工具,大大扩展了人类行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以普遍抽象的和无意识的形式建构起“第二自然”,由此决定了我们所能见的和不可见的。索恩-雷特尔则以对“现实抽象”概念的全力阐释,证明了支撑科学范畴“永恒性”逻辑的并不是唯心主义者所宣称的“先天的理念”,而只是人类生产和交换中存在的现实抽象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脑力劳动拜物教的经典表现。“科学的逻辑正是从这种抽象中,而不是从任何绝对的根源和天然的‘智识’圣水器中,衍生出它的永恒的性质。换句话说,永恒的逻辑是有时间性的。”(29)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pp. 200-201.如果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及必然灭亡的规律,那么索恩-雷特尔则从认识论角度揭示了资产阶级思维范畴的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曾用“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来说明货币是历史的、社会的范畴,仿此,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索恩-雷特尔的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形而上学,但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资本主义”(30)Alberto Toscano, “Materialism without Matter: Abstraction, Absence and Social Form”, Textual Practice, Vol.28(7), 2014, pp.1221-1240.。
其三,对认识论问题的追问实则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在今天受到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其认识论所富有的政治解放的意义——他对客观科学知识何以是有效的追问,表面上看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在深层次上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追问。因其通过探寻科学范畴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愈发展愈加失去其发展的合理性——在不断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释放出连其自身都越来越无法控制的破坏自然、加剧劳动异化的力量。对此,索恩-雷特尔提出这种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科学主义最终应通过“劳动的完全社会化”来克服,也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者将通过社会化的劳动、通过控制生产技术的合理应用以确保社会和自然的分离不再是必要的。“人民在社会实践中的物质实践要求把科学发现纳入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之中。研究结果将不再是脱节的;相反,它们将始终结合在一起……因此,人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面临着选择,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许实现社会实践和理论的理性,要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两者皆失。”(31)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p.184.
当然,索恩-雷特尔的理论短板也是显见的:他因迷恋于对商品交换领域的感性直观,在将现实抽象等同于交换抽象从而误判其真正来源时,实则暴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一些重大偏差:真正显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不再是劳动关系,而变成交换和占有关系;不是生产决定着交换的性质和方式,相反是市场的逻辑决定着生产,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实践的本体论地位就此被反转为交换关系本体论。在根本上,索恩-雷特尔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是同一的:一方面,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劳动之所以变得抽象化又是以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和雇佣劳动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交换行为中的抽象仅仅是对生产中已实现了的抽象的完成。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并互为条件,但索恩-雷特尔却将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截然分隔,反倒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最后,他还一再强调抽象范畴本质上只是对经济领域中现实抽象的反映,从而忽略了文化智识生产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有学者称其方法论“终究是一种经济的还原主义和决定论”(32)[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交往批判理论》,王锦刚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