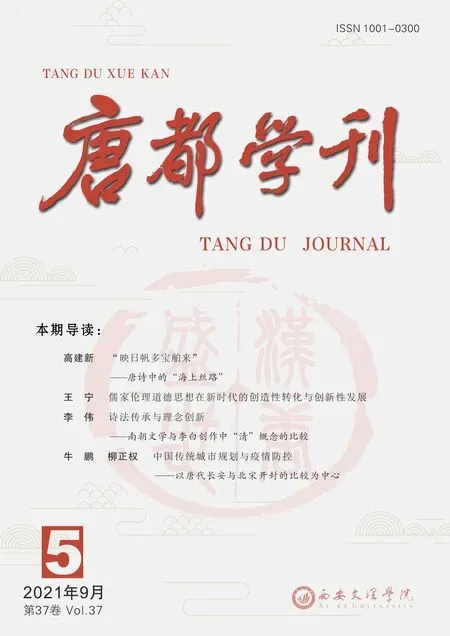唐代碑志中的盛世图景和书写策略
徐海容
(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东莞 523808 )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中国历史进入了千年一遇的盛世时代。结合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等人的作品看,唐代碑志文从一开始就充盈着对大一统政权的认可与颂扬,对太平盛世的期待与赞美,而在以大手笔著称的张说、苏颋的碑志作品中,这种盛世感知和礼赞更为明显。可以说,初盛唐碑志创作围绕着盛世建设而展开。那么,碑志又是如何描写盛世的、其讴歌盛世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本文就此出发,针对上述问题粗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盛世图景的出现
太平盛世是一个美好的历史图景,是古往今来人们的孜孜追求。《礼记·礼运》描述人类理想的小康社会:“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1]后世赞誉的盛世景象,也是关于时政清明、国泰民安、社会繁荣和乐的描述,如《后汉书·崔骃传》:“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2]《魏书·高闾传》:“今天下开泰,四方无虞,岂宜盛世,干戈妄动。”[3]以此为准,中国历史上商周时代的武丁、成康之治,两汉的文景、明章之治,都可谓盛世。但此后三国鼎立、两晋轮回、南北朝对峙,战祸频仍,民不聊生,乱世持续近四百年。殆至隋唐,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天下一统,拨乱反正,恢复盛世之治,成为时势的必然,成为人民的呼唤。因隋朝运祚较短,故这一任务是由唐人完成的。《贞观政要》载李世民即位之初就开始思考如何保障大一统政权的稳固性和合法性,以“永固鸿业”,使帝唐比肩“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4]294。这种思想在贞观群臣所撰《晋书》《梁书》等史籍中多有表露,如魏徵《群书治要序》就希望唐太宗“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5]1431。而此刻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建设,也激发着人们对于盛世的追求。“宪章前王,规矩先圣,崇至公于海内,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乂安,两仪交泰,功成化洽,礼盛乐和。”[5]151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杨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并序》等,都抒写唐王朝恢弘儒学、倡扬孔孟之道的文治教化政策,充满对盛世的展望。王勃《益州夫子庙碑》:“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5]1859李百药《夔州都督黄君汉碑铭并序》:“大唐乘乾御历,奄宅区夏”[5]10514,都赞颂帝唐应天受命,百废待兴。可见支持和维护唐代大一统政权的繁荣前进,迎接太平盛世的到来,成为时代需求和历史期待。而随着帝唐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期待更为迫切。
从初唐起,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最终出现良好的发展局面:“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此皆古昔未有也。”[4]15而“开元天宝中,……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5]3860。由此可见,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大唐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有序,人民生活富裕安康,整体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足可比肩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然而,这一切只是表象,真正的盛世是否到来,还要看维系和建设这一盛世的政治体制本身是否先进。
从中国传统政治体系来说,唐朝的建立意味着皇权专制再次成为大一统政治的建构核心,初唐君臣采取一系列以变法革新为核心的措施,使得这种大一统体制走向完善。首先,在中央层面改进三省六部制,设政事堂,互相监督制衡,提高政治效率。西方直到17世纪才兴起的三权分立学说,唐代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说明贞观王朝政治体制的先进及文明程度之高。其次,大力振兴纲纪,废除冗官弊政,又行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常平仓制等新政;值得一提的是,初唐革新魏晋以来的人事机制,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以科举制代门阀制,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此外,在处理对外交往及民族关系上,又持开明开放的态度。唐太宗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强调“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7]这种治国方略一直延续到玄宗开元年间,从政事堂制到中书门下制,从均田制到检田括户制,从府兵制到募兵制,这种不断与时俱进、日久弥新的先进体制,保障了帝唐社会盛世建设的坚持不懈。其间尽管经历了宫廷政变、权力斗争甚至冲突厮杀等波折,但革故鼎新、求实致用的基本建制始终未变,而且很快能医治好创伤,走上良性发展的大道。郑綮《开天传信记》载玄宗“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四方丰稔,百姓殷富”[8]。此时的唐代比肩乃至超越秦汉,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文化上,都居于世界最前列,达到中国历史的真正盛世,这是与诸如汉武、建隆、康乾等盛世所不同的地方[注]参见拙著《唐代碑志文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30页。。
二、盛世建设促进碑志创作的发展
刘熙《释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于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9]虽为应用文体,但相比于制诰、诏敕等,碑志以记述人类生死哀葬为本,与王权政治联系不甚紧密。但初唐以来,人们的盛世感受日益强烈,碑志的创作思想随之变化,如房玄龄《立碑议》呼吁唐太宗“刻颂立碑,显扬功业”[5]1386。其后张九龄在《请东北将吏刊石纪功德状》亦请“刊石勒颂,以纪功德”[5]2929,这种对于碑志功能的新思考体现着唐人的历史期许和时代认知,最终导致相关碑志制度的完善。《唐律疏议》:“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茔域之内,亦有石兽。”[10]唐代还明文规定禁止毁坏碑刻:“诸毁人碑碣石兽者,徒一年,即毁人庙主者,加一等。其有用功修造之物,而故损毁者,计庸坐赃论。”[11]对于碑志的书写,也明确到专人专职。《大唐六典》:“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12]将碑志看作时代建设的有力工具,并从法律层面予以保障,这就导致唐代碑志创作的兴盛,以致“勋庸道德之家,兼树碑于道”[13]。唐代碑志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说教、颂美及宣导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都配合帝唐的盛世建设。
说教型碑志主要产生于唐太宗贞观时期,像虞世南、于志宁、魏徵、褚亮、李百药等宫廷文士,围绕太宗的各项国策,写下不少说教性碑志。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大唐运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哉景命”[5]845。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我高祖乘时抚运,……元冠紫绶,贲帛嘉于琳琅;裂土剖符,宠命属于翘楚”[5]878。虞世南、李百药、魏徵等都是横跨两个时代的文人,入赘帝唐后,虽多此类应制奉诏之作,但境界开阔,思想明朗,与羁泊隋唐鼎革之际的虚糜文风明显不同。这种感怀人生意气、讴歌王政建设的碑志,充满着对于时政的阐释,对于前景的预见,虽多政治说教,也不乏虚美的套路,但透露出对盛世到来的展望,反映了当时政治开明、言路通畅、君臣齐心协力建设盛世的决心,这对有唐一代的文人精神影响深远。供职于朝堂中的学士如此写作,来自民间的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也心领神会,欣然动笔。王勃《益州夫子庙碑》描述唐王朝君权神授、王道政治:“国家袭宇宙之淳精,据明灵之宝位……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5]1861。其余如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杨炯《梓州惠义寺重阁铭并序》等,也都反映了这种决心和信心。至于陈子昂,在《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一文中感叹:“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5]2187,张扬盛世到来的气势如虹、势不可挡,将这种说教表现得更为明显。
颂美型碑志是随之出现的,在唐太宗贞观后期及武周革命时期日趋活跃。太宗、高宗、武后及玄宗都是好大喜功的,碑志“追述君父之功美”的传统功能,迎合帝王好被颂扬的心理,也受到广大士人的拥护和追捧,最常见的一类是把“尧舜汤武”“圣贤功德”等字眼嵌入碑志中,“纳苍生于仁寿,致君道于尧舜”[5]845。李峤《洛州昭觉寺释迦摩尼佛金铜瑞像碑》、崔融《嵩山启母庙碑》均应时制景,颂扬王政、润色鸿业,以“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欢娱,击壤尧年,识太平之歌咏”[14]的歌唱,夸耀武后的功德。上官仪、许敬宗的些许碑志,也体现出此类风格。当然,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的碑文也不乏颂美倾向,然而其文章中开阔的气象、高远的境界和宏大的感情正由此而来,其借颂美而传达出锐意进取、投身仕途的理念。开元时期,“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15],张说、苏颋等公然要求碑志“润色王道,发挥圣门”[16]1196,这就说明其所追求的是宫廷颂声的回归,其主张与初唐上官仪、许敬宗所追求的宫体张扬美饰的文风相呼应,这就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铭功颂美成为碑志创作的趋向。当然,颂美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凝聚人心,提高政治参与度,为创建帝唐盛世服务。
宣导型碑志几乎与颂美型碑志同时出场。从中宗到玄宗前期,特别是中间上官婉儿干预时政,“称量天下”之文,这就促使文人在构思方面下功夫,突破武后时期碑志以堆砌辞藻和骈俪对偶为能的浮夸套路,由单纯颂美转向政治宣导,以便文学更好地为时政服务,这在玄宗时集贤院学士群体的碑志中表现明显。如张说在碑志文张扬“圣皇在上,于昭于天。唐虽旧邦,其命维新”[16]950,宣称“致君尧舜,何代无人?”[16]742要求碑志文写作“济时适用”,倡导“事君效命之谓忠,杀敌荣亲之谓勇”[16]840的奋斗精神。这一时期碑志作家如苏颋、贺知章、徐浩、韦述等人都是此写法,通过典型人物的宣传,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指导士人参与帝唐盛世建设大业,张扬气势,蓬勃情感。如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
君臣同德,天地通气,以康九有,以遂万类。惟皇御极二十载,光格四表……故扬仄陋兼乎十等,选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观材,积时以观行。[17]
文辞骈散结合,论事明理,情感昂扬,气势蓬勃,在激发士人的时代认知方面多有开拓。
在盛世建设的大背景下,初盛唐碑志创作的无论说教、颂美、还是宣导,都体现出相互配合、三位一体的特点,这与文人的历史体认及现实感受相关。与周秦两汉君权继承的平稳有序不同,唐代自建立起,从玄武门之变的兄弟残杀,到武后、韦氏、太平公主至玄宗上台,政权交替始终伴随着冲突厮杀、宫廷暴力等非平稳因素,自然,一个充满着阴谋变数、诡谲争斗的政权也难以获得人民的拥护,这是不利于盛世建设的。所以伴随着李唐王朝的日益巩固发展,自然要对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加强美饰,追求“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16]1318的盛世之治,这就涉及文化领域的建设。当然,盛世建设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在探索与坎坷中前进,如此更需振奋士心,更需持续不断地对帝政建设作多方面的礼饰和解读,以规整和统一士人的思想行为,促进盛世之治,这就促成了碑志创作强烈的说教、颂美和宣导精神。连游离于庙堂之外的李白对此也心知肚明,其《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高唱“文明鸿业,受之元良,与天同休,相统亿祀。则我唐至公而无私,越三圣而殊轨。腾万人之喜气,烂八极之祥云……噫大块之气,歌炎汉之风……至矣哉!其雄图景命,有如此者”[18],足见其心。
三、碑志中的盛世书写技巧
盛世的标准首先表现为政治体制的先进和稳定。从初唐到盛唐,碑志文在描述帝唐政权时,多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依据,附会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歌颂这一体制的稳定,文馆学士及初唐四杰、陈子昂的碑文,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房琯《龙兴寺碑序》宣扬“此宇宙我高祖创集之,我列祖润色之,则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兴之”[5]3369,而写到君主,这一时期的碑志亦多以神武、英明、圣主等词形容,“盛唐篡历,天下文明……神皇临驭区宇”[19]7,“神皇玉册受天,金坛拜洛,顿纲而鹤书下,辟门而群龙至”[16]908“有唐神龙元年龙集丁巳,应天神龙皇帝出乎震御乎乾也。粤若我高祖拨乱反正,受天明命;太宗震远怀荒,立人纪纲;高宗见天之则,爱人之力:故我祖宗之耿光,天人之交际矣。”[5]2598都从天神地圣君亲的传统角度,颂扬唐王朝的君权神授、有序继承,肯定帝皇的盛世建设。当然,初唐碑志对盛世只是一种期待,一种希望,而具体的盛世标准是什么?文人在碑志中并未有明确表达,也只是充满例行的宣传天人感应、皇权神圣的模糊描写。至玄宗开元时期,唐代在各个方面达到强盛, “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 ‘康哉’之颂,溢于八纮。……年逾三纪,可谓太平。”[20]236文人借助碑志,全面展示盛世场景。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通过马政之繁荣颂扬帝唐建设:“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16]622,文中用了大段篇幅描写原野壮美、万马奔腾的景色,字里行间透露出昂扬刚健的盛世豪情。再如李邕《兖州曲阜县孔子庙碑并序》:“我国家儒教浃宇,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礼官而崇祀”[20]2666,从具体的文治教化方面展示盛世之景。盛世描写因而由抽象变为具象,由模糊变得清晰。
仅仅表现政治的平稳有序,经济发展的繁荣发达,展现帝唐的盛世风貌,这还不够。盛世碑志是盛世文化的写照,而唐代之所以达到盛世,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体制在稳定中又不断革新,充满宏大开明的气度。从初唐时代起,碑志就着力表现这些内容。李邕《郑州大云寺碑》、戴璇《大唐圣祖元元皇帝灵应碑》展现唐代建国以来帝皇励精图治、革新进取的场面。张说的碑文更注重从臣子的作为展现帝唐改革开放得力、国家繁荣富强的一面,如《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姚崇神道)碑(铭并序)》写姚崇“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公执国之钧,金玉王度,大浑顺序,休征来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逊”[16]743,《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写宋璟施政有为:“楝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国之舶车,海琛云萃,物无二价,路有遗金,殊裔胥易其回途,远人咸内我边郡。”[16]640其余如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李华《杭州开元寺新塔碑》、颜真卿《和政公主神道碑》及李邕《国清寺碑并序》《大相国寺碑》《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等,都有此类描写,抒发文人“遇非常之时,决希代之策”[16]1355的豪情。而褚亮《左屯卫大将军周孝范碑铭并序》写墓主“出使北藩。宣杨(扬)国威,晓谕边俗,班奉四条之书,肃清万里之外。”[5]10527陈子昂《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写墓主“奉天子威令,以喻越人,越人来苏,日有千计。”[5]2179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等,都从外交方面显示唐代综合国力的强大,彰显帝唐以战促和,怀柔绥靖、万邦来贺、四夷咸服的威仪和开明开放的盛世风度。
清代唐甄《潜书·用贤》云:“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21]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强大都是外在的表现,盛世的根本标准在于人的发展与成才,在于人生理想价值的实现。几乎每一位初盛唐文人,都在碑志文中表现了盛世多才、人生当有为的襟抱与气概。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姚崇神道)碑(铭并序)》宣称:“知人则哲,非贤罔乂,致君尧舜,何代无人?”[16]742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借张九龄之口高歌“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行之在我,何必古人”[5]4491,贺知章《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也借墓主“大丈夫非降玄纁不能诣京师,岂复碌碌从时辈也”[19]33的豪言,弘扬经世致用、入世参政的儒道精神,展现人生奋发有为、发展成才的理想抱负。这种描写在集贤院学士群体碑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苏颋《御史大夫赠右丞相程行谋神道碑》、韩休《赠邠州刺史韦公神道碑》等,都将个人的成才发展与国家盛世建设结合起来,借时代写人,写人写国政,展现盛世之下人才的学以致用、全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碑志还通过胡人华化的描述,展现帝唐盛世之治。如张说《拨川郡王(神道)碑(铭并序)》一文讴歌墓主“有由余之深识,日之先见,陋偏荒之韦毳,慕上国之衣冠。圣历二年,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从之者七千人”,特别指出“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16]850。碑文用了不少篇幅颂扬墓主论弓仁投奔帝唐、献身盛世建设、维护中华一统的作为,展现唐代胡人华化的民族融合之风和地缘政治格局。这与史传关于墓主“本吐蕃族也。父钦陵,世相其国。圣历二年,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公[22]4126”的简单记载形成对比,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亦有着此类胡人华化的描写,用意深刻。
四、盛世碑志的体质与形态
盛世之治需要盛世之文。王勃、杨炯、张说等,为配合盛世文化建设,一直将礼乐王道奉为变革文体的准则。王勃倡导文章的实用功能,“气陵(凌)云汉,字挟风霜”[22]428, “礼乐咸若,诗书具草”[22]32。卢照邻《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也强调“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5]1691。杨炯《王勃集序》指斥当时文坛“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23]36。陈子昂也倡扬文体革新,追求“风骨”“兴寄”。玄宗时集贤殿学士集团的形成更确定了从追求礼乐入手改革碑志文的基调,张说要求碑志写作要“润色王道,发挥圣门”[16]1196,追求“济时适用”“雅有典则”[24]。《旧唐书》载张说“为文俊丽……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20]3057从初唐四杰到张说、苏颋,文人将碑志文体改革与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将士人个体的奋斗成才与王朝的盛世建设结合在一起,最终使得盛世之任顺利完成,而唐代盛世碑志的特征也得以形成。
盛世碑志的中心便是发扬文学的政教精神,弘扬儒道思想,行文尤为注重典范人物的塑造,倡扬积极入世、努力国家建设的生命价值,如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写墓主“言为士范,行乃人师……性笃天伦。行必由信,不负黄金之诺;举无失德,逾慎白圭之玷。”[5]2086而张说、苏颋的碑文中此类描写更多。这主要表现在:(1)突破传统碑文的单线叙述模式,在具体的环境中突显典型人物,铺陈排比,气势凌厉,情景辽阔壮美,人物塑造生动形象。(2)行文详略得当,主次分明,综合运用顺序、倒叙、插叙、追叙等多种写作手法,起伏跌宕,叙写有力,具有深厚广阔的审美意蕴。(3)文辞语句骈散结合,在记人写事的基础上更追求议论、抒情及说理,张扬情感,激荡士心,整体呈现出雄壮豪迈、壮丽伟岸的气象。
伟大的时代诞生伟大的文学,盛世碑志的另一体征便是对于骨气端翔、清新刚健、雄伟壮丽的审美风格的追求。杨炯《王勃集序》说王勃的赋颂碑铭是“以兹伟鉴,取其雄伯”,以致“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23]36。王勃虽仕途失意,又英年早逝,但其身体力行,倡导文风改革,追求文学创作的“逸势孤标,奇情新拔”“天然壮丽”[16]1329,以迎接盛世到来。这种审美追求在杨炯、陈子昂、张说、苏颋、张九龄、姚崇、贺知章、王维、李白等人的碑文中反复出现,都通过系列壮丽场景的描写,展现唐代繁荣兴旺的社会生活,行文铺陈排比,夸饰渲染,通篇清新豪迈、高华宏博。
从思想内容到文体形式,唐人赋予碑志文深远的历史传承和强烈的现实需要,使得碑志文创作将壮大的声貌气势与繁富兴旺的社会生活及政治格局结合起来,最终确立了盛世碑志文的体质。确立的关键在于碑志文创作情感力度的壮大、精神气势的昂扬奋发、章法结构的纵横捭阖和思想内容的浩博雄健。唐代盛世碑志无论写战争军事、写政治宦游,其对乡关的眷恋,对战争的畏惧,对人生苦短的忧伤,最终多为事功致用、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所代替,行文铺陈排比,张扬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价值观和奋斗精神,整体焕发出昂扬进取、乐观向上、雄浑博大的审美风貌。
综上所述,唐代盛世碑志以雄浑刚健、华茂壮丽、宏正典雅为特征,有利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度,提升人们对王朝政治的认同感与参与度,立此存照,垂示将来,传之不朽,这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及人民家国情怀的促进,有着深远影响。中唐以后,士人渴望王朝振兴,呼唤政治一统,碑志创作伴随着文体革新,在思想内容和创作体式上出现了演变。而晚唐王朝动乱,碑志创作自然不复盛况,日益体现出衰世体征,皮日休、罗隐的碑志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