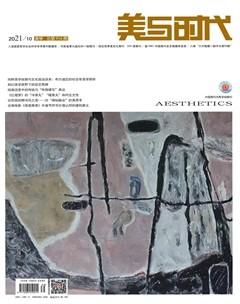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一种人类学式的美学理论
摘 要:斋藤百合子在《熟悉事物的美学:日常生活与世界创造》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其日常生活美学理论,就日常生活美学的概念范畴、具体应用以及日常生活美学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说明。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态度和方法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这一理论仍处于发展初期,故而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不足,其容纳万物式的研究方法也使得研究领域变得过于庞杂,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精简。
关键词:斋藤百合子;日常生活美学;文化人类学
在《熟悉事物的美学:日常生活与世界创造》(Aesthetics of the Familiar: Everyday Life and World-making)(以下简称《熟悉事物》)一书中,斋藤百合子针对学界对她的日常生活美学理论提出的一些质疑进行了回答。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就日常生活美学概念、具体应用实例以及日常生活美学对影响和改造世界的重要作用展开阐述。纵观全书,可以看出斋藤百合子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日常生活美学是一种比较年轻的美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而文化人类学虽然没有漫长的学科历史,但已经具备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由于日常生活美学与文化人类学在研究范围、态度、方法上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將二者进行比较,可以对日常生活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文从斋藤百合子的《熟悉事物》出发,针对其日常生活美学研究的范围、态度和方法进行分析,希望能够说明这种日常生活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存在的优势与不足。
一、“日常生活美学”的内容
由于日常生活囊括的范围过大,并且其自身带有一种琐碎性和主观性,这就给研究带来许多麻烦。如果要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行为作为研究的重点,那么从一方面来说,因为内容庞杂并且处于一种永恒的不断生发的状态,使得研究难以面面俱到,不能涵盖各个内容和对象;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斋藤百合子在著作中提到的,“根据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家庭、工作环境、职业、兴趣爱好等因素,什么能够被视作‘日常要根据情况而定”[1]10。这样一来,因为个人习惯、社群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极端主观性,研究形成的理论很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会显示为一种以群体或者是个人为单位的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
因此,斋藤百合子在叙说其日常生活美学研究理论之前,先为自己的研究划定了范围。首先,这一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共享某一文化的社群的日常生活。不同于传统美学,尤其是艺术中心理论能够给人提供的具有很大强度、深度的极端体验,日常生活是日复一日频繁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为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熟知的,同时也正因其重复、平凡、细碎、微妙而极易被人忽略。其次,虽然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但是斋藤百合子并没有遵循传统美学根据某一对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而是将“体验”这一动态过程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核心,她说:“日常生活美学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大量的事物和行为,而是一种基于我们对其采取的态度而产生的体验模式。”[1]10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达到的目的并非用日常物取代艺术,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纳入美学范畴,重申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和整体性,倡导人们唤起对于庸常生活所能带给人的平静、无言的审美满足感与对日常生活的气息的审美感受。再次,除了关注对过程的体验之外,斋藤百合子同样提出要考虑日常生活美学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的影响及其塑造社会的功能。在她看来,日常生活美学与传统美学的一大不同就是,后者有超越世俗的倾向,持有一种静观的审美态度;而前者则是要融于世俗之中,感受、体验并进而改造、创造世界,具有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
总而言之,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其中,她着重关注的是在参与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由多种感官经验相互补充、增进从而塑造的整体体验,并且强调日常生活美学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效果。
而这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有相似之处。首先,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突破学科最初的“抢救式研究”,当今的文化人类学不再限制于研究原始部落和少数族群,而是拓展到都市社会,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咖啡厅、垃圾桶等的研究。其次,文化人类学与斋藤百合子提出的日常生活美学一样,同样关注行为的过程和体验模式。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模式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通过关注具体的行为过程来发掘背后的深层架构。最后,二者都重视自身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影响、改造世界的效果。同时,日常生活美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也存在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二者都关注活动过程,但日常生活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更加注重感性经验,它要发掘的是体验模式,而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发掘生活现象中的行为模式。
二、使日常生活成为审美活动的重要态度
虽然斋藤百合子希望将日常生活纳入审美领域,但进入了美学范畴的日常生活毕竟与模式化、程式化了的日常生活存在差别,其差别就在于看待该行为、事物的态度。对于程式化了的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倾向于体验‘日常的对象和活动,无论它们是什么,主要都是出于务实的考虑。专注于完成某项任务通常会掩盖这些‘日常对象和活动的美学潜力”[1]10。而美学视角下的日常生活更加注重对过程的体验,在这一体验中,虽然不排除务实态度的存在,但主体采取的更多是审美态度,人们活动的动机和对结果的要求都有所降低。根据《熟悉事物》,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以下几点使日常生活成为审美活动的重要方法(态度),即陌生化/注意、对话和参与。
(一)陌生化/注意
“当生活中充满活动和信息时,我们倾向于打开‘自动驾驶仪,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正带着感官接受世界。生活变得平淡无味,但实际上不是应该责怪生活,而是我们对生活的贫乏的看法。”[2]日常生活之所以显得庸常机械,是因为它的审美特质和惊奇性在重复中被逐渐湮灭,进而沦为一种“背景”。因此,要将日常活动重新召回审美领域,使其从背景中脱身而变成审美对象,“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打破习惯性的方式来体验过于熟悉的物体、环境和事件”[1]12。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上施加更多的注意力,从无意识和条件反射的自动模式中跳脱出来,有意识地去注意、体味事物和行为的每一个细节。其次,可以通过改变熟悉事物的位置、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来将其陌生化,从而发现看待它的不同视角,探索它潜在的丰富的可能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陌生化同时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陌生化可以重拾日常生活的惊奇感和美感;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也可能削弱日常生活带来的家园感、安全感,也就是“日常感”。因此,陌生化应当针对那些已经沦为机械程序的日常偶尔被运用,作为使日常生活由背景變为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方式,而不应当被用在每时每刻。它的重要作用应当是带来震撼,“如果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以及周围的每个物体都变得特别,它们的特殊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消失”[1]20。
(二)对话
在“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上,“苏姗·菲根(Susan Louise Feagin)就戏剧谈了两个观点:一是关注一种现象,即现代戏剧有意或特意设置的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二是做出一种判断,她说:‘欣赏戏剧表演不是个人经历,而是在与他人共享的空间里发生的一种活动”[3]。从她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美学具有对话性,其一是与审美对象的对话,其二是与另一审美主体的对话。
就前者来说,日常生活美学与传统美学在欣赏/体验方式上是不同的。传统美学,尤其是艺术中心的美学,需要欣赏者专注于某个被“框架”限定范围的艺术品,并且经常只是运用一种感官。而日常生活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场域,没有必然的范围限制。恰恰相反,斋藤百合子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引导人们去感受某物/活动与其他事物/活动之间的联系;同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欣赏是一种全感官的自由运行……运用某一感官,也并不排斥其它感官的协同”[4]。这样,我们在进行体验时需要调动各种感官相互补充、配合,进而形成一种完整的、未被割裂的感觉经验。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体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5]。正因为如此,为了使某个体验获得更加全面而丰富的内涵,每个主体都需要和另一个主体进行更加密切的交流。同时,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也能够促使日常生活重新从“背景”中突显出来。由于日常生活的主观性,在不同主体看来,同一个事物会有不同的审美效果,加强对话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细致地看待事物。同时,对话也使得多元的审美趣味得以被平等地展示和输出,这对于将美学和道德相结合的愿景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失的前提。
(三)参与
斋藤百合子对日常生活美学的体验者的要求是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每个审美主体都亲身参与对对象的体验之中。也就是说,在欣赏一个作品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创作者。
一方面,这种参与是参与体验某一事物或活动。例如,商场内部有时会设立一些积木墙,这些积木墙由众多长方体的木块累积堆叠而成,其初始状态是平整的、平平无奇的,但行人用手或其他工具推动、拉动这些木块,就会改变其整齐划一的形态,而使其呈现出凹凸不平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欣赏者也成为了一个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共同对这件作品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参与也是通过体验的过程来实时参与对个人和世界的改造。斋藤百合子在《熟悉事物》中以洗衣、晾衣这一活动为例,除了发掘其中的审美特质之外,还尝试将日常生活和伦理道德、社会风俗、世界创设联系在一起。透过她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美学和传统的艺术中心美学不同,艺术通过欣赏者的静观与思考来对世界发问,通过点亮欣赏者的思想来进而试图改变世界;而日常生活美学本身就是从历史中继承发展而来,它是通过行为和活动本身的点滴累积,从直接的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在层累的变化中改变世界。
以上几点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既相类似又有所不同。文化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般都是以一个“社区新人”的身份进入某个群体当中,体验他们的生活,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并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学者的目的在于调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带有局外人的视角和心态,即使是对日常生活的现象进行研究,这种心态也会使其对每个被熟视无睹的细节抱有充分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这种注意、对话和参与都是日常生活美学所倡导的。但不同点在于,人类学研究毕竟是一种“向外”的研究,而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却是“向内”的,研究对象是主体自身的体验和活动过程。
三、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得到的启发
首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在这些共同点上,日常生活美学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例如,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采用体验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零散的、个人的经验之中提炼出可书面化的材料,归纳得出一种体验模式或心理模式,从而使自身的理论话语更加系统化,更有理论性,突破现今较为琐碎零散的描述式理论写作。虽然将关注重点放在对对象的体验上,但日常生活美学要想成为一种得以通过思辨进行传递和交流的理论,还是需要探索个体体验背后蕴含的深意和结构,否则只能发展为一种培养审美能力的美育教程,而非一门美学分支学科。
其次,虽然文化人类学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美学的参考对象,但后者毕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研究者不应停留在它们的共同领域,而应该就不同点进行深入研究,如,更多地关注感性经验而不是日常活动的现象,继续深入对体验和体验模式的研究,等等。从斋藤百合子的《熟悉事物》一书来看,作者还是没能深入地讲述“体验”的具体感受和过程,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描述更多取材于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些书面作品)。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当经验进入文本时,它便与即时的、生动的经验产生了距离,而变成一种回忆性的“再经验”,这就与日常生活美学对当下体验的重视形成了一个矛盾。或许参照文化人类学的参与和访谈的研究方法,注重收集口述材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
总之,只有立足于美学自身的特殊研究对象,发挥美学研究自身的长处,才能使日常生活美学突破风俗史、物质史的写作,与文化人类学有所区别。
参考文献:
[1]Yuriko Saito. Aesthetics of the Familiar:Everyday Life and World-mak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2]Lotte Dars?. Artful Creation:Learning-Tales of Arts-in-Business[M].K?benhavn:Samfundslitteratur,2004:120.
[3]王确.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12(12):105-107.
[4]张法.西方日常生活型美学:产生、要点、争论[J].江苏社会科学,2012(2):17-22.
[5]徐梦.斋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理论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7.
作者简介:胡灵璐,武汉大学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