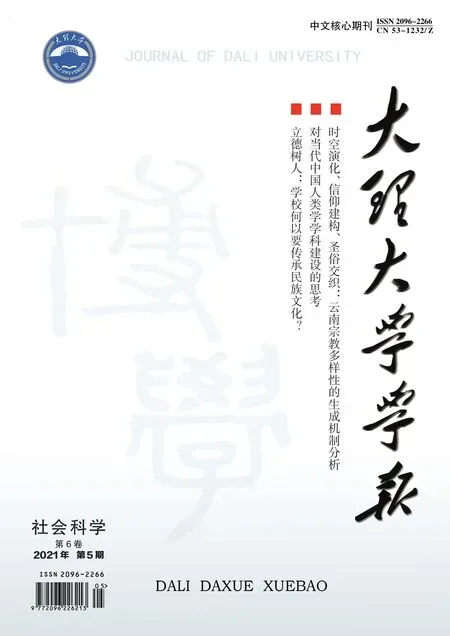时空演化、信仰建构、圣俗交织:云南宗教多样性的生成机制分析
孙浩然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昆明 650500)
云南是我国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典型地区,云南的宗教关系在不断层累叠加中生成,按其时间先后顺序,大体经历了原始宗教独立演化,本土宗教与佛教互动,本土宗教与佛教、道教互动,本土宗教、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互动,本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宗教互动等阶段,各大宗教互动交往的程度深浅不等,从冲突到和谐的实现路径有别,与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融合的程度也有差异,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有快有慢,但置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大格局之内,无疑增加了宗教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云南边疆的多元宗教,从横向—纵向、宏观—微观、静态—动态等各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认识,而作为多元立体的宗教关系,也应从上述角度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剖析。如既要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宗教形态,也要从纵向研究不同宗教的发展历程;既要从宏观层次探讨国家政策对宗教关系的影响,也要从微观层面分析日常生活互动中的宗教交往;既要从静态角度截图观察一个时期的宗教关系,也要从动态角度分析宗教生态的演化历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困局。
关于云南多元宗教关系,学术界已经展开研究。我们拟突破现有研究的分析范式,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神圣与世俗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时空演化、信仰建构、圣俗交织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假设作为分析框架,旨在将割裂的二元性转化为整合的二重性,将宗教本身所固有的互相对立但同时相互融合的属性还原给宗教本身,更贴切地分析多元宗教生成演化与和谐相处的现实。第一,多元宗教的生成与演化离不开特定时空场域,可以从整体结构、生成脉络、内部逻辑、外在情境等因素入手展开分析,可称之为时空的演化与演化的时空,其关键词是时空演化。第二,从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宗教尤其是神灵体系都是信仰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出来的,宗教神灵一旦被建构出来且成为根深蒂固的信仰,反过来也会影响信仰者创造历史的进程,可称之为信仰的建构与建构的信仰,其关键词是信仰建构。第三,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交织重叠,如许多重大节日最初都是宗教节日,作为神圣的集体狂欢,不仅有助于宗教信仰的延续,也能调节重复化、例行化的日常生活,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宗教化与宗教世界的生活化,其关键词是圣俗交织。
一、时空演化:时空的演化与演化的时空
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宗教活动,莫不在特定时空之中展开。然而,时空观念却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时也受到宗教的影响。如东是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是太阳在木上的形象,显然与扶桑神话有关;中字的形象是在祭坛中央插着象征氏族的图腾旗帜,祭坛处在部族生活的中心区域,而祭祀活动也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在日常生活的时间节点上,宗教节日具有重大意义,往往作为一段时间的中心,也象征新的开始。宗教创立和生成的地方,作为圣地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可以说,宗教在特定时空中生成演化,宗教的生成演化也影响到特定时空的社会呈现。
云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必然对云南宗教演化产生影响。云南立体的气候和民族分布,也使宗教呈现立体分布特征。云南文山的民间谚语说:“壮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彝族住箐头、汉族住街头”,类似的谚语也在云南其他地方流传。不同民族信仰的宗教适应各自生产生活的需要表现出一定差异,空间范围越大,居住的民族越多,生产生活的方式差异越大,宗教的形态就可能越多样。时空交织对宗教演化产生一定影响。从时间看,有些宗教经过长期传播,扩大了影响范围,有些宗教则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了。从空间看,高山大川的阻隔,延缓了部分宗教遭遇现代化冲刷的进程,一些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反而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较好地保留了下来。
中心—边缘是常见的空间分类模式,相对于政治中枢,云南被视作边疆。然而,中心—边缘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中央王朝经略云南的行军路线几经变迁,客观上折射出中原王朝和云南政治中心的变迁。例如庄蹻王滇是率领楚国军队从东往西经湖南、贵州进入云南,而汉武帝征服西南地区则是以成都为根据地,自北向南实施经略。诸葛亮五月渡泸,征服南中,大体上也是从成都出发,自北向南推进。唐朝经营云南,在北、东、南三个方向设立军事据点,基本上形成弧形扇面,向云南腹地推进。忽必烈从六盘山出发,自北而南穿行数千公里,革囊渡江,攻灭大理。朱元璋则是由东向西讨伐云南,在曲靖白石江一战消灭元军主力,继而进据昆明,平定全滇。值得注意的是,行军路线与商贸路线一样,都能带来多元宗教,交通重镇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文化吸纳和宗教吸纳功能。云南自古就是内地通往东南亚的交通孔道,当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1〕285。所谓僄越,应是古缅甸的侨民,身毒之民则是古印度的侨民。可以推测在汉晋时期,缅甸、印度的侨民和商人,沿着古老的蜀身毒道带来异域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宗教文化,丰富了云南宗教生态的内容。
云南乃至缅北那些为数众多的命名为孔明山、孔明城、诸葛营、诸葛寨、诸葛村的地方,历史上诸葛亮未必亲履其地,但当地人却将诸葛亮神化并顶礼膜拜。贵州、云南有不少地方名为关岭、关山、关坡、落索坡等,附会关羽第三子关索追随诸葛亮南征。实际上,这些地名大体上从东向西分布,与明军征讨云南的行军路线高度相符。可以判断,关索信仰随明朝军队进入滇黔,最开始在军屯中流传,随着军屯与商屯、民屯的融合,也为地方百姓所信仰。澄江县阳宗镇民间传说,关羽的三女儿关银屏嫁给了蜀庲降都督俞元人(今澄江县)李恢之子李蔚,与关索之妻鲍三娘等女将作为先锋南征,最后驻兵澄江,死后与李蔚合葬金莲山。澄江民间相传“三合湾”就是诸葛亮南征时三路兵马会师的地方,百姓每年还要在县城东“三组塘”畔的李氏祠堂演戏敬香。翻检云南文献,我们经常看到附会地名作为证据,建构英雄传说或宗教神话的例子。
宗教一旦在特定空间中生成传播,最终会影响乃至改变这一空间的形象特征。例如佛教在南诏大理国广泛传播之后,建构了白饭王、阿育王的祖先认同,苍山洱海之境不再是“罗刹鬼国”,而是有了“妙香佛国”的美誉,佛教化的大理形象深入人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98-1976)将世界定义为“天、地、人、神之纯一性的居有者的映射游戏……这种游戏出于转让过程的合抱起来的支持而使四方之中的每一方都与其他每一方相互依赖……四方中的每一方都在它们的转让之内,为进入某个本己而失去本己”〔2〕。所谓“妙香佛国”,也可从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理解为特定时空范围内一场人神互构、圣俗交织的映射游戏。
不同宗教相遇具有严格的时间序列,宗教在特定空间传播的先后,会影响宗教关系的性质。例如清朝道光年间(公元1821年—1850年),云南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一带怒族信仰的原始宗教与传播进来的藏传佛教发生冲突,经过调适而和谐相处,部分怒族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光绪年间,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又与传播进来的天主教冲突,经过调适后和谐相处。民国时期基督教传入,经过调适与上述宗教和谐相处,若细分起来,四种宗教至少有九种关系模式。当藏传佛教进入时,只面临同原始宗教的关系,至基督教传播时,则要面临同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三种宗教的关系。从横截面分析,若发生宗教冲突,往往是以某两种宗教为主,其余宗教为辅。从历时性上分析,越晚传播的宗教,面临的宗教关系就越复杂。当然,若前面传播的第一种乃至第二种、第三种外来宗教都已经本土化,那么就可简化为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此外,宗教自身的力量有大有小,也不能简单以时间先后进行判断,在人类宗教史上,“后来居上”的例子举不胜举。
相对而言,某一地域中的民族按其居住的先后顺序可分为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两大类,但随着外来民族与土著民族交往互动,逐渐扎根,也会成为世居民族。相应地,某一地域中的宗教也可分为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两大类,而本土宗教既包括土著民族信仰的宗教,也包括世居民族信仰的宗教。从形态上看,本土宗教可以是从原始宗教到文明宗教的任何一种宗教,而外来宗教如果彻底本土化之后,也可以成为本土宗教。依据外来宗教信仰载体和传播特征,可以将外来宗教分为传播宗教和移民宗教两种。传播宗教由传教士或传教团有意识地向特定地域传播,他们在当地并没有信徒基础,难免会与本土宗教争夺信徒,因而引起冲突。而移民宗教则由移民带入特定领域,有延续信仰的人口基础,可以不必同本土宗教争夺信徒,只要本土宗教能够尊重其风俗习惯,一般不会引起冲突。例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属于传播宗教,明朝时期的道教属于移民宗教,汉族移民宗教通过人口增殖、社会交往等,使道教自然而然地影响了部分少数民族。通过土著与移民的交往互动,云南的地方知识也进入外来宗教的文化体系之中,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与云南地方知识的小传统,在历史长河中水乳交融。
宗教在特定时空之中演化,打上特定时空烙印的同时,也影响特定时空的社会呈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中国乡村一般有三种历法,第一种是适用于农耕的历法,与二十四节气紧密相关,它告知人们什么时候该下苗、什么时候该收割等;第二种是节庆历法,它告知人们重要的公共社会活动该有什么节奏;第三种是择日用的历书,用于择吉〔3〕。宗教节日具有极强的吸附集聚功能,能够吸引较大范围内的人群参与庆典仪式,也为商品贸易搭建了平台。宗教节日不仅可以调节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也能为地域范围内的众多社区成员提供交往联系的纽带,增进地域认同和社区团结。
二、信仰建构:建构的信仰与信仰的建构
建构不是简单的虚构,而是通过重新组织各种要素,形成支配结构的过程。支配结构一旦形成,人们倾向于不断赋予其意义,继而形成建构的结构化与结构的建构化循环往复。分析宗教的历史建构与建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宗教的本质,明白在特定条件下人们是如何创生新的信仰并将之作为“宗教真实”予以崇拜。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释。”〔4〕我们有时要运用解构的方法,还原人与神关系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结构,以此解开宗教创生的密码。在宗教信仰中,我们经常看到如此吊诡的现象:人虽然在场但是缺场,神看似缺场然而在场。多元宗教就是围绕人与神的关系,在建构的结构化与结构的建构化重叠互构中层层加码。我们将云南宗教历史上几个比较突出的相互建构实例分析如下。
第一,根据日常生活和实际生产需要,不断建构自然崇拜的信仰形态,也增加了宗教信仰风俗的内涵。即使瞬时爆发的宗教情绪也不能当作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持续沉淀的宗教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境交相作用的结果。神灵不会凭空产生,自然崇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应运而生。不可否认,如此产生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例如在农业社会中,农人形成了很多与占卜丰歉相关的巫术,有些介于宗教与民俗之间。云南彝族等氐羌族群的火把节,曾经被赋予柏洁殉夫的道德内涵、火烧松明楼的历史情节、除魔驱邪的宗教象征、星回节的天文知识等。实际上,火把节最初应源于农业生产祈求丰收的宗教仪式。《昆明县志》记载:“六月二十四五两日,斫松为燎,高丈余,入夜争燃之。村落用以照田,以炬之明暗,占岁丰歉。”①参见陈荣昌修,李锺本纂,高国强、王飞虎校注《民国昆明县志校注》,民国十四年刻本。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占卜丰歉的逻辑符合巫术思维,与《山海经》中某物出现则大丰、大荒、大凶、大兵、大水等的记载异曲同工,只是神秘色彩略逊一筹,借助占卜的事物不再是稀奇的怪鸟、怪兽、怪鱼等,而是人们熟悉的蛇、鸡、犬、树、石、洞等动物、植物或自然物,相关记载在民国以前编纂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兹不列举。
第二,基于民族关系的实际需求,建构异族英雄崇拜、祖先崇拜或民族同源神话的信仰形态。我们以诸葛亮神话为例进行分析。诸葛亮南征确有其事,但民间围绕这一史事建构了诸多神话。《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中已经渗透神话因素:“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府城;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1〕247隋唐时期有关诸葛铜柱、诸葛石碑之类的记载,神话色彩就更浓。《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上》:“广德初,凤迦异筑柘东城,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蛮为汉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5〕明清时期诸葛亮南征神话在云南民族地区大量出现,旨在调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明清时期,汉族移民深入云南边疆,大力渲染诸葛南征神话,边疆少数民族将诸葛亮作为“祖公”“老爹”崇拜,认为是诸葛老爹教会它们耕田、种茶、建造房屋等,诸葛亮神话客观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见,民族认同不一定是血缘认同,人文始祖也不一定是血缘始祖。
诸葛亮神话建构的手段多种多样,或者更改诸葛亮南征的行军路线,诸葛亮并没有亲至永昌,但民间却传说诸葛亮“乃于普坎立南征碑纪绩,班师抵永昌,断九隆山脉以泄王气。回驻白崖,立铁柱镇诸蛮”〔6〕25。或者将山川道路、关隘村寨以诸葛亮名义命名,川南、滇西、滇中、滇东一带尤为集中。或者附会自然景观、人文风俗,如《滇略》记载:“广通县翠屏山中有汤团箐,云武侯擒孟获驻师于此。时腊月二十四日也,军士追思荆楚,以汤团祀灶,乃炊而食之,未尽者弃之而去。至今箐中小石,形类汤团然。”〔7〕456诸葛亮神话并非一场简单的造神运动,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云南的历史。
第三,附会宗教经典,辅以民间传说,建构宗教圣地。《滇绎》引陈鼎《滇黔纪游》说:“滇西为古佛国,名山多见于佛经,如宾川鸡足山。”〔7〕457从明代以来,人们附会佛经的相关记载,逐渐推动宾川县鸡足山成为迦叶尊者守衣入定等待弥勒成佛的佛教圣地。此类附会虽不易证实,但也难于证伪,或者人们根本就不愿证伪,因为这些神话可以为地方社会增加声望,最终“证据”不断叠加,人们自然深信不疑。从现代眼光分析,这些附会建构总有开端,总有始作俑者,总有附和者、追捧者,需要获得集体承认支持才能成功建构并广泛传播。因此,即使是建构出来的,宗教神话也可以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宗教神话建构生成并被人们接受后,经过世代展演不断传承沉淀,成为地方文化中的神圣叙事资源,有些也被记载下来作为文本广泛引证,与之相关的地名、祥瑞等也被民间创造出来,作为第一象征的符号文化,坚振了人们的信仰。例如大理州有一些地方以凤凰命名,如凤羽、凤仪等,作为有凤来仪、人杰地灵的论证,为地方笼罩了一层神圣色彩。
明代以来,民间传说建文帝在云南武定狮子山正续禅寺出家,好事文人题诗、刻匾、撰联为证,人们言之凿凿,地方志书载之确确,正续禅寺也随之成为滇中名刹。洱源县民间传说建文帝躲藏在牛街西北观音山腰的眠龙洞,一日三餐都有白米从石钟乳中流出,人们还在洞口修盖了一座兰若寺。可见,宗教与神话可以互为论证,人们建构神话寻找的诸多“证据”,也成为地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成为信徒顶礼膜拜的对象。
第四,以宗教神话修改历史文本,建构宗教认同。从南诏大理时期的《铁柱记》等文献开始,至元代、明代的《白古通》《南诏野史》,云南的地方文献不断穿插叙述宗教神话,在渲染大理妙香佛国宗教底蕴的同时,也建构了白族的祖先世系和民族认同。在大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文人和文本代表了知识权威,文人辗转相抄,文本相互引述,增加了所叙知识的可信性、合法性,并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进而深入人心。至清朝前期,仍然有学者将神话当作历史,把历史演绎成神话,官修志书和各类稗官野史,如邵远平编纂的《续宏简录》等,几乎都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叔叔白饭王后裔张仁果为滇王的神话,《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载的庄蹻王滇反而很少有人引述。这些记载没有考据,以讹传讹,重复沿袭,作为“常识”在文化精英和民间大众中传播。同样,白族的民族起源神话也被人为篡改,为佛教信仰张本。九隆神话、金马碧鸡神话经过南诏大理国,至元明时期就被佛教徒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例如重构后的九隆神话将滇西乃至南亚东南亚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乃至不同国家的祖先追溯到阿育王,表现出强烈的佛教文化认同,其中隐含的外向心理是断然不可取的。
元人张道宗《记古滇说》记载了重构后的金马碧鸡神话,讲述古印度阿育王的三个儿子追逐神骥来到滇池,最后滞留在东山、西山、北野。“阿育王忧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为哀牢彝所阻。遂归滇,各主其山,死而为神”〔6〕9。阿育王三子一舅的神话杂糅了汉文史籍文本和民族传说,既能迎合士大夫的口味,也能赢得普通大众的欣赏,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张道宗为元人,此神话在大理国甚至南诏后期就萌生了,应该早就有民间口头流传的版本,也可能是笃信佛教的统治者为了彰显自己信仰纯正和世系高贵而建构出来的。
三、圣俗交织:日常生活的宗教化与宗教生活的日常化
宗教信仰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往往嵌套在一起,世界上或许没有脱离日常生活的宗教生活。在深山野林参禅打坐的宗教生活看似避世高隐,其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修行,早已重复化、熟悉化、例行化、平凡化、日常化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日常生活。所以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日常生活可成为悟道之资粮。在一般信徒那里,宗教生活更是与日常生活重叠在一起,在圣徒那里,则可达到日常生活宗教化的境界,所谓“搬柴运水,无非是禅;扬眉瞬目,无非是道”。信仰是一种生活,生活也是一种信仰,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相互转化,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相处。云南多元宗教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相互依赖、和谐相处。
卢克曼(Thomas Lukman,1927-)认为:“宗教的基本功能在于,把一个自然族类的成员转化成一个历史地产生的社会秩序内的行动者。”〔8〕119“宗教的私人化是现代社会中生活全面私人化的一个核心部分。生活的私人化是社会结构在功能上高度分化的后果之一,几乎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8〕135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互构,宗教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有机融合,使制度化、体系化的宗教与日常化、常识化的宗教并行不悖,使宗教矛盾在生活熔炉之中逐渐化解,而不在信仰层面出现冲突。可以说,任何宗教功能,最终都要落在生活世界的功能之中。
神圣与世俗是宗教研究中常见的一对概念,研究者喜欢在圣俗之间划出截然对立的界限,但普通信仰者在实践中却往往将二者混淆起来。简单说,所谓圣,是宗教生活、信仰世界;所谓俗,是社会生活、世俗世界,二者时常交织互构。宗教生活向日常生活的转化,日常生活向宗教生活的转化,最重要的中介可能是宗教节日仪式或宗教节日庆典,在地方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人群凝聚和民族团结功能。简单说,神圣即属于神的事物,而世俗即属于人的事物,这涉及神圣物与占有物之间的关系。涂尔干(Durkheim,1858-1917)说:“神圣性质的交流事实上常常会带来一种占有。神圣化就是一种占有方式。其实,如果神圣化指的不是把某些物归为神或圣人所有,如果他们不是把某些物占为己有,还会有什么含义呢?”〔9〕实际上,宗教徒往往把他们在世俗社会中享有、占有的一切,都看作是神灵的恩赐,一些特殊的事物也被赋予了神圣性,作为神灵的象征,神圣不可侵犯。“一人之美食,他人之毒药”,同样也可说“一人之神圣,他人之世俗”。在不同宗教体系中,神圣物可能被看作世俗物,而世俗物也可能被看作神圣物。因此,神圣与世俗都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交织转化的。
人群集体的命运,有时与宗教的命运相关联,放弃自己信仰的神灵,也意味着放弃既有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按照新宗教的要求规范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秩序。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认为,人的生命是独享的,人们的活动呈现个体化、多样化的形态,遵守共同的法律法规、习俗禁忌等,使多样化、个体化的人能够共同生存〔10〕。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开展其他社会活动的前提。郑震认为,日常生活是“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日常生活的时空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和不断重复的时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基础”〔11〕。一般而言,为谋求生存、保证生活而开展的活动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越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娱等活动中,对宗教的依赖性就越强,日常生活宗教化的倾向也就越明显。一些原始部落的人们出猎之前要先祈祷猎神,过去一些人出门也要先占卜吉凶。《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自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谷,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资以为粮。欲取其木,先当祠祀。”〔1〕303按照祀法规定,自然物若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也可享受祭祀。这种祭祀崇拜大都始于人们自发的宗教情感,后来则经国家权力认可获得合法性。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中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之间的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机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面纱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2〕在古代社会,人们受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特定阶段的日常生产生活总是与特定内容的宗教生活相结合,日常生活可以宗教化,宗教生活也可以日常化。宗教生活日常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一些宗教活动最终成为民俗活动,原本神圣色彩浓厚的宗教节日成为世俗节日。如汉族的春节、彝族的火把节、哈尼族的苦扎扎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瑶族的盘王节、苗族的山花节等。宗教改变其介入生产生活的路径,与日常生活融合起来,其重心不在彼岸世界,而在现实世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宗教场所、宗教活动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世俗化乃至媚俗化、商业化伤害了宗教信仰,也超出了日常化的合理范围,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和引导。
在具体研究中,如何将神圣与世俗、宗教化和日常化的概念操作化并进行科学测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方法论问题。测量指标和操作化应基于宗教的自身要素、宗教生活内在外在维度展开,并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阐释。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逻辑关联的命题假设,不但可以在云南和中国的宗教事实中进行检验,也可以在整个世界宗教的事实中进行检验。与此相似,我们可以将宗教多元与宗教和谐的内在维度、测量指标具体化,就宗教的宽容度、兼容性、和谐性等进行量表分析。经过经验化的验证之后,甚至可以作为对策建议,在宗教冲突的热点地区尝试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