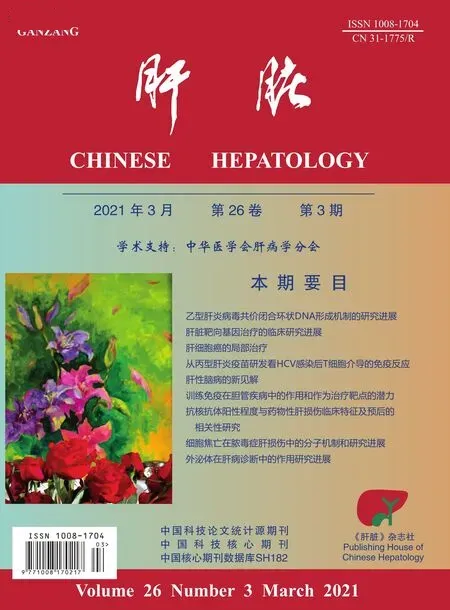训练免疫在胆管疾病中的作用和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
沈波 陆伦根
胆管疾病是一类以胆管细胞损伤为特征的疾病总称,包括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胆道闭锁(BA)和胆管细胞癌(CCA)等[1]。在这一过程中,胆管细胞固有免疫反应激活,免疫细胞浸润和胆管异常修复共同导致了胆管疾病的进展。目前,胆管疾病仍然缺乏有效治疗手段,部分患者从胆管炎症进展为胆管纤维化甚至胆汁性肝硬化,最终肝移植。由于供体肝脏的稀缺,寻找有效的治疗靶点阻止疾病进展是目前胆管疾病研究的重点。
免疫反应与胆管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固有免疫细胞记忆功能与胆管疾病间的关系正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认为只有适应性免疫具有记忆功能,而固有免疫不具备。但最新研究发现,固有免疫细胞同样具有免疫记忆功能[2, 3]。这一功能特指固有免疫细胞在第一次被病原体激活后产生了免疫记忆,在被再次激活后会产生更强大和持久的免疫反应,被称为“训练免疫”(trained immunity)[4]。鉴于训练免疫在胆管疾病中作为治疗靶点的重要潜力,本文就训练免疫在胆管疾病中的作用、调控机制和潜在治疗潜力等方面作一介绍。
一、训练免疫在胆管疾病中的重要作用
肠道微生态的改变被认为是胆管疾病中训练免疫发生的最重要初始因素。目前认为在胆管疾病中,肠道微生态紊乱导致肠黏膜屏障功能下降[5],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通过肠道进入胆管,促进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训练免疫的产生。有研究表明,PSC和PBC患者肠道菌群均发生紊乱。在PSC患者中,肠球菌、梭杆菌和乳酸杆菌比例上升[6]。另一项研究中,Rothia菌、肠球菌、链球菌、梭状芽孢杆菌、韦氏菌和嗜血杆菌比例在PSC患者中也出现异常上升[7]。与此类似,PBC患者中也出现了有益的非致病性细菌减少导致致病性细菌比例上升的情况[8]。此外,Allegretti等[9]研究发现在接受粪菌移植PSC的患者中,33%的受试者碱性磷酸酶水平下降。Bajaj等研究显示,粪菌移植明显改善肝性脑病患者的肝脏功能和认知能力。总之,这些研究均表明,失调的肠道微生态再平衡可以改善胆管疾病的恶化。而胆管疾病中肠道稳态的失调又会破坏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对于内毒素的免疫耐受,导致训练免疫的产生。
训练免疫中的效应细胞包括胆管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尽管胆管细胞并不属于固有免疫细胞,但可以发挥类似作用,并产生训练免疫作用[10]。胆管细胞可以表达多种Toll样受体(TLRs),确保其对于病原体能产生免疫反应。在免疫反应过程中,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会与TLR4相结合,促进NF-κB激活,分泌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包括IL-1β、IL-6、MCP-1、TNF-α、IFNγ和TNF-β[11]。除了TLRs,胆管细胞还可以表达胞内模式识别受体NLRP3炎症小体(NLRP3)。NLRP3激活可以导致caspase-1的前体裂解为激活状态的capase-1,并促进IL-1β和IL-18的分泌,导致细胞焦亡和炎症反应[12]。
除了胆管细胞,巨噬细胞也是训练免疫中重要的效应细胞,它在肝脏中分化为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和库普弗细胞。巨噬细胞在外界病原体的刺激下异常激活TLRs。研究表明,PBC患者外周血来源的单核巨噬细胞对TLRs配体的激活更加敏感[13]。PBC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受到刺激后也可以产生更多促炎因子[14]。研究表明,巨噬细胞也可以在胆道闭锁中被激活。在胆道闭锁模型中,巨噬细胞激活后可以迅速产生IFN-γ诱导胆管细胞凋亡。而在胆管细胞癌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也可分化为M1和M2两个亚型,并且主要转化为M2型产生抑炎因子IL-10和趋化因子17(CCL17),促进肿瘤进展[15]。
作为适应性免疫过程中重要一员的NK细胞,也可作为训练免疫的效应细胞。研究表明,PBC患者胆管受损的程度与NK细胞的数量相关。NK细胞分泌的IFN-γ可以激活CD4+T细胞,导致胆管细胞受损。在胆道闭锁疾病中,NK细胞更是发病过程中的初始事件,与疾病的进展密切相关。而在CCA动物模型中,NK细胞的浸润对于胆管细胞有损害作用。其分泌的多种细胞因子IFN-γ和IL4可持续激活CD4+T细胞,导致胆管细胞受损[10]。
总之,胆管疾病中不仅存在训练免疫的启动因素,也存在着固有免疫效应细胞。在受到外界刺激后,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可以在第一次受刺激后保持长期高反应,产生免疫记忆效果,即训练免疫。再次受刺激后,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分泌促炎因子和趋化因子破坏免疫平衡,损伤胆管细胞并导致胆管疾病产生。
二、调控训练免疫的具体分子机制
在胆管疾病中,固有免疫细胞产生训练免疫主要受代谢重组和表观遗传的调控。而PI3K/AKT/mTOR通路在代谢重组调控训练免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胆管细胞受损后,PI3K/AKT/mTOR通路激活可以促进胆管细胞增殖并产生大量促炎因子(IL-6和TNF-α)和CXC趋化因子。除此之外,PI3K/AKT/mTOR通路还招募其他固有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和NK细胞,激活其分泌炎症因子[16]。在PSC和PBC中,mTOR通路通过代谢重组调控细胞生长、增殖、凋亡和蛋白合成,影响胆管疾病的进展。在大鼠胆总管结扎的肝纤维化模型中,胆管纤维化的进展过程伴随着AKT/mTOR通路的激活,揭示了两者间密切的联系。而在胆管细胞癌模型中,mTOR通路也出现了表达上升的情况。Mckay等[17]研究发现,阻断该通路介导的代谢反应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而在以肝内外胆管扩张、胆管增生和多囊肿形成为特征的多囊性肝病中,mTOR通路也是介导胆管细胞增殖和肝囊肿形成的重要通路。研究发现,在多囊蛋白缺陷小鼠模型中,雷帕霉素(mTOR通路抑制剂)显著减少了胆管细胞的增殖和肝囊肿形成。因此,该通路已经成为治疗胆管疾病具有潜力的靶点之一。
除了代谢重组可以调控训练免疫外,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也可以诱导固有免疫细胞产生长期的高敏反应,也就是训练免疫的产生。研究发现,胆管疾病中频繁出现DNA的甲基化和乙酰化修饰。特别是在PBC中,几个基因频繁的甲基化已经得到证实。CD40L低甲基化与患者血清学IgM水平相关,也与CD4+T细胞过度表达有关[18]。除了在PBC中,胆管闭塞中也存在着DNA低甲基化。研究表明,DNA低甲基化会激活IFN-γ反应基因的激活,并通过激活IFN-γ下游通路和抑制TGF-β通路起到损伤胆管细胞的作用。除了甲基化修饰之外,CD40L基因也常在CD40L启动子区域H4发生组蛋白的乙酰化,并导致CD40L表达的增加。而在PSC中,DNA甲基化的改变没有被观察到。但另一项临床研究中,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存在富含Th1的乙酰化顺式调节元件,显示了表观遗传改变在PSC中的存在[19]。
三、作为治疗靶点的潜力
目前针对胆管疾病中训练免疫调节通路具有治疗潜力的靶点分别是:调控代谢重组的PI3K/AKT/mTOR通路和DNA的甲基化。PI3K/AKT/mTOR通路是介导代谢重组调控训练免疫的重要机制,抑制mTOR通路的激活起到了治疗胆管疾病的作用。而mTOR通路的抑制剂雷帕霉素在胆管疾病的动物模型中被证实显著改善肝内炎症和肝纤维化,促进肝功能的恢复。除了雷帕霉素外,姜黄素也可以通过抑制mTOR通路中ERK1/2的磷酸化抑制胆管细胞的增殖,并进一步减轻胆管纤维化[20]。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在胆管细胞癌的大鼠模型中,二甲双胍通过AMPK/mTOR/HIF-1α/MRP1和ERK通路抑制胆管细胞的糖酵解,并进一步减少促炎因子的产生,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17]。总之,这些研究均提示了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治疗胆管疾病的潜力。但仍需更多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除了代谢重组的调控外,DNA甲基化调控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斑马鱼的胆道闭锁疾病模型中,抗炎因子强的松的使用可以逆转低甲基化导致的胆管缺损,起到治疗作用。
综上所述,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保持胆管的稳态。但在受到外来刺激的情况后,代谢水平和表观遗传的改变会诱导胆管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产生训练免疫,并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破坏胆管细胞,导致胆管疾病的产生。而在这一过程中,mTOR通路介导的代谢重组和DNA的甲基化是调控训练免疫的主要机制。随着对于胆管疾病中训练免疫机制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希望更多针对胆管疾病新靶点和药物的研发会给临床治疗胆管疾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