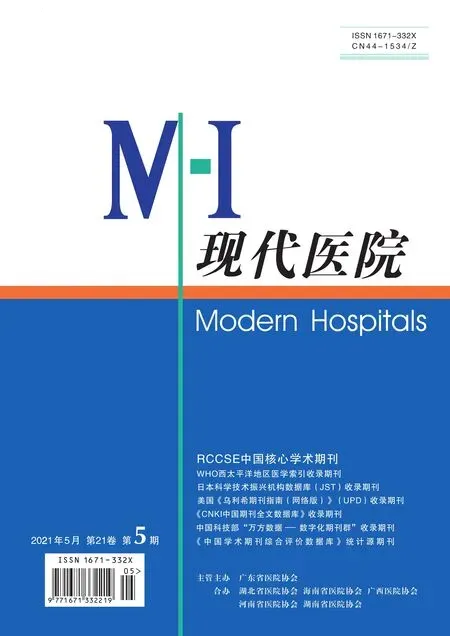构建医媒互动机制 和谐医患关系
高 仪 张 茜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我国也深受其害,在抗疫过程中,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一时之间,“最美逆行者”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之上,媒体都是溢美之词,医媒关系似乎无比和谐。但事实上医媒关系并非一向如此。
仅仅在两年前,山东卫视一则《聊城:主任医师竟然开假药》的新闻,挑动了社会大众敏感的神经,成为重大舆论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谴责医生医德败坏,图财害命。卫生行政部门连夜开会,对当事医生免职,并暂停其执业活动一年,对分管副院长和医务处主任诫勉谈话。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两名帮助购药者先后被刑事拘留。但很快,舆情出现反转,从自媒体披露出大量事实和细节,为人们还原出一个完整的“假药门”,随后公安机关通报医生无罪。网络上对医生、家属的行为深度剖析,对法理和伦理进行激烈的争辩。人们转而同情医生,谴责患者家属,进而批评最初播报的媒体无良。
1 医媒关系与医生形象变迁
在我国,医生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一再发生变化。近代社会,媒体直接影响医生社会形象的建构。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医媒关系经历阶段性的变化,同时,医生形象也呈现出很大的变化。
1.1 同在体制内
建国初期,由于媒体和医院都是“体制内的兄弟单位”,二者基本上是同气连枝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多以正面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1960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通讯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篇通讯曾作为新闻写作的范文被选入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文中描写公社医院二十多名医护人员与众人一道,排除万难救死扶伤的感人事件,“阶级友爱,情深似海[1]”。
这一时期的医媒关系亲密无间,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奋斗。媒体几乎没有负面报道,塑造的医生人物都是白求恩式的光辉形象,道德高尚、医术精湛。“医患矛盾”似乎并无踪迹。
1.2 监督与被监督
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开始影响到媒体和医院,这些行业内部纷纷面临竞争和转型。媒体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祖国形式一片大好”,主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彰显社会责任。医院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等诸多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在这个契机下,医疗纠纷成为绝佳的话题,医媒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主流媒体依然继续报道医生的好人好事,但偶尔也有一些负面报道,例如“新疆一儿童遭三家医院拒诊死亡事件”。
2000年07月20日,《中国青年报》以《医院,怎会有那么多冷酷的心》为题,报道一名三岁幼童因烫伤,先后遭到三家医院拒诊,最后导致死亡的事件。7月25日,自治区卫生厅公布了处理决定:对涉事医院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予以处罚,并要求全区各医院自查、整改。
由于媒体的监督,医院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惩处和舆论谴责,开始害怕媒体“曝光”。媒体报道出来的医生不再是清一色的医德高尚、无私奉献者,也有一些冷漠自私、不负责任的形象。医患矛盾的问题浮出水面。
1.3 承上启下的“茶水门”
2007年3月20日,中国新闻网刊登《记者用茶水当尿液送检医院化验出“发炎”》的报道。记者分别到杭州10家医院称病,用茶水冒充尿液样本做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不同程度地检测出白细胞和红细胞,5家开出了消炎药。记者据此质疑医院误诊、乱开药。报道一经面世就成为爆款,引发公众对医院的强烈不满。
这次“茶水门”与以往不同:首先,报道内容并非真实的医患纠纷,而是记者精心策划的新闻创意,记者存在以“尿道感染”症状误导医生作出不正确诊断的欺骗行为。其次,这个创意的科学性存疑,论证推理结果也存在缺陷[2]。再次,该报道遭到全国百余家医院医生的自发验证,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专门正式向公众回应澄清,但媒体拒绝承认错误。直到今日,事件仍存争议,媒体和医方互相质疑对方的职业道德,公众也被撕裂成两个阵营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医院和媒体的公信力都被消耗了。
1.4 从冲突到对抗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传播的渠道,也大大增加了媒体的影响力。传统媒体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需要比拼速度和爆点。医疗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天然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医患纠纷涉及民生、道德伦理和法律,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和戏剧性,因此备受青睐,“医患纠纷”渐成热门题材。
社会上逐渐形成对于医患双方的刻板印象——医生掌握专业知识占据强势地位,并借此敛财;患者往往贫困、病苦,容易受到医生蒙骗而人财两空。一些媒体迎合社会同情弱者的心理,开始用惊悚的标题和夸张的语言报道医疗纠纷,甚至选择隐去一些事实,呈现出医生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形象。随着媒体对于医患纠纷的倾向性报道增多,有些甚至严重违反医学常识,加重了部分患者对医生的误解和偏见。
2002年1月7日,《生活时报》刊发《出院后发现“丢”了左肾,医生偷卖病人器官?》一文,开启了“丢肾”时代,2013年陕西延安高某,2015年河南农妇项某,2016年江苏徐州刘某某……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丢肾的新闻传出,直接怀疑医生偷肾,贩卖人体器官。这些报道一度引发民众恐慌,但调查结果均显示,并不存在犯罪事实而是病人的肾萎缩。这样的真相媒体很少报道,导致公众不知真相只知丢肾,对医生的敌对和愤慨日益增加。2016年《新安晚报》的“丢肾门”再次出现,却遭到医生们在网上的激烈回击,《中国之声》在《新闻晚高峰》节目正式澄清事实,随后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认定存在不实报道,对该报社作出行政处罚。
至此,丢肾的时代告一段落,公众终于不用担心做手术的医生偷器官了,但仍担心不给红包被缝肛门,担心八毛钱能治好的病要价十万,担心新生儿被护士扇耳光、被烤死……按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医护人员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但真相并非如此。在没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媒体就已经代替法院做出了舆论审判。医护人员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承受着社会的误解和敌对。随着这些不实报道层出,医生的形象彻底变成道德沦丧、谋财害命的凶手。医患关系急剧恶化,暴力伤医事件频发。
1.5 自媒体时代的转机
医媒关系继续走向对立,双方往往各执一词,以往媒体占据话语权,医院有苦难言。但随着社交网络的成熟和自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失去了垄断地位。“人人皆媒体”的时代,医院或医生运用这些手段对一些明显有悖医学常识的报道进行了驳斥并科普,将传统媒体有意隐去的细节还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医生的恶劣形象,开篇介绍的“假药门”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2 恶化的医患关系
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很多矛盾背后有着更深的原因,但媒体在医患纠纷的报道中,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2.1 框架理论
框架是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这一概念源于贝特森(Bateson,1955),他认为框架类似于“场景”、“镜框[3]”。后经戈夫曼(Goffman,1974)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恩特曼(Entman)认为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4]。
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2011)中指出,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和处理的特定原则。这些原则来源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这些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新闻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和反馈新闻事件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受众个人经验较为间接或较复杂的新闻事件,在缺少对照信息源的情况下,媒体的主导性框架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个人对社会真实的感知[5],新闻所呈现的医患关系,选择性地放大了部分真实,但也反过来建构了医患关系[6]。在新闻框架下,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媒体在报道纠纷时更多地展示医务工作者的负面内容,影响了人们对医生的评价,无形中引起公众恐慌,加剧医患矛盾。
2.2 拟态环境
1922年,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李普曼(Lippmann)在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提及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问题。李普曼将现实分为客观现实、象征现实(即拟态环境)和主观现实三个层面,受众的主观现实是他们在认识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呈现的象征现实形成,这种经过媒体中介形成的主观现实,是与客观现实存在偏移的“拟态”的现实。受众接触到的医生形象经过媒体处理后选择性呈现,久而久之沉浸在这种“拟态环境”中无法自拔[7]。李普曼认为,“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各种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8]。在媒体的宣传和影响下,公众对医生形成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刻板印象,而无视大部分医生无私奉献、德高医萃的事实。医患关系在“拟态现实”中,从亲密走向对抗。
2.3 传播的负面作用
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提到,“人们普遍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若缺乏适当的控制,则为恶的可能性更大”[9]。他们认为媒体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大众媒介持续不懈地宣传会使人们完全丧失辨认能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10]。
2.4 全方面的信任危机
医学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即使是法官也很难直接对医患纠纷作出评判。但一些媒体直接使用审判性的语言下定论,“做手术丢肾”、“婴儿被烤死”这样的描述已经不是单纯地报道“医疗纠纷”,而是直指医师违法犯罪、故意杀人。受众会本能地产生恐慌,对于医生的刻板印象从“救命恩人”变成“杀父仇人”,丧失信任感。人们还未见到医生,已经带着对立的情绪,时刻提防医生谋财害命,这样的后果无疑是可怕的。
2007年轰动全国的“肖志军拒绝签字案”,任医生如何解释劝说,肖坚决拒绝手术签字,终使孕妇失去抢救机会,酿成一尸两命的悲剧。据报道,肖自述,拒绝签字的理由是不相信医生[11]。“八毛门”发生后,患儿家长因不相信医生,而拒绝手术的现象激增,5日内接连出现了三起家长拒绝手术治疗的病例,这在该院以前是非常罕有的[12]。一些患者和家属因为媒体的帮助获得舆论支持,对于赔偿的期望值也在扩大,拒绝接受依法取得的结果,有的耽误病情危及生命,有的动辄打骂医护人员,还有人采取极端手段杀害无辜医生。
医院往往在案件中名誉受损,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为平息事态只能蒙受巨额损失和委屈,也导致了一些优秀的医务人员的流失。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5年16年间媒体报道290例暴力伤医事件[13]。医生除了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还陷入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之中。有学者指出,在台湾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不绝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体的过度舆论审判,将医生“妖魔化”,一旦司法机关判决医生有错则更是大肆渲染,医生无错则相当于没有新闻价值就不吭声,而不会平衡报道或者洗刷医生清白[14]。经过多次血泪和金钱的教训,为了保护自己,医生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性医疗”,诊断前尽量多做检查,保存证据;危重病人不敢收治;新技术新疗法不敢开展……最终的不利后果还是由病人承受,或医疗费用增多,或求治无门。
诚然,相比于正面新闻,公众往往对刺激性和负面性的信息更加感兴趣,他们的这种猎奇和嗜好也影响了媒体[15]。在激烈的竞争中,为博取公众的眼球,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以“伸张正义”为名,片面传递患者的声音,选择性地放大部分事实、略去部分关键事实,甚至肆意怀疑医生杀人,引起社会的恐慌,严重违背了新闻伦理。后互联网时代,速度的竞争使得许多媒体在不能很好地了解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便做出报道,但由于缺少系统的问责机制,犯错的成本太低,“宁错不慢”成为整个行业的无奈现实[16]。媒体看似花极小的代价换来爆款新闻很值得,但屡次出现问题损害的却是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对自身和行业都是重大损失。
2007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广东省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并有问卷调查显示,77%的医护人员把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归于媒体[17]。针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问责,天涯论坛贴出文章《信息时报:医患紧张祸起媒体?号错脉了!》回应[18],标题恰恰用的是“号错脉”这样敏感的字眼,一方面讽刺了医生,另一方面容易产生误诊的联想,试图争取公众支持,但评论区的回复绝大部分都在反驳和批评媒体。由此可见,如果任由这样全方位的信任危机继续发展,无论医患双方还是媒体,甚至全体公众,将无一是赢家。
3 医疗纠纷报道的积极作用
回顾这些医疗纠纷报道,也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体现了媒体监督的重要作用。这些报道促进了医疗机构尤其是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完善医疗行为,加强行业自律,为消减类似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
3.1 改进医疗管理制度
前文的“幼童遭拒诊后死亡”事件发生后,引起当时卫生部的重视,在此后制定的医疗安全核心制度中,首诊负责制一直被列为首位,成为核心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对转诊转院制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手术安全核查制度上,在此项核心制度未实施前,患者手术部位做错的报道屡有发生,甚至出现将手术患者张冠李戴的现象。落实手术安全核查制度后,确实大大降低了此类错误的发生。
3.2 改善医疗服务
2017年,陕西榆林一孕妇因不堪忍受分娩疼痛坠楼。案件被报道后,客观上推动了全国无痛分娩的推广和使用,惠及几千万孕产妇。
3.3 促进纠纷的合法解决
一些纠纷经报道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这些纠纷归于合法途径解决。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假药门”,纠纷发生后死者家属激烈地谩骂,让医护人员甚至很多病人都不堪其扰,求着当被告而不得。引发公众关注后,家属的行为也得到了制止,案件回到合法的解决途径。
4 自媒体时代——建立开放合作的医媒关系
现代医疗技术日新月异,治愈了很多历史上的绝症,但依然存在巨大的未知性和高风险性,无法做到让人长生不死,加上社会经济等原因,医患之间存在矛盾在所难免。回顾医媒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体对于医患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媒体报道医疗纠纷应当帮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促进纠纷妥善解决,但如果方法不当便会起到相反作用,造成严重后果[19]。媒体与医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一方针对而另一方回避的模式不可取,互相发起舆论对抗也不是上策。自媒体的兴起,事实上对医生和媒体都起到了约束作用。一个开放合作的新型医媒关系呼之欲出。
4.1 医院主动开放
4.1.1 提高信息透明度
自媒体时代,由于通讯设备的普及,人们已经完全暴露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环境中,很多事实无从隐瞒。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对媒体往往“又恨又怕”,既恨其断章取义,也怕影响自身名誉。面对媒体的质疑,医院常采取回避态度,集体噤声,主动放弃解释、化解误会和矛盾的机会。而媒体缺乏医学知识,又从正常渠道得不到反馈,容易产生猜忌,听到患者单方面声泪俱下的控诉,也容易相信院方理亏而采取维权式的报道。当今社会,公众要求知情的意识越来越强,希望医院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化解不安。医院主动发声,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面向媒体和公众,既可以解释误会,澄清事实,也可以说明理由寻求谅解。
2014年一组手术室自拍的照片传遍网络,患者还在手术台上,医生却在合影。照片引起公众巨大的愤慨,认为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漠视生命。而后当事人解释原委后获得了谅解。截止2014年12月23日上午,12万余人参与了搜狐网对手术室自拍事件的评价调查,近六成人认为“有不妥但无大错,应理解医生初衷”、“处罚过重”[20]。
此后,在“八毛门”、“缝肛门”等事件中,院方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主动对外公开说明一些事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扭转了公众对医院的误解,也维护了医院名誉。
4.1.2 充分利用自媒体
社交平台和个人直播的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帮助医院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现医疗纠纷的不实报道后,医生专业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驳斥更具说服力,无疑更加吸引受众的眼球,在自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帮助医院实现舆论的逆转。
同时,医院还可以利用自媒体科普医学知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疾病。例如羊水栓塞、主动脉夹层等疾病都容易导致病人突然死亡,引起纠纷。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些疾病,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误解。
4.1.3 纠纷调解引入媒体监督
利用媒体的公信力,主动邀请媒体报道医疗纠纷,可以督促患者采取合法手段维权[21]。科学审慎地引导媒体介入医患纠纷,选择合适的介入时机,有助于更好地化解误会、解决问题[22]。媒体、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行为可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实现医患双赢[23]。
4.2 媒体主动合作
医院虽小,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大事。医院中蕴含着民生问题,也有家庭伦理的矛盾,有现实也有理想,有死的哲学也有生的心酸,有牺牲也有奉献……医院就是社会的缩影。
2014年上海市广播电视台和上海市卫计委合作,进驻医院拍摄新闻纪录片,先后播出两季《人间世》,受到广泛好评。该片聚焦医患双方面临病痛、生死考验时的重大选择,通过全景化的纪实拍摄,真实呈现了医生和患者的现实状态和困难,全方位地展现种种问题,通过换位思考和善意的表达,探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是面向大众的生命教育公开课,引发社会的共鸣和反思。“直面生死、直视问题、直击人心[24]”,既没有刻意美化医生,也没有故意抹黑医生,却引发观众的收视热潮,备受好评。这是一次医媒合作的成功尝试,既彰显了媒体的职责和使命,又为缓和医患关系起到很好的效果,开创了医学类传播报道的新模式。
《人间世》的成功除了媒体从业者专业、出色的工作外,离不开传媒界和医学界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也给医患关系的构建带来了启迪:医媒的良性互动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基础。媒体直接影响公众看待世界、认识科学。面对医学的风险和局限,要重建医患信任,首先是建立医媒信任,让医生不再害怕媒体。“只有医者敞开心扉,镜头才能充分呈现[24]”。
4.3 规范自身行为
开放合作的基础是信任,源自于医媒双方的自律和他律,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国家先后出台多部法律法规,建立了完整的监督体系,全方位地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制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以保障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而目前,尚没有专门规范媒体传播的法律,立法现状不符合媒体合法有序发展的要求[21]。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eonid Hurwicz指出:处于监督地位的监督者也需要被监督,其监督权应有所限制地行使。记者的职责在于挖掘事实,并传递给公众,而不是发动舆论审判[25]。媒体侵权往往会造成当事人的名誉受损和间接经济损失。因此,需要完善问责机制,明确失实责任,规范媒体报道医疗纠纷的行为,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职业操守[16]。
5 结论
因此,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媒体对医患矛盾的负面的新闻报道,对医患双方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因此负面报道传播速度极快,使其产生的消极影响迅速发酵,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如果想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得到媒体管理层的支持[26]。
总之,医媒关系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改善医患关系,首先应当改善医媒关系,建立开放合作的医媒互动机制。医患纠纷背后往往存在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守护健康需要医院、媒体、患者三方同心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