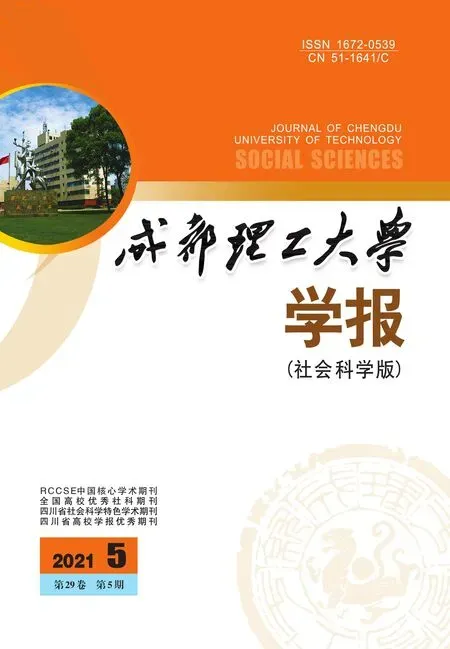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
——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唐佳红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合肥 230039)
历来关注嘉靖初年政局的研究者,都将目光集中在始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止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大礼议”之争,新继位的嘉靖皇帝在推尊乃父兴献王的问题上,与以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传统中枢官僚联合科道言官的文官群体产生了巨大矛盾,前者认为自己并非武宗之后,因此“继统不继嗣”,意图推尊其生父为帝;而后者则恪守传统儒家礼法,引大儒朱熹的“濮议”认为应以孝宗为皇考,不宜以兴献王为统。双方围绕“继嗣继统”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博弈,这场君臣之间的政治博弈以争夺礼制话语权为中心展开,深刻影响了嘉靖一朝以至整个明代后期的政治局势。一般认为,“礼议”之争实质是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人们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关于礼法和伦理上的争论,鲜少有人注意到发生在嘉靖初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之外的一个小插曲,即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中官崔文家人李阳凤违法事件所引发的大规模君臣冲突。与“礼议”不同,它是发生在法司、科道官与皇帝、宦官集团之间,以刑事司法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一场政治角力,从中引发的对司法体制与君臣伦理探讨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下于大礼议,其处在大礼议之争的大背景下,又具有其特殊的政治意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其看作大礼议之争引发的君臣群体对峙的一部分,对嘉靖初年政治及整个明代后期的司法体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李阳凤案的始末
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的这一起群体事件,首先是由当时内官监太监崔文的家人李阳凤等所引发,本文将其称之为“李阳凤案”。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内官监太监崔文家人李阳凤等,抵工部匠头宋钰,求贿不获,因以他事嗾文杖钰几死。事在法司,问未决,又为阳凤诉冤得旨,改令镇抚司讯理。”[1]748《世宗实录》记载该案较为简略,其实其中另有内情,由其引出的另一件案件更是该案的关键所在。据《皇明大政记》记载:“李阳凤者,太监崔文家厮养也,怙文宠,谋莞城卒,勒索工值。有身在宫所而巷伍又征役钱者,怨声载道,御史刘黼发其事,工部尚书赵璜又移文刑部,执李阳凤等鞫之。”[2]425据此这一案件同时牵涉到两件事,一是李阳凤索贿不成,殴打工部匠头的案件,二是李阳凤等人私自向工人勒索钱财等事,两事皆涉及李阳凤等人。这两件事的个中细节及联系,在时任刑部尚书的林俊关于此事的奏疏中披露得更为详细:
嘉靖二年闰四月十六日,该校尉陈贤赍捧驾帖,该太监崔文题,为分豁妄捏虚词陷害良善代伸私忿事,奉钦依:是,陈泰、曹浩、宋钰、张奉、宋铎、李阳凤、梁方、小陶儿,锦衣卫都拏送镇抚司,打着问的明白来说。钦此,钦遵。案查先为漏网余党挟雠,拨置内臣殴打公差人役事,奉本部送准工部咨。据作头宋钰告称,差委城垣工所,跟随委官陆员外,看工计料,有管工崔太监名下被革投充军匠李阳凤、梁方,时常向钰言说,要科敛铺户人等财物不遂,计禀崔太监,差写字小陶儿督领军牢,捉至工所,喝令重责二十五棍,以致内损伤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经行提李阳凤、梁方等到官,小陶儿、张奉未到。续为修浚城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黏送刑科抄出,巡视南城监察御史刘黼题:据牌儿头陈泰等呈称,自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年闰四月,每日拨夫十名,毎夫贴好钱五十文,交与夫头曹浩。随拘曹浩供称,崔太监分付五城,每日拨夫十名,每夫办钱五十文,打点管家及掌案李阳凤、梁方等用。等因题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黏送到司,查提问。[3]434
林俊的这封奏疏梳理了在中旨干涉该案前关于该案件的文移往来,转引了法司、皇帝及相关衙门关于该案处理的相关文件,并且将案件相关人员的供词一一陈述,让我们对该案的全貌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事情起于修建京城九门城壕的工部匠人作头宋钰因拒绝与督修管工、内官监太监崔文手下的李阳凤、梁方二人合作科敛附近的铺户,二人恼羞成怒,禀过崔文后,差写字小陶儿带领卫兵将宋钰打成重伤。案发后涉案人员被拿送法司鞫问,这一案件本应到此即告结束。但不料巡城御史刘黼又借机上奏,从牌头陈泰处讯得工夫夫头曹浩自嘉靖元年(1522年)四月该工程开工起,即按月向工夫索贿,办纳役钱。曹浩随即供称自己是受管工太监崔文指示,不得已盘剥工夫,将这些钱用于向李阳凤等人行贿。毫无疑问,这些钱最终应当为崔文私吞了。
自此从一件简单的伤害案件引出了隐藏于其背后的一件关于城垣造作工程的贪腐案,工科给事中胡汭上疏劾称,城垣工程经年不竣的原因在于“监工等官故延引岁月,干没钱粮”[1]731,崔文督监的工程中存在着的腐败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该案将作为工程监管的崔文卷了进去,使得崔文深感自身难保,因此向世宗求救,四月十六日,请得中旨,令锦衣卫将一干案犯“拏送镇抚司,打着问的明白来说”,将一干案犯移交镇抚司审问。从刑部的谳词并未将崔文描述为案首,且在审理案情过程中亦未传讯崔文来看,以刑部为首的法司考虑到崔文在当时备受世宗信任,本想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避免将事态扩大,并不打算深究到底。此外,崔文并非该案的直接参与者,他大可以将这一系列违法行为一并推诿给李阳凤等人,在刑部没有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最多治崔文一个管教不严、纵放家奴之罪。但镇抚司从法司处强行接手案件的行为则彻底触动了林俊等人的底线,在当时世宗与文臣集团剑拔弩张的大礼议之争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又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针对宦官和其背后的皇权的言官群体运动。
二、奉诏还是守法:林俊与明世宗的交涉
在世宗下旨将李阳凤案涉案人等全部由锦衣卫“挐送镇抚司打着问”以后,林俊即当即上疏表示“不胜惊骇”,并称“作头宋钰所告,及巡城御史刘黼所参李阳凤等拨置科敛等情事亦颇小。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凡大小罪犯,无不由之。锦衣卫谓之亲军,所以侦伺机密、察奸细;镇抚鞫讯大盗妖言”,林俊奏疏中称该案情事颇小,即从案情上而言,李阳凤案只是一件情节颇轻的伤人及私自科敛案,最多事关工部造作工程中贪腐问题,并不涉及妖言大盗等重大案情。再加上该案由工部提出,本已先请刑部案理,于情于理,都没有任何理由在案件审讯中途转交给镇抚司。他首先引用祖宗之法指出锦衣卫镇抚司有侵官之嫌,并将矛头间接指向嘉靖皇帝:“今不待法司问结,而辄付镇抚,是固臣等奉职无状,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废祖宗之法……伏愿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将李阳凤等付法司,从公究问归结;将臣等禠职,罢归民亩,以为法官失职之戒。”[3]434林俊该疏看似自罪,实则绵里藏针,将世宗置于破坏祖制、排斥忠臣的尴尬境地,企图借此逼迫世宗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在林俊于嘉靖二年四月十六日上此疏之前,还发生了另一件性质相近的案件,这一案件可以说是李阳凤案的前奏。四月十四日,林俊听闻“有户部主事罗洪载为因放粮,责打锦衣卫百户校尉,被奏送镇抚司究问,群校摧挫陵辱百端”,认为“锦衣鞫问事体非宜,恐有手下乘机报复之事”,请“别下都察院究问,庶法得其平,人无私议”,疏上以后,世宗回复“该衙门知道”[3]433,不置可否,照旧令镇抚司审问。这一事件的原委在《明世宗实录》中记载较为详备:
初,锦衣卫百户张瑾率校尉杨受等支俸粮通仓,横取狼籍,洪载捕受等,按其罪,事连瑾,瑾阳惧,求杖以脱罪。洪载不虞其绐己,卒杖之,瑾遂奏洪载擅笞禁卫官校,且以斋日榜掠人。上怒,令下狱考讯。[1]714
林俊上疏之后,时任户部尚书的孙交、吏部尚书的乔宇及众多科道官陆续上疏,“大小臣工疏十七上”[4]725,请世宗收回成命,下法司从公问拟。然而世宗最终以镇抚司“具狱词”,旨意“调罗洪载外任,张瑾夺俸三月”[1]715。尽管林俊等一众文官质疑镇抚司会挟私报复,因而提出了从镇抚司处取人以都察院案理,镇抚司拷讯犯人的方式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但站在嘉靖皇帝的角度来看,罗洪载私杖锦衣卫是事实,而张瑾违法亦不得姑息,因此世宗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办法,使肇事双方都受到了惩罚,可见世宗并未听信锦衣卫所劾罗洪载“擅笞禁卫官校”的一面之词,处理结果也并不能说太失公允。但这一结果显然无法抚朝廷众多文臣之心,因为在他们的立场看来,该事件完全为锦衣卫官挑起,责任不在罗洪载,他们多认为锦衣校尉不过为爪牙武夫,行事刻毒,折辱文臣,而“主事罗洪载罪遭惨刻”[4]506,纯属无辜。李阳凤案发生后,御史秦武即将两件事相提并论:“张瑾一卫士耳,李阳凤一役夫耳,侵害部属,牵制法吏。二臣力言,并不见听,事关国体,不可不慎。”[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明代文官集团从群体身份认同上,对身为宫禁环卫的锦衣卫已经存有相当的反感与偏见。此外,从处理刑事的专业角度而言,他们认为镇抚司不谙文法,只知棰楚,“夺法司之狱而下之镇抚,必奸佞之徒快私愤,复睚眦”[6]360;从个人职守而言,他们则以为锦衣卫“越介胄之职,侵刀笔之权”[7]1898,无法容忍禁卫之官借皇帝淫威侵夺法司权力;而从集体利益角度而言,他们认为镇抚司与宦官为一丘之貉,而文官素来与厂卫互不相能,因此在涉及双方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并不信任镇抚司可以从公问理。正如刑部主事杨永祐所说:“镇抚司平素受制内臣,承望崔文风指不暇,又岂敢直阳凤之罪以昭国法乎?”[8]688正是由于有这一次的经历在先,林俊又担心崔文“有所肤诉,或假手以济其私”[3]435,又或由于先前在罗洪载案上的受挫,导致其意有不平。基于种种原因,林俊此次与世宗据理力争,拒绝移交案件。
四月十九日,即林俊疏上三天以后,世宗即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回复法司:“宋钰、李阳凤等,还送镇抚司问。”[3]435收到圣旨回复后,林俊再次上疏坚持己见,与世宗针锋相对:“法者,祖宗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诏旨者,陛下一时之权宜也。奉诏少缓,罪止臣等一身。若守法少移,则负祖宗、负朝廷,得罪于天下后世矣。是故臣等宁冒违诏之诛,不敢废祖宗之法,以从陛下之命。”林俊首先将“诏旨”与“国法”置于对立的立场上进行讨论,并且以汉代循吏张释之自比,声称冒死不奉诏废法。并称世宗“夺取刑部见问之囚,付之镇抚司,以为解脱之计。恐此途一开,后有重大狱情,皆将扳求内降,以图幸免”,请求世宗“恪守成法,收回成命。将李阳凤等仍付本部或都察院从公问结,将臣等罢归田里”。林俊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彻底激怒了世宗,二十一日,他再次降旨强调前令:“宋钰等只照前旨,挐送镇抚司问。”并称“林俊等显是违旨,着回将话来”[3]435-436。世宗这一次回复声称林俊“违旨”,并令其回话,对一个四朝元老而言,可谓相当严厉。尽管他不太可能真的要追究林俊的“违旨”之罪,但已经传递了出一个信号,即世宗在这一件事情上态度坚决,绝没有让步的可能。一天后,林俊奉旨回话上疏,再次强调了“祖宗大法不可废”的观点,但较前两次的奏疏的语气已较为缓和:“其李阳凤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问,以正事体、公圣政。”并再次请求解职退休,试图作出最后一次努力。二十五日,世宗第三次下旨“李阳凤等只着镇抚司从公究问”[3]436-437,但放弃追究林俊抗旨不遵的罪责,最终李阳凤等人还是被移交,改送锦衣卫镇抚司狱接管。林俊感到“不安其位”,“以不得其职,乃上疏乞致仕”[9],在五次上疏乞休后,最终于当年七月因郭九皋案去职。
在林俊与世宗的三次交涉中,林俊皆以奉守祖宗大法的职责自居,坚持公案应由公法裁决,按照三法司的正常司法程序来讯理;而世宗则凭借自己一国之君的特殊身份,将个人权威加于国法之上,利用诏旨干涉国家司法程序,强夺法司之守。两相比较,尽管林俊在事实上更据有法理及舆论上的优势,但由于世宗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以皇帝旨意不可违抗为由强压林俊,坚持圣裁不容他人置喙,使得林俊最终不得不以乞辞自解,世宗也因而取得了对法司关于李阳凤案审理权的第一阶段的胜利。但这件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林俊上疏乞求解职后,更多的官员本着“极言直谏”的诤臣精神,掀起了一场延绵数月之久的抗疏运动。
三、明君之道——李阳凤案的深入讨论
事实上,在世宗驳斥林俊第一封上疏之前,除了作为刑部长官及这件行政纠纷案当事人的林俊抗疏与明世宗据理力争以外,尚且未有其他官员参与进来。而在世宗第一次回话仍旧强令刑部移送李阳凤等人至锦衣卫镇抚司后,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杨廷和、毛纪等人也无法袖手旁观了,他们当即主动上疏声援林俊,称嘉靖帝的处置恐使“法令不一,异议纷起,有伤治体,大为圣德之累”,请将“李阳凤等并陈泰等仍令法司一并问拟”[10]729。作为当时外朝文官集团的魁首同时也是朝廷宰辅之臣的杨廷和等人的参与,直接鼓动了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科道文官集团。尤其是在世宗第三次屈林俊之议,并且言辞之中颇有究问罪责的意思,致使林俊最终不得不称病乞休,更激起了言官集团的义愤感,他们认为世宗“因崔文一家奴之故,而简老成体国之臣”[8]161,有违明君之道。加之世宗在先前罗洪载事件上的处置失当,大拂文官集团之意,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使得众多官员深感他们心中的公共法理与儒家政治理想的沦丧。吏科给事中张嵩上疏称:“陛下误听太监崔文,夺取刑部见监犯人李阳凤等付镇抚司问,该部尚书林俊等执奏不发,陛下责其违旨,竟以夺之,臣工相骇,父老私议。”又质疑世宗给林俊的谕旨回复太过专断,难以服众,“且圣谕近又曰:着镇抚司从公问。是为俊等不能从公者乎?窃原圣谕不过欲遂崔文之计,而又不安废俊等执法之公,故不得已,姑为是少慰之词耳。岂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乞仍将李阳凤等付法司问,仍复还法司问拟。”面对文官们的诘问和请求,世宗仍旧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打官腔:“已有旨。该衙门知道。”[6]485-486
本着“法者,天子与天下共”的原则,自四月末开始,大批言官开始交章上疏指陈时事,先后计有“六科给事中刘济等、十三道御史王钧等、工科给事中余瓉等、五城巡视御史祁杲等交章论谏,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共八十人”[11],从六科到御史,几乎整个科道官群体都参与其中,李阳凤案引起的诏法之争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林俊与世宗相持的阶段,他们所争论的焦点还是法司职守是否当为皇帝诏旨所夺,林俊援引“祖宗故事”的目的也在于此,其与世宗的争执,究其根本仍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及行政职权上的纠纷。如果说在林俊与世宗周旋的第一阶段,双方尚且还围绕着李阳凤案的主审权展开,林俊最多只谈到世宗的要求是否符合祖宗所垂法统的核心价值观,其目的仍在为刑部对李阳凤案的主审权张本。而在主要由言官参与的第二阶段,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已经转移到世宗对内官的失驭及其对中旨的滥用上去了,自四月二十五日林俊上疏乞休后,翰林院修撰唐皋即上疏称林俊挂冠,世宗为一阉宦排挤一大臣,将有损于世宗的声誉,使世宗无以“自解于天下”。甚至称世宗“即位二年于兹,虽无武宗以来危乱之形,而有正徳以后灾变之大”[8]161,将世宗的行为上升到了“非明君所为”的高度。换言之,对李阳凤案的讨论已经上升到对世宗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明君之道”的政治道德层面了,这里所谓的明君之道,第一是继续林俊关于诏法问题的讨论,即皇帝不应以私意(中旨)破坏国法(尤其是祖宗法度)的守统思想,第二则是对君主亲贤臣、远小人的道德自觉的要求。
(一)中旨与国法之争
“夫所谓中旨者,必其纤毫无与于外廷,而突从内降者也。”[12]中旨是一种不经内阁、六科抄发而径自从禁中下发执行的旨意,具有极强烈的皇权专制色彩(1)。明代皇帝利用这种旨意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的侵夺,在三法司之外另外树立了一条法轨,这即是由皇帝、厂卫、诏狱构成的中旨司法体制(2)。世宗在处理李阳凤案时,径自以中旨干涉刑部司法程序,即招致刑部尚书林俊的质疑,他认为世宗以中旨助长镇抚司侵夺法司之守,破坏祖制国法,理不能容。而在面对科道官及文官大臣们的抗疏执论时,世宗所采取的方法便是以“该衙门知道”或“已有旨”来回应,这两句官话代表着世宗在朝廷公私事务上皆得独断的特权:皇帝个人的决定既不需要对臣下解释,而臣下更无资格质疑圣意。但在文官们看来,所谓的“已有旨”或“该衙门知道”,不过是皇帝无视群议,以旨意纵容内官环卫的借口,所以刑部主事杨永祐称:“陛下每曰知道了,而群小之胡为自如也。”[8]687兵科给事中赵汉则直言世宗借中旨为崔文脱罪:“夫谓已有旨,则文之罪不必诸人之再言;谓该衙知道,则文之罪已逃。”[8]681表达了对世宗以中旨独断专行,任意干涉国家行政的不满。时任南京工科给事中顾溱更是直言在这一事件中世宗对科道官的公正言论充耳不闻,甚至以诏旨压制群臣异议:
今也每见含糊,至于庄诵邸报,曰已有旨了、曰已有旨了罢、曰已累有旨了、曰已累有前旨了罢。甚至谏者之词稍或过直,有犯权势,则便着镇抚司知道、或便着回将话来。虽元老大臣,略不优礼,若此者不一而足。……故圣旨之颁,是是非非,惟求其当,焉以快人心而已。苟前旨之未当焉,则陛下速当俯从天下所请,以光圣治,可矣。[13]161
从顾溱的话中可以看出,朝廷上下之所以反对中旨干涉政务,即在于中旨之发,出自皇帝独制,多有欠缺考虑之处。臣下对皇帝的作为发出质疑,据理向世宗讨要说法,固然也在情理之中。而世宗应对臣工质疑,仅仅申言“已有前旨”,拒绝做出任何解释,以皇帝逞一时之快的旨意剥夺了大小廷臣对相关事务的参与权,这种简单粗暴的君臣互动关系,致使科道官集团在这一问题上与嘉靖皇帝的矛盾的进一步加深。李阳凤案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明世宗又借用几次刑事案件主动兴起数次与法司的“夺人”之争,这即后续的程景贵案、郭九皋案和刘最案(3)。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太监李昙等买卖私盐为廵检程景贵所发,“昙怒,诬之于东厂太监芮景贤,奏差官校逮系景贵赴京”[14],然而“程景贵已解都察院,俱改命送镇抚司逮问”[1]774,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都察院左都御史金献民、科道官刘济、汪思等陆续上疏请将程景贵交付法司,以免锦衣卫挟私报复,皆不报。七月(4),栾州民赵纪诬告临洮府知府郭九皋,东厂太监芮景贤奏闻世宗,世宗遂差官校解挐郭九皋至镇抚司审问。陕西御史刘翀认为厂卫无权在京外捕拿朝廷命官,“乞将赵纪、陶淳与九皋同解法司问理”[1]837,章侨等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亦言其事,受到世宗“轻率妄言”的严厉斥责[6]374。林俊疏言请世宗“勿与臣下争胜”,“将知府郭九皋提解永平府听理,将赵纪所吿事情选差刑部、锦衣卫官各一员,前去会同”[4]719,相比在李阳凤案上的戆直,林俊此次言辞已经十分恳切,但世宗仍旧不听,林俊心灰意冷,再次告休,科道官请世宗慰留,但世宗这次却爽快地应许其乞骸骨,林俊因此去职[2]48。同月,给事中刘最执奏“崔文以左道蛊惑圣心,糜费内帑”,世宗以刘最“不谙事体,率尔妄言”,判谪广德州,又称“崔文已有旨了,饶他”[6]694-695,明目张胆地左袒内官。如果说在罗洪载案上,世宗尚且还想维持表面上的一碗水端平,在刘最事件中,则已经公开利用内官来打压科道官了。前因李阳凤案世宗已屈众臣之心,此时又破坏了言官风闻言事的职权,给了言官们以极大的震慑。工科给事中卫道称世宗以“以文一人之故,既失一大臣,又逐一谏臣”,请“敕法司将崔文、李阳凤等通行提问,亟赐罢斥”。世宗的回复针锋相对:“朝廷设言官,务以指实具奏,不许虚词奏扰。刘最劾奏,事不以实,轻率妄言,回话又不认罪,姑从宽调外任,以称朝廷优容之恩。”[6]103世宗这一回应,否定了言官“祖宗以来,固已许之”的风闻言事的职权[14]162,等于彻底钳制住了言官之口。不久,刘最更遭重判谪戍。世宗利用中旨,假手厂卫、宦官等亲近内幸弹压士大夫的行为,已经相当昭然。刑科给事中刘济为刘最辩驳说:“最罪不至戍,且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何以示天下?”[15]2332但随着明世宗逐渐独握大权,刘最的命运“裁决于中旨”,已经成为了言官乃至整个外朝文官群体在嘉靖朝政治生活中的缩影。
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兵科给事中邓继曾以罗洪载案及李阳凤案以来的刘最案、郭九皋案、程景贵案等径出世宗独制,侵法司之官,皆不孚人心,称“近来中旨,多戾皇言,事不经考,文不会理”,请世宗凡“批答旨意及传奉事理,一以祖宗为法,仍命司礼监官送下内阁,据理度时”,世宗以邓继曾“言词忤慢”为名,竟命下镇抚司打问[6]437-438。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李阳凤案事发开始,世宗多以“有旨”应付文官群体的质疑,但从未对言官施以人身折辱,到此时竟以言事不当贬斥甚至刑讯科道官,可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随着林俊、孙交等人的相继去职,世宗力排众议,逐渐在与言官及其背后的法司大臣的对峙中占据优势。世宗在李阳凤案及其后续案件中掌握主动权,既在刑事事务上压过法司,取得了对司法权的专擅,使“法司几成虚设”,又彻底钳制住了言官,极大地强化了个人权威。明世宗取得与法司及言官围绕李阳凤案展开的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标志着他在这场与文官群体的“中旨与国法”之争中成为最终赢家,进而奠定了嘉靖一朝“朝廷之大事,皆出于中旨”的基本格局[7]1239。
(二)宸衷独断或是奸邪乱听:李阳凤案背后的“大礼议”
在参与抗疏的言官们看来,从世宗下旨取付李阳凤等下镇抚司到后来逼退林俊,导致“九卿灰心”的一系列行为,并非出自皇帝英明独制,而是受到了奸人如崔文之流蒙蔽的结果。杨永祐即称崔文等人“伺隙投间,首倡左道,蛊惑圣心”,“宫闱蛊惑君父,纵放家人,扼捥卿相,凡此皆人臣之大恶”。杨永祐甚至设想了崔文“蛊惑君父”的具体场景:“必崔文巧佞谮诉曰:‘陛下明旨,林俊且敢抗,故林俊不惟不得执法,且冒违旨之罪。’”[8]678-688工科给事中赵汉则言:“文之挟皇命拒人言以讳己罪,其为壅蔽可谓甚矣。”甚至说崔文“在能矫诏狱以制人,在能制尚书以回话,在能加言官以奏扰”[6]367,将之比于正德时的大珰刘瑾,已将崔文刻画成一个权倾朝野,欺君罔上的权阉了。
从时人的奏疏中,可见朝廷上下都将世宗在李阳凤案中做出的一系列“不合理”的举动,归因于崔文“恐奸贪败露而为脱免之计”[8]678,蒙蔽欺骗世宗所致。因此文臣集团很快将注意力从李阳凤案上转移开了,将主要矛头对准了本来只是居于李阳凤案幕后的崔文,并且将崔文视作诱导世宗不顾舆论非议,一意孤行的罪魁祸首。吏科给事中黄重言及罗洪载案及李阳凤案,即谈到世宗偏信奸邪,发出政令不谨,再请“崔文送法司惩治,以后左右近幸,不许妄进邪说”[4]540。可见在科道官的认识当中,崔文的主要罪责已经不在于纵容家奴科敛,贪赃枉法的刑事责任,而在于其“诱引变乱之罪”[6]485,即崔文在夺取李阳凤案的主审权上引诱世宗偏离法轨,变乱纲纪,导致君主有伤明君之德的政治伦理责任了。他们甚至将世宗所下的“可骇可叹之旨”归咎于“左右群小,耳不知书,身未练事,乘隙招权,弄笔取宠”所致[6]437,这是林俊被黜退之后科道官们所关注的焦点。总之,明代士大夫将一切罪责归于皇帝左右的奸佞,刻意将李阳凤案中的世宗书写为一个受到小人谗惑的君主。那么事情的真相是如何的呢?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到嘉靖二年(1523年)所处的广阔背景中考察,就能很容易发现李阳凤案背后的政治意涵,这与当时陷于胶着之态的礼议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史载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8]7795,崔文不过为一内官监太监,绝无能力亦无胆量左右“聪明天纵”且以权术闻名的明世宗的决定,更别说“矫诏以倾卿相”了。因此李阳凤案争端之起,一开始或许由于崔文之请,但之后的一系列举动,无疑都是世宗个人的乾纲独断,其目的无非在于借此打压在礼议之争中屡屡与其作对的文官,尤其是作为其辅翼的科道官集团。法司之首林俊即是大礼议之争中杨廷和一派的核心成员,《明史》记载:“俊数争‘大礼’,与杨廷和合。尝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礼,因辑尧、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条以上。”[15]这也就能解释何以在世宗下旨切责林俊时,作为外朝之首杨廷和等人率先出面声援林俊(5),并且称世宗听信小人之言,“岂一人之言可听,而众人之言顾不可听乎”[10]729?杨廷和的话一语双关,表面上指责世宗在李阳凤案中偏听崔文之说,而屈折林俊等人的骨鲠之言。但在当时礼议正酣的背景下,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已经至为明显,这与礼议中九卿大臣疏奏世宗“以一二人之偏见,挠天下万世之公议”[1]950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即暗指世宗在礼议中偏信张璁、桂萼等人的意见,而置持礼派官员的意见于不顾,试图借用舆情,站在道德制高点批驳世宗 “倒行逆施”的行为。杨廷和在这一关键时刻加入林俊所代表的法司阵营,既有着为林俊仗义执言的考虑,想必也有借此为礼议张势的意图。
如同持礼派认为“桂萼首倡乱阶,张璁再肆欺罔”[1]1007,世宗乃是“惑于桂萼之邪说”方兴大礼议,将张璁、桂萼等人视为奸臣、小人加以刻画一样,批判崔文也与之异曲同工。这是由于在儒家政治传统中,君父为尊者,臣子无权将罪过归咎于皇帝,在对皇帝提出批评的时候,往往需要构建一个为皇帝错误行为承担责任的“奸佞”形象,桂萼等人如是,崔文也如是。另外,攻讦崔文也是为了在谏诤过程中避免与皇帝直接冲突,“在君主专制制度下, 人们不敢将此归咎于皇帝,而把所有怨恨发泄到张璁、桂萼等人身上”[16],故而必须将这些“奸臣”作为代替皇帝的受过之人。在李阳凤案中,崔文便扮演了桂萼等人的角色,成为文官们攻击的对象。所谓“崔文之奸固结不去,何有于信任君子,屏斥小人”[6]510,其实这都是文官集团借此表达对世宗中旨不谨的批评,也是对抗世宗独断专行的委婉方式。科道官们之所以坚持要严惩崔文,其实即借惩治崔文以挫抑世宗,其具有的政治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李阳凤案本身的刑事意义了。
杨廷和出面参与李阳凤案的抗疏以后,朝廷上下立即开始对崔文群起挞伐,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否为持礼派策划的又一场集体诤谏,以扩张他们在正面礼议战场上的声势。刑科给事中张逵指称世宗在处理李阳凤案中听信谗言,“政事不关于宰执者非一,刑罚不行于贵近者甚多。台谏会奏,而斥为渎扰;大臣执法,而责以回奏”[15]5435。既黜台谏,又屈大臣,言辞十分激切,已经论及皇帝对内阁权力的侵夺问题,这种激烈的言论攻击正是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的深刻反映。对于文官集团的醉翁之意,世宗也了然于心,如同他深知言官指驳张璁等人的目的“非专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15]5520,其指驳攻击崔文也即意在“仇君”,指驳世宗破坏纲纪,政令昏庸。明人尹守衡谈到世宗在处理李阳凤等数案中所采取的态度时说:“上故英明,争臣持论,中或指斥太过,故上亦不乐。”[17]言官们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过激的言论让明世宗对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故“自刘最及继曾得罪后,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15]5463。后来的左顺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即由于言官与世宗在嘉靖二年(1523年)的种种冲突之中积怨已深。同时文官们试图在李阳凤等案上坐实世宗“倚信群小”,对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关乎对世宗政治决策的权威性和正确性的评价,将直接影响到明世宗兴起“大礼议”的正当性,明世宗也不可能做出丝毫让步,势必要与文官们相持到底,以至不惜屡兴诏狱与之正面相抗(6)。
因此,所谓的忠臣排斥阉宦、奸邪乱听只是这场斗争的烟幕弹,烟幕背后的真相是文官集团借该案表达对世宗的宸衷独断的异议,是嘉靖初年尖锐的政治矛盾的体现以及礼议之下君臣对峙范围的延伸。
四、结语
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年)的由李阳凤案引出的诏法之争,是明代各种政治矛盾纠缠的必然结果,并不能将它孤立地看作一次政治上的纠纷。第一,从司法角度而言,李阳凤案是明代长久以来司法危机的爆发。明代诏狱自创立以来,已使得法司深感职守被侵夺,再者,由于文官群体对厂卫群体始终存在偏见,对他们干涉国家司法本已难以容忍,所谓“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15]2329,正是当时文官集团对厂卫专权的政治心理的真实写照。因此,这是明代长期以来厂卫与法司之间的矛盾在特殊时期的集中爆发,由此引发了中旨国法之争。而这一矛盾的本质,是皇帝“凡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皆取诏行,得毋经法曹”[18]的中旨司法体制与“法为天下公共”的传统法律治理思想的背道而驰。文官们屡屡强调使用中旨是“政出多门”“法令不一”,甚至援引祖宗成法,其根本目的无非在于遏制长久以来皇帝以中旨干涉政务尤其是刑事事务的现象。而明世宗利用李凤阳案及其之后的一系列“诏法之争”达成了他的目的,保证了中旨作为皇帝诏令的权威性。同时在李阳凤等案上主动挑起镇抚司与法司的夺人之争,借此屈折三法司及其他以恪守法统自居的大臣,实现了其对生杀赏罚大权的稳固掌握,建立了一套由天子独领的“法外之法”。
第二,从时代背景而言,李阳凤案是“大礼议”下君臣角力在司法领域的继续扩大,是嘉靖初年君臣对立、政治矛盾尖锐的统治危机下,在司法领域内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在李阳凤案中,无论是杨廷和还是林俊、毛纪、孙交、乔宇、赵璜、金献民等朝廷重臣,或是刘济、张翀、邓继曾、赵汉、曹怀、李锡、黄重、王钧、祁杲等科道言官,我们都无法忽视他们在李阳凤案以外的另一重集体身份——他们都是“大礼议”中持礼派的核心成员。因此,李阳凤案实质上是世宗依靠宦官、锦衣卫等近习私人打压文官群体的一起政治事件,同时也是文臣面对压迫而做出的反击。由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持立场与礼议基本一致,故而对崔文的批判与礼议之争也相始终。林俊、孙交等人所以告休,其根本原因也并非世宗在这些案件上徇私,在李阳凤案发生以前,他们早有告去之意,如御史刘廷簠等所言:“乔宇、孙交、林俊同时召用,廷和、宇求去,此交与俊所以不安其位也。”[1]648李阳凤案的发生不过是一个契机,使“林俊、孙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19],进而推动了这一批持礼派核心大臣的下野。
因此,李阳凤案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具有两层政治意涵,它是明代司法体制及统治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考察嘉靖初年政治局势的崭新视角。
注释:
(1)今人对明代中旨的研究,可参见王晓明研究生论文:《明代中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19年。
(2)有学者评价这种中旨司法专制体制“在于君主僭越于制度,对于执法权的掌控……有此制度上的设计,君主置一切罔顾时,可以牢牢假此掌控士夫,这是有明一代专制秘钥之所在”。参见任文利:《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
(3)明世宗借刑事案件实现自己个人政治目的手段并非其偶然为之,而已成为他的一种惯用手段,这一点可以参见他对嘉靖五年李福达案的处理。参见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明史研究论丛》,2007年。
(4)该事件《明世宗实录》虽然系于嘉靖二年十月条目之下,但事实发生的时间当在七月上旬,这一点从谈及本案的奏疏集中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因此误系该案于十月。
(5)杨廷和等人的奏疏发于四月,其中只论述到世宗第一次还旨命李阳凤等人“还送镇抚司问”的事情,可见该疏上于四月二十一日之前,为可见奏疏中最早支持林俊者。
(6)关于张璁及杨廷和等人的立场是非问题,可参见田澍;《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1期;张立文:《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