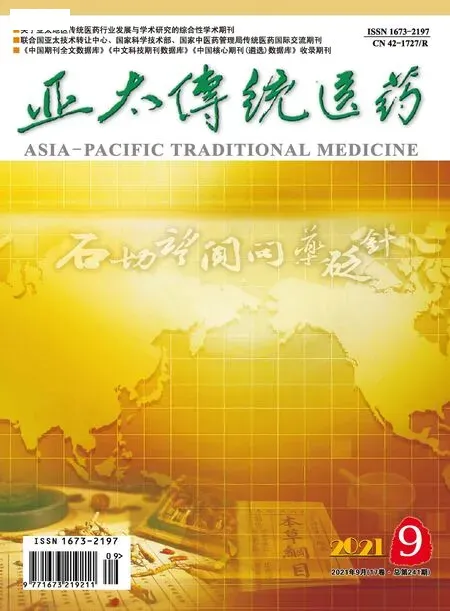中西医对调节肠道菌群与慢性肾脏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张 广,罗富里,董必成,吴国庆*
(1.永康市中医院,浙江 金华 321300;2.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4;3.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 南昌 330004)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中医称为肾衰病,慢性肾脏病在我国患病率为8%~16%,总患病人数超过1.2亿人,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现代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在慢性肾脏病的发生发展及治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肠道菌群失调表明益生菌减少、条件致病菌增多,通过免疫、微炎症等途径影响肾脏衰竭的进展速度,是中、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尿毒症期的高危因素之一。
中医将慢性肾脏病病机归结为虚、湿、瘀、毒[1]。肾病日久由虚入损,脾升清降浊失调,肾藏精泄浊障碍,最终导致脾肾阳虚,脾肾阳气不足,三焦输布失利,膀胱气化失司,水湿运化不畅,日久瘀滞血脉,导致湿瘀互结,浊毒化生,故慢性肾脏病病位在脾肾,而“脾”的运化和抗毒功能与肠道菌群对机体代谢、免疫等功能的作用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这与“肠-肾轴(gut-kidneyaxis)”和“慢性肾脏病-结肠轴(chronickidneydisease-colonicaxis)”学说相互印证。
1 肠道菌群与慢性肾脏病相关性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排泄、免疫器官,也是最大的储菌库及内毒素池,其内储藏大约有100万亿微生物,这些庞大的肠道微生物构成肠道菌群,形成肠道微生态的动态平衡,参与维持肠道黏膜组织学与解剖结构的完整性。肠道菌群与人体的关系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益共生的,人体为肠道菌群提供寄居场所,肠道菌群参与人体的消化吸收、能量代谢、免疫调节等生理活动[2]。其中益生菌可合成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促进肠道蠕动及食物的消化,为人体提供营养和能量,还能抑制致病菌群的生长并分解毒害物质,对于人体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致病菌大量繁殖时会产生致癌物等有害物质,使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引发多种疾病[3]。中性菌有双重作用,在生态平衡状态下,对人体无害,当肠道菌群失调时,可致病。根据研究显示,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十二指肠及空肠内的肠道菌群数量远超过正常人群,大约含有106mL好氧菌和107mL厌氧菌,好氧菌约为正常人的100倍,致病厌氧菌数量也明显增加,而一些益生菌群却在减少,如乳酸杆菌、普雷沃氏菌、双歧杆菌等[4]。
肠道菌群在人体健康状态下始终保持动态平衡并与人体相互依存、相互抑制、相互竞争,参与人体的一些代谢活动,如降解难消化的植物多糖,促进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合成维生素B、维生素K和氨基酸等[5]。并且,肠道菌群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有效降低人体对事物的过敏度。同时,肠道菌群可修复肠上皮细胞,包括诱导热休克蛋白表达、上调黏蛋白基因、竞争性抑制病原菌、分泌抗菌肽、抑制肠道炎性反应等[6],形成天然的肠道屏障,维持肠道的结构与功能。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与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当肠道的这种平衡被打破时,便可引发疾病,而疾病的发生发展病情变化亦可导致肠道菌群发生变化。
慢性肾脏病如今已经为全球健康问题,发病率日益增长,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紊乱加快慢性肾脏病的进展,伦恒忠[7]、戴铭卉[8]、黎志彬[9]等实验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能量摄入、营养支持、代谢平衡、炎症、神经激素反应及免疫系统发育和免疫调节中有重要作用。罗学文[10]、杨桂莲[11]、陈靖霖[12]等临床研究证实当患者肠道菌群发生改变,其肠黏膜屏障功能改善、代谢毒素尤其肠源性毒素硫酸吲哚酚、硫酸对甲酚水平下降,肾功能得以保护,各种研究皆证明通过经肠道治疗调节肠道菌群可对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肠道菌群产生影响。
2 肠道菌群失调与慢性肾脏病相互作用的病理机制
2.1 肠道菌群失调影响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肠道屏障
肠道屏障主要包含生物屏障、机械屏障、免疫屏障和化学屏障,可以使营养物质进入到血液内,也可防止有害物质进入组织、器官及血液循环,在人体代谢、免疫功能及营养方面有重要作用[13]。当肾功能受损,水溶性、不与蛋白结合的小分子毒素、中分子毒素、蛋白结合性尿毒素不能通过肾脏排泄,大量蓄积体内,其中蛋白结合性尿毒素来源于食物,属于肠源性尿毒素,可促使肠道屏障的破损,包括绒毛的高度改变、隐窝的延伸、固有层与炎症细胞的渗透、肠壁水肿、肠道缺血及结肠上皮屏障破坏[14],使其通透性病理性增加而成为“渗漏性肠道”,患者可在无临床感染的情况下表现出全身微炎症状态,出现内毒素血症[15]。而通过中药调控肠道TLRs/NF-κB信号转导通路,可减少循环中的肠源性毒素LPS、IS,修复肠道屏障功能,从而延缓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减轻微炎症反应,达到保护肾脏的作用[16]。
2.2 肠道菌群失调影响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内毒素代谢
尿毒症毒素除了甲状旁腺素、β2微球蛋白尿素和肌酐等中小分子毒素,还有肠源性尿毒素,肠源性尿毒素大多来源于食物中的蛋白质或含氮物质,由经肠道菌群腐败作用及体内转化生成。正常情况下肠源性尿毒素也经肾脏排泄,但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不足以排泄体内过多的肠源性尿毒素,致使毒素蓄积在体内,患者因此处于一种高毒素状态,长此以往,高毒素状态将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进展和发生,如尿毒症脑病、心力衰竭等。其中硫酸吲哚酚(IS)和硫酸对甲酚(PCS)目前最常见、研究最多的肠源性尿毒素,通过对IS、PCS含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在毒素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当IS、PCS过多时,其很难被透析治疗所清除,可持续损伤肾脏上皮细胞,诱导肾间质纤维化,并促进氧化应激和微炎症[17],能加速肾功能下降。
2.3 肠道菌群失调与炎症反应
微炎症并非是微生物或寄生虫感染引发的炎症反应,而是肾衰竭导致的各种并发症缓慢进行性发展,是一种非显性炎症状态,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急性时相蛋白明显升高和炎症因子相对升高的表现。具体表现为炎性介质、细胞因子的活化,可通过对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激活来诱导炎性反应的发生。与微炎症状态的相关因子有很多,现在研究较多的炎性因子主要是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正五聚素蛋白3(PTX-3)等。大量临床研究已证实CKD的发生与患者体内微炎症状态有密切联系,具体表现为CKD患者具有较高炎症因子水平,同时炎症状态会通过加重微血管损伤进而提高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18],加重患者病情。肠道就是微炎症的源头,菌群及其代谢物皆可参与微炎症反应,当肠道微生物的生态平衡紊乱时,可产生大量内毒素并诱发宿主发生炎症反应,内毒素还可通过血液循环诱发肾脏发生功能障碍。
2.4 肠道菌群失调影响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免疫功能
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包含免疫诱导组织和免疫效应组织两部分。免疫诱导组织由肠道相关淋巴组织构成,包括小肠派尔集合淋巴结、孤立淋巴结、结肠补丁以及肠系膜淋巴结,其中的淋巴滤泡发挥免疫诱导作用。上皮细胞层和黏膜固有层构成免疫效应组织。黏膜固有层内有大量的T细胞、B细胞、IgA源性浆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等,这些免疫效应细胞是肠道黏膜免疫系统的主体[19]。而肠道黏膜固有层内存有很多辅助性T细胞及调节性T细胞,辅助性T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能够有效地防御细菌和真菌的感染。而调节性T细胞与肠道内肉毒杆菌诱导的免疫逃逸和免疫不应答相关[20]。同时,肠道黏膜固有层内还有IgA源性浆细胞产生大量分泌型IgA,它附着在小肠内分节丝状菌上,并与细菌、病毒和毒素等相结合,在肠道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患者肾功能受损,肠道毒素增多,菌群失调,T细胞、B细胞、IgA源性浆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减少,肠道屏障通透性增加,蓄积体内的毒素和细菌可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单核巨噬细胞系统被激活,大量细胞因子、炎症因子、氧自由基等细胞有毒物质释放,不仅激活肠道黏膜的免疫系统,还加重肠道菌群失调,加重全身性微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调通过影响人体免疫功能、肠道屏障、毒素代谢及微炎症加重慢性肾脏病病情,但现代医学在调节肠道菌群方面尚缺乏相关研究,中医治疗该病优势独特,当慢性肾脏病患者出现肠道菌群失调时,根据人体出现的消化道症状、心血管病变以及内分泌失调以及神经系统症状,中医辨证分析不难发现肠道菌群对慢性肾脏病的影响,病位在脾肾,病因在于伏毒内蕴,而这也印证了慢性肾脏病脾肾学说、伏毒学说,奠定中医药调节肠道菌群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理论基础。
3 基于肠道菌群探讨慢性肾脏病中医理论
3.1 脾肾学说
脾肾学说缘于《黄帝内经》与《难经》,后世刘征堂[21]详细地阐述了脾肾相关理论。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化生血气,为后天之本,肾藏先天之精,为生命之源,是先天之本,脾肾为先天滋养后天,后天补养先天,其与机体的免疫功能和营养状况息息相关。脾的运化有赖于肾的促进,肾所藏之精有来于脾的水谷之精培育,故二者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脾肾两脏病变亦可互相传变。肾阳亏虚,则不能温煦脾阳,或肾主水失常,水湿泛滥,损伤脾土;脾虚失运,无力化生水谷精微以滋养肾脏,无力运化水湿则水湿内停,影响肾主水的功能。肠道菌群失调造成肠道功能失调,从中医学角度病位主要涉及脾胃,是脾虚证的生理病理表现[22]。肠道微生物与中医学的脾胃关系密切,从脾胃调节肠道菌群,有助于肠道生态平衡状态,可达到治疗慢性肾脏病的要求。这与现代医学“肠-肾轴”“慢性肾脏病-结肠轴”学说相契合,其理论核心主要是指肠与肾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肠道通过物质代谢调节肾脏功能,延缓CKD发展,减少或延缓CKD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而肠道菌群失调则可导致尿毒素蓄积和诱导全身性微炎症反应等加重肾脏的损伤,阐述了肠道微生态变化与CKD间的关系。刘名波[23]实验研究发现,属脾虚证的小鼠肠道内的肠杆菌、肠球菌数量均明显升高,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拟杆菌数量明显减少,这直接证明了脾肾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
3.2 伏毒学说
伏毒[24]是指外邪入体伏而不发或内生毒邪潜藏于脏腑经络形体官窍,蓄积日久而发病。肠道菌群失调导致人体免疫、代谢等功能障碍而致使慢性肾脏病进行性加重过程往往时间较长,这与中医的伏毒的病变过程如出一辙,伏久发病。慢性肾脏病中虚为本,“湿、瘀、毒”为标,同时“湿、瘀、毒”既是病理产物也是致病因素。湿、瘀、毒是内生毒邪,也就是伏毒,它包含现代医学中的肠源性毒素,是直接影响肠道菌群失调的原因之一。伏毒产生与正气不足有关,但它们的存在又促使正气耗伤,致使正气更虚,邪毒更胜,日久体内中湿毒(如代谢废物肌酐、尿素氮等)不能及时从体内排除,使得“湿、毒”等有害毒邪蓄积。内生伏毒往往始于微而成于著。若正邪尚能抗伏毒,则邪正相安共处,伏毒潜留;伏毒内积,不得化解,酿郁成毒,消耗正气,损伤肾脏功能,导致伏毒出路受阻。因虚生毒,毒邪伤正,虚毒互为因果,量变生质,久病入肾,久病致瘀,伏毒藏匿肾络,肾络瘀血不化,化为瘀毒,瘀中蕴毒,毒中含瘀,瘀毒相织;瘀毒、湿毒伏于肾脏,肾络受损,脏气更虚,加速肾纤维化进展。上述乃内生伏毒致病。
4 基于调节肠道菌群探讨中医药对慢性肾脏病的治疗研究
虽然中药的组分和作用较为复杂,但通过对肠道菌群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中药的作用机制。Zeng等[25]通过焦磷酸测序、RT-PCR分析发现,对5/6肾切除大鼠肠道,予以大黄素结肠灌洗,能有效降低尿素和IS的细菌丰度,从而改善肾功能。曾玉群[26]通过大黄灌肠对CKD大鼠模型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证实大黄灌肠可延缓CKD进展,其可能分子机制主要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主要包括调节肠道菌群主要增加双歧杆菌益生菌的数量、恢复固有黏膜蛋白claudin-1、occludin,减少内毒素LPS水平,降低CKD状态的尿毒素IS生成,缓解CKD的系统炎症,进一步改善肾功能、肾脏炎症氧化应激及肾纤维化。Du等[27]和Tao等[28]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法(UPLC-Q-TOF/MS)发现使用黄蜀葵花提取物、山茱萸提取物可减少内毒素水平。
结肠透析是充分利用结肠生理学特性发展而成的结肠透析技术,以人体自身的肠壁作为天然的透析膜,模仿腹膜透析的原理,将透析液或者中药灌入患者结肠内[29]。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医学,基于中医通腑泄浊法,中药或透析液经肠道给药,药液可随气血津液的运行散布全身达到整体治疗作用。经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药结肠透析已被列入慢性肾衰竭中医临床路径,并且与国际防治慢性肾脏病的“肠-肾轴”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临床实践中具有显著的疗效。目前,慢性肾脏病与“肠-肾轴”理论的研究处于阶段,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预示着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虽然目前相关研究还不够全面,但毋庸置疑结肠透析具备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5 总结与展望
慢性肾脏病是缓慢性、进行性、不可逆性的疾病,目前为止,现代医学尚无特异性药物治疗,中医药根据中医理论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患者代谢功能、免疫功能及微炎症状态,从而延缓肾脏功能下降的过程,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迟患者进入肾脏替代治疗的时间,提高患者寿命,这对治疗慢性肾脏病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望今后可以通过分子生物学、代谢组学、生理病理学等多学科来解释肠道菌群与慢性肾脏病的关系,为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病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