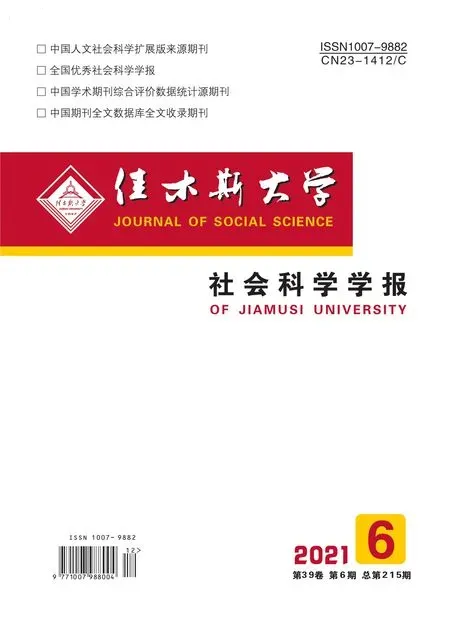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传统与变迁*
杜 洋
(东北石油大学 艺术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社会发展、文化置入、民俗意味,总是伴随于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之中,赋予生活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区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及族群生命以不同程度的关怀与眷顾。作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区重要的非遗存在,代表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深深涵化于杜尔伯特蒙古族文化生成与延续当中。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是蒙古族文化的具体呈现,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宝库中民间传统艺术的沉淀,更是传统文化变迁中民间艺术不断生长的支撑。深入认知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不仅说明了其研究意义的阐释,亦明确了其现存的生存态势,是为杜尔伯特蒙古族后代给予深层族群认同感的“高级”方式。
一、有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相关叙述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年来一直以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为重点,以深化民族艺术体制为发展动力,在音乐艺术的创新与传承方面始终坚持传统与变迁中不断融合的构建方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多年来艺术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大力强调极富本土特色的音乐类遗产,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给予当地人们以不同程度的肯定,是人们茶余饭后文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尔伯特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音乐类非遗所属中国传统音乐概念内的少数民族音乐体系。传统化体系中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体系包容于东方音乐体系框架之内,调式音阶属中国传统五声调式。在调式安排上,主要以羽调式为主,其次调式常用的是徵调式,角调式和其他调式偶尔也会使用,但是较为少见。蒙古族音乐旋律有其自身的代表性特点,均是以级进为主,在音程的跨度上经常出现四五度跳进,甚至六度、七度、八度以上大跳也很常见。[1]可见,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形态自由且可延伸发展,音乐旋律中总是透着某种“单纯性”。
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历史溯源并不十分久远,在遗产生成、延续过程中,其发酵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陈毓博、任广明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通过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相关文献的汇总,从仪式音乐、民歌、曲艺、器乐和音乐文化融合几个方面整理出对杜蒙蒙古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几个要点和相关文献的若干内容”[2],侧重于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的整体叙述。邵萱的《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一文中,在内容安排上主要侧重于对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田野考察研究,通过分析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共融关系,分析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3]赵月梅的《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地区的“蒙古四胡”艺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四胡”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包杰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蒙古四胡”所生存的艺术现状,对杜尔伯特蒙古族国家级非遗“蒙古四胡”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保护对策进行了阐释。[4]除此之外,刘喜宝、王鑫的《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关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建设的调查》一文中,介绍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为有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非遗的生成与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文化背景,为弘扬及发展所属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民族文化给出了三点建议。[5]
参考相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探讨脉络,相关资料中的论及方向并非从非遗的角度进行考虑,在有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涉入性提及中,多是对其音乐文化的总体综述,可见有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研究只是这一区域内音乐文化大框架范畴内的潜在性涉及,可谓是简单而“浅层”的探讨。因此,本文将跳出原有研究范畴,以一种较明确的形式对杜尔伯特蒙古族代表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深度考量,遗产内容中不仅有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国家级代表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有所属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黑龙江省省级代表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大庆市市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明确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透过其变迁明确其留存,在社会变迁、文化变迁、民俗变迁背景中对其进行描述,以思量其传统范围内的认同应在哪些“外力”的助推下才能够得以延续。
二、游走于民间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
(一)代表性国家级音乐类非遗项目
2008年3月,杜尔伯特“蒙古族四胡音乐”被批准为黑龙江省第一批省级非遗名录,6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8年6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江湾乡永丰村包杰被评为第一批黑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包杰“升级”为“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国家级传承人。在杜尔伯特地区,早于元代就已有“蒙古四胡”的出现,“蒙古四胡音乐”在漫长的杜尔伯特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着传统的变迁与变迁后的创新,杜尔伯特“蒙古族四胡音乐”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区域风格在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
杜尔伯特蒙古族四胡是杜尔伯特蒙古族地区所特有的弓弦乐器,别名“胡日”“四弦”“侯勒”和“胡儿”,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每个个体与族群之间较常见的乐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把四胡,属于蒙古族的特色乐器之一,现如今已成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杜尔伯特蒙古族四胡音乐,主要反映了居住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牧民们的生活形态,展现了杜尔伯特蒙古民族音乐特有的艺术韵味,蒙古族四胡主要有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之分。杜尔伯特蒙古族四胡音乐的演奏者熟练操作四胡,具有深厚的艺术文化感知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对音乐具有超高的情感共鸣。不同的演奏者,往往对曲子的理解力截然不同,鉴于演奏形式之不同,观众往往感受到的音色必然存在某种差异。杜尔伯特蒙古族低音四胡常用被用于伴奏蒙古族演唱及好来宝,音色柔美和谐,且深沉动听,代表性曲目有《八音》《八音梆子》《赶路》等。杜尔伯特蒙古族中音四胡不同于低音四胡,音色更加圆润且清爽明亮,不仅可以用来伴奏,也可用于独奏,常与高音四胡、马头琴等乐器进行合作演奏,代表作品有《阿斯尔》《老八板》和《蒙古八音》等。杜尔伯特蒙古族高音四胡音色清脆,音量较大,主要用于独奏、重奏和合奏等形式,代表作品有《花腰调》《诺恩吉雅》《欢乐的草原》等。
(二)代表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
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6月正式批准被列入黑龙江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11年,包文章被评为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振军,作为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文化馆副馆长,多年来一直系统的学习蒙古族长调音乐和短调音乐,在蒙古族民歌的演唱方面始终坚持着自己特有的演唱风格。包文章及杨振军,在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的音乐中渗透着蒙古族元素,二人坚持着对蒙古族民歌的热爱与瞻仰,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以最积极的热忱在进行着遗产的传承与延续。
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现已成功被列入黑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之一,以其独特的演唱方式与极具民族特色的乐器相结合充斥着浓厚的蒙古族草原化气息。杜尔伯特人民根据其所居住的社会环境不断地与区域文化加以交流并整合,最后形成了浓厚鲜明特色的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音乐。取材范围广泛,格调氛围雄浑,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一般分为“长调”和“短调”。杜尔伯特蒙古族长调,篇幅较长,气息宽广,情感沉郁,具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式表达。而杜尔伯特蒙古族短调则篇幅较小,曲调紧凑,节奏和节拍相对限定化,歌词简单,更像是一种即兴歌唱,演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声音洪亮深沉,曲调高亢悠扬,充分展示了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开朗爽快的性格。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创作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爱情友谊、山川草地等体裁内容,较为著名的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有《桑塞玛》《辽阔的草原》《牧歌》等优美动听的代表性作品。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以当地民间文化内容作为创作题材,较为真实地描绘了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的风俗生活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早于1987年,便出版了流行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区民歌的《杜尔伯特蒙古族传统民歌集》,其中收录了民歌共计96首,涵盖内容较广,包括宗教习俗、婚丧嫁娶、祝酒宴会、劳工生活、思乡念亲、歌颂英雄等内容,构成了杜尔伯特蒙古族优美的民歌文化。
(三)代表性市级音乐类非遗项目
2018年,经大庆市市政府批准,大庆市文广局确定,大庆市非遗专家评议小组、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有关第五批大庆市市级非遗名录共计17项。传统音乐类项目两项,其中一项为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杜尔伯特蒙古族“马头琴音乐”作为入选市级非遗传承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包洪声(蒙古名阿斯汗),就职于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歌舞团,黑龙江省省级马头琴代表性传承人,中国第五代马头琴代表性传承人。白青山(蒙古名阿古拉),杜尔伯特蒙古族马头琴音乐青年演奏家,现就职于杜尔伯特蒙古族歌舞团,马头琴首席。
杜尔伯特蒙古族市级非遗项目马头琴是一种两弦乐器,梯形长琴身,马头形状雕刻的琴柄,根据这一特色被称为“马头琴”,别名“潮尔”。马头琴与四胡在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心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头琴与四胡的发展轨迹与流行范围几近相同,同属于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乐器项目。二者亦有区别,首先是具有不同的外形结构,音色自然存在着一定的明显差异性。马头琴具有声音圆润,低音荡气回肠,音量弱的特点,演奏的曲目通常是气韵粗狂而宽广的。马头琴音乐在杜尔伯特蒙古族是区域音乐特色的彰显,经世代演变与传习,马头琴音乐已建构了属于本土特色的演奏方式,且逐渐有了属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一套系统演奏法。马头琴音乐擅长演奏杜尔伯特蒙古族长调音乐,马头琴的传统乐曲大部分是根据草原生活的蒙古族民歌改编而成的,以反映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情景及生活环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深受杜尔伯特乃至全国人们的喜爱。杜尔伯特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的演奏方式主要分为独奏、伴奏、重奏及合奏,演奏形式较为多样化。在现代文化的变迁与冲击下,传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演奏在维系传统内容的基础上,逐渐融汇了现代音乐形式、音乐类型,创作方式更加多样化、丰富化。杜尔伯特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著名的代表作品:《水灵》《八音》《欢乐的牧场》《秋雁》《乌利格尔叙事》等。除此之外,还有包洪声(阿斯汗)与多兰桌格共同以黑龙江扎龙境内的珰奈湿地为创作背景,基于回归湿地大自然美的意蕴,融合当地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创作了马头琴曲《女神湖》。
三、变迁中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21个民族,其中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8.2%。不同的《蒙古秘史》以不同的形式记载着关于杜尔伯特蒙古族的迁徙史记,早见于年成书的「蒙古」策·达姆丁苏荣蒙文本《蒙古秘史》称“都蛙锁豁儿有四子,都蛙锁豁儿死后,其四子对朵奔蔑儿干不以亲叔来看待,弃而迁之,成为杜尔伯特氏。”巴雅尔蒙汉合壁卷本《蒙古秘史》记为“朵奔蔑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有四子,同住的中间,都蛙锁豁儿死了。他的四个孩子,将叔叔朵奔蔑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离去了,做了朵儿边姓。”[6]在蒙语里,杜尔伯特意译为“四”,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道布莫尔根之兄道蛙锁豁儿有四个儿子,因此被称为杜尔伯特氏,世代传承。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是黑龙江省唯一一个以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的自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历史悠久,清初时期,清顺治五年,将杜尔伯特部改为杜尔伯特旗,隶属哲里木盟,此时期隶属于黑龙江省管辖;民国时期,1927年设置泰康设治局,1946年4月,旗和县分设,泰康县政府驻泰康镇,同年5月,改由嫩江省管辖,1949年5月,撤销嫩江省,划归为黑龙江省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1954年8月,改属新设之嫩江专区,到1992年8月21日,杜尔伯特蒙古族划归为大庆市领导,是清代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由额尔齐斯河畔迁徙布多北境,当前已迁徙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2001年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包含4镇、7乡。现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黑龙江省的西部,北邻林甸县与齐齐哈尔接壤处,东靠大庆市,南临肇源县,总面积高达6054平方千米。在历史长河的推进中,历史变迁,所属杜尔伯特蒙古族的音乐类非遗在历史进程中生成、发展,不断寻找着未来可得以认可的某种延续。历史变迁的推动,使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在历史长河中分散且留存。
秦汉时期,汉族人民向黑龙江省迁徙,黑龙江地区有了汉族文化,与中原进行频繁的人文交流。清王朝时期,大量人民被驱逐黑龙江流域这种极寒冷的荒地地带,众多人们为了生计开始狩猎、淘金等活动,并以此谋生。时至清末,更多流民例如像来自于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等地的人民闯关东迁徙到了黑龙江省流域,汉族人民的迁入,使得蒙汉两族之间在物质文化、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方面开始相互结合,为黑龙江省流域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形成给予了充分的参考。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迁徙至黑龙江省流域,原本只是使用蒙古语言的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在汉族人民的同质下使得汉语对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族人们的音乐依赖于语言文化,汉语势必对杜尔伯特蒙古族的音乐类型产生了较大范围内的交融和影响,逐渐产生了蒙汉两种语言交叉演唱的形式,即“风搅雪”的艺术形式,例如在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划拳》中便是如此。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形式已无法满足蒙汉民族的融合,文化形式在变迁中总是寻求某种中和,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变迁是随着文化环境的某种迁移而逐步完善的。文化的变迁,同化了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存在。
历史变迁、文化变迁,无不使得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在不断的“汉化”边缘中危险地存活着。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在生活中总是将音乐艺术放置于较高的位置,不管是从乐器的角度考虑,还是民歌的角度涉及,音乐艺术总是伴随着杜尔伯特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然而,在“汉化”影响下,使得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项目出现了“走样”和“变味”的倾向。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代表性国家级项目“蒙古四胡音乐”为例,国家级传承人包杰作为一位朴实本分的农民,其所有的工作重心还是农间耕作,因此在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上难以给予充分的考虑和思量。在不同民族的融合下,语言环境、民俗环境、教育环境皆发生了质的变化,杜尔伯特蒙古族的音乐类遗产在严重丧失母语的环境下,受众环境的积极性并不乐观。
四、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未来发展的思考
根据上述所论,人们的交通工具越发便利,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整个社会的个体与群体间相互流动广泛,杜尔伯特各民族或者族群之间开始学习汉语,这在促进区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杜尔伯特蒙古族的文化特性,使得杜尔伯特蒙语的使用环境氛围逐渐降低。那么,对于杜尔伯特蒙古族人们来讲,讲蒙古语进行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依赖于蒙语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势必会收到重大创伤,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技艺失传的危险,甚至有些音乐技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离开了人们的视域。因此,国家范围、社会范围、民间组织、教育范畴当前皆应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未来发展问题加以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为保护中华民族留存于人们的共同的人类财富做出积极努力。
首先,国家范围不仅要在相关法律范畴内为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驾护航,而且还要做到“快准狠”,发挥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积极寻找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可传之人,在保证传承人家庭温饱的基础上,对传人给予某种激励机制,提供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倡导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活动中来。现今,杜尔伯特蒙古族文化传承积极性较低,包括蒙古族本族人民,对汉语的学习激情高涨,所以十分容易忽略蒙语的魅力与特色。国家层面,可在广播电视、影视广告中普及蒙古族音乐,以便于更多人能够接触到独具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促进非遗文化与本土经济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经济势头为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带来的优势,设置相关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播放剧场等,以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演绎杜尔伯特蒙古族的特色文化、民俗风情、人文情怀、音乐技艺等。
其次,对于社会范围来说,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区域内推动民间文化、文艺活动是广泛宣传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中的个体、群体等应积极搜集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相关文物、可参考资料,合理有序的进行相关社会活动的安排。强调杜尔伯特蒙古族区域社会文化活动,有助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社会需求和娱乐需求,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产业以扩大本土文化的社会传播范围。同时,社会层面应设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公益非遗协会,以促进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全面发展与保护。社会组织可建立相关社团,不同的参与人员应具有不同的工作分工,不仅要深入探究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非遗的相关文化、史记等整合内容的问题,还应深入学习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培养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精通杜尔伯特蒙古族乐器和乐理,定期开展相关民歌演唱活动,在社会范围的协助下扩大主动学习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人口总数。
另外,重视民间组织对于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重要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其中的民间组织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社会群体或者由人民自由组织起来的一系列群体民间组织。杜尔伯特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民间,且扎根于民间而生存,对民间组织来讲,给予非遗于充分的保护是其自身使命与责任感的体现。民间组织应精心设计排练音乐类非遗项目的相关民俗活动、音乐演奏,精湛的技艺表现能够充分感染杜尔伯特蒙古族群众们保护遗产的情绪与心情。充分调动普通百姓参与拯救杜尔伯特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唤醒普通大众对稀缺音乐类文化遗产的兴趣,营造浓厚的艺术遗产氛围,使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遗产技艺得以发扬。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是杜尔伯特蒙古族人们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为使民间技艺能够永久留存,民间组织应紧跟国家保护非遗相关政策,通过引导社会大众进行抢救与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最后,从教育范畴考虑,最直接的方式是在学校范围内开展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相关涉入活动。如此,既可以通过教育手段普及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内容,又完善了在学校范围内对这类遗产的音乐教育活动。只有学生对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潜在认识和深层接触,才可以更好的传播、继承和创新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杜尔伯特蒙古族文化并没有广泛普及,存在分布不均衡的传承现实。因此,可以通过在学校举办蒙古族文化歌舞比赛、器乐竞赛等活动,以激发校园内教师与学生对相关领域的求知欲望和参赛信念。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是推进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非遗传承工作的直接方法,加大遗产教育力度,改变传统音乐文化的固有认知,产生学生们对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用科学直观而系统的视角审视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民间传承艺人可以走进校园,以“教育者”的身份抢救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是每位遗产传承人的责任。
五、结语
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这片秀丽而古老的土地上,蒙古族音乐文化于民间礼俗中浸润且遍布。尽管传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文化在“汉化”的涉入下已褪去原有铠甲,但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仍始终贯穿于杜尔伯特人民的衣食住行、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习俗风尚当中。对于人类瑰宝之一的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不单纯应依靠国家、社会、民间组织等单方面的努力,而是应该团结所有能够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去共同维护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给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带来鲜活的生命活力,在和平美好的时代里,使其经久不衰且绽放无限魅力。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在岁月的洗礼中,绽放其浓郁的蒙古韵味,汇聚了蒙古族的民族气息,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保护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全社会皆应形成共同认识,用行动去拯救。追踪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可以跨越已有研究成果,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重新认知,思考变迁之后杜尔伯特蒙古族音乐类非遗的未来发展之路,以便于今后有关本论题的相关探讨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