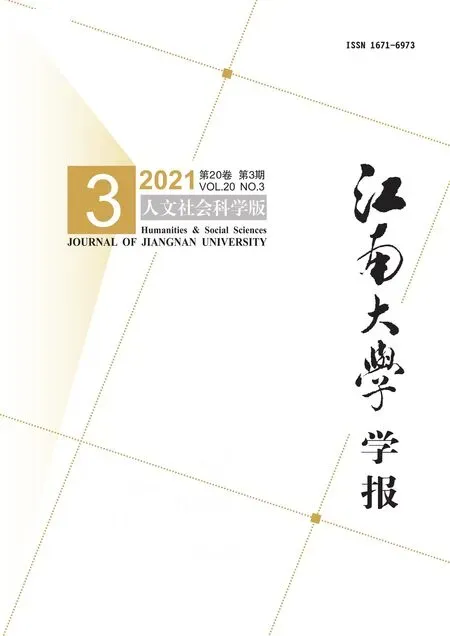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关于近世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以日本、美国、中国内地的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包含民俗学者)、宗教学者为中心,已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大致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中国民间信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考察;第二类是研讨中国民间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的研究,中国民间信仰这一研究课题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内地也出现了诸如《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这样的历史学者研究民间信仰的综合性论文集。[1]3但中国地域广阔,民间神庙众多,不同地域的民间信仰其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与国家祭祀政策的关系亦有较大差异,故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前,是中国文字记载最早的伏羲庙,也是济宁市现存最早的古建筑。微山伏羲庙北依凤凰山,南抱微山湖,始建时间不祥,宋、元、明、清时期先后重修。据传原微山伏羲庙,前有三圣阁,后有女娲殿,另有蓍草园、渡善桥、钟楼、鼓楼庙门等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而今由于战乱和人为破坏,(1)有关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的变迁情况详见杨复竣著:《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中国远古文明探源(下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162页;文平,刘赟:《千年古庙祀伏羲》,《走向世界》2020年第11期。现仅存伏羲大殿一座。2013年,微山两城伏羲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在论述微山县伏羲庙历史变迁的同时,重在分析地方精英阶层对伏羲信仰的态度和看法,以此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祭祀理念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一、微山县伏羲庙的历史变迁
伏羲,又称包羲、庖羡、伏戏等,是上古神话人物。传说伏羲作八卦,发明记事符号,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易系辞》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2]传说伏羲与女娲相配成婚,产生了人类,古人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始祖,也是人类的保护神,故建庙进行祭祀。我国很多地方都建有供奉和祭祀伏羲的庙宇,著名的除甘肃天水伏羲庙和河南淮阳太昊陵外,还有山东省济宁市邹城郭里镇庙东村羲皇庙(俗称人祖庙、爷娘庙),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渭南乡三阳川卦台山伏羲庙,河北省新乐市伏羲庙,台湾省台北市甘谷街“中华文化始祖太昊伏羲圣帝八卦祖师纪念庙”等,其中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当属微山县两城镇陈庄村的这座伏羲庙。
微山县两城镇在明清时期为鱼台县所管辖,故鱼台地方志中对此庙有详细记载。康熙《鱼台县志》卷十《陵墓》对鱼台凫山伏羲陵进行了详细考证:“(伏羲陵)在凫山麓其前为庙,东有画卦山,按《九域志》:兖、单皆有伏羲陵;《路史》又云:陵在山阳,鱼昔属单,又属山阳,作者固指名于所属也;《滕志》辨之曰:伏羲都陈,谓于凫山有墓,非也,未免拘墟之见。”[3](卷10《古迹》,P199)同书载“画卦台”在凫山,山之南麓有辛兴里,“里周匝伏羲遗迹甚众。山麓之半有伏羲陵,陵东一峰郁然者名画卦山,即画卦台也。前有伏羲庙,甚古,详孟褀记中。”[3](卷10《古迹》,P190-191)光绪《鱼台县志》同书卷一《山川志》记载凫山:“在县治东北七十里,双峰耸,翠状若凫翔,故名。”[4](卷1《山川志》,P65)同书卷一则记载伏羲庙:“在凫山麓,《齐乘》所谓颛臾风姓之国,实司大嘷之祠,邹鲁有庙者是也。后有伏羲冢,东有画卦山。”[4](卷1《旧迹志》,P122)按照地方志的说法,鱼台境内有伏羲陵、画卦台等众多遗迹,伏羲庙建于此地当属无疑。
清人徐宗干、冯云鹓所辑《济州金石志》卷八收录了众多与伏羲庙相关的碑刻,为我们了解其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视角。
伏羲庙中时间最早的一块碑刻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重建伏羲庙三门记”碑。《济州金石志》卷八记载“宋熙宁十年重建伏羲庙三门记碑”,南阳贡史郭翕撰并书。(2)(清)徐宗干,冯云鵷辑:《济州金石志》卷8《鱼台》,清道光二十五年闽中自刻本,第616页;清人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卷六中记载“重建伏羲皇帝庙三门记”:“大宋熙宁十年岁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阳贡吏陈翕撰并书。”光绪《鱼台县志》中亦做如此记载,故《济州金石志》此处记载有误。“按此刻正书文十六行前后年月题名二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18)关于此碑的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论述。北宋灭亡后,当时的鱼台县境属金朝管辖。《济州金石志》记载金泰和五年(1205)伏羲庙碑:“《寰宇访碑录》云泰和五年六月,石扶輗撰并正书,在鱼台县。”[5](卷8《鱼台》,P619)清人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则记载:“金伏羲庙碑,石扶輗撰并正书,泰和五年三月。”[6](卷12《山东中》,P1030)由于年代久远,此碑的内容已不可考。
伏羲庙中最为有名的一块碑刻当为元中统二年(1261)“重修伏羲庙记”。此碑由时任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孟祺撰,鲁人李禋书并题额。《济州金石志》卷八对此碑做了详细记载:“中统二年岁次辛酉秋九月望,住持道士孔志纯、蒋志清、王志朴、田志明立,凫山朱珍刊。……按此碑正书碑高八尺五寸广三尺六寸,文二十二行,前后题名年月七行,碑阴正书题名五十一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21)《山左金石志》记载“重修伏羲庙碑”:中统二年九月立,并额俱正书。碑高八尺五寸,广三尺六寸,在鱼台县凫山麓伏羲庙。右碑额题‘重修伏羲圣祖庙碑’二行,字径四寸,文二十九行,字径一寸,孟祺撰文,李禋书并题额。”[7](卷21《元石》,P84-85)此碑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进行论述。
《济州金石志》共收录有明清碑刻七块,其中年代最早的为明成化五年(1469)“伏羲圣祖庙记碑”。该碑由鱼台儒学生李朴撰文并篆额、书丹。《济州金石志》引其碑文云:“鱼台乃春秋鲁之属邑,凤凰山乃鱼台之境界,圣祖伏羲女娲二帝并祀,以为上世人伦之祖,及其殁,遂葬于凤凰山,是以建庙于斯,以为万世之观。然庙宇衰敝,道者福成力主其事,经始于天顺七年二月,讫功于成化五年十一月,可谓知所重矣。按此碑正书文十行,前后题名年月五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34)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塑画伏羲圣祖像记碑”,由儒学教谕莆田张清题额,训导永城袁友撰文。康熙《鱼台县志》记载袁友,永城人,举人,成化间任鱼台训导。[3](卷14《职官》,P333)“按此碑正书文十行,前后题名年月九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35)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伏羲庙神门记碑”,由书生高贤撰写。“按此碑正书文十九行,年月题名五行,无撰文姓名,碑阴题名三层,每层二十八行,在凫山庙内;又按记云古兖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有山名曰西凫,乃大圣人窀穸之所,建庙斯山之西,既曰西凫,则有东凫明矣。”[5](卷8《鱼台》,P635)明嘉靖九年(1530)“重建伏羲女娲庙记碑”,由监生李士龙撰文。“按此碑正书文十五行,年月题名四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38)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重修伏羲庙记”碑,由瑕邱后学郭震撰,郭尧宇书,韩守忠刋。“按此碑正书文十八行,年月题名三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45-646)
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太昊氏伏羲圣祖庙记”碑。该碑由鱼台训导竺该撰文,吏部待诠省祭官吴祥书丹,南京工科给事中邑人甄沛题额。碑文云:“鱼邑东境凤凰山旧有太昊氏伏庙,离县治七十里,庙制极其雄伟。又云河南陈州有羲皇墓,傍生灵蓍,而此地亦建庙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颛臾以主祭,故建庙于鱼之东者,就其后裔追祀地也。”[8](卷6,P144-145)《济州金石志》记载该碑名称为“重修太昊氏伏羲圣祖庙记”,作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鱼台训导竺该撰文,吏部待诠省祭官吴祥书丹,南京工科给事中邑人甄沛题额。“按此碑正书文十六行,前后题名年月四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39)此碑至今仍保存于伏羲庙中,惜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识别其内容。有关清代的碑刻,《济州金石志》中只收录了雍正十年(1732)“重修伏羲庙记”碑。该碑由巳酉科举人闫维墉撰文,邑庠生屈卜全书丹。“按此刻正书文八行,年月题名九行,在凫山庙内。”[5](卷8《鱼台》,P656)
二、宋元时期的伏羲庙
伏羲信仰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存在。[9]92到了商代,因为商人是东夷族后裔,崇拜鸟图腾。而东夷族的始祖就是太昊,所以,商朝的祖先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对伏羲的崇拜。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典籍都对伏羲的事迹做了记载,且都把重点放在伏羲所做的发明创造上,如始作八卦、以龙纪官、结绳为网、制嫁娶、作琴瑟等,喻示着伏羲信仰在这一时期已经初具雏形。西汉的大经学家刘歆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整理,并在《世经》中把伏羲作为中国人的始祖。及至到了东汉,班固又在《汉书》中引用了刘歆在《世经》中对伏羲氏地位的界定,并以“古今人表”的方式确定了中国古史帝王世系,把太昊伏羲氏列为中国古帝王之首。[9]93
唐代时,史学家司马贞从天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出发,写下了《补史记·三皇本纪》,系统梳理了前代有关关于伏羲的记载,为太昊伏羲立传。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颁布诏令,禁止在太昊伏羲陵园内放牧牛羊。继而,五代时期的统治者也下诏不许在太昊伏羲陵园内进行耕种等活动。唐王朝设立“三皇祀典”祭祀伏羲。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京师长安修筑三皇庙。唐朝时,设立“三皇祀典”来祭祀伏羲以及三皇庙的建立,标志着伏羲信仰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而“置令丞,令太常寺专校”,则意味着把伏羲信仰纳入到了国家宗教的范畴。从此,官方对伏羲的祭祀开始常态化,以后朝代的统治者们也基本上沿袭了唐朝时的做法,只不过,在祭祀规格和保护力度上有所不同而已。[9]95宋代延续了前代祭祀伏羲的政策。宋太祖于建隆元年(960)就为伏羲陵设置了专职守陵的人,并规定每三年祭祀太昊伏羲氏一次,且以太牢之礼祭祀。至乾德四年(966),不仅增加了守陵的人,由一户增加到五户;而且还增加祭祀的次数,由三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祭祀。此后,宋朝统治者还不断地修葺太昊伏羲陵庙。[9]95
依据《济州金石志》等史料的记载,伏羲庙中最早的一块碑刻应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重建伏羲庙三门记碑”。该碑由莆阳贡吏陈翕所撰,关于陈翕之生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碑文用大量篇幅高度评价了伏羲的历史功绩:
盖闻圣人不世出,出必有功于时也。……恭以伏羲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画八卦而备万物之象,兴文籍而书百世之名,以结绳为弊政而代之以书契,以神化为宜民而为之以善法,首正人伦,复为器用,通其变,使之无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则肃而庄;父子由之,则和而恭;夫妇由之,则愿而雍;兄弟由之,则友而悌。天下陶成于大顺,盖人伦正之始也。为网罟,以畋以渔;为栋宇,以宁其居;为耒耜,以济其饥;为舟楫,以便其涉;为弧矢,以威其乱;服牛马,以致其远。至乎揉木、陶火、铄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观俯察,而始立之法。[4](卷4《金石》,P323-324)
北宋立国以后,国家管控民间祠祀信仰的态度和措施出现重大的变化。朝廷和地方官打击淫祀风气的活动比以往唐五代积极许多。[10]考虑到宋代理学盛行,打击“淫祀”,维护儒家礼仪制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重要职责。在民间信仰领域,区分“正祀”与“淫祀”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陈翕用大量篇幅论述伏羲之功德的原因所在。
元代由于祭祀政策较为宽松,故民间祭祀伏羲之风极为盛行。虽统治时间较短,但《济州金石志》收录的元代伏羲庙碑刻却有5块之多。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元中统二年(1261)“重修伏羲庙记”碑。关于该碑的相关情况,上文已有相关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该碑由时任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孟祺撰文,鲁人李禋书丹并题额。孟祺(1230-1281),字德卿,宿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镇)人,元初名臣,著名农学家。早年随父徙居东平路,就学于东平府学,与阎复、李谦、徐琰,称“东平四杰”。得廉希宪、宋子贞赏识,随荐翰林修国史,后为翰林承直郎,曾出使高丽,辅佐丞相伯颜灭亡南宋,组织编写《农桑辑要》。至元十八年(1281),擢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因疾不赴任。同年卒,年五十一,追赠宣忠安远功臣、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封鲁郡公,谥号“文襄”。光绪《宿州志》卷十八《人物志》记载孟祺:“字德卿,苻离人,幼敏悟,善骑射,严实领东平行台,招诸生肄业,请元好问校之,入选者四人,祺与焉。官国史院编修,一时典册多出其手。当颜伯伐宋,授祺为行省咨议,诸将争趋临安,祺独谓以兵相迫,莫若以计安之,令彼不惧,正如取果,稍待时日耳。伯颜从其剖决。及入临安,奏祺前后,功累官浙东按察使、嘉兴府总管,进封鲁郡公,谥文襄。”[11](卷18《人物志》,P646)有关李禋,史料记载较少,只知其为山东人。
碑文首先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认为这种说法“恍惚怪骇”,完全是无稽之谈:
鱼台县治东北七十里而近,曰凫山,南麓曰辛兴里。世传上帝以兄弟作配于此,用成化育人民之功。诸不经之谈,所载亦往往如是。恍惚怪骇,绝不可考。说者谓至人以造化为准,乾坤生六子,中少长男女,迭相感合以适变,斯不亦娲、羲之事乎?抑上古之人,母而不父,淳淳乎与飞走无别,是之有无,果能必哉?愚以为圣人人伦之至,载籍所传嫁娶之礼,自伏羲而始,将以厚男女之别也。以是揆之,万无此理。敢为是说,诬圣人于千古之下,其故果何以哉?精于理者,必能辨焉。[4](卷4《金石》,P328-329)
在孟氏看来,伏羲作为“人文始祖”,符合儒家“圣贤”的标准,是“伦理道德”的化身,断不会做违背人伦之事,民间的种种说法都是对他的诬蔑和贬低,必须加以辨别并说明。
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伏羲庙草参亭记碑”由上文提到的李禋撰文,前海州东海县尉兼州学正鱼棠王璧书丹并题额。有关王璧的生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李禋在其所作碑文中云:
禋曩过岱岳祠下,见有所谓草参亭者,甚以其名不经,为可惜。近以事抵鱼台,过伏羲庙,新兴镇前巡检李青偕道者田志明等合辞来言曰:“日者草参亭成,幸辱文记之。”三辞不获,命乃曰:“必欲文之,先易其名而后可。”……窃谓草参,志敬也,凡奉香火者或远或迩,轮蹄负戴,跋涉川涂,蒙冒尘土,欲定馆而后见,则无以展其诚;欲径造而直前,则无以致其洁。遂于此先拜告,至而退翼日行事,此其意也欤,然则是亭之建也固宜。噫!圣皇之功德在祀典,所当通祀,况名为陵寝之所乎?……禋嘉其诚而悯其勤,故乐为之书。[5](卷8《鱼台》,P623)
由碑文得知,李禋初次在岱岳祠见到“草参亭”之名,认为其名“不经”,一开始并不愿意为其撰写记文。但在听了巡检李青、道士田志明等人的说法之后,李禋认为草参亭之修建完全为敬神、礼神而建,表达的是对神灵的崇敬,故修建此亭亦在情理之中。在李氏看来,伏羲并非民间俗神,其功德载在祀典,应当加以隆重祭祀。
元至治二年(1322)“重修伏羲庙记”碑由三物教民乡先生草亭处士吕惟恕撰文,山泉散人杨玉书丹。康熙《鱼台县志》卷十七记载吕惟恕:“博学能文,当元之世,隐居不仕,士论重之。”[3](卷17《人物志·隐逸》,P439-440)光绪《鱼台县志》卷三亦记载吕惟恕:“博学能文,当元末不乐仕进,时论高之。”[4](卷3《人物志·清尚》,P270)对于山泉散人杨玉,史料记载不详。碑文亦首先对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道之大原出于天,四时行品物亨天何言哉!以其有圣人继承天心,立人道之极也。昔伏羲王天下,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诸身,逺取诸物,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由此以降,圣圣相传而道统远矣。世传伏羲女娲氏以兄弟为配,成化育人民之功,夫圣人为人伦之至,若兄弟配偶,何以为万世法?而嫁娶之礼,使男女有别,亦自伏羲始,以是揆之,必无是理,岂敢以俚俗之语,诬圣人于千古之下哉
与上文所述孟祺的观点相同,吕氏认为伏羲作为上古圣贤,断不会做违背人伦之事,民间有关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纯属对圣人的诬陷。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加以辩解和说明。
三、明清时期的伏羲庙
明清两代,虽然国家祭祀政策有所改变,但依然极为重视对伏羲的崇祀。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访求帝王陵寝,太昊伏羲陵首列第一。明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亲拟祝文,赶赴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祭祀太昊伏羲氏。洪武八年(1378),派钦差大臣祭祀太昊伏羲氏。洪武九年(1379),诏令增置两户守陵户。清代对太昊伏羲氏的祭祀同样比较重视。清顺治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十七年(1660),连续三年修葺河南淮阳太昊陵。康熙七年(1688)、康熙二十八年(1698)、康熙三十二年(1702),又三次进行重修。根据《陈州府志》《淮阳县志》记载,明洪武2次、永乐1次、弘治2次、嘉靖1次、万历1次、清代顺治1次、康熙10次、雍正3次、乾隆10次、嘉庆5次、道光5次、咸丰2次、同治1次、光绪6次、宣统1次,这充分体现出了明清两朝统治者对伏羲信仰的重视程度。[12]明清以前,伏羲信仰在民间就已十分盛行。明清官方的重视和倡导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伏羲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随着伏羲信仰的日益世俗化和民间化,儒家知识分子对民间伏羲信仰的批评也更为激烈。
明嘉靖九年(1530)“重建伏羲女娲庙记碑”由鱼台监生李士龙撰文,《济州金石志》对其全文进行了收录。嘉靖《南宫县志》卷三记载李士龙:“山东鱼台人,监生,嘉靖二十六年任南宫县丞。”[13](卷3《官师·县丞》,P439-440)康熙《鱼台县志》卷十七记载李士龙:“字文変,其为人也孝友敬服于乡党,文学幽成乎多士。由嘉靖十三年选贡,任南宫二尹,有惠政,民爱之。子发初,亦以文业登例贡焉。”[3](卷17《人物志·儒术》,P436)
宋元以来,民间广泛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上文已有论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逐渐赋予伏羲、女娲以求子、医病、祈平安等功能,并亲切地称伏羲、女娲庙为“爷娘庙”。对于民间的此种行为,李士龙在其所碑文中亦做了详细记载:
盖尝稽之载籍,太昊伏羲氏继遂人氏而王天下,河出图,洛出书,则而画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泄造化之秘,尸阴阳之体,圣之至也。女娲氏与太昊同母,生而神灵,辅太昊为治。太昊殁,共工氏作乱,女娲灭之,以治天下,是为女皇。夫太昊、女娲兄妹也,生于成纪。太昊都宛邱,女娲都中皇,立庙于此,亦后人追崇神圣之意。奈何不谙故事者,率皆承讹踵谬,不曰人祖庙,则曰爷娘庙,谓为人祖,以太昊、女娲气化于混茫之初,而为形化之祖也。殊不知人之先太昊而生者亦已多矣,谓为爷娘,以太昊、女娲兄妹妃匹而为今之大父母也,殊不知二圣为何如人而有是哉
在碑文的最后,李氏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伏羲、女娲之功德,并借此机会对民间相关称呼和传说进行了驳斥:
夫上古男女无别,帝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是功也,女娲实左右之,故后世并称焉,称以人祖,谓其祖人伦也;称以爷娘,谓其功德足以为万世之大父母也。必如是说,然后夫人之祀为有名,而神灵之享为有功,乃天理、民彝之在人心,不可得而泯没者。否则于正伦之圣,反加以乱伦之毁;尊容之典,变而为污辱之号,误传误,疑传疑,蠧天常而蚀人纪者,莫大于是故。[5](卷8《鱼台》,P37-638)
清康熙年间,鱼台知县马得祯亦对民间祭祀伏羲的相关做法进行了驳斥。康熙《鱼台县志》卷十四载马得祯:“号冲霞,山西介休人,由内院供事出判彝陵州。时值大兵讨滇黔,运饷积劳,督抚保荐升铜陵知县,历俸三秊,以内忧回籍,士民数千人,舳舻数百艘,追送三百六十里,至浦口登陆乃返。起复,补授鱼台知县,康熙二十七季八月至今任。”[3](卷14《职官》,P315)康熙《鱼台县志》为马得祯组织纂修,在该书卷八《祠祀》中,马得祯首先记载民间有关伏羲庙的相关称呼和风俗:
(伏羲庙)在凫山麓,……后有伏羲塜,东有画卦山也,详《古迹》,见元邑人孟褀记中。今庙门古树繁阴,墀际栢挺,双干皆数千年物,真古祠也。土人呼人袓庙,又呼“爷娘庙”,其建于乡村中者,名亦然,像以女皇并塑云。上帝令兄妹为夫妇,以产天下,后世之人故呼“人祖爷娘”,岁以三月三日醮会多就而祈嗣焉。[3](卷8《祠祀》,P161)
在地方志中,马得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对民间的种种说法和行为进行了批驳:
此说鄙亵已甚,稍知礼义者又为之说曰伏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故塑帝后像匾曰人袓,就而祈嗣,此近似矣,而实亦悖也。……按伏羲氏同母女弟曰女娲氏,生而神灵,佐太昊正婚姻以重万民之命,是为神媒;继太昊治天下而为女皇,故后世立郊媒郊天,而以神媒配也。……《诗》之所谓以弗无子,袚无子,以求有子也。后因以为俗,若云女娲为伏羲后,则嫚神侮圣,若此为甚。即谓后非女娲,亦与祀义绝不相蒙。俗习迷昧,不独邑内,邻境皆然,故详释而附辨之,以冀见者之共悟云。[3](卷8《祠祀》,P161-162)
从马氏所作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伏羲、女娲兄妹配为夫妻的说法在清初已经广为流传,并被民间赋予了祈求子嗣等功能,以致身为地方官员的马得祯不得不专门撰文加以阐释和辨别。
四、结 语
微山县伏羲庙历史悠久,即使从北宋熙宁十年(1077)算起,其历史亦有千年之久。在这其中,有记载的重修就有十余次之多。虽然重修年代和立碑人各不相同,但都表达了儒家精英阶层对伏羲氏的敬仰。洪荒蛮野之初,混沌肇分,天开地辟,伏羲氏立人极,立人道,创书契,造琴瑟,人文著,人事谐,伦理明,乃万世生民之祖。碑文还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和斥责,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对民间的相关称呼和风俗,地方官员和士绅亦依据儒家礼仪制度和祭祀理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元至明清时期微山县伏羲庙发展的主线,即圣贤人物的功德化和神圣化。
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基本上是在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它的传播往往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渗透的,[14]民间信仰在中国人的精神及社会生活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他属于什么阶级,拥有什么样的身份,中国人都普遍相信鬼魂和神灵的存在。而就皇帝及各级官僚而言,他们也充分认识到民间信仰对国家的统治而言是十分有用的,他们反复提到“阳世有礼乐,阴世有神灵,凡是礼乐无法支配人民的地方,则由神灵去支配”。[1]3自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之下,在祭祀领域出现了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对民间信仰与祭祀活动进行控制和干预,力图将其纳入国家认同和制定的祭祀政策当中;另一方面,官方推行的这套祭祀体系虽然在民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又得不到民间的完全认同,民间往往是通过利用国家政策而按照他们自身的信仰观念与关系纽带在地方上建立祭祀的空间与等级体系。(3)杨渝东:《〈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评介》,载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29-430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礼”与“俗”之间的矛盾。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俗”不断改变“礼”。“礼”与“俗”代表了不同社会等级阶层中彼此平行而并行不悖的社会实践行为。精英之所以鄙视“俗”,正是出于保证“礼”的纯洁与正统的目的,因为“俗”很容易影响到“礼”。[15]历史上的“礼”不仅产生、提炼于“俗”,而且始终与“俗”密切互动。而“俗”和现实生活、具体实践密切相关,敏于变化,又为“礼”提供了根本动力。可以说,两者在彼此的对立和紧张中依存发展。[16]中国传统官员、文人、绅士往往以教化百姓为己任,在“礼”“俗”二字上大做文章,认为其上通国运,下维众生,兼为个人立身之本。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还是从下到上的“因俗治礼”,不过是其因应现实情境而采取的不同策略。
通过对微山县伏羲庙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伏羲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其本人的德行无关。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实际上是儒家祭祀理念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和渗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17]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伏羲既是上古圣贤,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伏羲作为民间神明,又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必须在保留其神圣性的同时,去除其信仰活动中的草根性,推动其由民间俗神向官方正祀的转化,即实现民间信仰的“儒家化”或“官方化”。在这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地方官员和士绅。身为儒家思想的捍卫者和倡导者,他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最终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