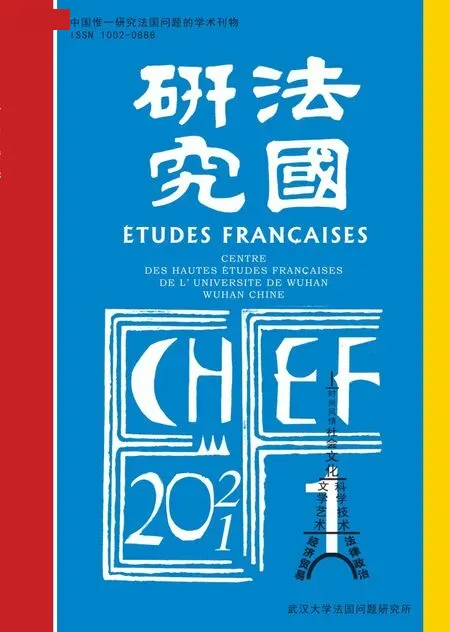勒·克莱齐奥对老舍家族叙事的接受
尹鹏凯 梁海军
法国著名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十分喜爱老舍,他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老舍作品的欣赏与认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末,老舍在法译介取得重大突破:由法国著名学者保尔·巴迪(Paul Bady)和法籍华人李治华(Li Tche-houa)翻译的小说《正红旗下》1987 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书名直译为《大年初一出生的孩子》(L’enfant du Nouvel An),这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未竟之作以“我”的口吻细述清末皇城一普通旗人“马甲”之家得“老儿子”的喜与忧,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家族、市井人物与他们的生活琐事,以满人家庭为主线复现当时皇城的社会风习与变迁。
1996 年至2000 年间,老舍逾百万字的《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L’effroi)、《偷生》(Survivre à tout prix)以及《饥荒》(La famine)于法国墨丘利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陆续出版,三部曲以抗战阶段北平沦陷时期的小羊圈胡同为背景,展现了祁家四代、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各类营生之人的命运,于大时代变革背景之下上演亲族、个人之抉择与国家命运的艰难碰撞。
值《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法译本1996 年在法国出版之际,勒·克莱齐奥便以《师者,老舍》(Lao She, Le professeur)为题为该书作序,表达了对老舍这位东方小说大师的尊崇之情。自新世纪以来,勒·克莱齐奥写作风格有所突破,小说创作隐含了更多的家族史因素。①勒·克莱齐奥:《饥饿间奏曲》,余中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 页。譬如,2003 年小说《变革》(Révolutions)中,作者构建了一部马罗氏(Les Marros)跨越世纪的家族史:数名族人的命运与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交织、融汇;次年《非洲人》(L’Africain)虚实间叙,“我”试图在回顾父亲数十年的非洲生涯与家族跨越重洋的变迁中寻求曾被忽视的身份认同;2008 年的《饥饿间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中,作者以女孩艾黛尔的成长视角呈现源自毛里求斯的法国布伦家族(Les Bruns)二战期间由盛至衰的没落历程。
回望两位作家的创作,“家族”已是谈论二人无法避绕的丰碑。纵观老舍的创作生涯,可以说其“顶峰”与“尾声”均落在家族史之上。而勒·克莱齐奥在其作品中所浸染的对于家族史的回顾与思考同样意义深远。正如这位法国作家本人曾于1983 年2 月14 日刊登在法国《解放报》上的《老舍,北京人》(Lao She, un homme de Pékin)一文中写道:“作家仅仅成为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成为一个历史专家,这就很不够了,还必须成为时代的表现者,通过自己的回忆,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图景,替那些无权说话的人说话。老舍正属于这些作家之列。”②勒·克莱齐奥:《老舍,北京人》,钱林森译。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62 页。勒·克莱齐奥的家族小说创作受到老舍的影响,尽管彼此家族叙事风格仍有相异,但前者对后者采取了积极的接受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的系列作品中体味到老舍成熟的家族塑造所带来的影响力,这是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民族文化背景亦无法割裂的。
一、以家族叙事框架表现时代变革与人物迷惶
“家族”在老舍与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创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老舍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代人为主要描述对象,展现了自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重大历史变革下北平数户普通人家的命运变迁;未竟之作《正红旗下》则写一户满族底层“马甲”之家得“老儿子”,借新丁降生、洗三、邻里来往等日常琐事展开,网入清末皇城市井小户的习俗更迭。同样,迈入新世纪,勒·克莱齐奥一连几部作品的创作重心均向家族倾斜:《变革》中以老祖宗让·厄德·马罗(Jean Eudes Marro)所留日记、卡特琳·马罗姑婆(Catherine Marro)口述回忆及让·马罗(Jean Marro)之成长经历三线并立,构建了马罗家族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流变史;随后,《非洲人》则将“我”父亲的非洲行医生涯作为主线,探究家族迁徙史在“我”身上种下的非洲印记;小说《饥饿间奏曲》进而以小女孩艾黛尔·布伦(Éthel Brun)的成长视角讲述发源毛里求斯的法国布伦家族二战前后由巴黎南下尼斯的兴衰史。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曾言:“小说是认识现实的惟一方式。”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予虚构小说作品以丰厚,在构筑小说中的家族史时,历史大事件不约而同地成为了作家们的“骨架”优选。
首先,老舍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是时代的积极表现者。事实上,自早期作品《赵子曰》(1927)、《猫城记》(1932)发表以来,其入世之心已然明朗。从揭示学生运动青涩积弊到“九一八”事变次年构建乌托邦猫国影射当局腐朽积弱,乃至后来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积极倡导抵抗文学,老舍小说一直对所处时代的问题有不同程度表现。清王朝日薄西山、共和国先天不足、抗战期残酷艰辛。生于世纪之交的老舍,人生正将直面前所未有之变局,这是一个激烈变革交错的时代。小说《四世同堂》集中展现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到抗战胜利期间的都城北平。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来说,没有哪一载不充斥着巨变,小说现实时间跨度不逾十年,但作者却能详尽地将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地安排在情节发展之中,渲染出激变的时代底色。
“七七”抗战那一年,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爷已七十有五,他什么都不怕就怕庆不了八十大寿。不料,老北平城不久就陷落了。然而,这却仅是苦难和窘迫的开始。祁老太爷对个人私愿能否实现的忧虑迅速蔓延到整个北平城居民对未来的惶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他们耀武扬威,将城中人与外部世界隔绝,北平成了风沙中的一座孤岛。随后的年岁中,作者陆续写到保定、太原、南京、广州等多地的陷落,这些消息陆续以各种媒介传到了祁家长孙瑞宣的耳中。国土危难,梓乡飘零,几乎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在此种阴霾之下而沮丧、心惊。时局不定,人心难安。老舍用简单而又悲壮的短句渲染出人物情感:“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①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34 页。但小说家也不忘寄予读者希冀,例如他提及的振奋人心的台儿庄战役。如若从今日回望历史,我们了解到这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彼时老舍却用以最朴素的表述将喜悦融入到情节之中:“杏花开了。台儿庄大捷。”(2017:490)承载着春日复苏希望的杏花吐出了捷报,这迟来的胜利使得瑞宣的坚定变成一种信仰。在第二部《偷生》和第三部《饥荒》里,作家不忘穿插许多国际记事:譬如市民从报纸得知德国三路进攻波兰、苏日之间成立的诺蒙坎停战协定,以及1941 年足以影响外部战局势的珍珠港被袭事件等。中国抗战的后期,可以说国际局势对国内战事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现实的观察家,老舍并未遗漏国际视野。虽然《四世同堂》的主要讲述祁家四代,且仅在北平城内展开,但是在混乱割据的上世纪,如果斩断祁家与北平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侃谈家长里短,在作者看来显然十分狭隘。虽然写的是无数传统中式家庭期许的“四世同堂”,小说家却“醉翁之意不在酒”,风暴的先声如何响亮在寻常百姓家才是他思忖所归。老舍继续将目光非常细致地聚焦于北平被占区的各个方面:他借瑞宣逛书摊反映日本人强制推行替代法币的伪钞和对新书、思想的管控;通过布店掌柜天佑自杀反映日本人接管城中商贸;以及令家妇韵梅忧心的粮炭管控;直接导致奸人冠晓荷被借“消毒”之名被活埋的传染病流行等。北平沦陷时期老舍寓居重庆,他本人未曾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但他将详尽的历史事实与自身丰富的北平城市经验相结合,借以合理想象呈现出那个荒谬时代人性的反常,勾勒出普通市民家族在被占区生活的艰辛、逼仄,以及他们难以排遣的迷失、惶恐、颓丧之情。
小说《正红旗下》延续了这一手法。文中先是多次强调“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而后先以舅家二哥福海信白莲教为伏笔,进而写老王掌柜得小儿子王十成回京讲到山东闹义和团对抗“大毛子”之事。戊戌新政是晚清残灯末庙时期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它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价值。而“义和团”是晚清时期一系列反抗的民间团体组织的统称,由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发展而来。1897 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后,鲁地反抗运动亦愈演愈烈,“大毛子”就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当地对洋人的蔑称。老舍在后半部还写到“洋垃圾”牛牧师来华却做了老大爷,皈依基督教的多老大狐假虎威一事。当时,洋人渗入京城生活的一大体现就是传教士的频繁活动。他们中有受过良好教育、能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乏为牟利来华的无良投机主义者。洋人渗入京城的另一大方面即租界的产生。《四世同堂》中便已多次提及被各国洋人占据的东交民巷,例如在东交民巷“英国府”做“摆台的丁约翰,梦想以妓女检查所所长一职位攀附权贵而出入东交民巷和北京饭店的大赤包儿。东交民巷地带自《辛丑条约》中正式被划定为使馆界后,便成为都城洋人势力的代名词。这些历史遗产都是中国蜕变历程留下的蝉壳,充分诠释了一个时代的激烈变革。但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变革中,北平普通人家的生活依旧苦涩。在北平,大家都习惯赊账,因为“赊账已成了一种制度”①老舍:《正红旗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2 页。,商贩们在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一组,形似鸡爪子,大家先吃先用,饷银到手便去还债,还了无余,再去赊。几口人辛苦一整年,到头来过年却因没得钱财底气而提心吊胆。“我”因为吃不饱而“干嚎”,“小孩们的饥啼是大风暴的先声”(老舍,1980:75),看着一个孩子挨饿便能想象着天下必有更多的孩子受着苦寒之痛。老舍自饥童的干嚎声联想到各式令人叹惋的时代悲鸣:
同时,在北京,在天津,在各大都市,作福的叱喝声,胁肩谄笑的献媚声,鬻官卖爵的叫卖声,一掷千金的狂声,熊掌驼峰的烹调声,淫词浪语的取乐声,与监牢中的镜僚声,公堂上的鞭板夹棍声,都汇合到一处,“天堂”与地狱似乎只着一堵墙,狂欢与惨死相距咫尺,想象不到的荒淫和想象不到的苦痛同时并存。(老舍,1980:76)
时代在变革涌动,有人却因此遭了跟头。老舍的家族叙事从宏观兼及微观角度充分联结真实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是梳理情节时间线的节点,亦成为反映时代变革、社会风俗更易的窗口,同时也充当了人物感情宣泄的诱因。时事纷扰,同一屋檐下的族人们面对时代浪潮的冲击,生活习俗与方式不得不做出妥协与改变,同时也无奈地感到迷失与惶惑。于小说家而言,家族框架之下展现的内核更偏向于对时代变革下人物命运的担忧。如此的激变之中,文艺作品于作家老舍已被摒弃了纯粹的精神愉悦而更注重社会功能,批判价值更重于文学价值,于是我们在一抵抗文人的家族小说中翻阅沧桑事变,也不足为奇了。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不失彼道,他同样积极地反映时代,以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渲染时代的变革特征。他试图将人物置身于所处时代变革的浪潮之中,将他们对应的情感、抉择与命运汇聚,从而呈现属于大部分人的时代回忆与情感底色。首先,相比老舍家族地域的稳定传承性,勒·克莱齐奥在小说《变革》中所展现的的“野心”似乎更大。这部家族史巨作中,家族绘卷上时间尺度延展近两个世纪,空间地域则横跨庞大的欧、非、美三大洲。小说里,通过打开卡特琳姑婆的“记忆之匣”和阅读老祖宗让·厄德的日记,年轻的让·马罗得知了法国殖民时期法兰西岛(l‘Île de France)的概况,知道了英国人如何打败法国人并接管此地又改回旧称毛里求斯(Maurice),以及这里曾经进行过蔑视人性的黑奴贸易。让还听闻二十岁的卡特琳姑婆当年如何经历普法战争,年过花甲是怎样碰上世界大战,紧接又是着二战。让的父亲这一脉,雷蒙·马罗(Raymond Marro)曾在马来西亚的怡保当兵,因此文中也提及了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还有直接加速法国第四共和国崩溃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令人叹惋:
每天还有那么多人死在阿尔及利亚,血流成河,淌入大海,大海变得粘稠、缓慢,变成血红,散发出腥味。①勒·克莱齐奥:《变革》,张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44 页。
以及借成年后让·马罗游历视角还原的1968 年墨西哥城,政府对学生、抗议者与无辜群众的残酷镇压事件——血腥的特拉特洛尔科之夜(La nuit de Tlatelolco):
之后,夜幕在广场上降临。装甲车打开了车灯。到处都是死者、伤者、孩子躺在地上,胸口被冲锋枪的子弹射穿。(勒·克莱齐奥,2018:325)
乍看这些事件乱如散沙,彼此分裂,但它们的身后都少不了马罗氏族人的卷入。本凌乱无序地发生于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的各类事件,通过绵延的马罗家族一脉而互相关联。战争与骚乱是小说家在《变革》中常用以凸显文题的元素。让·马罗厌恶战争和杀戮,这一切的流血让他觉得迷茫。他家族中曾有人因为战争丢了性命,如今同样的惨剧又成千上万次地发生在遥远与咫尺的世界之中。勒·克莱齐奥擅长利用族人见闻向读者传递情绪。在这两地的场景描述中,“血流成河”、“粘稠”、“缓慢”、“血红”、“腥味”、躺在地上的“死者”、“伤者”、“孩子”、以及那“被子弹射穿的胸口”此类意象仿佛构成人间炼狱,厌恶、恐惧与无助之情弥漫词间。家族中不同辈分的人物均代表着他们各自活跃的年代,一部家族史就是一部世界史。马罗家族见证了两百年来的殖民与罪孽、战争与离散、暴乱与颓丧。在时代的变革中,从家族小团体看到的一切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在随后的两部小说《非洲人》和《饥饿间奏曲》中,作家舍去了漫长的时间线,宏大的世界观也相对被淡化,家族人物关系变得简单,但变革仍然是主音,小说家以历史事件构筑时代棱角,它们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也促进人物情感的爆发。在这两部小说中,勒·克莱齐奥直接将矛头指向二战。1940 年,巴黎沦陷。战争断了“我”父亲的非洲梦,他穿越沙漠想在阿尔及利亚上船赶往法国南部与妻儿汇合,将他们带往非洲避难。而当战争狼烟烧到了非洲战场之后,他原以为自己靠着多年本地行医能与非洲人民成为朋友,却突然发现“而此时,医生只不过是殖民强权的另一个因素而已。”①勒·克莱齐奥:《非洲人》,袁筱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96 页。他曾经满怀热情的事业变得沉重。在俄果雅(Ogoja),惊疑流传,谣言散布,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现代西医的无知让当地所有外国人都成为“间谍”。父亲再次走进病房,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再成为那个带来西药、与村民分享知识的仁慈之人,恰恰相反,病人眼中对他满是害怕。在战争期间,医术成为了一种强权凌驾,医护成为了一种政治监控。战争还颠覆了家族原本的生活模式。在法国时,一家五口和保姆在尼斯的小房子里幽居,为了逃避盖世太保压榨还得不时前往山间避难。随后“我”、哥哥、母亲和外祖母终于来到俄果雅,与父亲在艾雅河、大草原之间生活,但战争还是影响了这片净土,它仍未逃离丑恶文明的剥蚀。人物的认知与情感都在时代的激变中历经考验:世界充满虚无性,战争蹂躏了医护的崇高也割裂了人种之间的信任。《饥饿间奏曲》中,二战也使得艾黛尔的世界迅速崩坏。曾经在巴黎上流社会沙龙中有头有脸的布伦家族于巴黎沦陷后破产,一家人继而南迁尼斯躲避战火。灾厄接踵而至。一边是国土蒙难:贝当将军的维希政府与德国纳粹合作成立了傀儡政权,法国东南地中海沿岸也沦为意占区;一边是饥荒爆发:“那些烂菜叶和绿根系也都要用钱买了。花园里,野猫互相残杀吃肉。”(勒·克莱齐奥,2009:168)1940 年,德军闪击法国,一路势如破竹。因多面受困,法国还未经战斗就放弃了巴黎以北的防御,政府南迁。这座著名的大城市中三分之四的居民选择撤离,一时几近空城。当时法国国内难民多达百万,布伦一家混在流亡大队中,手持“难民回乡公路交通通行证”前往南方避难。德国数周内迅速迫使法国宣布投降,纳粹入侵直接导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垮台,这让作为盟友的意大利眼馋不已,同年便占据了法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饥荒是战争的伴生子。由于社会动荡失序,以及大量人口南涌,一时间食物匮乏,难民们的基本温饱无法实现。艾黛尔感到绝望与迷茫:
现在,他们被惩罚像幽灵一样游荡,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食粮,只有烂菜果皮,似乎在这遥遥无期的冬天里,他们就靠泥土、煤炭、钢铁为食。(勒·克莱齐奥,2009:163)
布伦一家的遭遇同样也是当时百万流民的生活写照。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一小家庭背上都是巨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被魔幻充斥。无休止的战争、饥饿、流亡影响了数代人。勒·克莱齐奥同老舍一般,借家族的平台上演时代大戏,在他的小说中丰富的历史事件与对应的人物情感连续不断地给予读者冲击。正如老舍在总结个人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书中谈到:“小说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为用的。一些零乱的事实不能成为小说。”①老舍:《老牛破车》。北京:北京阅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5,76页。勒·克莱齐奥所展现的历史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总是与人,与家族中人紧密联合:家族框架内化了一整个时代的激变,也内化了人类共通的感触。因为,时代变革影响的绝不仅是一家人、一寸土,家族是“微缩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代人情感的集中流露之地。
在勒·克莱齐奥表现的时代变革与人物迷惶之后隐藏的实际是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法国著名翻译家克洛德·巴彦(Claude Payen),老舍的译者,曾感慨他“在憧憬与矛盾之中苦苦挣扎,以求从长久以来回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人文光辉中习得宽慰”。老舍满怀人文关怀,关注普罗大众的命运。勒·克莱齐奥也深知:现下,世界已经属于明天之人,生于激变时代的子民最终还是需要用那余生去弥补适应期间所落后的差距。“江河清洗历史,这众所周知。他们使尸体消失,在它们的岸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留太长时间。”(勒·克莱齐奥,2009:214)作家出生于1940年,他是经历过战火的一代人,他所大半生处的时代并不太平。勒·克莱齐奥长期在作品中反映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丑陋和弊端的厌恶:“殖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2018:17)“充满战争的世界,焦躁不安”。(2018:47)一方面他对现有的秩序提出了抗议,另一方面他却长久苦于寻求解决之道无果,只能逃遁:卡特琳姑婆于往昔记忆里逃离;让·马罗选择异国逃离;艾黛尔在战后恢复的新生活中逃离。但作家最终找到了老舍,老舍的小说是他所处时代的写照,其笔下悲剧性的深刻在于,虽然家族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享乐、投敌,有人守住气节、奋力抗争,但无论反抗与否最终仍然无人是胜利者。这种伤感之怀让引起了勒·克莱齐奥的共鸣,他们都听见了痛苦与呐喊,却难解、寡助。二人的最终指向共通:关注时代变革中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危机。
老舍曾主张:“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纪录,不是事实的重述。”(2015:107)勒·克莱齐奥敬重老舍,他选择倾注情感写作,选择对这些在生存与精神危机中挣扎的人们抱以无限怜悯与关怀。逃离是悲剧性的一种表现,它是面对冲击的乏力与困顿。正是在老舍处,勒·克莱齐奥找到了某种认可:无论人物如何反抗,时代的悲剧性已经造就,在变革中,迷失与惶惑在所难免。“兴许就没有什么战争,艾黛尔梦想着。[...]所有这一切不是那么容易讲述出来的。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中。”(勒·克莱齐奥,2009:201)艾黛尔的逃避似乎是作家态度的一次显影。勒·克莱齐奥淡化过程,他尝试用细腻的笔触将发生过的一切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轻盈,似乎这一切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人为地抹去,似乎时光可以回头、再重启。老舍即便舍弃文学性也要说教般讲出来的讽刺与批判,在他这里似可选择缄口不言。他以梦幻般的“轻”表现老舍的“重”,老舍训诫式的忧心在勒·克莱齐奥这里被解构。但实质上,呼喊与细语,都是同一种发声。
二、充分与个人回忆相结合,展现生活图景
勒·克莱齐奥于2019年出版的新作《在中国的十五场漫谈:诗意的冒险与文学的交互》(Quinze causeries enChine : Aventure poétique et échanges littéraires)中指出:“老舍的小说形式与现实主义流派的狄更斯、巴尔扎克小说,以及辛克莱·刘易斯和约翰·斯坦贝克的社会小说颇为相似。”①J.M.G.Le Clézio,Quinze causeries enChine :Aventure poétique et échanges littéraires.Paris :ÉditionsGaillmard,2019, pp.72-73.现实主义作家关心现实和实际,力图对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和呈现,为具备这种素养,个人的所见所闻往往成为作家们的第一手学习材料。老舍1899年出生于皇城北京,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丰厚的城市生活回忆为他之后创作小说提供了优质的素材,其家族叙事充分与个人回忆相结合,虚实间叙,巧妙“嫁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行文之初便交代:“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老舍,2017:10)这个胡同造型奇特,形似葫芦,葫芦嘴延伸到了西大街,祁家的房则在“葫芦胸”里。事实上,这“葫芦”就来源自老舍的生活记忆。小说家的妻儿在重访其出生地后,不禁发出感概:“在老舍的作品里,在跟老舍本人身世毫无关系的小说里,这个小胡同和小院子早就当过道具和布景了,而且,是那么逼真,那么详尽,反映得几乎和相片一样真实。”②胡絜青等:《论老舍诞生地》。老舍:《正红旗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5页。据相关考证,老舍的故居就是小杨家胡同“葫芦胸里”一处不甚体面的院子,且旧名的确为“小羊圈”,同坐落于西城护国寺一带。丰富的城市经验极大程度上帮助了老舍构筑《四世同堂》中的“布景”,景随人移:
瑞宣的路,最好是坐电车到太平仓;其次,是走烟袋斜街,什刹海,定王府大街,便到了护国寺。可是,他的心仿佛完全忘了选择路线这件事。他低着头,一直往西走,好像要往德胜门去。陈野求跟着他。走到了鼓楼西,瑞宣抬头向左右看了看。(老舍,2017:220)
短短数行,老舍在定制人物行动轨迹时,各种地标信手拈来,这正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运用。而在作者宣称是小说而非自传的《正红旗下》中,此种“嫁接”痕迹就更为明显。据夫人胡絜青坦白,小说中已出场人物在老舍家中几乎确有原型可查,且身份地位与性格也大致相当。此外,节日民俗与吃食玩意也是作者回忆的重点。老舍的家族叙事中蕴含一种普鲁斯特“小玛德莱娜式”的细致与爆发力,他对于生活细节的再编排具有令人惊叹的把控。普通人家如何过年守岁、操办新生儿的“洗三典礼”,如何祭灶王爷、应对亲邻家红白喜事他详略得当;街边的烙回头、炸三角、作锅贴、蒲包儿,院里的蟋蟀瓦罐、装红、蓝颏儿的鸟笼子等如数家珍。或许是因为年幼丧父,母亲辛勤操持家业,长在市井之中的老舍对于日常琐事与传统习俗秉承敏锐的感知。多感官并用使得家族记忆塑造更具体、形象。他将早期生活经验巧妙地融入小说创作当中,成为家族生活形象塑造的布景与道具。勒·克莱齐奥为此赞叹:“老舍所描绘的世界颇具思乡气质,它以才华横溢的舞台演绎着十分亲密的家庭生活场景。尤其是在《四世同堂》中,于我这是一本学习描绘城市生活的伟大小说。”①LeClézio :« J‘aime tousles écritsde LaoShe ».http://french.peopledaily.com.cn/Culture/6835740.html[2009-12-08]来自个人记忆中不胜枚举的生活细节令这位法国作家感到惊叹,他将老舍的小说作为构建自身小说世界的教材:《变革》中,小让·马罗走进拉卡塔薇娲(La Kataviva)公寓追随卡特琳姑婆无限记忆的路上,我们仿佛闯入了老舍所描绘的北平西城护国寺一带的“小羊圈”胡同。拉卡塔薇娲这个五层带阁楼的公寓是个小世界。从事各类职业的租户们居住在这里:摩洛哥战役中受伤瘸了腿的阿蒙将军、老姑娘萘特·皮考小姐、让德尔一家和聋哑女孩奥罗尔·德·索麦威、酒鬼公车司机冈德拉等。最神秘的屋顶阁楼就是卡特琳姑婆的寓所。我们不禁回想“小羊圈”也是个小世界:这里住着钱家、冠家、戏痴小文夫妇、洋车夫小崔等人,以及五号院“葫芦胸”里的祁家。
勒·克莱齐奥曾言:“老舍做的最出色,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回忆。”②勒·克莱齐奥:《师者,老舍》,刘玉婷译。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68页。作家同样把个人回忆融入家族形象构筑,为增加人物角色的可信度,他将自身或族人身上的回忆与合理想象的虚构情节相交融。他对于回忆的态度可以在作品中寻得明示:
每个人都是父母和母亲的结晶。我们可以不承认父母,可以不爱他们,可以怀疑他们。但是他们始终存在,他们的一切:他们的脸,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癖好,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手和脚趾的形状,他们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思想,也许还有他们去世时的年龄,这一切都会传承到我们身上。(勒·克莱齐奥,2012:3)
在勒·克莱齐奥看来,父母祖辈不仅能传承予后代形体、性格等可见可感的影响特征,还能给予他们记忆。家族的记忆作用于族内的每个个体身上,即便后人未能亲身经历前事亦能对其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1940年勒·克莱齐奥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当年恰逢巴黎沦陷。即便身处南部,远离纷争中心,他的童年生活依然罩于战争阴影之下。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作者将它赋予了艾黛尔。艾黛尔这个人物灵感来源于其母,但也杂糅了自身童年的战火记忆。小说《饥饿间奏曲》中,战乱、饥饿让艾黛尔身心备受煎熬,她所目睹的灾祸就来源于作者自己及家人的真实经历。二战结束后,作家时年八岁随母亲、兄弟前往尼日利亚探望为英军战时医生的父亲。追溯父亲非洲行医经历的《非洲人》中,或因年岁已久,记忆模糊,作家以虚实融汇的叙述方式重现了“我”在非洲度过的短暂童年时光,现实与想象并行。这部《非洲人》与老舍的《正红旗下》性质相似,虽然都以“我”作为叙述口吻,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并非完全写实。在勒·克莱齐奥的成长经历中,非洲的驻留时光占比不大,他对于那里的了解可以说是借成年后的再游历经历相对补全的。此外,作者还回顾了“我”的父亲青年时期在英国伦敦大象堡街区圣约瑟夫医院(Hôpital Saint Joseph d‘Elephant &Castle)学医的经历。父亲学业结束后被指派给南安普顿医院(Hôpital de Southampton)热带疾病部,引人关注的是,父亲这段经历在《革命》中已然出现,只不过被移植到了青年时期的让·马罗身上:让·马罗在同处于大象堡街区的圣托马斯医院(Hôpital Saint Thomas)学医,并于南安普顿医院实习,该院最终也向他提供了职位。早年的经历与自身的家族故事成为两位作家家族叙事取之不竭的素材,二人借助回忆以虚实融汇的组织方式中呈现家族生命的广度。小说人物命运也是对自身经历的另一次平行写照,一次遐想中的寻根之旅。
勒·克莱齐奥对于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还深入语言层面。他对于克里奥尔语(法语基础上与毛里求斯当地语言衍生出来的混合语:la languecréole)的热忱也可通过作品人物的态度传递:“克里奥尔语,卡特琳从未忘记。”他在多部家族史作品中均直接引用了克里奥尔语词汇。譬如“滴洛(Dilo)”代表“水”;卡特琳姑婆为讲的克里奥尔语谜语:水站着(Dileau dibout 意为甘蔗)、水躺着(Dileau coucé意为西葫芦);展现姑婆生活态度的座右铭“无所谓”(Napasfer narien)和“又能如何”(Ki péfer)等。该语词汇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出现频率不低。而现实中,勒·克莱齐奥也曾与妻子热米娅(Jemia LeClézio)于1990年合作出版过一本面向青少年的口袋书:《克里奥尔谜语,以及克里奥尔语和鸟类词汇的小词典》(Sirandanes,suivies d’un petit lexique de lalangue créole et desoiseaux),旨在向法国新生代翻译、介绍最常用的克里奥尔语谜语与词汇。语言是回忆的关键词,也是日常生活细节的忠实记录。勒·克莱齐奥与老舍,一个是毛里求斯后裔,一个是满族旗人,二人同样注重本民族传统语言在小说文本中的使用,对极具方言特色的词汇均展现出非凡的兴趣。老舍长期吸收满语、“京腔”进行文本创作,他拥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满汉兼收。法国研究老舍的著名学者保尔·巴迪(Paul Bady)曾在1982年于法国出版的《北京市民》(Gens de Pékin)序言中提到:“在所有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中,老舍是在文学中充分发挥说话语言长处的先驱者之一。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中,他对语言的运用是最好的。别的人有时把‘白话’和西洋化的句法及词汇混为一谈。而老舍运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其运用手法之娴熟真是天才。”①保尔·巴迪:《小说家老舍》,吴永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45页。老舍行文中引入了大量的满语词汇,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满族人称新生儿降生的“落草儿”;影射大姐姐夫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北京土话“玩鹞鹰子”;代指丈夫子女俱全,有福气的妇女的“全口(ke)人”等。生动有趣的方言词汇出现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使得细节更加丰满、可感。
最打动勒·克莱齐奥的老舍回忆也激起了他自身的回忆。他对回忆的追溯也是对身份认同的探求。原来,家族的记忆是可以真切地影响到后人身上的,经历、风俗、语言都是作家成熟的宝贵财富。正如勒·克莱齐奥曾说:“创作就是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怀疑的、混乱的时代里人类生活的真相,就是要记下人类生活的足迹。”(《老舍,北京人》:162)两位作家的家族叙述充分与个人回忆结合,勾勒生活图景,小说于是成了现实生活的反映。真正的作家并不自己说话,他们所创造、呈现的人、物皆具有表征意义,这些元素将大量信息以间接方式传递出而出,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文明的全景记录。
三、为“正在消失”的文明和族群发声
勒·克莱齐奥认为老舍实际上代表着满族文化,和他身后的毛里求斯族群一样,逐渐走向边缘化、丧失话语权,都属于“destribusen voiededisparition”①勒·克莱齐奥2014年11月接受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访谈:https://cn.ambafrance.org/Entretien-avec-Jean-Marie-Gustave-Le-Clezio[2014-11-30],即正走在消失道路上的族群。的确如此,老舍许多作品都着力表现了视界内满族人民的生存危机。这代人只赶上满人朝廷的“残灯末庙”,封建王朝的制度、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烂透。《正红旗下》中“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领子的参领,可儿子福海竟然是个油漆匠!只因次子顶不了父亲官职,二哥福海选择另学手艺谋生。满族人的佐领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老舍,1980:33)。近代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即便民间少数地区有“反清复明”成“扶清灭洋”的动向,但满族人内受排挤、外遭压迫的窘境仍未改变,更遑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老舍一方面感慨旗人制度和满人朝廷的固步自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熟透了的旗人,他正如二哥福海那般“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老舍,1980:30),所受的多元教育使他未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囹圄,他所忧虑的不仅是满族,而是外来文明及殖民侵略对这种杂糅的民族生态的冲击与破坏。正如勒·克莱齐奥在法文版《四世同堂》卷一序言中所说:“老舍的一生忠实于这个城市,忠实于革命理想,但始终保留这种不确定及孤独感,这种感情使他接近被强者背叛的、作为‘屠杀、抢劫、侵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小人物——就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师者,老舍》:166)这种时节,不仅满人,而是整个北平的居民,乃至全中国的同胞,都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他对旗人血缘的所忠使他接近这个羸弱负重的民族,他对北平市巷的归属使他接近底层的居民,他对中国的信仰使他为湮灭危机中的苦难同胞们忧心。存亡之际,沉默即背叛。老舍需要发声,为无权说话之人说话。保尔·巴迪了解老舍所哀:“在明天的社会中,他喜欢在小说中描绘的人物注定要消失。”②Paul Bady,―Pékin ou le microcosme,dans‗ Quatregénérationssousun même toit ‘ de LaoShe.” 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60,Livr.4/5(1974). pp.327.如果无人触动,届时老舍所熟悉和喜爱描绘的人物们,或都将成为了时代的旧民,逐渐消失地无影无踪。勒·克莱齐奥在老舍处找到了慰藉,终于他的逃离也非曲高和寡,在大陆东端,也有那么位捍卫衰微文明与没落族群的守夜人。
勒·克莱齐奥秉持着与老舍类似的担忧。在我们提及的这一系列家族史作品中,他以寻根之旅向读者揭示鲜为人知的秘辛,跨越广阔地域追寻家族印记在不同时空与自身的相遇。最初谈及作家勒·克莱齐奥,多数人都会对他作品中的世界性记忆犹新。这位作家似乎一直在“游离”,读者认为其在作品中深植“地理魔力(géographie magique)”,欧、亚、非、美等洲的各国,他都有写过,他曾被认为是“一位旅行者作家(un écrivain voyageur)”,但这一说法随后被作家本人否认,他认为这种丰富的地缘关系是一种“内化在想象与记忆当中的旅行(un voyageintérieur liéàl‘imagination et àla mémoire)”。①勒·克莱齐奥2014年11月接受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访谈:https://cn.ambafrance.org/Entretien-avec-Jean-Marie-Gustave-Le-Clezio[2014-11-30]客观上来说,这种风格的形成受到作家丰富家族地缘影响,他具有法国、毛里求斯的双重国籍,父亲是英国人而又在非洲呆过数年。其次,勒·克莱齐奥本人的异国游历经历丰富,曾于英法学习,泰国服兵役,墨西哥工作,非洲生活。虽然跨越多地,但是他的家族叙事并非是迁徙史,与所谓的世界性恰恰相反,他向我们所展示的反而极其私人化,他以诗性的语言在回忆与想象中向我们讲述他的家族故事。勒·克莱齐奥不写旅行,只是他的家族故事恰好建立在丰富的地缘关系之上。家族部署的流动性赋予他更高的地域接纳度,家族不再指向束缚与桎梏,而是意味着更多潜在的连接。家族记忆落在他身上成为融入别处的通行证:无论是父亲的非洲、外公的毛里求斯,通往这些世界大门的钥匙都在他手中。但连接多样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出每处都交浅?这些“握在手中的世界”终将如逐渐模糊的记忆一般历经新秩序对它们的抛弃。于是作家以回溯的方式寻找他被别处“旧梦”影响的根源,一次次的寻根之旅是他对家族历史的尊重,对往昔记忆的挽留,也是为他所代表的“正在消失“的文明和族群发声。
在作家的家族叙事中,对没落的怅然尤以《变革》为盛。对于逝去的毛里求斯时光,作家反复提到了罗兹利斯老宅(Rozilis)。罗兹利斯老宅象征着他身后一整个海岛族群的文化背景,和当时被铲除的房屋一样,这一整个旁支的文明如今也危如累卵,欧裔毛里求斯的历史正在消失殆尽,毛里求斯岛也已经不复从前面貌。它们仅是被少部分人的记忆唤起,或许不久地将来他的后代也只能在前辈的叙述中捕捉零散的家族记忆。让·马罗梦回罗兹利斯,战争,让看够了。他向往爱贝纳的荫蔽,童话般的自然歌谣在梦中流转;他向往婆娑绿影里的罗兹利斯老宅,马罗家族的昔日的蓬勃与生机。作者用“如梦童年(Une enfance rêvée)”来形容小让·马罗在尼斯的童年生活,因为他在拉卡塔薇娲公寓的阁楼里聆听姑婆所讲述的罗兹利斯过往是那般鲜活、如梦如幻,超脱现实的死寂与逼仄,带给他无限的慰藉。与令人失望的战争现实相比,罗兹利斯的惬意时光令人无比憧憬。那里的缓慢的节奏以及与自然融洽的共生仿佛就是一处“伊甸园”。无论是小说中还是现实里,勒·克莱齐奥都不愿意欧裔毛里求斯的文化痕迹逐渐消逝,他对那里的感情,正如北平之于老舍。勒·克莱齐奥曾写道:“如今,在推土机的进攻下,胡同这个老舍小说的‘主人公’难逃消亡的厄运。”(《师者,老舍》:169)胡同的消亡必然昭示着老舍所钟爱的描写对象——北平小市民的隐遁,而罗兹利斯老宅的消逝也恰恰宣告爱贝纳的“伊甸园之殇”。他对海岛族群的寂静抱有担忧,在他的家族叙事中流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如果不愿如主人公让·马罗一般只能在记忆中梦回梓乡,他必须发声。现代文明快节奏的更迭创造出一种空虚,作家对城市生活的空洞感到无助:“城市说到底很像医院的老年楼。一座悬崖,男人女人都挂在悬崖边上,下面是遗忘的大洋,活着的人残忍地推着他们向前走,每日、每夜、每刻。”(勒·克莱齐奥,2018:171)遗忘是人的本分,无论让·马罗如何向往,罗兹利斯的时光依旧逝去,时光覆水难收,所有的家族记忆在楼房瓦片的森林里,拉卡塔薇娲的阁楼顶部,卡特琳姑婆——一个失明的老妪的回忆中展开:无比脆弱。
法语文学翻译家金龙格曾评价勒·克莱齐奥是关注边缘人物的人文主义作家。小说《变革》中,勒·克莱齐奥借寻根之旅点燃了关注远方边缘族群的火炬。“这是大海那头的秘密,这个秘密令人失去了自己的根,不仅失去了罗兹利斯这一座房屋,还让人失去了整个毛里求斯,那里的天空、山岗、河流……。”(2018:24)其实单就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毛里求斯之于他并不像北平之于老舍那般熟悉,甚至他所描绘的毛里求斯的许多细节在后来向真正在那生活过的人求证得到的答案都是:并不存在。显然可见,高度还原并非他的目的,还原仅是作家唤起人们关注意识的一种手段罢。行文时屡次出现的克里奥尔语词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呢?甚至我们还可以在《饥饿间奏曲》的前半部以及作者的“非洲情结”中继续看到对边缘人物的关注。
在巴黎,布伦家族实为非主流文化移民的新贵。艾黛尔父亲亚历山大当年那个从海岛弹丸之地走出来的毛头小子引领着家族登上了巴黎的贵人台阶,即便发家,他们仍然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但作者的态度并不是讽刺,他写道海岛的人有着“唱歌一样的口音”。最后人物的命运也是笔者态度的彰显:大嗓门的姑姑们盼到了战后的团聚,憨厚、爱脸红的留尼汪小伙罗兰·费尔德成了艾黛尔的丈夫,他们一起挺过了战争与饥饿的艰难岁月。而反观亚历山大在巴黎的那位情人,当年何等风光的女歌唱家莫德,最后沦落到每日靠到集市上捡烂菜叶、到营地上为德国人卖唱度日营生。她代表着巴黎,原来的繁华巴黎在腐烂变质:“轻佻的高个子女郎变成了贫穷潦倒的老妪,眉清目秀的潇洒小伙子变成了弱不禁风的老翁。”(勒·克莱齐奥,2009:46)在《非洲人》中,作家借以非洲土地作为一个“理想国”来逃避自身所处的世界,为此他希望孕育自己的母亲是非洲人,如此就为自己安排了生理层面上寻根的合理性。但是直到父亲退休回到法国与他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才恍然发现,原来他的非洲基因早已种下,父亲才是真正的“非洲人”,正是常年在非洲行医的父亲,将非洲大陆的记忆承袭到他身上。其实,父母辈从非洲带回来的记忆一直萦绕着他,他的“非洲情结”并非全由童年短暂的非洲之旅造就。映照在父母辈身上的时光旧梦,最终转嫁在他身上,帮他构筑起一个遥远的非洲故乡。正是在这个非洲故乡,他看到了这里人民的羸弱和苦难,看到了他们被遗忘的沉默与无奈。作家借家族中“我”的父亲说出心中希冀:“远离海岸那个利益至上的腐朽社会,他梦想着非洲的复兴,从殖民桎梏和流行病的宿命中解脱出来。”(勒·克莱齐奥,2012:112)在见到无数孩子们因为饥饿和脱水而死去,作者的心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伤。一个曾经度过童年时光的柔情土地,何以成为万千人的坟墓?他引用了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诗歌抒怀,与这位英雄斗士般的反殖民者共同诵读世界对这片土地本不该有的忘却。
老舍和勒·克莱齐奥都是真诚而孤独的人,文化阻隔无法中断他们之间的共鸣。和老舍一样,勒·克莱齐奥总是能关注到正在消失的群体。时代在进步,但总有人摔跟头。正如家族之中有青壮,也有老弱。他们的发声不是偏激的卫道,而是生而为人不应摒弃的宽容。
结语
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的家族叙事受到老舍影响。这位法国作家欣赏老舍,称几乎读过老舍的所有作品。新世纪伊始,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明显的家族史方向倾斜,这与上世纪末老舍重要家族史作品在法国翻译出版存在相应关联。勒·克莱齐奥对老舍的家族叙事体系采取了积极的接受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以家族叙事框架表现时代变革与人物迷惶、充分与个人回忆相结合,展现生活图景以及为“正在消失”的文明和族群发声三个主要方面。两位作家的家族叙事是一次变革、磨难中的相遇。一方面,老舍对于家族意义的构建是对永恒价值的期许。他从小长在北平,对这里包含感情。对他而言,家族不仅是氏族血缘的联结,也是建立在地缘、劳动之上的稳定关系的维护——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在老舍所构建的家族体系中,我们看到家、城、国是有机的统一体。而另一方面,勒·克莱齐奥所突出的家族价值则更呈现出离散性、世界性。丰富的异国经历影响了其文本中的家族构建,“流动”是家族活动表现形式之一。同样,他也不再侧重聚焦于人物与土地的联结关系,而是穿越不同文化气息的地域,深入探索:哪里才是“我”真正的精神故园——一个使人无须继续迁徙能够停留、享受的“世界尽头(Le Bout du Monde)”便是吾乡。此外,叙述口吻方面,勒·克莱齐奥一改老舍说教式的忧心,即便面对宏大的战争、变革,他仍然把语言塑造得如梦如幻,透露出沉浸式的散漫甚至是疏离。
尽管两位作家的家族意义建构、叙述风格、所关注的边缘人物不尽相同,但二者殊途同归。家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常见单元之一,它可以见证时代、反映社会变迁,也尤其是展现人类生存、精神危机的窗口。面对时代冲击,他们以文字申诉,同样苦于无解决之道,但无论是“说教”还是“说梦”,两位作家的家族叙事对在时代变革下危机里挣扎的普通人都饱含伤感之怀,而非简单局限于满人和欧裔毛里求斯人。
如今,研究勒·克莱齐奥,“家族史”或可成为不可绕过的标签之一。从《变革》到《非洲人》再到《饥饿间奏曲》,勒·克莱齐奥一连串对于家族主题的把握清楚地表明出自己的一个创作动向。家族,一个庞大且令人敬畏的主题,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生存中众多基本思考。我们相信,探讨勒·克莱齐奥其对“师者”老舍的家族叙述接受仍应具有更广阔的文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