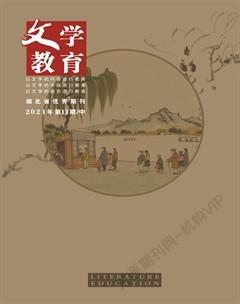《伦敦郊区》日常生活伦理与叙事艺术
汪婷
内容摘要:《伦敦郊区》中克里斯从少年的激进艺术观到成年后的平庸艺术观的转变,似乎表明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城郊生活的变化对其艺术观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小说中具有自反意识的叙事不仅可理解为克里斯建构叙事身份的努力,也可看成克里斯及巴恩斯建构日常生活伦理的尝试。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克里斯艺术观念的变化,探讨《伦敦郊区》的叙事艺术以及所表达的伦理思想。
关键词:善 日常生活伦理 叙事艺术 资本主义价值观
朱利安·巴恩斯(1946-),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与评论家,被誉为“英国文坛的变色龙”。他的处女作《伦敦郊区》(Metroland)一经发表,就获得了毛姆文学奖。该小说是克里斯在“自我探索”后得到的“自我发现”[2]45,克里斯面对资本主义技术文明和物质文化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一影响下,其进一步探析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从而实现了所追求的艺术理想。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人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态度的变迁,探讨这部小说所建构的日常生活伦理及其内涵。[1]
一.激进到平庸
作为资产阶级舒适的家,伦敦郊区不只是住宅集合区,更表达了根植于资产阶级文化且被称作“乌托邦”的价值观。克里斯认为这样舒适的生活只是以他父母为代表的城郊居民的追求,认为他们都是“精神上的流浪者……空虚得让人无法忍受。”(32)相反,他追求无归属,渴望未来能达到漂泊无依的状态,并以一种“狂热的愤世嫉俗”(15)的姿态表达出自己想要逃离伦敦郊区的愿望。
克里斯宣称自己的座右铭是“压垮卑鄙者”和“突袭资产阶级”(15),与托尼闲逛时,他提议捉弄资产阶级;在去学校的路上,他也热衷于在火车上抢占资产阶级最喜欢的座位。克里斯的叛逆来源其崇拜的法国文化,尤其是那些与反抗资产阶级道德最密切相关的法国作家,“我们喜欢法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因为它的好斗性”(16),“这是青少年势利和自命不凡的缩影”[3]15。少年克里斯的叛逆与其说是“受制于‘愤怒的年轻一代的政治隐喻”[2]53,不如说是其信仰根植于19世纪晚期的美学主义中。克里斯信奉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认为艺术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使人们变得更好——更友善……更敏感。”(29)此外,克里斯还将文学艺术作为克服“死亡恐惧”的替代性信仰(53),是他抗诉学校教育的“不满”(39)、抵制郊区生活的“无聊”(53)、抗击“资产阶级社会名人”(14)、理解多重“生活意义”的有效工具(31)。
小说第二部分描写了青年克里斯在巴黎的留学生活,其也见证了克里斯艺术理念由激进到平庸的过渡。克里斯宣称自己访学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融入法国文化,然而,他非但没有加入法国学生运动,甚至宣称“自己什么也没看到”(76),“几乎完全无视周围传统权威所面临的挑战”[4]25,讽刺的是他清楚地记着自己失去童贞的日期。这一现象表明了克里斯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忘记了少年时“自封的反资产阶级革命”[2]56。
在与法国女友安妮可交往过程中,克里斯学到了一种新的态度:真理不必通过战斗来达成、诚实的回应和表达都是有价值的。当安妮可询问他从何处学会了性爱姿势时,克里斯坦诚看过有关性爱的书,他的诚实回答换来了安妮可的微笑。性爱中的诚实让克里斯感到无比的放松,而性也使得克里斯变得成熟。在和安妮可的交谈中,克里斯认为没有必要用“任何虚构作家的作品”来获得真理(101)。由此可见,克里斯不再尝试用艺术来追求真理。由于内心的不安,克里斯将自己与马里恩相识的事情告诉了安妮可,他想表达“我爱你”,却犹豫说成了“我很爱你”(122),这使得安妮可最终决定和他分开。在安妮可离开后,克里斯重新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实践,艺术再一次成为了他内心的信仰。
在第三部分中,克里斯显然放弃了艺术,遵从了他十几岁时所鄙视的郊区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给他带来了快乐,塑造了他的身份,而艺术对他在伦敦郊区的成年生活意义不大。“我想我现在一定成长了”(133),这句话“既可以解读犹豫不决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解读为听天由命的决心”[4]37。一方面,克里斯已经到了心理成熟的年龄;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必须像个“成年人”一样行事,因为他有家庭和抵押贷款等责任。成年克里斯满足资产阶级的生活,满足科技带给他的便利。克里斯就曾为回到童年时被称为“病毒”的伦敦郊区而感到讽刺(135),却又感叹满足其便捷生活。此时的克里斯已抛却了少年时的叛逆精神和艺术理想,对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深刻联系失去了信心,他已成为资产阶级权势人物。
二.敘事艺术
与托尼的交谈使得克里斯陷入了婚姻焦虑中,在得知马里恩曾有过婚外情后,克里斯安慰自己“没有什么”(163),他以拼命做爱的形式接受了妻子的出轨。面对妻子的不忠,克里斯表现出的大度与日常生活价值的“善”的道德观相符合。
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查尔斯·泰勒提出自我是道德空间中的自我。道德空间构成了人们自我认同的基本框架,人们只有在这个框下才能使人格完满。“框架表达着有关善的问题空间中的我们的方向感”。[5]60泰勒认为自我与善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将自我与善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善的指引,我们将无法获得完整的自我的概念。“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与多元善共存,还必须为它们排序”[5]93,在排序后,将会发现独特有价值的善,而这独特的善会“提供判定自己生活方向的路标”[5]94,在它的指引下,自我可以确定自身并可以形成认同。
泰勒坚信自我要靠善来引导。他认为生活之善是“性质差别所规定的善是善良的生活的侧面或组成部分”[5]139,它确定了道德生活的内容。成年后的克里斯追寻体现个体独特性的生活方式,他不仅承担着家里的日常开支,还帮妻子分担家务活。当夜晚克里斯去安抚哭泣的女儿时,称赞了地毯、中央暖气等,这体现了物质上的舒适感让他感到一种“懒散的快乐”(176)。在述说这种快乐时,克里斯说明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展现了生活之善。
与托尼的对话,让克里斯意识到艺术的价值“取决于内在信仰”[2]64。从艺术殿堂巴黎回到曾被自己称为梅毒的伦敦郊区定居,克里斯自己也觉得无比讽刺。“我想我现在一定成长了”(133),这句话“既可以解读犹豫不决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解读为听天由命的决心”[4]37。克里斯的编辑工作,看上去似乎是对生活与艺术的妥协,但同时也是满足他文学兴趣和谋生的一种方式。虽没有少年时的激进艺术观,但“克里斯对日常生活的拥抱也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对艺术理想的抛弃”[2]61,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拥抱强调了“善”的价值观。
泰勒认为确立自我与善的关系就要叙述性理解自己的生活,即用叙述把握自我。《伦敦郊区》不仅是第一人称叙述主导的,而且是由叙述者回顾性地讲述的。小说的叙事基调总体上和蔼可亲,充满讽刺意味,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讽刺意味变得更加明显。讽刺程度的上升不是偶然的,它强调了一个事实,“成长的一部分是能够驾驭讽刺而不被抛弃”(135)。“叙事在构建与人物身份相一致的情节的过程中,造就个体可称为叙事身份的稳定特征。”[7]77随着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变化,克里斯的艺术理想从少年时的激进、青年时的清醒转变为成年后的平庸,表明他试图建构自我。
《伦敦郊区》是一部“机智的成长小说”[3]8。克里斯的成长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与巴恩斯本人的成长轨迹相似,如两人都是在伦敦的某所学校上中学,都迷恋法国文化,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都是教师。也就是说,该小说的取材完全来自于巴恩斯本人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在小说的最后,克里斯完成了从编辑向作者身份的转变,而这一变化与巴恩斯本人的经历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巴恩斯也经历了从教师、编辑、翻译到作家的转变。巴恩斯借助克里斯这个角色,不仅确立了自己作者的身份,还建构了日常生活伦理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Barnes, Julian. Metroland[M]. London: Vintage, 2009.(下文凡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只随处括号标注页码)
[2]毛卫强.《生存危机中的自我与他者——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3]Guignery, Vanessa.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4]Childs, Peter. Julian Barne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11.
[5]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12.
[6]马庆.《多元论下的本真性理想——查尔斯·泰勒现代性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7]Ricoeur, Paul. — “Narrative Identity”[J]. Philosophy Today, 1991a (1): 73-81.
基金資助:江苏大学第20批大学生科研课题项目“日常生活伦理与技术批判——《伦敦郊区》叙事艺术研究”(20CI0006)。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