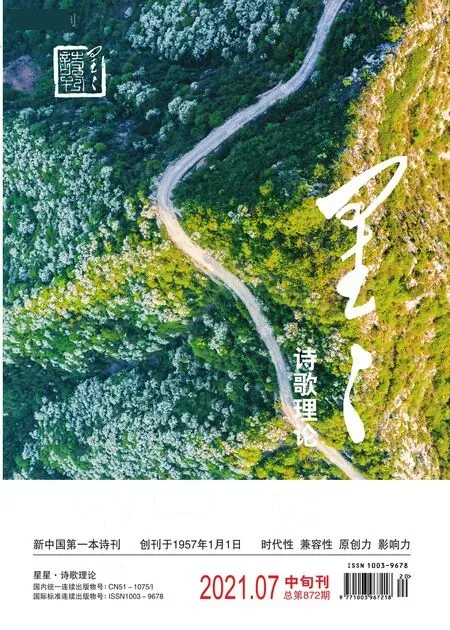军旅生涯如何成诗
——读刘立云的诗
>>>王辰龙
刘立云曾坦白道:“我从来不否认,我长期在部队服役,长期与军旅诗的创作和编辑出版纠缠不清。”从诗人对创作的自我鉴定中可知,对他而言,职业本身成为写作的一种原动力,也在题材层面上构成他诗歌谱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作为类型化的文本,刘立云谈及的“军旅诗”,其价值之一是使大多数人视野外的部队生活得到具体的呈现,令大众想象中略显虚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变得可知可感。不难发现,刘立云的“军旅诗”有军人充沛的见闻,但更可贵的是,他诗中有军人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印象里军人训练有素、不苟言笑的神态也随之多了几分俗常的情绪。诗人笔下,富于自传色彩的军人形象也会有不安和煎熬,例如,他在《四十二年那么厚的一种钢铁》中写道:“冰天雪地。生命中的第一班岗/旷野上的风像一群猛兽/在相互厮打,吼声如雷;有几次把他置身的岗楼/推搡得摇晃起来。他下意识把手/伸向扳机,又下意识/缩回来/他感到他触到了一块巨大的冰”。诗人追忆着“生命中的第一班岗”——野兽般的狂风,如冰的扳机,刘立云借助比喻使记忆中的场景由遥远变得恍若昨日,当年凶险异常的环境跃然纸上,历历在目。紧接着,诗人连用两个“下意识”的动作,精准传达出战士的紧张,以及“他”内心深处些许的恐惧。刘立云并未以英雄主义的方式去再现军旅生活,他没有刻意地把军人写成别样的群体,而是通过塑造特殊岗位上的凡人来达成两个层面的诗意:首先,任何身经百战的优秀战士,都是普通人在承受、克服诸多困难后才能完成的蜕变,也正因其艰难,方显可贵,这确保了“军旅诗”礼赞军人的诉求;其次,对特殊岗位背后的人之常情做剖白,随之构建起军旅生活与大众之间的情感相通性,读者面对的将是具体的人,而非概括性的职业,这也使“军旅诗”避免成为只有少数人能切近的独白。于是,从刘立云诗中可读到的军人心迹是曲幽的,如:“当我破碎,当我四分五裂,你知道/我的每个角,每个断面/都是尖锐和锋利的”(《玻璃》);“它肯定看见我内心凄楚,眼里含着一大滴泪”(《河流的第三条岸》)。
顾名思义,“军旅诗”主要指由有参军经验的作者写的、以军旅生涯为主体的诗歌,呈现部队生活以及士兵的见闻和体验是其专长。这一点,刘立云的作品也不例外。但在阅读他的过程中,有一个主题范畴外的话题逐渐清晰甚而尖锐了起来:作为个体经验的军旅生涯,直观地构成了诗歌内容的核心;但在此之余,它是否已被诗人转化为某些内在且独特的修辞方案?在题材上传达别样的生活,确实是“军旅诗”这种类型化诗歌的价值所在,然而,若就信息获取的丰富、全面和及时而论,去翻阅新闻报道或以叙事取胜的军旅小说,较之于读诗,想必能更有效地了解到部队是什么、士兵是谁?在如今这热点横飞、事件喧嚣的时代,诗人理应思考诗歌在当下整体文化语境中的位置和紧要性,寻求一种必须用诗而非其他方式去言说的缘由。独特的经验只是内容有新意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它不能与优秀的创作直接划等号。假如一个作者反复透支有限的个体经历,同时又缺乏由“一”到“多”的审视精神,最终抵达的,极可能并不是文本的深度,而会落入内容重复、意义浅显的窠臼。据此来考察刘立云诗歌中经验与修辞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说,诗人的军旅生涯已有效地转化为诗歌的修辞方案。在《玻璃》中,诗人将“我”的生存境况喻指为“玻璃”,推演它的“安静,薄凉/保持四季的恒温”的状态,预感着它最终的“破碎”和“四分五裂”。围绕“玻璃”的象征意义而展开的想象,似乎与军旅生涯没有关系,但诗中有这样一句值得注意:“现在我磨刀、擦枪/每天黎明闻鸡起舞/在奔跑中把一截圆木扛过来/扛过去”。玻璃的诞生需要经历由熔铸到定型的几番曲折,当它被用以形容生命,或许表征了个体因持续的承担和磨炼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一如上述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不论是“磨刀”“擦枪”,还是“闻鸡起舞”时肩负重物的折返跑,显然都与军事训练的经验相关,军旅生涯为诗人的想象力提供了细节充沛的支撑,使诗中的象征意味不失之于抽象、空疏。另一首《十二道门》里,面对靖西边地山冈上默默矗立的古堡,诗人未曾空想式地去揣测遗址的往事,也没有拾人牙慧,重复别人对古堡的讲述。诗人发现了古堡与军旅生涯之间的相似性,并把这种相似性逐步地从表象推进到精神纵深的层次,他写道:“一座叫十二道门的古堡/默默地矗立在靖西边地的这座/山冈上,就像我曾经默默地矗立在/我十八岁的哨位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其实在我的身体里就藏着这样一座古堡/你看不见它。我戎马一生/枕戈待旦一生/我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兵不卸甲/我就是可以随时关闭或打开的十二道门”。不仅是古堡引发了诗人对军旅生涯的回顾和总结,金戈铁马间的生命片断及其蕴含的意义也重新构筑了古堡的形神,使之从无声的景观幻化为崇高的纪念碑。在《四十二年那么厚的一种钢铁》中,诗人将十八岁从军到六十岁退休这四十二年的生活历程想象成钢铁,他写道:“他当的是炮兵/用破甲弹打坦克那种/当时他又想,那么四十二年近半个世纪/那么厚的一种钢铁/用什么弹头,才能将它击穿?”正是基于军旅生涯的经验,使诗人将年华逝去想象成弹头击穿厚铁的过程。
遥想当年辛弃疾,他常以“草木皆兵”的诗心,将戎马半生的经验转化为用军事意象摹写风物人事的修辞方案。反观刘立云的诗作,军旅生涯已延伸出去,进而在想象力、感受方式等层次上生长为诗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