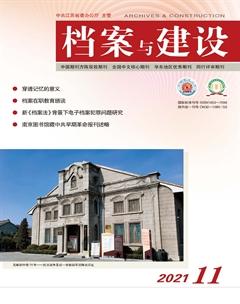档案在职教育琐谈
摘 要:基于对档案在职教育相关研究的文献分析,厘清档案在职教育的“我者”(即档案在职教育所隶属的职业)存在职业主体规模较小、职业环境因素多变、职业人员归属不明等现状,以及档案在职教育的“他者”(以相对独立于档案在职教育的档案高等教育为典型)存在与在职教育的区分度不高、与国外经验重合度较高、与档案职业渐行渐远等问题之于档案在职教育的影响,探讨档案在职教育研究和发展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及破解思路。
关键词:档案职业;档案在职教育;职业教育;档案高等教育
分类号:G27
On Archival On-the-Job Education
Hu Hongjie1,2
(1.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Secretarial Science Committee, of Chinese Society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41)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Archival On-the-job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problems of archival on-the-job education caused by both " My origin" (refer to archival occupation to which archives on-the-job education belongs) and " The others"(taking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as a typical example), such as subject scale, environmental and attribution of archival occupation, as well as Chinese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s distinction from onthe-job education, coincidence with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istance from archival occupa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and solutions to archival on-the-job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in China.
Keywords:Archival Occupation; Archival On-the-job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筆者1982年入职国家档案局教育处,那时国家档案局还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务院直属机构[1],国家档案局的教育中心也没有成立。教育处的基本职责有两项,其一是档案教育,其二是职称评定。因此,如果从那个时间算起,笔者的从业经历应该有几十年的光景,尽管其后的“职业”有所变更,但始终与“档案教育”难脱干系。[2]换句话说,在目前档案学界、业界所有“领军人物”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史前史”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再不论及档案教育领域的问题,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1 文献中的档案在职教育
综观近几十年档案学界、业界的研究领域,包括在职培训在内的档案教育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档案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笔者将观察的重点放在档案在职教育方面,以避免画蛇添足。
1.1 文献概述
笔者于2021年10月21日以“档案在职教育”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查找到有关文章67篇,分布在在职教育、全员化、档案专业、岗位培训等研究领域。在这些文章中,位于前6位的作者是胡振荣(3篇)、王培培(3篇)、李海英(2篇)、王燕燕(2篇)、连念(2篇)、翁勇青(2篇)。其中,胡振荣来自湖南省档案局,王培培、李海英和王燕燕来自北京市档案局,连念和翁勇青来自厦门大学。择其要者,他们的基本观点如下:
胡振荣在指出了我国现阶段进行全员化档案在职教育培训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后,全面分析了我国档案在职教育培训由于认知、体制、社会、管理、文化等原因徘徊不前的现状,重点阐释了构建合理的全员化档案在职教育培训机制与体制的基本框架与思路,试图解决档案从业人员“想学、要学”到“必须学”的关键问题。[3]王培培在区分档案专业“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概念的基础上,从培养目标、培养手段、培养师资、培养周期四个方面叙述了两者不同的侧重点,并指明了在档案工作中,用人单位要适时挑选档案专业人才,不能用“学历教育”的培养标准要求“在职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不能用“在职教育”的培养标准要求“学历教育”培养出的人才。[4]此外,作为“档案在职教育评估体系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她与李海英还就档案在职教育培训评估与全日制高等教育评估的区别及其自身的定位,提出了评估指标体系及内容。[5]连念和翁勇青则主要介绍台湾地区档案管理人员在职教育培训情况,并分析研究其特征和特色,以期有助于海峡两岸档案工作的交流互补与发展。[6]
据此不难发现,档案业界对档案在职教育的关切程度要略高于档案学界。个中缘由也不难理解,毕竟档案在职教育是档案职场的事情,业内人士应该更有发言权。而令笔者奇怪的是,档案学界与其他学界的最大区别在于“参与政务”,缺席档案在职教育研究有些不太正常。进一步观察则发现,学界“缺席”只是表面现象,其主要遮蔽点在于在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的某种关联(混淆)。
1.2 文献分析
从上述档案在职教育的发文量、作者分布及主要观点来看,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状况。
第一,档案在职教育的关注者不多。中国知网的数据是从1980年代到2020年代,总计发表文章不过67篇,如果剔除其中的重复发文和一些消息稿,这个总量还会大打折扣。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档案在职教育相对比较简单,无论讲授内容还是教育体系乃至教育需求,都无法构成一种成熟研究方向;其二是档案在职教育领域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或者已经被另外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所替代。简单地说,就是档案在职教育不成熟或者被包容。因此,要么无话可说,要么该说的话已经被其他人说了。
第二,档案在职教育的研究视角单一。从主要发文作者的机构来源看,基本上都是档案局或者档案馆的人员,文章大多数也是由于工作需要写就的成果。也就是说,档案在职教育的研究基本上仅限于档案业界。就事论事的文章,势必在研究视角方面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随着1993年之后的“局馆合一”,[7]档案业界大都参照了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档案职业的技术特征进一步被行政人员的管理要求所替代,从业人员的研究热情随之降低,写文章自然就成为一种“奢侈品”制作,非凤毛麟角而不能为之。
第三,档案在职教育工作相对薄弱。一直以来,我国档案在职教育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政策引导,即为了宣贯某项政策法规或者传达上级领导精神而开展的活动;其二是重复以往,即不断循环着档案管理的基本业务环节,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档案职业的发展和职业岗位要求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在职教育的研究多少有些无的放矢。
第四,档案在职教育的领域尚不明确。档案在职教育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档案工作人员入职后的岗位培训,还应当而且必须包括档案工作人员入职前的教育形态。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广谱性,即根据档案工作人员的基本职业特征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比如,既包括思想品德、基本理论,也包括专业素养、工作技能、业务环节及提升方法等。而在我们国家,这些领域基本上被纳入到档案高等教育的领域。无论是研究能力还是研究需求,档案在职教育都不可能与档案高等教育相提并论,进而必然会失去一些研究空间。
因此,档案在职教育的研究,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没有达到相当的研究水平,甚至几近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境地。
2 思考中的在职教育
就像一些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会产生一种特殊情感一样,笔者的工作经历也会多少影响自己的研究志趣。或者说,是因为对自己倾注一定热情和时光的事情,长期沉浸其中总会产生一些想法,不甘使其沉沦,凡此等等,总是觉得档案在职教育领域出现一些研究的问题,还是存在相当的提升空间,也值得下一番功夫辨其所以然。
2.1 档案在职教育的“我者”
所谓档案在职教育的“我者”,主要是指档案在职教育所隶属的档案职业。如果没有档案职业,档案在职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进言之,作为档案职业的组成部分,档案在职教育的开办、生存和发展都与档案职业的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档案在职教育出现问题,其根源还是来自档案职业。
我国档案职业的真正确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一些论者不断谈及档案工作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那些“源远流长”的档案工作并非现代意义的档案职业。所谓职业,基本上是指由特定功能和岗位构成的,具有有酬、连续、规范、稳定等特征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劳动分工。因此,并非所有档案工作都属于档案职业的范畴,也并非所有的檔案工作者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职业人员[8],近几年的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并没有包括“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档案馆”之外的企事业档案馆(室)人员就是一个佐证。[9-10]
199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大典》),档案职业被首次提及并列入其中。《职业大典》将职业人员分为8类,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军队人员和其他人员。其中,档案专业人员被归属于第2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10中类(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第7小类(档案专业人员),档案职业的代码为:2-10-07-00。在2015年的修订版中,《职业大典》再次明确将档案管理职业作为我国1481个社会职业之一,并将档案职业人员从档案业务人员改称档案专业人员。[11]
如果说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逐步职业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种职业化过程中对职业角色的认定则是一个不断明确的过程。档案在职教育无疑是这种“职业角色认定”的必然结果,即档案在职教育的出现,可以说明档案职业基本上具备了有酬、连续、规范、稳定等特征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劳动分工。当然,在档案职业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中,档案在职教育必然受到其渐进式的影响。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档案职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档案职业主体规模较小。根据2018年度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截至2018年底,我国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档案馆共有专职人员46412人(2019年降至41495人)。[12]其中,中央级653人,省(区、市)级3511人,副省级978人,地(市、州、盟)级9598人,县(区、旗、市)级31672人[13],档案职业人员数量仅占我国同年7.8亿就业人数的0.00595%。[14]如果按照《职业大典》的界定,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而非“专业技术人员”的话,这个比率还会更低。职业规模过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职业的发展及其社会地位。在经济学中,有规模效益的说法。所谓规模效益又称规模经济,是当企业的产量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各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了1+1>2的效应;也可以理解为即生产要达到或超过盈亏平衡点后所实现的效益。[15]虽然档案职业领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领域,但是规模过小必定会使其各种职业要素难于达到最佳的配置,也难于优化其业务工作环节。这就使得以档案职业“业务工作环节”为基本内容的档案在职教育失去了提升空间。
其次,档案职业环境因素“多变”。在档案职业研究成果中,论者通常都会有意无意地于文章标题使用状语。比如,信息时代、文旅时代、大数据视域下、区域性开放背景下、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等等。有学者戏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不小心在不長的几年中就经过了这么多的“时代”。玩笑归玩笑,但也说明了环境因素对档案职业的影响力。所谓环境,就是相对于中心事物的条件和背景。在行政学的研究中,专门有行政环境影响行政功能的内容。因此,职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档案职业内容的命题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我国档案职业自产生以来,其职业环境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档案职业的许多“业务工作环节”都会随着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进而使得以此为根基的档案在职教育缺少了稳定性,甚至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色。
再次,档案职业人员归属不明。1993年档案机构改革,各级各类档案馆成为了其属地档案局的另一个“牌子”,[16]档案职业人员也随之参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稳定档案职业队伍、提高工作人员待遇、统筹行政与事业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曾经是我国档案工作的特色和成功经验。然而,在这种“特色和成功”中,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机构政事不分、人员定位不明等。具体到档案职业领域,则集中表现为其“技术职业”的特征被行政特征所遮蔽。在档案职业人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的同时,其业务或者专业能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甚至在不断弱化。如此一来,被界定为技术类的档案职业,实际上是在向管理类职业靠拢。即便在2018年档案机构改革之后,部分档案职业人员还是“梦想回到过去”。长此以往,档案职业人员自然不大可能提升其“技术素养”,以此为基础的档案在职教育自然失去了发展动力。
在上述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档案在职教育无法进入良性发展的领域。加之一些论者极力推销的“国外经验”,也使得本来就根底不深的档案在职教育受到了疾风吹袭,一时间更加摇摆不定。
2.2 档案在职教育的“他者”
所谓档案在职教育的“他者”,主要是指相对独立于档案在职教育的档案高等教育,或者是独立于“我者”——档案职业的教育职业。从这个界定就可以看出,相对于档案在职教育的“他者”之体量。为了避免讨论的问题泛化至大而无当,本文将论及的“他者”仅仅限定于档案高等教育。
如果将1985年参加中央讲师团在河北大学档案学专业代课以及1996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执教的时间累计,笔者在档案高等教育领域的从业时间几乎超过了从事其他职业的总和,难免“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因此,说自己多少了解一些这个领域的情况,应该不算过分。
我国的档案高等教育自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专修科开始,至今已经有了近70年的光景。在近70年的发展中,档案高等教育从专科到本科、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目前基本上拥有了国家设置的所有高等教育层次的档案学专业培养方式。我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几乎用自己的成长历程诠释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已经被众多论者反复论证,已经没有多少锦上添花的空间。而作为本文所论及的档案在职教育之“他者”,笔者认为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似乎还有一些需要补正的地方。
首先,与在职教育的区分度不高。我国档案高等教育滥觞于档案工作的操作方法和业务环节,即把档案工作的操作方法和业务环节作为档案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反映在档案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乃至档案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这种情况在我国开办档案高等教育的初期是完全合理的,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的形式强化和弥补档案职业的实际需求。或者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形式的档案高等教育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作出了贡献。但时过境迁,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档案职业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包括在职教育在内的体系。如果档案高等教育还囿于传统的教学内容,一方面将限制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会挤压或者替代档案在职教育的空间。
其次,与国外经验重合度较高。我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势之一就是学习或者大量引进所谓的国外“先进经验”,以至于目前在我国档案高等教育领域所流行的理论中,真正属于或者源于我国档案职业领域的内容并不多,使得我国档案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外“先进经验”的试验田和推销点。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国外“先进经验”中,应当有一些是符合其原发地档案工作实际的,也可能在本国发挥过不错的作用,也不能排除这些国外“先进经验”会对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如果用这些国外“先进经验”完全替代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定是非常危险的。言及本文论题,如果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与在职教育区分度不高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我国档案在职教育领域普遍推广的是这些国外“先进经验”,进而使我国档案职业领域成为“国外经验的试验田和推销点”。
再次,与档案职业渐行渐远。包括档案高等教育在内的我国高等教育,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学习苏联模式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学习欧美模式,即从培养建设急需人才、发展专门学院到“宽口径、厚基础”。在此过程中,类似于档案学院这样的专门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特别是“211”“985”“双一流”等高等院校中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度挤压,开办教育的重点需要向“一级学科”倾斜。大学中一个“成功”的学院,往往要涵盖多个“一级学科”。这就意味着档案高等教育在上述具有示范效应的学校中很难独立生存,其招生数量、教师队伍都会出现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至少有两方面表现:其一是档案高等教育的规模缩小,在学院平台上档案学专业会不断地与“信息资源”“数字人文”等方向融合;其二是在已经“缩小”的档案学专业中,传统的档案管理内容也会相应减少,呈现去职业化的倾向。因此,原本可以替代档案在职教育的档案高等教育与档案职业渐行渐远。此外,由于学校教育的特点,许多所谓的教学实践环节都带有学生活动的色彩。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师生们都比较注重行为艺术的传播。进而使一些本该属于档案职业的“应知应会”,变成了可资渲染的内容。
如此一来,原本作为档案在职教育替代品的档案高等教育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泛化。不论这种“泛化”的价值与合理性如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档案职业的发展。
3 结 语
笔者认为,档案高等教育不能也不应该代替档案在职教育。档案在职教育是档案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档案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而发展档案在职教育的关键是健全档案在职教育的体系和课程设置。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开发模块化、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17]因此,档案在职教育,特别是入职后的教育和培训,必须以岗定教,符合在职人员的工作特点。[18]档案高等教育则可以适当拉开与档案在职教育的距离,按照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规律营造自己的发展空间。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学界的热点未必是业界所需,包括档案在职教育在内的档案职业之发展,应该按照自身的规律前行。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天津市档案局编.档案工作手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393-395.
[2]胡鸿杰(仿鲁).发展中的档案教育事业[J].档案工作,1984(05):18-20.
[3]胡振荣.基于全员化的档案在职教育培训机制与体制的构建[J].档案学研究,2011(04):71-74.
[4] 王培培.关于档案专业学历教育与在职教育侧重性的探讨[J].继续教育,2015(04):24-25.
[5]李海英,王海燕.论档案在职教育培训评估[J].档案学通讯,2005(05):32-35.
[6]连念,翁勇青.台湾地区档案管理人员在职教育培训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0(01):88-91.
[7][16]胡鸿杰.我国档案机构改革与档案职业发展[J].浙江档案,2019(05):27-30.
[8]胡鸿杰.社会与组织:档案职业辨析[J].档案学通讯,2016(05):8-11.
[9][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2018年度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EB/OL].[2021-10-25].http://www.saac.gov. cn/daj/zhdt/201909/2a5d923fbf064858bb9 3f3bd95982523.shtml.
[1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2019年度全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档案馆基本情况摘要[EB/OL].[2021-10-28].https://www.saac.gov. cn/daj/zhdt/202009/5ce902bafc3f490d995 96d55c8c33954.shtml.
[11]胡鸿杰.中国档案职业的形成与确立[J].档案学通讯,2006(01):5-18.
[14]中国新闻网. 2018年中国就业人数达7.8亿人 近70年扩大3.3倍[EB/ OL].[2021-10-26]. http://www. chinanews.com/gn/2019/09-26/8966538. shtml.
[15]百度百科.规模效应[EB/ OL].[2021-10-28].https://baike. so.com/doc/5895103-6107992.html.
[17]中國政府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10-26].https://mp.weixin. qq.com/s/2PJ4hp7zAJuskVxGur6Wvg.
[18]胡鸿杰,刘耀鸿.我国档案职业研究综述[J].档案管理,2021(05):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