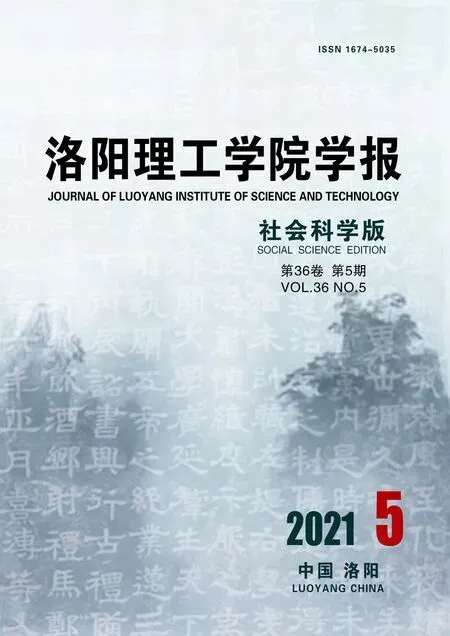从明代“古文”选本看明代“古文”的概念
谢 婉 仪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州 番禺 510006)
明代“古文”选本数量众多且盛行天下,是今天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笔者从明代众多的“古文”选本中,抽取选本名称中带有“古文”二字的部分选本进行讨论,以考察明代“古文”的概念。
一、明代以前“古文”概念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古文”的概念往往因时、因事、因人而变。《说文解字》阐明了“古文”的本义,即上古时期的文字。“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1]2,发明了小篆,而“古文由此绝矣”[1]2,这里的“古文”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2]3293,这里的“古文”指古代典籍。汉代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这里的“古文”是用古文字写成的经籍。此后,“古文”的概念又转化了。萧纲《与湘东王书》谈道:“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3]3011萧纲所说的“杨、马、曹、王”是“古之才人”,作“古文”,而“潘、陆、颜、谢”略近,是作“今文”的时人学习、模仿的对象。萧纲发此议论,是为了揭示有些时人致力于模仿古人、违背古代优良文学传统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萧纲标示了“古文”这一概念,即古代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往圣前贤的文章,且与“今文”相对。“古文”之目可追溯到萧纲之时,那“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4]19就值得思考了。唐宋“古文运动”号召时人取法于古人典范之文,此处的“古文”既是萧纲所说的历史概念,又是一个新的文体概念,有新变之意。明人将“古文”与“时文”对举,是源于对古与今、旧与新的思考。明人心中的“古文”概念具有复杂性,而“时文”主要指当时流行的八股文。在明代,由于市民阶层的扩大、举业的兴盛等因素,出现了众多的“古文”选本,这些“古文”选本阐发了“古文”在明代的多种含义。
二、明代“古文”选本概貌
明代“古文”选本多是书院的教材或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这些“古文”选本内容大同小异,较少受文学流派影响,且有特定的组成部分。
(一)“古文”选本产生的背景
第一,科举风习。“古文”选本作为科举教材,以举业为第一要务。明代科举考八股文,即“时文”。八股文于成化年间定型,此后一直盛行天下。在笔者搜集的“古文”选本中,最早的“古文”选本于成化年间出版,最晚的“古文”选本于崇祯年间出版。侯美珍在《明清八股取士与经书评点的兴起》中认为,八股文以经义命题,使得“大量选本充斥书坊”[5]。所以科举考试程式改变不大,古文选本的内容就基本相同。
第二,文学复古思潮。余来明在《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中认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6]。冯小禄、张欢在《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中认为“七子派与唐宋派的对立”也“延及八股文方面”[7]。“古文”选本作为八股文写作教材,也顺带成为当时文人领袖宣传文学观念的号角及文学流派相互斗争的阵地。复古思潮体现了明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矛盾。廖可斌认为,这一矛盾是“古典审美理想及传统文学形态与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的审美理想和新的文学形态的对立与冲突”[8]449-450,而人们对“古文”的极大热情,便是如此宏阔的历史时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明人在选本中将“古文”与“时文”对举,或对立看待,并说明自己的态度,也是受复古思潮的影响。
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看,科举考试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而是挑选合格的官吏,为封建王朝服务。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明代,这一观念更加突出。在明代,文学对科举的影响力不如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力那样强大。科举以一套固定的程式和方法来选拔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官吏,让书生们关心程式,逐渐远离文学,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吴志达认为,学子“一般都是中了举人、进士之后,或者绝意仕进之士,才认真从事八股文以外的文学创作”[9]255。但文学却受到科举文风的强大影响,“明代传奇创作的八股化是明显的例证,诗文方面无论是台阁体、复古派乃至反复古派,各个流派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极端化、绝对化,又何尝不是沾染八股文风的习气呢”[9]263。所以,服务于科举的古文选本受文学流派影响较少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二)“古文”选本的组成部分
明代“古文”选本由目录、序跋、凡例及正文等4部分组成。
从目录中可知,这些“古文”选本的编撰方式有以下几类:一是以文体形式为分类标准进行编选,有《古文精粹》[10]《续古文会编》[11]《古文澜编》[12]等3种选本;二是以朝代为分类标准进行编选,有《翰林古文钞》[13]《新刻合诸名家评选古文启秀》[14]等2种选本;三是把先人著作名称、文体形式、朝代名及作者性质等要素结合起来,并按一定的顺序完成编选,有《必读古文正宗》[15]《古文会编》[16]《古文选要》[17]《古文钞》[18]《古文选粹》[19]《合诸名家点评古文鸿藻》[20]《古文备体奇钞》[21]《古文奇奇赏》[22]《古文类选》[23]等9种选本;四是以书名为分类标准进行编选,只有《古文采华旁训》[24]1种;五是针对受众进行分类,只有《古文会选》[25]1种。
这些“古文”选本的选文范围略有差异,有的选本几乎涉及明代以前历朝各代,但不包括明代,如《翰林古文钞》;有的选本将明代已故文人的文章纳入“古文”范围之中,如《合诸名家点评古文鸿藻》;有的选本专注先秦两汉,如《古文采华旁训》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为选取对象;有的兼取先秦两汉与唐宋文,其他朝代的文章则不收录,如《古文选粹》。在将文体作为分类标准的“古文”选本目录中,没有完全相同的选本目录。可见,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含义较为模糊、宽泛,明人对“古文”这一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明晰的认识,编者的编撰动机、立场、观点与所用方法各不相同,选取“古文”各有偏重。但是,这些选本大都具有重秦汉文、唐宋文或秦汉唐宋文并重的特征,且篇目有较多重合,如《必读古文正宗》与《古文选粹》都从《汉书》中选取了《汉楚异姓诸侯王表》。
“古文”选本序跋重在反映选本的编选情况,略写编者的生平经历,并高度赞扬编者。如李嵩《古文类选·序》中,用“公邵于材而朗于识,行谊直驱古人,而于古人文辞业既能之,复深知之”[23]序一2来褒奖编者郑旻,这是明代“古文”选本序跋的典型。“古文”选本“凡例”也透露了明人对“古文”的思考。“凡例”描述“古文”选本的体例,解释“古文”选本的编选宗旨,展现“古文”选本的细节。如《古文奇奇赏·凡例》中“按时次先后,以《左》《国》为首,《离骚》附楚策之后”[22]凡例2,是对其编选体例的说明,“是集专为诸生举业之助”[22]凡例1,交代了编选宗旨。又如《新刻合诸名家评选古文启秀》的“凡例”暴露了编者将“古文”与“时文”混为一谈的错误。“古文”选本正文部分,大都采用“课文”与“评点”相结合的方式,为学子讲解所学的文章,是“古文”选本的主体部分。
三、“古文”在明代的作用
在明代,“古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古文”是传承经典益世教化之文,是古典审美理想之文,是科举考试的典范,是文学、文体的“源”“流”。
(一)“古文”是传承经典益世教化之文
明人认为“古文”是“往圣前贤之文”,有传承经典的作用。《古文精粹·序》言:“《古文》一书乃精选历代名贤所作也,其间雄辞奥旨足范后学。”[10]序一1《古文精粹》以“披沙而拣良金,凿璞而获美玉”[10]序一1为选取“古文”的宗旨,用来服务“览者”,借以“广其传”[10]序一1,扩大该书的影响力。为了帮助后学者,文体齐备是首要的条件,故《古文精粹》收录了26种不同的文体。《古文精粹》的编选宗旨是希望该书能成为后学者的典范。《必读古文正宗》由张鼐辑成并点评,周宗建作序。周宗建认为,“先秦、两汉、六朝、唐宋诸作”[15]序一2“有助于举业的认可和实效”[26]。《必读古文正宗》不仅收录先秦、两汉、唐宋的文章,而且也从六朝文中寻找佳作,以助力学子练习写作、考取功名。《必读古文正宗》表明,代代有经典,世世有正宗,每个朝代的佳作都应该收录。
明人还认为“古文”有益于政治教化。《古文会选》编者谢朝宣初到大理为官时,十分怜悯当地百姓。弘治十二年(1499),谢朝宣在云南设立大理苍山书院(后改为苍麓书院),教化民众。正德《云南志》云:“苍山书院在府城外西南陬,苍山之麓。弘治十二年巡按御史谢朝宣建。”[27]140明代王臣的《苍山书院记》云:“弘治十有二年秋八月,大理苍山书院成……侍御关右谢公朝宣,奉命来按是邦,恻然悯之,谋于按察副使太原王君槐,毁浮屠之刹若干,命有司改创书院于苍山之下,延名师以教庠序弟子员,若郡人之俊秀有志者,崇正黜邪之旨,于是乎晓然矣。”[27]413谢朝宣排佛教、毁佛刹,延请名师教化士人的举措,为提振士风做出榜样。谢朝宣在《古文会选·序》中说:“弘治戍午承乏按滇南,公余,取前数集抄录,间有所增,去其重,与夫近于俚者类为一编,名曰《古文会选》,提学王公世赏见之,欲以梓,示庠序。”[25]序一3-4谢朝宣作为大理地方官员、书院院长,亲自编选了《古文会选》,由学官王世赏助刻,《古文会选》极有可能在苍山书院作为教材使用。谢朝宣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接受能力,选取最易为学生所接受的文章,并订立了特殊的标准教导学生。《古文会选·后序》云:“彼无关世教者,虽工不录也。”[25]后序一3“有补于世教”是《古文会选》的选文标准。
《新刻合诸名家评选古文启秀》由王纳谏辑。王纳谏认为“古文”具有反应“成败兴坏”的社会发展趋势的重大价值,建议学习者“撷其英华”“以佐笔端”[14]序一1。《续古文会编》由钱璠辑。钱璠于嘉靖十二年(1533)知奉化县,政多便民又留心书史。“藩,常熟人……嘉靖十二年令奉化,临民一以忠诚,绝无炫饰,秋毫不取于民……尤留心书史以资仕学”[28]8。钱璠说“文章关系世教大矣”[11]序一1,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功能。钱璠认为宋代以前的“古文”,“率皆浑厚典雅,出入乎道德而非苟焉以作”“近世以举业为时文”[11]序一2,今文不知 “德”为何物,流连于“风云月露”违背了“德”。钱璠心中的“古文”,是上古至宋代以浑厚典雅为风格、以发扬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主旨,对社会政治发展有促进作用而载入史册的文章。
(二)“古文”是古典审美理想之文
明人认为“古文”是古典审美理想之文,是文学思想的反映。《古文会编》由黄如金辑,邵宝作序。《古文会编·序》云:“文一而已矣,自近世以举业为时文,于是有古文之名。时文之于古文,异体而同辞,异辞而同理,理既同,则其辞虽异,中有同者存焉。”[16]序一1邵宝认为“古文”与“今文”相同的地方在于“法”同,“字以声出,则法同;句以字成,则法同;章以句属,则法同,不如是,理不能达也”[16]序一1。邵宝属于茶陵派,深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茶陵派的核心主张是“把文学从理学思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8]53,恢复古典(尤其是汉唐)的审美理想。“上则经,次则传,又次则诸子”[16]序一1,由此可见,邵宝对古典十分重视。黄如金在《古文会编》目录中先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文,次列诸子文,还选取了多篇唐代名文,可见其重汉唐文,更加贴近茶陵派文学思想。邵宝、黄如金的“古文”概念,是符合茶陵派古典审美理想的文章,而古典审美理想凝结在“汉唐”文中。黄如金还期望学子的文章能“得乎法”“无失于体”,又“达理”,以传扬高尚的道德为最高目标,即“上之充然道德之发”[16]序一3。
《古文选要》由傅振商辑。傅振商是一位重视教化的地方官,一生建成了三座书院,分别为恒阳书院、顺德国士书院和天雄书院。傅振商在《古文选要·序》中说“择精要数首,录课儿辈”[17]序一2,说明《古文选要》是其创办的书院使用的课本。傅振商还有作品集《恒南稿》,收录于明万历刻本《木天馆稿二卷恒南稿三卷》中,今见于沈乃文《明别集丛刊》中。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龙锡为傅振商作《恒南稿序》[29]55-56。《爱鼎堂全集》中彭鲲化作《题木天恒南稿序》道:“自‘七子’沉沦之后,大雅久衰。魏偷任,邢盗沈,千篇一律,吞剥成套。而星垣妙思自构胸中,著作不休,皆出中肠,起衰鸣盛,文章一脉,始不断绝。”[30]245傅振商认为,“《檀弓》之精简工纟致,《左》《国》之奇艳粹博”[17]序一1与“先秦之雄辩纵横,两京之浑厚尔雅”均“不失古意”,“韩之雄宕,柳之深核,欧之和畅,苏之奔逸”[17]序一2,与“古文”是“异调同工”的,六朝“艳藻”则“于古脉日远,虽丽不录”[17]序一3。傅振商的文学理想是使古脉不致断绝。傅振商认同的“古文”,是具有“古脉”的文章,唯有继承中国古代优良文学传统并代表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先人文章,才能被称为“古文”。
郑旻的“古文”观综合了往圣前贤之文、有益世教之文、符合古典审美理想之文这三个观念,但其对“古文”概念的把握更加全面。郑旻的“古文”观念体现在其编选的《古文类选》中。李嵩在《古文类选·序》中先对“古文”风格作了整体性的评价:“左氏之文庄以则;汉之文浑以质;唐之文俪以析;宋之文辩以畅。”[23]序一2而后,李嵩对历朝各代的文学家的文章风格用一词进行概括,“正如毅,高如连,奇如迁……练如谊……舂容如修,峻爽如轼”[23]序一2-3。李嵩阐释了《古文类选》的编选宗旨,即学习者应以“味乎其文,模乎其辞,辩乎其人,究极乎其心”[23]序一3的方法来师古,并“根之理道,通之政术”[23]序一3,这样就会有“翼经明志”“光代润业”[23]序一3的作为。李嵩、郑旻心中的“古文”,是往圣前贤所作的、兼具政治教化功能与审美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作者的个性且风格稳定不变。
(三)“古文”是科举考试的典范
明代举业兴盛,考取功名是莘莘学子的毕生追求。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胜,学子们就要写好“时文”。明人认为,“古文”作为文章典范,对“时文”写作大有裨益。
《翰林古文钞》是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任瀛在“选馆”时自编的,是以“简约便习”为特点的参考书,常放在他的衣服夹袋中。任瀛为了进入馆阁,获得晋升机会,“夙夜匪懈,罔敢弗慎,其于文辞,尤殚厥心”[13]序一1,取法古代经典作品,以寻求作文的“藻思”,致力于成为“第一流人物”。《翰林古文钞》是科举选官制度的产物。任瀛选取“古文”供自己学习,为了方便,把选取的古文按朝代顺序进行归类,所以《翰林古文钞》的“古文”是指在科举体制中被奉为圭臬、视为典范的古代文章。类似的还有徐鹢编的《古文采华旁训》。从郑端胤跋中“士君子匡扶社稷功名之念不可无;羽翼道德功名之念不可有”[24]跋一1一句可知《古文采华旁训》与科举有关。姚一贯在序中说,“读者不得其要领,率苦于汗漫而难入,如望洋向若茫无涯涘”[24]序一1,其认为要领就是“极盛”的先秦两汉文。《古文采华旁训》的编撰动机在于劝导学子着眼于“古文”要领,帮助他们写好“时文”,以求取功名。
《古文选粹》由吉人编,李从心作序。李从心在《古文选粹·序》中谈到,“不读古人文字,是不读赋而能赋也”[19]序一2,这里的“古人文字”,是指古人所作的范文,也就是秦汉、唐宋文。吴承光的《古文钞》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这六部史书中选文,又将部分历史人物写下的名作,如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前出师表》等,收入“附集”,编成《古文钞》出版发行,为科举服务。吴承光是为了迎合科举制下学子的需求而编此书,符合其“阅兵武库,自当随取随足”[18]序四2的主张。
(四)“古文”是文学、文体的“源”“流”
“古文”是文学、文体的“源”“流”,体现了明人对学术的探索。黄道周在《古文备体奇钞·序》中说:“然《左》《国》《国策》独仍其意,而不别以体者,何盖言统也?盖为群言祖,实众体之体也,其犹两仪之先群象也。”[21]序一8《古文备体奇钞》所指的“古文”有两重含义,一指“《左》《国》《国策》”,是文学的源头;一指古代(明代以前)的文体,由“《左》《国》《国策》”派生出来。这就是《古文备体奇钞》目录把先人著作名称与各种文体结合起来进行排布的原因,类似的方法在许多明代“古文”选本中都可得见。
吴承光编选的《古文钞》,陈王道为之作序。陈王道认为“六经”为源,“诸子”为流,“两汉”载大道,这是“本”,可后世竟“本隐而末显”,所以他慨叹“古人之不作章斯久之”[18]序一3。吴承光在《古文钞·自序》中认为,“卦爻之辞、风雅颂、典、谟、训、诰”是“圣人之道”的体现,“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是而下即不纯合乎道”[18]序四1;司马迁乃“中古独步”;西京文章虽不能“尽继”圣人之道,但也是“流亚”;“东京”文“英华太露”[18]序四1,此后文章江河日下。王志坚在《古文澜编》序中也认为,“以六经为原本,以史汉为波澜”[12]序一3,此后的文章皆偏离了古道。陆承宪在《古文钞·序》中说,“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18]序三1,揭示了时人将古今对立的倾向,提出“古之不可推于今”[18]序三1,认识到古今有别的客观事实,因为有别,才会争议四起。陆承宪又说“家置一喙,人驰一说,谁能定之”[18]序三1,其认为读者的观念千差万别,古今争端终无定论,建议人们“兼爱”古今文,态度客观通达。
此外,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如王纳谏在《新刻合诸名家评选古文启秀·凡例》中认为:“或谓国朝之文而但取此数篇者,何也?曰,我朝如王弇州、李于鳞、杨升庵、汪伯玉,诸名公文集浩漫,非为不敢选,而亦不暇草草选也,余尚有《明文启秀》,以俟嗣刻。”[14]凡例2王纳谏编《新刻合诸名家评选古文启秀》,本应只选古文,但其却选录了少数时人的文章,如宋濂的《阅江楼记》、陈茂烈的《陈情疏》等。
四、结 语
综上,“古文”的概念以及将“古文”与“时文”对举的习惯,早在梁简文帝时期就已经出现,其后不断发展变化,奠定了明代“古文”概念的基础。明代“古文”选本大都是书院的教材或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从科举风习和文学复古思潮的历史背景中产生,较少受文学流派的影响,且内容基本大同小异,体例大都由目录、序跋、凡例及正文等四部分组成。明代“古文”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传承经典益世教化之文,是古典审美理想之文,是科举考试的范文,是文学、文体的“源”“流”。明代“古文”反映了明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思想、科举观念以及对学术的探索,也是明人对古与今、旧与新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成果都是明人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