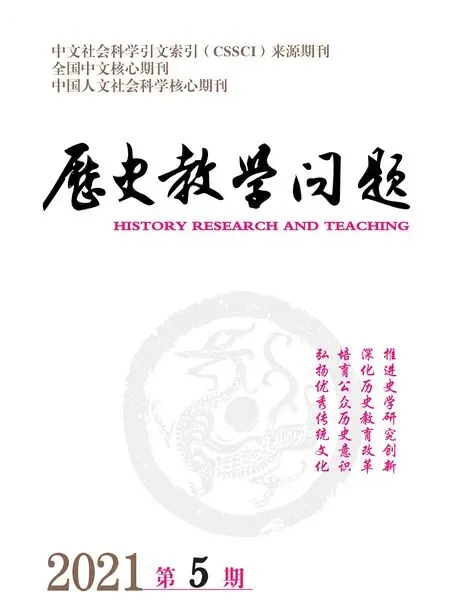从军记所见侵华日军的战地心态与战地观感
——以“香烟”为线索的考察
王 萌
作为一个奇特现象,在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中,日军中吸烟风气极为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声称“在战地,恩赐的烟酒如何在精神或肉体上赋予官兵活力,是超过常人想象的。适时适量的吸烟饮酒,对于增加士兵战斗力实有不小的贡献”。①《酒と煙草は必要戦場の士気鼓舞に大偉力》,《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42 年10 月25 日,第3 版。显然,日本军队吸烟风气的盛行,并非偶然现象。包括香烟在内的军需品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联系本应深入探讨,然而目前中外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鲜有涉及。②目前涉及军需品对于战地日军士兵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之影响的成果很少,仅见伊藤桂一:《兵隊たちの陸軍史:兵営と戦場生活》,東京:番町書房,1969 年,第182 页。此外,笔者也曾通过研究战争时代日本社会捐赠“慰问袋”的情况,指出围绕军需物品的兵民情感互动,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为其对外战争服务的现象,参见王萌:《寄往战地的慰问袋——战时日本民间的恤兵品捐赠研究》,《史学集刊》2018 年第2 期。日本战败之后,原日军官兵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描述他们侵华战争期间战地经历、体验、观感的从军记(包括日记、战记等形式),为我们研究侵略者在中国战地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动向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史料。不难发现,日军中吸烟风气盛行的现象也充分反映于从军记中,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吸烟、吸烟感觉等方面的描写。本文基于各类公私文献,尤其是日军官兵们的从军记,考察侵华日军部队吸烟风气盛行的原因,并通过解读从军记所描写的日军官兵对烟的情感,剖析其身处战地的心态与观感,管窥抗战时期侵略者的内心世界。
一、为何侵华日军中吸烟风气盛行?
近代以来,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宣传与推动下,“恩赐香烟”作为军需香烟的代表,对于日本军队的士气起到重要激励作用。所谓“恩赐香烟”,指的是以日本天皇名义下发的一种特殊纸烟,是战争时代日本皇室赠予陆海军官兵的一种特殊军需品。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岩谷商会从日本宫内厅获得制造“恩赐香烟”的特权,在日本军政当局要求下,于三日间生产数十万盒,以之激励赴朝日军的士气,“因烟纸标记‘恩赐’两字,我皇爱护军人如此优渥,何人不求马革裹尸以图报乎”。①《派遣軍兵へ恩賜》,《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894 年7 月4 日,第1 版。在甲午战争期间,岩谷商会于日军中大力推广其所生产的“天狗”牌“恩赐香烟”,“天狗”烟很快成为标志性的军需香烟。②日本たばこ編:《たばこ百話》,東京経済新報社1985 年版,第48 页。即使战争结束后,岩谷商会仍以“纪念恩赐”为宣传标语,从制售“天狗”烟中牟取巨利。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实施“香烟专卖法”,将包括生产“恩赐香烟”在内的制烟业与全国烟草销售业官营化,以此作为筹措巨额军费的手段。日俄战争期间,“恩赐”的烟酒由天皇派遣慰问使亲自交至战地日军司令官手中,象征日本天皇对于军队的绝对权威。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恩赐香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构建各种“军国美谈”的素材,被日本军政当局广泛运用于战争动员与宣传。在艰苦的中国战地,士兵们轮流吸食最后一根“恩赐香烟”的悲壮场景,③陸軍省つはもの編輯部:《美談皇軍の精華》,つはもの発行所1933 年版,第25—28 页。士兵吸完最后一口烟后瞑然而逝的忠勇形象,④長沼依山:《忠烈美談輝く美談》,興文閣書房1938 年版,第8-9 页。受到日本军政当局广泛宣传,成为战争时代日本国民“深受感动”的“军国美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获赐“恩赐香烟”成为日军官兵至高的荣誉,被视为能够赋予日军官兵为国尽忠、拼死前进勇气的精神武器。
从日军官兵从军记中不难发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恩赐香烟”被日本军政当局频繁下发于各地日军部队。例如,战初,当攻打南京的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首次获赠“恩赐香烟”时,士兵们的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如“感泣于鸿恩……将之作为最好的礼品保存至战友凯旋”,⑤《斎藤次郎陣中日記》,1938 年1 月22 日,小野賢二等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大月書店1996 年版,第51 页。又如“能够逐一领受恩赐香烟,参加此实为难得之恩典,宣誓今后必将为君国尽忠”等等,⑥《黒須忠信陣中日記》,1938 年1 月23 日,小野賢二等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第256 页。说明“恩赐香烟”的分配确实起到鼓舞部队士气的效果。然而,从军记也暴露出军需香烟因阶级差异而存在的分配不公等问题。有的士兵在日记中直书,“军官得三十根、下士官得二十根、士兵得十根、补充兵得二根、战伤者因获赐带菊纹的点心而不分配”等,⑦《大寺隆陣中日記》,1938 年1 月22 日,小野賢二等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第206 页。披露日军在分配军需香烟时奉行军官优先主义、底层士兵相较于军官所得甚少的真相。
我们发现,从军记中记载了大量战地士兵领受“恩赐香烟”的场景,反映日军对授烟仪式的高度重视。当高级军官前往前线督战时,授烟作为其重要的激励手段,受领部队往往还要为此举行一场庄重的仪式。⑧藤崎武男:《歴戦一万五千キロ大陸縦断一号作戦従軍記》,中央公論新社1999 年版,第83 页。士兵矢泽新五记载道:“(官兵们)于宿舍前整列站立,于(天皇)派遣的侍从武官抵达之际,举行将恩赐香烟与御酒赏赐于全体前线官兵的传达仪式。仪式在庄严肃穆中结束,官兵们返回各分队寝室后喜悦地将之分给室友。御酒因量有限,则混合普通酒后下发。”⑨矢沢新五:《生ffiて帰れまいこの命支那事変の記憶》,文芸社2007 年版,第97 页。在大战前夜,领受恩赐烟酒的阵前仪式被军官们刻意营造出悲壮气氛,以此达到唤起士气的目的。而对于如此激励之策的效果,一个士兵观察到:
(藏重)大队长徐徐地取出御赐香烟,祈求着成功。天皇陛下恩赐的印有菊花花纹的香烟,对于鼓舞士兵决死之行将起到最大效果。在中日战争初期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军歌“天空的勇士”(大槻一郎作词、藏野今春作曲),伊始便唱到的“在决定明日赴死之夜,领受恩赐香烟,旷野的风中飘着血腥,猛然怒视敌方的天空,不过点点星光闪烁”之场景,正于这片大地上上演着。⑩木下博民:《中国大陸戦痕紀行》,第三書店1997 年版,第204 页。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谋划与推动下,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以“恩赐香烟”为题材的军歌伴随“军国美谈”的传播在日本社会广为传唱,歌词中所描绘的日军官兵围绕“恩赐香烟”的决死心情,使后方民众感受到战地的悲壮与苍凉,由此酝酿出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气氛。然而,对于这种特殊的军需香烟,士兵们普遍回忆其口感不佳,“只是印了个菊花花纹,味道并不好,和带过滤嘴的‘敷岛牌’香烟差不多,还有点辣。如此而已”。①泽昌利:《太行噩梦——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与回忆》,鞠佟生、田酉如译,《山西文史资料》1998 年第5 期,第166 页,第34 页。有别于普通的军需香烟,日本军政当局对“恩赐香烟”的宣传,主要用以激发官兵慷然赴死的忠勇之心,起到激励士气的作用。
日本军政当局对军需香烟的大量供给,促使军中吸烟风气的盛行。军需香烟作为日军官兵三餐之外最受欢迎的补给品之一,日军官兵对其有很大的需求量。有士兵回忆,全面抗战初期战地日军士兵每人每日可分配香烟20 根或啤酒1 瓶。②泽昌利:《太行噩梦——一个侵华日军的日记与回忆》,鞠佟生、田酉如译,《山西文史资料》1998 年第5 期,第166 页,第34 页。以日军上海派遣军为例,仅1937 年9 月就收到来自日军粮秣总厂的“荣誉”“回音”“朝日”等各种品牌香烟100 万根。③《上海派遣軍用糧秣追送に関する件》(1937 年9 月29 日),《支受大日記(密)其11 15 冊の内昭和12 年自11 月18 日至11 月24 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2-4-99。从日军档案中可见,不仅战争初期,乃至进入持久战状态之后,军需香烟的供给仍维持着较高的量,④日军部队的香烟消耗量与日本国内香烟生产及运输能力相关,其数无法确考。仅以1938 年12 月为例,日军台湾军援助华南方面军的军需香烟量就达1000 万根,或可从中一窥士兵对其之需求。参见《波集団に対する兵站援助実施状況の件》(1939年1 月20 日),《陸支受大日記(密)第9 号2/2 昭和14 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4-9-98。从侧面反映战时日军部队对军需香烟的旺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侵华日军的军需香烟供给已基本实现本地化生产,东亚烟草公司等华北日商烟厂所生产供出口用的香烟,则被优先供应于当地驻屯的日军部队。⑤《野戦酒保品製造材料追送に関する件》(1941 年3 月18 日),《陸支密大日記第9 号2/3 昭和16 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6-27-50。
除军中瘾君子外,军需香烟同样受到不吸烟士兵的欢迎。在日本军队吸烟风气盛行的背后,军需香烟作为士兵间秘密交易的对象,尤其在战地日军出现食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可以交换牛肉罐头、馒头的“硬通货”。⑥田中英俊:《改稿湖南進軍譜——大陸最後の大作戦と軍の命取りになった「戦争栄養失調症」》,白日社2010 年版,第219 页。士兵森金千秋提到,为挣得外出游玩的零花钱,士兵们往往收集大量军需香烟,将之20 根、30 根地成捆出售于黑市,令他们担心的是,“这一交易多半会赌上性命。化装成中国人的宪兵下士官,或穿着上等兵或兵长军服的大尉宪兵队长,正为找士兵们的麻烦而擦亮着眼睛”。⑦森金千秋:《湘桂作戦》,図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尽管日本军部明确规定,包括“恩赐香烟”在内所有的军需香烟严禁流出军队,然而军需香烟黑市交易的存在,抗战后期已成为日军官兵们公开的秘密,反映当时日军军纪废弛的实相。
从日本军部档案与官兵从军记中均可发现,军需香烟被利用于牟取各种隐秘的经济利益。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驻屯伪满的关东军士兵往往利用中国东北市场与日本国内市场的差价,将包括香烟在内的各种军需品邮寄回日本国内牟利。对此日本军部特别规定,“除恩赐香烟之外,所有外国品,无论是否日本国内制造,都不得出口至日本国内”。⑧《製造煙草包有小包に関する件》(1936 年10 月21 日),《存書類甲輯第6 類昭和11 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陸軍省-大日記甲輯-S11-8-21。此外,为了掩盖日军在中国战地的暴行,日本军政当局对士兵寄回国内的照片严加审查,而作为战地士兵的应对之策,他们则会将照片隐藏于“恩赐香烟”的烟盒中,将之巧妙地寄回国内。⑨田中英俊:《改稿湖南進軍譜——大陸最後の大作戦と軍の命取りになった「戦争栄養失調症」》,第73 页。
可以看到,侵华日军部队中之所以吸烟风气盛行,不仅在于日本军政当局向底层官兵大量提供以“恩赐香烟”为代表的军需香烟,而且以“军国美谈”“军歌”等形式对军人的吸烟行为予以正面宣传;另一方面,战时日军官兵对于军需香烟具有旺盛的需求,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理上的需要,背后也存在包括牟取经济利益在内的其他意图。
二、“吸烟”描写显现官兵的战地心态
不难理解,侵华日军官兵在烟草的感官刺激下得以暂时忘却身处战地的孤寂,从军记中不乏有关其“吸烟”活动的描写。身处华中战场的士兵松岛博描述其作为瘾君子吞云吐雾时的快感:“在冷风中,注视着香烟隐隐约约逐渐被抽尽,吸烟带来的快感虽不至于使人沉醉,然而呼的一声吐出烟圈,到底使人心情愉快。”①1940 年9 月5 日,松島博:《華中従軍日記》,石崎書店1958 年版,第85—86 页。在普通士兵的精神世界中,“香烟有时胜米饭”。②藤枝正雄:《中国大陸従軍記馬の尻尾に掴まって歩く二つの星の兵隊》,近代文芸社1995 年版,第226 页。他们讴歌烟草的魔力,“吞吐着烟圈,真是赛神仙”。③1940 年10 月12 日,松島博:《華中従軍日記》,第92 页。有人直言不讳,“士兵的生活除去烟酒,所剩只有空白”。④1937 年10 月15 日,村田和志郎:《日中戦争日記》第一巻,鵬和出版1984 年版,第61 页。从一些“军国美谈”中可以看到,除自身享受之外,香烟还能热络士兵间的人际关系,传递“战友之情”,起到慰藉彼此心理的作用。
然而,吸烟对于普通士兵,也隐喻着战地的残酷。身处淞沪战场的军医藤原东一郎于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其领受并吸食军需香烟时的心态:“虽然一度获得了喜好之物,稍稍有些发愣。然而,接受此物时,或许因身处战地乎?却感到一抹孤寂与悲哀。”⑤1937 年10 月8 日,藤原東一郎:《羅山に散るまで日中戦争隊付軍医の日記》,文芸社2008 年版,第42 页。或许已预感到无法回归故土,藤原记录了普通士兵吸烟时的真实心境:“‘虽欲一口不吸地将之全部带回国内,然而可能再也无法回去’,不得不吐露的是,眼下的状况实不容乐观。”⑥1937 年11 月10 日,藤原東一郎:《羅山に散るまで日中戦争隊付軍医の日記》,第42 页。可以看到,吸烟不仅带给普通士兵投身战斗的亢奋感,也显现身处战地的紧张感与危险意识。
战争后期,随着日军侵入中国内地,后勤补给越发困难,军需香烟混杂着各种品牌,可谓五花八门。参与豫湘桂战役的下级军官藤崎武男对此说明道:“香烟是从武昌出发时配给的所谓‘兴亚’牌爪哇烟。它的味道根本赶不上曾经驻屯华北时品味过的‘三炮台’、‘哈达门’、‘前门’、‘红宝石皇后’等,即便如此,此时已属佳品。”⑦藤崎武男:《歴戦一万五千キロ大陸縦断一号作戦従軍記》,第243 页。军需香烟供给上的不足,成为导致战地士兵烦恼的问题之一。当部队中仅剩最后一根烟时,众人通过对其分食,“进入军歌所歌唱的军中生活状态”。⑧《目黒福治陣中日記》,1937 年10 月9 日,小野賢二等編:《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第360—361 页。因日军联队指挥部所在之地往往有小卖部可供士兵自由买卖香烟,出差当地的士兵往往大量采购,以此满足自身与战友强烈的烟瘾,有时“一举买进香烟二十五盒,由此从香烟的饥饿中解放,做好了猛吸一阵子的心理准备”。⑨1939 年4 月23 日,中村常賢:《陣中日誌日中戦線昭和13 年·昭和14 年》,刀水書房2007 年版,第117 页。战争末期,伴随军需香烟供给的减少,士兵的战地生活变得困苦,由此士气低落:
明日的攻击临近,士兵们即使豪饮也无法入醉,彼此沉默不语……鹿子木军曹与高木清伍长,晚饭后被叫至小队长伊藤少尉的房里。这是明日攻击前的一次谈话,与小队长促膝谈心的目的,可能这是最后的交谈。伊藤少尉伊始便问:“有烟吗?”回答道:“没有。”因为没有补给,士兵们将艾草叶子与杂草代替烟草吸食。即使下士官,也许久未见真正的香烟了。大概伊藤少尉作为军官享有特别配给,他拿出了一包崭新的“旭光”烟。
“抽一根吧”,伊藤少尉仔细地将之开封,抽出三根烟,每人一根。“旭光”牌香烟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将上海英商烟厂没收后由军方管理,将其原产的“红宝石皇后”牌(Ruby queen,即民国时期行销极广的“红锡包”——笔者注)改装后的牌子。至1945 年春,武汉地区每个士兵每周可分配一盒,加上大众化的“双鱼”牌香烟,一共可分得40 根。“旭光”不愧为散发着紫烟香气的高级烟,是于桌上轻轻敲击,就会洒出如砂糖般粉末的珍品,好像有人说混入了鸦片。⑩森金千秋:《湘桂作戦》,第218—219 页。
即使在日军统治下的武汉地区,战争末期普通日军士兵可分配到的军需香烟的量,已远低于战争初期。然而,少尉等低阶军官仍可获得特配的军需香烟,体现出日军军队仍维系着森严的等级特权,以及军需香烟在日军心理世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日本军政当局将“红宝石皇后”牌等外资香烟视为“敌性”物资,甚而将其改为日名,但仍不能掩饰日军军官对于此类高档烟的嗜好与热衷,侧面反映日军军官对奢侈品的追求与军中奢靡风气的盛行。
在战时日军部队香烟供给渠道出现不畅的情况下,“征发”成为日军部队获取中国民间香烟的主要方法。所谓“征发”,乃日军迫使沦陷地区民众提供必要物资或人力的征集手段,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军事用语。正如日本战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征发队一定要以军官为指挥官,征发的物品一定要给予赔偿。为了日后的赔偿,要给与票证。除此之外的行为,不是征发而是掠夺。然而,这一规定根本无法遵守,甚至很多干部都不知道它的存在。”①藤原彰:《中国戦線従軍記》,大月書店2002 年版,第109—110 页。现实中,侵华日军的“征发”等同于掠夺,香烟则是士兵们的重要“征发”对象。在日军反复“征发”的地区,民间物资日益匮乏,士兵能够“征发”到的香烟往往量少质劣,其口味根本无法与军需香烟相提并论,有士兵写道:“回忆起前夜恩赐香烟的香味,为强烈的烟瘾所驱使。当然不会有高档香烟,都是从当地征发来的用蒿纸包卷烟草之物,大概是决死之际最后的一口吧?在帐篷中所吸时却有着独特口味。”②森金千秋:《湘桂作戦》,第96 页,第142 页。虽然战地手制的土烟口感不佳,但对于明日生死未卜的底层士兵而言,仍不失为一种奢侈享受。他们将“征发”来的烟丝揉碎,用粗糙的纸张包卷而成,每当抽起这种土烟时,“眼前的烟圈就会轻轻漂浮扩散开来,使自己确认还活着的事实”。③吉岡義一:《零の進軍——大陸打通作戦湖南進軍》(上),「新老人の会」熊本本部2005 年版,第47 页。对他们而言,只有在烟草的刺激下才能暂时摆脱战争机器的束缚,恢复成正常的“人”。然而,“征发”作为战地士兵的“权力”,却根本不会顾及被“征发”者——中国民众的感受,即使为日军军官所表面禁止,往往底层士兵置若罔闻,为了获得包括香烟在内的更多嗜好品,“征发”成为他们身处战地的乐趣。
当来自后方的物资补给完全断绝,香烟等嗜好品的供应难以为继时,士兵们就会将荷叶、枯草代替烟草来满足烟瘾,然而其口味之粗糙,“甚而无法与(最后决战前)众人轮流分享的‘前门’烟相比”。④森金千秋:《湘桂作戦》,第96 页,第142 页。1944 年7—8 月衡阳会战期间,在衡阳郊外的日军野战医院中已出现某种“代用香烟”,“(伤员)有时一边与尚有气色的患者聊天,一边将干燥的荷叶切碎,用纸包卷起来,非常娴熟地制成‘代用香烟’。患者们将纸卷成漏斗状,填入碎荷叶,用带有火种的纸捻熟练地点燃了烟卷,吸食着这种代用品”,⑤読売新聞大阪本社社会部:《中国慰霊》,読売新聞社1983 年版,第150 页。“代用香烟”成为士兵临死前最后的嗜好品,反映当时日军士兵内心世界的百无聊赖与部队士气的萎靡低颓。
从军记中所描绘的吸烟百态,体现战地日军官兵心理世界的空虚、彷徨与焦虑。在持久战的形势下,大量日军被中国共产党率领的游击部队所牵制,日本军队陷入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吸烟虽然暂时缓和了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但不能抑制他们对战争未来的忧虑;战争后期,伴随日军的伤亡大量增加,伤员不得不通过吸烟暂时麻痹感官,抑制对死亡的恐惧。香烟成为日军底层士兵日益重要的心理安慰剂,军中吸烟的百态呈现出部队士气不断走向低落的真相。
三、官兵围绕“香烟”的战地观感
除对自身精神的麻痹之外,日军官兵以香烟为中介物,与战地民众产生各种联系,于沦陷区内构建出一种奇特的景象,从军记中记述了大量日军官兵围绕“香烟”的战地观感。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为了维持对沦陷区的长久统治,以及改善作为侵略者的形象,侵华日军于中国战地实行“宣抚”工作,通过医疗施药等形式笼络人心。作为对“宣抚”工作的“报恩”,战地民众往往以香烟为馈礼。一个宣抚班的士兵记载其经历:“今天也好,昨天也好,双颊遭受枪伤的居民,与村民一同来到医疗室,我对之加以治疗。他们则还以鸡蛋与香烟。”⑥1938 年6 月25 日,藤原東一郎:《羅山に散るまで日中戦争隊付軍医の日記》,第182—183 页。当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偏僻村落,对于不知日元、军票以及各种伪币为何物的村民而言,日军官兵手中的香烟作为能够换得其他物资的“硬通货”,在双方交流中确实起到中介作用。日军士兵细致地观察到战地民众对香烟的喜爱:
虽欲使中国人帮忙洗涤衣物,却无法给其报偿。日本的日元、军票,在朱村中并不通用。仅中国货币可流通,却谁都没有。实在没法,只能决定给他们香烟。虽想给他们一盒十根装的,然此朱村中,我们中队仅带来2 万根,原是不允许中国人来分享的。然而处于没米没糖等一切日用品的状态,终究也只能给他们香烟。虽一开始因客气不接受,但再给的话也会高兴地接受。妇女虽不吸烟,然而貌似她们丈夫的男子,则会直接接下。⑦1938 年12 月30 日,村田和志郎:《日中戦争日記》第三巻,鵬和出版1984 年版,第204 页。
显然,即使双方语言不通,以香烟为中介的经济交流依然通畅。然而,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官兵与中国民众围绕香烟的交流,也并非总是感到愉快。士兵松岛博于日记中特意记载了他与中国村民围绕香烟的龃龉与不快:
我留住该村民,示其有四盒烟,要他分些生姜来交换。我将十五株生姜放入装山芋的篮子里,给他三盒烟。虽告知此种烟三盒大概值三十钱,对方却因最初已看到四盒,故还索要一盒。我虽强调三盒已够偿付这些生姜的价值,但他仍旧缠磨,我只能再给其一盒。①1941 年8 月17 日,松島博:《華中従軍日記》,第176 页。
诸如此类现象,恰说明香烟的通货属性,为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双方所共同认可。如前文所述,香烟作为重要的军需物资,原本严禁流出军队之外。然而这样的禁令被中国底层社会物物交换的规则所打破,香烟的通货功能受双方利益的驱动而被扩大。随军人员向山宽夫在行军中细致地捕捉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围绕军需香烟的隐秘交易,为之感到惊异:
因心情舒畅,于船上观赏风景。已熟悉的船夫给我一根军官用的“旭光”高级烟。仔细观察下,他不仅经常抽“旭光”,而且手上还套着军用手套,脚上穿着军用袜。我一边抽着从他那得到的“旭光”,一边指着手套和袜子问道:“你怎们会有这些东西?”船夫只是笑而不语。②1944 年12 月17 日,向山寛夫:《粤漢戦地彷徨日記》,中央経済研究所1994 年版,第47 页。
向山还专门考察了湖南地区民间香烟的流通状况,揭露沦陷区这些隐秘交易背后的利益所系,惊叹战地物价的“光怪陆离”:
因手上没烟,故外出购买。二十根一盒,要花“中储券”八十钱。立刻抽起一根,不知怎的,点火后突然燃烧起来一下子就吸尽了,此外卷纸也并非真正的米纸,而是在薄纸上涂上石灰的仿造纸,吸的时候手指黏上了白色粉末。此乃身处战场,来自中国商人表面看来毫无破绽、令人意外的伪次品。所见五十根一盒、值“中储券”三四十元的长沙本地烟,相较上海的低档烟要好吸得多,而衡阳的香烟则比长沙的要贵十倍。若吸这样的烟,可谓挥金如土!③1944 年12 月26 日,向山寛夫:《粤漢戦地彷徨日記》,第63 页。
向山提到的“中储券”,系汪伪政权于其统治区域内强制流通的伪币,因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其价值本身存在很大浮动。据森金千秋对同时期湖南香烟市况的忆述,当时军需香烟20 根一盒,约值“中储券”80 钱至1 元,而日军普通士兵的俸薪每月仅约“中储券”三十元,即使中少尉级别的俸薪,也不过四五百元。由此不难想象,将军需香烟私下转卖于中国商人的日本官兵,从中牟取了巨大的利润。
尽管日军官兵将自身对香烟的嗜好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与中国民众的交流中,却大多对中国民众的嗜烟习气感到厌恶,甚至称目击中国人吸烟的形象,“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士兵村田和志郎目睹中国人吸烟的景象,对中国人的吸烟习气抱以更负面的看法,声称“中国人虽将亡国,然仍沉溺于吸烟,还悠哉悠哉喝着茶,热衷于赌博。不分老幼都在路边蹲着抽烟。水烟、卷烟与苍白的脸色,似乎进取之心也随烟圈飘逝而去”。④1938 年12 月12 日,村田和志郎:《日中戦争日記》第三巻,鵬和出版1984 年版,第156 页。村田的观感,显然居于侵略者的本位视角,将吸烟的中国民众视为体质孱弱的亡国奴,认为吸烟所带来的快感不过片刻欢愉,吸烟不过是精神上的麻木之术。村田由此对日军士兵的吸烟嗜好同样提出批评,“在起床的同时点上一根烟,这是野战医院士兵们的习惯,不外乎说明日本青年阶层被香烟渗透之深,若日本维持这一状态,二十年后日本人的体格恐怕也会变得如同现在的华南住民般孱弱。如今,尤其是华南民众,从儿提时即吸烟,年长后唯一的嗜好就是吸鸦片”。⑤1940 年2 月16 日,村田和志郎:《日中戦争日記》第七巻,鵬和出版1986 年版,第100 页。村田将嗜烟之风上升至“亡国论”的高度,声称“如果没有抑制嗜好品的自制力,则未来必至亡国之途”,显然,他对日军中的吸烟风气保持高度警惕,而这种警惕的心理来自于对中国民众吸烟活动的曲解,是其居于侵略者统治中国、殖民中国的立场而出发的偏见。
从松岛博、向山宽夫、村田和志郎等人的从军记中可见,他们都围绕香烟细致观察过战地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他们无不对中国民众的吸烟行为感到不快、惊异或厌恶,说明当时日本士兵意识深处对战地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轻蔑心理,也揭示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以烟为中介的交流并不具备平等性。村田等人将吸烟等同于“亡身亡国”,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日军部分士兵对自身吸烟风气的反省,当然这一反省也是基于军国主义的立场而发的。
结 语
近代以来,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推动下,香烟成为重要的军需物资,服务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记述身处战地的心态与观感,是从军记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原日军官兵从军记中,关于自身乃至战地中国民众吸烟场景的书写屡见不鲜,有的极为细致,说明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助推下,以香烟为代表的军需嗜好品不仅在日军部队中广泛流行,而且在底层官兵的日常生活、心理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言论受到严厉控制的日军部队,一些日记中对吸烟活动的描写,从某种意义而言,不过是官兵们“以烟抒志”,表达其战地心态与观感的一种独特方式。
日军官兵从军记中的吸烟描写,无不带入各种军国主义的要素,体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战地底层官兵的苦闷与彷徨。日本底层官兵围绕香烟的情感特殊且复杂,立体、鲜活地反映了他们身处中国战地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心态显然具有多重性,其中至少包括:身处战地的孤独感、对战争前景的不安感、以武士道精神维系的战友之情、面对持久战体制下战地资源的枯竭的危机感等。尤需指出的是,从军记中记录日军官兵围绕香烟的战地观感,揭示日军官兵与战地中国民众围绕香烟的各种互动,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民众的吸烟嗜好所持厌恶或批判的态度等,反映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侵略者对被侵略者根深蒂固的轻蔑心理。这些复杂的情感相互关联与交织,既反映了侵华日军底层官兵精神世界的麻木与空虚,也揭示了其现实中对战地中国民众所宣扬的“共存共荣”的虚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