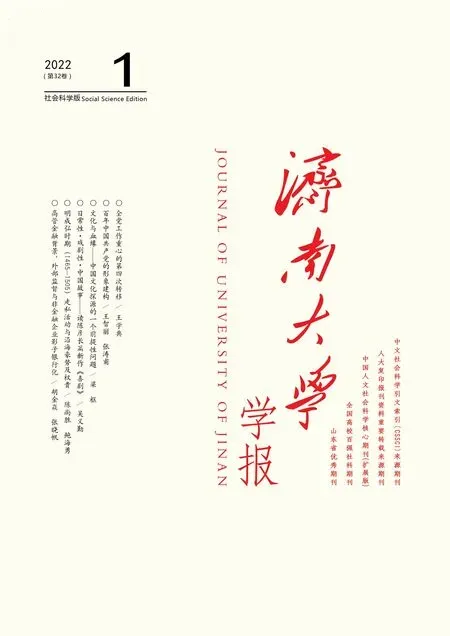明成弘时期(1465-1505)走私活动与沿海豪势及权贵
——兼论15世纪下半叶东亚海洋贸易体系
陈尚胜,鲍海勇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学界对于明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多把“隆庆开海”看成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此前为官方的朝贡贸易阶段,此后为私商贸易阶段①参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所谓“隆庆开海”,是指隆庆元年(1567)明朝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其背景则是东南沿海地区曾发生以中国海商为主体反抗“海禁”政策的“嘉靖倭乱”(1552-1564),迫使明朝更改“海禁”政策②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尚胜:《隆庆开海: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人民论坛》第611期(2018年10月下),第142-144页。。随着月港的开放,明末漳州督饷(征收关税)官员曾延请龙溪(今福建龙海市)举人张燮(1574-1640)编写带有海外通商指南性质的书籍《东西洋考》。《东西洋考》不仅保存了大量明代后期漳州地区商民的海外贸易资料,而且追溯了闽南地区商民从事海外走私贸易的历史。其中记载:“闽在宋、元俱设市舶司。国初因之,后竟废。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③(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页。从这条史料看,张燮认为沿海豪势到海外进行走私贸易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后来这些走私商人又把外国商人勾引到闽浙沿海,导致“嘉靖倭乱”的发生。不过,“嘉靖倭乱”带有中国私商与葡萄牙人海上走私贸易的背景,反映出新航路开辟后全球贸易的影响①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1页。。或者说,它是在“海禁”政策环境下,世界市场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联动效应②陈尚胜:《隆庆开海: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人民论坛》第611期(2018年10月下),第142-144页。。但成化、弘治时期,葡萄牙人尚未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市场与欧洲人主导的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尚未出现。那么,成弘时期中国私商出海走私贸易的背景究竟如何?其走私贸易的具体状况怎样?近年,刘正刚先生在整理明代孤本《皇明成化条例》时,结合相关条例,探讨了成化时期的海洋走私贸易活动,认为成化时期存在着沿海民众接买番货、外国使臣夹带私货以及与中国军民联手走私三种情况③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研究——基于条例考察》,《暨南学报》,2019年第8期,第66-78页(下同)。。他的研究提出了人们以往未曾关注的明代成化时期海洋贸易问题,深化了学界对于明前期海洋走私贸易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在刘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引明末官员张燮所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的情况,再对成弘时期沿海商民走私问题做一专门考察。张燮所说的“成弘之际”,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确实为同一个阶段,并且是明代社会的转折时期④刘婷玉:《成弘之际的“盛”与“变”——作为转折时期的成化、弘治时代》,陈支平、万明主编:《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91页。。因此,本文试将海洋走私贸易活动的考察范围从成化年间扩大到弘治时期。
一、成弘时期海洋走私活动与官方应对
明太祖为了对付逃往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势力,洪武初年(四年以前)即采取“海禁”政策,禁止沿海商民出海贸易⑤曹永和:《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4年,第41-70页。。而建国后沿海地区连年的倭寇活动与对日交涉的失败,使明太祖将“海禁”政策作为一项国策贯彻并作为“祖宗定制”延续到后代⑥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然而,明朝自宣布“海禁”之初,就出现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如洪武四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自派人出海行贾⑦《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以下明代各朝实录版本,皆同),第1307页。。宣德时,官员军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⑧《明宣宗实录》卷103,宣德八年七月己未,第2308页。,又有漳州卫指挥覃庸等私通番国⑨《明宣宗实录》卷109,宣德九年三月辛卯,第2448页。。正统间,浙江备倭都指挥朱兴役使军士越境贩易⑩《明英宗实录》卷41,正统三年四月丁卯,第802页。。景泰年间,有“都指挥张土纵家奴下海,私易番货。”⑪《明英宗实录》卷267,附录:景泰七年六月癸卯,第5668页。不过,洪武至景泰年间的海洋走私活动还只是零星出现,但到成化、弘治时期走私贸易案例却在显著增加,笔者根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和相关资料整理出这一时期的主要走私案例20起,并附1起出海时间、地点及人物均不明晰的案例,另附1起市舶太监开设港口准许夷商入港贸易的案例,详见下表:

续表
上表所列的20起案例,若从成化弘治时期40年时间考虑,基本上每两年就有一起,而实际发生的走私案件数量当在此数之上,成弘时期的海洋贸易走私活动显然已经超过以前。针对沿海地区走私贸易逐年增多的情形,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开海通商,如成化年间福建佥事章懋“建议番货互通贸易以裕商民”①《明史》卷179《章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同),第4751页。。但朝廷并未采纳,而是要求都察院到东南沿海各府县河口张榜重申“海禁”法令。成化七年二月宪宗颁发谕旨:“近闻有等奸顽之徒,擅造违式大船,将带违禁物货,前往番国买卖,恁都察院便出榜去福建、广东、浙江各府、州、县常川张挂,通行晓谕,有犯了的,即便拿问,正犯处以极刑,家口发沿边卫所充军。钦此。”①(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兵部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45-149页,第150-152页,第152-154页。
上引宪宗谕旨只是针对本国商民下海并到外国买卖番货的行为,不久又对在陆境内地本国官民与外国朝贡使节接触购买番货的行为做了严格规定:“今后凡遇进贡夷人往回,不许一应人员私与夷人往来交结,因而透漏事情,并将一应铜钱什物私自卖与,在京听锦衣卫官校缉访,在外听所在官司体察,如有故违,就便拿问究治,……将犯人发边卫充军。其在内会同馆等衙门、在外镇守守关并沿途官司及伴送官舍通事人等,敢有纵容夷人出入城镇市肆之间,与人交通收买应禁物,事发一体治罪。……各出榜通行晓谕各处军民人等,不许与各夷交通往来,投托管顾,揆置害人,敢有故违,照依兵部奏准事例,正犯俱发边卫充军。”②(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兵部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45-149页,第150-152页,第152-154页。从该条规定看,明朝管治的对象并非入境后违规的外国朝贡使团成员,而是那些与“夷人”交易往来的本国官民。
同时,明朝针对沿海地区商民海上走私贸易日益活跃的情形,又出台一些新的“条例”来补充以前法令不周之处,以应对新的走私贸易活动。如表中的方敏案和丘九重案,他们虽然接买番货,却不曾自造违式大船,所以不能完全按照以前的“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的条例,因此未对他们处以极刑,而改往广西边卫充军。此后,明朝即把“违禁通番接买番货,不曾打造大船,比例奏请充军”③(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兵部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45-149页,第150-152页,第152-154页。,作为一项新条例确定下来。弘治元年,南京上新河有奸商贩卖番货胡椒等物,南京都察院认为旧例只有出洋“接买番货”的规定,而且仅限于福建、广东、浙江三地,而对内地兜售番货和三省以外的地方并无相关处置规定。都察院在研究后即做补充规定:“除打造大船、将带物货、前往番国买卖者,事发照前项钦奉圣旨榜例问拟发边外,其除打造大船专一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或又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虽不曾打造大船,事发问拟明白,俱发边卫充军。若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下收买贩卖者,事发到官,若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照方敏等事例,不分首从,问拟明白,奏请定夺。若不及前数者,止照前例发落,番货俱尽数入官,牙行、停货人家不行首官者,事发一体治罪。”④(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兵部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第145-149页,第150-152页,第152-154页。他们奏呈孝宗皇帝,获得批准,通行两京、南北直隶和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内容并在弘治年间收入《大明会典》,从而由权宜之法上升为国家常法:“凡海禁,弘治十三年令,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而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或探听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若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番货入官。”⑤(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132《兵部15》,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791册,第346页。成弘时期的这些条文表明,明朝仍恪守洪武时期以来的“海禁”政策,不断补充并完善相关法令则例⑥参见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研究——基于条例考察》,《暨南学报》,2019年第8期。,以打击并制止海洋走私贸易活动。
二、成弘时期海洋走私活动与沿海豪势及权贵
从前面《成化弘治时期海上走私活动一览表》的具体年代分布看,走私活动的频发时段是在成化时期,在20件例案例中占有16起,而弘治时期仅有四起,说明成化弘治时期新条例的出台对海洋走私活动具有一定的扼制作用。不过,细察弘治时期的四起案例以及附2案例,却有3例是手握大权者所为,这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一时期海洋走私贸易活动中的不同群体及其走私活动强度。
我们若是从走私者的身份和背景来观察,就会发现包括下列四种类型:第1、第4、第5、第13起案例,是沿海地区卫所军官利用防海职权私自组织下属或与下海商民合作进行的走私;第2、第3、第6、第7、第9、第10、第13、第14、第15、第18、第20起案例以及附1案例,都是由沿海及内地商民进行的走私;第8、第11、第12起案例,为明朝官员借访问外国机会带大量私商进行的走私;第17、第19起案例是由两广总兵官主导的走私,第16起以及附2两起案例则是由市舶太监主导的走私,这4起案例可称之为权贵走私。
从上述四种类型走私贸易的案例数量看,明朝沿海及内地商民走私贸易共有11起(包括附1则有12起),占表中所列20起中的半数偏多,显然是这一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的主要类型。而细察明朝沿海及内地商民走私贸易的11起案例,其中第13起广东潮州府海阳县民丘九重等潜往大金门岛接买番人喇哈翁宗熙苏木,通过贿赂潮州卫指挥佥事李雄,才得以装运货物至南京等地发卖,带有与有权者勾结以完成走私的背景;第14起案例中的福建某大侠私通番射利,这位“大侠”在地方上应是一位豪势人物,所以能“盘结下上”,既可找到当权者帮忙,又能驱使普通人下海贸易;第18起案例中的沿海贪利之徒治巨舰出海与夷人交易,从他们能打造“巨舰”本身看,应是家资不菲之人,这应是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所说成弘之际之“豪门巨室”。此外,我们从案例10中福建汀州人谢文彬和案例20中江西信丰县民李招贴、福建人周程等人行迹看,他们也都属于违禁下海,在下海成功后即借助外国朝贡使节的名义(谢文彬以暹罗朝贡使节身份、李招贴与周程则诱引爪哇官员子弟携带过期勘合朝贡),实则骗用权力寻租来获取走私贸易利益。由此而观,在沿海及内地商民走私的11起案例中,至少有4起案例或与沿海豪势或与权力寻租有关。
另外三种类型有10例,也占表中所列20起案例的一半。这三种类型,则直接带有不同程度权力的背景。其中,沿海地区卫所军官的权力有限,他们主要利用防海职权私自组织下属或与下海商民合作进行走私贸易,这类案例共有4起。如前节所述,沿海卫所军官利用防海职权走私贸易,是明朝洪武时期以来已有的现象。另外,《明实录》中还记载,正统五年浙江曾发现百户徐定纵家人下海案①《明英宗实录》卷66,正统五年四月癸巳,第1276页。。不过,从成弘时期海防军官4起涉案的具体情况看,只有案例4一例仍沿袭了以往海防军官直接派人下海通番的模式。另外3例(表中案例1、案例5、案例13)则显示海防军官走私贸易行为的新动向,他们更多的是接受部下或商民贿赂,坐受通番之利。如案例5福建都指挥佥事王雄则是受部下贿赂,听任部下与番商互市,并在巡海过程中遇番舶挑衅未予反击而致使官兵受伤;案例13中的潮州卫指挥佥事李雄也是接受了下海商民的贿赂,听任他们接买番人货物并装运到南京等处发卖;而案例1则稍有不同,广海卫人叚镇出海通番诱使爪哇朝贡使节驾贡舶前来潮州停泊,而广海卫指挥周岳则借检查贡物封舱之机私扣爪哇朝贡物品,表明广海卫军人叚镇下海通番之前与指挥周岳之间应有串通,周岳可能也接受过叚镇的贿赂。
成弘时期,明朝使节携带众多私商进入藩属国家进行走私贸易的案例则有3起,说明这一时期官员利用官方对外交往渠道进行走私贸易的案例在上升。据《明实录》记载,早在宣德时期就有人“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②《明宣宗实录》卷103,宣德八年七月己未,第2308页。为此,明宣宗命令南京都察院严禁私通外番,并通告沿海军民与各级官员。此后的正统至天顺时期(1436-1464),官员假借朝廷干办之名擅自入番走私的情况因有宣德新规而受到抑制。但到成弘时期,领命册封海外藩国的官员却借这种外交机会,违禁携带庞大的商人队伍进行私人海外贸易,如案例8中的工科右给事中陈峻使团,案例11中的礼科给事中林荣与行人司行人黄乾亨使团,案例12中的行人司右司副张瑾与礼科给事中冯义使团,他们在分别奉命出使占城或满剌加国的过程中,不仅随行人员达到千人,完全超过明朝派往藩国册封使的一般规模(明朝派往海外册封使团,洪武年间规定在五百人左右,一般在二三百人至七百人之间不等)①谢必震:《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而且“多挟私货以图市利”,甚至还出现货物太重而发生沉船以及人员伤亡事件(如林荣、黄乾亨使团)。从明朝制度上说,他们三人身为六科给事中,作为言官本掌有稽察官员言行之责,临时受命出使却带头违规,说明明朝纲纪的松弛。这种大量带人并带货的违规出使,也属于权力寻租。由于他们的册封使权力带有临时性,这种行为应近似于权贵走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执掌国家国防大权的两广总兵官与代表皇帝提督市舶司的广东市舶太监,也直接组织走私贸易,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如案例17中两广总兵官、安远侯柳景安排百户陈谦等人私通外夷②《明孝宗实录》卷54,弘治四年八月戊午,第1059页。;案例19中继任两广总兵官毛锐“广营邸舍以处番旅,私造船舶以通裔夷”③《明孝宗实录》卷142,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第2460页。;案例16中的广东市舶太监韦眷与番禺县民王凯父子勾结,私造巨舟招人下海通番。按:皇帝派遣太监提督市舶,始于永乐年间,其用意在于加强对外国使节朝贡贸易的垂直管理与对市舶司机构的直接领导,意在代表皇帝来控制利权。随着宦官势力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膨胀,市舶提督往往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等职④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于此可见,市舶太监并不满足于对三年一贡或五年一贡的“朝贡贸易”的控制,还要通过其它途径来满足个人对权利和财富的占有,如成化初年福建市舶内官蒙信死后,“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指明朝各行省的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廷秀(指何乔新,时为福建按察司副使)独力辞之不获,则受而输于公帑。”⑤(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页。还有另一位福建右布政使朱英,会“提督市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赀遗藩臬,力辞不能却,乃受而输于官。”⑥(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3《湖广辰州府、郴州府、永州府》,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35册,第370页。上述两例说明,当时皇帝派往福建的市舶内官蒙信,生前曾以提督市舶之权获取不少个人财富。成化十二年,福建市舶太监施斌也死于任上,当时福建巡按叶稠与三司官员上奏:“市舶提举司专理琉球一国贡物,事务不繁,内官施斌既卒,宜勿更差。”他们认为比较廉洁的福建镇守太监卢胜可以兼任,但宪宗皇帝并不同意,又派来内官韦查前来提督福建市舶⑦《明宪宗实录》卷152,成化十二年四月乙未,第2780页。。而通过表中附2案例,我们还看到弘治时期镇守福建的内官邓原,深悉广东番舶贸易所带来的厚利,便在福州上王地方开凿新港,使夷船通过闽江可以直接入港。邓原要求每年进港的番舶都要缴纳税银若干,贮之官库,以备福州修桥等地方事业之需⑧(明)叶溥、张孟敬纂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正德福州府志》卷6《地理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第115页。。与蒙信借提督市舶之权来获取个人财富不同,邓原则是借提督市舶之权来增加地方财政利益,应是为公。不过,他在福州开放“番舶”贸易,却破坏了王朝旧规。在广东,韦眷身为市舶中官,私造巨舟通番,又“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⑨《明史》卷304《韦眷传》,第7783页,第7783页。;番人马力麻诡称苏门答剌使臣欲入贡,私市易,“眷利其厚贿,将许之。”⑩《明史》卷161《陈选传》,第4389页。韦眷的违法行为曾遭到当地官员抵制,如番禺知县高瑶曾捉获韦眷走私的胡椒、象牙、沉香、苏木等物,“没其赀巨万于官”⑪(清)戴肇辰、苏佩训修、(清)史澄、李光廷纂:《光绪广州府志》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41页。。左布政使陈选也曾阻止和揭发其不当行径,韦眷因此对高瑶和陈选怀恨在心,构陷于朝,致二人俱被逮,“自是,人莫敢逆眷者”⑫《明史》卷304《韦眷传》,第7783页,第7783页。。正德年间来到广东担任巡按御史的高公韶还曾指出,“旧例,岭南诸番入贡,其所附货物,官税其半,余偿之直。其不以贡来者,不许贸易,与之交通者,罪至死。后以中人镇守,利其入,稍弛其禁。顷者,权豪贪纵,任其住泊。”①《明武宗实录》卷123,正德十年四月丙午,第2470页。在他看来,广东沿海地区走私贸易泛滥正是由于市舶太监只顾征税增收而放松对番舶的入贡标准,地方权贵们也贪图利益而听任番舶任意停泊。
上面所述的沿海地区卫所海防军官、明朝出使蕃国官员、总兵官和市舶太监所主导的走私贸易活动,都带有权力寻租的性质。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则说明纲纪已经松弛。当然,他们要完成走私贸易行为,还需要普通民众下海来具体承担,如广东市舶太监韦眷私造巨舟走私就要招人下海通番。于此可见,明朝出使官员、两广总兵官和市舶太监等权贵势力进行走私贸易,必须有普通民众的参与。那么,普通民众最初又何以能从王朝政策中获得下海允许的呢?
本来在“海禁”政策下,沿海民众不仅出海贸易受禁,连下海捕鱼等谋生活动也受禁。明英宗即位初,海防官员就曾认为,“下海捕鱼者恐引倭寇登岸。行在户部言今海道正欲提备,宜敕浙江三司谕沿海卫所严为禁约,敢有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英宗皇帝)从之。”②《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七月己丑,第141页。因此,正统十一年巡海都指挥同知王瑛因受贿赂而放任部下出海捕鱼,即被人告发并被英宗皇帝敕令巡按御史予以查处③《明英宗实录》卷145,正统十一年九月辛卯,第2863页。。不过,沿海民众需要下海捕鱼谋生,又势难严禁。所以,弘治十七年三月兵科给事中张弘至建议,“海滨之民以捕鱼为生,编竹为筏随潮往来,宜令所司稍弛科禁,使之安业而盗自弭。”④《明孝宗实录》卷209,弘治十七年三月丁丑,第3890页。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张弘至题奏开放海滨渔民下海捕鱼之前,漳州知府谢骞已于景泰四年通过登记船只的办法就开放了渔禁⑤参见据万历四十一年闵梦德编修《漳州府志》卷13。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3页。。而沿海开放渔禁,就为普通商民出海走私提供了方便。
然而,普通商民下海走私贸易,下海时或回乡后要想不被发现和追究,要想完成置货下海或把番货变卖,还需要在海防官员、地方官员或沿海豪势中寻求保护伞。所谓“豪势”,指在地方上比较强横而又有一定权势的人。明朝太祖开国后,一直高举打击富豪政策,使豪势一时失去存在空间。此后,太宗与宣宗皇帝从维护赋役稳定角度,派廉干大臣核实田亩,严防豪势恃强凌弱侵占土地,并严禁有人借机容隐人口与侵占水利⑥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12“永乐九年正月甲子”、《明宣宗实录》卷15“宣德元年三月壬戍”、卷36“宣德三年二月甲寅”、卷87“宣德七年二月庚戌”、卷107“宣德八年十一月丙午”诸条。。但正统元年(1436),户部尚书黄复已了解到,“南、北京畿之内并各边境水陆田地,权豪势要占为己业”⑦《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戊子,第293页。。成化年间佀钟为官时也发现,“河间、濒海民地为势豪所据”⑧(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28,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二册,第1195页。。弘治年间巡抚魏绅在题奏中也称,“应天、镇江等府,滨海田地新涨洲涂尽为势豪所据”⑨(明)张学颜等:《万历会计录》卷16《南直隶田赋》,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32册,第182页。。显然,从正统至弘治时期一些人通过兼并土地,在沿海地区开始形成豪势阶层。接着,沿海豪势又染指官方仓储,并通过操控粮价来获取利益。成化末曾任福建参政的刘大夏在巡视海道时即发现,“兵久弛,仓储为势豪所侵”⑩(明)项笃寿:《今献备遗》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册,第675页。。王弼在担任福建兴化府知府时,也了解到“豪右私牙侩,通海舟贩籴,谷价遂翔贵”⑪(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91,第六册,第3952页。。表明一些人因为贩运粮食而介入海洋运输业,沿海豪势作为一股海洋运输势力开始出现。
沿海豪势介入盐业生产和销售,也是他们迅速扩充自己经济实力的重要基础。本来,明朝盐业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各盐场灶户进行盐业生产并交给官府收买,官盐运销则通过开中法,令商人输送米粮等物资供应边镇,官府则给商人以盐引,由商人到盐场支领食盐自行运销到指定地区。正统六年正月,两浙巡盐御史张淑巡查海盐生产时却发现,已有私人染指盐业生产,产量在百斤至万斤不等,遂对产盐二千斤以上者按律治罪,其余一概取缔①《明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乙卯,第1463-1464页。。成化四年初,户部官员奏报:“近因豪势搀中,致令盐法不通。”一些官盐生产的灶户,由于“贫穷,借贷于官豪之家,为其占据役使。”还有一些灶丁每逢纳课,那些豪势却“百端阻抑”,从而把控了盐业的生产和销售,由是“私盐横行,官盐沮格”;“私盐盛行,官盐价贱。”②《明宪宗实录》卷51,成化四年二月丙辰,第1048页。弘治初年,雍泰在浙江任右布政使时,也看到“势豪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恣肆横行”③(明)陈建撰、(明)高汝栻订、(明)吴桢增删:《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26《巳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十八年》,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第438页。。盐业的产销,已成为沿海豪势阶层获利的重要来源,却使明朝设计的食盐制度与边镇粮饷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诚如后来史学家所指出的,“淮、浙盐自成化间为势豪乞中者所挠,有司不敢与忤,每事姑息。以是盐法日坏,商病而课不充,边储匮乏。”④(清)夏燮:《明通鉴》卷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
凭借着土地兼并和控制盐业的雄厚基础,沿海豪势可以修造“巨舟”、“巨舰”、“大舶”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成化时期,朱瑾任福建莆田县丞时,即了解到当地“贵豪造巨舶,通岛夷,为奸利”⑤(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卷38《县》,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44册,第677-678页。。而福建按察使副使辛访在巡视沿海时也发现,“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遂“捕其渠党,而置诸法,没入其舰”,不料“事连达官”,他们竟诬陷辛访是在激变良民⑥(明)何乔新:《椒邱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显然,福建濒海大姓与一些官员在走私贸易活动中已结成利益共同体。此外,我们在前面对普通商民走私活动的考察中,也看到沿海豪势的身影。所以,明朝虽屡申下海之禁,“然滨海巨室,亦时时私通,买卖不绝。”⑦(明)李豫亨:《推篷寤语》卷9《毗政篇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06页。可见沿海豪势阶层已成为海洋走私贸易的中坚力量。如此看来,明末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所说的“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应是看轻了沿海豪势在当时走私贸易活动中的能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成弘时期海洋走私活动主要来自三股力量:一是沿海甚至内地的普通商民,二是东南沿海社会的豪势阶层,三是闽粤地区官场上的部分权贵和朝廷中临时受差出使海外的官员。从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看不少也带有沿海豪势的身影,而权贵势力则使走私贸易更加大规模化,它反映出政治纲纪的松弛与明王朝对于东南沿海社会掌控能力的下降。
三、成弘时期海洋走私活动与贸易网络
海洋走私贸易活动,离不开人的流动与商品的流动,因此,我们再就《成化、弘治时期海上走私活动一览表》中一些有详细记录或可追踪其它相关资料的案例,对海洋走私活动中的人的流动与商品的流动进行讨论,以考察当时的贸易网络。

成化、弘治时期海上走私活动一览表
我们先看表中案例9成化十四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商人方敏兄弟与广东揭阳县民陈祜等人的走私案例。据成化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掌都察院事王越奏报皇帝的巡视海道副使张诰提审犯人时所得供词:“问得犯人方敏,招系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成化十四年三月内,敏明知有例,军民人等不许私出外洋,盘接番货,不合故违,商同弟方祥、方洪,各不合依听,共凑银六百两,买得青白花碗、碟、盆、盏等项磁器共二千八百个,用船装至广城河下,遇有熟识广东揭阳县民陈祜、陈荣,海阳县民吴孟,各带青白苎麻等布,亦在本处货卖。敏等访得南海外洋有私番船一只出没,为因上司严禁,无人换货。各不合与陈祜、陈荣、吴孟谋允,雇到广东东莞县民梁大英,亦不合依听,将自造违式双桅艚船一只,装载前项磁器并布货,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开船越过缘边官富等处巡检司,远出外洋,到于金门地方,遇见私番船一只在彼,敏等将本船磁器并布货,兑换得胡椒二百一十二包、黄蜡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扁箱、锡二十块过舡。番船随即挂蓬驶出外洋,不知去向。敏等艚船驶回里海,致被东莞千户所备倭百户郭庆等哨见,连人船货物捉获,呈解巡海张副使处,蒙行广州府卫委官眼同秤,盘得胡椒、乌木、黄蜡、番锡、沉香,俱解送布政司官库收贮,船只发回南海卫改造战船备倭。”①(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册,第902-903页。从这份史料可见,江西浮梁人方敏等人与广东揭阳人陈祜等人都卷入了这起海洋走私案。陈祜等人作为潮州府揭阳县民,地处粤东沿海,可以依靠榕江和近海交通航线把货物运输到珠江口。但方敏等人地处江西东北的饶州府浮梁县的内陆之地,却敢于携货前往广州寻求走私贸易,显然浮梁县与广州之间存在着一个市场网络,其运货路线应是取由江西至广东的水道,即从浮梁取昌江水道进入鄱阳湖再取赣江水道,在南安府大庾县横浦驿上岸过大庾岭(梅岭),在广东南雄府保昌县凌水驿再下水,取浈水、北江至广州五羊驿②参见(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湖口县由江西城至广东水路”条,载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207-208页。。这条商道即是由江西至广州的驿道。
从货物流动看,方敏兄弟运景德镇磁器到广州珠江内河,和陈祜等人运揭阳苎麻布至广州,都是寻求外贸机会,他们听说外海有外国商船出没,又合伙雇请东莞梁大英打造违式双桅艚船出海,绕过东莞县当地巡检司,到达南海金门海域(即今广东台山市上下川岛附近海域),与外国船交易胡椒、乌木、黄蜡、番锡、沉香等货物后返回,被东莞千户所海防官军所抓。按:苎麻纤维早在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就曾发现,曾被外国人称作“中国根”。而广东揭阳的苎麻布业,据清雍正《揭阳县志》记载,“苎布九都皆有,乡无不织之妇故也,其细者价可倍纱罗。”③(清)陈树芝纂修:《揭阳县志》卷4《物产》,第50页,清雍正九年刻本(爱如生方志库)。明代揭阳苎麻布的生产是否如此?结合陈祜等人外销情况与清雍正方志记载来看,揭阳的苎麻布应是特别有竞争力的商品。而江西景德镇瓷器,更是远近驰名的货物,据当时人记载,“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一些“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④(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7《陶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909页。。所以,方敏等人作为内地民众,专门携带瓷器到广州寻求外商,就是为了谋求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曾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1451年定稿的《瀛涯胜览》中就曾明确记载,占城国人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器,纻丝、绫绡、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花绢、纻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锡兰国人“甚喜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将宝石、珍珠换易”;祖法儿国人也是“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土鳖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⑤(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27页、第56页、第77页。而方敏等人从外国商人换回的胡椒、乌木、黄蜡、番锡、沉香等物品,在《瀛涯胜览》和约成书于1520年左右的《西洋朝贡典录》中都有介绍,如《西洋朝贡典录》书中介绍,出产胡椒的国家有爪哇、彭亨、苏门答剌等,出乌木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满剌加、暹罗等,出产黄蜡的国家有真腊、爪哇和苏禄,出番锡的国家有满剌加、苏禄和苏门答剌,出沉香的国家有真腊、爪哇、满剌加、浡泥、暹罗、苏门答剌等⑥(明)黄省曾著、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校注》,卷上“占城国”条、“真腊国”条、“爪哇国”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下同),第12页、第15-17页、第29-30页、第41页、第45页、第47页、第49页、第60-61页、第69页。。
再看表中案例10所记暹罗使节谢文彬在南京贸易违禁货物案,依据《明史·暹罗传》,但具体案情不详。不过,在现存明人奏议中,却保留有一份关于暹罗朝贡使节杜文斌在南京与内地商人违规订购违禁丝织品的奏状。根据最后审讯杜文斌堂侄杜瓒结果,杜文斌是福建汀州人,暹罗名为柰英必美亚,“先于正统十三年间因支盐买卖,遭风飘流过海,今在暹罗国封为岳坤等官,今充为使臣差来进贡”①(明)王恕:《太师王端毅公奏议》卷4,《参奏南京经纪私与番使织造违禁纻丝奏状》,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下同),史部第199册,第250—251页,第250—251页。,这与《明史·暹罗传》所记“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基本情况相近,显然《明史》所记“谢文彬”,应是明代成化年间这份审问状中的“杜文斌”之误,而暹罗官名“岳坤”(Ockan),也被《明史》误写为“坤岳”。“据南京锦衣卫巡捕委官百户蔡瑛呈:据周璋首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户籍,成化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暹罗国进贡使臣杜文斌等到于上新河湾泊,有经纪韩源、陈质等引领邻人石聪、钱鹏等合伙用礼,俱赴番船交结,卖过象牙、苏木银共银七百三十六两回家;又凭中人田宽会约在城机户陈冔等,家织造各样大红黄并八宝闪色抹绒花样、遍地金花帏幔各样缎疋,共织一百一十五疋。后有中人田宽来与璋说,石聪等领银织造番使缎疋缘由,亦来邀璋前去番船成交。比时,有璋不合听从到船,凭田宽领银五百三十一两。其石聪就行俵发机户陈冔等定织各色违禁缎疋,有璋并无分文入己。不期又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有安南使人裴山到于上新河,有彼中人阮福因前成交,来与石聪用言说,其使要织各样缎疋,可去成交。有璋又不合与同,石聪到于使臣船上,承揽织金违禁纱罗缎疋共三百余匹,俱各将象牙作银,交与机户吴斌等写立合同,依样织造,待回交付。内有各样纸札,该银三百六十七两。其石聪等因嗔璋在伙,设计勒璋自立合同,虚受倭人安息油料等香该价银四十四两六钱六分,余无分文银两,与璋收领见有合同存照。其石聪等因前恠恨有璋在伙,却乃唆令暹人使人杜文斌于原定织造数内,勒璋自立合同,领银一百二十九两,分投开款,另认织五彩抹绒幔边二疋并蟒龙大红缎疋。有璋止收现银二十九两,依从织缎二疋,内银一百两也系石聪等要得,侵谋银两肥己,暗设奸计,叱喝伴送番船官处,拘璋到船威治,勒写收银一百二十九两。供状在官,故令陷害,今思若不状首,委被奸徒石聪等纠众私结番船,领银织造玄黄官花样遍地金缎疋,事属违例。如蒙准首,乞赐行提各犯石聪等到官,追究私结番人,伪织违禁缎疋,欺凌㳅骗银两情由,明正其罪,庶免日后不致陷害,负损身家性命,为此将原领番银、香货并织违禁缎疋数目,并领象牙逐一开单,粘连具状。”②(明)王恕:《太师王端毅公奏议》卷4,《参奏南京经纪私与番使织造违禁纻丝奏状》,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下同),史部第199册,第250—251页,第250—251页。根据上面奏状内容,可知暹罗国使节杜文斌、安南国使节裴山分别在前往北京朝贡途中,曾在南京卖出象牙和苏木等货,通过石聪、周璋等人联系机户私订违禁缎疋。周璋由于与石聪等人在织造缎匹银两分配上的矛盾,遂到官府告发。按照明朝的制度设计,外国朝贡使团在从入境口岸登陆前往北京途中,可以在沿途主要城市通过官方牙行与当地商人进行少许交易,以便订购当地货物。就此案来说,周璋与石聪等人行为都是绕开官牙而属于“私结番商”,并帮助外商订购违禁丝绸产品,违反了《大明律》中的“与朝贡夷人私通往来”和“织造违禁缎疋”等条文。
根据这起案件后来的审问情况,办案人员查出南京丝织机户违规承接织造的缎疋有四百余疋,它也反映了当时南京民营丝织业的盛况。其实,南京只是当时江南丝织业的一隅,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的丝织业都很发达③据《明英宗实录》卷317“天顺四年七月癸卯”条记载,“降工部右侍郎翁世资为湖广衡州府知府。初,上欲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叚七千匹。工部奏:其处巧匠多取赴内局,且丝料有限,请减增造之数,以苏民困。上怒,讯其主意者……”(第6623页)从明英宗突然加派七千匹彩缎的情况可知,当时苏、松、杭、嘉、湖五府的丝织业非常发达。。清雍正时期从吴江县析出的《震泽县志》中曾记载苏州一带丝织业,“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①(清)陈和志修、倪师孟等纂:《震泽县志》卷25《生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946页。明代万历时人王士性也曾记载湖丝,“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②(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第80页。由于江南生丝生产与丝织业的坚实基础,其产品一直行销国内外。王士性还认为,“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③(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第80页。在王士性看来,人口密度与社会分工,以及手工业生产与商品经济有着层层递进关系。而上述几起走私案例,显然与瓷器、丝织品的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的扩大有着密切关联。
暹罗等国朝贡使节带到南京销售的象牙、苏木、各种香货,在先前外国使节朝贡活动与中外普通商民贸易中司空见惯。尤可注意的是,外商在与南京本地商民接触中将象牙、苏木等货折算成银两的现象。明初,官方货币是宝钞,政府禁止用银两作为流通手段,但到正统年间宝钞已日益贬值,民众大多弃之不用,更多人使用铜钱、实物货币(布帛、米谷、金银等)。成弘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国内市场的扩展,白银开始在流通领域大量使用④邱永志:《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9-40页。。与此同时,明朝也在这个时期推行田赋、徭役、盐课、茶课、钞关关税的折银化改革,完全接纳白银作为货币⑤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308页。。傅衣凌先生曾明确指出,“明代白银的大量使用,实在成化、弘治年间,即是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六世纪初。”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发达是白银流通于市场的主要原因⑥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收于傅氏《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251页。。
我们再看表中记载其他广东与福建商民走私的10个案例。先看广东商民走私的4起案例:案例1记广东广海卫人叚镇经常泛海贸易,从他与爪哇国使节梁文宣熟识的情况看,叚镇应去过爪哇。成化元年,梁文宣作为爪哇使节入明朝贡时,叚镇即利用他与梁文宣熟识的关系,引导爪哇朝贡船舶至潮州港驻泊,潮州卫指挥周岳利用封盘验货机会,私留爪哇国朝贡商人玳瑁百余斤,事发交巡按御史讯问,得悉周岳与叚镇“为奸利日久”⑦《明宪宗实录》卷19,成化元年六月戊申,第379页。。于此看来,叚镇应经常在潮州与爪哇之间进行走私贸易。案例13所记成化十八年潮州府海阳县民丘九重、蔡三等人潜往大金门岛接买番人喇哈翁宗熙苏木之事,又是一例与潮州相关的走私案。而文中所说的“大金门岛”,位于广州府新宁县境内,即今天台山市所属的上川岛。据明人记载,“上下川之左曰大金门,右为大小金门,诸夷入贡,风逆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而番船舶往来之冲。”⑧(明)郭裴:《广东通志》卷14《郡县志一·广州府》,第34-35页,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爱如生方志库,第1418-1419页。由于上川岛为番舶到广州的必经之地,番舶常在此避风驻泊,也就成为中外商民进行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从此案可见由新宁上川岛→潮州的走私线路,再由潮州装运番货海运到南京销售的物流方向。而关于“大金门岛”(即上川岛)的走私贸易据点,我们从案例9中的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方敏、潮州府揭阳县陈祜等人在东莞合雇梁大英打造双桅艚船,前往金门岛寻求外商进行贸易的事实中也可得到印证。此外,案例15记载成化二十年广东潮州沿海曾发现通番巨舟37艘,被明朝官军发现并追捕,走私贸易者30余人被抓、85人被杀之事。显然,潮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走私集团,他们是去上川岛与番舶交易,还是去海外国家贸易,可惜史料未载。
再看福建军民走私的6起案例:案例6是记福建龙溪的两个走私集团(丘弘敏等29人、康启道等26人)经常到暹罗、满剌加国进行走私贸易,说明在福建龙溪与暹罗、满剌加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固定贸易路线。龙溪为福建漳州府辖县,可凭九龙江西溪与北溪等水道入海,海洋交通十分便捷。明嘉靖时人桂萼曾在《福建图序》中说,“海物互市,妖孽荐兴,通番海贼不时出没,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①(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82《桂文襄公奏议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三册,第1865页。由此可知,当时龙溪县与其南邻漳浦县的两县居民,多参与海上走私贸易活动。《西洋朝贡典录》中也记载,暹罗国由漳州而往②(明)黄省曾著、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校注》,卷中“暹罗国”条,第55页。。案例20记江西信丰县民李招贴与福建人周程等一百余人走私集团前往爪哇国贸易,但周程所属福建的具体户籍不明。李招贴、李廷方等人户籍所在的江西赣州府信丰县,完全属于内陆县份,他们与福建人周程一起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估计是李招贴等人先后取信丰江、雩水、贡水、锦江航道至瑞金,由陆路至汀州,再由汀州取鄞江、韩江水路至潮州③参见(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赣州府至福建汀、潮二府水、陆路”条,载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17页。,在潮州与福建人周程汇合,因此周程等人有可能是汀州人,也有可能是潮州邻近的漳州漳浦人。从这个案例再结合前面案例9中所涉及的潮州府揭阳人陈祜等人走私情况看,在漳州、潮州近海地区与爪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贸易网络。此外,案例3所记福州府福清县薛氏出诸番互市,案例5记福建都指挥佥事王雄接受部下贿赂听任部下与岛夷互市,案例7记载龙溪县民29人泛海通番,案例14记载福建某大侠通番射利,这4起案犯到何处通番,可惜史料不详。
从以上考察可见,当时从事海洋走私活动的商民主要来自福建漳州府和广东潮州府,而少数来自福建福州府和内陆的汀州府、江西饶州府、赣州府的商民,以及少数卫所军士也参与了海上走私活动。他们航海走私的目的地,资料显示出来的有占城、暹罗和爪哇,还有广州府珠江口附近有番舶停泊的岛湾。据两广总督闵珪在弘治六年的奏报:“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备倭官军为张势,越次申报,有司供亿,糜费不赀,事宜禁止。况夷情谲诈,恐有意外之虞,宜照原定来贡年限事例,揭榜怀远驿,令其依期来贡。”④《明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丁丑,第1367页。文中所说的“番舶”,是指外国船。本来,明朝对于外国船只来华,限定于朝贡活动,有朝贡才有贸易,并有时间限制(如规定占城、暹罗、爪哇等国三年一贡),同时又颁发勘合号簿给外国王室,口岸官员通过对比勘合号簿以确定外国朝贡使节真伪。一旦确认外国朝贡使团的身份,明朝则对他们提供免费接待。而外商船只纷纷来到广州⑤据《明史》卷81《食货五》记载,“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第1980页),可见广州是大多数海外国家朝贡使团的登陆口岸。,从而造成地方政府接待供应紧张。所以,两广总督闵珪奏请要对番舶根据贡期予以限制。不料,礼部官员却提出相反意见:“自弘治元年以来,番舶自广东入贡者,惟占城、暹罗各一次。意者,私舶以禁弛而转多,番舶以禁严而不至。今欲揭榜禁约,无乃益沮向化之心,而反资私舶之利。今后番舶至广,审无违碍,即以礼馆待,速与闻奏,如有违碍,即阻回,而治交通者罪。”⑥《明孝宗实录》卷73,弘治六年三月丁丑,第1367-1368页。在礼部官员看来,弘治以来从广州口岸入境朝贡贸易使团仅有占城与暹罗国各一次,如果再行限制,将使外国朝贡贸易使团更少。而且,广东严禁“番舶”,只能使本国商人的“私舶”越来越多。最后,礼部官员也提出,要对不符合条件的“番舶”实行驱逐,并查处与番舶来往的中国私商。不过,无论从两广总督闵珪的奏报来看,还是根据我们对走私案例的考察来看,广东沿海络绎不绝的番舶,也是本国商民私通交易的结果,他们已形成一个贸易交易网络。这个贸易网络显示,江南出产的丝织品、赣东北所在的饶州景德镇瓷器与广州外贸市场已有紧密联系,甚至赣南地区商民通过汀州与潮州以及漳州也有走私贸易通道。同时,一些走私商民从广东番舶那里交易得到的胡椒、苏木等商品,通过广州至江西抵南京的商道内销,或通过海上运输的路径销往江浙地区。从案例13的情况看,这条海上通道需要取得沿海卫所军官的保护,最后遭到查处,说明它不如陆上商路安全。
反观这一时期江浙沿海地区海洋贸易走私案,从前面表格看有明确地域属性的则仅有一例,即案例4所记成化五年浙江海门卫前指挥李昇组织兵众泛海走私案。为何这一时期江浙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案例比较少?或与江浙沿海正面面对倭寇侵扰活动而明朝防控更加严密有关,而粤闽沿海地区向来是中国与东南亚海洋贸易的纽带。
与叚镇、丘弘敏、康启道、李招贴、周程等走私团伙贸易对象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爪哇等地而目的国比较分散不同,明朝官员走私目的地都是当时东西方贸易都市的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如案例8和案例12所记载的明朝册封使陈峻和张瑾,都是利用到占城册封新国王的机会,却带着庞大的商队前往更远的满剌加国贸易①按:据《明宪宗实录》卷220“成化十七年十月丙辰”条记载,张瑾回国后被礼部所劾,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违规贸易受审,而是因为他要册封的占城国王孤斋亚麻勿庵已在抵抗安南人扩张时战死,张瑾却接受安南人所立傀儡提婆苔者的百余两黄金贿赂对其册封,原占城王弟古来遣人来粤求援时事情露相。礼部遂劾张瑾擅自封立,当正典刑。法司比依大臣专擅选官罪,判张瑾坐斩。(第3807-3808页)。案例11中的册封使林荣直接受命前往满剌加,不料却因为船上人太多而携带的货物又太重从而导致船难事件。成弘时期普通商民出海走私与朝廷官员出使走私之所以有如此区别,说明普通商民更重视到占城、暹罗、爪哇等香药原产地采购货物,从而降低采购成本,而朝廷出使官员一致前往满剌加国,说明他们更重视从大贸易都市采购到丰富的异域货物。
四、余 论
上述成化、弘治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所发生的20起走私案例,说明明朝海洋走私活动已从洪武至天顺时期(1368-1464)的零星发生,开始活跃起来。与以前的沿海卫所士官走私活动现象相观照,成化弘治时期的海洋走私活动主要来自三股力量:一是沿海甚至内地的普通商民,二是东南沿海社会的豪势阶层,三是闽粤地区官场上的部分权贵和朝廷中临时受差出使海外的官员。同时,普通商民走私活动背后也有一些沿海豪势的身影,并间有与流寓东南亚的华商合伙走私的背景;而权贵势力则使走私贸易更加大规模化,它反映出政治纲纪的松弛与明王朝对于东南沿海社会掌控能力的下降。为了维持“海禁”,成化弘治年间明朝又推出新“条例”来打击走私。从弘治年间走私活动的发案率来看,它比成化时期有所下降,但只是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有所扼制,权贵势力的走私活动却在抬头,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走私贸易频发地是闽粤沿海的漳州、潮州以及广州沿海地区,也有少数饶州、赣州以及汀州等内陆地区商民参与了走私贸易。从闽粤赣商民走私的贸易对象来看,少数案例显示出他们航海贸易目标国是占城、暹罗和爪哇,多数案例却表明他们是与临时停泊在广东沿海港湾的番舶商人进行交易。而且,这些番舶都是来广州开展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其中,一些入境的朝贡使节还在进京途中的南京私交内商订购中国的违禁丝织品。如此看来,成弘时期本国商民的走私贸易与外商朝贡贸易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
本来,根据明初的国际贸易方针,只准外国商人来华的朝贡贸易,不许中国商民出国贸易。而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七下西洋积极招徕四夷,外国使团入明朝贡贸易十分活跃。不过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终止,外国使团再也不能搭乘明朝船队入明朝贡,外国对明朝贡贸易增加了海洋运输成本,一些路途较远国家(如印度洋海域的国家)的贡使也就不常来甚至不来,如景泰至天顺年间(1450-1464),前来进贡的海外国家除日本与琉球外,则只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锡兰①参据(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至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5-314页。按:15世纪40年代以后,一些生活在爪哇的穆斯林华人,开始用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优势,积极开展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参见陈尚胜:《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03-112页。。因此,异域宝物的减少,首先给皇室消费带来不便,天顺二年(1458),司礼监太监福安说,“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②《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二年二月戊申,第6154-6155页。同时,国内市场所消费的东南亚胡椒、苏木等香药,到成化初年也出现“京库椒木不足”的局面③《明宪宗实录》卷97,成化七年十月丁丑,第1846页。,国内市场亟需通过扩大贸易渠道以补充产自于东南亚等地的香药。在此背景下,粤闽沿海地区的一些商民开始前往占城、暹罗、爪哇等地走私贸易,并引导外商以朝贡的名义前来广东,而市舶太监更乐见其货,广纳番舶来华贸易。史书记载:“成化、弘治之世,贡献至者日伙,有司惟容其番使入见,余皆留停于驿,往来设燕馆待,方许入城。衣服诡异,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竞观之,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④(清)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2页。于此而观,粤闽地区走私贸易兴起与国内对东南亚香药的消费市场有着密切关联,而皇室的宝物消费匮乏也促成市舶太监违规开纳番舶贸易。
成弘时期粤闽沿海地区商民的走私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正是在明朝下西洋活动终止后,以及消极的“海禁”政策,中国商人(无论官商和私商)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开始式微。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中国陶瓷在已发现的东南亚沉船中几乎完全不见,直至15世纪最后十年才开始出现⑤[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13-17世纪东亚的海上贸易世界》,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61页。。而安南黎朝自15世纪40年代以后,通过向占城扩张陆续占领南海的重要港口和以香木宝库闻名的长山山脉一带,利用新领土上的产品积极开展对周边国家的贸易,并介入南海贸易圈⑥参见[日]桃木至朗:《10-15世纪南海贸易与大越=安南国家》,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174页。。尤其是琉球王国从15世纪30年代以后,积极开展与暹罗、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等国的通交贸易,并将东南亚的商品转输到明朝、日本和朝鲜,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扮演了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贸易中间商的重要角色,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⑦据《历代宝案》第一集卷39-43,台北:台湾大学影印本,1972年版;并参据[日]小葉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の研究》第三篇《南海通交贸易》,东京:刀江书院,1968年版,第373-538页。。而粤闽沿海走私商人在广东近海及东南亚邻国海域的贸易活动,多少补充了东亚海域贸易过程中的中国商品的不足。
总的来说,成弘时期粤闽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还是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内发生,只是带有一定的国内消费需求和外国来华朝贡商人的采购需求,因而它的活动能量还极其有限。它不像后来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中外商民合伙进行走私活动,带着新兴的世界市场的巨大能量,因而具有大规模性,并且形成对抗性。这正是15世纪后期与16世纪中叶明朝东南沿海地区两场走私贸易活动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