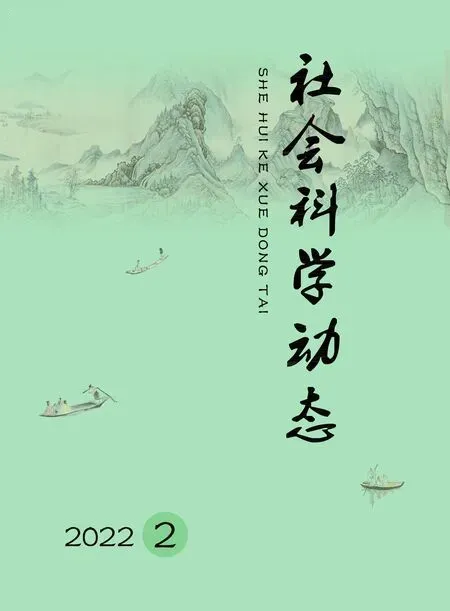乌托邦反思与欲望时代的精神救赎
——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思想价值
张 慎
“乌托邦”是人类在有缺陷的现在中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构想与追寻。卡尔·曼海姆曾将乌托邦定义为一种与现实状况不一致的“思想状况”和“超越性”取向。当这一思想取向“转化为行动时”,必然会打破现有的“秩序”。①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正是通过晚清、建国以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实践的遭遇和结局,反思了近现代中国乌托邦实践的历史,思考了百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在《人面桃花》 (2004)、 《山河入梦》 (2007)、《春尽江南》 (2011)出版之后,谢有顺、张清华、洪治纲、南帆、孟繁华、李遇春、姚晓雷、熊修雨等研究者就在相关作品评论中探讨了三部曲中乌托邦的性质和类型,挖掘了这些乌托邦理想失败的根源,并剖析了格非对乌托邦的情感态度。如,张清华认为,在 《人面桃花》中“传统、民间、人文、外来(现代文化)、本能(无意识)”等诸种因素纠缠在陆秀米的革命行动中,正是她的革命构想的复杂性导致了她“试图一揽子解决教育、医疗、公正(法律)、道德、民生等等社会问题”的乌托邦实践的失败②;李遇春将三部曲中的乌托邦实践分为古典江湖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共产主义乌托邦三种,并指出格非对乌托邦的“情感价值立场是复杂而冲突的”,体现了“人物(作者)在百年乌托邦冲动的背反与轮回中的心理困惑和精神痛苦”③;熊修雨则从乌托邦构想本身“经不住理性的检验”、“乌托邦的主体”的复杂和困惑、乌托邦实现手段的暴力残忍等方面,挖掘了这些乌托邦失败的根源④。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三部曲围绕如何处理乌托邦实践与私人欲望的关系的思考。即使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也仅是有所提及而没有充分地正面挖掘,或者简单地将相关思考认定为对乌托邦的“欲望化”和“畸形的乌托邦伦理的滥用”,没有看到格非思考的复杂性,从而简单地认为格非“把乌托邦定位为一种缺乏必要历史内容支撑的、非理性的、虚妄的个人欲望盲目冲动的产物”,造成了“历史认知偏颇”和“文本审美价值”的损伤⑤。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简单地认为三部曲体现了格非对乌托邦的否定,从而将格非的思考与情感判定为“反乌托邦”“乌托邦的幻灭”“乌托邦的消解”“乌托邦的陆沉”,没有注意到其思想上、情感上的复杂性。
事实上,早在2004年 《人面桃花》出版后,格非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及对乌托邦的复杂态度:“最初的动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来我看法兰克福学派,莫尔的乌托邦,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蓝图,你只要想去做这个桃花源,可能会有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但现在这个社会又太功利了,必须要有反思,如果连梦想都没有了,其实也挺可怕。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最初的动机。”⑥可见,格非反思了乌托邦实践中的“强制、暴力和集权”等现象,并没有完全否定乌托邦的意义,而是肯定了乌托邦在这个“功利社会”中的精神价值。在三部曲中,虽然乌托邦实践大都以失败告终,但在那些乌托邦追求者身上,却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超越功利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灵魂出窍”的“欲望时代”,超越世俗的乌托邦情怀与理想主义精神不仅使《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王元庆、绿珠等人没有与世俯仰、随波逐流,而且还成为他们审视社会、反思人性、忧世伤生的精神立场所在。陈守仁、庞家玉等人在生命结束之时的幡然醒悟中,以诗歌为象征的超越精神,更是他们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这种种现象,昭示出“江南三部曲”乌托邦思考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正面剖析格非思考百年乌托邦的历史实践、知识分子理想与历史进程关系的丰富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些思考的时代性意义。
一、乌托邦理想与私人欲望的辩证
整体来看,乌托邦在“江南三部曲”中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呈现为“事功”的乌托邦社会实践,即清末民初的陆侃、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人面桃花》),新中国成立后的谭功达、郭从年(《山河入梦》),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元庆、绿珠(《春尽江南》)等人所追求的社会乌托邦实践。不论其具体的理想与最终的实践结果有着怎样的差异,他们都试图设计、确立一种“桃花源”式的生活形态与社会制度形态。另一种则是呈现为“精神”形态的乌托邦情怀与价值立场。这种乌托邦精神在那些执着追寻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身上强烈地体现出来。在三部曲中,尽管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等人从“事功”层面看都是失败者,其实践的具体构想、过程和手段也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从精神层面看,他们对现实的审视与不满,对社会理想、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与顽强坚守,却有着动人的一面。可以说,面对作为“事功”的乌托邦社会实践与作为“精神立场”的乌托邦情怀,格非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其反思的对象,后者则是其在“欲望时代”语境中所要打捞的“梦想”。
格非对作为“事功”的乌托邦实践的反思,紧紧地围绕着乌托邦实践与私人欲望的关系而展开,呈现为三种情形:
第一,私人欲望与乌托邦实践纠缠,最终成为乌托邦失败的根源。在《人面桃花》中,张季元的“蜩蛄会”、王观澄的花家舍、陆秀米的革命等乌托邦实践的失败,大都与私人欲望有关。张季元等人试图通过其触目惊心的革命纲领《十杀令》来实现其大同理想⑦。《十杀令》的残酷性首先会让人反思乌托邦实践中的暴力与不人道问题。然而,还应该考虑的是,既然曾经“只身怀揣匕首,千里走单骑,行刺那湖广巡抚”,其后又“从汉阳上船,亡命日本,一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几近于死”⑧的清末革命者张季元能够接受《十杀令》,其中必然有某种“革命的合理性”。陆秀米最初读到《十杀令》时,对何以要杀掉有恒产者百思不得其解。当她遭遇革命挫败、有家产者纷纷退出革命之时,她才理解了这一决定:对于革命而言,“有恒产者无恒心”。私人欲望恰恰是动摇革命的潜在因素。因此《十杀令》的部分条目是对财产、性欲等私人欲望的威慑和压抑。吊诡的是,即使革命者张季元自己也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沉溺于梅芸与陆秀米的情感欲望之中难以自拔。他所构想的革命后的婚姻形态里虽有婚姻自主的因素,但是一旦女方父母或女性自己不同意男性的追求,便以“杀掉”对方来解决问题。这无疑夹缠了太多暧昧情欲和男性霸权,背离了乌托邦作为人类生活理想的要求。
王观澄苦心建构的“家家户户的房舍都是一样”“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倒也其乐融融”的花家舍世界,最终因头领们的血腥火并而覆灭,根源也是头领们的权力欲望引发了利益矛盾。不仅如此,小说借尼姑韩六之口剖析王观澄的内心世界,指出他的花家舍理想本身便是一种“大执念”,“脱不了名、利二字”⑨。同样,陆秀米革命的失败,直接原因是龙庆棠变节投靠了清廷,但其革命队伍内部的“藏污纳垢”则是更为内在的原因。如果说倡导乌托邦的知识分子还有些许超越个体欲望的追求的话,普通百姓参加“革命”则更多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例如老虎对革命的认识是:“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⑩金大牙的革命观是:“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过些日子,等我们攻下梅城,杀了州府老爷之后,再接你老人家去衙门里去住。”⑪他们很少从理想的、超越性的角度来理解革命,而是仅仅将其视为满足个人物质利益、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从而使革命缺失了超越性的维度,异化为阿Q式的利益与权力的争夺。而且,即便是陆秀米本人的革命理想,也同样难以摆脱个体欲望的纠缠。从日本归来领导革命之后,陆秀米的性格发生了鲜明的变化。领导革命后的陆秀米看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高高在上的,连她母亲都说“她那双眼睛,不认得人”。陆秀米的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成长”,倒不如说是“革命”“赋魅”的结果。与张季元等人的 《十杀令》所体现出来的掌握他人生杀大权的情形相似,革命使得陆秀米产生了一种左右历史、“拯救”世人的救世意识与精英心态。她对这种救世心态的沉迷,与王观澄的“大执念”有着共同的心理根源。
《山河入梦》书写了谭功达主政的梅城县农民们不断抗拒合作化运动的情形⑫。这种情形,历史地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与农民们的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谭功达继承陆侃、王观澄、陆秀米等人的“桃花源”“大同世界”梦想而进行的修大坝、凿运河、通沼气等构想与实践,同样脱离了当时民众的实际需求,带来的只能是劳民伤财的结果。从而使他的乌托邦实践难脱“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的诟病⑬,并在权力倾轧中成为他的罪责——“导致梅城民穷财尽,路有饿殍,光是官塘一乡就饿死了六个人”,“把偌大的梅城县当成他个人的资产阶级桃花源,用十二万梅城人民的生命作抵押,来满足他资产阶级的虚荣心。”⑭因此,谭功达的失败,虽是白庭禹、钱大钧等“朋友”的权谋算计直接造成,但他的乌托邦理想根本不切合民众的实际需要,劳民伤财,失败也是必然的。
可以看出,倡导乌托邦实践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超越个人私欲的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他们都无法摆脱个人私欲的纠缠。这些私欲,有时是他们实践的动力,有时则成为解构其自身理想的潜在威胁——例如,张季元对陆秀米的情欲一度使他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并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你,革命何用?”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倡导者的私人欲望不受约束,极有可能将革命异化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最终会将社会乌托邦实践导向危险的境地;以各自的物质需求与权力欲望来理解、参与“革命”的民众,则是纠缠在乌托邦实践进程中更为强大的欲望力量。这些私人欲望,既是他们参与“革命”的动力,又会转化为退出、分裂革命的根源,成为乌托邦实践的最大威胁;被动承受社会乌托邦实践的民众,同样依据历史经验、物质利益的满足情况来作出选择和判断,缺乏知识者的超越性和理想情怀。因此,如何处理私人欲望,是社会乌托邦实践的成败关键。
第二,极端压抑人的情感欲望,导致乌托邦走向了人类理想生活的反面。如果说以上几种乌托邦实践都因私人欲望的渗透、纠缠而失败的话,那么《山河入梦》中郭从年的花家舍世界则恰恰相反,是以“最好的制度”压抑了人情、人性与人的欲望。他的乌托邦实践不仅开展了社会改造工程,试图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一种“完满”的制度形态,而且开展了人性改造工程。郭从年深深地知道欲望是乌托邦的潜在威胁,因此他“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⑮,通过无处不在的101监督组织、鼓励人们相互告密揭发的“铁匦制度”、严密的信件检查制度等手段,严格控制花家舍民众的欲望和思想。他以“最完美的制度”既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行动,使其不用任何命令便“自主”劳动,也有效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然而,这种泯灭人情、灭绝人性的生活,不可能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形态,同样走向了“乌托邦”的反面。花家舍表面上“秩序井然”,但花家舍人“都比较健忘。三天前的事情他们都完全有可能记不清了”,因此他们一年到头反复观看 《白毛女》,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他们整天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又心事满腹,闷闷不乐。因为他们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思考政治、道德、礼仪等种种方面的“界限”,思考“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⑯。在这样的制度中,活泼好动、“脸上永远带着孩子气的笑”的小韶竟然多次自杀未遂,从而被送进学习班接受“改造”,最终将被阉割为“一个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在恐怖的外在监督与内在自我规训中,花家舍人丧失了独立的精神主体。当谭功达得知小韶将被改造之时,感到“自己心里很深的地方,有一朵娇艳的什么花正在一点一点地枯萎”⑰。格非借小韶的遭际,揭开了花家舍制度阉割正常人性的残酷性,从而揭示了社会乌托邦实践与私人欲望的另一重关系:如果彻底灭绝了人的情感欲望,乌托邦实践同样会走向人类生活的反面。
第三,欲望泛滥而缺乏节制,乌托邦实践彻底受挫。《春尽江南》所描写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恰恰是与郭从年的花家舍世界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人的欲望缺乏必要的控制而走向了泛滥,一切社会乌托邦实践和理想主义情怀都受到了挑战。在小说中,一直坚持乌托邦实践的王元庆试图建设一个“花家舍公社”,却因其构想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遭受了合伙人张有德的黑手,被迫退出了花家舍项目。花家舍从此沦为一个权力与金钱角逐、道德与理想彻底沦丧的销金窟与“伊甸园”。王元庆用最后的资金建成了一所现代化精神病治疗中心,不料这医疗中心也在房地产潮流的冲击下,面临着被迫拆迁的局面。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乌托邦实践无法抵抗欲望潮流的席卷与冲击,最终走向了挫败。历史仿佛真如《山河入梦》中的郭从年所言,“人的欲望是不会有节制的。要么太少,要么太滥……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人的欲望“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法约束的”,人性欲望最终将导致“花家舍人民公社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⑱。从 《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到 《春尽江南》,社会乌托邦实践或者被物质欲望、权力欲望之争导向了血腥的屠戮,最终崩溃瓦解;或者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或者为了追求乌托邦的“纯洁性”而残酷地压抑、扼杀人的情感欲望,最终走向了乌托邦作为人类生活理想的反面;或者被世俗欲望异化为权力与金钱角逐、道德与理想沦丧的销金窟与“伊甸园”。成也欲望,败也欲望,格非显然是在“江南三部曲”中展开了乌托邦理想与私人欲望关系的辩证。
二、欲望时代与乌托邦实践的双向审视
欲望泛滥而缺乏节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恰恰是格非反思百年中国乌托邦实践的时代语境。因此,在反思乌托邦实践历史的同时,格非又不得不审视其身处的时代现实。正如他自己所言,反思乌托邦实践中的“问题”与审视这个“太功利”的时代,是其创作的两个主要动机⑲。这就使得“江南三部曲”呈现出双向审视的格局:一方面面向历史,审视百年中国的社会乌托邦实践,反思其带来的灾难与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则面向现实,审视当下时代的欲望失范。
首先,格非对百年中国社会乌托邦实践的反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反思乌托邦的思想潮流的延续。反思社会乌托邦实践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20世纪以来的重要思想潮流之一。特别是随着对20世纪人类社会灾难的反思,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以及乔治·奥威尔等人都对社会乌托邦工程进行了深入反思。计划机制导致社会乌托邦工程的物质匮乏与精神贫乏,使当今人们一谈起乌托邦,便将其与“压制性权力主义以及凶残的计划联系在一起”⑳。“理想国”“乌托邦社会工程”已然成为人们反思、警惕的对象。9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转型、历史反思以及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乔治·奥威尔、汉娜·阿伦特等人的著作的传播,“革命不如改良”、“告别革命”、反思“理想社会”、反思社会乌托邦工程同样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思想潮流。
乌托邦产生的最终根源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匮乏与缺陷。正是由于现实的匮乏与缺陷,人们才试图寻求、建构更美好、更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只要现实社会生活的匮乏依旧存在,对乌托邦的追求就不会终结。正是因为乌托邦代表了人类超越现实的理想与希望,拉塞尔·雅各比才立意要在批判乌托邦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今天“拯救乌托邦本身”。当然,这种“拯救”并不是重新肯定人类无视理性的局限而详尽地规划社会进程、安排人们的日常事务、调节全部的社会生活等做法,而是对乌托邦施以“解剖刀”,将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区分为“蓝图传统”与“反偶像崇拜”。前者“精确地规划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规定“乌托邦的居民应该什么时候醒来,他们该穿什么,午饭应该吃多长时间”,具有反自由的权力主义倾向㉑;后者则在理智上不墨守成规,拒绝将未来具象化㉒。通过切割掉乌托邦的“蓝图传统”这一恶性肿瘤的方式,雅各比重新肯定了乌托邦的意义。其他反思社会乌托邦工程的思想家同样没有否定乌托邦本身:卡尔·波普尔反对“乌托邦社会工程”,却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李泽厚、刘再复则在提出“告别革命”的同时,强调“放弃理想社会,却不能放弃社会理想,有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各种各样的社会理想,我们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大同也好、小康也好、桃花源也好、大观园也好,总的有个理想才好,人活着,总得寻找点意义,才有所追求”㉓。
这些思考,一方面提醒人类必须警惕为了实现乌托邦而出现的人类理性与权力的僭越,警惕那些轻视世俗生活的所谓“理想社会”“理想国”之类的乌托邦“蓝图”。另一方面,警惕“理想社会”又并不等于要完全放弃社会理想与社会改革。从根本上说,追求社会理想的初衷必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世俗生活。顺应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情感欲望,无疑是社会乌托邦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因此,雅各比将“对奢华和肉欲的渴望”视为他所肯定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的最大特征㉔。然而,基于对人性中幽暗部分的警惕,不论是社会理想的倡导者、实践者还是承受者,都应该意识到社会理想的实践隶属于社会公共领域,应该避免私人欲望对公共事业、公共领域的干预和绑架。
其次,基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格非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整体诊断为“欲望时代”,并在《春尽江南》中对这个时代“症状”进行了剖析和呈现。从社会层面上看,欲望失范导致了社会乱象频出:小说丰富地纪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暴力拆迁、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畸形教育、法治尴尬等“时代怪现状”;从精神层面上看,欲望失范导致了人的精神无着与“灵魂出窍”: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是格非对时代精神症状极为准确的诊断与概括。在这个时代,为了最大化地满足个人欲望,每个人都想不择手段地去“淘汰所有的人”。商业上,张有德淘汰王元庆、陈守仁征用春晖纺织厂的土地是如此;生活上,春霞霸占谭端午的房子也是如此。甚至连杀人犯吴宝强都要“利益最大化”,“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在这样的“恶性竞争”中,伦理道德的底线不断地遭遇挑战,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人”㉕:他们“没有过去,也谈不上未来。朝不及夕,相时射利。这种人格,发展到最高境界,甚至会在毫不利己前提下,干出专门害人的勾当。对于这样的‘新人’来说,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㉖
不仅如此,这种“恶性竞争”还渗透到了教育事业中,使得教育“异化”为培养这种“新人”的工程。在家庭教育中,庞家玉一直给自己的孩子若若灌输“一步都不能落下”、“要是打个盹儿,伸个懒腰,别人就把他超过去了”等竞争意识。更可怕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是家长们争面子的重要砝码——每当自己的孩子考出好成绩之后,庞家玉、胡依薇都会给对方打电话,刺激对方;而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对方的刺激则使得她们对孩子越发歇斯底里:庞家玉对若若从责怪、怒骂升级为拍着桌子的失去理智的狂叫,胡依薇则竟然拿毛衣针扎女儿戴思齐的脸。恶性竞争已然使得家庭教育失却了人性内涵。而在学校教育中,学校不仅毫不考虑给学生心灵所带来的影响,而是功利主义地邀请家长中的“成功人士”来演讲。更可怕的是,若若的班主任鲍老师居然建议用对付驴拉磨的手段来对付孩子的学习……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作用之下,若若对同学戴思齐生病住院不仅毫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她呀!狗屁了,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了。”㉗甚至希望她永远不要出院。在若若这里,戴思齐只是必须被“淘汰”掉的“竞争对手”,既无同学的情谊,更无同情怜悯之心。可见,在《春尽江南》中,格非借若若的教育历程揭示了为“恶性竞争”所异化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将若若这一代人培养成为缺乏同情心的“灵魂出窍”的“新人”的残酷历程。面对这样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欲望时代,“知识分子何为”成为格非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于是,他试图在这个“功利”时代,重新打捞乌托邦“梦想”。
三、乌托邦精神的人文情怀
乌托邦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除了为社会发展提供改革的愿望和动力外,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精神作用:“它以一个虚构的完美世界映照出现实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保持一种精神的自由,以超越现实而不是臣服于现实的姿态来宣示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乌托邦精神世界的塌陷意味着人的物化,所以乌托邦作为一种人之为人的人的自由本性的证明,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㉘乌托邦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在别处”的理想主义精神、超越性维度、疏离并审视现实的精神立场,有着可贵的人文价值。如果缺失了这种乌托邦精神,缺失了对现实的反思、洞照与批判,我们只能沉溺于社会现状与世俗欲望之中,成为雅各比所批判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种在精神向度与价值立场上审视现实的乌托邦精神,恰恰是“江南三部曲”所要展现的另一种乌托邦形态。
从“事功”层面上看,“江南三部曲”中的陆侃、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无疑都是“失败者”。他们的乌托邦“事功”实践也正是格非立意要反思的对象。然而,从精神层面来看,这些人物对现实的审视与不满,对社会理想、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与顽强坚守,却具有动人的一面。在这些执着追寻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身上,强烈地体现出一种不满于“有缺陷的现在”的理想主义精神、超越并审视现实的批判立场。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无疑是《春尽江南》中的“失败者”谭端午形象。在“事功”方面,不论他那种对任何事情都习惯性地持“不妨试试”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还是将唐宁湾房子的证件丢在中介公司等行为,都可看出他与时代的疏离、行动的孱弱。然而,他却能够在时代的冷落、庞家玉的数落嘲讽中接受自己的失败,甚至“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为自己“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感到“庆幸”,从而表现出对这个时代自觉的疏离态度。也正是在与时代的自觉疏离中,谭端午与现实保持着清醒的审视、批判的关系,不断思考着时代问题的症结。甚至可以说,谭端午的自觉疏离,是一种对时代的自觉抵抗:“今天这个时代,老成、狡诈,我们不可能轻易驾驭它,对个体来讲,今天是个强大得多的对手。从这个角度来讲,端午要面对的挑战肯定比秀米和谭功达更孤绝。正因如此,他的坚持才更有价值。”㉙谭端午自居于时代的“边缘”,成为了自我的反省者、历史的反思者与时代的批判者。在他身上,乌托邦已经不再是作为“事功”的具体社会实践,而是转化为一种精神持守和价值立场,成为一种烛照社会人心的精神尺度和忧世伤生的情怀。
已有的评论在评价谭端午的这种退守内心的选择时,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例如,南帆质疑了谭端午退守内心的选择,认为没有公共领域的清平,“一己的私密情感”也实是难以持守,正是由于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等知识分子被迫由公共领域退守到私人空间,最终导致“一己的私密空间再度失守”㉚。洪治纲则从谭端午身上看到了“支撑着人物的心灵世界,并与现实构成了尖锐的对峙”的“某种乌托邦精神”,认为《春尽江南》恰恰是在“凭吊那些人类曾经念念不忘的乌托邦情怀”㉛。而格非自己也有意要肯定谭端午的这种选择:“我觉得在当今社会当中,一个个体要能接受失败、接受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整个社会已经停不下来,在发展主义关于成功的道路上已跑得太快了,停不下来的话就不会有自我意识的反省,就不会对自己的生活、生命进行反观,这在中国是最可怕的。”㉜
从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担当与公共情怀来看,谭端午的这种选择自有其不足。因为,私人的操守不能弥补公共情怀的缺失,精神向度的忧世伤生也无法取代具体的社会改革实践。不过,也应该看到,谭端午的人生选择是他反思自我、反思时代的结果。谭端午也曾汲汲于社会乌托邦实践,参与过“席卷全国的大事”。失败之后,他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正是在自我放逐的时候,他与李秀蓉发生了关系,写下了那首残诗《祭台上的月亮》。后来,谭端午将这首残诗续写成一首完整的《睡莲》。稍加对比就可发现,两首诗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有着不小的差异,分别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精神立场。在 《祭台上的月亮》中,“广场的飓风”与“青萍之末的祭台”、“花萼”与“肮脏的亵衣”相并置,意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揭示了理想与现实所形成的强烈的反讽关系,表达了谭端午对历史与自我的强烈嘲弄,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放逐”情绪。而 《睡莲》则强化了“月光”这一超越性意象:“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广场的飓风”也罢,“祭台”“浮云”“亵衣”也罢,由“月光”这一超越性的视角看去,便有了审视的距离。“月光”的尺度,也正是理想的尺度。尽管“溃散”与失败一直纠缠着,但乌托邦理想已经转化为一种超越性的、审视性的精神立场,没有因时间的流逝、时代的改变而消泯。20世纪80年代“诗人”所具有的“祭司”地位,给谭端午“不断地更换女友”带来了不小的方便,并残酷地将19岁的李秀蓉当作了“可以直接享用的供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诗人的地位迅速地由时代的“祭司”变成了“边缘人”与“失败者”。谭端午开始从“牺牲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知识分子不再是倡导社会乌托邦工程的精英与领袖,而是成了居于社会边缘的审视者与批判者。不仅如此,谭端午开始警惕知识分子对时代发言时的那种精英意识与故作姿态㉝。可见,谭端午由事功追求到精神立场的选择,从时代“祭司”的精英身份到边缘人、疏离者的转变,体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在历史反省与时代转型中的思想调整与身份调整。暂且不论这种调整是被动还是主动、知识分子从“祭司”到“边缘人”的变化存在哪些得失、谭端午的这种选择是否是一种“退守”,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种乌托邦精神坚守所发挥的审视、批判社会人心的价值功能,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春尽江南》中,王元庆的那些可以作为时代生活“标题”的“疯话”、绿珠对社会人心的批判性反思,同样体现了超越时代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乌托邦精神。在小说中,“既是对现实的回应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性的象征”的诗歌㉞,无疑是这种乌托邦精神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在征地上不择手段、施心用狠的陈守仁,临死时念念不忘的居然是自己偷偷写下的诗歌;在事业上同样不择手段、甚至出卖肉体的庞家玉,离家出走时带走的恰恰有《海子诗选》。不论他们的反省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一旦开始审视自己,他们都产生了精神救赎的渴望。而作为乌托邦精神的象征的诗歌,恰恰成了他们自我心灵救赎的重要途径。也许,以诗歌为象征的乌托邦精神,是格非为这个“灵魂出窍的时代”所开具的精神药方。
总之,“江南三部曲”对乌托邦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小说在乌托邦构想本身的不健全、乌托邦实践主体(包括倡导乌托邦实践的知识分子、参与乌托邦实践的民众、承受乌托邦实践结果的人民)的复杂性、乌托邦实践的暴力手段等方面的反思,都可以引申出重要的历史话题与思想话题。不过,在申说这些命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江南三部曲”对乌托邦与欲望关系的辩证思考,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江南三部曲”正是在对乌托邦与欲望的双向审视中,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格非的反思,重申了乌托邦应该顺应人类物质需求与情感欲望、满足人类世俗生活的初衷;并在对“欲望时代”的批判性审视中,重新打捞乌托邦的人文精神价值,以期为这个“太功利”的时代提供救赎的精神资源。
注释:
①[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92页。
② 张清华:《〈山河入梦〉与格非的近年创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③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 〈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④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⑤姚晓雷:《误历史乎?误文学乎?——格非〈人面桃花〉等三部曲中乌托邦之殇》,《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⑥⑲吴虹飞、格非:《告诉你们一个写作的秘诀》,《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1期。
⑦⑧⑨⑩⑪格非:《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17、129、155、189页。
⑫⑬⑭⑮⑯⑰⑱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89、86、229、334、330、329、333页。
⑳㉑㉒㉔[美]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9、9页。
㉓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1页。
㉕此处的“新人”,事实上是格非对“灵魂出窍”、底线沦丧的一些人的“分类”和命名。参见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
㉖㉗㉝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335、322页。
㉘耿传明:《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㉙丁杨、格非:《愿读者在小说中找到自己》,《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
㉚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篇三部曲 〈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㉛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㉜㉞格非、木叶:《衰世之书——格非访谈》,《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