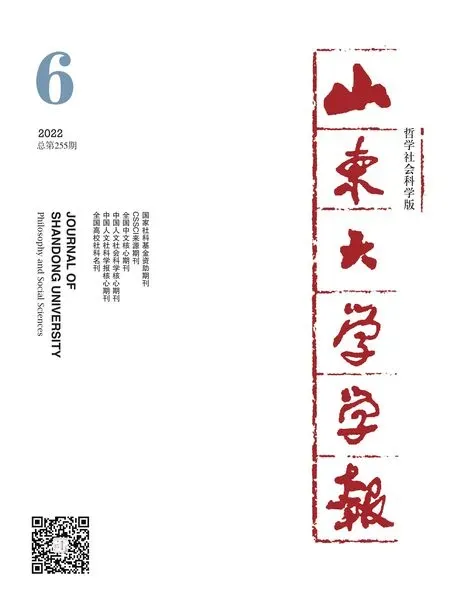论担保从属性的类型及其突破
李运杨
一、引言
从属性是担保法教义学中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1)在概念使用上,有人区分从属性与附随性,认为从属性一般针对保证,附随性一般针对担保物权。参见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第四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第41页。本文认为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不大,因为从属性与附随性均来源于德语中Akzessorietät一词的翻译,故本文统一使用“从属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在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之间建立单方依赖关系的法定机制(2)李运杨:《担保从属性:本质、功能及发展》,《澳门法学》(澳门)2020年第2期。。从属性好比一条连通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的管道,将所担保债权身上发生的各种变化单向地传输到担保权身上,使二者时刻保持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我国担保制度中规定的保证、抵押权、质权及留置权等典型担保权均为从属性担保权,而且从《担保法》到《物权法》再到《民法典》及《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担保从属性的程度呈现强化之势。但是,现代担保制度的发展趋势已经表明,从属性并非担保权的固有属性,独立性担保的存在本身就能说明该问题;而且,即使是具有从属性的担保权,也并非在各个方面均完全地依赖于所担保债权。因此,在我国担保制度强化从属性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之间的关系。
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涉及权利的产生、存续等多个方面,由此产生了从属性的不同类型。关于从属性的类型,存在不同学说。我国台湾地区一般将担保权的从属性具体化为三种类型,即成立从属性、移转从属性和消灭从属性(3)郑玉波:《论抵押权与其所担保之债权之关系》,《民商法问题研究》(二),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107页以下;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我国大陆多数学者也认为担保权的从属性具体化为三种类型,即设立(发生或存在)从属性、移转(处分)从属性和消灭从属性(4)高圣平:《担保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孙鹏、王勤劳、范雪飞:《担保物权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由于“三分说”不能涵盖担保权在范围与抗辩方面对主债权的依赖性,于是便出现了“四分说”,将担保权的从属性具体化为成立从属性、内容从属性、移转从属性和消灭从属性(5)程啸:《担保物权研究》(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页以下。。该说将范围和抗辩上的从属性合并为内容从属性,但范围从属性与抗辩从属性分别侧重担保权的效力范围和担保权的抗辩权,各有倚重,分开为宜。另外,我国还有观点将效力从属性作为从属性的一个类型(6)高圣平:《民法典担保从属性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法学》2020年第7期。,该观点是以担保合同的从属性为逻辑起点。由于本文认为担保从属性应该是指担保权的从属性,与担保合同无关(7)李运杨:《担保合同的从属性抑或担保物权的从属性?——以区分原则为视角》,《中德私法研究》2020年第19卷。,故不宜存在效力从属性,所谓效力从属性的内容应纳入消灭从属性的范畴。为科学、全面地展示担保从属性的内容,本文赞成“五分说”(8)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7—762页。,将从属性具体化为五种类型,分别是设立从属性、处分从属性、范围从属性、抗辩从属性以及消灭从属性。
与从属性的类型划分相比,从属性的突破对准确理解与适用从属性更为关键。这是因为担保从属性不是一个僵化的教义,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原则,其在绑定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的同时还应设置多种突破。这就要求从属性的法律适用不仅需要考虑自治与管制的关系,还要考虑不同担保类型的差异,比如自己担保与他人担保的差异、人保与物保的差异、登记型担保物权与占有型担保物权的差异等,所以不存在统一适用的从属性,只存在程度不同的、分别适用于不同侧面的从属性。从属性涉及物权法与债权法的衔接以及不同主体利益的平衡,可以说,如何科学适用从属性是一个极具理论性与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现行法对担保从属性的相关立法表达存在诸多不足,有关担保从属性的规定不仅散见于不同的章节,呈现碎片化的状态,而且对从属性的突破规范不足。为此,本文将采用类型化的方法系统论述担保从属性的五种类型,并分析每种类型应设置何种突破,以期全景式地呈现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的关系。
二、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在设立上的关系
(一)设立从属性
设立从属性是指,担保权的有效设立以所担保债权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债权不成立,担保权也不能有效设立。设立从属性将担保权的设立与所担保债权的成立绑在一起,在所担保债权成立之前,不发生担保权设立的法效果,在作用方式上类似于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比如,当事人将债权的产生设置为保证合同生效或担保物权设立行为生效的延缓条件,在条件成就前,保证债权或担保物权不设立,唯在条件成就后,才能发生保证债权或担保物权设立的法效果。
设立从属性在我国法中有明文规定。对于人的担保,《民法典》第681条规定保证合同的目的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体现了保证担保的设立从属性。就物的担保而言,设立从属性事关担保物权的存在目的或立法的价值取向。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担保物权的立法存在两种价值取向,分别是以保全债权为立法重心和以投资为立法重心(9)陈本寒:《担保物权法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从属性框架下的担保物权原则上是债权保全型担保物权。我国《民法典》第387条第1款中的“为保障实现其债权”即是关于担保物权设立从属性的一般性规定(10)刘保玉:《第三人担保的共通规则梳理与立法规定的完善》,《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另外,《民法典》第394条、第425条中的“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以及第447条中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也分别表明我国抵押权、质权以及留置权的设立目的均为保全债权。
(二)设立从属性的突破
现代担保制度已经允许为设立从属性设置例外,该例外体现在可为将来债权设立担保。所谓将来债权是指,能成立但目前欠缺构成要件尚未成立之债权。比如,在借款尚未发放之前,被担保的借款返还债权就是一个将来债权。已经成立但附有抗辩权的债权虽然当前无法实现,但不应作为将来债权,因为它所有的成立要件已经满足(11)Eichel, Künftige Forderunge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32.。法律允许为将来债权设立担保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因为实践中的债权人在答应提供信贷之前,往往需要把担保先确定下来。所以,为设立从属性设置例外,根本原因是为了满足交易实践的需求。对于将来债权,只需债权的成立原因具有可确定性即可,债权额度的可确定性不是必要的。另外,附生效条件和期限的债权也属于广义上的将来债权(12)Eichel, Künftige Forderunge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S. 33.,在此应同样对待。
可为将来债权设立担保在我国法上具体有两个体现。首先,可为将来债权设立最高额担保。《民法典》第420条、第439条及第690条分别承认了最高额抵押、最高额质押及最高额保证。在设立最高额担保时,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额虽已确定,但具体的所担保债权还未产生。当事人通过约定,可以为将来不特定之债权预先设立最高额担保权,这突破了担保权设立上的从属性(13)崔建远:《最高额抵押权的争议问题及其解决》,《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最高额抵押权中部分具体主债权不成立,不影响整个抵押权的存在,该规则应同样适用于最高额质押与最高额保证。
其次,不仅可为将来债权设立最高额担保,为鼓励担保交易,还可以设立一般担保。对此,我国制定法虽无明文,但《民法典》第387条第2款、第689条规定了反担保制度,第三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被担保债权是第三担保人向主债务人的追偿权,在第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之前,该追偿权就是一个将来债权。债务人提供的反担保不限于最高额担保,也包括一般担保,所以,反担保制度的承认本身就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可为将来债权设立一般担保的典型体现。另外,为将来债权设立一般担保也已获得我国判例认可(14)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四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无论是最高额担保,还是一般担保,它们的设立从属性都应被缓和,究其原因,它们都是意定担保,而意定担保的目的是为信用授予关系提供媒介,故应宽松认定它们的从属性(15)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申政武、封涛、郑芙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14页。。可为将来债权设立意定担保权在比较法上也能找到立法例的支持,如《德国民法典》第765条第2款、第1113条第2款、第1204条第2款分别规定可为将来债权设立保证、抵押权和质权。当然,如果所担保债权无从特定或无发生可能性时,对质权而言,即使有质物的交付,质权亦未有效设立,质押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对抵押权而言,纵有抵押权登记,该抵押权亦属无效,抵押人可根据所有权妨害除去请求权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16)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册),修订五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6页。。
作为我国法中的法定担保物权,留置权在设立从属性上要求则很严苛,只能在现存债权上产生留置权,不允许在将来债权上存在留置权(17)高圣平:《担保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而且,留置权的成立以债权已届清偿期且未受清偿为要件。一旦留置权产生后,当事人约定延缓债权的清偿期,此时只阻止留置权的实现,不能导致已成立留置权的消灭(18)董学立:《论留置权的特殊消灭原因》,《法学论坛》2004年第3期。,因为此时的债权既非将来债权,也并未消灭,只是延长了履行期限而已,仍有担保之需求。在此应指出的是,虽然意定担保权设立时的从属性被缓和,但在担保权实现时须以被担保债权的存在并且数额确定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设立从属性的突破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推迟了对担保权从属性的要求。
三、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在处分上的关系
(一)处分从属性
处分从属性是指,担保权人对债权所为之处分及于债权上的担保权,担保权人不得单独处分担保权。债权之处分一般可分为债权之让与和债权之出质,这两种情形均可触发处分从属性的适用。
根据处分从属性,当债权之上设立质权时,该债权质权的效力也应及于担保权,即债权连同所附担保权一并成为质押的标的。从表面上看,这会形成一种有趣的“担保权上的担保权”现象。其实,这里担保权上的质押应被理解为担保权的移转,即质权人在获得债权质权的同时额外获得另外一个担保权。比如,为担保某一债务,债权人以其附有抵押担保的应收账款为他人设立质权后,质权人不仅获得一个质权,抵押权也一并移转给质权人,只不过在实现时存在先后顺序而已。当出现质权的实现事由后,质权人首先应实现应收账款质权,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向其履行,在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履行时,始得以抵押权人的身份实现抵押权。
当债权被让与时,担保权一并移转,此时又可称为移转从属性。由于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就移转从属性有所论述(19)李运杨:《担保的移转从属性及其例外——以中德比较为视角》,《中国海商法研究》2020年第2期。,本文此处仅作一补充。移转从属性不仅适用于意定债权让与(《民法典》第547条、第407条),也适用于法定债权让与。对于法定债权让与场景下的移转从属性,我国制定法中虽尚无明文,但在解释上可类推适用第547条,将法定债权让与纳入“债权人转让债权”之中。
《民法典》规定的法定债权让与情形有第三人代为清偿后的债权移转(第524条第2款)、连带债务人清偿债务后的债权移转(第519条第2款)。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债权作为一种遗产移转到继承人处,也是一种法定的债权让与(第1122条)。第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是否发生法定债权让与的效果,《民法典》虽缺少明确规定,但本文认为,第三担保人通过主动行使清偿权的方式清偿债权人与通过被动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使债权人受偿应受到同样对待。若否定第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的法定债权让与,第三担保人仍可通过行使清偿权的方式实现法定债权让与的效果。因为,对保证人或提供物保的第三人而言,若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他们的财产就会面临被强制执行的风险,故他们属于对债务的履行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
(二)处分从属性的突破
处分从属性的突破是指,当事人对主债权债务的处分并不必然及于担保权,其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债权人可仅以其债权为他人设立质权,而自己保留担保权(2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册),第638页。。此时,成为质权客体的债权是一个无担保债权,但对债权人而言,该债权仍是一个有担保债权,自己保留的担保权不会因缺少所担保债权而消灭,因为债权人虽以其债权出质,但其债权人身份未变。需说明的是,就债权的出质而言,此处构成处分从属性的约定突破,但就债权的让与而言,此处不构成处分从属性的突破,因为债权未让与,担保权自然保留在原地。
第二,债权人让与债权时,担保权可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不一并让与。对此,《民法典》第407条第2句虽然只针对抵押权作了规定,但其所确立的规则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担保权,包括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也包括自己担保与他人担保。法律规定的担保权不一并随主债权让与的情形是指,在最高额担保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担保权不得转让。对此,《民法典》第421条针对于最高额抵押权确立的规则也适用于其他最高额担保。当事人约定的排除移转从属性的情形主要有两种。第一,在转让部分债权时,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只转让债权而不转让担保该债权的担保权。第二,在第三人提供担保时,担保人与债权人约定,担保人仅为特定债权人设定担保或禁止被担保债权转让的,当被担保债权未经担保人同意被转让的,担保权并不一并移转。《民法典》第696条第2款规定的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禁转约定在本质上就是保证担保中当事人对移转从属性的约定排除。该规则应是所有第三人担保的共通规则,但《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0条并未将该款确立的规则上升为第三人提供担保时的一般规则,值得商榷。
第三,除了债权让与会涉及移转从属性及其突破,免责的债务承担亦然。这是因为,担保的从属性一般被描述为“担保权从属于主债权”,但从债务的视角亦可将其称为“担保债务从属于主债务”(21)高圣平:《民法典担保从属性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法学》2020年第7期。。在债务人自己提供担保时,若主债务发生移转,根据移转从属性,担保债务原则上应继续担保新债务人的债务,除非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再为发生移转的债务提供担保,而且债权人对此表示同意。但在第三人提供担保时,若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由于新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可能不如原债务人,故为保护第三担保人利益,此时宜突破移转从属性,即担保债务原则上不一并移转,而是归于消灭,除非第三担保人同意继续为新债务人提供担保。《民法典》第697条第1款、第391条分别规定,在保证担保与第三人提供物保时,若未经担保人同意发生债务承担,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其背后的原理就是移转从属性的法定突破,殊值肯定。
四、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在范围上的关系
(一)范围从属性
范围从属性涉及担保权的担保范围与所担保债权的数额之关系,一个与范围从属性相关的前置性问题是,所担保之债权有无种类上的限制?虽然担保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变价权,但《民法典》第681条、第386条在对保证与担保物权下定义时使用的是“到期债务”,而非“到期金钱债务”,也就是说,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产生的任意一个有担保需求的债权都可以作为被担保债权,不限于金钱债权。只要所担保债权能够转化为金钱债权即可,比如所担保债权可以因为债务不履行转化为以金钱支付为内容的损害赔偿之债。因此,以行为为给付标的的债权也可以作为被担保债权(22)高圣平:《物权法担保物权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而且,即使未转化成金钱债权,担保物权的实行方法也不以拍卖为限,比如,债务人之债务为交付房屋,如债务不履行,可以采用代物清偿的方式实现抵押权(23)郑玉波:《论抵押权与其所担保之债权之关系》,《民商法问题研究》(二),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第110页。。其实,早在罗马法时期,质权的担保对象既可以是金钱债权,也可以是其金钱价值确定了的其他给付(24)Kaser/Knütel, Römisches Privatrecht, 20.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4§31 Rn. 21.。因此,担保从属性并不限于对金钱债权的从属性。
范围从属性是指,担保权的担保范围原则上由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决定(25)Vgl. Medicus, Die Akzessorietät im Zivilrecht, JuS 1971,497, 499.。此处担保权的担保范围,又被称为担保权的效力范围(26)郭明瑞、房绍坤、张平华:《担保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是指担保权人就担保物之变价得优先受偿的范围(物的担保)或得就保证人之责任财产受偿之范围(人的担保)。此处被担保债权的数额,是指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目前对于“主债权”一词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指与担保权相对而称的全部被担保债权,内容上包括主债权(即原本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另一种是指与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从债权相对而称的原本债权(27)高圣平:《民法典担保从属性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法学》2020年第7期。。由于立法者多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主债权”(28)《民法典》第389条、第393条、第416条、第419条、第442条、第684条、第691条,这些法条中的“主债权”均宜被理解为与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并列的主债权。,故本文从之。与此相应,“从债权”系指主债权之外的其他债权,至于哪些从债权应当纳入担保权的担保范围,则属于范围从属性的突破问题。
担保权的担保范围与被担保债权的数额本是担保合同中两个不同的事项,但借助于范围从属性,二者之间得以建立起单方依赖关系。比如,在分期付款中,所担保债权因部分清偿而部分消灭,担保权自动部分消灭;若是抵押担保,抵押人可以请求就消灭部分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即使未办理此项变更登记,抵押权的效力亦当然地缩减至该余存债权范围(2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册),第641页。。但有种观点基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认为,主债权与抵押权之间并无量上的对应关系,主债权虽因部分清偿等原因而部分消灭时,抵押权不能相应地部分消灭(30)郭明瑞、房绍坤、张平华:《担保法》(第五版),第115页。。这种观点未能注意到担保物权的范围从属性与不可分性之间的区别。不可分性是担保物权的行使问题,在所担保债权未全部清偿前,得对担保物之全部行使担保物权,而范围从属性涉及的是优先受偿的范围问题。抵押权部分消灭,不影响抵押权行使的不可分性(31)高圣平:《动产抵押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4年,第5页。,抵押物之全部仍须担保余存债权。在所担保债权的一部分因清偿、抵销、混同等原因消灭时,担保权人虽仍得就整个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但其效力范围仅限于未清偿部分。
范围从属性旨在使债权人从担保人处获得的给付恰好等同于所担保主债权的数额,不多也不少,既保护了担保人利益,也实现了担保目的。但是,当事人往往会在设立担保权时对担保范围作出特别约定,或在设立担保权后对所担保主债权的数额作出变更,此外,担保权设立后在主债权之外还会出现一些从债权。当出现这些情况时,为了保护担保人或实现担保目的,有必要突破范围从属性。
(二)范围从属性的突破
第一,在担保权设立时,担保人可以与债权人约定只担保部分主债权,以突破范围从属性。比如主债权的数额是100万,当事人约定只担保其中的80万。但是,当事人在担保权设立时不可约定超额担保。比如主债权实际数额为100万,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却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是150万,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主债权为150万的抵押权不应予以登记(32)石晨谊:《不动产登记中抵押权的从属性原理及应用》,《不动产登记》2017年第34期。。信贷实践中,债权人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有时会就保证债务本身约定违约金,该类约定虽然会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但该加重部分源于自身债务的违反,不涉及所担保的主债权,因而与范围从属性无关,不属于超额担保。基于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此类约定原则上应属有效。
第二,担保权设立后,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增加所担保主债权的数额时也会存在突破范围从属性的问题。担保权的效力范围是否随着主债权数额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应视债务人和担保人是否同一及担保权的种类而定。若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应突破范围从属性,担保权的效力范围不得相应增加,旨在保护担保权设立时担保人的预期(33)Vgl. NK-BGB/Bülow,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2016,§1210 Rn. 16.。若是债务人本人提供的担保,此时应区分担保物权的类型,分别判断是否突破范围从属性。若为登记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权,由于担保范围存在登记公示及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仅有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增加债权数额的约定不能扩大抵押权的担保范围。抵押权的担保范围不得随意增加也符合抵押权的特定性。抵押权的特定性是指除了要求抵押物须特定外,还要求所担保债权亦必须特定,即债权数额非在登记簿上登记不可,抵押人只在确定金额之范围内予以担保(34)刘得宽:《抵押权之附从性和特定性》,《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若为占有型担保物权,如动产质权与留置权,由于不存在担保范围的公示问题,当事人的意思在确定其担保范围时就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当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增加债权数额,担保权的担保范围也可相应地增加。总之,为了保护第三担保人的利益或潜在第三人的信赖,在所担保主债权增加时,应突破范围从属性,担保权的担保范围并不当然由所担保主债权的数额所决定。
第三,在所担保主债权数额恒定的情况下,亦有可能将主债权之外的特定从债权纳入担保范围,以突破范围从属性。在哪些从债权可纳入担保范围问题上,应首先区分具体从债权的类型。主债权的法定利息具有法定性,任何人都能预见到;实现担保权的费用是担保权实现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费用,也能够被任何人预见到。为充分实现担保目的,此类能够被第三人预见到的从债权可当然地纳入到任何类型担保权的担保范围,无须当事人的事先约定或额外登记。但约定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或实现债权的费用能否纳入担保范围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担保权的类型。
对于登记型的担保权,比如抵押权,由于存在担保范围的公示及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所以在确定担保范围时应格外慎重。由于多重抵押的广泛存在,抵押权的担保范围问题不仅涉及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利益,还涉及后顺位抵押权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因此是一个三人关系问题。约定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于第三人难以预见到,无法当然地纳入担保范围。对此类从债权,惟在当事人约定将其纳入担保范围且予以明确登记的情况下才可纳入。换言之,此种范围从属性的突破同时需要当事人的“合意”与“登记”。仅凭当事人的约定无法将此类费用纳入抵押权的担保范围,这是因为,从根本上看,担保物权的“公示”才是担保物权优先受偿效力的来源,当事人对担保范围的约定,仅产生债权法上的效果,不会产生物权法上的效果(35)邹海林:《论〈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担保物权”的制度完善——以〈民法典各分篇(草案)〉第一编物权为分析对象》,《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对于实现权利过程中所产生的律师费是否属于抵押权的担保范围,要看该律师费是指向哪种权利。若该律师费是指向抵押权的,则当然属于;但若是指向债权的,则否(36)Vgl. NK-BGB/Zimmer,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2016,§1118 Rn. 4.。当事人欲将后者纳入抵押权的担保范围,须事先就此达成合意并办理登记。
抵押权的担保范围应与抵押权的登记相关联,这在德国法上体现的相当明显。在法定的从给付之外(《德国民法典》第1118条),《德国民法典》在第1115条中还规定了意定的从给付也可纳入抵押权的担保范围。该条的标题是“抵押权的登记”,言外之意是意定从给付要想纳入抵押权的担保范围,必须登记。该条第1款第1半句规定:“在抵押权登记时,登记簿上应登记债权人、债权的数额,如果债权计息的话,还应登记利息,如果还有其他从给付须缴纳,这些从给付的数额也应登记。”该条中所称的利息仅指约定利息,因为法定利息属于法定的从给付,已经规定在了第1118条中,不具有登记能力(37)Jauernig/Berger, 15.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4§1115 Rn. 5.。由于抵押权巨大的经济意义,权利的核心内容应当直接从登记簿上就能清晰可见,而不能为了确定权利的内容追溯当初的原因行为(38)NK-BGB/Zimmer,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2016,§1115 Rn. 1.。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抵押物上的负担额度从登记簿上就能得以判断(39)Jauernig/Berger, 15.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4,§1115 Rn. 1.。可见,如果当事人仅约定了利息或其它从给付,但未在登记簿上加以登记,那么这些意定从给付不可能纳入抵押权的担保范围。
对于非登记型担保权,比如动产质权,虽然存在担保权设立的公示,但不存在担保范围的公示,所以在放宽担保范围的问题上不涉及第三人的信赖保护。在动产质权中,由于质物已移转占有,同一质物成立多个质权,或由第三人取得质物之情形,在社会交易上究属少见,故放宽质权担保之债权范围,应无损害第三人之虞(4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0页。。因此,质权设立后,质物应对所担保债权的每种发展状态负担保责任。与登记型担保权不同,在认定动产质权的担保范围时不再区分约定利息与法定利息,两者均可纳入担保范围;而且当出现违约时,担保范围亦包括违约金。此外,替代原给付请求权的损害赔偿也属于质权的担保范围(41)Vgl. Palandt/Bassenge, 76.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7,§1210 Rn. 1.。质权人的花费也要纳入担保范围,其中包括保管质物的费用、诉讼费用。与抵押权不同,此处的诉讼费用不仅包括基于物权而向质押人提起的诉讼,还包括要求债务人本人履行债务的诉讼(42)NK-BGB/Bülow,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2016,§1210 Rn. 21.。除了合同利息外,质权的担保范围还包括迟延利息(43)NK-BGB/Bülow, 4. Aufl., Baden-Baden: Nomos 2016,§1210 Rn. 8.。当然,当事人若有相反约定,可以将这些费用排除在担保范围之外。质权担保范围的认定规则对留置权和保证应同样适用。
总之,为了充分实现担保目的,有必要突破范围从属性,将主债权之外的一些从债权纳入担保范围,但是应基于担保权的类型分别认定从债权的种类。我国《民法典》第389条对所有类型的担保物权之担保范围作了统一规定,未区分担保权的类型,尤其是忽略了登记型担保权的特殊性,将不当扩大登记型担保权的担保范围,有损交易安全。
五、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在抗辩上的关系
(一)抗辩从属性
抗辩从属性,是指在担保权的实现过程中,担保人可向担保权人主张债务人基于主债权债务关系所享有的抗辩权(44)刘贵祥:《民法典关于担保的几个重大问题》,《法律适用》2021年第1期。。严格来讲,抗辩从属性应被称为抗辩权从属性,因为抗辩从属性中的抗辩应仅指排除权利可实现性的抗辩权,而不应包括权利未发生的抗辩与权利已消灭的抗辩,因为后两种类型的抗辩原则上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并且在法律效果上会导致主债权未发生或消灭,担保人可以通过设立从属性或消灭从属性防御债权人的权利主张。
当第三人提供担保时,当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消灭债务的形成权但不行使也未放弃时,为了保护第三担保人,第三担保人也应享有拒绝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权,其背后的原理也是抗辩从属性。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形成权不仅包括撤销权、抵销权,还包括解除权、减价权,但不包括选择权,因为《民法典》第515条虽然规定了债务人的选择权,但债务人未行使选择权的法律效果只是债务的内容不确定,并非债务是否消灭不确定。只有当所担保债权存在可被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的可能性时,为了保护第三担保人的利益,此种不确定性亦应传输到担保权身上,以实现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的同步性,这正是从属性的应有之义。所以,第三担保人基于抗辩从属性可得主张的抗辩权既可以来源于债务人的抗辩权,也可来源于债务人的形成权。对于保证担保中的抗辩从属性,我国《民法典》第701条第1句及第702条已有明确规定,其他类型的担保应类推适用。
无论是债务人所享有的抗辩权,还是债务人所享有的形成权,当通过抗辩从属性这条管道传输到担保人身上后,担保人均获得一个抗辩权,该抗辩权的效力体现为拒绝承担担保责任从而排除担保权的可实现性,担保权并不消灭。但是,当担保物权将面对一个永久性的抗辩权时,为了便于担保人的二次融资,应赋予担保人消灭担保物权的权利,即此时抵押人可以基于排除妨碍请求权要求抵押权人去办理注销登记,出质人可以请求返还质物(45)比较法上的立法例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169、1254条。。
(二)抗辩从属性的突破
抗辩从属性要求,债务人享有的抗辩权,担保人均可主张;债务人不享有的抗辩权,担保人一律不得主张。但抗辩从属性的适用涉及债权人与担保人利益的平衡,若严格贯彻抗辩从属性的要求可能会有违担保目的或损害担保人利益。因此,为了平衡担保目的与担保人的利益,有必要突破抗辩从属性。由于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对此有所论述,在此仅择其要点(46)详见李运杨:《第三担保人的抗辩权体系》,《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8期。。首先,当债务人享有的抗辩权是涉及债务人支付不能风险的抗辩权时,为了实现担保目的,担保人不得基于抗辩从属性主张此类抗辩权。其次,在主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情况下,为保护第三担保人利益,应突破从属性,第三担保人仍可主张被主债务人放弃的抗辩权。
六、从属性担保权与所担保债权在消灭上的关系
(一)消灭从属性
消灭从属性,是指当所担保主债权因清偿、免除、混同、提存等原因而全部消灭时,担保权也随之全部消灭;在所担保主债权未消灭之前,担保权不消灭。对于担保的消灭从属性,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如第682条第1款第2句和第388条第1款第3句,此两句虽然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主债权消灭,担保权也消灭。此外《民法典》第393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其中第1项便是“主债权消灭”,这也是关于担保物权消灭从属性的规定。消灭从属性中的“消灭”当指“全部消灭”,若仅是“部分消灭”,则涉及范围从属性。除了位于担保制度中的规定外,位于合同编通则部分的第559条也是关于消灭从属性的规定,其中的“从权利”包括了担保权。
在适用消灭从属性时应准确辨别所担保主债权是否确实已经消灭。清偿行为虽然可以导致主债权消灭,但若第三人代为清偿,根据《民法典》第524条第2款,主债权并不消灭,而是发生法定债权让与,即第三人成为新的债权人,相应地,担保权也不消灭,而是一并移转给第三人。债权与债务的混同一般可导致主债权消灭,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比如当债权人在其债权之上为他人设立质权时,债权并不因混同而消灭,相应地,其上的担保权也不消灭。当债权人免除债务人的全部债务时,同样如此,如果被免除的债务上已经为第三人设立质权,该免除的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对第三人而言,担保权依然存续(47)程啸:《担保物权研究》(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二)消灭从属性的突破
1.法定突破
《民法典》在规定消灭从属性的同时,也规定了消灭从属性的突破。无论是第682条第1款第2句、第388条第1款第3句,还是第559条,均允许法定例外,即当法律另有规定的,所担保债权消灭后,担保权可以不消灭。比如,第566条第3款规定,主合同被解除后,担保权并不消灭,而是继续担保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在债权人有效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后,原债权债务关系从解除权有效行使的那一刻转化为一个“返还债务关系”(48)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9.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5,§18 Rn. 2.。根据该返还债务关系,原合同的每一方有权要求对方返还已经履行的给付和所获收益。如果所得标的物不适合返还或不能返还,则应赔偿其价值。由于返还请求权或价值赔偿请求权均由原给付请求权转变而来,原来债务关系中的担保不应消失,而是应自动及于现在的返还债务关系(49)但也有不同观点,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册),第642页。。
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在主合同因行为人无行为能力、被撤销等原因而自始无效的情况下,原始意定债权虽不会产生,但基于法律规定可能产生不当得利之债,仍有担保之需求。如借款合同无效但所借款项已经支付的情况下,基于借款合同的还款请求权不存在了,但债权人却享有一个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是在当事人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担保权是否为不当得利之债继续担保?对此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按照肯定说,若原债权不存在了,通过对设立合同的扩张解释,抵押权应继续担保不当得利之债,因为不当得利之债是原债权的替代(50)Baur/Stürner, Sachenrecht, 18. Aufl.,München: C.H.Beck 2009,§37 Rn. 48.,二者之间具有债权同一性(51)Wilhelm, Sachenrecht, Berlin: De Gruyter 2010,Rn. 1588.。按照否定说,借款合同无效后产生的不当得利债权不受抵押权担保(52)MüKoBGB/Lieder, 7.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7,§1113 Rn. 84.,因为不当得利债权跟原借款债权在性质和内容方面存在重大区别(53)RG JW 1911, 653, 654.。
本文持肯定说,认为担保人所担保的内容在本质上应是一种请求债务人为特定给付的请求权,是一种权利地位,而不问它的产生理由或表现形式(54)Vgl. Rimmelspacher/Stürner, Kreditsicherungsrecht, 3. Aufl.,München: C.H.Beck 2017§15 Rn. 85.。在借款合同无效案例中,被担保的是债权人享有的请求债务人支付一定金钱的请求权。不论债权人的这种法律上的资格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的,还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产生的,请求权产生的事实基础是同一的,即债权人将借款支付给了债务人这一事实。借款合同无效后,借款债权不产生,不当得利债权等值地出现在原债权位置上,是原借款债权的替代。即使按照否定说,担保物权不再继续担保,担保人有权要求注销抵押登记或返还质物,但债权人基于不当得利之债却可享有一个留置抗辩权,因为他所享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与抵押权的注销登记或质物的返还义务来源于同一个生活关系。可见,在不当得利之债清偿之前,抵押人注销抵押登记的请求权或质押人返还质物的请求权并不能实现,在结果上跟继续担保的效果相同。
而且,如果原担保不能继续担保不当得利返还之债,在债权人对主合同无效事由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优先受偿的地位,则明显对债权人不公(55)黄家镇:《论主债权瑕疵引发的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在担保人和债务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使原担保继续担保不当得利之债,并不会损害担保人利益,不当得利之债本应就是他法律上不得逃避的债务。在担保人和债务人非同一人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原债权债务的内容是有预期的,令其对不当得利之债继续承担责任,有可能加重其责任。因为不当得利之债和原债在履行期限、计息等方面存在不同,比如,多数情况下借款合同中债权履行期限往往晚于立刻到期不当得利之债。如果按照不当得利之债的履行期限确定担保物权的实现时刻,担保人需立刻承担担保责任,这样会有损担保人利益。因此,为了不加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担保人的履行时间仍按照原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确定(56)Vgl. Wilhelm, Sachenrecht, Berlin: De Gruyter 2010, Rn. 1588.。在计息方面,法定的利息一般低于约定的借款利息,所以按照不当得利之债的标准确定利息一般不会损害担保人利益。
总之,合同解除之后的返还债务关系和合同撤销或无效后基于不当得利所产生的返还关系虽然在适用场域和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在原担保是否存续这一问题上,原则上应统一对待。当然,如果当事人事先明确排除了对返还之债的担保意思,则不应继续担保。
消灭从属性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所担保主债权未消灭之前,担保权不消灭。但是,有时即使所担保主债权未消灭,担保权亦应消灭,以突破消灭从属性。比如,当附有担保物权的债权面临一个永久性抗辩权时,所担保债权在我国法中并未消灭,但是由于担保物权的可实现性已经被永久地排除,其存续对债权人而言已经没有利益可言,而且还不利于担保人的二次融资,故此时应赋予担保人消灭担保物权的权利。另外,所担保主债权未消灭但担保物权消灭的情况还出现在所有权与担保物权混同时,即提供物保的第三人将担保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所担保债权未消灭,但担保物权因与同一物上的所有权发生混同而原则上应消灭。
2.约定突破
除了法律的规定可以突破消灭从属性之外,当事人的约定可否为消灭从属性设置例外呢?对此,之前的《担保法》与《物权法》曾存在冲突,该冲突在《民法典》中仍然存在。一方面,《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第4句及第682条第1款第2句均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第559条却规定“债权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面对制定法层面的冲突,在经济形势下行的大背景下,《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条第1款强化了从属性,否定了当事人继续担保约定的效力。
对此,本文认为应区分彻底排除从属性与仅排除消灭从属性。与人的担保不同,在物的担保中存在物权法定原则,由于《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典型担保物权均为从属性担保物权,并未规定类似于德国法中的土地债务一样的独立性担保物权,所以当事人彻底排除从属性的约定宜被否定。换言之,从属性的弱化应以不改变担保物权的从属性特征为最低限度(57)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册),第621页。。但是,当事人若约定仅排除消灭上的从属性,并不会改变担保权的从属性特征,担保权在移转、范围及抗辩等其他方面仍从属于所担保债权,这就如同担保权的移转从属性因当事人的约定被排除后不改变担保权的从属性特征一样。此类仅排除担保物权某个方面的从属性之约定并未创设独立性担保,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应当允许。据此,若当事人事先约定担保人对主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该约定仅突破消灭从属性,基于意思自治的基本原理,理应被允许。而且,《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半句及第2款已经规定,在借新还旧业务中,旧贷上的担保权因为清偿而消灭,但旧贷的担保人若同意继续为新贷担保,则该担保权继续存在,该规则背后的原理其实就是消灭从属性的约定突破。
借新还旧业务出现在不动产抵押中,当事人在旧债权消灭后,未办理抵押权的注销登记,而是用以担保其后新发生的债权。此种约定不因违反从属性而无效,因为担保的从属性原则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拒绝例外的原则,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原则(58)Habersack, Die Akzessorietät, JZ 1997, 857, 864.。它在将担保物权和债权捆绑到一起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特殊约定。只要没有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旧债权消灭后未办理抵押权的注销登记,当事人约定将其用作担保新债权的应予认可。这样不仅可以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能简化了当事人先办理注销登记然后又办理设立登记之繁琐的程序(5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10号判决书。。当然,新的担保应在登记债权额的范围内有效,超过登记债权数额的债权成为无担保债权。
在人的担保中,由于不存在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当事人在保证的基础上不仅可以约定排除消灭上的从属性,还可以同时约定排除其他方面的从属性,使担保权在成立、范围、抗辩、移转等方面均不依赖于所担保债权,从而创设真正的独立性担保。其实,已经被司法解释所认可的独立保函就是一种当事人通过约定所创设的独立性人保。
七、结语
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典型担保均为从属性担保,其与所担保债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且复杂。作为一种立法者运用的法定机制,从属性使得担保权在设立、范围、处分、抗辩及消灭等方面均依赖于所担保主债权。但是,由于从属性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原则,基于从属性产生的系列规则在规范性质上应属任意性规范,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可以突破从属性。从属性的诸多突破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有时甚至是混乱的景象,但其背后有一定的逻辑可循,择其要点可作如下总结。
第一,从属性的适用应回应交易实践的需求,贯彻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比如,允许当事人为将来债权设立担保,以突破设立从属性;允许当事人约定对所担保主债权的处分不及于担保权,以突破处分从属性;允许当事人约定担保权在所担保主债权消灭后继续担保新的债权,以突破消灭从属性。
第二,从属性的适用不应损害第三担保人利益。在第三人提供担保时,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增加主债权数额的,应突破范围从属性,担保范围不得相应增加,以保护担保人。同样,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时,债务人提供的担保原则上应继续为新债务人担保,但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则应突破移转从属性,原则上不再继续担保。
第三,从属性的适用不应背离担保目的。为实现担保目的,担保人不得主张主债务人享有的涉及支付不能风险的抗辩权,以突破抗辩从属性;同样,所担保主债权因合同被解除、被撤销或无效而消灭后,担保权应继续担保债务人的返还之债,以突破消灭从属性。
第四,从属性的适用应兼顾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登记型担保物权存在担保范围的登记及第三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适用范围从属性时应格外谨慎,原则上只有经过合意且办理登记的债权才可以纳入登记型担保权的担保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