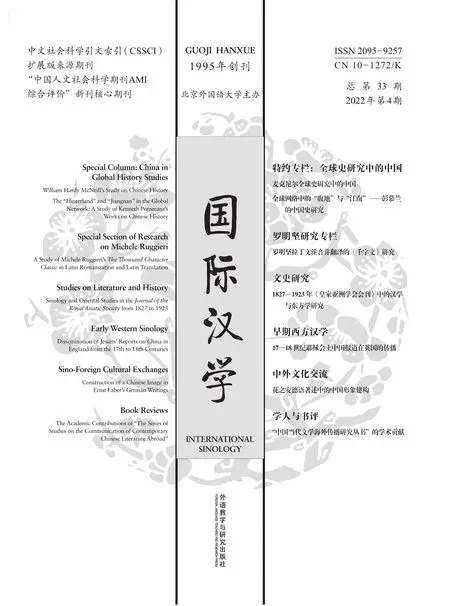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主体:比丘林时期*a
□张 冰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同文化间不断传播、不断扩大交流的过程。探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特别是作为文化传播中首要因素的文化传播者,即文化传播主体问题,不仅是基于文献史实基础之上的、重要的中俄文化交流、跨文化理论的学理探源,也是阐明中俄文化以及人类文化传播的本相和规律,乃至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形式,“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四分之三的领土都在亚洲,拥有三分之一的亚洲陆地,是中国最大的邻国,虽然中国文化在邻国俄罗斯的传播大大晚于一些并不与中国接壤的欧亚国家,但至今也有三百余年复杂的发展流变。仅就传播主体而言,三百多年间,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主体至少经历了以俄国北京传教士汉学家为传播主体的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1777 —1853)时期,以学院派汉学为传播主体的瓦西里耶夫(王西里,В. П.Васильев,1818 —1900)时期,20 世纪开始的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新闻出版等国家机构为传播主体的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 —1951)时期和当代以知识精英、社会大众、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等为传播主体的全球化新媒体时期。
起源地在欧洲的俄国15 世纪开始向亚洲扩张,《元史》中已有中俄直接交往的确切记载,但只是俄罗斯人被掳往北京服役的简单记录,并且这些俄罗斯人的最终去向始终成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他们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中国的记载。在旅行印度的特维尔商人尼基京(А.Никитин,?—1475)1471 年撰写的《三海航行记》(Хожд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中,俄罗斯才有了通过二手或者三手信息获得的关于中国的零星介绍。1619 年,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哥萨克军役贵族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生卒年不详)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后,向沙皇呈上了最早的和最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文献之一《见闻记》(Роспись),它是汇报性的简报,目的是为俄国政府的政治军事利益服务,行文简明扼要,枯燥肤浅,并未涉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最终引起俄罗斯人对中国兴趣的是1668 —1669 年御前大臣、时任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彼得·戈都诺夫(П. Годунов,?—1670)与人编撰的《关于中国和遥远的印度的消息》(Ведомость о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и о глубокой Индии)。这本书里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引起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关注。但是,中国对于俄罗斯而言仍旧模糊不清,充满了神秘和未知,更遑论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解。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基本上处于材料信息积累和尝试分析这些材料的最初阶段。
直到1715 年,俄罗斯在施行“东方推进”举措中向中国派出了“北京传教士团”,其后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自公元988 年成为俄罗斯国教后,便与俄国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东正教会依附和服务于俄国政权,成为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目标的重要工具。“这种局面在彼得一世(Пётр I,1672 —1725)统治时期得到彻底强化。1721 年,彼得一世废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制,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开始称宗教部,后称圣务院、正教院、东正教事务衙门等)管理教会……教会实际上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一个行政机构。”a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1618 —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284 页。17 世纪,西欧已经出现了俄国东正教教堂。1700 年6 月18 日,彼得一世签署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东方语言的圣旨,下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挑选“两三个素质好、有学问并且年龄不太老的修士”派往中国,谕旨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文知识,以及了解中国人的迷信信仰”。bН. Адорат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ып.1: История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1685–1745). Казань, 1887, C. 57.
东正教会伴随着俄国领土的疯狂扩张,建立起一系列派往各国的传教士团:1715 年,北京传教士团;1794 年,东正教开始在美国传教;1847年,耶路撒冷传教士团;1869 年,日本传教士团;1898 年,伊朗传教士团;1900 年,朝鲜传教士团……他们为沙皇政权服务,公开从事传教活动,向俄国传递了大量的异域政治外交社会文化信息,客观上在打破俄罗斯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隔绝状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相关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俄罗斯汉学肇始于18 世纪的俄国传教士团。正是1807 年派往中国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1808 —1821)传教士团领班、俄罗斯汉学奠基人、首位闻名欧洲的俄罗斯汉学家尼·雅·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 —1853)巨大的奠基贡献,形成了中国文化俄罗斯传播主体谱系中以俄国北京传教士汉学家为传播主体的比丘林时期(1715 —1837),为中国文化的俄罗斯传播,中国精神思想文化典籍的俄文翻译研究成为中国文化俄罗斯传播的重要路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首批本土中国文化传播者的培养
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在北京的非官方代表,作为非官方的外交机构行使职能,调研中国,进行满汉语学习,客观上推动了中俄语言的直接相遇和相互影响,培养出了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的传播主体、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首批俄国本土汉学家,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其采取的汉学人才培养举措。
其一,俄国传教士团在北京俄罗斯馆组成了专门的“俄罗斯学校”,纳入清朝官制管理,受辖于理藩院,设有专门的教学行政管理官员,由国子监派出满语和汉语助教为随传教团前来的学生等人授课。1795 年,为了加强学生的汉学基础,俄罗斯馆还私自聘了满汉教师,并陆续制定出一系列的人才培养规范,使北京传教士团成为俄国汉学人才培养的发端。
其二,研习儒学经典,按照中国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汉字学习和汉学启蒙,所有人员都要学习掌握汉、满、藏等语言,采用《三字经》为识字课本。因此,《三字经》最早的译本便由1729年来京的传教士团随班学生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1707 —1761)完成,介绍到俄国。1829年,比丘林再次把 《三字经》翻译成俄文出版后,此书成了许多俄国学校和学习汉语者的汉语和汉学启蒙教材。同时,北京传教士团组建的俄罗斯学校强调对中国儒学经典“四书”的学习和掌握。1838 年,比丘林曾在《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文cН. Я. Бичурин, Взгляд н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в Китае//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 5 и 6. май и июнь.1838: 1–73.谈到,“四书五经”是中国私塾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对于中国人而言,“像基督徒的经书一样重要”。aН. Я. Бичурин, 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2016, C. 53, 54.比丘林还在其所作《汉文启蒙》(Ханьвэнь цимэн,1838)中以中国传统语言学知识阐释汉语语法体系,使得俄国的汉语教学向专业化迈进。
其三,逐渐提高选派学生的素质,从1807 年起,要求北京传教士团随班学生主要从俄国大学,大多从圣彼得堡神学院“大学生”中选派,并且改革北京传教士团的学生培养机制。
1816 年,比丘林上书提议改组北京传教士团,提出十年三段的培养学制:第1 —5 年,主要是语言学习和翻译能力的培养;第6 —8 年,主要研读儒家经典“四书”;第9 —10 年,开始从事专题(中国文学、儒学、历史、地理、法律政治、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等)研究。据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18 年批准了关于北京传教士团此后工作的指令,其中规定,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随班学生“除完成学习汉、满语文这个主要任务外,从医学到哲学(特别强调‘儒学’),从法律制度到农村经济,均应安排专人,分头搜集资料进行研究”。b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24、25 页。
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1821 —1830)团长加缅斯基(П. И. Каменский,1765 —1845)在其制定的“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工作指南”中,亦明确了学生们的主要课程是学习汉语、满语,“其他课程设置要与他们先前的功课、愿望和能力相一致,有人着重于中国的医学和自然史;有人着重于当地的数学状况,关注中国文学、哲学特别是孔子的学说体系;有人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统计和法学;还会有人收集农业、农民的家庭生活、土地耕作、手工业和艺术方面的信息。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莫斯科自然工作者学会、彼得堡矿物学会和自然经济学会都会让这些学生(还包括教堂第一服务人员)担任自己的通讯员。”cВ. Ваг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рафа М.М.Сперанского в Сибири, с 1819 по 1822 год. Т.2 / Вагин В. –М.: Книга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2011, C. 633.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1892 —1964)高度评价了加缅斯基的“指南”,他说:“对于培养中国学家来说,这个指南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给大学生们定下了指定的具体专业领域。这种细化有助于团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很好地学习掌握与日后实际工作相关的中国学专业领域知识,也有助于教授专业课程。”d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C. 129.
俄国北京传教士团,特别是从比丘林担任领班后,通过采取有鲜明汉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计划、教师设置等措施,在掌握了语言翻译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儒学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研习,再进行具体的专科研究,达到“专才”教育成为“中国通”,特别是中国儒学经典,“汉学专才”的人才培养目标,最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首批俄国本土汉学家。其中包括俄罗斯首位汉学家和满学家罗索欣,俄斯汉学奠基人比丘林,汉学家加缅斯基e1819 年,加缅斯基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巴黎亚洲协会会员、北方古董哥本哈根协会及科学艺术爱好者自由协会会员。,两次(1850 —1858,1865 —1878)担任传教士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1817 —1878],以及第一位俄罗斯本土汉学院士、第十二届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瓦西里耶夫等。
二、首批俄国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
18 世纪彼得大帝的全面“欧化”改革,不仅从德国“移植”来了俄国首位汉学家巴耶尔(Готлиб-Зигфрид Байер,1694 —1738),也使欧洲对于中国精神思想的关注和西方的汉学成果引入到了俄国。1830 年,巴耶尔编写的包括《大学》部分内容的《中国博览》(Museum Sinicum)在彼得堡问世,标志着中国典籍开始传入俄罗斯。但是不懂俄语的巴耶尔编入的《大学》是拉丁语译文和汉语对照本,印数少,且鲜有俄国大众读者,影响力有限,学术水平亦受到俄国学者的质疑。
这种状况在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回到俄罗斯后得以改变。传播主体是文化传播中首要并且不可或缺的一环。北京传教士团成员作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主体——传播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诸多著述让俄国人首次知道了中国文化”aН. А. Самойлов,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VII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тенденции, формы и стади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ПбУ. – СПб.: Изд. до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4, C. 146.,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其一,使俄罗斯有了中文人才,结束了俄国外事外交工作中缺乏汉语、满语翻译的状况。此前,直到18 世纪中叶,中俄两国都缺乏汉俄、满俄译员,两国的外事往来文书都是使用拉丁语,谈判交流只能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以拉丁语居中转述。学成回国的传教士团随班学生,特别是传教士团中产生的诸多汉学家,很多在俄国外交外事部门任职,如比丘林曾任外交部亚洲司译员,罗索欣曾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翻译工作。中俄直接的官方交往不再借助第三方语言,中国语言自此进入俄国官方社会,中俄双方建立起了更加畅通的相互认知往来通道。
其二,传教士汉学家积极编写汉语学习教材、辞书,教授汉语、满语和开办汉语学校,传授汉、满语和中国文化知识。罗索欣回到俄罗斯后,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担任满汉语翻译与教学工作。1741 年7 月17 日,他获批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所中文(汉语、满语)学校,并第一个编写了满汉语教材,不仅教授学生学习中文,而且向他们讲授中国文化礼仪和民族传统。他最早把《三字经》《千字文》译成俄文,既用于教学,也介绍给俄国读者,掀开了俄罗斯翻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精神文化的第一页,被誉为俄国汉学第一人。
1831 年,比丘林在恰克图开办汉语班,1832年改制为学校,他亲任教员,在那里几乎待了十八个月,亲自拟定教学大纲,编写了俄国第一部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汉语语法》(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为俄国的汉语教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比丘林还推荐回国的第十届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К. Г. Крымский,1796 —1861)担任恰克图汉语学校的教师和翻译。1835年,比丘林按照外交部的指令从彼得堡返回恰克图重新开始教学工作,直到1838 年才回到彼得堡。比丘林拟定了俄国汉语学校的首份教学大纲,将学校学制设为四年,通过汉俄语法对照学习、贸易专题会话练习、汉语短文和书面语的翻译等汉语学习实践,恰克图汉语学校不仅培养出汉语译员,满足了当地俄国商人的需求,有助于俄国商人与中国人的通商贸易发展,而且加深了俄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比丘林参考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所作的《汉文启蒙》,是恰克图和后来许多俄国学校的汉语学习教材。
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1716 —1786)等人都编辑过汉语小词典,比丘林在汉语学习中也很重视词典的作用,他自己就编辑过《汉俄词典》《汉俄语音简明词典》《满汉俄词典》等几种词典,这些词典显然有助于最早的俄国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但遗憾的是,因为都是手稿,没能出版,所以也没有在后来的汉语教学中发挥作用。
其三,传教士团成员同探险家们一起,也为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的汉、满、藏、蒙东方学文献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18 世纪,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1700 年,彼得一世提出了一系列的“斯拉夫语”图书出版计划。18 世纪最初的25年里,俄罗斯图书的出版量超过了此前的150 年。1714 年,彼得堡设立了俄罗斯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最古老和最主要的图书馆之一,1724 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时,该馆正式成为科学院图书馆。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图书馆的藏书就达一万余册。当时,私人藏书也蔚然成风,出现了许多私人图书馆,彼得一世不仅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还有一千五百多种藏书。“俄罗斯帝国副宰相奥斯杰尔曼(А. И. Остерман,1686 —1747)和其他显贵都收藏有中文图书,它们大概来自欧洲。”a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T. V (1742–1743). СПб., 1889, C. 324. Cм. И.Ф. Попова, О первых поступл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академию наук и их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в XVIII в.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 (6), 2007, С. 230.
“图书馆的首批中文书籍实际上是俄国驻中国朝廷的外交官朗格(Ланг)1930 年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带来的8 套共计82 本书。其他东西也同样是从这些传教士那里获得的。”b[Бакмейстер И.Г.] Опыт о библиотеке и кабинете редкостей и истор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Имп.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зданный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Иоганом Бакмейстером, подбиблиотекарем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 переведенный Васильем Костыговым. [СПб.,] 1779, С. 93–94. Cм. И.Ф. Попова, О первых поступл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академию наук и их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в XVIII в.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 (6), 2007, C. 232.其中包括两部汉籍《经史海篇直音》和《字汇》,这应该是目前已知最早传入俄罗斯的汉籍。而1818 年设立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亚洲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东方手稿、文献收藏地,东西欧东方学书籍馆藏地以及东方钱币收藏地。c目前,圣彼得堡大学高尔基科学图书馆拥有的700 余万本藏书,15 万本珍本和手稿中,有着大量的中国手稿和木板年画。
作为俄国精神、文化和科学中心的东正教教会,很早就有了教会图书馆。“古罗斯图书馆(藏书库)始建于教堂和修道院,它们是收藏图书手稿的主要中心。”dОсновы библиотечного дел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библиотекарей, работающих с фондам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вт. кол.: М. Н. Глазков, прот. Борис Даниленко, мон. Елена (Хиловская), Ю. В. Климаков, Н. В. Лопатина, прот. Петр Мангилёв, Е. А. Плешкевич, Н. А. Степанова, С. П. Фунтикова, С. А. Чазова; отв. ред. Н. А. Степанова. М., 2016, C.13.对图书资料收藏的重视同样体现在俄国海外传教士团的管理政策中,俄国的海外传教士团基本上都有着与俄国国内教会图书馆相同的设置,为俄国国内和当地教会图书馆收集所在国的图书等资料成为传教士团的一项重要使命。“……根据拨付的款项按照书单为该图书馆收集图书。”eИ. Л. 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О библиоте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 21-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Ч. 2. – М., 1990, C. 132–133.“传教士团必须尽可能利用拨给它的资金为传教士团图书馆搜集图书、地图和城市平面图……当发现好书和珍贵物品时,应该购买两份,一份留给传教士团,另一份运回俄罗斯。”fИ. Л. 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0, № 5.Цит.по:肖玉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载《清史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79 页。1795 年,由第八届北京传教士团(1796 —1808)团长、修士大司祭格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и Грибовский,?—1814)在北京创建的传教士团图书馆不仅成为第一座俄国东正教会的海外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籍,而且历届北京传教士们都将大量的中国典籍等图书带回了俄罗斯。
罗索欣在中国收藏了许多汉文和满文书籍,1741 年,他曾将从中国带回的52 种书以242 卢布30 戈比的价钱卖给了科学院;g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Архива РАН. ф. 3, on. 1,ед. хр. 59. JIẾ203. Цит.по: И. Ф. Поповой, О первых поступления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академию наук и их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и в XVIII в.//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 (6)2007, С. 236.同年,他编撰了科学院图书馆最早的汉文和满文书籍目录《中国书目》(Реестр китайским книгам)。1742 年,罗索欣从奥斯杰尔曼伯爵藏书中选出23 种中文书籍移交给了科学院图书馆;1748 年3 月,他建议科学院图书馆从私人手上收购了15 种汉、满文书籍,还为这些书详细编目,估价193 卢布80 戈比。1761 年,罗索欣去世后,他的遗孀将55 种汉、满语书籍以32 卢布的价钱卖给了科学院。hВ. П. Таранович, И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 и его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ю//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III[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5, C. 238–239.比丘林1821 年回国时,“随身携带了12 箱汉文、满文书籍,和他的一箱手稿,一箱颜料,6 卷地图、地形图。能登记的书有:5 部汉语字典,2 部满语字典,中国历史(43 部,2 箱),汉文和满文的满族历史,“四书” “十三经”,清、辽、元历史书籍,法律问题著作和其他书籍。”a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C. 96.加缅斯基,也就是修士大司祭彼得,自费购买了许多汉语、满语和蒙古语书籍,他将其中的上百册图书捐赠给了俄国圣彼得堡神学院、外交部亚洲司、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莫斯科大学、伊尔库茨克市宗教学校、市立中学和恰克图的蒙古语学校等各家机构。
不过,这些中国典籍的保存、整理和传播等工作并不尽如人意,人们大多只是通过各种书目了解到相关信息。
三、开启了从中文翻译中国典籍,“援中入俄”的传播中国文化之路
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汇集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通道。自16 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 Ruggieri,1543 —1607)将《三字经》译成拉丁文始,中文典籍外译已有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国思想文化正是借此路径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发展。俄国北京传教士汉学家成为“比丘林时期”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的传播主体,与其开启了直接从中文将中国典籍翻译成俄语,“以译代著”“援中入俄”的文化传播路径密切相关。
(一)索罗欣、列昂季耶夫等人的中国典籍俄译
俄国传教士汉学家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最早开启了直接将中国典籍译成俄语的工作,使得中国文化典籍译成俄语传入俄国,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作为第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来到中国的罗索欣,出色地掌握了满语和汉语,并翻译了《三字经》和《八旗通志》等中文书籍。1741年罗索欣回国后,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满汉语翻译和中文教学工作,他不仅用自己翻译的《三字经》《千字文》进行中文教学,还指导他的学生沃尔科夫(Яков Волков,1728 —?)首次在俄罗斯翻译了中国典籍“四书”,尽管是摘译,“沃尔科夫的手稿《四书》只有残缺(16 章)的《论语》译本”b科布杰夫:《〈大学〉在俄罗斯的命运》,张冰译,载《国际比较文学》2020 年第3 期,第509 页。。
1745 年,罗索欣在向科学院上交的已完成译稿清单中,有《中国名师道德箴言》《三字经》《哲学问答》《孝经》等16 种著作。此外,他完成的译著还包括:1750 年,《亲征溯漠方略》(五卷);1756 年,《资治通鉴纲目》;1761 年,《八旗通志》(八旗通志初集,罗索欣翻译时将其分为16 卷,翻译了其中的5 卷,即,第1 —3、6、7 卷)等,总计约三十种各种题材的满、汉语著作。然而当时俄罗斯科学院的现状是,科学院首位汉学院士巴耶尔在罗索欣回国前三年已经去世,负责其工作的米勒(Г. Ф. Миллер,1705 —1783)院士和费舍尔(И. Э. Фишер,1697 —1771)院士尽管对中国历史地理等充满兴趣,肯定了罗索欣工作努力成果丰厚,然而他们只是利用索罗欣的翻译成果及其提供的知识信息,他们不了解索罗欣工作的巨大价值,根本不关心他的译作出版事宜,甚至压制罗索欣译作的出版。这两位历史学院士和科学院的其他院士一样,都不懂中文,对中国知之甚少,并且和外务委员会一样轻视中文。因此,罗索欣只被当成一个普通翻译,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他完成的庞大的译作手稿在其有生之年基本上都没有出版,大部分存藏于圣彼得堡科学院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圣彼得堡的萨尔蒂科夫 – 谢德林国立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少部分手稿在莫斯科和喀山。
在中国学习生活了11 年(1744 —1755)的第三、第四届北京传教士团随团学生列昂季耶夫回到俄国后的命运要比罗索欣好得多,他的中国典籍翻译成果大多得以发表,为世人所知。
1756 年列昂季耶夫回国后先到外务委员会从事公文翻译工作,次年来到科学院成为罗索欣的同事,协助其翻译《八旗通志》,完成了第4、5、9 —16 卷的俄语翻译。在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1711 —1765)的直接帮助下,冲破科学院德国学者的层层阻挠,最终,科学院于1784 年资助出版了俄语译著《八旗通志》aИ. К. Россохин, А. Л. Леонтьев, Обстояте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состояния маньджу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войска,восьми знаменах состоящего. И. К. Перевод Россохина и А. Л. Леонтьева; Иждивением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84.,包括16 卷正文和1 卷注释(第17 卷)。此时距罗索欣病逝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罗索欣与列昂季耶夫“在翻译过程中严格地尊重原文,努力完整而准确地传达中国文化的内容。尊重原文看似一种翻译方法,实际上反映了译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态度。欧洲早期汉学家随意篡改中国作品的现象在俄国汉学家身上很少能看见。他们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从西欧传到俄国的被扭曲的中国形象”b阎国栋:《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夏之卷,第160 页。。
1772 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思想》(Китайския мысли),并分别于1775 年和1786 年增补再版,内容不仅包括雍正的谕旨言论,还有《孙子兵法》的摘译,首次将这部中国现存最早的军事经典介绍到俄罗斯。1780 年,列昂季耶夫将中文版《大学》c据别尔科夫(П. Н. Берков,1896 —1969)通讯院士根据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 —1951)院士的口头转述:“列昂季耶夫的译文不是译自汉语而是译自满语。” См. Д. И. Фонвизин, Собр. соч. в 2-х томах. Т. 2, C. 676.全文翻译成俄语出版;1784 年,他又将《中庸》翻译成俄语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从中文翻译出版的儒学经典著作,也是列昂季耶夫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中国典籍俄译做出的巨大贡献。
列昂季耶夫翻译事业的继承人阿加福诺夫(А. С. Агафонов,1746 —1792)的译作题材选择则突显了对社会、政权的“迎合”性。阿加福诺夫是俄国第六届北京传教士团学生,有十年(1771 —1781)的中国生活经历,1782 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翻译,任职伊尔库茨克总督府,1787年调回圣彼得堡。1784 年,阿加福诺夫翻译了马融的《忠经》,译名为《忠经,或者关于忠信之书》dДжунгин, или книга о верности. Переведенная с манжур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Алексеем Агафоновым в Иркутске 1784 г. по открытии того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а. М.,в тип. Компании Тип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 указного дозволения, 1788.,1788 年在莫斯科出版。本书开篇是译者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伊尔库茨克总督雅各比(И.В. Якоби,1726 —1803),庆祝新总督府的设立,并向总督大人、女皇陛下和沙皇帝国表达自己的忠诚。同年(1788),他从满语翻译的中国皇帝的“圣训系列”《圣祖圣训:圣德》(1662 —1722 年康熙论生活行为准则)、《圣祖圣训:求言》《圣祖圣训:论治道》在圣彼得堡出版;1795 年,《圣祖圣训:圣德》改书名为《皇帝——大臣的朋友,或者康熙之子雍正所集清朝皇帝康熙的朝廷政治训诫和道德标准》eГосударь — другсво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или проидвр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поучения и нравоучительны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манжур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Кан-Сия, собранные сыном его ханом Юн-Джином. Перевод с манжурского Алексея Агафонова, СПб., 1795.在圣彼得堡再版。将反映中国皇帝用人行政、治国安邦的谕旨实录译介到俄国,当然首先是迎合时势,针砭时弊,不过客观上延续了列昂季耶夫同一主题的翻译,有助于俄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管理思想、中国历史发展。
列昂季耶夫是18 世纪俄罗斯翻译中国典籍数量最多的翻译家,在当时俄国出版的120 种有关中国的译著(书文)中,他自己就有20 多种,译作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哲学、民族学、法律、医学各个领域。“列昂季耶夫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翻译题材广泛,内容深刻,还在于他在其注释和说明中试图解释中国现实的诸多现象,时而出现的极其冗长的释文显示出他具有深厚的中国文献知识和对于中国清代生活各方面的深刻认识。”f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C. 75–76.
(二)比丘林的中国典籍俄译
1777 年,比丘林(乙阿钦特)出生于喀山阿库列瓦村一个普通的神职人员家庭,8 岁时进入喀山宗教学校(1798 年易名喀山神学院),1799年22 岁时毕业;1800 年在喀山受洗入教,教名为“亚金夫”(Иакинф);1802 年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修士大司祭;1808 —1821 年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1828 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1829 年,成为公共图书馆荣誉馆员;1831 年,被法国东方学家推荐为巴黎亚洲协会会员。比丘林是位天才的学者,知识渊博,精通汉语、满语和蒙古语,编纂有多部汉语词典,以法号“亚金夫”闻名于俄国和西欧,五次获得俄国科学院杰米多夫奖。比丘林的翻译研究使俄罗斯的汉学、蒙古学研究置身于欧洲东方学研究的前沿,为俄罗斯知识界深刻地认知中国,为整个社会大众了解中国文化,为汉学在俄罗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比丘林勤奋治学,在他彼得堡墓地上铭刻着碑文“无时勤劳,垂光史册”。他著(译)有一百多种中国翻译及研究作品,主要内容分为:(1)中国 语言和文化,如:《尚书》(Шу цзин,Древняя кита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译稿,1822)、《大学》(Да-сио или высшее учение, служащее ключом к добродетели,译稿,1823)、《中庸》(Чжун-Юн,手稿,1823)、《三 字 经》(Сань цзы цзин,или Троесловие, с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ым китайским текстом,1829)、《汉 文 启 蒙》(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Ханьвэнь цимэн,1837)、《由孔子首立、中国文人接受的中国历史基本原则》(Основные правила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е Конфуцием и принятые китайскими ученым,1839)、《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1840)、《中国民情与风尚》(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1848)、《儒 教 概述》(Описание религии ученых,1906);(2)中国疆域历史地理,如:《资 治 通 鉴 纲 目》(Цзы-чжи тун-цзянь ганму,译稿,1825)、《西藏志》(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а в нынешнем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и,《卫 藏 图 识》,1828)、《蒙古札记》(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1828)、《北京志》(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宸垣识略》节选,1829)、《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1829)、《准 噶尔和东突厥历史与现状》(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摘译自《西域传》《西域闻见录》等,1829)、《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 年—公元1227 年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ода до Р. X. по 1227 г. по Р. X.,摘 译 自《廿 三史》《通鉴纲目》,1833)、《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 世纪迄今)》(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1834)、《中华帝国详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1842)、《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1849 —1851)、《东亚中亚史地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Срединной Азии,1960);(3)其他,如:《中国钱币》(Опис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монет,手稿,1838)、《中国农业》(Земледелие в Китае,1844)等。
首先,比丘林完成了诸多汉籍在俄罗斯的首译,他的中国典籍俄语翻译,富有开创性,影响力大。他翻译的《西藏志》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藏学著作,他翻译的《准噶尔和东突厥历史与现状》是俄国第一部关于中国西部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西域传》《汉书》《西域闻见录》的译文。比丘林的翻译工作引起了俄罗斯和欧洲学术界、知识界的关注和赞誉,深化了俄罗斯和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和俄罗斯的传播和影响。《卫藏图识》《北京志》《蒙古札记》等在彼得堡出版后,介绍评论纷至沓来,不乏赞美之词。著名东方学家、出版家、文学家先科夫斯基(О. И.Сенковский,1800 —1858)称《卫藏图识》的译本《西藏志》可以列入欧洲总体文艺学经典。比丘林的多部译著也相继被译成法语,在欧洲反响强烈。
比丘林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建立在其大量的汉籍翻译和整理的基础之上。《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一书是他在翻译《元史》、蒙古史的基础上撰写完成;《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 —公元1227)》一书是在翻译《新疆志聊》《西域闻见录》等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他的《中国农业》是根据清鄂尔泰所撰农书《授时通考》写成。比丘林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在源自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译文材料进行详尽的注解和阐释分析,使得他的研究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史实引证可靠性强,阐发令人信服。正如普希金(A. C.Пушкин,1799 —1837)所说:“有关卡尔梅克人逃亡史实最可信最客观的披露,我们应该归功于亚金夫神父,他深厚的知识和严谨的著作让人们如此清楚地看到了我们与东方的关系。我们满怀感谢地在此载入他提供的自己尚未出版的有关卡尔梅克人著作的片段。”a比丘林曾将《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 世纪迄今)》一书部分手稿送给普希金,对其创作《普加乔夫史》帮助很大,普希金的这段话正是因此而发。См. М. П. Алексей, -А. С. Пушкин и китай.// А. С. Пушкин и Сибирь. Москва-Иркутск, 1937, C. 134.
比丘林首次提出了作为世界文化组成的中华文明独特性的论题。他认为,研究中国不能盲从西欧,不能盲目采用外国资料,俄国学者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尽管有评论批评比丘林对中国的看法不确切,过度迷恋,别林斯基(V. G.Belinsky,1811 —1848)就曾著文批评比丘林把中国现实的很多方面理想化的做法,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使人们可以看到浩繁的中国史料,向俄国读者介绍中国,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扭转了关于东亚各国民族的错误认识,坚决反对追随西欧学者,坚持俄国的学术观……比丘林对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意义是巨大的: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丰富而多样,他对书刊上关于这个国家的虚假消息给予了尖锐的、公正的批判,使得更广大的俄国社会关注过去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些方面,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些由西方引入的不正确的看待中国的态度。”bП. Е. 斯卡奇科夫著,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编:《俄罗斯汉学史》,柳若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171、173 页。
总之,“比丘林时期”是奠定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发展的基石,是一个以传教士汉学家为传播主体的特殊时期,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的起始时间划定为俄国首批北京传教士团的派出时间1715 年。这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俄国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出了俄国首批本土汉学家,他们学习研究中国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形式将中国文化体系、中国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带到俄国,成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主体。他们的汉籍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特别是比丘林以其史无前例的大量译著和编译著述,开创性地确立了以译代著、“援中入俄”的传播中国文化之路径。随着历史的发展,19 世纪的俄国进入了社会变革、民族觉醒、经济发展、文化模式更新的时代,人才需求迫切,教育从个体行为发展为公共事业,发展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国立大学、专业学院和私立院校等高等学校加速建立。喀山大学1837 年设立俄罗斯首个汉语和中国语文教研室,标志着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中心转向了大学体制之中。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也从俄国传教士汉学家为传播主体的“比丘林时期”发展到以学院教育体制的汉学专业学者为传播主体的“瓦西里耶夫时期”,但此时俄国仍然在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传教士中培养出的中国文化传播人才仍然在中国文化向俄罗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