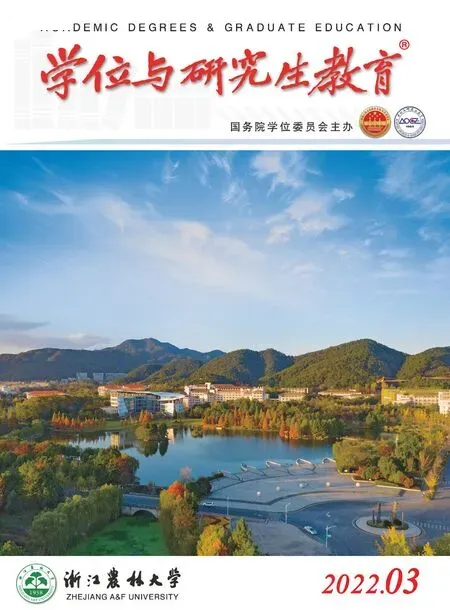“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表现、实质和现实意义
宋德发 荆莹莹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极为有限——1939—1946年,复学和新招收研究生219人,毕业78人[1],但是其经验却弥足珍贵。可以说,在招生、管理和培养等各个方面,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都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换言之,今日研究生教育遭遇的种种疑难和困惑,都可能从西南联大那里找到解决之道。比如,导师和研究生该如何相处?这个研究生培养中的关键性问题,借助重温西南联大导师和研究生融洽相处的故事,或许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表现
由于西南联大以本科教育为主,因此西南联大的故事多与本科教育相关,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故事很少。尽管如此,通过广泛的、细致的阅读,以及对“蛛丝马迹”的耐心追寻,依然能够发现一些导生融洽相处的动人细节。这些动人细节可以归纳为两类情况:一是学术上的融洽相处;二是生活中的融洽相处。
1.导生学术上的融洽相处
(1)导师对学生进行细致入微的学术指导。1939年考取研究生、师从吴达元的李赋宁回忆说,吴达元指导研究生十分认真:“吴先生让我细读莫里哀全集,与莫同时代的剧作家 Corneille,Racine,文学批评家Boileau,寓言作家La Fontaine等,为了全面了解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文学的背景。我的作业是每周用法文写一篇读书报告。吴先生认真批改。逐渐我的法文写作也有了一些进步,阅读法文的速度也有了提高。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我对法国文学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1942年考取杨石先研究生的何炳林回忆说,杨石先不管工作多忙,“每份书面报告都要亲自指导、校正,提出学术性意见,甚至连文字修辞也动笔修改”[3]。1943年入学的王浩回忆说,他的两篇课程论文不仅得到了冯友兰的耐心指导,而且经冯友兰的推荐获得公开发表:“记得冯先生对学生是很善于鼓励的,例如我有两篇在课堂写的报告,都由他推荐到《哲学研究》发表了。”[4]
(2)导生进行平等宽容的学术对话。朱德熙求学期间曾寄居于北院的研究生宿舍。他经常看到沈有鼎到宿舍来找研究生李荣君讨论学术问题:“沈先生常常光临我们的斗室,目的有两个:一是跟同屋的李荣君讨论等韵问题,二是顺便刮刮胡子(他大概没有剃刀,而胡子又长得极快)。他来找李荣君讨论等韵是带点求教的味道的。须知当时沈先生是名教授,而李荣君是刚考上研究院的学生。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沈先生的为人,也可以看出联大的风气。”[5]杨振声指导研究生写论文,学生迟迟写不出。杨振声询问缘由,得知学生与他观点不尽一致,怕写出来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完全相同,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6]周礼全 1946年师从金岳霖攻读研究生。在一次学术讨论中,金岳霖提出他的一个哲学理论,遭到周礼全的反驳。金岳霖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礼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岳霖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礼全不甘示弱,也生气地立刻回应说:“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周礼全冷静之后,为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准备等下次上课时正式向导师道歉,但宽厚的金岳霖并未心生芥蒂:“一星期后又上课时,我很紧张地走进金先生的房间。他似乎比平时更亲切地叫我坐下。他不再提上周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我们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金先生又花了一二十分钟时间,非常细致地和非常严谨地进一步陈述他上周提出的那个理论。”[7]
(3)导生进行平等互利的学术合作。季镇淮1941年师从闻一多攻读研究生。1943年,季镇淮写了一篇谈“七十二”的文章初稿,闻一多看完后,非常欣赏这篇文章提出的见解,但觉得还有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于是,他当即中止了自己正在写的文章《庄子内篇校释》,“足足忙了五个昼夜才改写完毕,最后自己又亲手把稿子誊清……”[8]此文在《国文月刊》发表时,闻一多坚持署上三个人的名字(还有一位作者是参与讨论的助教何善周)。“闻、季、何相次而下的作者排名,也凸显了季先生在其间的分量。”[9]此文发表后,大部分语文老师认为很有参考价值,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学界新人季镇淮的名字不胫而走。
2.导生生活中的融洽相处
(1)导生聊天。任继愈1939年师从汤用彤教授和贺麟教授攻读研究生。他回忆说:“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谈学问,也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师生关系十分融洽。”[10]62可以说,内容广泛、形式自由的“聊天”,既是导生生活关系融洽的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导生生活关系融洽的一种典型表现。
(2)导生散步。1943年入学的研究生茅于美,深情回忆起导师吴宓和众弟子散步的往事:“我们师生数人有时走在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上。那街道两边是店铺,没有人行道。车马熙来攘往,挤挤搡搡。先生总是尽量照顾我们。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栏,唤着[张]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到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11]身教胜于言传,无声胜于有声,吴宓通过他亲切、自然的绅士行为,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研究生的人格。
(3)导师请客。阎文儒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攻读研究生。据他回忆,当时文科研究所的导师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予在昆明读书时,文研所负责人学术权威人士,对下乡攻读之研究生,必招入其宅,享以盛餐。”[12]茅于美回忆说,吴宓尽管自身生活清苦,仍会不时自掏腰包,邀约她以及张苏生、俞铭传等研究生下小馆吃便餐:“进店大家落座,由先生点菜。先生一定要问清堂倌某菜价若干,某汤价若干。然后他掏出一支铅笔,在一张店里给的纸片上正楷写上菜单,每盘菜记上价钱,再仔细算出总数。有时算错了,在纸片上涂改,也与改我们的文章那样涂得方方正正的。估量带的钱够了,才正式叫菜。这是我们被邀请吃饭从未见过的,吃毕先生必坚持由他付钱。”[11]如果说,通过“聊天”“散步”,导生从“师生关系”升华到“朋友关系”,那么通过“请客”,特别是通过“家宴”,导生关系则从“朋友关系”升华到“家人关系”。
二、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实质
谈及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当年的研究生任继愈认为,“师生之间朝夕见面,经常交流,有学术的,有思想的,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10]63可以说,“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这一源于切身体验的感悟,深刻、准确地揭示出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实质。也诚如郑天挺先生在193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所畅想和规划的那样,即将恢复的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准备“采取书院精神”:“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13]在后来的办学实践中,西南联大实现了这样的畅想和规划。而从导生融洽相处的种种表现来看,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和古代的书院教育有三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三个方面实质上体现和代表了三种注重人格训练,且朴素、有效,值得普遍借鉴和推广的研究生培养路径。
1.导师注重成为道德表率
西南联大的导师和古代书院的教师一样,严格要求自身言行,努力成为道德楷模。换言之,西南联大的导师之所以深受弟子们尊敬和爱戴,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德行堪称表率,即他们以自己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处处起到榜样作用。如对研究生学业细致入微的指导,是导师敬岗爱业的充分体现;导生平等宽容的学术对话,是导师大气和大度的充分体现;导生平等互利的学术合作,是导师成人之美、提携后学的充分体现;导师自掏腰包请客,是导师宽厚仁慈的体现。一言以蔽之,西南联大的导师是非常纯粹的,他们的学问与人生是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他们的水平可能有高低之分,为人风格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不虚伪、不做作、不功利,能用真面目、真性情、真感情去面对学生。
何兆武认为,“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14]在西南联大,正由于导师们的纯粹,所以他们能够构建一种和夫妻关系一样圣洁的师生关系,从而成为“旧大学”的典范:“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今日,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15]
2.导师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关爱研究生
西南联大的导师喜欢和研究生聊天、散步,经常请研究生吃饭,甚至请研究生到家里吃饭,这与古代书院的教师也是很相似的:“古代书院教师对生徒爱护有加,他们不仅担负授业的重任,还不忘在生活和人生规划上给予弟子们帮助和指导。在生活上,书院教师常常给予弟子周到的关怀和照料。”[16]当然,无论是聊天、散步还是请客,都需要一个客观的前提,就是导生能够“朝夕相处”,而西南联大恰恰具备了这个前提。
西南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诚如何炳棣所言:“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17]151在“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的情况下,导生经常能收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惊喜。
和本科生相比,西南联大的研究生与导师相处的空间更为紧密,这是由于研究生人数更少,加上研究生办学模仿古代的书院,师生得以住在同一个地方,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最初在昆明靛花巷3号共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后来为躲避日机轰炸,又搬到了郊区的龙头村,这两种情况都能为师生朝夕相处创造绝佳的条件,诚如王玉哲回忆的那样:“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如罗常培先生、汤用彤先生和郑天挺先生,大部分时间和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几十个师生每天除了读书之外,便促膝纵谈学问,别无他事。”[18]吴大猷的弟子黄昆也感叹道:“我有很多时间和吴先生住在一起,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研究生向导师学习最好的机会。”[19]
3.导师注重对研究生进行无声的启迪和熏陶
钱理群先生说:“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说,即所谓零距离接触外,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20]115与此相通,在西南联大,正因为导师成为道德伦理具体和真实的实践者,才能让研究生在心理上容易信服他们;正因为导师在日常交往中与学生建立起密切的情感纽带,才能让研究生在心理上容易亲近他们。由此,研究生才以导师为镜,不断审视自身的行为,努力提升自身的学识和人格,朝着理想的学术和人生目标前行。
三、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现实意义
当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往往将赞美和希望寄托于“远方”和“过去”。诚如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所言:“人们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不满,就会构造一个‘非我’来与‘自我’相对立,把一切理想的、圆满的,在‘我方’无法实现的品质都投射于对方,构成一种‘他性’而使矛盾得到缓解。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一定是对方的现实,而是我方的需求。”[21]西南联大作为“过去的大学”的杰出代表,扮演的正是“非我”角色。
应该说,出于映照今日大学(“自我”)不足的需求,我们在不少方面有“美化”乃至“神化”西南联大的地方。可是,就导生融洽相处的表现而言,西南联大的美好又是千真万确的。因此,重温西南联大那些温暖如春的导生相处的故事,最直接、突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现实竖起一面镜子,借助这面镜子,我们要深刻反思当今的导生关系。
钱理群先生谈到书院式教育对今日研究生教育的借鉴意义时说:“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变化的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即使不是这样露骨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20]114-115
当今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导生关系的不融洽,至少说远没有西南联大时期那么融洽。导生关系的不融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导生日常相处的不融洽(或缺乏日常相处,或日常相处方式出现了异化)。何炳棣称西南联大师生的关系是“‘面对面’的师徒关系”[17]156,这种“面对面”主要是通过日常相处来实现的。缺乏日常相处的教学无法真正做到“面对面”,缺乏“面对面”的教学是缺乏温情和温度的教学,构不成真正的教育。要知道,教学的教育性总是以优良的师生交往为基础,再具体点说,教学的教育性一是依托于教学内容,二是依托于师生交往,所以说,“真正的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作为教师,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显现自身作为教师的存在,就是要在真实的师生交往过程中显现教师生命的本质。教师之为教师的价值就是显现在鲜活的师生关系之中”[22]100。这一推论适用于所有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尤其适合于最需要师生日常相处的研究生教育。
无须讳言,与西南联大相比,当今的导生相处“十分融洽”者少,疏远淡漠者多,甚至隔阂对立者也时有出现。当然,导生相处的不融洽,既有研究生的原因,也有导师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既有表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总之,当今导生相处的不融洽,学生要从学生的角度找原因,导师则要从导师的角度找原因。
从表层看,当今导生朝夕相处的紧密空间不复存在,导生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如今大部分导师不仅不像西南联大那样和研究生住在一起,反而居住在校园之外甚至另一个城市,导师下课后就要匆匆搭车或开车赶回家中。一些过着“双城生活”的教师,为了方便,甚至还要求将课程集中安排在自己“最方便”的那一两天上完,以免自己跑来跑去。这样,他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基本不会在校园内现身,研究生想见导师一面有时要难于上青天。从深层看,今日导师缺乏与研究生朝夕相处的心态,通俗地说,导师们太忙,无暇顾及研究生的诉求和感受,导生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们知道,“教育在闲暇中,教育的基础性条件是闲暇,甚至可以说教育即闲暇,年长者与年轻人在一起的自由交流,就构成了教育的基本形式。”[22]35遗憾的是,当今导师们的闲暇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匆忙和焦虑,对此,尚存闲情逸致的戴建业感到无比的惋惜:“我就职的华中师范大学就在桂子山上,每到中秋时节满山丹桂清香扑鼻,可很少有教授和学生赏桂闻香。老师匆匆忙忙上课,又匆匆忙忙回家,他们时时刻刻放不下的是项目、论文、填表,连上课都成了他们的副业,哪还有心思去欣赏丹桂?”[23]吴承学也有同感,他说:“名目繁多的科研、教学项目,各种级别的科研奖励、人才计划等,数不胜数,令人心驰目眩。学术成果就是荣誉,就是地位,就是金钱。现在,已经有一套非常严密和严格的绩效考核体制,项目、论文、人才与评奖、各种会议成为学者生存的主要方式与评价标准。因此,许多年轻学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耗在这些无休无止的俗事杂务之中。但这并不是他们所乐意的。”[24]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当今导师对研究生日常的学术指导变得松懈,导师和研究生亲密的日常交往变得稀缺,类似于“聊天”“散步”“请客”之类加强导生联络和感情的日常互动更是成了奢侈品,所以,陈平原先生才会说:“现在的学生经常抱怨,说,老师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很伤心。我相信,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当面和不当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科技发展了,但传统的‘熏陶’的概念,依然有效。”[25]
反思当今不融洽的导生相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融洽的导生关系。如何重建?其实西南联大导生融洽相处的故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生动、感人、易学的教学案例。今日导师如果能够缓一缓匆忙的脚步,缓一缓焦虑的心情,以西南联大的导师为榜样,先“照葫芦画瓢”,再结合时代特征和自身情况,有所补充和创新,就可以取得不俗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言,无论是从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出发,还是从教育常识出发,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认识到融洽的导生相处是建立融洽的导生关系的基础,认识到融洽的导生关系是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秘诀之一,认识到研究生主要是通过“观”教师的“行”而非“听”教师的“言”,才能真正掌握做学问的意义和方法,才能真正敬畏学问、热爱学问和投身学问。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陈平原认为王瑶当导师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喜欢同研究生聊天:“我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那时没有选课的规定,就是跟导师谈话。三年期间,王瑶先生没给我正式上过课。只是每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聊天。他抽烟斗,因此,我也属于被‘熏陶’出来的。”[25]
实际上,各种西南联大的故事中,涉及本科教育的,通常都会绘声绘色地讲述教师在课堂上讲课的风采,但涉及研究生教育的,几乎没有描绘导师们课堂讲课的场景,更多是深情回忆导师与研究生课外融洽相处的细节。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讲”得如何不是最重要的,“做”得如何才是最重要的;导师“有声”的教导并不是最重要的,“无声”的启迪和熏陶才是最重要的。正可谓“教育是关爱,不是指挥;教育是亲近,不是摆布;教育是介入,不是干预;教育是启迪,不是外加;教育是建议,不是命令;教育是促进,不是安排;教育是辅导,不是取代;教育是交谈,不是唠叨;教育是权利,不是恩赐;教育是欣赏,不是耳提面命;教育是生长,是师生共同的生长;教育是生活,是诗画般的生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