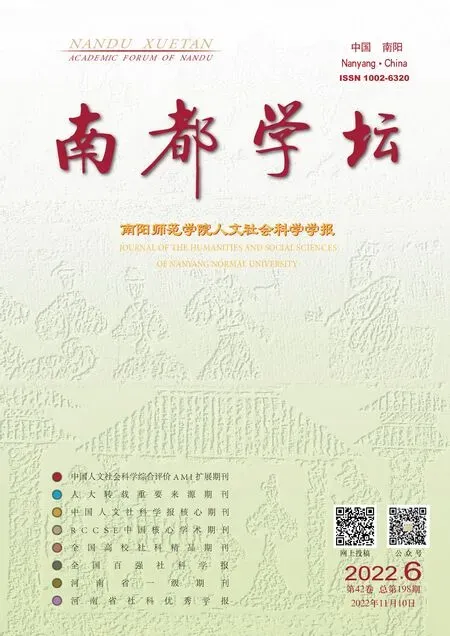秦汉谏诤与舆论
涂 盛 高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谏诤为对他人之过失进行规劝,以求其改正过失。而目前谏诤之通说为:谏诤为臣下对君上过失之进行规劝,以助君主改过迁善。谏诤的对象限定为君主,包括皇帝或称制太后;谏诤的主体一般是百官吏民,极少情况下为非称制太后、皇后、太子(1)目前研究谏诤与舆论的论文或著作较少,主要有:黄宛峰《汉代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环节》(《南都学坛》1988年第3期)认为两汉统治者尤重视民众对地方官吏的毁誉,“举谣言”与“行风俗”的实施,体现汉代统治者重视民意、重视吏治。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了汉代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从一个侧面介绍了汉代的舆论情况。。
谏诤与舆论有密切关联。某些情况下,进谏者为了达到良好的进谏效果,往往收集舆论作为自己进谏言的依据,或者将舆论中发现的问题向君主进言。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长期深居宫中,与外界隔离,为了让自己的施政不脱离现实,亦要体察舆论,从舆情中发现自己过失或者获得良策,从而改进自己施政的不足。
谏诤与舆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曾经从民间意见,如民俗、民谣、民歌、歌谣等中访求得失。《尚书大传·虞夏传·择巡守》言:“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1]西周亦有此制,《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俗。”[2]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风诗”,大部分为民间歌谣,反映民间讽刺怨怒之声。统治者时常派人采择此等歌谣。“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牗户,尽知天下所苦。”[3]可见,先秦统治者对舆情已经有主动意识,派人向下采访,从舆论中寻求吏治得失、民间疾苦,用来改进自己施政的不足。所以,《汉书·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1708
“谏诤的舆论含义是双重的。首先,它本身是特殊形态的舆论,谏诤中陈述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即民意的体现,进谏者从舆论中发现民意所向,从而进谏君主以求为民谋事。其次,谏诤的形式是舆论意见从民间流向君主的必经途径,君主深居内宫与民间隔离,不甚了解民情,重要手段是百官吏民之进言舆情。谏诤的作用方式明显带有舆论特征。谏诤以舆论意见影响君主决策,无任何政治制度的强制性,因而它本身不是政治形式,其作用之发挥完全与君主个人爱好关联。”[5]可见,谏诤虽与舆论紧密关联,但其作用的发挥与君主个人意志、素质、爱好关联,很难对君主形成实质的制约。
一、秦汉时期有关谏诤的舆论形式
秦汉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宽严程度时起彼伏,秦代对舆情管制前期松后期紧,汉代对舆情管制大体较为宽松,只有到桓、灵时期有所紧缩。秦汉时期有关谏诤的舆论形式有:流言、讹言、妖言、谶言、歌谣和谣言等。以下具体述之。
(一)流言
流言“指公开散布、传播言论。‘流言’有时确与虚假、没有根据的言论有联系。但没有根据难于确认的言论,未必等同于污蔑、诽谤”[6]8-9。元帝时宦官石显与大臣周堪、张猛争权,石显等利用自己的权势,在君主和民间传播周堪、张猛的不利言论。故刘向给元帝上书曰:“群小窥见间隙,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4]1945成帝为太子时,其父元帝认为其放纵轻佻,不堪为嗣,屡有立定陶王为太子之意。外戚史丹有宠于元帝,元帝晚年多疾,史丹侍疾,向元帝进谏不应废太子,其依据引用道路流言。“皇太子以适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4]3377哀帝宠幸董贤,屡欲封其为侯,但丞相王嘉屡次封还封董贤为侯的诏书,据舆论之流言来解释原因。“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4]3492以上三则事例皆是大臣引用民间流言来劝谏君主。
(二)讹言
讹言,《辞海》等工具书的解释为“‘诈伪的话,谣言’,‘谣传’,‘虚假、谣传的话’。在汉代,‘讹言类言论’所包含的信息与‘虚假、伪造、荒谬’并无必然联系,却常常带有怪诞妖异的色彩,因时因地变化流动,无根无源,难于证实,却在民众当中广泛流传。”[6]23由于汉代科学尚不发达,迷信思想很严重,对于讹言,上至君主,中至官吏,下至布衣皆信之。汉成帝时,承平日久,社会矛盾积累甚多,民间扰扰不安。建始三年(前30)秋,关内大雨四十余天,讹言纷纷,说京师即将发大水,讹言影响甚大,流传甚广,多方途径,传入成帝耳中,成帝甚至为之下诏,指出京城讹言大水将至。“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4]306-307汉哀帝时,前凉州刺史杜邺被举方正,直言上书指出民间讹言盛行。“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4]3476王莽新朝时,民间曾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天凤二年二月,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4]4139
(三)妖言
吕宗力对“妖言”的解释是:“反常、怪异的言论,就叫做‘妖言’。甚至,对上不敬、不利在上位的言论,都可能被标签为妖言。”[6]7妖言往往是对最高统治者不敬或不利的言论,故最高统治者认为此种言论危害统治秩序,往往加以扑灭。秦设有“妖言罪”,秦始皇曾将某些儒生的言论视为妖言,从而大坑儒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7]258
因秦始皇多年征伐,大兴土木,大修陵寝,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百姓之咒怨,百姓甚至刻石骂之。“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至其晚期,妖言甚多,诛不胜诛,始皇对其亦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游幸的方式来压制。“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7]259
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眭孟认为有布衣升为天子,坐妖言而被诛。“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孟坐伏诛。”[4]1400
(四)谶言
谶言“指以口语或者文字表述的异常言论或者征兆,其中暗藏玄机,以隐喻、隐晦的方式启示天命所归,预言个人或者政权的命运”[6]120。秦始皇虽统一天下,但国家并不稳定,尤其到其晚期,谶言很多,如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7]348。“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7]252汉光武帝即位前,群臣劝进者皆被拒绝,后其太学同学强华奏进《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此谶有汉光武帝“受命之征”,汉光武帝“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8]21。之后欣然接受群臣劝进而即位。
(五)歌谣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民间歌谣即是民间即兴、自由创作的大众文学,也是珍贵的社会政治史料。”[6]91歌谣与流言、讹言、妖言、谶言不一样,流言、讹言、妖言、谶言在一定情况下为统治阶级打击的对象。而歌谣是汉代民众参与时政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担当了社会舆论监督的角色,反映当时社会的民间生态及吏治好坏。在汉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歌谣,一方面他们用歌谣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民间的歌谣,从而能够体察民心所向,以及官吏政绩何如。即使是一般民众也习惯以歌咏抒发心声。正因为民间歌谣具有反映民意的功能,汉代政治思想家普遍认为君主施政必须认真聆听歌谣,尤其是要重视歌谣中的讽刺怨怒之声。
秦亡之后,项羽主导分封,项羽与范增心中疑忌刘邦,负约将刘邦封于蜀地。刘邦的将卒多山东之人,歌思东归。“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7]367汉高祖七年,刘邦亲征匈奴,被匈奴三十万精兵围困于白登七日,情况十分紧急。汉高祖采纳陈平的计谋,侥幸逃脱,但此事并不光彩。当时军中传唱:“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毂弩。”[4]2144这首歌谣,影响非常广泛,反映当时平城之围形势危急。
少数歌谣所述的对象,甚至可以是天子或者太后。此种歌谣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某些行为的看法。
汉文帝弟淮南王刘长骄蹇不法,文帝时曾擅杀辟阳侯,又谋为“东帝”。汉文帝六年其谋反事败,群臣建议按律当斩。汉文帝念同胞之情,不忍置其于法,废其王位,贬逐蜀地,所封之国入于汉。后来民间歌谣讥讽此事,讽刺汉文帝兄弟不和,汉文帝因贪图淮南王地而将其废逐。“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对舆论倍感压力,不禁叹息,最终追尊淮南王以平息舆情。“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7]2144东汉章帝时,其嫡母马太后自称节俭:“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8]411但长安城还是传出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8]853此歌谣实际上讽刺马太后的奢靡。另外,马太后年轻时注重修饰。“《东观记》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9]马太后的服饰及其梳妆引领当时社会的风潮,而马太后自己却标榜节俭,难免不引起时人的讥讽。
二、舆论影响谏诤的主要形式
当然,舆论只能间接影响谏诤,最高统治者通过第三方的形式获取舆论,从而了解吏治得失、民心所向,改进自己的施政方针。
(一)举谣言
“谣言”一词,在汉代的意义,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理解和使用的“凭空捏造”之意,而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本文中,谣言与歌谣通用。舆论形式虽多种多样,但在秦汉国家与社会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谣言。汉代,百姓对于各级官吏甚至君主的政绩和处事,往往通过歌谣的方式表达出来。如琅琊太守陈俊被百姓歌颂,“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8]691。董宣为洛阳令,京师号为“卧虎”,民间歌之“枹鼓不鸣董少平”[8]2490。张堪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8]1100。
谏诤歌谣,即百姓将谣言或歌谣直接告诉君主,或通过官方的途径传至君主,或官方主动采择民间歌谣、谣言。从而使君主能够根据百姓的歌谣、谣言而对各级官吏做出相应的处置,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进谏的目的。东汉光武帝将其制度化,称之为“举谣言”。“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广求民瘼,观纳风谣。”[8]2457“汉光武帝以其个人在基层成长的经验,建立了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核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6]112
采谣言职责本属三公,采择之后,向君主条奏。“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8]2204君主亦可下诏求谣言,东汉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东汉灵帝熹平五年“令三公谣言举事”;光和五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蠡害者”。君主甚至自己可以派遣使者采择谣言,“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8]2717。官方通过多种手段获取谣言,最终汇报给君主,由君主对谣言关涉人员进行处置。
举谣言的目的为了解地方吏治,解决民生疾苦。朝廷对于贪残无道、祸害百姓的官吏往往会进行处置。桓帝时,“诏三府掾属举谣言,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范滂指出这些刺史、权豪之党为民害。“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8]2204处置结果如何,史无明载,无法确定。但上有正直官员的弹劾,下有民众的强大舆论,这些被弹劾的官员当很难安然无恙,即使朝廷做表面文章,亦要处置一批官员。如东汉灵帝时,对于被谣言所举的官员,也会做相应的罢黜。“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8]2431谣言导致其被免职,由刘焉担任益州牧。
举谣言能否顺利进行与朝廷内部政治是否清明有关,“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8]2457。东汉开国初,朝廷非常重视舆论,根据谣言对郡县官进行处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先不讨论此种情况好坏,但建武、永平称为东汉治世,可见此种制度在整顿吏治、监督官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东汉末灵帝时,宦官专权达到顶峰,此时亦举谣言,但却发挥不了舆论的监督作用。“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因主持的官员太尉许戫、司空张济受宦官贿赂且畏其权势,暗地为宦官开脱。“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为完成任务找替罪羊,“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8]1851。根本达不到通过举谣言发现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的目的,反而导致边远地区有政绩官员被“虚纠”,举谣言没有发挥作用。
(二)行风俗
《史记·乐书·序》:“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7]1175简而言之为“博采风俗,助流政教”,引申为行风俗。“何为行风俗,即由朝廷委派‘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的使者巡行州县,观赏风俗之化,考察地方官员为政得失。”[10]行风俗,主要是风俗使采择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歌谣等民间舆论,报与君主,由君主对关涉官员直接处理。一般情况下,风俗使不能直接处置官吏,但风俗使可向朝廷甚至君主进言汇报,君主根据风俗使的汇报,对相关官吏进行处置,这种处置包括对政绩好的予以提升,政绩差的给予降级或者罢黜。风俗使如果有君主的诏令授权,可以对一定级别以下的官员直接处置,一定级别以上的仍要报与君主处置。
王尊与李固之升迁,在于风俗使将其治化良状汇报君主,君主对其予以升迁。“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4]3229“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杜乔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还,拜太子太傅,迁大司农。” 风俗使亦举劾地方官吏,如风俗使杜乔在行风俗过程中举奏地方官员贪污,“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8]2092风俗使雷义“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8]2688。
汉安元年遣八个风俗使巡行天下,“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凡刺史或其他两千石的官员涉嫌贪污的,风俗使报君主处置。“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对于“墨绶以下”的官员,则可行使专断之权,“墨绶以下,便辄收举”[8]2029。此为风俗使出使前君主对其进行的授权。
风俗使者按照君主的诏旨巡行地方,体察风俗,采择歌谣,不能逾越权限,否则君主会给予重罚。如汉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行风俗,矫制而突破权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回京后,被御史大夫张汤劾“矫制大害,法至死”[4]2817-2818。最终被处以死刑。
风俗使除了对地方官吏政绩进行舆论采择外,还可按照君主的要求巡行地方,完成君主交代的其他任务。如汉成帝时,孔光行风俗,“振赡流民,奉使称旨,由是知名”[4]3353。风俗使代表汉成帝存恤百姓,访查吏治,劝课耕桑。“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4]3471
(三)刺史巡行择舆论
汉武帝时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十三州刺史,按照六条诏书指定的授权范围对所巡视范围内的郡守进行监察,即“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六条诏书当中的第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4]742。刺史找寻所巡视地方的“讹言”,换句话讲也就是收集当地的舆论。
召信臣政绩卓著,百姓歌颂,“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采择舆论,发现召信臣政绩卓著,上奏君主,君主对其予以奖励。“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4]3642
(四)谏言者引舆论对君主进谏
谏言者进谏,如单纯就事论事,可能说服力不强。如谏言者能够采择当时的舆论并结合自己的论点而进谏,说服力可以大增。谏言者可通过多种形式采择舆论。首先,谏言者生活在当下,可亲自赴民间采择舆论;其次,可派下属及亲朋赴民间采择;最后,可与朋友、同僚交流中了解舆情。
刘邦被负约封在蜀地,其将卒多山东之人,“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后,韩信向刘邦进言:“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7]367即谏言刘邦利用歌谣当中所反映的思乡情绪,顺势而为,逐鹿中原。刘邦采纳其意见,最终夺得天下。汉高祖亲征匈奴,困于白登,当时军中传唱:“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毂弩。”这首歌谣,影响非常广泛。之后,高祖与匈奴定和亲政策,不再征伐匈奴。到吕后时,匈奴单于遗书谩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议击匈奴。季布指出:“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4]3755吕后接受了季布的意见,平城之歌至少起到一定的作用。即使到汉武帝时,国富兵强,廷议讨论与匈奴的和或战,“主和”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亦指出:“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4]2400用平城之歌主张自己的和亲策略。
汉桓帝永寿年间,梁冀专政,连岁荒饥,灾异屡现。“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而太学生刘陶上言:“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8]1846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举宗室刘瑜贤良方正,刘瑜至京师后,上言:“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连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8]1855刘陶之“听民庶之谣吟”、刘瑜之“听闻歌谣”,皆是引舆论劝谏君主。
三、舆论在谏诤中的作用
舆论在谏诤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反映吏治好坏,反映民间疾苦,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的看法。因此舆论之谏诤作用对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吏治及百姓的穷苦现状。
(一)反映吏治好坏
“汉代地方郡守掌握极大的权力,主要有六个基本而极其重要之权力,第一,对本府官吏有绝对的控制权。第二,对于属县行政有绝对的控制权。第三,对于郡境吏民有向中央察举之特权。第四,对于刑狱有近乎绝对之支配权。第五,对于地方财政有近乎绝对之支配权。第六,对于地方军队有相当之支配权。”[11]权力虽大,监督却不到位。虽说宣帝中兴,但此时已发现郡国守相舞弊之风,“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4]273。汉元帝时贡禹亦指出自武帝以来,地方选人已有不正之风。“(汉)武帝以来,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4]3077。即使中央派出相应的主管部门或监察机构进行巡查,由于当时选人实行察举制,地方属吏与长官之间如君臣关系,往往周旋长官的危难,更逞论举报长官。另外,主管部门或监察机构往往还与地方利益勾结,更难发现地方吏治好坏。此则为官僚监督官僚之制度弊端。但通过舆论监督,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权力制约的弊端,可一定程度上发现地方吏治的好坏,通过舆论监督弥补权力监督的不足。
冯野王、冯立兄弟先后担任上郡太守,为民兴利,境内政治清平,百姓安康。上郡之百姓讴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4]3305天子闻之,冯立被升迁为东海太守。酷吏宁成,对上对下均酷急,“为小吏,必陵其长史;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吏民惧怕宁成之暴,号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7]3145。舆论上闻汉武帝,最后宁成还是被抵罪。
(二)反映民间疾苦
汉代国土面积广阔,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多数地方离京城较远,民间的疾苦很难反映到君主那里。通过舆论,即君主派遣特使巡视各地采择舆论,可以了解百姓的疾苦。有些歌谣流传面广,君主自己就能听闻。通过舆论了解民间疾苦后,君主在施政过程当中,多少会调整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民生。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哝胡。”[8]3281这是汉桓帝时期大规模汉羌战争的写照,反映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百姓生活困苦。由于史料匮乏之原因,此条难于展开论述。
(三)反映民间对最高统治者的看法
秦汉时期,君主掌握最高权力,为最高统治者。君主一方面从制度上被神化;另一方面被周围的御用文人美化。体制内可能无法直接表达对君主的不利评价,但是体制外的民间,无论当时环境是否险恶或者社会管控宽严与否,民间还是敢于直接表达对最高统治者的不同于体制内的看法。
秦始皇虽雄才大略,但为政十分残暴,时天下经过统一战争,急需休养生息,而秦始皇不顾民力,大肆开边,大兴土木,大修陵寝。百姓怨气冲天,体制内不敢进谏,而民间却敢于表达。秦始皇后期,黔首刻石骂之,“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秦始皇虽因传言大兴杀戮,大力镇压,如黔首刻石咒骂事,秦始皇“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但是对于层出不穷的民间妖言以及其所代表的的民心舆论,最后不得不默然。妖言“今年祖龙死”由使者讲述于秦始皇之后,秦始皇也不过是“默然良久,曰,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也,并言,祖龙,人之先也”[7]259。对于舆论已经是无可奈何。
东汉桓灵时,宦官、外戚专权,政治黑暗,百姓生活困苦,民间有歌谣讽刺咒骂最高统治者。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这是一首强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歌谣。“城上乌,尾毕逋”者,直指桓帝“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人主好聚敛,自然群下迎逢,盘剥百姓以为己之升迁资本,故百姓直接咒骂桓帝当死。“‘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桓帝)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8]3282,讽刺灵帝母董太后之聚敛。
四、局限性
汉代统治者施政一定程度上采择民间舆论,但有野心的政治家往往伪造民意或诡称民意,用舆论为自己造势。王莽“篡汉”所采取的是和平手段,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即派遣风俗使去全国各地采风俗,证明己之施政良善,为取代汉朝奠定舆论基础。“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4]4204汉平帝元年,王莽遣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4]359。风俗使主要的职责是,“宣明德化”,即将王莽治国的政绩向全国各地传达,“专行诛赏”,指对异议之人进行镇压。“采择歌谣”,即将天下歌颂王莽的歌谣采择回京。八使回京后,“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4]4076。舆论没有显现民间疾苦、吏治好坏、民间对统治者的不同看法,反而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变成王莽篡夺权力的台阶步骤。
即使民意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但民意往往很难掌控,对于励精图治的君主,民意可能会被过分利用。而对于昏庸的君主,民意往往被打压。
东汉光武帝生长于民间,创立“举谣言”制度,此制度对于发现民意、体察民情有重要意义。但是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出现不少弊端。光武帝为雄才之主,吏事精美。但“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说明光武帝过度相信舆论,单凭舆论而不进行深入的核实调查就改换守长,助长舆论喧哗之声,导致舆论往往没有反映实情。“论议之徒,岂不喧哗。”引起官员过分惧怕舆论,做很多表面的工作,反而有害于治化。“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8]1141-1142
对昏庸之主而言,舆论作用根本无法发挥,“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8]1996。在昏主之朝,要举行舆论监督很难,往往被“邪枉者”阻止。因“邪枉者”往往是舆论批评对象,为了不让舆论上达天听或者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他们往往要阻止舆论监督。
即使举行了所谓的舆论监督,也因有群小在内,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派当时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来主持其事,但两人皆为胆小怕事之徒,对宦官子弟不纠举,“承望内官,受其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为了完成任务,找替罪羊,“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导致当地的吏民诣阙陈诉。虽经过司徒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但结果“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曹操“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8]1851。舆论监督成为一纸空文,不但不能发挥监督作用,反而导致正直官员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