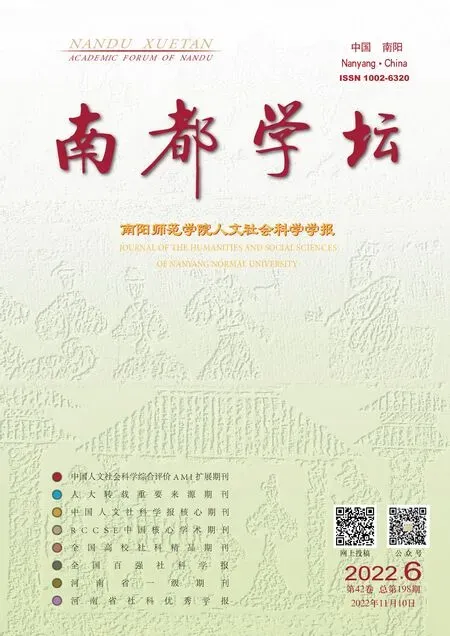汉代“男耕女织”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翟 麦 玲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农业经济形式,也是家庭劳动中男女分工的一种模式。对于男耕女织,传统看法是男子承担农田劳动,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从事纺织,处于从属地位。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吴承明、李伯重、于琨奇、李根蟠、彭卫等都有相关论述(1)吴承明《论男耕女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认为,个体农户耕织紧密结合是封建社会后期用棉时代的事。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指出,十六、十七世纪明代,江南许多地方农家男女同耕同织。到清代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但夫妇并作的模式尚存在。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文中认为,秦汉时期大多数妇女并不纺织,所需衣物从市场上购买。李根蟠《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文中认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程度与范围远不如后世,不同地区存在不平衡性。彭卫《汉代女性的工作》(《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一文指出,“男耕”与“女织”也并非截然对立。。前辈学者对“男耕女织”的论述侧重点、观点虽各有不同,但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男耕女织”应重新认识。鉴于汉代的“男耕女织”问题,目前尚未有专文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传世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从性别的视角探讨汉代 “男耕女织”模式中各阶层妇女的角色与地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汉代对“女织”与“男耕”同样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与纺织业都起源于妇女。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男子逐渐成为农田劳动的主力。甲骨文对“男” 字的书写从田从力,即是很好的说明。而纺织则因需要更多的技艺与韧劲,也就成了女性的专职。《商君书》:“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57可见这种分工在神农时代已经形成。
中国古代虽一直以农为本,但纺织却一直受到宫廷的重视。春秋时期,管仲在建议齐桓公给精通蚕事者以重要奖励时就说:“民之通于桑蚕,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2]57墨子也说:“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3]284可见重视蚕桑的原因乃蚕桑可使民富国强。
汉代,农桑并重依然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如中央的农桑令大都农桑并提:“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4]125,“朕亲耕,后亲桑……欲天下务农蚕”[4]151。据统计,《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中类似诏令有45次之多。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时也确如中央政策所言。如西汉的黄霸在颍川“务耕桑”[4]3629;龚遂在渤海“劝民务农桑”[4]3640。东汉的王景在庐江“教用耕犁”“训令蚕织”[5]2466;童恢在不其“耕织种收,皆有条章”[5]2482;刘宽在南阳教民“种柘养蚕”[6]324;崔寔在五原“为作纺绩、织纴、练缊之具以教之”[5]1730;茨充在桂阳“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5]2460。
在汉代朝廷重视及牛耕技术的推广下,汉代耕织结合的经济区域逐步扩大,男耕女织成为家庭经济的两大来源。“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4]1128,说明汉代女织支撑起了经济的半边天。
二、农田劳动中有各阶层女性的参与
“男耕”并不意味着女子就此退出了田间劳动。汉代文献资料及近年来发现的画像砖、画像石中的农耕图,则可以很好地说明汉代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先看文献记载中各阶层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情形。
1.小农家妇人在田间。与夫一起耕耘:东汉逸民庞公“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5]2776。蜀人廖立被废为民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7]998。丈夫在家,妻子一人赴田间:东汉逸民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嚗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5]2768。妇到田间为夫送饭:汉末,常林为诸生,性好学,常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7]659。寡妻与子去田间: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植,以给供养”[5]1760,可见小农家妇女从事田间劳动非常普遍。
2.婢女在田间。有学者认为汉代奴婢多从事家务劳动,很少下田干活。其实,汉代奴婢从事田间劳动也是普遍现象。如汝南地主李叔坚家“儿婢皆在田中”[8]349;豪强地主田庄“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5]1648。此外,江陵凤凰山167号、168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不少手持农具的女俑。可见汉代婢女从事农业生产不足为奇。
3.地主家或地方小吏的妻子在田间。地主夫妇一起耕作:西汉杨恽失去爵位返回家乡后,“身率妻子,勠力耕桑”[4]2895。《四民月令》是东汉崔寔所著农书,其中在提到劳动者时,虽没明确指出他们是奴婢、用人或雇工,但从上下文意可以推断出地主的妻子与儿女应是与他们一起劳动的。至于地方小吏的妻子则是独自在家务农:高祖为亭长,“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9]346。东汉魏霸为巨鹿太守,“妇亲蚕桑,子躬耕”[10]426。司徒史鲍恢到司徒司直王良家,见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5]933。汉代官吏工作时期一般都居于官府,妻子居于家中。而汉代官员俸禄不高,所以妻子需要从事农耕来分担养家的责任。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农耕图中也可以看到多个田间劳动环节中女性的身影。
1.播种。成都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中,两男子手持锄头边刨坑边后退,两妇女弯腰往坑中下种。甘肃嘉峪关新城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一农妇在前播种,一农夫在后打土块[11]36、一男子在前驱牛耕地,一女在后播种[11]34。
2.锄地。山东黄家岭画像砖上一男扶犁耘耕,一男操耙耱地,三个妇女在锄地。汉代春耕祭祀仪式中也有“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12]702的环节。
3.往田间送饭。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除了男子耕耱外,还有一妇女挑着担子带着两小孩朝田间走,及大树下一人持杖而坐的画面[13]24。持杖者可能是监工,送饭女子可能是地主家的奴婢。河南南阳七里园乡出土的画像石:下层一农夫头戴尖顶冠,手持长柄锄为禾苗除草壅土;右端一农妇,梳髻着襦,肩扛一锄,锄柄端系一水罐,锄根部挂一篮状物,招呼耘田者喝水用饭[13]30。农妇扛锄,说明她送完饭后还要锄地。
4.收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7]725,描述的是男女共同收割的情形。东汉桓帝时的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14]93,讲的是男子服兵役后,收割庄稼都由女性来承担。
5.麦场上碾打。嘉峪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男的持杈扬场,女的抱麦子[11]33、一农妇持连枷打场[11]36。
可见,女子参与农业劳动在汉代是很普遍的现象,正如《氾胜之书》区种法条载:“丁男长女治十亩”[15]43、“大男大女治十亩”[15]47。可见“男耕女织”的提法给了人们理解上的误导。
三、“女织”由各阶层女性承担
在汉代,耕田是男女共同的事,但纺织则是女性的专职。汉代纺织分官营、私营两种。官营又分京师织室和地方服官两大部分。私营则包括私人作坊生产与家庭纺织两种。
1.官府作坊中的官婢纺织。西汉京师长安的东西织室是“主织作缯帛之处”[4]90,年“官费五千万”[4]3070。齐郡设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4]3070、“主作天子之服”[4]286。蜀郡设有锦官。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16]。蜀锦西汉时已经非常有名。扬雄《蜀都赋》:“尔乃奇人,自造奇锦。”[17]东汉时蜀地的“女工之业,履衣天下”[5]535。官府织室的费用和产量反映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这些女婢的工作很重要,一般不可随意赎取。
2.官僚、地主家的妇女纺织。《四民月令》:正月“命女红趣织布”[18]2、六月“命女红织缣练”[18]68。“女红”应该指地主家的妇女与婢女。汉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14]36该诗虽然是在夸耀豪门的天伦之乐,但对大妇、中妇的纺织描写,无疑是对妇人勤劳贤惠孝顺品质的赞美。《机妇赋》:“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揽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19],则是对贵族妇女纺织时曼妙身姿的歌颂。
再看史书中对官吏夫人纺织个案的记载: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4]2652。张安世勤俭持家,穿的衣服是其夫人亲自纺织制做。东汉巨鹿太守魏霸“妇亲蚕桑,服机杼”[20]2343。曹操的丁夫人归家,曹操来见,“夫人踞机如故”[7]156。孙权的赵夫人纺织技艺高超,“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京中谓之‘机绝’”[21]。可见,纺织这种妇功美德也被贵族妇女所崇尚。然也有反对其妻亲织者,如鲁相公仪休,“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9]3102。这种个别反对的现象,也恰好说明汉代官僚地主家妇人纺织已是一种普遍状况。
再看汉代画像石中官僚地主家妇女纺织的情形。
江苏铜山的一块画像石:刻有四位妇女,有的纺线,有的织布,梁上悬有四轴纺线。坐在织机上的妇女正转身接抱另一妇女送来的小孩[13]55。图下方是屋内两人坐榻上交谈,屋外有刚卸的豪华车马。
江苏沛县的一块画像石:左边一织女坐在机上织布,中间一人抱一婴儿递给织女。右边一妇女正坐在纺车前纺线。旁边挂有络丝用的篗等纺织用具[13]53。
山东滕县的一块纺织、垂钓画像石:上层刻画的是众宾客登水榭观看垂钓的场面;下层刻画的是一组家庭纺织场景,左方一人坐于织机上织布,织机架上吊一放纬线的布兜,其身后一妇人领一婴儿观看,中部一人坐于纺车旁纺线,其上方悬挂两轴纺线[13]60。
上述三块画像石上的纺织图,从房屋、周围场景及有小孩在场等因素分析,应该是地主家的妇女或婢女在纺织。妇女纺织图被搬上画像石,反映了汉代社会对纺织女性的赞美,或是对理想女性的一种追求。
3.私营纺织作坊中的女工纺织。《西京杂记》:“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22]从文中记载分析,陈宝光的妻子应该是纺织作坊的经营者,其雇佣不少女工,不然她们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高端的锦和绫供贵族消费。在汉代,雇佣劳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手工业领域都有雇工,而且女子外出做雇工也不足为奇,这就为私营作坊雇佣女工提供了条件。
下面的画像石有可能反映的是私人作坊中女工纺织的情形。
山东滕县的一块画像石:左右两侧分别搁置一台斜织机,各有一名妇女坐于机架上织布,其旁均有一人观摩。中部有两人分别在纺线和络丝。右侧一女工正将缠绕在地上三角框上的丝缕,通过屋檐下的悬钩,悬缠在手中的篗子上。左侧一女工一手握丝在纺车前摇纬,丝线上穿屋檐悬搭至纺车[13]61。这幅画刻画了私人作坊中络线、摇纬、织丝一系列工序流程。
江苏邳县博物馆藏的纺织画像石:右侧刻一脚踏板斜织机,一妇女坐在织机上编织布帛。其上方悬有几轴纺线。另一人坐在纺车前络线。下方有一绕纱器,一人在前举手操作[13]54。绕线器是调丝工具,可见图中女工从事的是丝绸纺织。
江苏铜山的一块庄园纺织画像石:屋内有一脚踏提综斜织机,一织女坐在织机前转身与纺纱女交谈。待纺的丝一端结系在纺车的铤子上,纺者一手摇纺,一手握丝,丝的另一端穿过檐下的横杆,下垂成两段。纺车右方为一络纱女,其前放着一个由三根短箸搭成的三角形架。丝的一端绕在箸上,其上端也穿过檐下的横杆操握在女子的手中,这是女子在调丝,门口有两女子走来[13]57。这可能是东汉大田庄丝绸纺织作坊分工协作的场景。
4.小农家妇女的纺织。“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4]1121,讲的是冬天的晚上,小农家的妇女为了省照明费一起夜织的情形。“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2]539,反映了齐、襄妇女人人都擅长织锦绣。庐江府焦仲卿之妻刘兰芝是织布能手,“十三能织素”“三日断五匹”[14]73。崔寔把中原纺织技术传到五原郡后,民得以免寒苦,说明五原的妇女也基本学会了纺织。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女性的脚下放置一副带杆纺轮,可见,东汉时新疆妇女也在从事家庭丝织。
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部有两妇女在织机上操作,其织机与民间散存的织机类似[13]62。安徽萧县一画像石:“中层,一女子站在纬车前,左手摇纬,右手引线,扭头窥看身后一男子与织机上的织女热吻。”[23]江苏沛县留城的一块画像石中也有一妇女席地而坐,正在纺纱的图景。
汉代女性不仅仅从事纺织,纺织前后的采桑、养蚕、缫丝、印染,纺织、刺绣、裁衣等一系列工序,也都由女性承担。很少见汉代男性从事纺织的。但明清以后男性从事纺织行业就比较常见了。
四、家庭女织的收入多于家庭男耕的收入
汉代的女织产品,无论来自官府作坊、还是私营作坊或地主、小农家庭,剩余产品都会投入市场。尤其是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畅通以后,纺织品市场比粮食市场更为广阔。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粮食价格,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都存在差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要对家庭女织和男耕收入做大致比较,就需要一个普遍状态下的参照物。《九章算术》描述的社会生活主要是西汉宣帝以后,其中反映的物价、粮食产量等,除了兵荒马乱灾荒年份外,基本上通行于汉。所以,以下比较中涉及的产量、价格等就以《九章算术》为主。
先看家庭女织的收入。
汉代织品的价格有种类与品质之分。根据《九章算术》中的数学题可知:一匹缣472-512钱[24]99-78、一匹素500钱[24]100。其中缣是双经双纬的粗厚的丝织物,素是无色无花纹的丝织品。
女子纺织的速度,学者经常引用《九章算术》中这条记载:“今有女子善织,日自倍。五日织五尺,问:日织几何?”[24]89这道题是说女子丝织技术速度日进,第五天达到熟练程度以后可以1日织2.531尺。这样1月可织76尺,即7.6丈,1.9匹。1匹按最少472钱计算,1个女子1个月可以收入896钱。《西京杂记》载,陈宝光妻“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陈宝光妻技术高超、从事高端产品,所以一个月创造价值5000钱,相比普通女子的896钱,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也可以和汉乐府中记载的女子织布速度做比对。汉乐府《上山采蘼芜》:“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14]71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14]73。诗中新妇、故妇、刘兰芝的织布速度分别大致为1日1匹、1.3匹、1.6匹。若按其中最低速度1日1匹,1匹472钱的价格计算,1个女子1个月的毛收入可以达到14160钱。当然文学作品中的女织速度不排除有夸张的成分。
再看男耕的收入。
汉代的主要农作物有麦、黍、菽。据《九章算术》,其价格分别是:一斗麦4钱;一斗菽3钱;一斗黍6钱[24]310。汉代10升1斗,10斗为1石,即1石麦40钱,1石菽30钱,1石黍60钱。
对汉代亩产的认识,学界虽然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认为汉代亩产2石比较客观。一个自耕农家耕种的土地一般在10到100亩之间,中等自耕农不过70亩。这样中等自耕农家庭1年粮食产量大约140石。按每石50钱,则中等自耕农一家一年农耕收入才7000钱。其中还包含家里妇人及其他人的劳动。
如果说7000多钱是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那么一个男子一年治田可以收入多少呢?《淮南子》:“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25]可见一个男子一年种田10亩,亩产4石,一年最多可以收获40石(2)汉代亩产因土地质量,灌溉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有1石、2石、3石的,4石算是高产。。1石按平均50钱计算,则一个男子一年农耕可以收入2000钱。
所以,无论是一个男子一年耕田收入2000钱,还是一个家庭一年耕田收入7000多钱,和一个普通女子一个月至少可以收入896钱都是不能相比的。
当然了,男子在农闲时也可以外出佣工。汉代佣工的价钱因工种、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九章算术》:“今有取保一岁,价钱二千五百”[24]102,这个佣价应该具有普遍性。这和汉平帝时官府给出的佣价“顾山钱月三百”[4]351也比较吻合。所以一个男子一年的农业收入加上佣工收入应该有4500多钱。而普通女子一年纺织理论上可以收入10752钱,如果考虑到疾病等不测因素折半计算,女子一年还有5000多钱的收入。即使这样,男子创造的收入还是没有女子的高。
如果家里男子是地方小吏,一个月也只有几百钱的收入,还是不能和家里妇人创造的收入相比。所以在焦仲卿的母亲要求他休妻时,其对母亲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14]73。言外之意就是家里收入主要靠妻子,娶到善织的妻子是他的幸运。但如果一个家庭的男子为地方长吏,那他一个月的俸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26],合计3000钱,则比普通妇女织布的收入要高,但仍比不上私营女作坊主一个月可以有5000钱的收入。当然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
汉代家庭女织创造的经济价值高于男耕,一方面与女子勤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4]1121有关;另一方面和汉代农产品与纺织品的比价有关。秦时一石粟与一匹布的比价是1∶1.8;西汉前期,粮食与细布的比价是1∶6.4;东汉初居延地区一石麦与一匹帛的比价为1∶10;甘肃玉门地区粮食与布帛比价为1∶16[27]。可见,从秦到汉,纺织品价格一直在直线上涨。《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28]225织品昂贵,女织地位可见一斑。
汉代女织创造的财富,不仅为家庭,也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汉代税收包括租、赋、税三大部分。租是按田亩征收谷物和刍稿,赋是按人和户征收货币,税是按照行业征收的杂税。汉代租轻赋重,而且粮食价格远远低于织品价格,所以家庭的赋税支出,包括人头税、户税及成年男子为免役而交的代役税,也即更赋,很大一部分就落在女织上。如果说秦的算赋主要针对女性征收,汉代的赋钱主要用于国家军事开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汉代女性虽然很少出现在军事前线,但前线的供给主要靠后方的女性输出。
五、余论
汉代的生产结构、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虽然可以用“男耕女织”来概括,但这并不表明女织处于从属地位。相反女织在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与其贡献不协调,则在于古代男权社会礼制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