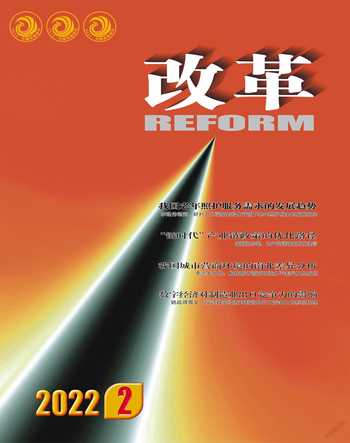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与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
李建伟 吉文桥 钱 诚
我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预计2022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上升,老年人口规模、空巢老人规模、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高龄老人比例正在迅速提高,老年照护服务需求正在激增。发展好老年服务业,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必需的照护服务,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共享发展的重要内涵。当前,我国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效益不高、人才队伍短缺等问题仍很突出,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常态化的准备仍不充分,尤其是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发展缓慢,专业护理人才供给不足,职业能力建设不到位,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与未来深度老龄化和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快速发展的形势不匹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带来的老年照护服务新挑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口深度老龄化和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多元化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切实做好护理人才中长期培育发展规划,不断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满足广大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多层次照护服务需求,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仿真模型及其参数估算
合理预测人口结构及老年人口发展趋势,是研究养老服务业护理人才需求的基础。人口预测可分为宏观仿真和微观仿真两大类型。宏观预测模型是将人口细分为若干类子群体(比如按单岁或5岁分组的人口数),以子群体为单位进行加总测算。微观仿真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代表性样本(比如1‰或1%),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所抽取样本个体的生育、死亡、婚姻、迁移和家庭状态变化等过程进行模拟,从而汇总得出人口的总体特征和分布特征。
考虑到数据特点,本文采用宏观仿真方法预测人口的总量、结构和趋势。通过分别预测生育率和死亡率,建立不同年龄人口迭代方程,预测人口、老年人口和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规模趋势。其中,模型的数据来源为国家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对照参考了已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在实际估计城市、镇、乡村人口结构变化时,需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建伟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其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但在人口普查数据中缺少经济因素数据,在实际预测分析中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影响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包括收入差距、生活成本、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多方面,收入差距是主要因素,只要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综合收益(包括收入、生活成本、社会保障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收益)大于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收益,乡村劳动力就会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鉴于未来较长时间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从业收入还会持续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未来劳动力还会持续从乡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并通过农村育龄妇女向城镇转移改变人口在城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分布。
在经济因素和人口流动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决定未来人口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的关键因素是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与一般人口模型将生育率和死亡率作为外生变量给予假定赋值不同,本文在估计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时利用指数模型进行趋势外推估计其未来发展趋势,其原因是我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均表明我国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呈现较强的内在规律性,这比其他人口迭代模型仅对这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进行简单假定要更为科学。
综合上述因素后,假定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内在趋势方程为:

其中,Y是2010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Y是2000年的育龄妇女生育率,α为生育政策等外部因素对生育率的调整因子,β为经济因素等理性选择对生育率的影响因子。生育率调整因子α大于1,意味着生育率提高;影响因子β小于1,则表明生育率呈下降趋势。
人口死亡率由生物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卫生条件等多方面决定。这些因素在理论上可以予以考虑,但实际预测中由于人口普查数据缺乏相关指标,很难进行量化分析。我们用指数模型将这些因素抽象为影响因子β,主要考虑就是我国死亡率呈现较强的内在规律性。人口死亡率内在趋势方程为:

其中,S为基期死亡率,S为第一期死亡率,α为死亡率调整因子,β为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因子。死亡率调整因子α大于1,意味着死亡率提高;影响因子β小于1,则意味着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引致死亡率下降。
根据模型,分别估计不同年龄段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等式参数,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同时,根据模型,分别估算不同年龄段城市、镇、乡村人口死亡率等式参数,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分城乡低龄和高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参数估计

表2 分年龄段死亡率参数估计
利用我们构建的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进行预测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规模的峰值大约出现在2023年前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持续加重。在生育政策对后期生育率具有长期影响的情况下,镇的育龄妇女生育率算术均值将保持在高位,从2017年的56.50‰平稳提升到2050年的58.64‰,但城市和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均值仍将保持下降趋势,分别从2017年的32.82‰和55.50‰下降到2050年的14.57‰和31.52‰。城市男性和女性人口死亡率算术均值分别从2010年的37.97‰和33.99‰下降到2050的16.40‰和11.10‰,镇男性和女性人口死亡率算术均值分别从2020年的40.44‰和35.53‰下降到2050年的17.49‰和16.81‰,乡村男性和女性人口死亡率算术均值分别从2010年的53.71‰和42.94‰下降到2050年的37.40‰和22.10‰。根据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趋势估计,可以预测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征及基本趋势。
二、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向深度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快速发展
从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快,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空巢老人规模大幅度攀升,城乡老龄化分化日趋严重,城镇老年人口规模扩张快于乡村、占比不断提高,但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养老负担明显高于城镇,且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根据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模拟预测结果,2022年我国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将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老年抚养比还会快速攀升,空巢化老人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城乡老龄化分化趋势还会持续加重。
(一)我国人口正在快速走向深度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速度正在加快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根据WIND资讯宏观数据库提供的各国人口数据,1980—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变。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0年的8 821万人上升到2020年的1.91亿人,20年时间规模增加了1.15倍;老年人口增速也远高于上述五国,同期法国、瑞士、美国、英国和日本老年人口的增幅分别只有41%、47%、54%、32%和64%。人口快速老龄化使我国迅速成为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91亿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4.9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54.2%。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老年期,200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当年老年人口增加规模和增速分别从2000年的142万人和1.64%上升到2020年的1 297万人和7.30%(见图1)。

图1 1991—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增加规模(万人)与老年人口增速(%)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也明显加快。2003—2020年,我国高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规模从1 447.3万人增加到3 580.1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5.82%,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从13.4%提高到18.78%;同期低龄老年人口(65—69岁)规模从4 251.6万人扩大到7 400.6万人,年均增速为3.52%,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从39.4%下降到38.82%;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规模从5 091.5万人扩大到8 083.89万人,但年均增速只有2.9%,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从47.2%下降到42.4%(见图2,下页)。

图2 2003—2020年我国低龄、中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万人)及其构成(%)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仍将保持快速上升趋势,2022年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运用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进行的模拟预测分析表明,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人,老龄化率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27亿人,8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4 403万人,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将提高到19.4%。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人,老龄化率将提高到20.5%,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5 964万人,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将提高到21.2%。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率将分别提高到3.46亿人和25.8%,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比将分别提高到8 483万人和24.5%。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和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分别达到4.49亿人和1.75亿人,老龄化率和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将分别提高到37.3%和39%(见图3,下页)。

图3 2020—2050年我国分年龄段人口规模(万人)变化趋势和老龄化与高龄化程度(%)
(二)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空巢化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抚养比也大幅度上升。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计算,我国老年抚养比从1990年的8.3%缓慢提高到2000年的9.9%后提升幅度加大,2008年提高到11.3%,此后提升幅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大幅度提高到19.68%。根据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模拟预测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测算,预计2025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3.9%,超过少儿抚养比(23.1%),2035年和2050年老年抚养比将分别提高到40.3%和66.7%,少儿抚养比将分别下降到15.8%和11.9%,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社会抚养负担的主要因素(见图4,下页)。

图4 1990—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率、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及其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家庭小型化、年轻子女与老年人异地分居现象日益普遍,老年夫妇户和独居老人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口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空巢(只有一对夫妇和独居老人)规模从2000年的2 339.7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 150.0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从26.5%上升到34.9%;其中城市空巢老人比例从30.9%上升到39.1%,镇空巢老人比例从29.9%上升到35.7%,乡村空巢老人比例从24.5%上升到32.7%(见表3,下页)。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第四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空巢老人比例为51.3%,其中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为51.7%。另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8年进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2018年全国空巢老人比例为49.02%,城市、镇和乡村老人空巢比例分别为53.48%、47.44%和48.09%。未来,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队列,老年家庭空巢化特征将更加明显。基于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的老年人口预测数据,按照2015年和2018年民政部与北京大学抽样调查空巢老人比例的均值50%估算,到2025年我国空巢老人规模将达到1.13亿人,2035年和2050年会分别增加到1.73亿人和2.25亿人。空巢化老人规模的持续扩大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带来巨大冲击,未来社区、机构养老助老服务需求会快速扩大,对专业护理人才的需求也会迅速扩大。

表3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空巢化情况(人、%)
(三)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养老负担明显高于城镇,城乡老龄化分化日趋严重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持续流向城镇,这种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在推动我国非农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城乡常住人口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城乡持续人口流动的影响,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且分化日益严重。2000年乡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为7.5%,城镇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只有6.1%,到2018年乡村老龄化程度已提高到13.8%,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仅为10.6%。根据人口迭代宏观仿真模型预测数据,2019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7年乡村老龄化程度将超过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和205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分别提高到33.4%和53.2%。未来城镇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将持续快速上升,但始终低于乡村老龄化程度。预计到2025年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到14%,比乡村晚6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34年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到20.6%,比乡村晚7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城镇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上升到31.2%,比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低22个百分点(见图5,下页)。

图5 2000—205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抚养比及其发展趋势(%)
我国城乡人口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以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意味着农村年轻人口流向城镇后仍会承担起生活在农村的老人的养老负担,但城乡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分化走势,也意味着乡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远比城镇更为复杂、严重。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意味着乡村人口老年抚养比更高,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代际平衡关系比城镇更不平衡,乡村社会养老负担更为沉重。2000—2020年,乡村常住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已从11.2%提高到28.13%,同期城镇老年抚养比仅从8%提高到14.64%,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要比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养老负担高50%左右。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乡村老年抚养比还会持续大幅度提高,与城镇老年抚养的分化会日益严重。预计乡村老年抚养比将从2018年的20.7%持续提高到2025年的30.7%、2035年的58.2%和2050年的127%,即到2050年乡村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1.27个老人的养老问题。城镇老年抚养比也会持续上升,预计从2018年的14.4%持续提高到2025年的19.6%、2035年的30.1%和2050年的50.7%。乡村与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比率也将从2018年的1.44倍不断提高到2025年的1.57倍、2035年的1.83倍和2050年的2.5倍。面对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养老负担日益不平衡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乡村老年抚养比的持续大幅度上升,未来乡村养老问题仅依靠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是难以承担的,以农村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持续,社区与机构养老将成为乡村老年人口养老的必然选择。
(四)城镇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占比持续提高
随着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持续转移,我国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也快速扩大,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快速提升。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分别为2 940万人和5 881万人,到2006年分别增加到3 443万人和6 976万人,这一时期城镇和乡村老年人占比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33%和67%左右。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到2017年城镇老年人口首次超过乡村老年人口,到2019年增加到9 569万人,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也持续提高到2019年的54.1%;乡村老年人口规模也持续扩大,到2019年增加到8 152万人,但乡村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到2019年降为45.9%(见图6)。

图6 2000—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和城乡老年人口规模(万人)及其占比(%)
三、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演变特点与发展趋势
人的生命周期大致经历健康稳定与健康衰减两个时期,老年人处于健康衰减期。随着年龄的提高,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逐步下降,产生失能半失能的概率会不断上升。2000年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也不断扩大,预计我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及其比例将从2020年的4 563.6万人和17.11%持续上升到2030年的6 952.6万人和17.44%、2050年的12 606万人和22.06%。
(一)我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演变特点
为从有限的数据资源中探查老年人口失能演变规律,我们对2010年城市、镇和乡村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城乡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有四大演变特点:一是城市、镇、乡村老年人在各年龄段的失能、半失能比例依次上升,即各年龄段乡村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情况比镇老年人严重,镇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情况又比城市老年人严重。这一特点表明,不同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很大,城镇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较低,是因为城镇老年人的医疗条件、物质生活和健康意识比农村更好。二是城乡之间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的差距会随着年龄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如乡村与镇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的比率从60—64岁年龄段的1.32倍下降到100岁以上年龄段的1.04倍,镇与城市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的比率从60—64岁年龄段的1.49倍下降到100岁以上年龄段的1.11倍。这一特点表明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对低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远大于对高龄老年人的影响,尽早缩小城乡健康服务差距或尽早提升乡镇老年人健康服务水平与质量,对降低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至关重要。三是城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提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60—64岁城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提升幅度较小,65—84岁城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提升幅度趋于逐年加大、呈加速提升状态,85岁以后城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提升幅度趋于下降,其中城乡半失能老人占比在90岁以后趋于下降(见图7、图8、图9)。四是城镇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会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城镇老年人生活保障较好、失能半失能比例相对较低,城镇化程度提升会降低整个社会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而高龄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远高于中低龄老年人,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必然会提高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

图7 2010年不同年龄段全国、城市、镇、乡村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及其相对变化(%、倍)

图8 2010年不同年龄段全国、城市、镇、乡村失能老人比例及其相对变化(%、倍)

图9 2010年不同年龄段全国、城市、镇、乡村半失能老人占比及其相对变化(%、倍)
(二)我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的发展趋势
从模拟预测结果来看,我国城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规模从2010年的2 984.6万人持续扩大到2015年的3 729.1万人、2020年的4 563.6万人、2030年的6 952.6万人和2050年的12 606万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比例从2010年的16.8%下降到2015年的16.43%,此后持续上升,到2020年提高到17.11%,2030年提高到17.44%,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22.06%(见图10)。

图10 我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模拟预测结果(万人、%)
分城乡来看,城市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扩大最快,从2010年的495.6万人扩大到2015年的667.3万人、2020年的876.9万人、2030年的1 520.9万人和2050年的3 690.4万人,失能半失能比例2010—2015年变化较小,平均为10.72%,2015年以后持续上升,从2015年的10.71%提高到2020年的11.18%、2030年的11.93%和2050年的16.62%。
镇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从2010年的475.3万人持续扩大到2015年的620.5万人、2020年的786.3万人、2030年的1 289.7万人和2050年的2 647.9万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从2010年的14.86%下降到2015年的14.83%,此后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15.66%、2030年的16.1%和2050年的22.4%。
乡村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最为庞大且不断扩大,从2010年的2 013.8万人持续扩大到2015年的2 441.3万人、2020年的2 900万人、2030年的4 142万人和2050年的6 268万人,失能半失能比例在从2010年的20.28%下降到2015年的19.89%之后,将持续攀升到2020年的21%、2030年的21.68%和2050年的27.12%。
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主体是半失能老人,2010年半失能老人达2 459.4万人,占失能半失能老人的82.4%。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半失能老人规模将持续扩大,到2020年增加到3 720万人、2030年增加到5 601万人、2050年进一步增加到9 541万人,占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比例将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81.5%、2030年的80.6%和2050年的75.7%,半失能老人在从2010年的13.85%下降到2015年的13.47%之后,将上升到2020年的13.95%、2030年的14.05%和2050年的16.7%(见图11)。

图11 我国城乡半失能老人规模和半失能老人占比模拟预测结果(万人、%)
城市、镇和乡村半失能老人规模都将持续扩大,但乡村半失能老人规模最大,到2030年将增加到3 420万人、2050年增加到4 959万人,城市和镇半失能老人规模增长相对较快,到2050年将分别扩大到2 566万人和2 016万人,分别是2010年的6.7倍和5.2倍,2050年乡村半失能老人规模仅是2010年的2.9倍。
城市、镇和乡村半失能老人比例2010—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分别从2010年的8.32%、12.23%和16.95%下降到2015年的8.25%、12.13%和16.57%,2015年以后均恢复上升趋势,到2030年分别上升到8.97%、12.96%和17.9%,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11.56%、17.06%和21.46%。
相对半失能老人规模,失能老人规模相对较小,却是护理服务需求的刚性群体。从模拟预测结果来看,2010年我国乡村、镇、城市和全国60岁及以上失能老人规模分别为330.6万人、84.3万人、110.3万人和525.2万人,失能比例分别为3.33%、2.64%、2.38%和2.96%。2015年乡村、镇、城市和全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增加到406.6万人、113万人、153万人和672.6万人,失能比例分别为3.31%、2.7%、2.46%和2.96%,与2010年失能比例变化不大。2020年乡村、镇、城市和全国失能老人规模将扩大到489.2万人、147万人、207.6万人和843.8万人,失能比例分别提高到3.54%、2.93%、2.65%和3.16%。在2030年人口结构达到超级老龄化时,乡村、镇、城市和全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增加到721.8万人、251.7万人、378.1万人和1 351.6万人,失能比例将分别提高到3.78%、3.14%、2.65%和3.16%。到2050年失能老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1 308.9万人、631.6万人、1 124.7万人和3 065.2万人,失能比例将分别提高到5.66%、5.34%、5.07%和5.36%,城乡老年人口失能比例则趋于接近(见图12)。

图12 我国城乡失能老人规模和失能老人占比模拟预测结果(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模拟分析得到的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5年失能老人比例均低于全国老龄办的抽样调查结果,但变化趋势相同,均呈下降趋势。我们模拟分析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略低于全国老龄办的抽样调查估计规模,2012年、2013年和2015年分别少334万人、339万人和334万人。考虑到我们的模拟分析结果本身已经存在高估成分,全国老龄办的抽样调查数据可能对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存在更大程度的高估。
(三)我国低度、中度、重度失能老人规模及其结构的发展趋势
不同失能程度老人对照护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别。按照民政部颁布的行业标准,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人员配置标准相当于轻度老人的3倍。在失能老人占比不断提高、失能老人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不同失能程度老人的发展趋势,对研判老年护理服务需求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按照洗澡、穿衣、移动身体、如厕、吃饭、在房间内外移动六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国际通用标准,国内学者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的失能程度作过不少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基于全国老龄办抽样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CHARLS数据作出的分析,如陈泰昌基于全国老龄办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是,我国城乡老年人重度失能比例从2000年的0.5%逐步提高到2006年的0.7%、2010年的0.8%和2015年的1.3%,中度失能比例基本稳定在0.3%,轻度失能老年人口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8%下降到2006年的5.4%、2010年的5.2%和2015年的2.3%。我们对这一结论的准确性有较大疑问,重度失能比例高于中度失能比例、2015年轻度失能比例出现巨大幅度下降,有违老年人失能状态转移的基本规律。周晓蒙、刘琦基于北大CHARL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没有呈现明显的线性变化趋势,基本围绕四年均值上下波动,他们对老年人分年龄段失能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与老年人失能状态转移的基本规律更为吻合(见表4)。
综合国内关于老年人失能程度的研究,我们采用周晓蒙、刘琦关于2002—2011年我国老年人失能程度的均值作为预测,分析我国失能老人结构变化的基础(见表4),假定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失能程度结构保持不变(见表4失能老人构成),根据我们模拟预测的失能老人规模数据,对未来老年人失能程度及其规模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轻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456.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724.9万人、2030年的1 148.7万人和2050年的2 489.8万人,中度失能老年人口从2010年的48.4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83.7万人、2030年的142.4万人和2050年的397.7万人,重度失能老年人口从2010年的2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5.1万人、2030年的60.6万人和2050年的177.7万人。受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影响,轻度失能老人在失能老年人口中的占比趋于下降,从2010年的86.98%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85.91%、2030年的84.99%和2050年的81.23%,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老人占比不断上升,分别从2010年的9.22%和3.8%提高到2020年的9.92%和4.16%、2030年的10.53%和4.48%、2050年的12.98%和5.8%(见图13,下页)。

图13 2010—2050年我国不同程度失能老人规模及其构成模拟预测情况(万人、%)

表4 2002—2011年我国城乡老年人失能程度与失能老人构成(%)
四、我国老年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
照护服务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需”,即使生活能够自理的健康老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护理服务需求。随着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老年照护服务需求规模也将不断膨胀,对专业护理人才的需求也会快速扩大。
(一)我国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
全国老龄办进行的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乡60岁及以上老年人需要提供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从2000年的6.6%上升到2010年的13.7%和2015年的15.3%,其中城市和农村老年人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从2000年的8%和6.2%上升到2015年的14.2%和16.5%,60—79岁的中低龄老年人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从2000年的5.1%上升到2015年的11.2%,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从2000年的21.5%上升到2015年的41%。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与老年人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表明,2015年生活自理老人只有11.9%的需要照护服务,92%的失能老人日常生活需要照护服务。老年人潜在照护服务需求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生活条件和照护服务的可获得性。比较2010—2015年城乡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和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2010年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13.7%)明显低于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比例(16.8%),但2015年需要照护服务老年人比例(15.3%)已与我们分析得到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16.4%)接近。按92%的失能老人需要照护服务粗略估算,2015年需要照护服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占老年人的比例为15.1%,与15.3%的抽样调查数据基本吻合。据此判断,2000—2015年需要照护服务老年人比例的上升,主要原因是生活条件改善,老年人的潜在照护服务需求日益显性化。按照这一趋势,未来我国城乡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将随着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的持续上升和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迅速扩张。基于社会保障应保尽保的原则和托底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服务需求的需要,考虑到健康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健康老年人也需要提供必要照护服务,我国需要照护服务老年人的比例要比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更高,即到2025年我国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比例和规模低限是17.1%和5 630万人,到2030年将分别上升到17.4%和6 950万人,2050年会进一步分别上升到22.1%和12 606万人。
(二)我国老年人护理人才的需求发展趋势
提供老年人照护服务所需要的护理人才与老人护理模式密切相关。目前,老年人所需照护服务主要由家庭成员、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主体提供,其中传统的家庭成员照料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模式。从全国老龄办第四次抽样调查情况来看,94.6%的城乡失能老人由包括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在内的家庭成员照料,由医疗护理机构和养老机构照料的仅有1.3%,由家政服务人员照料的占3.9%。从老年人自身所期望的护理模式来看,89.9%的失能老人更愿意选择在家里接受照护服务,自愿选择到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老人只有4.5%。基于老年人照护服务的现实需要,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实施“9073”的养老模式,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料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9073”模式的提出符合当时社会状况和老年人照护需求,但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城乡居民家庭的小型化和“421”家庭(4位老人+一对夫妇+1个孩子)的普遍化,由家庭成员提供老年人照护的护理模式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对有一个以上失能老年人的“421”家庭,一对夫妇难以承担在兼顾工作的同时照料失能老人和孩子,对有中度、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维持家庭照护更为艰难,中度与重度失能老人护理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特别是重度失能老人需要一对一的照护人员配置,一对夫妇难以承担起重度失能老人高质量的照护服务,家庭护理模式会对重度失能老人家庭生活质量造成重大影响。基于我国特殊的“421”家庭结构,未来由家庭成员提供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家庭护理模式占比会不断下降,由社区、家政、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提供照护服务将成为日渐重要的老年人护理模式。
老年护理模式由以家庭护理为主向以社区(家政)与机构护理为主的转变,对老年专业护理人才的需求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缺乏能够准确反映老年护理模式转变趋势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对家庭护理占比的下降趋势作出准确估计,只能按家庭护理占比分为90%(基准方案)、80%(低托底方案)、50%(中托底方案)、20%(高托底方案)四种情况,对未来老年护理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在四种分析方案中,我们将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均视同为机构护理,对由机构护理的老人,护理人员按照半失能1∶17、轻度失能1∶8、中度失能1∶5、重度失能1∶3配置。据此估算的老年护理人才需求结果如下:
在90%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护理、10%由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机构照护的情况下,机构所需要照护的半失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372万人和84.4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560万人和135万人,2050年进一步上升到954万人和307万人,照护服务机构需要配置的护理人员将从202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2.2万人、2050年的101万人,其中照护半失能和失能老人需要配置的护工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21.9万人和11.9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32.9万人和19.2万人、2050年的56万人和45万人,每年需要净增加的护工人数将从2020年的1.3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2.2万人和2050年的2.6万人(见图14,下页)。

图14 基准方案下2010—2050年1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机构照护所需配置的护工规模(万人)
从1979年开始政府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55—1961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大约1.2亿人)已进入老龄状态,随着这批人年龄的增长、失能半失能程度的上升,独生子女家庭的照护负担不断升高,机构照护需求将快速增加。假定80%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仍由家庭护理,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机构照护比例提高到20%,由机构照护的半失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744万人和169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1 120万人和270万人,2050年进一步上升到1 908万人和613万人,照护服务机构需要配置的护理人员将从2020年的67.6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104.4万人、2050年的202万人,其中照护半失能和失能老人需要配置的护工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43.8万人和23.8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65.8万人和38.4万人、2050年的112万人和90万人,每年需要净增加的护工人数将从2020年的2.6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4.4万人和2050年的5.2万人(见图15,下页)。

图15 低托底方案下2010—2050年2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机构照护所需配置的护工规模(万人)
如果进一步减轻家庭照护压力、提高机构照护老人比例,将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护理的比例降为50%,由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机构照护比例提高到50%,未来机构所需要照护的半失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1 860万人和422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2 801万人和676万人,2050年进一步分别上升到4 770万人和1 533万人,照护服务机构需要配置的护理人员将从2020年的168.9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260.9万人、2050年的505.6万人,其中照护半失能和失能老人需要配置的护工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109.4万人和59.5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167.4万人和96.1万人、2050年的280.6万人和225万人,每年需要净增加的护工人数将从2020年的6.4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11.2万人和2050年的12.9万人(见图16,下页)。

图16 中托底方案下2010—2050年5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机构照护所需配置的护工规模(万人)
2030年我国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这是因为1962—1972年生育高峰期(年均出生人口2 732万人、累计2.99亿人)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前后将进入老龄时代。这部分生育高峰期的人口家庭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届时超过7 000万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主要由独生子女家庭照护,老人家庭照护难将是重要社会问题。就提升老年人照护服务水平和质量而言,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机构照护是必然选择。假定由社区、家政、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机构照护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提高到90%,即由社会承担大部分老年人的照护服务,在此情景下,机构所需要照护的半失能、失能老人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3 348万人和759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5 041万人和1 216万人,2050年进一步上升到8 587万人和2 759万人,照护服务机构需要配置的护理人员将从2020年的270.3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417.4万人、2050年的809万人,其中照护半失能和失能老人需要配置的护工规模将分别从2020年的175.1万人和95.3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263.6万人和153.8万人、2050年的449万人和360万人,每年需要净增加的护工人数将从2020年的10.2万人上升到2030年的17.8万人和2050年的20.6万人(见图17)。

图17 高托底方案下2010—2050年90%失能半失能老人由机构照护所需配置的护工规模(万人)
五、积极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老年照护服务发展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我国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照护服务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快速深度老龄化、老年照护服务急剧扩大的难题,应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多元化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切实做好护理人才中长期培育发展规划,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一)顺应社会需求变化,大力发展多元化老年照护服务体系
针对家庭小型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421”家庭照护压力加大等家庭结构变化趋势,考虑到多数老年人更愿意居家养老的传统习惯,应全面推进老年人家庭、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大力支持发展社区助老服务,鼓励家政服务机构向养老照护服务方向发展,鼓励专业护理机构向家庭和社区照护服务延伸,为健康老人居家养老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居家照护创造便利环境条件。
普及完善城乡社区老年照护服务,探索“以老养老”“互助养老”等模式,鼓励健康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完善农村互助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探索构建起面向弱势群体的救助型、圈层化的互助服务供给体系,在有条件的农村扩展互助性的助餐、文化娱乐、面向有生活照护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照护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成立社区基金会,发展社区经济,形成可自循环、可持续的互助性村居共同体。
做好机构养老与照护服务动态需求发展研究,加强区域性养老与照护服务机构发展规划。根据各地区机构养老与照护服务需求发展趋势,各级政府应做好中长期养老与照护服务机构发展规划,统筹各方面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的照护服务。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照护服务,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引导鼓励社会资金建设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非营利、低盈利、公益性、普惠型养老照护服务机构。支持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展养老,鼓励养老机构以需求为导向扩大护理型床位供给,更好满足失能失智老人不同层次的护理服务需求。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老年照护服务。
改革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兜底特困老年人照护服务。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探索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提升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效率。进一步完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三无”老人政府供养制度,强化对失能、半失能特困老人的兜底保障。
完善养老服务筹资体系。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失能老人经济负担,促进养老产业发展。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普适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统一覆盖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等级评定的规范标准,推动长期护理保险标准化、精细化发展。参照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建立健全多主体协同、多层次保障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在强化发展由个人和企业缴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同时,支持发展基于个人自愿原则的商业保险及互助保险体系。探索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护理补贴制度,对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老人,经过评估,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为他们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经费补贴。
(二)立足长远,切实做好护理人才中长期培育发展规划
做好职业护理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全国开设护理专业的高职院校共有506所,但招生规模有限,毕业生人数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养老照护市场需求。从长远发展来看,现行职业护理教育机制难以适应未来规模不断上升的护工市场需求。应在做好照护服务需求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以满足预期市场需求为导向,规划好护理人才动态化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尽快建立起适应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养老照护服务市场需求的专业化养老照护服务人员教育培训机制。
改革办学体制。鼓励职业护理院校面向市场、面向就业自主办学,优化学科和课程设置,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提高职业护理专业办学层次。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健全以学校、企业、养老机构及社区为主体的多主体、多层次、多学科,体现专业性、市场化和应用性为导向的护理人才开发培养体系。健全“中等卫生职业学校—高等卫生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护理继续教育”的现代护理教育体系。
鼓励行业协会、高校举办养老护理中高端人才培训,在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科技助老等重点领域,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示范带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打造中国特色养老护理职教品牌,培育国际一流的中国养老护理职业教育。
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社会化培训。在我国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中,一线护工的缺口非常巨大,单纯依靠学历教育培养的年轻人难以完全填补这一缺口,建议通过建立养老护理员入职补贴和岗位津贴制度,逐步建立依据职业技能等级和工作年限确定服务价格的制度,增强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吸引力。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养培训,依据老人照护工作的不同需求,分层级培养人员,依托职业学校和具备良好带动效应的龙头养老机构及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增加一线养老服务人员的供给,并提高其整体服务水平。
加强养老护理职业标准体系建设,畅通养老护理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完善职业资格评价标准与职称评价体系,加大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力度,建立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职称评价和技能等级评价制度。引导行业协会设置多层次的专业技术岗位,为从业人员打通职业发展通道,实现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打通护士、家政服务人才同养老护理人才开发标准体系,形成人员互通的转型通道,鼓励社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才进入养老护理领域。
强化老年照护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加强老年照护服务人员职业保护,研究出台劳动保护和津补贴政策,提升从业人员工作安全感和幸福感。探索通过设立国家级、行业性表彰,提高养老护理从业者社会地位。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与支持养老护理人员的良好氛围,结合弘扬中国传统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提升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三)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强化早期健康干预,延长老年人预期健康寿命。尽快制定老年人健康干预及评价标准,强化慢性病预防、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有效控制或延缓老年病的发展,延长老年人预期健康寿命,抑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失能半失能比例快速上升势头,减轻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
完善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精神障碍类疾病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机制,针对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和随访管理,为老年人特别是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纾解、悲伤抚慰等心理关怀服务。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基层老龄协会、老年大学等,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自觉主动维护身心健康。
深入推进医养康养结合。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全面深入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活动,从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心理健康、伤害预防、疾病预防、合理用药、康复护理、生命教育和中医养生保健等方面,促进老年人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
大力发展适老化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培育智慧养老与照护服务新业态,提升养老照护服务的效率,减轻服务对人力的依赖,减少养老护理员的人员缺口。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研发可穿戴的老年人健康支持技术和设备,开展远程实时查看、实时定位、健康监测、紧急救助呼叫等服务,大力发展“互联网+老年健康”智慧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