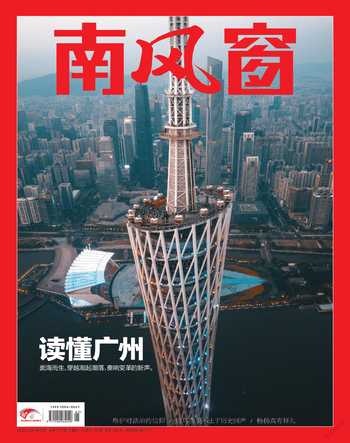拜登,进退失据
雷墨

乌克兰危机的走向扑朔迷离,同样扑朔迷离的还有中美经贸关系。2020年1月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于去年底到期后,中美双方都选择“默契式沉默”——既没有表态协议终止,也没有明言协议延期。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经贸安排就这样带着惯性滑行。这一方面反映出处理中美经贸问题的难度,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近期传出的消息似乎表明,局势的发展难言乐观。
2月9日,美国商会副会长麦伦·布里恩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未履行第一阶段协议购买美国商品承诺的磋商失败,拜登政府将考虑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包括重启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众所周知,以美国的行事逻辑,贸易调查后大概率会是加征关税。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方发出的最为清晰的、能让人联想到贸易战的信号,尽管是以“非官方”的形式。此前,美方官员多次释放“中国未能履行购买承诺”的消息。
早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拜登就曾把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称为“灾难”,认为这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但他入主白宫后,一直维持着其前任的关税政策。如果拜登政府启动对华贸易调查并伴随加征关税,美方不能指望中方会无动于衷,那么中美就有重燃贸易战的危险。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政府对贸易战的担心,远大于加征关税的冲动。不过,“默契式沉默”的时间窗口在缩小。
惯性滑行
2月1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提交了《202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这份报告除了对中国诸多“未履行承诺”的不实指控外,也提及了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并强调其重要性。但该报告通篇未出现“第二阶段协议”的字眼,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走向,主基调是视“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情况而定。除了此前多次谈及的敦促中国改变贸易行为、联合盟友施压,基本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政策方案。
事实上,去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没有“硝烟弥漫”,但也没有出现任何改善。在对华经贸政策上,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政策调整或初步定型的滞后程度,远超包括美国商界和政策研究界在内的预期。这种“无为”的背后,体现的是拜登政府政策雄心与经贸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变成动荡之源,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变化是中美关系质变的表征,而且过程尚未完成。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义”(即战略竞争),如何重构双边经贸关系将是重中之重。但是,鉴于经贸关系兼具竞争性与互利性,以及极强的外溢效应等复杂特征,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始终伴随着矛盾性与举棋不定,客观上呈现的效果就是惯性滑行。
截至目前,中美上一次高级别经贸对话,还是去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财美国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外界普遍预期的后续高级别对话,以解决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到期后的安排,并没有出现。不过据外媒报道,几乎也是在那次通话后,中美一直在较低层级上保持接触与沟通。今年1月13日记者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证实了“双方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沟通还没有产生“可见”的积极效果。中美经贸关系惯性滑行,引起了美国商界的不满。
在美国商界不满的声浪升高的背景下,贸易代表戴琪在去年10月4日的演讲也没有体现出任何新意,总体上可以说是“抽象大于具体”。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关于对华经贸政策的“宣示”,给外界的影响是语焉不详的“打太极”。
外溢效应等复杂特征,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始终伴随着矛盾性與举棋不定,客观上呈现的效果就是惯性滑行。
戴琪那次演讲后不久,《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为“外交糊状物”(diplomatic mush),“无论特朗普总统的对华贸易政策有何缺陷,但至少他有一个政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者爱德华·奥尔登的文章称,评估了几个月拿出来的产品,与其说是政策或战略,还不如说是一个“耸肩”(shrug)——他们真的不确定该怎么做。而且,进入2022年,拜登政府的这种惯性滑行,依然在继续。
政治逻辑
作为外界眼中的政策高手,拜登政府为何在如此重大的政策议题上反映如此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验再丰富的团队,也扛不住挑战接踵而至造成的“系统过载”。很少有人会怀疑拜登政策团队的专业和经验,但这些与能否高效地解决现实问题不能直接划等号。除了国内问题堆积如山、政治内耗,拜登政府所面临外交难题,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让其手忙脚乱。稍远一点的有阿富汗撤军、法澳潜艇风暴,近期的乌克兰危机更是让其政策团队极限承压。
此外,团队内部分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决策圈内为争夺政策主导权而较劲,是美国政府里永恒的故事。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边打边谈”期间,曾多次上演过争吵的剧情,以“团结”示人的拜登政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以经贸议题为“责任区”的耶伦和戴琪,倾向于与中国接触沟通;而从外交、战略视角看待问题的布林肯和沙利文,更热衷于对抗施压。经贸问题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不可能与整个中美关系联动。
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拜登政府乃至整个美国政治圈将经贸议题政治化,以政治而非经济逻辑来思考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华经贸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外交糊状物”,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国内强势的反华声浪,极大地压缩了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空间,导致其更倾向于从“政治逻辑”而非“经济逻辑”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
在经济逻辑上,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0年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谁为美国关税买单?》的研究报告,结论是关税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商影响微乎其微。该智库2021年9月发布的题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分析贸易战以来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变化(逼外资企业离开中国),以及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提升作用(逼工作岗位回流美国),结论是“没有效果”。
毫无疑问,取消关税属于“经济理性”,但拜登政府在乎的是“政治理性”。戴琪发表政策演讲后,《金融时报》评论道:“等了几个月没拿出什么东西,方法本质上还是特朗普的延续,这或许就是美国政治现实的反映。”这篇分析指出,政治上看这种现状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民主党担心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丢掉众议院和参议院,所以废除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和取消对华关税都不可行。
从中美双边角度来看,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模糊不清”,在于其政治雄心太高,导致政策很难落地。同样是把中美关系确定为战略竞争关系,特朗普的政策行为简单粗暴且毫无章法,拜登极力想展现技高一筹。细化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充分反映了拜登政府的这种意图。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塑经贸关系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延伸。但经贸关系的独特性,决定了战略竞争框架下的“三分法”,很难奏效。
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在香港、新疆、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发难,这属于对抗;两度派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赴华,想的是合作。所以,在这些领域,拜登政府的政策相对“清晰”。但是,即便从美国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都兼具“竞争、合作、对抗”的特点,很难划出清晰的界限,而不是“战略竞争”所能定性的。这是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贸关系本身的属性,拜登政府的政策意图,也增加了调整的难度。这个意图,就是重塑中美建交以来的经贸关系。拜登政府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在不切断经贸联系的前提下(因为事实上也做不到),弱化双边的相互依赖性;从多边层面抵消中国经济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拜登所说的“美国必须赢”。
压力增大
根据美国商务部2月8日公布的数据,2021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1.1万亿美元,再创历史纪录。其中,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是3553亿美元,仅次于2018年的4182亿美元。不难想象,这样的数据很可能刺激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也可能成为经贸上对华施压的“论据”。美国的贸易调查一般会持续数月,根据这个时间轴,如果拜登政府近期启动对华贸易调查,结果的出炉的时间,很可能撞上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
选举期间经贸议题的政治化无疑会进一步升级,客观上压缩拜登政府的决策空间。所以是否迈出启动贸易调查这一步,拜登政府一直比较谨慎。2月1日,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在一次视频会议上,一方面称中国未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的购买承诺,另一方面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她说:“说实话,这些对话并不容易。这些对话非常困难。但你知道,从我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我们正在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将是一如既往地诚恳。”
在经济逻辑上,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对于中美对话的细节,双方都比较谨慎,没有过多地向媒体透露。彭博社2月14日援引熟悉该事务的美方人员的话称,拜登政府正在評估中方是否会做进一步让步,并认为可能性不太大。根据该报道,拜登政府在对下一步措施做决定前,会让磋商继续下去。以美国的外交风格,能单方面解决的问题,是不太可能“诚恳”对话的。在经贸问题上,虽然美方官员多次声称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但工具箱里真正能用的并不多。
中国与世界以及美国的经贸现实,是拜登政府重要的压力之源。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目前中美两国针对对方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分别是20.7%和19.3%,分别是2018年7月贸易战爆发以前的2.6倍和6.2倍。所以有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经济都在“适应”贸易战。该所学者尼古拉斯·拉迪分析称,2019年全球的外来直接投资剧降了2/5,但进入中国的外资却逆势增长了10%,达到2120亿美元,他的结论是,与美国推动的“切割”相反,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在加深。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去年8月的一份研究报告,则从跨国企业动向的角度论证了“脱钩”根本没有发生。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数据,离开中国的跨国企业在总数中的占比,从贸易战前两年的7.08%,增加到了2019年的11.42%。但在同一时期里,在华跨国企业的总数,从257404个增加到了308569个。其中,在华的美国企业数量,从16141个增加到了16536个。该研究的结论是,尽管跨国企业担心地缘政治风险,但美国政府制造出来的“风险”,并没有逆转经贸趋势。
某种程度上说,拜登政府的压力,也是自我催生的结果。摆脱压力,需要从正视现实开始。正如2月1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所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希望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打压措施,为双方扩大贸易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