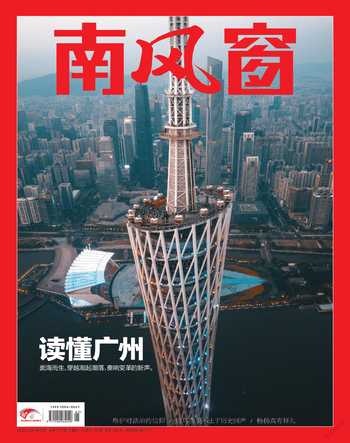渠岩: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是艺术
何国胜

“前卫”和“传统”,这两点在渠岩身上都适用。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却致力于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的传统事业——乡村建设。
一百年前,梁漱溟和晏阳初等致力于乡村改造,试图以此拯救中国。一百年后,渠岩接续这一历史脉络,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探索乡村复兴的艺术路径。而这一投身,就是整15年光阴。时间也交了答卷,15年来,一南一北,渠岩收获了两个成功的乡村建设案例。
山西太行山腹地的许村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村,艺术彻底改变了这个古老村落的面貌,也激活了它的古老生命;广东佛山顺德的青田村,从当时“最没有希望”的村子,成了当地乡村建设和传统岭南乡村风貌的典范。
这当然不是孤立的成就,它像是一个药引子,也像是一处药方,给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治疗方案”。
渠岩想做到的是:改变一直以来人们对乡村的那种充满现代化鄙夷的问题眼光,让乡村恢复成充满道德礼俗、精神信仰和完整历史的美好生活场所,并批判那些打着乡村建设的旗号却只做“乡村美容”之类表面工作的行为。
而这一切,都要从渠岩本人讲起。
想进入艺术史,先离开
渠岩,1955年出生在江苏徐州,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中长大。这样的成长经历带给他时时保持反思和批判的自觉,而这也是他作为当代艺术家的底色。
给渠岩做一个具体的身份归类是比较难的。当下,他是广东工业大学的特聘教授,掌舵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但另一重更重要的身份是当代艺术家(当代并非指时间,而是指当代艺术这一艺术类别),这也是渠岩更为看重的身份。
但要想再往下细分他的身份就难了,不像有的艺术家叫作摄影艺术家、油画艺术家、雕塑艺术家等。1985年从山西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渠岩的艺术创作和理念一直在转向、跨界,他曾先后是油画艺术家、摄影艺术家、装置艺术家……直至今天的乡建艺术家,而正是这种艺术创作的流动,使得对渠岩的具体身份归类变得“吃力”。
大学毕业初,渠岩就投身于中国现代美术新思潮运动,史称“85新潮”美术运动,倡导独立自主的创作精神。彼时,“当代艺术还处于地下半地下,它是边缘的,(但敢于)挑战主流”。渠岩告诉南风窗记者,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当代艺术被国内和国际接受,也受到资本的青睐。他们那一批穷艺术家靠自己的创作,改善了自己的经济境况。
1992年,渠岩到捷克布拉格工作學习了5年。那是重要的5年,它涂抹了渠岩的思想底色、塑造了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也是他之后不断转向、跨界的思想动因。这种影响是他在布拉格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东欧知识分子,他的精神力量非常强大,有独立的人格,不会被权力和资本裹挟,始终有一个独立的批判精神,还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渠岩说,在布拉格他还发现了中外艺术家的区别:“中国艺术家多是从技艺出发,但他们(东欧艺术家)是从思想出发,从观念出发,就是说他们的艺术家首先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艺术家的思想底色。”
1997年回国后,渠岩发现中国当时的当代艺术已经被资本和权力裹挟,丧失了独立性、先锋性和批判性。“收藏家喜欢什么,他们就画什么,不是根据社会问题来创作作品,而是根据市场来生产作品,就跟房地产一样,不是为了住,而是一个金融产品,艺术也变成金融产品。”渠岩说,还有人迎合国外收藏机构“东方主义”的喜好,专门生产该类艺术品。
2000年初,渠岩难以忍受当代艺术丧失问题意识的现状,从彼时的美术圈出走,转向了摄影。当然选择摄影只是因为创作工具的需要,他坚持的是艺术应该关心和介入社会问题的初心。
选择摄影只是因为创作工具的需要,他坚持的是艺术应该关心和介入社会问题的初心。
6年间,他创作了“人间三部曲”——《权力空间》《生命空间》《信仰空间》,直指当时农村的突出问题——基层权力、农村医疗和精神信仰。创作初期,摄影圈和当代艺术圈都将渠岩排除在外。摄影圈觉得他的摄影过于空洞、简单,当代艺术圈觉得那种摄影算不得艺术。后来,这些作品的批判价值被发掘,摄影圈和艺术圈又争着拉他入圈。
可渠岩一转身又弃了摄影。他发现不少人又开始跟风,又开始以艺术市场需求和流行理念来生产作品,而这是他所批判和厌恶的。这正如他自己所言:“你要想进入艺术史,就要先离开艺术史。”渠岩就是不断地离开艺术的主流,离开艺术史已经纳入的艺术形式和创作理念,用自己的问题意识、批判性不断创作有价值的当代艺术来进入艺术史。
抢救一个你们看不上的村子
让他进入艺术史的正是他已经深耕了15年的艺术乡建。2007年,渠岩因在山西晋中和顺县拍过作品,被当地政协主席邀请去他老家许村看看,希望渠岩在那里办个艺术工作室。这一看就开启了他到如今15年的艺术乡建之路。在许村他从跟村民一起捡垃圾开始改造村子,三四年后他靠着自己资源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举办了“第一届许村国际艺术节”,并一直持续了下来,每两年一届。
每一届,渠岩都会邀请20个艺术家到许村创作,10个国内的,1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凭借着艺术节的影响力,每次都会吸引成千上万游客到来。而这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许村的知名度。使得许村从“隐居”于太行山的小乡村,变为国际知名的艺术乡村。
2013年,由于在许村的成功,广东工业大学邀请渠岩成立了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学校领导希望他在广东地区也做一个乡村建设的项目。两年后,顺德区领导邀请渠岩到当地做乡村建设。当时虽然应承了下来,但渠岩心里有疑虑。尽管之前没去过顺德,可他知道那地方是个“经济巨兽”,现代化的进展可能早已将传统乡村挤兑殆尽。
2015年12月,渠岩动身去考察顺德乡村。当地官员带着渠岩走了好几个村子,可没一个入他的“法眼”。他见到的不是被现代化破坏的村子,就是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模板旅游村。一连几天下来,渠岩没有看到他认为的真正的乡村,心中已有了放弃的想法。在顺德的最后一天,陪同他考察的一个当地官员见他有些失望,就小心地问:“老师你到底想看什么样的村子?”渠岩看他真诚,就说:“我想抢救一个你们都看不上的村子,一个在你们眼里毫无价值的村子。”

该官员想了想,面露微笑说:“我知道老师想看什么样的村子了,走,跟我到我的家乡青田村看看,青田村就像你说的那样,落后和破败,没人光顾和搭理,没准你会喜欢。”到青田一看,渠岩大喜过望,“青田呈现出了特殊的岭南地域风貌。传统的线索清晰可见,历史的遗迹有迹可循”。老榕树、小桥、围绕村庄的水系、家宅、庙宇、书院、祠堂以及随处可见的土地神信仰,这些都跟岭南传统乡村匹配上了。在渠岩的新书《青田范式》中,他如此记录了与青田村的相遇。
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传统村落,渠岩满心欣慰。同时,上述官员告诉他,青田之所以能完整存续,是因为它离城镇远,且交通不便,幸免于加速的现代化车轮之下。渠岩也由此想到,“在乡村礼俗社会崩塌的今天,假如没有重新建立乡村道德秩序,只用经济发展的模式开发乡村旅游,以村民致富的方式来谋求发展,就算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但不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存留的问题和矛盾、不恢复传统乡村的道德伦理体系,这类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会带来自我膨胀和物欲横流的后果”。
他见到的不是被现代化破坏的村子,就是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模板旅游村。
本着这个理念,针对青田的改造抑或拯救开始了。
青田九条
广东很多村在行政建制上属村,可没有乡村的模样,走进去全然一副城镇样貌。青田没有城镇容貌,单是一副纯正的乡村“脸”。车越接近村子,老房、鱼塘、宗祠,这些乡村元素就不断闯入视野之中。
进入青田,村口一座桥,桥两侧数珠老榕树。桥右侧一方池塘,塘内一池荷花,只是在冬日,全是枯荷。池塘北边是千石长街,干净平整,街旁宗祠和关帝庙香火依旧,村子东西两处的更楼依然矗立。
村内九条巷子依次排开,有些人家门墙挂一小盆花,门前有亲水台阶。村东河道处有竹制篱笆,两侧的现代式新房围着中间的传统旧居。以前的老蚕房成了青田乡建的展览馆,无人居住的旧宅也成了青田学院。这是现在的青田村。
乍一看,它的变化似乎不甚显著,尤其是在你没有见过之前的青田情况下。而这恰是渠岩的精巧之处——在不改变村子原貌的情况下,对乡村进行深度的改造。因为他着力的不是“美容”之事,而是乡村中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与各种“对象”的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人与灵魂的关系、人与圣贤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的关系、人与农作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富裕关系。这些关系则对应了青田村最为重要,也是每一个乡村最有价值的地方——宗族凝聚、乡规民约、血脉信仰、生态永续、民艺工造等。
渠岩将此总结为青田范式,也叫作“青田九条”。他们的乡建团队花了一年时间对青田村的历史脉络和民俗文化进行搜集整理,对村落形态和建筑遗存勘测整理,作为青田复兴的基础。破败的旧书院、关帝庙和宗祠得到了修复,连同它们一起修复的是耕读传家的传统忠义礼信的信仰、老旧的传统民居也被修旧如旧,消失已久的成人礼——烧番塔被重新复活、现代化下水系统和水系治理盘活了村内原已污染没有生气的“死水”……

青田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渠岩为了让村民认识到水对青田的重要性,花了不少心思。其中,他邀请著名艺术家吴高钟做了《一口口水》的行为艺术。参与者站在青田河道边,用塑料软管将河水吸进嘴里,再将嘴里的河水吐进一个玻璃试剂瓶中,直至装满500毫升的玻璃瓶。“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异常考验大家,因为河道水质的污染,自然会让参与者的心理产生抗拒。”渠岩在《青田范式》中提到,这让参与者清醒地认识到水污染的危害和保护水的重要性。
青田没有城镇容貌,单是一副纯正的乡村“脸”。车越接近村子,老房、鱼塘、宗祠,这些乡村元素就不断闯入视野之中。
这一系列想法和實践也正是渠岩对艺术乡建的理解:“艺术乡建就是运用当代思想的启蒙,找回失落的民俗,再续历史的文脉,激活乡村的肌体,链接村民的情感,让古老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使自然环境恢复其原有的灵气。”
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
乡村建设早有传统,于渠岩而言,他的艺术乡建既传承了百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又融入了当代艺术的精髓——敏锐地发现社会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而这区别于现有的也是主流的两条乡村建设道路——国家治理和经济开发。
这两条道路,前者是政府推动的整理手段,“它始终把乡村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对象来介入治理”。渠岩说,现代化的思维导致人们总以一种有问题的眼光看待乡村,它是相对于城市的先进、文明而言的落后、愚昧。所以,它总是要被治理、改造。
后者是只以增加收入和盈利为目的开发方式,鲜少顾及乡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经常是推倒那些没有文物价值却有历史文化价值、承载乡愁的建筑,建造批量雷同的的民居和基础设施,或者是直接按照城镇的模样生硬改造。
渠岩认为这两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找准乡村建设问题的核心,甚至于没有搞清楚农村和乡村的区别。在他的观察和实践中,乡村相对最重要的问题是“天地人神都垮了,道德伦理崩溃了”。且这种问题的负面效应不止出现在乡村,还外溢至城市和更广泛的地区。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根在乡村”,渠岩说,乡村道德礼俗的崩溃导致人没有了道德约束,也就失去了敬畏感。而这样的问题通过建房子搞开发是无法解决的。

另外,混淆农村和乡村的概念,使得多数人建设或改造者,找不准乡村价值的核心。“农村是个生产单位,它对应工厂,工厂不管生活、信仰、礼俗道德,概念来源于苏联集体农庄,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生产粮食,提供给革命和城市,把其他功能给取消了。”渠岩告诉南风窗记者,乡村则是个更丰富的概念,“乡村是血脉家园,是天地人神共同建构的,它不光有生产,还有生活、信仰、伦理、秩序河道德”。
混淆农村和乡村的概念,使得多数人建设或改造者,找不准乡村价值的核心。
而解决这些问题,渠岩觉得艺术是比治理和开发更好的方法,也是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但这条路在乡村的顺利铺就,并非是易事。乡村的复杂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地方性的系统和文化对外来改造者是一种挑战。在15年的乡建工作中,渠岩探索出了一套他检验过后行之有效的方法——多主体在地实踐。
多主体正是对应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它包括:村民、新乡贤、当地政府、艺术家等。只有平衡好各主体间的利益、观点,各主体共同发力才能推进艺术乡建。因着这个方法,渠岩又总结出在进行艺术乡建时的四种身份——启蒙者、谦虚的在地学徒、各种关系的协调者和日常政治的战士。
四种身份对应着四种工作,启蒙者着重对当地官员和政府的启蒙,让他们明白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学徒主要向当地村民学习,掌握习俗、禁忌和历史;协调者则是在各个主体间充当桥梁,化解意见的对立;日常政治的战士便是跟乡建过程中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点斗争。
渠岩乐于跟人分享自己的乡建经验,但他从未奢望自己的经验成为乡建的“万金油”和乡建问题的“特效药”,“我只能像医生一样,给你号脉找出你到底是什么病,但能不能治好,不是完全我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