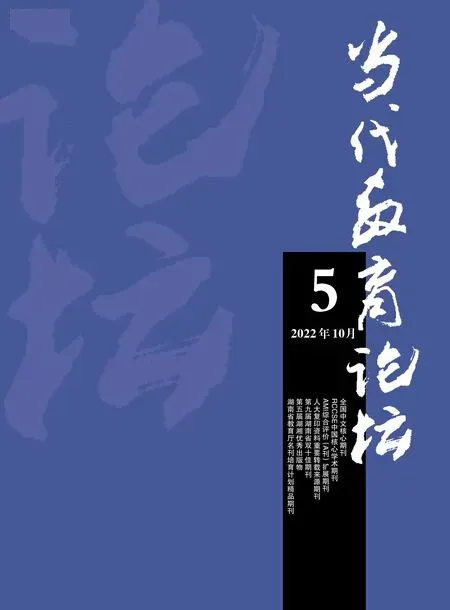古典诗词音乐化及其美育功能研究*
王 胤 沈文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中国古典诗词凝聚了历代盛世的精华,融合了众多贤才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华彩乐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传达的讲诚信、持正义、守民本的核心理念经久不衰;它求同存异、文以载道的人文精神和孝悌忠信、孝老爱亲的美德更是一脉相承。当代的文艺工作者,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中华文化既要坚持自己的根本,还要与时俱进”的理念,和诗以歌,以现代音乐对古典诗词进行艺术再造,力求激活古典诗词的生机和神韵,使古诗词的生命力再次扩张,促进诗词与音乐的进一步结合,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彰显中国古典诗词的美育功能。
一、诗乐一体:中国古典诗词的音韵美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诗歌就已经备受青睐,例如,《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古体诗”一般是指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以五言、七言、乐府诗为主。五言诗最初是在汉代以民谣的形式传播,现存最早并且最成熟的五言诗当属《古诗十九首》,虽无从考证是何人何时所作,但其情真意切、语言质朴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七言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柏梁台体”。三国时期曹丕的《燕歌行》是目前可考的文人创作的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到唐代,出现了讲究平仄相间、对仗工整的格律诗,这就是现在学术界公认的“近体诗”,它包括律诗和绝句。一般认为词滥觞于唐代,最初被称为“曲子词”,经过五代十国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在宋代迎来鼎盛时期。同时,后人根据古典诗歌体式也创作了不少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审美价值的诗词。例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依据“沁园春”词牌创作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开国元帅陈毅的《青松》等。这些作品虽是近现代人所写,依然可以算作古典诗词范畴。古典诗词的语言凝练且富有音乐美,同时也拥有跳跃性的言语结构,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从诗词产生开始,它注定和曲乐音调分不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诗词的诗乐一体,才在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这种传承与诗词的音韵美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押韵美、平仄美和复沓美。
(一)押韵美
诗歌离不开押韵,只不过各有不同。有些诗歌是每句押韵,如前文提到的《燕歌行》,整篇诗歌十六句,均押“ang”韵。还有的诗歌除个别首句入韵外,大多数都是隔句押韵。《广韵》是我国最早的讲究韵律的官修著作,可以视作中国古典诗歌诗韵的源头,后经王文郁的收集与整理,写成《平水新刊韵略》,书中列举的一百零六韵也被称为“平水韵”。近体诗的押韵,均以“平水韵”作为参考。每一首诗的韵脚都必须是“平水韵”中同一韵里的字,否则就叫“出韵”[2]。尽管“平水韵”在南宋时期才成体系,但它却能准确反映唐朝文人写诗用韵的基本准则,有着独具魅力的押韵美。例如,杜甫的《登高》用的就是一百零六韵中上平声的第十韵“灰韵”。上平声的“灰韵”一共包含八十七个字,其中二十个是“双韵字”(即两韵或两韵以上兼收的字)[3]。《登高》首句入韵,并且隔句押韵,诗人从“灰韵”中选取“哀”“回”“来”“台”“杯”为韵脚,韵脚规矩,音节工整,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带给读者美好的诵读体验,其中“台”字属于双韵字,在“灰韵”中读作tái,例如“将台”“拆台”“兄台”等;在上平声第四韵“支韵”读yí,意思是“我”,例如《尚书·汤誓》中的“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登高》无论是韵律还是沉郁顿挫的风格都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有“古今七律第一绝”的美称。
词韵和诗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在古代有着“诗庄词媚”之说。自隋唐萌生科举制以来,近体诗尤其是律诗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押韵有特定的规矩,端庄严格,而词只能算是作诗闲暇之余的产物,故而世俗妩媚。宋朝的词律一般都以当时盛行的语言为基准,也有人根据坊间词作或者当时盛行作品的用韵加以整理,但都不可考。今天所说的词韵,通常是指“吴中七子”戈载编写的《词林正韵》。《词林正韵》总共将词韵分为十九部,舒声(平上去)十四部,入声五部。例如,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和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采用平声韵,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和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用的是上声去声韵,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等用的都是入声韵。虽然词韵的规则不像诗韵那样严格,但丝毫不会遮掩词的美感。悠扬的古乐配上长短不一的歌词,曲词相得益彰,这也正是宋词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
(二)平仄美
除了押韵,字声的调配和抑扬顿挫也能增加美感。近体诗的平仄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复杂,其实只要注意诗歌“平仄相间”这一特点,就变得简单多了。一般来说,五言律诗共有四个句式:(1)仄仄平平仄;(2)平平仄仄平;(3)平平平仄仄;(4)仄仄仄平平。这四类是近体诗平仄变化的基本形式,四种句式的交替出现就形成了四种不同格式的律诗,绝句也同理,七言诗在前面加上相反的平仄即可。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的首句就是上述的第三种句式,但关于诗中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平仄,诗人做了一些改变。“竹”字本应处在“平”声的位置,但在古代是入声字,属于仄声;“莲”字本应处在“仄”声的位置,但它是平声。这是因为近体诗中有些地方不必刻意遵守平仄之律,这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意思是在近体诗中,七言诗第一、三、五个字,五言诗第一、三个字可以自由平仄,同理七言诗中第二、四、六个字,五言诗中的第二、四个字平仄必须严格分明。有了平仄的律动,读者自然而然会依据平仄有所停顿。朱光潜曾这样评价诗歌:“诗的本质之一是音乐性……诗是一种音乐,也是一种语言。音乐只有纯形式的节奏,没有语言的节奏,诗则兼而有之。”无论是朗诵还是吟唱,节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汉字有一个特征,一字一音节。在固定的字数中,各个音节组合成表意的结合体往往有停顿[4]。如白居易的《忆江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诗中“曾栽”“杨柳”“江南岸”“遥忆”“攀折”“何人”等表意组合之后形成停顿。再如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朱雀桥边”“野草花”“旧时”“王谢”“堂前燕”等处应停顿。在井然有序的节奏中,我们既能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音韵美,也能体悟作者的匠心独运。正是有了总体规律下的灵活变动,中国古典诗歌才能脱颖而出,给人舒适的审美体验。
词的平仄比诗歌的要求更加严格。词在创作之初是用来给歌姬们演唱的,但当时没有现代音乐技术作为支撑,于是产生了词牌。每一类词牌有着固定的格式,例如《念奴娇》《浪淘沙》《沁园春》《破阵子》《水调歌头》等都对词的字数、句数、平仄等有严格的要求。从平仄上看,词在某些地方的平仄上规定必平和必仄;从字数上看,词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都有平仄要求。例如,三字句的平仄一般用律诗后三字的平仄,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左牵黄,右擎苍”就属于“仄平平”;六字句的平仄一般用七言律诗的前六字的平仄;八字以上的句子平仄就是组合式,相当于律诗前三字的平仄加后五字的平仄。词还有表示停顿的“一字豆”,它区别于前文所提到的“一字句”。“一字豆”的“豆”相当于“逗”,它仅表示停顿,并不独立成句,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对”字主要起到领句的作用。词句与词句之间在平仄下相互交错,形成高低起伏,词的情感也会随着起伏的平仄流露出来,读者就自然而然地领略到了词作的意旨。
(三)复沓美
“复沓”语出《庄子·外篇·田子方》“适矢复沓,方矢复寓”,表示又一次射箭,后来用作修辞手法表示词句的反复吟唱。复沓是古典诗词外在形式的一大特征,“重章叠句”是《诗经》的一大特点,既加强了语气,又丰富了情感,做到了音意完美地结合。在古典诗词中复沓主要是指叠字、叠句。叠字,指的是诗词中单个字叠加,或语气表达需要,或作拟声意。如《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当初男女主人公相恋时,欢歌笑语,男子“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他还没到老年,心里就充满了怨恨。“晏晏”意为欢笑、和悦的样子,“旦旦”意为真诚、诚恳的样子。再如《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写出了飘坠的落叶声,“滚滚”极尽深秋江水之状,格调高亢,字字深入人心,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时间的永恒,一股秋气迎面而来,画面灵动自然。
叠句,指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形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例如《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芣苢”就是车前草,整篇仅换了几个动词,在回环往复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劳动的过程,传达出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给读者以欢快愉悦的体验。宋词中也不乏叠句佳作。例如,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两处叠句带动全诗,相互呼应,写年少之时无愁“强说愁”和深谙世故后愁情满怀却又故意避而不谈,读起来意味深长。
诗歌独特的音韵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主脉,正如席勒所说:“诗是蕴蓄于文学中的音乐,而音乐则是声音中的诗。”的确,诗词诗乐一体,既拥有凝练的语言文字,又有不可替代的音韵修饰,情感因此而忱挚,思想因此而深远。
二、和诗以歌:中国古典诗词的音乐化
中国古典诗词的音韵美为古典诗词的音乐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或者说,中国古典诗词诗乐一体的艺术特征为古典诗词音乐化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再创空间。诗词与音乐的有机融合,词与曲相互生发、激荡、烘托、渲染,其艺术效果会大大扩张和增强,不仅有美妙的听觉效果,更能具象地传达细腻深刻的思想情感。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到的“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就强调了“声”的效果。总体来说,古典诗词音乐化大致有两类:一是直接谱曲;二是艺术再造。
(一)直接谱曲
使用原版诗词,直接谱曲的不在少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四大名著相继被搬上电视荧幕,与此同时,老一辈的作曲家依据名著中的经典诗词,以名著主题特色为依托,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经典诗词歌曲。1987年版《红楼梦》总作曲王立平几乎一个人完成了《红楼梦》主要诗词的谱曲。电视剧中的音乐,王立平最先谱写的是《红楼梦序曲》和《枉凝眉》。这是两支旋律完全相同的乐曲,奠定了整部《红楼梦》的基调。《枉凝眉》是整部《红楼梦》的一条主线,呈现了宝黛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诗中“阆苑仙葩”指的是林黛玉,“美玉无瑕”指的是贾宝玉。全诗情感低沉惆怅,语气哀怨动人,适合忧愁婉转的曲调修饰。如果读者带着原有的感情储备,和着音乐再读《枉凝眉》,就能深刻体会到他们美好的爱情,但同时又感觉这爱情却如同镜花水月,无法成为现实。这是王立平呕心沥血的要旨,更是曹雪芹创作的初衷。除此之外,表达对处境焦虑不安和对生命迷茫的《葬花吟》、唱尽痴儿怨女相思之苦的《红豆曲》等,词美曲妙,美不胜收。曾被人诟病“女人无法为男人戏谱曲”的作曲家谷建芬别出心裁,为明朝学士许慎创作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谱曲,并用作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曲。此曲在歌唱家杨洪基的演唱下,豪放中渗透着含蓄,高亢中又蕴含着深沉,让听者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探寻历史的永恒价值,在对与错之间寻求生命哲学的深邃。还有苏越谱曲的《月满西楼》(歌词是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曲调哀转,写尽“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王龙作曲的《锦瑟》,诗乐合一,耐人寻味。
(二)艺术再造
进行艺术再造的诗词歌曲,同样不乏成功之作。例如,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高仲武评论张继的诗,“事理双切”而且“不雕而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1993年,一首《涛声依旧》传唱大江南北,由陈小奇作词、作曲,毛宁演唱,后来收录于专辑《请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歌词的灵感来自《枫桥夜泊》,陈小奇在符合诗歌“乡愁”基调的基础上,还增设了“情愁”。例如,歌曲副歌部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有原诗的客舟孤苦,也有爱情的欲见不能。陈小奇抓住了整首诗的诗眼“愁”,并结合自身经历展开合理的想象,使原诗的“乡愁”和新设的“情愁”完美交织一起,取得丰富的听觉效果。陈小奇深谙古音之道。“宫”“商”“角”“徵”“羽”是中国古乐中最常用的五个基本音阶,分别对应西方音乐唱名的“Do”“Re”“Mi”“Sol”“La”五音,缺少的“Fa”对应“变徵”,“Xi”对应“变宫”。阅读《涛声依旧》的简谱会发现,整首歌没有“Fa”和“Xi”,也就是说陈小奇完全按照古代音乐传统来谱曲,这样既能将古乐传统与古典诗词紧密结合,也能激发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被“天下称之”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李清照的传世之作,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短短三十三个字将人物对白和景色融为一处,充分显示了词人用词用句的深厚功底。这首小令借睡梦初醒后的询问,用自然清新的语言含蓄委婉地描摹了词人的内心世界,在字里行间也露出词人难平的苦闷。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歌《知否》正是将《如梦令》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重现词人倚窗观花的情景。歌曲《知否》的主歌是后人所写,副歌是原词,主歌以“一朝花开傍柳”开篇,与词中以景衬情之风不谋而合,主副歌的无缝衔接既表现了李清照的怜惜之情,又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
所谓雕缋满眼却似浑然天成,和诗以歌虽非天然形成但能引发出自然天成的感叹与审美效果,同时也令诗词更添华彩。人们在哼唱之余,自然而然会受其审美格调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进万家的法门之一。
三、入境融情沁心:中国古典诗词音乐化的美育功能
(一)美育界说
1.中外的美学历程
有人认为美是个体对事物所产生的“感觉”,这就牵扯到美学的内涵问题。探讨美学内涵,就不得不追溯中外的美学历程。在18世纪的欧洲,人们思考美的现象并积极探索“美本身”,于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建立起来。在此期间,鲍姆嘉通提出的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的观点[5]3,极其具有代表性。但美学集大成者应属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依托并超越了鲍姆嘉通的观点,将个体的认知、意志、情感与哲学上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分鼎立。由此,美学走入哲学体系,成为哲学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当代西方美学主要有费希纳提出的心理学经验美学和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转向。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美学逐渐摒弃形式主义的审美,注重以“实践”为中心的审美。
在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里,也蕴含着“美”的意蕴。老子曾将美归属为“道”“气”“象”,并辅以“秒”“玄鉴”“味”等。但是中国古代对美的论述大多零散或繁杂,往往与当时统治阶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流传于世的专著极少。中国古典美学大多孕育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儒家的礼仪思想、释家理性的意识结构、道家超然物外的生活原则都为中国古典美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倡导美学的先驱当属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他们的美学理论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学认识广度都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现代中国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呈现多元化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个体可以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自由的发展。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美仅仅是个体对事物所产生的“感觉”,而是基于实践的现实视野来获取审美,这点和现当代西方的审美理念不谋而合。纵观中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众多学者都越来越认为美不是独立在外的客观实在,也不是纯粹意愿上的“主观”,而是依托实体物象的精神和谐[6],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因此,这对古典诗词音乐化的美育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美育的内涵
从中外美学历程中萃取的美的内涵打破了美是“感觉”的论断,基于此再探究美育的内涵,对研究古典诗词音乐化的美育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借鉴意义。优美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实现,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和谐统一,是纯粹的美[5]222。纵观中国历史,最早注重美育要追溯到孔子,《论语·泰伯篇》中提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的品德修养应该从学习《诗》开始,接着把礼作为修身立命的根基,最后大成于音乐。由此可见,诗、礼、乐在孔子看来是衡量人一生的法度,把艺术教育看作道德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恰恰也是美育的重要途径。西方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是英国哲学家席勒,他在《美育书简》中谈到只有通过美育教化众人,才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才能消除社会矛盾。他虽然过分夸大了美育的作用,但他主张通过艺术感染力,净化人类心灵,引导人们对美的感悟,指导人们积极向上,从而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思想,这即便对当下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近代史上,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受席勒理论的影响开始关注美育在中国教育中的作用。王国维认为教育应该对学生“心育”,心育包含德、智、美三个方面。蔡元培曾经对美育做了解释:“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7]蔡元培在这句话中明确了美育的目的以及价值,点明了美育是区别于显性知识的情感熏陶。如同顾明远所说的那样,美育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程度上的审美技能,并由此衍生出一定的审美能力,从而美化心灵、语态、形态等[8]。所以,我们在谈论美育的时候,不应只狭隘地认为美育就是认识美的事物,拥有美的感悟。美育范围广泛、意蕴丰富,它以人类思维和心理活动为载体,呈现出社会美和艺术美,反过来又通过社会美和艺术美来影响社会个体,引导人们积极向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民族乃至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育的内涵是丰富的,外显出来的形式更是多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音乐都是该时代备受追捧的音乐形式,为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对古典诗词的再创作无疑是美育的重要载体。所谓诗词育美、诗性化美、诗化人生[9],通过诗词音乐化的美育,我们可以获得积极向上的美学趣味和充满活力的精神追求。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化节目登上电视媒体。《经典咏流传》是继《中国诗词大会》之后,将中国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央视首档原创音乐文化节目,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古典诗词以全新的生命力。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创造出的艺术作品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读出,它明确要求艺术作品能够培养、塑造出有审美能力素养的大众[10]。自2018年《经典咏流传》第一季播出以来,深受社会各个年龄层次群体喜爱,大众的审美素养也因此逐渐得到提高。事实上,古代诗词不经人们口口相传,何来今天的经典诗词。《经典咏流传》之所以赢得各年龄层次的听众喜爱,就是因为听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体味到了诗词意境,感悟到了诗词情感,并能从中涵养心灵,熏陶心智。这是古典诗词音乐化的强大美育功能所在。
(二)美育功能
1.体现诗词意境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不论哪种诗词,它都有与众不同的意境。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11]216《康熙字典》中也谈到意为“志之发也”。作者如若胸中无“志”,写下的诗词也无所谓“意”了,换言之,从作者的诗词中能反观其志。许慎认为“境,疆也,从土竟声”[11]291,“境”的本意是指边境、疆土,用在这里则引申为程度、地步。由此可见,“意境”就是作者“志”的程度。在诗词当中“意境美”是必不可少的审美范畴,作者往往将自己无限的心志融入有限的诗词中,等待读者的挖掘与体味。王国维也指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2]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借助想象,将自己内心所思所想徘徊于天上人间,“苏词一出,中秋之词尽废”的说法也源于此。词人同时集抽象与具象于一词,勾勒出一种明月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经典咏流传》(后文歌曲不再说明)第一季第八期,王佩瑜演唱的《但愿人长久》,配合现代科技,将诗人中秋望月的意境描绘得清新如画。哪怕科技特别发达,能重塑诗人创作的那个夜晚,没有音乐的陪衬,总会少些情韵。词的境界取决于高尚伟大之人格与深邃渺远之感情,因此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歌一定是经典的,境界也一定是高的。学生在体味诗歌意境的同时,诗歌内隐的境界也会浸染着学生。诗乐的意境审美功能就在于能将学生的想象力调动起来,萦绕在诗词周围,同时也帮助学生对诗词进行确切解读。音乐使诗词获得艺术升华,而学生的境界也随之得到升华,审美情趣也得到了提升。美育在内核上可以理解为教人建设、体验和领会充满意蕴的意象世界的教育[13]。雷佳在第二季第二期演唱的《蒹葭》,诗歌出自《诗经·秦风》,全诗景中有情,给人一种凄迷朦胧的美。“伊人”这一意象充满意蕴,她可以是心上人,还可以是你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种美感中,人们往往会进入“无我”之境,深受美的熏陶。令人寻味的还有诗人开创的“在水一方”这一具有普遍意义但又充满朦胧诗意的艺术意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是古代文人从小吟诵的诗歌总集,于是歌曲创造性地加入童声合唱,体现出“古风童韵”,焕发出独特的青春光彩。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伊人”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美的向往,孩子们也会受这种意境的影响,朝着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前进,这也是诗词音乐化美育的初衷。
2.感受诗词情感美,增加学生的思想高度
有的诗词注重意境的渲染,有的诗词却以情动人。董仲舒认为:“情者,人之欲也。”由此可见,古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其实就是自己的欲望。他们心中有了渴望并将渴望描绘出来,就形成了诗词。诗词是一种语言艺术,作者将自己主观的情感附着在客观的语言文字上,当学生通过文字与作者情感互通,就能感受诗词中的情感美。音乐则能通过旋律影响学生,用听觉沟通作者和学生,此时,学生会在舒适的审美感受中丰富精神世界并领略到诗词的情感美。孟庭苇在第一季第九期演唱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可谓曲尽意不尽。李煜的《虞美人》是典型借物寄情的作品,身为一国之君,面对家国破碎,词人心中始终对故国有一个心结,同时感慨往事消逝,可谓字字珠玑、含血带泪。孟庭苇用她婉转朴实的歌声带领学生贴近词人满腹愁绪、潸然落泪的情绪,感受词人积蓄于胸的悔恨哀愁。在词作和旋律的配合下,学生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李煜产生同情,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家国情怀,从而升华了自我的思想。第五季第二期胡夏演唱的《苏幕遮·怀旧》重启了范仲淹羁旅乡思之情。这首词以沉郁刚劲之笔力抒写低沉宛转的哀思,意境宏远。整首歌曲风悠扬,符合婉约派风格,胡夏的演唱仿佛就是词人自己的诉说,歌曲将美景和柔情交织在一起,带给学生视听冲击感。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物皆动我之情怀”,词人心中的忧思融入眼前的秋景,配合缠绵细腻的音乐,顺着词曲作者的指引,学生自然而然感受笼罩全词的深挚之情。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学生就会生成自己特有的思想情感,对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也将有不一样的认识。
人人都拥有情感,古代先贤将他们的情感注入文字中,为学生感同身受提供了有利载体。就像蔡元培所认为的,人类的感情有薄厚之分,由薄到厚就需要陶养。蔡元培对感情的理解十分独特,以感情的强与弱、厚与薄为价值尺度,在这一价值尺度下,借助一定的形式来陶养,感情的强和厚会生成“高尚”的价值结果[14]。诗词音乐化就是陶养的有利形式,借助诗词文本这一载体,配上音律,学生就会从诗词以及音乐中提升自我的思想高度。当学生的思想与社会达到和谐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关爱身边的人,不论是细小的关心还是博大的关爱,都会在令他人获得美感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修为,做出平凡而又高尚的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因此构建。
3.启迪听者心灵美,引领学生的价值观
“乐”是古代“六艺”之一,乐教就是“修内”,涵养情志,陶冶情操,诗词音乐化美育功能的最终目的就是美化人们心灵,体会古人价值取向。如第一季第三期的《将进酒》,诗歌是忧愁的,“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时光飞逝只有想做宰相的李白才能抒发出来;诗歌又是豪放的,所以诗人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凤凰传奇的演唱有抒情也有激情,康震教授评价这首歌为“凤凰涅槃”。欣赏这首歌,学生能借音符领会诗人潇洒豪迈的情怀,体味古人的奔放洒脱,这对今天青少年的价值引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季第一期屠洪刚演唱的《大风歌》,意境开阔豪放,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刘邦平叛归来的理性思考。刘邦渴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千秋伟业,渴望寻觅英雄来守护大汉王朝,这是作为王者对家国兴亡的担忧。歌曲极大地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有利于唤醒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谭咏麟在同期演唱的《定风波》,主歌部分是对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艺术再造,“放下千斤重”“纵有失去不怨命”道尽苏轼一生的沉浮,紧接原词,词中旷达倔强的情怀展现了出来。更令人动容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时候运用衬词“哈哈”,尽显苏轼凡人难以步趋的潇洒和从容,足见曲作者和演唱者的用心良苦。透过这首歌曲我们感受到的是苏轼虽身处逆境屡遭贬谪却不颓丧的性格,苏轼是文化领域的英雄,谭咏麟将词人“不坠青云之志”的一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这一切都启迪学生要认识到寒冷中有暖阳,困境中有希望,低靡中有喜悦,对学生的价值观起到了引领作用。类似题材还有平安演唱的《沁园春·长沙》,展现出少年毛泽东雄视天下的凌云壮志,词曲之间回荡着刚强坚毅、凛然浩荡之气,传达出奋发向上的青春激情。这些都将对当代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激励人们弘扬向上向善的中华优秀人文精神。前文提到的作曲家谷建芬,致力于美育事业,古稀之年还坚持为中小学课本上的一些诗词谱曲,至今已谱写了《游子吟》《七步诗》《敕勒歌》《春晓》等50多首好学、好唱、好听的经典儿歌,并在全国大多数中小学校园里传唱,体现了自信自强的劲健风格特质[15]。
王国维十分看重理想人格的指引,他认为这种人格可以超越个人利益的界限,从而通往自由之路。在王国维的美育理念中,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作家超越了政治地位,他们代表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是洞察世界本相、忧念苍生的启蒙者,是指导国民拔除卑劣之嗜好、过上高尚纯粹生活的领路人[16]。古典诗词音乐化最终的目的就是“化育”,启迪心智,端正价值观。最终,青年一代必将跟随领路人,走向通往理想人格的康庄大道。
当然,并不是说诗词音乐化的美育功能一定要泾渭分明,因为在欣赏的同时,学生的审美会被诗词音乐熏陶,通过欣赏诗词音乐进入意境,在意境中寻找情感共鸣,最终心灵受到触动,价值观得到升华,这是多方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往往三者交织之处正是心领神会之时。柏拉图认为,要防止年轻人受到“罪恶、放荡、卑鄙和肮脏”的不良影响,就必须“找一位能工巧匠把大自然的美丽表现出来,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养成一种对美的热爱,养成一种把美融入灵魂的习惯”[17]。最好的美育手段就是诗词音乐化,它能滋养心灵,让人格趋向完美,性格变得高尚优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5]250。2017年,美育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经典咏流传》等诗词音乐文化节目应进一步被重视起来,利用起来。
四、结 语
诗乐的怡情教化功能历来备受重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足见诗词音乐化在美育中的地位。礼能“制其宜”,而乐能“导其和”,所以诗、礼、乐指导我们的言行举止,净化我们的心灵。“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荀子认为音乐能使人快乐,是人类情感必不可少的,音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如果能充分利用好音乐,就能将人“引于好善”。古典诗词诗乐一体的音韵美是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它的押韵美、平仄美和复沓美为古典诗词的音乐化提供了巨大的审美再造空间,由此,古典诗词的美育功能因为音乐元素的有机融入而大大提升。庄子说:“美成在久。”古典诗词音乐化的美育势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应是始终向上、向善的。中国古典诗词借助音乐这一表现形式,走进千万读者心中,这背后彰显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