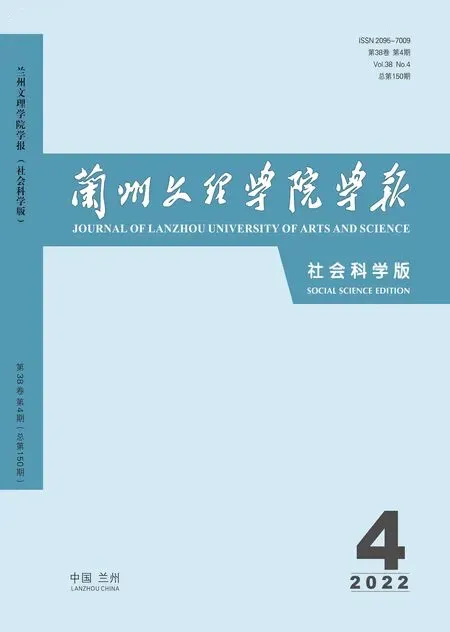从《长安十二时辰》看唐代多元对等的文化格局
——否定主义文化哲学实践
焦 旸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改编自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同名影视剧用浓烈华丽的视听语言、充满张力的叙事节奏、高度还原的历史细节在2019年暑期引起了收视狂潮,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这个发生在天宝年间有关长安的故事,不仅向观众传递了盛唐气象的恢弘壮观,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于唐风古韵的强烈向往,甚至令人想要去西安一探究竟,在昔日的唐都想象当年的长安一百零八坊。
无可置疑,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也最为自信的朝代之一。唐人没有受制于充满了天人崇拜的汉代经学,全面接收新兴的事物,充分发展自我的观点。这样务实而自由的氛围使得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众多突破性与开创性的成就。唐代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富裕以及中外交通的发达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但归结起来,唐王朝“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格局,更是为唐代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多元”“对等”“互动”的概念取自于国内学者吴炫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所谓“多元”是指多种多样不同类别的文化观念与体系;所谓“对等”则是世界观之间的对等,即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放弃由某种文化观念统治、同化人类的企图,进而形成一个多元对等的平衡、和谐的世界;所谓“互动”可以表述为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是借他者文化的思想材料进行符合自己文化性质的改造工作,其目的是再创造自己的文化思想,而不是被他者文化所改变。“多元”“对等”“互动”的思维模式与唐代总体的文化格局有着高度的契合,而《长安十二时辰》这一文本又从文学和影视创作的双重视角为之提供相应的佐证。下面,本文将从华夷并举:唐与外来文化的多元对等;三教并重:儒道释的多元对等;男女平等:封建王朝的性别多元对等三个角度出发,以《长安十二时辰》为基点扩散开来,对唐代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格局进行相应的论证。
一、华夷并举:唐与外来文化的多元对等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多是以中原为中心或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传统文化,这一文化多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统称为“夷狄”“蕃胡”,强调华夷之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类观念更尽显对外来文化的蔑视、排斥态度。但唐代却独树一帜,为各类外来文化敞开了大门。武德五年,唐高祖在给高丽王武建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柔怀万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唐太宗更是发出“自古帝王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的感叹。唐高宗继承了这种政策精神,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周边各国力主实行“抚育”和“柔服”。处于极盛时期的玄宗皇帝更是气势恢宏地宣布要“开怀纳戎,张袖延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言:“历史上,唐代却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2]据统计,仅在长安就有八千余名外国留学生,近万家流寓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以及成千上万的波斯、阿拉伯、欧洲商人。这些外国人不仅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在朝廷做官,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他们从世界各地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给传统的华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史称,唐代“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洛阳也是“家家学胡乐”。这类局面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唐王朝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开放型政策,对“多元”文化更是抱有一视同仁的友好态度。
当然,唐代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常依据自身需要取舍。在唐代中外文化汇聚的过程中,组成唐王朝的各个民族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既不是因其为异己文化而排斥,也不是漫无选择地一律吸收,而是在“对等”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社会的层序结构、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文化水平,分别对外来文化作出遴选和抉择。以宗教为例,唐代佛教的发展没有照搬印度,而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不同的宗派类型。而在这些宗派中,禅宗的中国化又最为典型:它一改天竺佛教繁琐、难解的缺陷,突出了简单易懂的特点。禅宗的宗旨概括起来只四个字“净心自悟”,即只要抛掉一切妄念和杂念,认识到佛在自己心中,就可以顿悟成佛。不仅如此,唐王朝还善于吸收借鉴各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之形成良性的“互动”,来滋养、补充、发展自己的文化。如在音乐方面,传入中国的“胡部新声”到玄宗时已渗透到唐的大曲当中。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和胡乐交融的杰作,《秦王破阵乐》也是在唐代清乐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音乐成份而形成的。唐代的舞蹈融合了西域地区诸国的特色:如当时流行的剑器舞、胡旋舞等都来自于异域。在绘画方面,当时用色彩深浅晕染来表现物体立体感的凹凸法来自印度,被称为“ 天竺法”。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里显然也揉进了异国情调。在科技方面,僧一行撰修的《大衍历》在不少地方采用了印度《九执历》的成果,波斯人李殉撰《海药本草》记载了124种外来新药,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以还原历史见长的《长安十二时辰》中,故事就发生在大唐天宝三载的长安城,适逢上元灯会,圣人诏令:“汝等无论来自何方何国……十二时辰内,皆可于坊间自由来往”,这一时间地点的选择为紧凑惊险的情节发展提供条件的同时,更是显露出唐王朝“柔怀万国”的气派。为了确保圣人(历史原型为“唐玄宗”)于花萼相辉楼招待各国使节的宴席顺利进行,扬我大唐国威,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统摄长安城贼事策防的靖安司司丞李必(历史原型为“李泌”)强强联手,十二时辰内解除“狼卫”所造成的危机。在小说和影视剧的文本中,不仅宴请各国来使的情节刻画是重中之重,在对长安城风俗人情的塑造过程中更是处处体现着像是“回民坊”“祆祠”“景寺”这类充满异域风情的地点和突厥人、粟特商、波斯僧、昆仑奴、胡旋舞、胡饼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元素……诸如此类的描写杂糅在紧凑的故事情节之中,共同铸就一个华夷并举、鲜活立体而又符合历史原貌的长安城。
二、三教并重:儒道释的多元对等
唐代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体现在外交上是华夷并举,体现在宗教思想上则是三教并重。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书中,作者郭建龙提出:“儒教、佛教、道教共同繁荣,是唐代哲学的最大特征”[3],又表示在这其中“佛教给了唐代思辨的武器,道教给了人们想象力,儒教则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稳定性”。唐代文化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两汉与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化成果,实现了儒道释三教的多元对等。就儒教而言,唐王朝的统治者追随汉代“尊儒”的传统,肯定儒教在维系政治结构上所发挥出的功效,但又敏锐地意识到仅在儒教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治国人才的局限。于是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上采取多样化的标准,除传统的考察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外,设立更为灵活且贴近现实的“进士科”。在明经、进士这两大学位之外,还有专供有专长之人考取的学位,如秀才科、明法科、书学科、算学科等,分别为皇帝提供文学、法律、书法和数学方面的人才。唐代通过多元化的考试机制,为学子们提供了多条路径接近中央政府,避免了人才的单一化。在“多元”科举制度的冲击下,儒教的地位自然下降,虽然表面上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被弱化,与道教和佛教三足鼎立。
在对待道教和佛教的关系时,唐代是具有特殊性的。由于唐代皇帝把李姓追溯到了老子,道教也因此受到了优待。在高祖时期,三教的次序是老先,次孔,末释。甚至在科举中也纳入了道教的科目,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出身。这一特殊性自然也体现在了《长安十二时辰》中,在推动故事情节上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太上玄元巨灯”,就源自《旧唐书·高宗纪下》所记载的“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唐高宗追尊“老子”称号的历史典故。不言而喻,这座“用去了永州一年赋税,修造了一年之久”的太上玄元巨灯当然是用老子的形象所筑成的。由这一细节可见,道教在唐代确实有着崇高的地位。当然,唐代统治者对于其他的宗教也并不排斥,而是采取了兼收并蓄、三教并举的态度。对待从印度传来的佛教,除去唐武宗时期外,始终是予以大力扶持的,也因此才能产生以禅宗为代表的本土化宗派类型。三教的“多元”“对等”使唐代的思想文化得以自由发展,唐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得以自由地驰骋,儒道释三教“互渗”“互动”共同造就魅力无穷的唐代文化格局。
《长安十二时辰》的两位主角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唐代“三教并举”的多元文化特征:作为主角之一靖安司司丞李必可以说就是一位体现着儒道合流、“多元”“对等”的人物形象。他出场亮相时的描写如下:“少年人脸圆而小,青涩之气尚未褪尽,眉宇之间却隐隐已有了三道浅纹,显然是思虑过甚。他穿一袭窄袖绿袍,腰间挂着一枚银鱼袋,手里却拿着一把道家的拂尘”[4],尽显道家出尘脱俗、飘飘欲仙的气质。影视剧里的李必更是头戴莲花冠、竖插子午簪、身着道袍、手捧拂尘,一副标准的道士形象。这样一位仙风道骨的少年为何会眉头紧蹙、思虑过甚呢?只因他一心帮太子出谋划策,更想做宰相守天下百姓,身怀“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的理想,大发“上天生我钟鼎之家,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智福佑大唐百姓”[4]的感慨。从李必这个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出儒道文化合流后所造就的治国理世之才的形象,而在另一位主角张小敬的身上,性格特点则更加复杂和立体。张小敬本是长安城万年县负责辑事捕盗的不良帅,人称为达目的、不讲规矩的“五尊阎罗”,实际上却是一位重情重义、为守长安百姓九死无悔的好汉。因帮自己在安西铁骑第八团的旧友打抱不平失手杀死上司而被捕入狱,兼获死罪。李必称他“熟知长安明暗黑白的规矩、通三教九流、懂多方语言、胜心重、有牵挂、想活”[4],可以说是极为贴切的描述。只有这样一个一心向着长安百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英雄人物,才能在危机关头救长安城于水火之中。张小敬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主角形象、英雄形象,但从这个具有多面性格特点的圆形人物身上,我们更能体会得到儒道释三种宗教思想“多元”“对等”“互动”后对大唐普通百姓所渗透出的影响。
三、男女平等:封建王朝的性别多元对等
在古代封建宗法制的等级社会中,卑幼的子女毫无人身自由权可言,处处受制于家长的管束。女子所受的限制则更多,甚至连独自外出的机会也被剥夺。即便有事出门,也必须“拥蔽其面”,严重束缚了女性的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然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唐代毕竟不同于其他更为封闭保守的封建王朝。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开放、礼法约束减弱,在室女子无论高门宦女还是普通的民间女子,均能在不大受约束的情况下,于一些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5]《集异记》补编中则记载了盛唐时洛阳士女于元霄节出外观灯的情景: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杖于上阳宫,时华灯齐放,“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闻,士女纷委”[5]。这是节日里士女们外出游玩观光的记载。《长安十二时辰》中也不乏对上元佳节女子外出赏灯场景的描绘。唐代的女子不仅可以外出,参与社会交往,甚至在受教育方面也享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虽不能像同辈男子一样上学读书,但却拥有在家中习文读书的权利。如德宗时,女学士、尚宫宋氏五姐妹,幼“皆聪惠”,其父宋庭芬“教以经艺”,并“课为诗赋”[5]。故五女“年未及笄,皆能属文”[5]。还有牛应贞,这位生长于民间的官宦女子,十三岁便能“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5],此后又“学穷三教”“著文章百余首”[5]。这些例子皆反映出唐代女子,特别是出身于儒门世家的女子受教育的普遍性。
以铁腕手段驾驭群臣的女皇武则天,更是凭一己之力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发起挑战,曾设立多项法令以提高妇女地位。如上元元年,在《建言十二事》里提出改变过去为父服丧三年,而父在只为母只服丧一年的传统制度,提议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使得在服丧方面,父母的地位平等。垂拱四年,武则天为祭祀祖先而修建的明堂,更是“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6],让包括妇人在内的所有百姓进入参观。在武则天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下,她的思想行为,都对自古以来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儒家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予以空前的打击,使得男女的地位相较其他的封建王朝而言更加平等,成为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中极具特殊性的一个章节。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檀棋、王韫秀、闻染、鱼肠、许鹤子等一众女性形象,也都塑造得“巾帼不让须眉”,鲜活立体且极富个性。拿檀棋来说,作为李必的贴身侍女,她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主人的饮食起居,更是身手矫健、头脑灵活、有勇有谋,关键时刻救张小敬和李必于危难之际,甚至愿意为了保长安城的周全而牺牲自己。王韫秀作为王宗汜大将军(历史原型为“王忠嗣”)的千金,虽娇蛮任性,但关键时刻也懂得审时度势,能领兵抗敌。鱼肠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反派刺客,但却有情有义,为了回报恩人才卷入这场毁灭长安的不归路当中,至死无悔……《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每一位女性角色,都是有血有肉,使人记忆深刻、过目不忘的女英雄、女豪杰,共同体现着唐代在性别的“多元”“对等”上所显现出的宽容态度。
四、结语
在《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里,当主角张小敬被问及为什么尽心竭力为靖安司办事时,少言寡语的他罕见地说出这样一段话:“你曾在谷雨前后登上过大雁塔顶吗?那里有一个看塔的小沙弥,你给他半吊钱,就能偷偷攀到塔顶,看尽长安的牡丹。升道坊里有一个专做毕罗饼的回鹘老头,他选的芝麻粒很大,事先翻炒一次,所以饼刚出炉时味道极香。还有普济寺的雕胡饭,初一十五才能吃到,和尚们偷偷加了荤油,口感可真不错。东市的阿罗约是个驯骆驼的好手,他的梦想是在安邑坊置个产业,娶妻生子,扎根在长安。长兴坊里住着一个姓薛的太常乐工,庐陵人,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必去天津桥上吹笛子,我替他遮过好几次犯夜禁的事。还有一个住在崇仁坊的舞姬,叫李十二,雄心勃勃想比肩当年公孙大娘,她练舞跳得脚跟磨烂,不得不用红绸裹住。盂兰盆节放河灯时,满河皆是烛光,如果你沿着龙首渠走,会看到一个瞎眼阿婆沿渠叫卖折好的纸船,说是为她孙女攒副铜簪,可我知道,她的孙女早就病死了……我想要保护的,是这样的长安,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继续过习以为常的生活。”[4]
唐代“多元”“对等”的文化格局,它有别于历史上各个 “独尊儒术”或是“儒道统一”的主导性文化,是更加尊重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别,更加尊重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下,才会产生如张小敬这般爱着长安、守着长安,虽九死一生,也无怨无悔的小人物。正如国内学者吴炫在《多元对等互动:基于文化创造的阴阳八卦》一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学者的儒家化依附性思维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窄化”,“由于我们受《易经》《易传》的‘强’‘弱’思维制约,会把儒道文化的现实政治性之‘强’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认知,也会把殷商、先秦、唐宋为代表的尊重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非主导性文化当作现实的‘弱文化’去对待,从而忽略了这种文化与秦、汉、明、清为代表的轻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主导性文化一直处在互动消长的历史运动中”[7]。我们不能片面地把儒家文化或是儒道文化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从《长安十二时辰》中所体现出的尊重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唐代多元对等的文化格局,无疑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例证。